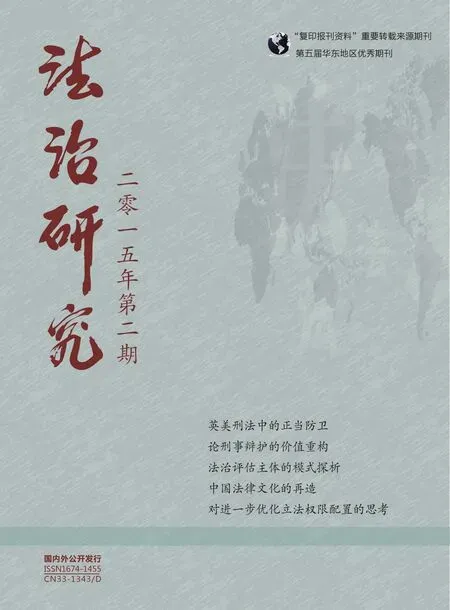生与死的距离
——论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法律缺陷与改革
陈妍茹
2014年12月15日,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案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给了我们一个深刻反思的机会。死刑冤案是当事人及其家属的巨大悲剧,也是国家司法乃至法治实践的惨痛教训。任何国家都无法避免错误判决的发生,施行死刑的任何司法错误都是无法逆转和补救的,无辜者枉死的代价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的重压。通过分析查找现行法律的漏洞,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并建立死刑冤案的有效防范机制,将是我们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推进依法治国精神、实现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步骤。
在我国目前废除死刑还无法实现的前提下,学界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重点已经转向如何切实推进限制死刑的目标。笔者认为,改革死刑立即执行判决的交付执行时间及其相关规定,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限制、控制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适当延长交付执行的时间,能够给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必要的救济时间,保障司法机关实施纠错所需的程序推进期间,是贯彻现代法治崇尚程序正义的理念,主动预防冤假错案发生的有效机制。
一、我国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立法理念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交付执行。
为什么法律规定必须在7日内交付执行?传统理论认为,死刑快速交付执行能维护司法机关裁判的尊严,满足社会正义的要求,预防新的犯罪发生。国内外大量的死刑研究表明,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具备有效的一般预防作用。“死刑存续的两个支撑点都存在疑问,死刑能遏制犯罪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至于用死刑来满足民众的报复心,则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它符合文明时代人类的理性。”1贾宇:《死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所以,强调死刑报应功能和威慑力早已不被当代刑法所赞同。
人类对刑罚目的的认识已经实现了理性的飞跃,从原始社会同态复仇的报应主义转为了现代社会倡导的教育刑理念。菲利说,“在人类处于最野蛮的状态下流行只有惩罚规定而没有关于矫正罪犯规定的刑法典。人类文明的逐渐进步将导致与此相反的只有矫正而没有惩罚的观念”2[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就整个世界的刑罚演进史来看,是一个从生命刑发展到身体刑再到自由刑为中心的运动轨迹。刑罚从单纯地强调惩罚性和严厉性转变为倡导教育性、谦抑性、人道性等。随着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教育因素在刑罚属性中的地位加强,正是刑罚进化的必然结果。它通过对犯罪的谴责,使犯罪分子认罪伏法,在思想上受到深刻的教育。现代刑罚如果缺乏教育性,将不成其为刑罚。死刑恰恰是报应主义的典型体现,在满足人类最朴素正义诉求的同时,践踏了人类的身体权和生命权,也剥夺了犯罪人得到教育改造的机会。
还有观点认为:“对死刑的执行时间作出如此规定的目的,既是为了消除罪犯因长时间的静等而造成的精神上的痛苦,减少死刑执行上的不人道因素,也是为了避免罪犯利用死刑执行前较长的时间间隙而采取逃跑、自杀等行动,可以使罪犯不再危害社会或者防止罪犯因死亡而无法执行。”③袁帅锋:《死刑执行时间的古今比较与反思》,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4期。这种说法同样很难成立,始终处于严格羁押和监控状态下的死刑犯,再去危害社会或逃跑、自杀的几率也很低。快速执行死刑让很多罪犯临死前来不及见家人最后一面,带着无尽的遗憾和对人世的眷恋悲凉离去,难道是人道的吗?与其去比较迅速行刑和长期等待行刑给罪犯造成的精神痛苦,不如去考察哪一种执行程序更利于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利于实现公平正义。那么,死刑执行程序中应该树立怎样的立法理念?首先,死刑执行程序应该树立生命权至上、尊重生命的价值观。“当出现生命价值与其他价值相冲突的情形时,为实现公平正义的要求,我们理应优先保护生命权的价值。”④韩大元:《死刑冤错案的宪法控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法治国家应把尊重生命权的价值、树立生命权至上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基本共识。正如波普尔倡导的致力于最少数人的最小的不幸的减少一样,杀得快必须建立在杀得对的基础上。如果杀错了,即使只涉及到最少数的人,也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极大损害。死刑立即执行的现行立法导致死刑案件被告人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快速交付执行死刑,没有给予死刑案件的被告人程序上必要且充分的救济时间,也没有保障司法机关发现错误后实施纠错的必要期间。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众多冤假错案发生后人们最痛心和最遗憾的就是冤者已逝,假如他们没有被仓促执行死刑,假如他们有机会进行申诉获得救济,结果可能完全不同。
其次,死刑执行程序应当树立实现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的立法理念。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从刑事司法公正的层级来看,可以将其分为充分的司法公正和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所谓充分的司法公正,是指刑事犯罪不仅被揭露、证实,而且刑事司法的过程和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要求;最低限度的司法公正是指从刑事司法的结果来讲未冤枉无辜,从程序上来看保障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⑤王敏远:《完善司法公正的体制性基础——以刑事司法为视角的分析》,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11期。现代刑事诉讼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很难实现高层次的充分的司法公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述道:“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公正”,这表明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要实现司法公正是非常困难的,但通过不懈地努力去实现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和追求。
死刑执行程序作为死刑案件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确保死刑判决正当性和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合法诉讼权益的重要环节,其程序设置应当以实现和保障司法公正为风向标,然而,有缺陷的制度就会影响司法的公平正义。法律制度是司法公平正义的保证,制度的最大效用也在于保障公平正义,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和保障司法公正。
二、我国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法律缺陷
我国死刑执行程序除停止和暂停执行的两种死刑变更情形之外,没有赦免或减刑等其它可诉诸的救济渠道和程序设置。罪犯在死刑判决核准之前,还抱有强烈的求生欲望,而在核准之后,从签发执行令到执行死刑最长只有7日,进行纠错和寻求救济的机会十分渺茫。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进行修改后,立法理念和很多具体内容都有非常大的变化,更注重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的公平公正,但是对于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的时间没有修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快速执行死刑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和缺陷,与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程序存在一定冲突和矛盾,必须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交付执行时间短暂,违背国际公约倡导限制死刑、保障生命权的理念
国际社会在推动和倡导废除死刑的同时,为尚未废止死刑的国家限制死刑适用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标准,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其中,生命权是联合国国际公约死刑国际标准的根据。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生命权的措施缺失或不完善,都是违反公约义务的表现。联合国有关死刑的国际公约及决议,均督促各成员国遵守死刑执行的最低标准,保证为死刑案件中的被告提供最细致的法律程序和最大可能的保障。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权利国际公约》)要求各成员国必须为面临死刑的被告提供最低的保障。1984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保证面临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以下简称《保障措施》)则进一步要求为死刑被告人的程序权利提供更多、更严格的保障。
《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以大赦、特赦或减刑。”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载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0/content_698226.htm,2014年12月29日访问。《保障措施》第6条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均有权向较高级的法院上诉,并采取措施,确保上诉得以提出。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都有权寻求赦免或减刑。在任何上诉或采取其他申诉程序或与赦免或减刑有关的其他程序期间,不得执行死刑。”⑦王水明、景卿:《联合国国际公约与死刑国际标准》,载《人民论坛》2013年第5期。我国政府于1998年10月5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了 《权利国际公约》,并多次承诺会尽快实施该公约,因此,国际公约确立的相关标准是我们在法律制定和修改时需要参照和考虑的。
死刑是剥夺生命权的刑罚方式,一旦执行将无法逆转和补救。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布伦南所言“或许死刑最让人感到恐惧之处,不仅在于其适用过程中存在的歧视或恣意,更在于某些情况下无辜者也可能被处死”⑧W.Brennan,Jr.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8 Notre Dame J.of Law.Ethics&Public Policy,1994(1).。最大限度地对其加以防范是所有保留死刑国家面临的共同课题。国外立法也大多规定,只有当死刑案件被告人用尽全部救济之后,法院仍然维持死刑判决的,才能交付执行。重要的是,在被告人寻求救济或申诉期间不能执行死刑。在美国,被判死刑者可以获得多重救济,可以直接上诉;可以要求州法院重新审查;可以申请联邦人身保护令、赦免和减刑。有学者认为美国刑事被告最多有九次寻求救济的机会。⑨陈永生:《死刑与误判——以美国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载《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通过这些较为充分的救济,“不仅强化了死刑案件被告人的权利保护,也有效地限制了司法适用,尤其是大大降低了死刑的误判与错杀率”。⑩李奋飞:《美国死刑冤案证据剖析及其启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我国死刑执行的法律规定没有达到国际公约要求的最低标准,也缺乏类似国外立法针对死刑被告人的充分救济手段和渠道。死刑案件在经最高人民法院死刑复核之后,死刑案件被告人不能再提出上诉或重审要求,也没有申请赦免及减刑的程序,可采取的唯一措施只有申诉,但提出申诉期间不能停止死刑裁判的执行。《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由于申诉需要经过审判机关审查,符合条件的才能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而死刑交付执行的时间最长只有7天,致使实践中死刑案件被告人空有申诉的权利却几乎无法获得再审的机会。可见,我国死刑相关制度存在着违背国际公约死刑国际标准的情形,也与国际社会强调限制死刑、崇尚生命无价的理念相左,尤其在保护死刑被告人程序性权利方面亟待进一步努力。
(二)交付执行时间短暂与死刑变更程序的规定相冲突,不利于纠错和罪犯权利的救济
死刑变更程序是死刑执行程序中设置的纠错程序,包括停止执行死刑和暂停执行死刑。《刑事诉讼法》第25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交付执行。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二)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三)罪犯正在怀孕。”第252条规定:“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在执行前,如果发现可能有错误,应当暂停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死刑变更并非终局程序,被执行人能否免于一死,还要看裁定结果。但中止执行死刑为被告人提供了一线生机。在曾经轰动一时的“刀下留人”案中,死囚董伟已被押送到刑场准备执行,临刑前法院突然接到最高法院的通知,要求中止执行死刑。当然,中止执行并非终局程序,效力未定,被执行人能否免于一死,还要看裁定结果。董伟案经二审法院重审后维持原判,最终仍执行了死刑。但可以看到,死刑变更仍然是死刑犯获得救济的一个途径。这里存在的问题:
第一,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死刑变更以权力机关为主导,被告人无权申请。法律只赋予审判或执行机关有权决定死刑的变更,且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导致实践中法律适用的随意性过大、法律约束力欠缺。执行机关(我国死刑的执行机关就是法院)如何在执行死刑命令签发后的7日内从程序上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可能需要改判?谁提出停止或暂停执行死刑的申请?提出申请后谁作出是否上报的决定?如果曾提出死刑变更申请仍被执行死刑,事后证明是冤假错案谁来承担法律责任?这些基本的程序推进问题都没有解答,仅靠审判或执行人员的职业意识或工作经验去实施法律规定,可行性和有效性必定大打折扣。并且,法律本应更注重保障与死刑变更程序有重大利害关系、处于弱势的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但我国这种立法模式却否定被告人的申请权,立法者的天平是否有失平衡不可不深思。
⑪ 参见王震宇、黄娟:《两岸死刑案件法律救济途径比较研究》,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第二,交付执行时间短暂,审判机关难以作出死刑变更决定。死刑变更程序中要求审判机关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应当停止执行或暂停执行。但事实上,由于交付执行的时间过于短暂,要求在7天内经过审查、作出停止执行的决定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时间显然不够,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如果7天内遇上法定节假日,时间如何计算。而且,要求审判机关发现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死刑判决本来就经历了一个比普通案件时间更长、程序更复杂的审判周期,从一审程序直到执行程序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裁判者都没有“发现错误”或者是“有错不纠”,怎么指望在7天之内忽然变更判决?法律裁判不是科学发现,不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靠证据说话,随着时间的经过,证据材料毁损湮灭的可能性只会加大不会减少。既然审判机关已认定案件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作出了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在死刑执行命令签发后,转而又要求他们在7天内去寻找判决的“错误”,质疑自己的结论,既不合乎逻辑也有违情理。
第三,交付执行时间短暂,死刑案件被告人难以引发死刑变更程序。被告人得以引发死刑变更程序、阻止死刑判决发生效力的主要条件有两项,第一项是怀孕,适用范围仅为女性且一般不用等到临刑前才发现。另一项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首先,这一条件的规定用词模糊,没有明确界定“有可能需要改判的”具体标准,可能造成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混乱和不平等。其次,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其他重大立功”的行为,7天内难以依照法定程序完成审查和认定,进而启动死刑变更程序。根据《刑法》第68条和199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属于重大立功的情形有:(1)犯罪分子揭发他人重大罪行,经查证属实的;(2)提供侦破重大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3)阻止他人的重大犯罪活动的;(4)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5)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突出表现的。“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重大罪行”的标准,一般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等情况。其对于检举揭发立功而言,犯罪分子检举揭发的必须是他人的犯罪行为,且必须是经查证属实;对于提供重要线索立功而言,其提供的必须是其他案件线索,且必须是重要线索和经查证属实的案件线索。据此,死刑变更中,罪犯所“揭发的重大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必须符合刑法关于“重大立功”的认定标准,是经过“查证属实”的犯罪行为或案件线索。可见,这里的案件必须是大案、要案、其他案件,司法机关想要在7日之内完成对犯罪行为或线索的“查证属实”,难度可想而知。
综上分析,死刑交付执行时间短暂没有赋予审判机关及罪犯启动和推进死刑变更程序所必需的诉讼期间,违背了司法认知活动发现、提出、证明的运行轨迹,无法使死刑变更这一纠错和救济程序发挥应有的效力。
(三)交付执行时间短暂与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冲突,不利于死刑案件被告人申诉权利的保障
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赋予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的权利。这项权利同样适用于经过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但为什么司法实践中鲜见死刑执行阶段申诉成功的呢?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法院收到申诉材料后,先要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法定条件的才能决定予以受理。由于法律没有规定申诉审查的诉讼期间,导致实践中的申诉审查缺乏时间约束,案件通常一拖再拖。即使法院决定受理申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再审审理也需要3到6个月诉讼期限才能审结。被告人即使提出申诉,法律规定申诉不能停止死刑裁判的执行,从死刑命令下达到交付执行最多只有7天,很可能在申诉审查决定未作出之前被告人就已经被执行了死刑。
实践是检验法律规定合理与否的有效标准。2014年岁末引发全民关注的呼格吉勒图案,申诉竟然长达18年之久才启动再审程序。1996年6月年仅18周岁的呼格吉勒图被法院判决死刑并立即执行,距离案发仅61天,2005年“真凶”内蒙古系列强奸杀人案凶手赵志红落网,2014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才决定再审。同样,河北聂树斌案申诉也长达19年。1995年聂树斌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核准执行死刑,2005年“真凶”王书金落网,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才决定将案件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每一个判例,都可能为公众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块基石;而每一次失误,也都可能成为这一信仰崩塌的链条”⑫《在每个案件中体现公平正义——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之二》,载人民网,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3/0228/c1003-20624293.html,2014年12月14日访问。。这两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在有“真凶再现”的情景下,尚且需要被告人家属、社会人士和媒体十几年坚持不懈的申诉才得以发动再审,那么现行法只给死刑案件被告人最多7天的申诉期间,无异于变相剥夺了其寻求救济的唯一路径,一旦判决出现错误,后果不堪想象。“申诉制度设计的如此不合理、不科学,而现行法律对死刑立即执行这样一种特殊的执行程序又欠缺相应的安排,导致司法实践中死刑罪犯申诉权得不到保障,只能是纸上谈兵。”⑬郝双梅:《论我国死刑执行程序的法律完善》,载《天津法学》2012年第4期。
(四)交付执行时间短暂,不利于人民检察院有效发挥执行监督的作用
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检察院对死刑立即执行实施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44条规定,人民法院将罪犯交付执行死刑,应当在交付3日前通知同级人民检察院派员临场监督。由于法院交付执行时间最长也只有7日,对检察院而言则只有最短4日最长7日的准备时间。检察院的执行监督一方面要监督死刑执行的时间、地点、方法、停止行刑等程序性的问题是否合法,另一方面也要考察执行前后罪犯权利的保障问题。死刑执行监督关乎罪犯的生与死,其严肃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要求检察机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审阅案卷、命令、核实材料,实践中难免流于形式,难以真正履行执行监督的职责。
三、改革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时间的设想
(一)废除“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的称谓,改称“死刑的判决”
死刑立即执行中,“立即”强调的是马上、立刻、毫不等待。由上可知,我国现行法律存在片面强调快速执行死刑,忽视了给予罪犯必要和充分的救济时间,损害了死刑被告人应当享有的程序权利,存在“误杀无辜者”的巨大风险。因此,在维持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笔者主张废除“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的称谓,改称为“死刑的判决”。《刑事诉讼法》第248条已经存在这种表述,“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三)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因此,这一称谓的改变不存在太大的障碍。
据此,死刑判决将相应地区分为死刑的判决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判决两种。同时,《刑法》第48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可以相应地更改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满足缓期执行条件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
(二)延长死刑判决交付执行的时间至少为1年
笔者主张,对于不符合缓期两年执行条件的死刑的判决,应当将交付执行的时间从现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7天延长到至少1年。这样在时间上基本可以满足死刑变更程序、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检察执行监督程序启动和推进的需求。延长后,死刑执行命令的签发与交付执行之间有了一定的时间间隔,既给予了审判机关一个纠错的期间,又是死刑案件被告人寻求救济的程序保障,也可缓解现行交付执行时间短暂与相关法律规定的冲突。时间延长到1年,死刑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近亲属便有时间和机会采取各种法律手段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寻求辩护人的帮助、寻找新的证据、提出申诉等;审判或执行机关也有充分的时间审慎地审查是否存在裁判错误、死刑变更执行的情形等各种问题。
1年时间也明显区别于美国、日本等许多虽然保留死刑,死刑交付执行时间却普遍长达数年、数十年的“死囚等待”现象。不会给罪犯造成长期等待的巨大精神痛苦,也不会“大大增加个人诉讼成本和国家司法成本”⑭夏勇、吴玲:《“死囚等待”——美国的不立即执行死刑制度及其启示》,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
(三)增设死刑判决的特殊申诉制度
死刑判决在被告申诉期间不能停止判决的执行,这一规定漠视了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和死刑交付执行时间的短暂性,忽视了死刑被告人申诉权难以真正行使的客观事实。建议在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增设关于死刑判决申诉的特殊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可以在交付执行前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申诉期间应当中止判决的执行。”
首先,应当赋予辩护人申诉权。死刑犯处于严格的羁押状态,难以真正有效行使申诉权,辩护人的介入能有力地保障罪犯申诉权的行使,为了充分保障死刑被告人的利益,应当允许辩护人在被告人授权下提出申诉。其次,死刑案件的申诉期间应当中止死刑执行,等待法院审查申诉的结果。一旦法院受理案件进入再审后,再审期间法院便可以决定中止原裁判的执行。如果法院决定不予受理的,可继续计算交付执行的诉讼期间。最后,建议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受理申诉、作出审查决定的诉讼期间,以避免诉讼的拖延,审查以3至6个月为宜。
(四)完善死刑变更程序,赋予死刑案件被告人申请死刑变更的权利
死刑变更程序中应赋予死刑案件被告人基于一定的事实和理由申请停止死刑执行的权利,这是临刑前的最后一条救济途径。将现行法由法院这一笼统的主体决定变更死刑执行的权力改变为由审判机关中具体办案人员申请的模式,使权责相对应,以便在错案追究责任的时候可以落实到具体的责任人。建议增加下列规定:
1.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在执行前有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可向原审或终审人民法院提出停止死刑执行的申请,由接受申请的法院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立即上报最高院作出裁定。
2.死刑案件的审判员、陪审员、执行人员在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可以向原审或终审人民法院提出停止或暂停死刑执行的申请,由接受申请的法院决定是否受理。决定受理的,应立即上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3.有证据证明已经执行的死刑案件是冤假错案的,如果在死刑执行前提出过停止或暂停执行死刑的申请,未被依法受理或决定不予受理的,由相关的法院及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责任。
(五)人民检察院提前介入执行监督
为有效发挥检察院对死刑执行实施监督的职责,在延长死刑交付执行时间至少1年的前提下,建议检察院介入死刑执行程序、实施执行监督的时间提前至死刑交付执行前的3个月。提前介入死刑执行,为实施具体的监督工作提供了时间保障,更有助于扩大检察监督的内容和范围,“建立涵盖执行前阶段的人性关怀,遗言、遗嘱、会见的帮助执行和律师介入制度,执行后尸体处理、死亡认定,及相关的死亡证明制度的监督保护,给死刑犯以更多的人性关怀”⑮于晋云:《死刑立即执行监督现状及问题》,载《法制与经济》2013年第1期。。由此,既丰富其内涵又加强其作用,让执行监督走向实质化,避免监督的虚化和走过场。
四、结语
改革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交付执行的时间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从数量上减少、控制死刑,体现司法正义和人道主义的关怀。“Dead Man Walking,是美国狱警的一句俚语,当死囚走出牢房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狱警就会说这句话,表示死囚将走上最后一段人生旅程,仿佛阴阳两界的叹息桥,走过去即将属于另一个世界”⑯何汀:《死刑执行前的人性思考》,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3年9月。。让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那么短暂,多给死刑犯一点时间和一线希望,因为没有人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罪大恶极的人也应该死得有尊严。程序权利的保障是对于死刑正当性的重要补充,临刑前能够使罪犯穷尽救济手段、情绪得以舒缓或释放,对于立法者、受刑者及其家属和行刑者,或许都可以或多或少卸下一些心灵的重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