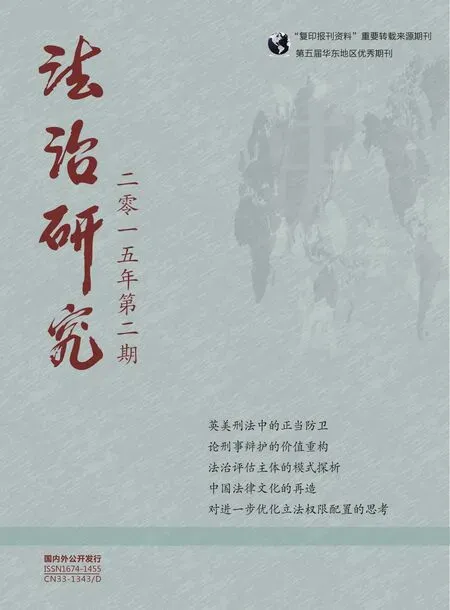当“现代的利益博弈”转向“传统的遗传资源领域”*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的深层根源及其矫正原理研究
钭晓东 黄秀蓉
伴随着人类对资源环境干预范围及力度的不断扩张,资源存续与保护在当前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个发展问题。遗传资源作为地球上一种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财富,在文明演进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遗传资源这一基石,其既为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问题应对提供了丰富的遗传基因、工具与经验,也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演进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及生态系统保障。伴随着人类文明演进的进一步深入,曾经被一度遗忘的遗传资源及其价值已经日益受到关注,遗传资源领域在当前已经日益成为获取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的一个新途径。
为了便于遗传资源的获取和研究,推动基因工程的进步,国际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采集全球各种动植物遗传资源,建立各类基因银行或基因库,整理各类物种的遗传密码信息,开始了遗传资源获取、使用及后续研发等方面的诸多探索。不过,在具体的探索进程中,各国在遗传资源的分布、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能力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也正是基于这些差异,目前国际社会在相应的“遗传资源所有权、获取及其惠益分享等”问题上还存在着诸多争议和分歧。在相关的利益分配与调整中,作为“利益相关者”,涉及规制知识产品的创造者、传播者、利用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利益分享者”,则要考虑独占权利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①吴汉东:《知识产权的多元属性及研究范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显然,伴随着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的迅猛发展,各国农业、医药、化工、环保等产业对遗传资源的依赖日益加重,遗传资源已成为一种特殊资源,其占有数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而与此同时,遗传资源生物研发技术迅猛发展及其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强化,更使遗传资源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现代利益博弈转向传统领域”的一个重要现代议题。
一、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的国际社会分配失衡之症结
就当前遗传资源的分布、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能力等方面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目前的境况是——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拥有量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则有更充足的资金、更先进的技术及研发机制。而这也带来了遗传资源获取及研发后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问题”。就这种惠益分配失衡的根源及其主要症结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层面
(一)症结之一:遗传资源的分布失衡
就分布而言,遗传资源在自然界中的分布是不均衡的。自然条件、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的不同,使得各地的遗传资源分布也呈现出差异性与多样性。不仅不同种类的遗传资源在地带分布上有明显差别,即使同一种遗传资源,也会因为不同属性的地带规律性影响,呈现出很大的空间差别。因此在分布上,有些地方的遗传资源丰富,有些地方匮乏。对此,在2001年10月22~26日德国波恩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获取和利益分享不限名额工作组会议中,就曾形成了三类不同利益的集团:其一,欧盟和日本等为代表,生物技术发达,但是遗传资源匮乏;其二,美国和加拿大等为代表,生物技术发达,遗传资源也较丰富;其三,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生物技术相对落后,不过遗传资源丰富。虽然以上的利益集团划分只是一次国际会议中的界定。不过,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充分表明这样一个现状——遗传资源在国家社会分布的失衡。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的品种及储量在现有的遗传资源中,占有绝大部分比例。特别位于或部分位于热带和亚热带的国家与地区,拥有的遗传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比例最高。地球上80%的陆地生物多样性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国家。巴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代表,其生物多样性为全世界生物多样性的70%,除澳大利亚外,这些国家几乎全部都是发展中国家。
我国作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地质历史古老、国土辽阔、海域宽广、自然条件复杂多样,孕育了极其丰富的遗传资源物种与生态系统组合,形成了遗传资源多样性。作为全球重要的生物遗传多样性中心,我国拥有众多有活化石之称的珍稀动植物,遗传资源不仅丰富,而且特有程度高。②国家环保局编:《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拥有高等植物32800种(特有高等植物达17300种,其中种子植物有5个特有种,247个特有属),居世界第三;脊椎动物6347种(特有物种占667个,为中国脊椎动物总数的10.5%),占世界总数的14%;鱼类3862种,占世界总数的20.3%,都位居世界前列。作为世界上微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现在已报道的物种数目占世界报道总数的10%。许多优良品种的遗传资源在不同的区域得到了相应的保存。我国作为世界8个作物起源中心之一,在漫长的农牧业发展过程中,培育和驯化了大量经济性状优良的作物、果树、家禽、家畜物种等数以万计的品种。多种多样的农作物、家畜、鱼类品种资源及其野生近缘种既包含了其特有的原始遗传性状,也保存了千百年来劳动人民人工选择的优良品质,构成了我国巨大的遗传资源多样性资源库③薛达元、林燕梅:《生物遗传资源产权理论与惠益分享制度》,载《专利法研究》(2005),第38页。,具有极大的遗传资源多样性价值。
然而,相比较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当前许多先进的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但是在遗传资源储有量上,许多发达国家却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就成了被发达国家攫取遗传资源的重要对象,成了发达国家系列研发活动的主要遗传资源“输出国”。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从发展中国家“输入”的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而与此相反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正在大量的“输出中流失”。如当前我国遗传资源流失的确切数量就难以统计,其中输入与输出的比例据估计已经达到1∶10。如就大豆而言,大豆原产于我国,世界上90%以上的野生大豆资源分布在我国。④罗莎:《遗传资源惠益分享与知识产权保护》,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6页。而美国目前作物基因库中所保存的大豆资源已达20000多份,仅次于中国,而且很多原产我国的大豆资源成了美国的专利产品。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上“一进一出”的不同境况,表明了“遗传资源的国际分布不均衡”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当然,这一事实构成了遗传资源获取及研发后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的一个客观原因。
(二)症结之二:遗传资源价值评估的失衡
遗传资源价值结构的复合性。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资源开发及利用视角进一步深入到遗传资源多样性层面,遗传资源在各个领域的价值正在不断地被认识与展现。据估计,世界经济中的40%以遗传资源产品及其加工为基础。世界上贫穷人口85%~90%的食品、燃料、药品、居所和交通等都来源于遗传资源及其产品。源自遗传资源的商品全球市场价值在5000~8000亿之间。不过,遗传资源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部分,作为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与基础,显然,其价值内涵与一般的资源是不同的。一般资源的价值大多都直接体现在资源实物本身及其经济价值上。但是,遗传资源的价值是复合的,而不是仅仅限于遗传资源实物的经济价值,其价值结构是一个明显的复合体。因此,当前人们对遗传资源价值的评估仅限于对遗传资源经济价值的关注是不完整的。遗传资源的价值内涵需要有一个确切的重新认识与完整界定。
关于遗传资源的价值内涵,《生物多样性公约》曾作过相应界定,将遗传资源的价值分为外在价值和内在价值两个方面。就其具体组成看,遗传资源的价值可分为经济价值、生态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遗传信息价值等不同的类别,会在不同层面给予呈现。例如:其一,它是人类健康所涉及的医药药品及医疗方法的重要原料或重要来源。数据表明,在当今世界经常使用的药品中,有一半以上是来源于植物或者植物的化学合成复制品。治疗心脏病、小儿白血病、淋巴癌和青光眼的基本药品,其原材料基本来源于植物。其中每年在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都超过了400亿美元。其二,其为不同类型的工业提供原料。现代工业化进程需要更多和更新的遗传资源得以发现与开发,以便为各种工业生产提供必需的原材料和新型能源。其三,其在生物圈的维持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其中包括维持物种与生态系统进化、清除有机垃圾、消除污染物、分解死去的植物和动物、降解有机废物等不同方面。其四,其在自然界演变与人类文明演进中的遗传信息价值。
尤其是伴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一步迈入到信息社会,深入到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层面,遗传资源作为自然界演变与人类生态文明演进中的一种重要的基石性资源,其所包含的深层遗传信息价值将更彰显出它的价值。
显然,在界定与认识遗传资源价值的时候,不应仅关注其作为资源实物的经济价值,必须对其“价值复合性”的特征作一完整的把握。尤其是对遗传资源所包含的“遗传信息价值”重要内涵的认识。遗传资源所包含的“遗传信息价值”不仅对农业和制药业等产业发展,而且对信息社会推进与人类文明演进都具有重大意义。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个重要组成,特定的遗传信息在整个自然界演化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遗传资源所包含的遗传信息又很少以单一的形式出现与存在,很少直接体现在某一单一基因或单一化合物中,而大多表现为含有多基因组合或多样化的协同的状态。这些特征的把握构成了我们正确与完整认识与评估遗传资源价值内涵,并对之加以认真研究、保护与利用的基础。
2.遗传资源的遗传信息价值需要得到充分认识。虽然目前在很多时候,遗传资源被认为是由自然提供的一种生产要素。但是,它与同样是生产要素的传统矿物资源有很大不同。如要获取并开采煤铁矿时,需要首先找到一个有一定储量规模的矿藏,其后的相应开采与提炼才有必要。但是,遗传资源的获取及其生物技术研发与价值衡量却大为不同。在相应的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很多时候只需采集少量遗传资源样品即可完成,而且还可以不需要原产地的后续资源支持而进行大规模制造。因此,从根本上说,遗传资源相关技术研发及其产品价值集中体现在知识生产与信息传递阶段。其更关注的是——利用遗传资源所得的遗传信息及相应知识产品的价值,而不是遗传资源的直接利用。⑤杨远斌:《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利益分享模式研究》,华中科技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5页。显然,对于遗传资源相关生物技术研发而言,其除了遗传资源实体的“显性价值”外,还包含着诸多更为重要的(诸如遗传信息使用、创造与传递)“隐性价值”。该类“隐性价值”随着技术研发与生产的深入,可以衍生并聚集到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惠益上。显然,这种隐性惠益与有形的实物价值有很大区别。若仅基于物权视角,遗传资源所有者和持有者在由遗传资源所衍生的利益中就只是分享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其在遗传资源信息使用、创造与传递等方面的贡献并未获得公平合理的回报。
因此,当前国际社会之所以出现“发展中国家面临发达国家对遗传资源大量攫取和‘生物剽窃’,彼此之间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的境况,其中遗传资源所包含的遗传信息价值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定,是重要的主观原因。
二、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的深层根源:国际社会利益博弈的失衡
从表面上看,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仅是相关利益分配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其实质反映的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遗传资源获取、研发、利用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虽然,从地理位置和分布情况看,遗传资源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但在与发达国家的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的利益博弈”中,发展中国家却因“自身在经济与技术研发实力上的劣势、知识产权制度的功利性、发达国家主张的所谓人类共同遗产”等因素影响,处于不利的地位。
(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技术研发实力上的劣势
从经济实力与技术水平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曾通过《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所拥有的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86%,而占世界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只占世界总产值的14%。⑥朱炎生:《发展权的演变与实现途径》,载《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同时,在遗传资源获取、研发、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中,发达国家也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经济与技术研发实力上的优势,辅之以“遗传资源是人类共同的遗产”的幌子,通过生物剽窃、生物勘探等方式,窃取、骗取等手段,攫取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并将之知识产权化,独占遗传资源的知识产权惠益。而且,有些甚至还要求发展中国家支付高额的遗传资源研发产品使用费,从而在“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的利益博弈”中占据有利位置。
例如就国际多边种质资源的交换机制而言,国际上所建立的种质资源库例如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ARCs),名义上是在利益对等基础上,收集“各国”的遗传资源,为“各国”的遗传资源“共同利用”提供便利。但事实上——收集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因为遗传资源大国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但这些种质资源库建立的实质目的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发达国家的需求,为发达国家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用提供便利。显然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及其分配是不对等的。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遗传资源利用的需求巨大,同时又借助其在遗传资源价值的认识及信息掌握的优势,要求发展中国家大量提供优质的遗传资源(例如中国农科品种资源研究所20年间的记录,通过官方交换途径,向国际机构和国家输出约2.8万个遗传资源材料,从质量上看输出到国外的材料大都是国外育种机构指定要求的遗传材料,很多是野生亲缘种和优良的地方品种⑦薛达元:《中国生物遗传资源现状与保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另一方面,则是发展中国家基于经济与技术研发水平差距,对遗传资源不够了解、信息掌握不完全(不管是对自己的,还是对发达国家的遗传资源),不仅利用水平低,而且利用数量又少,也没能提出对等的交换优质遗传资源的条件。因此存在一系列问题,如:所欲换取的“目的性遗传材料”不太明确,对获取的国外遗传资源不能提出具体统一的清单,所谓的“对等交换获取”实质却陷于“主观、盲目”等。显然,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了自己在经济与技术研发实力上的优势,主导了国际多边种质资源交换机制的设立与运行,使利益博弈发生了偏离。
(二)知识产权机制运行的功利性取向
知识产权作为现代类型的知识及其创新的保护机制,它在促进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这一保护机制也在不断加强与扩展。但是,种种迹象表明,现行的相关知识产权制度即使宣称其宗旨是促进人类社会知识产品的开发与技术进步,实际上其首要的目的与作用却是——维护知识产品与研发技术背后的经济利益。一定程度上,现有的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在立法目的上就具有很大的功利性,如在专利立法中,它只对那些直接应用于实际产业的实用技术提供保护,至于该技术对人类知识总量及后续创造有多大贡献,专利法并不关注。专利法自身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承担起促进整个人类技术进步的重任。“它只有在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时才搬出,促进人类科技创新之类的目标来。”⑧崔国斌:《基因技术的专利保护与利益分享》,http://sub.whu.edu.cn/cctcc/swjszlfg/xzgd2.htm,2014年3月5日访问。在遗传资源的获取与研发过程中,目前的现实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研发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利用遗传资源创造出相应的知识产品。相反,发达国家却利用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价值认识、信息掌握、研发与经济实力上的劣势,窃取、骗取或无偿获取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并以此为基础研发出相应的知识产品,进而控制发展中国家对遗传资源使用及相应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当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例如1991年,美国默克药业集团公司仅用100万美元就买下了对哥斯达黎加的植物资源进行筛选、研究和开发的权利。1997年,有“皇冠名珠”之称的印度香米被一家美国公司申请了专利,直接影响印度每年3亿美元的香米出口,尽管后来印度政府费尽周折,仍失去了16项专利权。2001年,美国的一家公司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出一种品质与泰国“茉莉花香米”十分相似的新品种,在美国申请专利保护。对此,泰国农民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政府保护本国传统香米的生产和出口。据统计,美国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占其总量的90%,日本占85%。⑨《中国生物多样性履约简报》2004年第1期,http://www.dloer.gov.cn/ReadNews.asp?NewsID=311,2014年8月8日访问。
显然,对于遗传资源的获取与研发这样一个过程,现行相关知识产权制度所保护的仅仅是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之后衍生出的知识产品。如果说,此类衍生出来的知识产品是“流”的话,那么发展中国家及其拥有的遗传资源就是“源”。但是处于“源”位置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在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惠益的“流”中获得利益,反而还会因为发达国家设立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等知识产权,不仅在遗传资源使用权上受限制,而且还要付出高额的研发产品使用费。可以说,现行相关知识产权制度从根本上忽略了衍生权益的遗传资源及其所有者利益。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其保护的仅仅是发达国家在“合法外衣”掩饰下对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的盗用。发达国家在“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的利益博弈”中,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表面上的“保护知识产权”的特性,利用了其在经济与研发技术上的优势,获得了非己所有的遗传资源的排他性知识产权,达到了“垄断性控制相应遗传资源及知识产品与排他性享有惠益”的目的。显然,现有知识产权机制运行的功利性取向加剧了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甚至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公平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的一种阻碍。这样的结果使知识产权机制在立法本意与保护创新的理念等方面,都受到相应程度的质疑。
(三)发达国家的“人类共同遗产”的幌子
人类共同遗产是国际法的一个原则,其在1979年的 《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明确规定。那么,遗传资源是否也可归之为“人类共同遗产”,对此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争论。发达国家出于自由获取遗传资源的需要,认为遗传资源是“无主物”、“共有物”、“人类共同遗产”,犹如太空与深海,每个人都有权免费地使用。1983年世界粮农组织制定了植物基因资源的行动纲领,具体规定了有关基因材料采集、保护与提供的基本原则,指出该行动纲领的原则是“植物基因资源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应该在全球范围内无偿提供给各国研究人员”。1989年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通过的第4号决议(Resolution4/89)也认为,植物遗传资源是需要保护的人类共同遗产,应为当代及后代共同的利益而被自由获取并使用。⑩同注⑦。显然,发达国家正是利用这样的旗号掩护,利用发展中国家对遗传资源价值认识的不完全及相关法律规则机制的不完备,而大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生物勘探与生物剽窃,无偿或者低价攫取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
从表面上看,将遗传资源归之为“人类共同遗产”以供自由获取,体现了一种公平。但是在实质上其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差距 (无论在遗传资源拥有量、对遗传资源价值的认识程度,还是在经济与研发技术水平,遗传资源获取、研发与使用的法律规制等方面);而且双方的权利义务也处于一个不对等的位置。因此,如果说“人类共同遗产”的提出,其目的是追求遗产的全人类公平分享;那么,不同等的状态与不对等的位置,在遗传资源“人类共同遗产”幌子下,恰恰导致的是利益分配的更不公平。在全人类共同遗传原则下,利益只是属于那些掌握了先进研发技术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基本无法获取利益,最终还可能因为利用本国遗传资源而向发达国家支付高额的知识产品使用费。这明显违背了“人类共同遗产”口号提出的初衷,也加大了两者在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上的失衡,也使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境地。
为此,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发达国家主张的“人类共同遗产原则”幌子提出质疑,主张自然资源国家主权;认为遗传资源既然位于一国国内,就应当视其为国内“资源”,属于所在国主权管辖和控制下的“自然资源”,国家对遗传资源享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谈判期间,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发达国家提出“人类共同遗产”这一主张,主张对其本国生物多样性及遗传资源的永久权,最终在CBD缔结谈判中取得胜利。CBD的序言中指出:“重申各国对自己的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第3条明确规定:“依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各国具有依据其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权利,同时亦负有责任,确保在它管辖或控制范围内活动,不致对其他国家的环境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环境造成损害。”第15条再次确认:“各国对其自然资源拥有主权权利,因而可否取得遗传资源的决定权属于国家政府,并依照国家法律行使。”这明确了遗传资源提供方对其境内的遗传资源享有永久主权。根据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原则,发展中国家对遗传资源以及遗传资源相关经济活动 (如获取和商业开发等)都享有绝对的永久主权。具体而言,享有占有、使用和自由处置其遗传资源,自由决定和控制遗传资源的勘探、开发、利用和营销,根据国家发展与环境政策管理和保护遗传资源,管理外国的获取及获取后续活动,公平合理分享遗传资源开发活动产生的惠益等权利。对其境内生物资源的获取及其他相关活动,发展中国家有权进行管制,其他国家或其国民获取和利用其生物资源必须以 “共同商定的条件”为基础。因此,在发展中国家向使用者提供生物资源时,必须要求可以获取技术并分享惠益。⑪Ayesha Diaz,In the Light of UNCED:Permanent Sovereignty over Natural Resources,(24)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Law,4,1994,P.16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遗传资源是全人类的遗产,应该为大家自由使用”也许是人们的普遍认识。但是,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理论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共同遗产”这一原则所谓的合法性。显然,在当前这个经济、科技竞争激烈的国际社会中,发展中国家无疑处于相对劣势,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理论无疑是不可缺少的自我保护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坚持自然资源的国家主权理论,才能争取与发达国家同等的国际地位,有效增加遗传资源领域谈判的分量,运用法律武器抵制外来干涉和掠夺及发达国家所强加的各种不平等条件,使本国的遗传资源获得保护。当前,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立场和出发点上还有诸多不同,因此双方关于遗传资源获取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配的具体建议还相去甚远。对于当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惠益分配上的失衡及其意见的分歧”问题,如果说“遗传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是其中的一个客观条件原因,“价值评估的失衡”是其中的一个主观认识原因,那么“双方利益博弈的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后天的法律制度建构问题,其有待法律制度自身的调整来加以解决。
三、“从失衡到公平分享”的法理基础:关民共享理论
(一)知识产权制度不应排除非创造性劳动
一般情况下,鼓励创造性劳动是知识产权制度设立与运行的重要目的。因此,我们会很容易认为——只有那些为专利产品提供了创造性劳动的一方,才有权分享专利。所以,对于“遗传资源提供方可否参与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的问题”,许多人可能就会有一系列疑虑:仅仅因为提供遗传资源原材料,就要求参与专利成果分配,这样是否公平?仅仅基于对遗传资源的占有就要参与惠益分享,是否会动摇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基础?为此,许多人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遗传资源提供方在遗传资源知识产品创造过程中,只是采取了交付遗传资源的行为,并未对之付出创造性劳动,那么就不应该享有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显然,这样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诚然,鼓励创造性劳动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美国1793年专利法起草者杰斐逊也提出“创造性应当得到慷慨奖励”的价值哲学。但是,必须明确的是,“鼓励创造性劳动”只是知识产权制度目的追求的一个方面,“科学合理衡平知识产品的利益相关人的利益”才是其真正的深层功能与终极目标。忽略了这一功能与目标定位,将会给相应的利益相关人带来极大的不公平。
泰国香米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⑫胡培松、唐绍清、魏兴华:《泰国香米事件及启示》,载《中国稻米》2006年第4期。2001年,美国研究人员Chris Deren利用从国际水稻研究所获得的泰国香米的种子(KDML105香米)作为研究的原材料,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开发出一种品质与泰国“茉莉花香米”十分相似的新品种。该品种比传统的泰国香米要矮小,只需少量阳光就能在美国广阔的平原上栽种,而且可以机械化推广。同时,ChrisDeren也准备在美国申请专利保护。但是问题是:Chris Deren的研发原材料,是以泰国香米的种子为研究样本;同时Chris Deren既没有与哪一方签订任何转让协议,也没有与泰国政府订立有关利益分享的协议。如此,如果专利申请得以成行,那么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怪圈——原本应在该专利中受益的对象(泰国香米研究样本的拥有方)并未因此而受益,相反却因此付出高昂代价。样本提供方会因为Chris Deren的专利获取,不仅失去对该问题进行相应研究与申请专利的机会,而且还要支付高额使用费。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此后的香米遗传资源使用中,原料提供者会因为专利存在而受到诸多限制,失去继续生产这些原材料的权利,迫使泰国农民面临放弃世代种植香米的境地。这对于泰国香米研究样本提供方而言,显然极为不公平。为此,泰国上至总理下至广大农民开展了一场举世瞩目的“泰国香米”保护战。泰国商业部外贸厅、泰国大米出口商协会、美国经营泰国大米进口的公司(作为3个受损方),于2002年1月底联署向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FTC)状告美国侵权方,最后迫使其撤销了部分专利。类似的案例还有印度香米事件。显然,简单将遗传资源提供方排除在知识产权惠益分享之外既不合理也不公平,其违背了知识产权制度运行的深层目的。
更何况,即使是“未提供创造性劳动”,也不意味着必定无法享有知识产权惠益。职务发明创造的相应规定恰恰给出了相关的论证。如我国的《专利法》第6条第1款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第3款规定:“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申请专利的权利和专利权的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显然,在职务发明中,单位事实上并未提供创造性劳动,而仅仅是提供了相应的资金、材料等条件,其在专利技术的生产中所担任的角色只是相当于一个投资人。但是《专利法》却将专利权授予了单位。而这与遗传资源的提供者所处的角色是完全一致的。显然,让遗传资源原材料提供者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无可厚非。
(二)惠益分享的理论阐释:关民共享理论
有关提供非创造性劳动的惠益分配问题,美国威廉·伊文教授和爱德华·弗里曼教授提出的著名的 “关民共享利益原则”进行了重要的理论阐释。“关民共享利益原则”主张利益应由利益创造者和创造利益的相关贡献者共享。尽管该理论最先提出是基于经济伦理视角,但是将之延展至遗传资源领域也是有充足的理由。不可否认,研究人员的研发行为在遗传资源之知识产品的形成及其利益产生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但是遗传资源提供者在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首先,其所提供的遗传资源是相应知识产品衍生之源,否则所谓的知识产品研发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遗传资源提供者在遗传资源的使用、保存过程中长期以来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为知识产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财富;另外,遗传资源自身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研究样本,一般不能从普通市场上得到。它的特定性与有限获取性更是使样本提供者的贡献很难替代;同时,也只有原材料提供者能够在知识产权惠益分享中获利,研发者才可能源源不断地获得遗传资源样本。
在当前国际社会,有关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的要求日益高涨。特别是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印度代表团在1996年WTO的有关会议上,就指出TRIPs第27条第3款(b)关于生物技术专利保护的规定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有冲突,要求对规定进行研究和修改,巴西和一些非洲国家也表示了支持和赞同。⑬张清奎:《试论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所面临的新挑战》,载《专利法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2000年12月,欧美生物技术顾问联合论坛第二届欧美峰会在华盛顿召开,论坛也在向峰会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农民利益的保障与研究优先,对任何一项发明所利用的传统或土著的医学或农业方面的知识给予一定的回报等。国际社会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始采取措施对待相应的“生物剽窃”行为,要求利用遗传资源开发产品的现代技术公司与资源国分享有关生物产品利润或支付特许使用费。⑭资料来源于http://www.chinagenenet.com/news-news.asp,2014年8月8日访问。而《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及《波恩准则》国际条约的签署,更是为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奠定了制度基础。CBD第15条第7款规定缔约国可以采取立法、行政、政策等措施,以期与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国公平分享研究和开发此种资源的成果以及商业和其他方面利用此种资源所获的利益。CBD第19条则规定了具体的惠益方式,如让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遗传资源的研究中,以及发展中国家优先取得遗传资源的惠益。这是关于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第一次在国际条约上予以确认。而2001年各国代表在德国波恩制定的《波恩准则》更是详细规定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步骤,确定了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给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享进一步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支持。
因此,法律在授予相应的遗传资源专利权过程中,必须考虑遗传资源样本提供者的贡献。更何况在当前,许多基于商业目的的遗传资源基因研究还具有巨大的功利性,基因关键环节的突破将会带来无穷的经济利益。因此,必须遵循“关民共享利益”原则,考虑“高价值研究样本的有限可获取性与潜在价值无限性”之间的利益衡平。否则,对于提供遗传资源研究样本一方而言,明显有失公允。
当然,“关民共享”毕竟是一种伦理准则,带有浓重的同情弱者的感情色彩。但是感情不能代替法律。因此,还需要相应的制度配置给予进一步的落实。
四、“从失衡到公平分享”的现实基础:“遗传资源提供行为”的价值评估
遗传资源提供方如果要在遗传资源知识产权中获得公平、合理、充分的惠益分享,首先就需要对“遗传资源的提供行为”在遗传资源知识产品形成中的贡献与价值作一完整的评估。显然,它与一般情况下的知识产品研发原料提供有很大区别。正是因为围绕遗传资源所形成的一系列特殊性,决定了“提供遗传资源”的价值与意义必然远胜于提供一般“物”。这些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遗传资源自身的特殊性使遗传资源不同于一般的原料。其特定性与有限获取性,使其一般不能从普通市场上得到,也不同于传统矿物资源铁、煤等在全球各地有广泛储备或分布。而这也使提供者的提供行为在知识产品研发中的贡献无法替代。
2.遗传资源知识产品形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更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对于传统的知识产品研发(如传统意义的专利研发),研发样本提供者主要是通过销售用于制造专利产品的原料来获得利益。因此,即使提供者不参与专利惠益分享,也不会直接与专利权人产生利益冲突和显失公平问题。因为传统意义的专利技术研发者在获得专利后,只要专利产品继续生产,就对原材料有不断的需求,则原材料提供者就可不断借助原材料的提供而持续获利。然而,以遗传资源为本体的专利研发与生产却存在极大不同。研发者在提纯出遗传资源基因后,就可以大量对该遗传资源进行复制,因此也就不需要再购买该原材料,遗传资源提供者自然也就很难继续从专利的后续生产中获益(提供者甚至还可能因为知识产权的存在而失去继续生产该原材料的权利)。
3.遗传资源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知识产品研发原材料的另一原因是其还包含了诸多重要的遗传资源信息。这些信息是其他原材料所没有附带的。而这些信息恰巧是知识产品形成的关键因素。在遗传资源知识产品研发与生产过程中有三个独立的阶段:遗传资源的提供;遗传信息的发现、鉴定与解码;基本信息的处理与相应知识产权产品的市场开发。其中,基础研究阶段关注于发现、鉴定和编码DNA序列或其他的生物化学信息。在产业开发阶段中,前期得到的这些基本信息用于开发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这些过程包括在新的遗传信息基础上合成新的遗传基因、开发高产作物或新型技术等)。⑮同注⑤,第 26 页。
不可否认的是知识产品的真正价值在于相应信息的传递与创造,而并非单纯“物”的交接。遗传资源的研发与生产和传统矿物资源有很大不同,前者更关注在利用遗传资源中得到的信息和知识产品的价值,而不是对遗传资源本身的直接利用。因此,简单将“提供遗传资源的行为”定性为是对于普通“物”的一种转移或交易,进而从物权转移视角来界定利益分享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其价值评估也是不完全的,不能直接延伸至遗传资源中遗传与生物化学信息的价值体现与保护。
因此,如果遗传资源的价值需要重新进行完整的评估(正如前文所阐述的),那么同样的,在遗传资源知识产品研发与生产过程中,对遗传资源拥有方提供遗传资源行为的价值也需要一个完整的认识;必须从“所提供的物、提供物中所包含的信息”两个基点对“提供遗传资源行为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与完整认识。这是后续相应遗传资源知识产权界定及其惠益分享的基础。
五、余论
综合而言,就当前遗传资源的分布、遗传资源研发技术与能力等方面比较而言,国际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发展中国家在遗传资源拥有量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发达国家则有更充足的资金、更先进的技术及研发机制。而这也带来了遗传资源获取及研发后的“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分配失衡”。在此期间,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已经充分意识到了遗传资源在未来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价值。为此,发达国家借助自身的经济和研发能力优势,通过合作研究、出资购买,甚至剽窃的方式,大肆攫取发展中国家的遗传资源,并在此基础上研发新的技术或植物品种,并通过申请专利、技术转让等商业化途径获得巨大商业利润。另一方面,发达国家还借助西方现行的知识产权规则,非但不承认这些遗传资源的来源,不支付这些“原料”开发及保护的任何费用,让提供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分享相关研发成果的惠益;相反,还通过专利权、植物品种权等知识产权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收取高额的遗传资源研发产品使用费。这使得作为遗传资源提供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相应的权益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原有遗传资源的使用权益甚至还受到了限制或排除,成为了新一轮的遗传资源开发及利用过程中的受害国。
显然,国际社会在不断强化遗传资源生物技术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却忽略了对遗传资源生物技术创新的源泉——遗传资源所有者的知识产权惠益保护。一定程度上,在当前遗传资源意味着巨大战略性价值的时代背景下,相关的欧美知识产权规则已经演变成为发达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工具。这显然对发展中国家(作为遗传资源主要提供方)极不公平。这种不公平的利益分配也加剧了“遗传资源研发后的知识产权归属及其惠益分配的系列纠纷”,进而也使之成为当前一个急需研究解决的课题,已经引起了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广泛关注。无疑,从目的与价值追求看,相应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形成及机制运行已呈现出受控于处于强势地位的遗传资源使用及研发方的利益取向,从而影响对处于经济及技术弱势的遗传资源提供方的真实需求的关注。进而从根本上影响知识产权惠益在遗传资源提供方与使用研发方的合理分配及分享。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系列公正、有效的遗传资源利用及其知识产权惠益分享的国际条约与国内制度,另一方面,需要各国(尤其发展中国家)积极提升各自在“现代战略性资源——遗传资源”领域的保护及博弈能力。这无疑对于公平分享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惠益,提高各国保护遗传资源的意识及积极性,实现人类对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与此同时,从更深层次看,这也是对当前国家生态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重要检验,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生发于传统、深入到生态治理”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