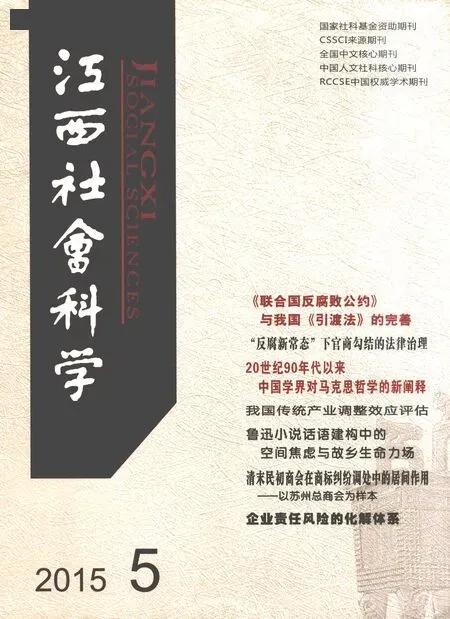土家族古代饮食文化体系与阶层性特征
■杨洪林 郭 心
饮食文化是一个民族外化于行的符号体系,历来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无论是具有人类学萌芽意义的中外游记作品,还是人类学成熟之后的经典民族志,都或多或少关注过饮食文化现象。以饮食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饮食人类学自二战以后在西方学界兴起,并逐渐形成唯物派、唯心派与政治经济学派等三大流派。虽然我国历史学、民族学界早有关于饮食文化的专题研究,但直到21世纪初才有西方饮食人类学相关理论的译介。经过十多年发展,我国饮食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成果数量偏少,理论建构不足等问题,“作为一门学科而言,中国的饮食人类学还相当落后”[1]。
从饮食文化探知民族文化的内在规律和特性是一个重要研究视角。“饮食文化在功能上、表象上对人类的生存和演变做了最为‘形而下’的表述、表达和表演,同时,其中也包含着深邃的‘形而上’的哲理、学理和道理。”[2]土家族饮食文化也概莫能外。土家族古代饮食文化指的是唐宋羁縻时期和元明清土司时期的土家族饮食文化。在土家族研究中,学界习惯将“从形成到改土归流的土家族早期发展阶段”称为 “古代”。[3]本文以此作为研究时限,还在于该时期土家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受中央朝廷治理方式影响,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之中,其文化主要按自身演进规律向前发展,没有经历改土归流后大量汉族移民文化的强烈刺激和官方的“文化改造”,其文化能呈现土家族文化的一些固有特点。本文无意通过饮食文化或食物研究来探寻土家族的民族边界,只希望能够呈现土家族古代饮食文化的概貌及其蕴含的意义、社会运行机制。土家族与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毗邻而居,很早就形成了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相似,文化互动频繁,很难以个别饮食文化事象划分民族的边界。但是,如果将土家族古代饮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它不但与其他民族文化有显著差别,还在民族内部呈现出阶层性特征。这种差别从古至今皆有,南宋庆元元年(1195)叶钱在为宋辅的《溪蛮丛笑》作序时,写到包含土家先民在内的五溪蛮“语言服食,率异乎人”[4](P336)。虽然他的言辞充满对少数民族的贬低和歧视,但也显示了宋时土家族与中原汉族在语言、服饰和饮食等方面的巨大差异。
一、土家族古代的饮食体系
土家族古代的食物来源于家庭种养和渔猎采集。渔猎采集所获得的食物在土家族古代饮食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特别是在收成较差的“荒年”渔猎采集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土家人世居于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武陵地区,虽然从地理上看属于 “腹里”,但由于自然生态屏障,“道路险侧,不可舟车”[5](P2-3),中央朝廷将之“弃同荒徼”。面对这种自然地理状况,土家族古代长期实行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方式,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粟、高粱、黍、荞麦、燕麦、大麦、小麦、蚕豆、黄豆、豌豆、绿豆、水稻等。乾隆《永顺府志》引《永顺土司志》载:“永邑山多田少,刀耕火种,食以小米、糁子为主。稻谷多仰永定卫、大庸所两处。”[6](卷十《风俗》)乾隆《永顺府志》也载:“山田多种露粟,以资民食,间植小米。”[6](卷十一《艺文》)据同治《来凤县志》卷二十九《物产》记载,糁子即粟。以上文献将同一物种的不同名称并列,说明该区域有多个品种种植。《容美纪游》①载,土民之家“虽有大米,留以待客,不敢食也”[5](P55)。可见,土家族古代以粟等旱地作物为主粮。
改土归流后,土家族的主粮逐渐被玉米取代。玉米传入土家族大致在清康熙至乾隆初年,乾隆二十年(1755)左右已成为土家族的主粮。[7](P160)除粮食作物外,土家族古代还种植蔬菜类的芥菜、萝卜、茼蒿、莴苣、油菜、韭菜、茄子、白菜、甜菜、芹菜、葱、蒜等;瓜类的冬瓜、王瓜、菜瓜、丝瓜、苦瓜、南瓜、西瓜、瓠瓜等;水果类的橘子、石榴、枇杷、樱桃、木瓜、花红、李、梨、桃、杏、梅、枣等;养殖的有猪、牛、羊、鸡、鸭、鹅等。
土家族古代通过渔猎采集的食物有野菜、竹笋、蘑菇、野果等山地植物及真菌;鹿、獐、麂、虎、熊、兔、野猪、野鸡、豪猪、竹鼠、蛇等飞禽走兽;鱼、虾、蟹、鳖等水生生物。容美土司在举行丁祭之时,献祭的有“羊、豕、鹿、獐、鹅、鹜、雉、兔、梅、李、榛、枣,凡有之物皆荐”[5](P52)。这些祭品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渔猎采集而来。在采集的食物中,土民常用的有葛粉和蕨粉,“葛粉为粮,腹易充”[5](P31),尤其是荒年,土民以之为主粮。顾彩在容美居住时,应招服役的土民所带的食物“以葛粉、蕨粉和以盐豆,贮袋中,以水溲之”[5](P55)。此外,渔猎采集的食物不仅种类多,数量也多。《山羊隘沿革纪略》记,改土归流前,接近容美土司的山羊隘“山则有熊、豕、鹿、麂、豺狼、虎、豹诸兽,成群作队,或若其性。水则有双鳞、石鲫、重唇诸色之鱼,举网即得,其味脆美。时而持枪入山,则兽物在所必获;时而持钩入河,则水族终致盈笥。食品之嘉,虽山珍海肴,龙脑凤髓未有出其右者。其间,小鸟若竹鸡、野鸭、凤凰、锦鸡、上宿鸡、土香鸡,真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之概……春来采茶,夏则砍畲,秋时取岩蜂、黄蜡,冬则入山寻黄莲、剥棕,常时以采蕨、挖葛为食,饲蜂为业,取其蜜蜡为赋税之资”[8](P489)。
但这种状态在改土归流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移民大量进入土家族聚居区开发,生态严重破坏,这些动植物逐渐变得珍稀起来。虽然土家族古代的田产主粮——粟的产量较低,很多人食不果腹,但因有渔猎采集食物作为补充,其食物种类相较于今天更多,饮食结构更复杂。萨林斯也认为,“在自然状态生活的那些人生活更好一些。因为他们能够享受大自然给他提供的更大的能量”[9]。这些食物为土家人提供热量、蛋白质、矿物质等维持机体运转所需物质。从这些饮食对象可发现,能否满足机体需要是土家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也显示出“食物在滋养集体的心灵之前必先滋养集体的胃”[10](P4)。
就人的生物习性而言,人是杂食性动物,每天都需要饮食。但人们在获取食物方面,存在季节和时间分布不均问题,需要保存食物,调节使用。土家族常用的食物保存方法有晒干、风干、腌制、烟熏及其他粗加工和深加工方法。晒干、风干主要用来保存粟、高粱、黄豆等种子类及根茎叶类食物。腌制是土家人将食物保鲜的方法之一,制作时将新鲜的鱼肉、猪肉等经过处理后贮藏在坛中或瓶中。《容美纪游》的作者顾彩在返程途中,曾食用过土司赠送的“瓶中鱼鲊,极美”[5](P101)。烟熏主要用于肉类食物保存。熏制加工既能利用热量蒸发掉多余水分,达到防腐目的,也能让烟雾的独特香味融入肉中,形成独特口味。仅《容美纪游》记载的烟熏食物就有虎头脯、干鱼、鹿腊、野猪腊等数种。此外,土家族古代制茶也用“柴烟烘焙”。
土家族聚居区是传统的茶区,“诸山产茶,利最溥,统名峒茶”,到土司地区贩卖茶叶的“茶客来往无虚日”[5](P90)。《永顺府志》载:峒茶“四邑皆产,而桑植为多。味较厚,土人不谙制造,柴烟烘焙,香气损矣”[6](卷首《上谕》)。顾彩的《采茶歌》也载:“采茶归去不自尝,妇姑烘焙终朝忙。须臾盛得青满框,谁其贩者湖南商。”[5](P48)这些茶叶除被当成商品出售外,也是土家族制作日常饮料的主要原料。粗加工后存储的食物主要有葛粉、蕨粉等淀粉类食物。葛粉、蕨粉都是从植物的根茎中加工提取。蕨粉的加工方法是将挖来的蕨根洗净后“于平石上击碎,合水置于缸中,以取其汁,随将根取出,俾净,融成粉以充饥”[11](卷十二《风俗志》)。葛粉的加工方法与之类似。深加工的食物主要是酒类,土司之家有酿造的白酒,一般土民之家有砸酒。这些存储食物的方法是土家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土家族古代的食物烹饪有煮、蒸、炒、烤等方式,烹饪调料主要是葱蒜等物,油盐醋酱较为稀少。煮是最为常用的烹饪方式,不仅主食、野菜等物用来煮食,茶水也用煮的方式制成。《容美纪游》载:“改火法依古行之,春取桑柘之火,则以新火煮新茶敬客。”[5](P55)还载:“二月中已有鲜笋可食……惜司中无油盐醋酱,不善烹饪耳。”[5](P32)明清时期实行食盐专卖制度,但土司地区被排斥在食盐专卖体系之外,难以买到食盐,以致“与人钱钞都抛却,交易惟求一撮盐”[5](P94)。土司之家尚且“无油盐醋酱”,土民之家更为稀缺。用蒸的方式烹饪的食品有蒸肉、蒸鱼等。烤的主要是一些新鲜的鱼虾、兽肉等。顾彩在路途中就曾与随行人员一起“取溪中鱼蟹,炙之下饭”[5](P103)。此外,土家人还有“水溲”、腌制后生食和直接生食的饮食方式。
在土家族的古代饮食体系中,“吃什么”首先是由自然环境和技术手段决定的,需要自然环境能够供给这些物品,并有相应的技术手段去获取;其次是人的主观能动选择,选择既能为机体提供热量、蛋白质、矿物质,也符合心理需要的食物。“怎么吃”不仅要它“有利于吃”,而且还要“好吃”。这两个看似非常主观的条件,其实质是人们适应生态环境的结果。
二、食物与土司治理
土司围绕食物控制开展社会治理。他们通过贡赋食物与中央朝廷保持向上的联系,通过馈赠食物维持与周边土司以及汉族人之间的横向交往,通过控制食物完成对官僚系统和土民的向下治理。
土司虽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但他也是地处边远的少数民族代表,无论是朝廷还是土司自己都有土司是“荒徼武夫,见闻僻陋”[5](P6)的认识。朝廷在采用隔离措施限制土司做大做强和土司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允许土司到京城朝贡,以体现朝廷对土司地区的治理。土司们也为了表达对朝廷的忠心,积极进京献贡。据统计,明代,湖北有48个土司进京朝贡,朝贡次数达348次。当时,朝贡次数较多的土家族地区土司,有容美土司47次,石柱土司46次,施南土司37次,酉阳土司34次,散毛土司30次。[12](P253)虽然朝廷为了应对土司越来越频繁的朝贡行为和越来越大的朝贡队伍,规定三年朝贡一次,每次启程不超过100人,进京不超过20人,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没有遵照此例。在朝廷与土司相处融洽的时期,一个土司一年数次朝贡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嘉靖七年(1528),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朝贡率领千人。”[13](卷三百十《湖广土司》,P7989)土司在入京进贡时,所携带的“方物”除了朱砂、水银、楠木、马匹之外,很大一部分是蜂蜜、羊、茶叶等地产食物。嘉靖元年十一月,礼部在奏议土官朝觐事时,涉及鄂西容美、忠建两宣抚司,皇帝允许“通事、把事、头目人等,止以马匹、方物多寡为差。凡进香、茶、黄蜡,每杠(扛)五十五斤,由布政司传送者,所赏生娟炤(照)数加”[14](卷二十,P577)。此外,至迟在明嘉靖以后,土家族地区的部分土司已有田赋定额。土司用食物——粟米抵缴赋税。如嘉靖元年施南土司的田赋额度为 “秋粮,粟米六十五石六斗一升七合七勺五抄”[15](卷二十)。土司通过贡赋这些食物保持与朝廷的联系,以示接受王朝的治理。
土家族的很多土司虽为“世仇”,但也是“世亲”。土司间以姻亲为纽带,通过馈赠食物,互相走访,来协调和平衡互相的关系,但有时土司之间的矛盾也可能因为所送食物数量不多,品质不高而激化。如“丙如(容美土司)即宣慰向大鹏(桑植土司)之婿,迎娶时,大鹏以责礼不备,尽篪使者之衣,夺其斧鬵”[5](P83)。土司之间订立盟约也通过“行歃血礼”,这种“吃”的形式来缔结。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一,保靖土司派干办舍人余星到容美土司处商讨结盟事宜,“丙如率舍把与之登坛,行歃血礼”,自后“保靖有难,容美救之;容美有难,保靖亦然”。[5](P83)土司与汉族人之间的联系通过食物来实现的机会更多。到容美土司、桑植土司、永顺土司地区贸易之人,多是因贩卖茶叶和食盐而来。“客司(容美土司)中者,江浙秦鲁人俱有,或以贸易至,或以技艺来,皆仰膳官厨,有岁久不愿去者,即分田授室,愿为之臣,不敢复居客位。”[5](P47)顾彩在容美土司游历期间,其饮食起居都由土司供给。其与土司见面当天“返寓仍送肴六簋,酒一壶,后为常”[5](P17),返程的时候,容美土司送“川马二匹,黄连二斤,峒被二床,峒巾十条,茶叶四篓,密饯二瓶,路菜十种及程仪”[5](P101)。可以说,土家族土司通过馈赠食物与周边土司及汉族人之间建立起了一张联系紧密的横向关系网。
土司对官僚系统和土民的食物控制首先体现在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上。土司地区的山林、土地都属于土司所有,虽然“其田任自开垦,官给牛具,不收租税”,但是“民皆兵也,战则自持粮糗,无事则轮番赴司听役,每季役只一旬,亦自持粮,不给工食”。[5](P55)一些不能“赴司听役”的土民,赋税“不从田亩征收,永顺名火坑钱,民间炊爨,每一坑征银二钱二分;保靖则名锄头钱,每一锄入山纳银三五钱不等;桑植则名烟户钱,与火坑钱相等”[6](卷首《上谕》)。土司治下的很多官员“名虽官任,趋走如仆隶”[5](P44)。土民不但自持粮食接受土司征调,还要接受下层官员的食物盘剥。“凡膏腴美产,尽为舍把占据”,“土官向日凡畜养蜂之家,每户每年征收蜂蜜、黄蜡若干”。[6](卷首《上谕》)“土司旧例,凡官舍往乡,所属头人俱按人户科派吃食”,“外来穷民来至土司地方挖山种地,该管舍把每年勒送钱米”,“每年每户派送食米,并鸡鸭肉肘”。[6](卷十一《檄示》)其次,土司通过操弄饮食禁忌,独享特殊美食。“洋鱼味同鲂鱼,无刺,不假调和,自然甘美,龙溪江所产也,民间得之,不敢蒸食,犯者辄致毒蛇,贵官家则不忌。”[5](P89)土民日常所食荞麦以苦荞居多,“甜荞不恒有,供官用”[5](P90)。再次,土司在盘剥土民食物的同时,也施予一些食物,以博得土民的拥戴。如每年五月十三日,容美土司以祭奠关公诞辰,“演戏于细柳城之庙楼,大会将吏与宾客,君(容美土司田丙如父亲田舜年)具朝服设祭,乡民有百里来赴会者,皆饮之酒,至十五日乃罢”[5](P78)。田舜年还在司治所在地中府正天泉发源处,“累石为茶灶,安铜铛,筒饮壁间水,注铛中烹之,满则塞其窦,将竭则又注,竟日饮千人,亦不竭”[5](P86)。容美土司还在中府设“小酒肆”,“即便诸将吏往来也”[5](P35)。
土司还有一套围绕饮食文化展开的内部治理措施。如田丙如虽然已袭职容美土司宣慰使,但其父田舜年在举办诗会时,因其“不工诗”,只得“专司酒食”。容美土司还令不认真学习的子女“与猪狗同食”;子女在藏书之所学习时,“家人送食盒至,悬绠他处,提而上之”[5](P65)。土司举办宴会(见图1),“客西向座,主人东向坐,皆正席,肴十二簋,樽用纯金。可笑者,于两席间横一长几,上下各设长凳一条,长二丈,丙如居首,旗鼓及诸子、婿与内亲之为舍把,及狎客之寄居日久者,皆来杂坐,介于宾主之间,若篦箕形。酒饭初至,主宾拱手,众皆垂手起立,候客举箸乃坐,饭毕,一哄先散,无敢久坐者。亦有适从田间来,满胫黄泥,而与于席间手持金杯者。其戏在主人背后,使当客面,主人莫见焉。(余至始,教令开桌分坐,戏在席间,然反以为不便云。——原注)行酒以三爵为度,先敬客,后敬主人。子敬酒于父,弟敬酒于兄,皆长跪,俟父兄饮毕方起;父赐子,兄赐弟,亦跪饮之。如他司土官在席,皆丙如与对跪相劝,君公然以父辈自居,不酬酢也。三爵之后不妨竟别,或兴至移席花下,则饮无算(席法亦不拘,或散坐,或踞石——原注)”[5](P45)。从座次排列和敬酒过程来看,土司举办的宴会是一个权力操演的场域,每举行一次宴饮就是对权力的一次操弄。

图1 土家族土司宴会场景示意图
诚然,土司在处理内政外交过程中有多种手段和方式,对食物的控制和操弄只是他们的手段之一,或许这种手段更为隐蔽。但是这种方式在土司的治理过程中却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土家族文化的整体面貌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饮食与土民生活
土家族古代人口占比最大的是土司治理下的土民。土民每天的生活基本是围绕饮食活动展开的,获取食物和享用食物是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土民获得食物之后,如何吃,以及喜欢怎么吃包含了深刻的文化意义。考察土民的饮食文化活动,发现土民具有生食的饮食遗风和共食群居的饮食文化特点。
人类饮食文化的开端都是从生食开始的。据相关研究,人类约在100多万年前的早期猿人时期才学会用火。在此之前,人类所食皆为生食;在此之后由于火种保存困难,取火技术落后,仍然有相当多的人过着生食生活。这种状况直至取火和火种保存技术有了巨大进步之后才有所改观。土家族在明清时期还有较强的生食遗风,如今也还有生食“残存”。《五溪蛮图志》记载:“屠牛羊类,先取肚肺,不濯洁生食。然后分割大块,以火燎毛,煨炙半熟供馔。”[16](第二集《五溪风土》,P71)这种生食遗风不仅在土民的日常生活中有所保留,在祭祀活动中也有体现。宋代,土家族地区的人们在祭祀仪式中首先进行的是 “呈生”。“呈生”就是用还未宰杀的牺牲祭奠神灵。《溪蛮丛笑》记载:“祭祀,必先以生物呈献。神许,则杀,以血和酒,名呈生。”[4](P341)
现今,在土家族聚居的母语存留区,还保留有一种“玩菩萨”的活态仪式。仪式由土家族敬神的人——“梯玛”主持,仪式祭词大部分用土家语演唱。仪式开始的第一个环节是“告家先”。“告家先”时,梯玛首先在堂屋面向神龛燃香、鞠躬,然后杀“养牲”。“养牲”是一头8到10斤的仔猪。宰杀时,刀手在堂屋中间面对神龛横放一条板凳,板凳下面放一个碗接猪血,随即将仔猪拖到板凳上宰杀。旁人要用火纸蘸一些鲜血。这些蘸血的火纸,一部分放置到梯玛用大方桌搭建的祭台上,一部分随即烧掉。梯玛介绍“家先菩萨是可以喝生血的”。刀手随后将仔猪提出堂屋,找一些柴禾将猪毛烧掉洗净,送到厨房。厨师将猪肉砍成几大块,连同内脏在锅里用开水“毛”一下,然后捞起来盛在瓷盆里,并在猪头上撒一些盐,备好之后就摆到祭台的正中央。“毛”就是煮到3、4分熟,猪肉收紧即可。梯玛解释“毛”一下而不熟透的原因是“家先以前是这样吃的”,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才高兴”。“家先”是对事主家已经去世的祖先的统称。传统仪式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存储器。土家族“玩菩萨”仪式中的饮食文化活动是土家人对祖先饮食行为和饮食习惯的集体记忆。
土民共食群居的饮食文化特点在日常饮食活动和祭祀活动中都有体现。土民的日常“炊爨之所”是“火铺”(也有“火炉床”、“火床”等称呼)。如今,土家族地区还有高低两种火铺存留。土家族的这种火铺在宋代的《溪蛮丛笑》中就有记载:“睡不以床,冬不覆被。用三叉木支阔板,旁燃火炙背。”[4](P341)这条文献只点明了火床具有供人们休息睡觉的功能,其实,火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饮食烹饪功能。明代的《五溪蛮图志》记载:饮食烹饪“在火炉床为之。如台基状,置火炉于中。一家大小饔飧在是,亲疏亦在是”[16](第二集《五溪风土》,P71)。饮食炊爨的火铺是土家人日常活动的中心,不仅吃睡在此,待客也在此。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楚南苗志》载:“以旁一间为卧室。置火床于室内,以木为之,其阔半室,床中穴孔。另用泥砖从地砌之,为火炉,乃炊爨之所。冬月,则合室男女坐床上,围炉向火,惟令尊长居上耳。客至,亦坐火床。夜则环炉以寝。临卧,用帐幔相隔。俾夫妇共被,以示区别。”[17](卷六《土志》,P220)这种围绕火铺形成的共食群居文化,改土归流后被汉族流官大加批判,永顺知府、鹤峰知州都发布过文告,严令土民改进。雍正八年(1730),永顺知府袁承宠发布《详革土司积弊略》文告,怒斥“半室高搭木床,翁姑子媳联为一榻。不分内外,甚至外来贸易客民寓居于此,男女不分,挨肩擦背,以致伦理俱废,风化难堪”[6](卷十一《檄示》)。流官们都希望利用手中的权力来 “移风易俗”,推行“大传统”,但历史表明往往事与愿违,“小传统”在传承过程中也有稳定性的特征,一种文化在日常生活中还能发挥它的功能时是难以强制变迁的。
土家族古代的饮品有茶、酒、砸酒等物。土家族地区是传统的茶区,茶叶资源丰富。土家人将泡茶与烹饪结合,发明了油茶汤。油茶汤的制作方式是将茶叶、豆干等物用油炸之后再用开水泡饮。酒在土司之家日常皆有,对于一般土民或许是稀罕之物。土民饮用较多的是一种名为“砸酒”的酒精饮料。因饮用时所用吸管材质差异,也有将“砸酒”称为“钩藤酒”“藤酒”“竿酒”“芦酒”的。《溪蛮丛笑》将其记为钩藤酒,“酒以火成,不醡不篘。两缶东西,以藤吸取。名钩藤酒”[4](P337)。《容美纪游》也记载:“以曲拌蒸,晒干收贮,买酒者汆之贮筒中,开水灌之,随用筒吸饮,已成美酒,吸完加水,味尽而止,名曰砸酒。”[5](P90)砸酒的制作方法与普通酒类的制作方式相似,只是在粮食蒸熟发酵之后不进行蒸馏,将酒糟和酒一起存储在密闭容器中备用。砸酒的酿造原料在古代主要是荞麦、高粱,改土归流后逐渐被玉米、糯米替代。明田汝成《炎徼纪闻》记载:“饮食恶草,以荞灰和秫粥酿为臭渖。”[18](卷四《蛮夷》,P55)清毛奇龄《蛮司合志》也载:“以荞灰和秫麋酿为败渖。”[19](卷一《湖广》,P350)土家人古代饮用砸酒的方法有一竿众人轮流吸,也有多竿众人一起吸。光绪《长乐县志》卷十六《杂纪志》较为详细地记载过土司之家用砸酒宴客的盛况。土民饮用砸酒的方式与土司基本相同,只是没有繁琐的宴饮仪式和奢华的菜肴。土民“以曲蘖和杂粮于坛中,久之成酒。饮时,开坛沃以沸汤,置竹管于其中,曰‘咂竿’。先以一人吸咂竿,曰‘开坛’;然后彼此轮吸。初吸时,味甚浓厚,频添沸汤,则味亦渐淡”[20](卷十二《杂志》)。西南的羌族、彝族、藏族、苗族等民族都有饮用砸酒的习俗,体现了西南民族有很多文化共通的地方。
土家族古代的很多祭祀活动有多人参与,祭祀完毕,所有参与人员在祭祀地点共同用餐。《楚南苗志》载,九月九日重阳节,“合村勷资设馔,倩巫祭土地神”,“祭毕,撒馔于庙前地上,列座共饮食之”。[17](卷六《土志》,P223)土家人不仅祭祀一村一寨的土地神后聚在一起共食,祭奠一家一户的家神也是如此。同治《恩施县志》载:“新葬之冢则于社前祭之,本家男妇及内戚偕往,祭毕,于墦间饮食。”[20](卷七《风俗》)如今,梯玛在举行“玩菩萨”时,做完“解一钱”的“起兵”仪式后,至“收回兵马”前,梯玛及其助手吃饭不能上桌子,只能在祭台前的地上。用餐时,饭菜用碗盛好,放在祭台前地面竹席上,梯玛及其助手们围绕饭菜蹲成一个圆圈,不用桌凳。这种饮食方式与土家族古代祭祀活动后的饮食方式有相似之处。
可以说,后世土家族饮食文化承接的主要是土民饮食文化。随着健康观念的普及,后世土家人转而食用熟食,但是由生食衍生而来的大块吃肉的饮食习惯仍有保留。在土家族的母语存留区,人们烹饪肉食时不放配菜。普通村民之家烹饪的腊肉,每片约有50克。他们认为只有用大片肉来待客“心才诚”。土家族共食的饮食文化特点也在后来的“为会头”中体现。以前,土家人的各种人生礼仪以及修房造屋都要请客送礼,名为“为会头”。21世纪以前,事主家“为会头”一般要为客人持续供应3天饭菜,客人送的礼物主要是稻谷、玉米、面条等食品。
四、结语
饮食人类学通常关注的是一个民族吃什么、不吃什么、怎么吃,以及喜欢怎样吃等饮食文化活动背后的规则和机制。土家族的“饮食文化与武陵地区特殊的自然与社会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21],在选择吃的对象时生态环境和技术手段是主要影响因素,在吃的方式上出现了社会分层。我们通常以权力地位将土家族古代的人们划分为土司和土民两个阶层。这两个阶层不仅在经济、职业、受教育程度、社会声望等社会分层因素上有巨大差异,而且在饮食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特征。这些特征既是社会分层的体现,也是社会分层的依据。土司阶层的“朝廷命官”和“荒徼蛮夷”的复杂身份认同,体现在饮食文化中就是他们既保持了相对于中央朝廷来说是“小传统”的文化因子,也彰显了相对于土民来说是“大传统”的文化要素。土民的饮食文化“小传统”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与“大传统”有程度不一的互动,但一些体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传统”得以长期保存。
注释:
①《容美纪游》为清顾彩所作,主要记载作者自康熙四十三年(1704)正月二十七日至七月初八日在容美土司游历期间的所见所闻,记述方式为按日逐条记载。该书是研究土家族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文献,具有人类学早期民族志作品的意蕴。
[1]陈运飘,孙箫韵.中国饮食人类学初论[J].广西民族研究,2005,(3).
[2]彭兆荣,肖坤冰.饮食人类学研究述评[J].世界民族,2011,(3).
[3]雷翔.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5,(2).
[4](宋)朱辅.溪蛮丛笑[A].五溪蛮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2012.
[5](清)顾彩.容美纪游[M].高润生,注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6](清)张天如.永顺府志[M].乾隆二十八年抄刻本.
[7]杨洪林.明清移民与鄂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甑学贤.山羊隘沿革纪略[A].容美土司史料汇编[M].鹤峰: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等,1984.
[9]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6).
[10](美)马文·哈里斯.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M].叶舒宪,户晓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
[11](清)李焕春.长乐县志[M].咸丰二年刻本.
[12]段超.土家族文化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15](明)薛刚.湖广通志[M].嘉靖元年刻本.
[16](明)沈瓒.五溪蛮图志[M].伍新福,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2.
[17](清)段汝霖.楚南苗志[M].伍新福,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8.
[18](明)田汝成.炎徼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清)毛奇龄.蛮司合志[M].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0](清)多寿.恩施县志[M].同治七年刻本.
[21]王希辉.土家族饮食文化变迁的历史考察[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