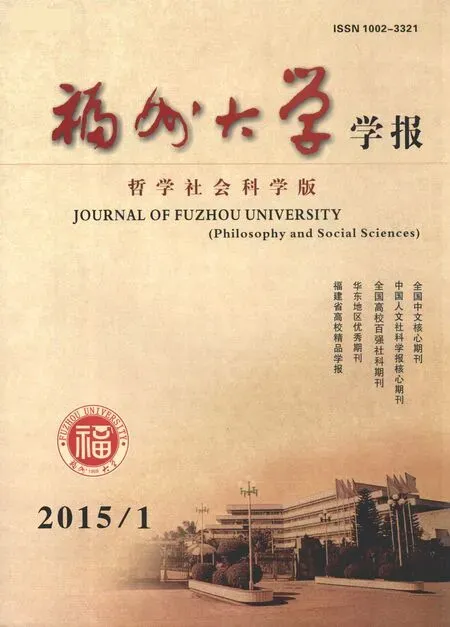对赌协议之性质及效力分析——以《合同法》与《公司法》为视角
华忆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对赌协议之性质及效力分析
——以《合同法》与《公司法》为视角
华忆昕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100088)
摘要:对赌协议是我国私募市场中一种常见的新型投资工具,其旨在通过估值调整机制维护投资人的经济利益。然而,由于我国《公司法》、《合同法》对于对赌协议规定的缺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对赌协议的性质和效力展开了广泛的争论。以《合同法》、《公司法》的相关规范为切入点,来分析对赌协议的性质及效力,以求在现行法下调和立法和实践的冲突,并寻求对赌协议的合法化路径。
关键词:估值调整机制;附条件合同;射幸合同;合同效力;合同履行
对赌协议于我国而言是一项舶来品,其英文名为Valuation Adjustment Mechanism (简称VAM),直译为汉语就是“估值调整机制”。对赌协议的实质是投融资双方对未来不确定事件的一种约定,根据约定事件的出现与否,来安排投融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关于英美法中对赌协议的具体内容,Kaplan和Strmberg的研究对此做了一个比较完善的整理,他们通过对美国自1987年到1999年14家风险投资企业(venture capital partnerships)对119家企业的213次投资合同进行研究后,将投资协议涉及到的常用的条款归纳为六类:包括财务绩效(financial measures of performance)、非财务绩效(non-financial measures of performance)、分红回购(meeting dividend of redemption payment)、企业行为(certain actions being taken)、证券发行(offering of securities)、以及创始人去留(founder staying with firm)等。[1]英语语境下,似乎并未有人对对赌协议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这大抵是因为对赌协议已成为一项司空见惯的投资安排制度,融入英美的投资市场之中。而在我国,对赌协议的发展仅处于起步阶段,其产生之初就成为了法学界、金融界热议的焦点。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对“海富案”[2]的宣判,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对赌协议究竟有没有发生异化,其属于何种性质的合同,其效力如何,又如何对其进行合法化规制更是成为了近年来合同法、公司法、金融法等部门法领域的热点问题。
一、对赌协议之存在价值
作为一种被我国私募市场广泛应用的新型金融工具,对赌协议的存在对于投融资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对赌协议的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投资方而言,对赌协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其经济利益。对赌协议之本质为一种估值调整机制,其通过合同的安排,以“多退少补”的形式保障投资方能够在其投资未达到预期效果时获得一定的股权、资金或其他经济或权利性补偿。而采用这一方式的制度原因为我国《公司法》及《证券法》对于投资方的保护不足。一方面,《公司法》对于优先股的规定尚属空白,投资方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只能以合同的形式与原股东达成一致,附加传统的优先股所带有的部分权利,要求公司和原股东做出书面承诺,使部分优先权在契约责任下得以实现。[3]另一方面,《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有着较为严苛的规定,而通过对赌协议约定补偿条款、回购条款能够成为投资方退出的替代路径。
2.对于融资方而言,对赌协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随着我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小企业对于资金有着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源于企业融资难问题,即(Macmillan Gap)[4],而其产生的原因在于资金的供给方不愿意以中小企业所要求的条件提供资金。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商业银行似乎更倾向于贷款给规模更大、效益更好的大型企业,中小企业难以从商业银行募得资金;另一方面,随着民间资本资金需求量的增加,民间借贷利率“水涨船高”,加大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这种问题之下,使用对赌协议,将股权或者资金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意义上的担保形式,增强融资方的信用,成为保证融资的手段。
3.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对赌协议能够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之活跃度。基于以上两点,对赌协议一方面保障了投资方的投资利益,另一方面迎合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能够激励和促进中小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经营管理。因而,能够促进资本市场中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投资效率,提高市场的活跃度。
二、对赌协议之合同性质分析
“不同类型的合同成立与生效的条件及法律效力等特点,将争议的合同归入相应的合同类型中,能够准确、便捷地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正确地适用法律”。[5]自对赌协议进入我国资本市场以来,关于其性质就一直众说纷纭,并未产生一种学说使这一争论能够定纷止争。纵观目前学者之文献,对于对赌协议的合同性质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对赌协议是一种射幸合同;[6]2)对赌协议是一种附条件合同;[7]3)对赌协议既是一种附条件合同又是一种射幸合同。[8]
(一)附条件合同与射幸合同之概念厘清
附条件合同的本质为一种附条件的法律行为,即“当事人在意思表示个附设条款指明一定条件,把条件成就(发生或出现)与否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发生或终止的根据”[9]。而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缔约时不确定,而且在缔约后完全因偶然的情事而决定的合同”[10]。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条件对于合同的影响这一本质问题上却存在很大差异。
1.条件的成立与否对两者的影响不同
在附条件合同中,根据所附条件为延缓条件或停止条件,法律性行为开始发生或失去效力。[11]也就是说,在附条件合同中,条件的成就与否影响的是合同的效力。例如,甲乙约定,若甲考上大学,乙将民法书赠与甲。此时,在合同签订后,合同处于成立未生效状态,仅有在甲考上大学时,该赠与合同才发生效力。
而在射幸合同中,若双方当事人无特殊约定,则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之时,合同即成立,而按照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例如,甲与保险公司约定,当约定的风险产生,则保险公司对甲进行一定的赔偿。此时,甲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于合同签订时成立且生效,风险的产生影响保险公司赔偿义务的履行。
综上所述,在附条件合同中,双方的权利义务是确定的,条件的成就与否影响的是合同的效力;而在射幸合同中,合同的效力是确定的,条件的成就与否影响的是双方的权利义务内容。
2.当事人干涉条件成就与否的后果不同
在附条件合同中,由于条件的成就与否能够直接影响合同的效力,从而影响当事人利益的实现,因此,实践中不乏当事人为了自身利益而违反诚信原则,“恶意阻止或者促成条件发生”[12]的情况出现。为了保护合同相对方的信赖利益,各国合同法均对这一情况作出了规制,例如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
而在射幸合同中,禁止当事人干涉条件的成就与否的规定却并非绝对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阻止条件的出现是为法律所倡导的。例如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可能通过加强自己注意的方式极力避免风险的发生,此时,不发生风险对于合同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有利的结果,这种“双赢”局面是法律所倡导的一个结果,因而,无需对其进行规制。但值得注意的是,射幸合同的“双赢”局面并不多见,在当事人恶意干涉条件成立与否损害相对人、第三人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情况下,法律依旧会对这种干涉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制。
由此,尽管附条件合同与射幸合同在形式上具有较大的类似性,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两者也难以区分,但两者在本质上却并不能等同。在本文中,对于两者概念的厘清有利于正本清源,准确判断对赌协议的性质,并依据对赌协议的性质判断其法律效力。
(二)对赌协议并非附条件合同
有学者认为,对赌协议的实质是投融资双方针对目标公司未来不确定的经营业绩进行约定,当约定情况满足时,有利于融资方的条款生效,当约定情况不满足时,有利于投资方的条款生效,因而,“对赌协议其实更接近于附条件的合同”[13]。本文认为,对赌协议在内容上并不符合附条件合同的特征,理由如下:
首先,从对赌协议的生效时间看,对赌协议在合同当事人签字盖章时即成立生效。一般而言,投资合同条款中往往包含“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生效”的内容,而对赌协议作为合同的具体条款之一,在没有特殊约定的情况下,其生效时间应当与合同整体的生效时间相同。由此可见,对赌协议中约定的条件仅影响投融资双方权利的实现与义务的履行,并不影响对赌协议的效力,因此,对赌协议并不符合附条件合同的特征之一。
其次,从法律对对赌协议中投融资双方对于条件成就与否的干涉的规制情况看,法律并不禁止投融资双方促进条件形成的情况。对赌协议的本质为估值调整机制,“投资者向某企业投资,相信不是为了一笔赔偿,而是希望将来企业的股权价值上升,投资得到回报”[14],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赌协议当事人之间具有利益的一致性。故,在对赌协议中,投融资双方促进约定条件达成,投融资双方“双赢”,法律对此并不进行干涉。因此,对赌协议不符合附条件合同的特征之二。
综上,对赌协议在内容上并不符合附条件合同区别于射幸合同的两个特征,因而,其不是附条件合同。
(三)对赌协议是非零和性的射幸合同
射幸合同在我国仅是一种学理上的划分类型,而并非法定的有名合同。因此,判断对赌协议是否满足射幸合同的类型应结合学理上对于射幸合同的定义以及域外法对于射幸合同的规定。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964条[15]以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1912条[16]对射幸合同的定义,可以总结出射幸合同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双方一开始就应当完全知道该契约的风险和交易规则”[17],在这基础上双方要有射幸意图,“即至少从表面上看,当事人明确具有侥幸冒险的意图”[18];2)“合同基础不确定,即作为合同基础的事件是不确定事件”[19]; 3)“法律后果不确定,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受该不确定事件的影响”[20]。
套用于对赌协议,投融资双方在对赌协议中已就风险和交易规则作出了约定,而从合同约定条款看,双方对于是否能够达到业绩目标具有侥幸意图,满足射幸合同的第一个特点;投融资双方约定的对赌条件一般涉及企业上市、业绩目标等几种类型,均属于不确定事件,满足对赌协议的第二个特点;而根据对赌条件的实现与否,投融资双方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将发生变化,符合射幸合同的第三个特点。由此观之,对赌协议应属于射幸合同之范畴。
然而,相较于博彩合同这一“零和”性的射幸合同,对赌协议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非零和性,即双方在利益追求上具有一致性。如前所述,对赌协议实际上仅是“法律人设计的一种交易结构,以保证在双方对估值无法达成一致时能够把交易进行下去”[21],其主要作用在于保障投资利益和促进生产经营。而无论是投资方还是融资方,其签订对赌协议的目标均是通过此种方式来促成交易,以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而并非从对赌协议本身获取利益。从这一点而言,对赌协议双方在合同利益上具有一致性。
三、对赌协议之效力分析
对赌协议作为股权转让合同的一种形式,对其效力的判断涉及合同法、公司法、金融法等多个方面。在海富案中,最高院以公司法为视角对对赌协议的效力进行了司法认定,然而,这一判断并没有为对赌协议的效力争议盖棺定论,而随着实践中对赌协议形式的多样化,对于对赌协议效力的讨论已然成为了司法适用之热点。
(一)合同与合同履行关系的厘清
“合同是指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22],只要满足合同签订主体适格、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内容合法即可认为其有效。而“合同的履行实质合同生效后,各当事人依照合同的约定为给付的行为”,对其合法性的判断应结合履行行为所涉及的具体部门法之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对于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把“合同行为本身违反禁止性规范与履行合同义务的行为违反禁止性规范严格区分开来”,不能以当事人对合同履行的不合法来否认合同行为本身的合法性。例如,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所有物品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但法律并未因此否认该买卖合同的效力。
尽管由学理观之,合同和合同的履行行为之间有着较大的差别,但从对对赌协议效力认定的实践情况来看,许多案例正是将两者混为一谈,以对赌协议履行行为的违法来论证对赌协议本身效力的瑕疵。本文认为,对于对赌协议效力准确判断的前提即为区分合同和合同的履行,将对对赌协议效力的讨论严格限制在合同行为本身的范围内。
(二)对赌协议的合同法及公司法效力分析
对赌协议属于合同的一种,其在有效要件上首先应受到《合同法》的制约。我国《合同法》分别在第52条和第54条中就合同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作出了列举式的规定。对于这两条的适用,对赌协议与其他合同无异,在此不再赘述。然而,合同法第52条第5款中作出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之合同无效的规定。这一条文就将对于对赌协议效力的判断由单纯的合同法判断引致公司法、金融法等其他部门法的判断上。本文认为,应在对赌协议几种典型条款的设计模型下,分别讨论其合法性。
1.股权对赌
股权对赌是指投资方与原股东之间根据合约安排互相转让股份。[23]其具体方式为:投资方和融资方先对目标公司的现有价值进行预估,并在此基础上协商设立企业未来的业绩目标。若目标公司未达到该目标,说明其价值被高估,则原股东应依照合同约定无偿向投资方转让一定比例的股权,使投资方在总投资资金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增大;反之,若目标公司达到了该目标,说明其价值被低估,则投资方应按合同约定无偿向原股东转让比例的股份,使投资方在总投资资金不变的情况下持股比例减小。国内较具典型性的股权对赌为浙商创投与普路通之间签订的对赌协议。[24]对于股权对赌的合法性分析应结合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其进行分类分析:
第一,投资方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公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依此规定,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之间可以自由转让股权,无需征得其他股东的同意。投资方在入股目标公司后即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因而其与原股东之间依据对赌协议产生的股份转让属于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行为,只受当事人自我真实意思的约束,并不存在违反公司法之情形。
第二,投资方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间的对赌协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依此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中,无论交易对方是否是公司股东,股东均可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其所持股份进行自由转让。与有限责任公司一样,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对赌协议的实质仍是一个附条件的股权转让合同,其并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因此,是合法有效的。
第三,《公司法》特别规定的限制股份转让的几种情形。《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对公司发起人、任职期间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转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25]若目标公司参与对赌的股东属于上述人员,则依照《公司法》规定,其股权转让具有一定的时间或数量限制。由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效力上的相对独立,在这种情形下,股权转让无法切实发生,但这并不影响对赌协议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中,《公司法》对于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都并未作出限制。由于股东之间的股份转让并不影响公司的资本状况,因而,其行为本身并不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而对于可能影响公司经营情况的发起人、董事、监事、公司高管的股权转让行为,公司法为保护债权人利益也通过对处分行为的约束对该行为进行了限制。
2.股份回购
股权回购的对赌是指投资方入股前约定如果在一定期间内无法达成预设业绩目标,那么目标公司股东或目标公司应该按照约定的价格回购股份。[26]强制赎回在商事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合同中回购条款的设置,其常见的条款设计为:例如海富案涉及的对赌协议中的部分内容就表现为这种形式。按照合同的签订主体区分,回购条款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投资方和原股东之间签订的回购协议。与股权对赌一样,这种情况的实质也是股东之间的股权转让,因而,无论是股份有限公司还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的回购都是为《公司法》所允许的。
另一类是投资方和目标公司之间签订的回购协议。对于这一种对赌协议形式,学界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海富案中,有学者对于最高院的再审判决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对赌内容之所以无效,是由于该条款使得股东有机会非法抽回出资,违背了公司法上的资本维持原则,侵犯公司债权人利益。[27]笔者认为,这一论述的实质是否认了当事人在商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公司法》分别于第七十五条和第一百四十三条就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况和程序作出了说明,因此,只要目标公司按照法定程序对公司股权进行收购便不违反《公司法》的强制规定。即,在合同签订之时,对于目标公司而言,股权回购并不属于履行不能的情况,也不必然导致抽逃资本行为的发生。对赌协议只是对投融资的权利义务和风险承担作出了规定,认定若目标公司无法达到业绩目标,则目标公司需要履行以合法程序收购股权的义务,并承担无法以合法程序收购股权的法律风险,并非强行要求目标公司为履行义务而违背《公司法》之资本维持原则。而至于目标公司采取何种方式偿还“对赌”失败之资金,属于目标公司的内部事务,与对赌协议的合法性本身无涉。
3.现金对赌
现金对赌是指投资方与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股东在对赌协议条款中约定:若目标公司未达到预期的业绩目标,则目标公司或目标公司股东需要给予投资方一定的现金补偿。
对于现金对赌的合法性,本文认为,其论证逻辑与股权对赌、股份回购类似,即,现金对赌条款仅就目标公司无法达到业绩目标的情况下对投融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及风险承担进行规定。在目标公司无法完成业绩目标的情况下,为融资方设定了资金补偿的义务,而对资金来源并未作出规定。即便融资方动用了资本公积金对投资方进行补偿,其实质也是融资方履行行为的违法行为,而并非对赌协议本身的不合法。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是在目标公司没有盈利产生的情况,也不能说明对赌协议的不合法。这是因为,在对赌协议签订之时,目标公司的盈利状况是难以确定的,而对于投资方而言,其所关心的是如何设计合同条款以保障其投资利益,而至于目标公司将以何种方式保障其投资利益并非是其关心的内容。因而,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而言,其并不会在对赌协议中涉及目标公司应以何种资金来对其投资利益进行补偿。笔者认为,以现金对赌为范式的对赌条款所约定的仅是一种风险承担,即目标公司认为其能够达到业绩目标,并同意承担其在未达到业绩目标的情况下无法以合法方式履行合同的不利益。而以对赌协议的结果去反推对赌协议效力的合法性在法律逻辑上是难以成立的。但必须承认的是,对于补偿款来源约定的不明确,确实使得对赌协议常常游走于“合法”的边缘,对其司法上的效力认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在对赌中以资本公积金偿还投资方补偿款的情形。尽管《公司法》并未明文禁止以资本公积金偿还投资方补偿款的行为,但依据资本公积金的性质分析,虽然其无需像注册资本一般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但是,作为企业所有者投资的一部分,其具有资本的属性,是一种资本储备。尽管法律上对资本公积金没有明确的规定,从实际上讲,其主要用途在于转增股本,巩固公司财产基础,增强公司信用。因此,资本公积金一旦投入公司即作为公司净资产,反映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不得任意抽取、支付给股东。否则,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提前分配了利润,导致企业资本规模的缩小,将损害到公司的财产和信用基础,从而侵犯到债权人利益。[28]本文认为,资本公积金主要来源于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即使向投资方返还这部分溢价款,也只不过是将公司“增资后形成的资产回归到其本来应具有的公允水平”[29],相比目标公司本应具有的价值水平,债权人的地位并没有被削弱。
四、结论
通过上文对于法律经济学、合同法、公司法等领域的展开讨论,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即在法律经济学领域,对赌协议有利于投资方维护自身经济利益,融资方满足自身资金需求,资本市场促进自身活跃发展;在合同法领域,对赌协议本身并不使用合同法第52条关于合同无效的规定;在公司法领域,违法之可能性主要存在于对赌协议履行之违法而并非对赌协议本身之违法,因而,对赌协议总体上在我国现行法上适法。
基于此,本文认为:司法过于宽泛地认定对赌协议可撤销、无效并不能禁止该类协议的产生,亦对于经济发展不利。司法在认定对赌协议可撤销、无效应当保持谦抑,认定无效、可撤销应当进行限缩而关注于一些较为关键的节点,并依此勾勒出对赌协议合法性的司法判断标准。
该标准在依据合同法进行判断时主要关注合同法上诚实信用义务的履行情况:其一,关注对赌协议的缔约程序是否合法,尤其是考察是否存在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情形;其二,对赌协议的估值调整条款中,估值调整的补偿数额是否相对于合同当事人当时的地位、财产状况过高,以至于有赌博之虞。
该标准在依据公司法进行判断时主要关注对于债权人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其一,关注对赌协议是否会引起抽逃出资,从而危害债权人利益;其二,关注对赌协议是否有违同股同权原则,从而危害中小股东利益。其中应区分对赌协议与对赌协议的履行行为,抽逃资本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融资方对对赌协议履行的不适法而并非对赌协议本身的不合法。而随着金融监管机构对于优先股的逐步认可,绝对的同股同权原则也正面临着挑战。
堵不如疏,在对赌协议已经日益普遍化、资本市场日益开放化的今日,一味地对其进行禁止,不仅难以使其得到有效的规制,反而将使其走入离岸对赌、地下对赌等规避法律调整的路径,从长远而言,将更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因而,本文认为,有必要在现行经济、法律模式下,对对赌协议之合法性进行有效解释,并进一步促进对赌协议之合法化发展。
注释:
[2](2012)民提字第11号,最高人民法院在这一判决中认为投资方与股东之间的对赌有效,投资方与目标公司之间的对赌无效。
[3]李有星、冯泽良:《对赌协议的中国制度环境思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第1期。
[4]Frost R,“The Macmillan Gap 1931-53”,Oxford Economic Papers,1954,pp.181-201.
[5][11][12][22]江平:《民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85,143,144,575页。
[6]谢海霞:《对赌协议的法律性质探析》,《法学杂志》2010年第1期。
[7]强力:《私募股权投资中对赌条款的性质和效力》,《中国审判》2012年第12期。
[8][13]胡晓珂:《风险投资领域“对赌协议”的可执行性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1年第9期。
[9][10]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98,507页。
[14]杨宏芹、张岑:《对赌协议法律性质和效力研究——以“海富投资案”为视角》,《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5]《法国民法典》在第1964条规定:“射幸契约是指当事人相互间的一种约定:所有的当事人或者其中一当事人或数当事人是获利还是损失,均依赖于某种不确定的事件。例如:保险契约;航海方面的高风险借贷;赌博性游戏与赌注;终身定期金契约。”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1页。
[16]2006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民法典》第1912条对射幸合同做出如下定义:“如因合同性质或根据当事人意愿,任一方的义务或者履行的程度取决于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则合同为射幸合同”。原文为:“A contract is aleatory when,because of its nature or according to the parties’intent,the performance of either party’s obligation,or the extent of the performance,depends on an uncertain event.”参见Civil Code-Louisiana State Legislature,http://www.legis.state.la.us/lss/lss.asp? doc=109159,2014年3月25日。
[17]黄风、罗马法:《射幸契约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杨振山、[意]桑德罗·斯奇巴尼:《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94页。
[18][19][20]陈传法、冯晓光:《射幸合同立法研究》,《时代法学》2010年第3期。
[21]彭冰:《“对赌协议”第一案分析》,《北京仲裁》2012年第3期。
[23][29]张先中:《私募股权投资中估值调整机制研究——以我国〈公司法〉资本规制为视角》,《法学论坛》2013年第5期。
[24]2008年8月,普路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与浙商创投、李菊香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书》中约定了利润承诺(业绩对赌)条款:如果公司2008年经认购方认同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税后利润大于或等于3,500万元人民币则公司上述股权比例维持不变。否则,公司大股东陈书智先生将按照如下情况将相应股份无偿转让给两位本轮投资认购方(浙商创投、李菊香) : (1)假设:2008年审计净利润大于或等于2,190万元,小于3,500万元,陈书智先生将转让2.5%股权给两位投资人,两位投资人按照投资比例分配这2.5%的股权。即:浙商创投分得2.333%;李菊香分得0.167%。(2)假设:2008年审计净利润大于或等于1,750万元,小于2,190万元,陈书智先生将转让5%股权给两位投资人,两位投资人按照投资比例分配者5%的股权。即浙商创投分得4.667%;李菊香分得0.333%。参考:春秋正道_XGL:“【IPO业务】近期企业境内IPO涉及对赌条款的案例总结”,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83760f0100ou5x.html,2014年5月1日。
[25]《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作出其他限制性规定。
[26]王云霞:《对赌协议的法律适用及风险防范》,《西部法学评论》2013年第1期。
[27][28]朱涛、李博雅:《“对赌协议第一案”中被遗忘的资本维持原则》,《法人》2013年第10期。
[责任编辑:石雪梅]
作者简介:华忆昕,女,浙江杭州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4-08-12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321(2015) 01-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