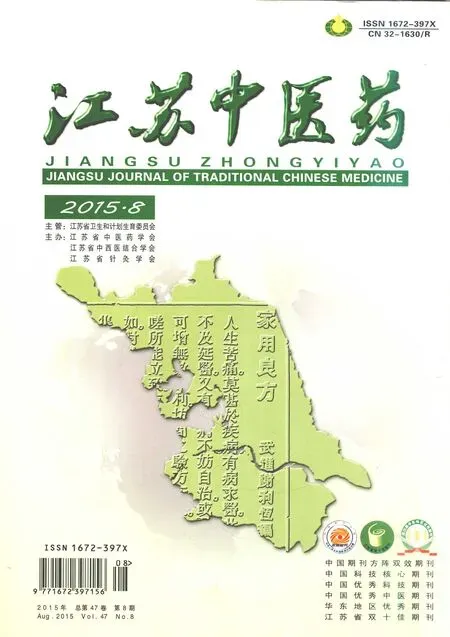苓桂术甘汤治验4则
丁艳霄
(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四科,湖北武汉430074)
苓桂术甘汤治验4则
丁艳霄
(武汉市东湖医院内四科,湖北武汉430074)
苓桂术甘汤 结核性胸膜炎 肝硬化腹水 中风 心包积液 验案
苓桂术甘汤出自《金匮要略》和《伤寒论》,由茯苓、桂枝、白术、甘草组成。《金匮要略》记载:“心下有痰饮,胸胁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伤寒论》也记载:“伤寒若吐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主要用来治疗痰饮引起的病证,笔者循“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古训,运用该方治疗结核性胸水、肝硬化腹水、中风后口角流涎、心包积液,效果确切,现报道如下。
1 结核性胸膜炎伴胸水
李某,男,58岁。2014年3月14日初诊。
右侧胁肋部胀痛1月。患者诉1个月前出现右侧胁肋部胀痛,在外院查胸片提示 “右侧胸腔积液”,行胸腔穿刺,抽取胸水发现结核杆菌。行正规抗结核和胸腔穿刺抽胸水治疗,胸水未完全消除,仍时感胀痛,口苦,食之无味。舌淡红、苔白腻,脉弦细。中医诊断:“痰饮”之“悬饮”,证属肝郁化热、伤脾生湿。治法:温化痰饮,健脾利湿。方以苓桂术甘汤化裁。处方:
茯苓、薏苡仁、黄芪各30g,桂枝、白术、当归、白芍、法半夏各15g,柴胡、甘草、生姜各10g。水煎服,5剂。
3月20日复诊:诉夜间尿多,起夜4~5次,胸胁胀痛大减,食欲好转,口苦消失。舌红、苔少,脉沉细。遂于上方去法半夏、柴胡,加枸杞、沙参、麦冬各15g,再投5剂。诸症俱消。复查胸片提示胸水消失。嘱患者继续正规抗结核治疗,并口服理中丸4丸,每日3次善后。多次随访,未诉不适。
按:结核性胸膜炎由结核杆菌引起,如出现咳嗽、咯血、潮热、盗汗,属肺痨范畴,肺痨多以阴虚为常见。该患者并无肺痨之表现,而表现为胸胁胀满、口苦、脉弦,颇似“小柴胡汤证”,但患者纳差、苔白腻、脉弦细,说明有脾虚生湿之像。患者右侧胸腔积液,《景岳全书》指出:“肺金旺于西方而主收敛,故其气藏于右。”《幼幼集成》也指出:“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阳从左升,阴从右降。”因此,本病病机与肝郁化热伤及脾、肺,脾失健运、肺失通条有关,故以苓桂术甘汤加减。方中茯苓、薏苡仁、黄芪健脾利水,同时还兼“培土生金”之功。桂枝、白术、当归、法半夏均为温性药物,遵“当以温药和之”之要旨。其中桂枝归肺与膀胱经,以宣肺气,气行则水行;柴胡理气,载药直达肝胆之位;生姜化饮;甘草调和诸药。因此,本病初期尽管有温热之象,借助此象配合温热之药,热热叠加,促饮速除,故见效甚快。二诊时,舌红苔少,考虑与温药太过及火热伤阴有关,故减法半夏、柴胡之温药,加枸杞、沙参、麦冬之养阴药,一为健运中土,斡旋中焦之枢纽,二为“阴中求阳”,三为补脾肾之阴,免伤阴太过。诸药合用,药证合拍,效果显著。
2 肝硬化腹水
巴某,男,54岁。2014年4月14日初诊。
腹胀、腹水2月。患者既往有慢性乙肝病史15年。2月前因感腹胀,查B超提示肝硬化、腹水。近10日来,腹胀加重,腹部胀大如鼓,双下肢水肿,不欲饮食,动则喘气,行动困难。舌质淡红、苔白滑,边有齿痕,脉沉细。中医诊断:“鼓胀”,证属“肝脾不和,水湿停留”。治法:调和肝脾,行气利水。予以苓桂术甘汤联合逍遥散加减。处方:
茯苓、黄芪、薏苡仁各30g,白芍、炒白术各20g,木香、佛手、当归各15g,红参、桂枝、柴胡、炙甘草各10g,薄荷、砂仁各6g。水煎服,先投7剂。
4月22日复诊:诉腹胀明显减轻,喘气好转,每日尿量约3000mL,频繁矢气。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上方去柴胡、佛手、薄荷,加沙参、麦冬、菟丝子、枸杞各15g,再投7剂。
药后复查B超提示少许腹水,腹胀消失,食欲好转。
按:肝硬化腹水属于中医“鼓胀”范畴。鼓胀为“风、痨、鼓、膈”四大顽症之一,说明本病为临床重证,治疗较为困难。《医碥·肿胀》曰:“气水血三者,病常相因,有先病气滞而后血结者,有先病血结而后气滞者,有先病水肿而血随败者,有先病血结而水随蓄者。”因此,本病是气、血、水杂合而致。利水药物多选用具有利水、行气作用的药物[1]。本病缘起肝郁气滞,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水湿内停。气滞则血瘀,“血不利则为水”,水、血不利则气滞更甚,如此则病情反复而加重,最终虚虚实实,治疗棘手。在治疗上要攻补兼施,气、血、水共治,缺一不可。本病病位虽在肝,但与肺、脾、肾密切相关。尽管患者水肿明显,《景岳全书·肿胀》所云:“凡水肿等证,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但是如从水肿入手,不能达到疏肝之功。而脾属中焦,为全身气、血、水交通之枢纽,从脾入手,可协调肝、脾、肾,疏通气、血、水。苓桂术甘汤温阳利水,逍遥散为调和肝脾之经典方。方中茯苓、黄芪、薏苡仁利水;木香、佛手行气;当归活血;红参、白芍大补脾胃之气,与木香、桂枝、柴胡、薄荷、砂仁相伍,补中有散,散中含补,此为攻补兼施之法。复诊时,患者症状好转,去柴胡、佛手、薄荷,防止行气太过,加沙参、麦冬健脾胃,菟丝子、枸杞滋补肝肾,遵“肝肾同源”之理。
3 中风后口角流涎
王某,女,52岁。2014年5月13日初诊。
患者有高血压病史20余年,肥胖体质。1月前突然出现口角歪斜,流涎不止,查头部CT提示“脑梗死”。经过针灸等治疗,无明显好转。舌质暗红、苔白腻,脉濡缓。中医诊断:中风后遗症,证属“脾虚痰饮内停”。治法:健脾化饮,活血利湿。方以苓桂术甘汤联合补阳还五汤加减,处方:
茯苓、薏苡仁、黄芪、地龙各30g,桂枝、白术、当归、川芎、赤芍、白芍各15g,桃仁、红花各10g,生姜、甘草各6g。水煎服,7剂。
5月21日二诊:诉仅夜间睡眠时少许流涎,口角歪斜略有好转。舌质暗、苔薄白,脉弦细。上方加红参、川牛膝各10g。再予7剂。
5月29日三诊:未再流涎。予补阳还五汤联合六君子汤、苓桂术甘汤等方制成蜜丸善后。
按:脑梗死属于“中风”范畴,结合该患者症状体征,当属于“中经络”。《素问·通评虚实论》指出:“仆击、偏枯……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患者形体肥胖,多湿多痰,痰湿阻滞经脉,故口角歪斜。《素问·调经论》说:“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痰湿循口角而出,故流涎。《灵枢·经脉》记载:“胃足阳明之脉……还出挟口,环唇,下交承浆……属胃络脾。”故使用苓桂术甘汤温化痰湿,补阳还五汤补气活血。方中茯苓、薏苡仁、黄芪健脾益气利湿,桂枝、白术温阳化饮。中风的发生,亦可因“风”“火”“痰”“瘀”“气”“虚”六类病理因素的变化而出现玄府流通障碍、玄府郁滞或闭塞[2],故用桂枝发汗解肌,通玄府。痰饮内停,必阻气血运行,故用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活血化瘀。但湿邪多黏滞,非灵动走窜之地龙难以消磨,故加地龙,以搜风剔络祛痰。二诊病虽有好转,但诸症仍在,加红参大补脾肾之气,川牛膝引水下行。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水利,水利则湿除。
4 心包积液
周某,女,45岁。2014年5月14日初诊。
患者尿毒症行血液透析5年,近1周感胸闷,活动后喘气,双下肢无水肿。查脑钠肽(BNP)正常,心脏彩超提示“心包积液”。舌质暗红、苔黄腻,脉弦细。中医诊断:“痰饮”,证属“脾肾阳虚”。治法:温运脾肾,化气行水。予苓桂术甘汤联合肾十味,处方:
茯苓、黄芪各20g,桂枝、白术、枸杞、菟丝子、补骨脂、淫羊藿、盐巴戟肉、盐杜仲、骨碎补、川断、仙茅、沙苑子各15g,红参、瓜蒌、薤白、木香各10g,生姜、甘草各6g。水煎服,先投7剂。
5月22日二诊:患者胸闷、喘气明显缓解,效不更方,再投10剂。
6月3日三诊:患者复查心包积液消失。再将上方化裁制成蜜丸以善后2月。嘱患者规律血液透析,控制水的摄入。随访至今,多次复查无心包积液。
按:心包积液是血液透析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与透析不充分、肝素的使用有一定关系,严重时可填塞心包,导致患者猝死。古籍《医贯》说:“心之下有心包络,即膻中也,象如仰盂,心即居其中。”《灵枢·胀论》也说:“膻中者,心主之宫城也。”可见,中西医均意识到心包的重要性。尿毒症透析患者多无尿或少尿,因此单纯利水之法见效较差,故予以苓桂术甘汤温化水湿。方中茯苓健脾利水;桂枝温通经脉,助阳化气;白术燥湿利水;“久病及肾”,肾为水脏,故配合李可老中医之经典肾十味,补肾精、温肾阳,以蒸化水液;红参大补元气,桂枝助红参之阳并化气,助瓜蒌、薤白宽胸散结,以行气滞;《灵枢·经脉》记载“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下膈,历络三焦”,故加木香通行三焦。此方补中有散,散中有补,故疗效颇佳。
苓桂术甘汤虽然主要治疗痰饮之证,但根据中医学之“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的理论,本方所治疾病颇多。本文中四个典型病案,皆与水湿痰饮有关。胸腔积液、腹水、口角流涎、心包积液等均为水邪的外在表现,究其病因,不外乎与肺、脾、肾有关,但均表现为虚实夹杂,因此水湿痰饮主要责之于脏腑虚损,正如《内经》所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血、水乃人体正常物质,其中某一项病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两项。治疗上还是着重调理肺、脾、肾,兼顾气、血、水。肺主气,脾生血,肾主水,故调理肺、脾、肾为本,治疗气、血、水为标。如此标本兼顾,则效果甚佳。方中茯苓归脾、肾经,调脾肾而行水;桂枝归肺经,化气行气血;白术归脾经,益气健脾、燥湿利水。另外,白术有收涩之功,可以防止桂枝发散太过。甘草归心、脾、肺、胃经,补脾益气,润肺,调和诸药。因此,苓桂术甘汤除温化痰饮功效之外,还有调气行血利水之效。临床上应详细参详,灵活运用,方能获佳效。
[1] 佟雪飞,郭海军.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治则方药浅析.江苏中医药,2014,46(1):65
[2] 何婷婷,陈维铭,钱涯邻.论缺血性中风血脑屏障病变玄府病机.江苏中医药,2015,47(1):8
编辑:吴 宁
R289.5
A
1672-397X(2015)08-0054-03
丁艳霄(1974—),男,本科学历,主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疾病。doctorbym@163.com
2015-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