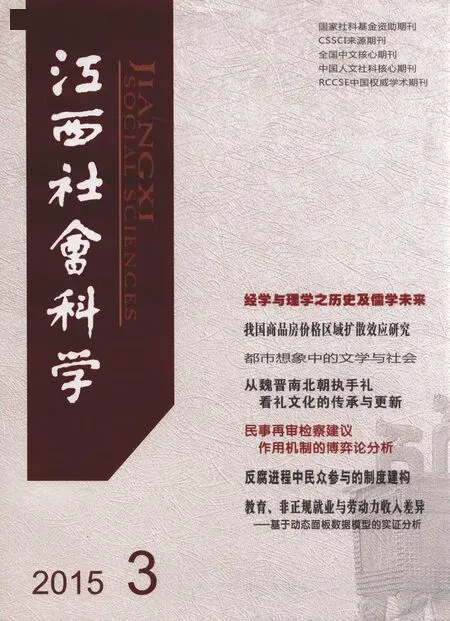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路径研究
李辞
我国刑事再审程序启动路径研究
李辞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被定义为纠错程序,而无论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还是实行职权主义的大陆法系,再审的主要功能都是为被判决人保留一条救济途径。我国刑事诉讼法允许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与控审分离原则相冲突,也有悖于既判力理论,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应当仅限于有利于被告人的情形。法院与检察机关对当事人申诉的审查是通过封闭的行政性方式进行的,当事人难以当面发表意见,而对申诉的听证化改造也并非解决申诉难问题的关键。检察机关应当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更多地受理、审查当事人的申诉,为审判中立提供外部保障。
刑事再审;再审的启动;控审分离;既判力;审判监督
李 辞,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8)
最近一段时间,于英生案、聂斌案、呼格吉勒图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再审及改判引发了社会的极大关注。从这些案件的纠正情况来看,再审程序大都是由检察机关发起的,应当说,检察机关在我国再审程序的启动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检察机关作为我国宪法授权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对生效裁判的监督正是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阵地,这种诉讼监督对冤错案件的纠正也至关重要。然而,同样有权直接启动再审程序的法院却为何很少主动提起再审?当事人通过申诉引发再审的情形为何更加难得一见?这些问题都与再审程序的职能定位存在紧密联系。有鉴于此,笔者拟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职能定位进行一番剖析,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路径进行一些理论与实务上的反思,并结合我国实践分析检察机关在再审程序启动中的重要作用。
一、救济还是纠错:刑事再审程序的职能定位
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即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时,通过决定或抗诉的方式启动的一种特别审判程序。将对生效裁判的重新审判程序称作“审判监督程序”,几乎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特有。法国将这一程序称作“非常上诉途径”,而德国、日本的再审程序大体上与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相当。
在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基于“陪审团的裁判视为真相”的理念,凡是陪审团作出的生效裁判,法院几乎无法更改。美国尽管允许在某些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对已决案件进行重新审判,但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限制之下,这种重新审判程序不得对被告人造成任何不利的后果。
在职权主义下的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也没有被打造为一种纯粹的纠错程序,在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再审程序甚至成为一种专门对被追诉人实施救济的诉讼程序。譬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禁止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即便是因为事实认定的错误而导致“实际有罪”的人被宣告无罪,也不得对该判决进行任何变更。[1](P556)日本的再审制度属于“非常程序”中规定的两项对已决裁判进行重新审判的制度之一,是一种“以认定事实不当为理由对已经确定的判决重新审理的非常救济程序”[2](P361)。这一定义说明,日本将刑事再审程序视为对被判决人的一种救济程序,因此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自然没有存在的空间。与法、日不同,德国刑事诉讼法则在原则上禁止不利于被告人之再审,但允许在几种特殊情况下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但即便如此,德国法许可的不利于被告人之再审,大体上都是基于原审裁判自身的问题。对于原审裁判生效后发现的“新事实”、“新证据”,只要不是来源于被宣告无罪人的自白,一概不得作为提起再审的理由。相较法国和日本而言,德国刑事诉讼法上的再审虽然体现了一定的纠错色彩,但并没有过分偏离保障被判决人利益的主线。
可见,不论是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英美,抑或是秉承“职权主义”的法德,在对已决案件的重新审判问题上,都持有这样一种立场:不得轻率启动再审,并且一般情况下再审不得对原审裁判作出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变更。总体上看,再审程序在西方国家被设定为一种对被判决人的救济程序。
不同于西方国家,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并没有区分有利于被判决人与不利于被判决人的情况。我国立法意义上的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在新中国时期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即已存在,该法第三编第五章对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主体、法定事由及审理程序等作了较为系统的规定。1996年《刑事诉讼法》大体上沿袭了1979年《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根据该法第204条,再审的法定理由包括:“(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该条所规定之再审理由的前三项都是由于原审裁判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存在错误,第四项针对的审判人员存在违反职务义务的行为,体现了些许程序性救济的意味,但通过“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字眼可以窥见,立法仍然更为关注生效裁判存在的实体性错误。
2012年《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项再审的理由——“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这是立法首次明确地将程序性违法作为再审的理由。但尽管如此,新刑诉法下的再审程序也绝非对被判决人的救济程序,各种包含“错误”字眼的表述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审判监督程序纠错的职能,只不过纠错对象从纯粹的实体性错误延伸至严重损害程序正义(可能影响审判公正)的错误。
刑事再审程序的职能定位乃是基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上长期奉行的“不枉不纵”、“有错必纠”之理念。[3]《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为了及时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行使诉讼职能时还必须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立法者试图通过对公检法机关的程序分工、确立依靠“事实”和法律的诉讼原则,使得犯罪人受到定罪科刑,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进而实现“不枉不纵”的诉讼目标。然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某些情况下“不枉不纵”可能“暂时”没有实现,诉讼活动可能冤枉了无辜的人,抑或是放纵了有罪的人,因此,有必要从反方向通过“有错必纠”来补救错误,以实现“不枉不纵”。在“不枉不纵、有错必纠”的理念下,我国的再审程序自然而然被塑造成了纠正司法错误的程序。至于法的安定性、人权保障等诉讼价值,在“不枉不纵”的“最高价值”和“有错必纠”的司法立场面前,都显得次要了。
二、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理论樊篱
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力,来源于《刑事诉讼法》第243条。根据该条前两款的规定,上级法院认为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确有错误”时,有权提审或者指定下级法院再审;各级法院院长对本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认为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的,应当交本院审判委员会处理。可见,有权发动再审的法院不仅仅是作出生效裁判法院的上级法院,各级法院对自身作出的生效裁判,只要认为确有错误,同样可以启动再审程序予以纠正。然而,尽管立法赋予了法院再审启动权,在实务中,法院主动提起再审却饱受诟病。由法院启动再审程序,存在三方面的理论障碍。
(一)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受到控审分离原则的羁绊
控审分离,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自1808年《拿破仑法典》奠定现代检察官制度以来,法官兼控诉权与审判权的纠问式诉讼模式便被彻底废除,检察官成了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专门机关之代表,扮演着法官裁判入口把关者的角色。在控审分离原则下,法院进行审判活动,必须以“诉”的提出为前提。在无人提起再审申请的情况下,法院主动启动再审,其本质是由再审法官庖代控方行使诉权,并审理自身提起的诉讼。这种情况下的再审程序无疑背离了“控审分离”的基本原则,甚至导致再审审判呈现出一定的纠问色彩。因此,在现代法治国家,再审的申请都是由检察机关或原审被告人向法院提出的。
然而,诚如林钰雄所言:“重大违误之判决若未予纠正,借由刑事诉讼程序所欲追求之法和平性,也是空中楼阁。”[4](P314)对于某些“确有错误”的案件,检察机关没有提起再审抗诉,当事人又未提出申诉的,如果法院拘泥于司法的被动性而不主动提起再审,并进行必要的改判,则显失公正。[5]特别是对于有利于被判决人的案件,保留法院启动再审的权力,也契合保障人权的理念。但即便如此,法院提起再审还是要受到控审分离原则的羁绊,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法院极少主动适用再审启动权。
(二)法院提起再审有悖于司法权的被动性
刑事再审程序的提起属于法院行使司法权的行为,与主动干预社会活动的行政权不同,司法权具有“不告不理”的被动性。纠问制度之所以要废除,并非只是为了将控诉职能从裁判职能中分离出来,纠问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法官主动司法,造成了被告地位的客体化。司法权之所以具有被动性,是因为一旦法官主动进行司法裁判,那么审判的中立就难以保障了。因此,在当今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中,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案例寥寥无几。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再审程序更多的纠错使命,在当前立法下难以完全禁止法院主动提起再审,但基于“被动司法”的理念,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法院审判的中立性,在再审启动权的行使上,法院应当秉持谦抑原则。同时,法院也不应当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进行再审,审理的对象是其他法院作出的裁判,上级法院是初次接触该案件,多少尚能保持一定的客观性和中立性。而法院对本院作出的裁判进行重新审判,集审判的发起者与裁判者身份于一身,审理的又是自己审理过并作出裁判的案件,那么连最底线的控审分离都无法满足了。
(三)既判力理论下法院不宜提起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
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是一项与英美法上“禁止双重危险”相近的诉讼原则。一旦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案件作出判决之后,判决即产生法律上的确定力,这种确定力被大陆法学者称为“既判力”,对于具备既判力的判决,法院不得进行第二次审判。大陆法系的既判力理论致力于维护法的“和平性”,这不仅是为了捍卫司法权威,更是为了保障公民(包括犯罪人)的“法律安全感”。人们不希望被犯罪行为侵犯,这是对“公共安全”的需求。而没有犯罪的人同样不希望受到国家的羁押、起诉甚至审判、定罪,这是对“法律安全”的需求。[5]即便是真正实施了犯罪的人,一旦被国家审判机关宣告无罪,便可从司法追诉程序中解脱出来。如果国家可以多次对其公民的同一行为进行审判,那么不仅被判决人的法律安全感将荡然无存,这种判决生效后的重复追诉行为也会导致社会一般公民的法律安全感落空。
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判力,法院只能主动发起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从理论上看,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本就损害了法和平性,也有悖于控审分离的原则。假使法院是出于对被判决人的权益保障,对被错误定罪的被告人宣告无罪或减轻被告人的刑罚,尚可谓是基于人权保障的理念不得不令法安定性作出价值让渡,那种不利于被判决人的再审除却权且兑现了实体正义的价值之外,便不具备任何价值可言。这种对实体正义的恣意苛求是以牺牲程序正义、司法权威、人权保障等诉讼价值为代价的,而实体上的正义,充其量只是刑事诉讼的外在工具价值罢了。为了追求外在价值而牺牲程序正义的诉讼内在价值,显然是本末倒置。
三、当事人申诉的效能不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申诉制度,确立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该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2012年刑诉法完整地保留了这一条文。1996年修法时,立法规定再审申诉制度是为了“赋予不服已生效判决、裁定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救济手段”[6](P482)。然而,申诉权显然难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救济途径,因为当事人提起申诉的,执行机关“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也不必然产生启动再审程序的法律效果。与一些国家的“非常救济”制度相比,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申诉制度显然效能不彰。于英生及其父母经过长达十余年的申诉,才终于得到一次重审的机会,呼格吉勒图案同样是经过了十年的拉锯才得以平反。其他冤案中的申诉中,当事人家属的遭遇也大体如此,聂树斌案中,在王书金承认其犯罪的情况下,聂母的申诉仍然无法获得一次再审的机会……
从一系列错案的纠正过程可以看出,与媒体的报道、普通公民的来信相比,当事人的申诉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待遇,其效力也便如同“信访”一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检察机关一旦提起抗诉,则必然引发再审。在引起再审的程序上,当事人的申诉在法律效果上处于比检察机关再审抗诉更低的层级。严格地说,申诉也不具备“诉”的性质和功能,法院、检察院对申诉的审查也往往是采取封闭的行政性方式进行,申诉人发表意见的方式仅仅是递交申诉状。对于当前我国再审申诉效力的问题,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以听证的形式对申诉进行审查。有学者提出:“接受再审申请的法院应以诉讼方式对此申请进行审查。为避免再审程序启动上的任意性和随机化,法院接受的无论是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还是当事人提出的申诉,都应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举行听证程序,并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开始再审的裁定。”[7]由于对申诉进行听证将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审判资源的紧张,有学者进一步建议构建律师代理申诉制度,即申诉原则上应由律师代为提出。[8]
以听证程序取代当前行政化色彩浓厚的申诉审查制度,是为了真正赋予申诉权以诉权性质。但在笔者看来,一旦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能够启动听证程序的申诉权,将对法的安定性造成极大的破坏。因为既然这种诉权的行使对被判决人而言不存在任何不利的后果,那么又如何能够遏制申诉权的滥用呢?这样状态下的申诉与上诉又有何区别?至于律师代理申诉制度,从理论上看,对于避免不必要的申诉似乎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我国,大多数刑事被告人都属于贫困群体,难以负担律师费用,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又不适用于申诉人,这样的制度对无力聘请律师的被判决人是否会产生一种待遇上的不公呢?何况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即便申诉由律师代理了,又能引起法院更多的重视吗?面对这些难以解决的实践困境,对申诉的“诉讼化改造”似乎并非解决当下申诉之问题的必经之路。
四、由检察机关提起再审的理论根柢与现实优势
在我国,检察机关与法院一样,是有权直接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3款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比被告人、被害人一方的申诉,人民检察院是以“抗诉”的形式提起再审,抗诉一经提出,则自然产生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法律效果。在我国,检察机关在再审程序的启动中享有独立的司法权。相较法院主动发起再审与当事人的申诉,在我国,由检察机关提起再审具备理论上的基础与现实中的优势。
(一)享有再审启动权是检察官客观义务的应有之义
在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被禁止提起再审,这固然是“禁止双重危险”理论的应有之义,从检察官诉讼角色的角度上看,作为诉讼一造之当事人,检察官对法官或陪审团作出的生效裁判惟有遵行,而不得享有僭越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又由于刑事追诉活动是以国家之力在对抗公民个人,出于“公平游戏”原则,检察官甚至无权对一审裁判提起上诉。英美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当事人主义”造成一个并不明显的弊端——检察官角色的异化,为了与辩方进行对抗或者达成辩诉交易,在实践中检察官即使掌握了对被追诉人有利的证据,也往往不会主动开示给辩方。对检察官掩藏证据的行为,立法上也不存在任何制裁措施,因为检察官在诉讼中被视为类似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法官自然不能因为原告不为被告说话而惩罚检察官。在对抗制诉讼模式下,一旦如果赋予检察官独立的再审启动权,势必对被告利益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与英美检察官的角色定位迥然不同,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官被视为负有客观义务之中立司法官,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检察官均得客观行使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上也存在诸多体现检察官客观义务的条款,如检察官不仅要收集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还要积极获取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检察官认为法院对被告人量刑过重得提起抗诉;等等。由于职权主义诉讼构造导致控辩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负有客观义务的检察官理应对被追诉人提供一定的“诉讼关照”,在被追诉人申诉效果不彰的情况下,假使检察机关认为生效裁判对被告人科刑过重,便有义务为被告人的利益提起再审抗诉。当然,考虑到对生效判决的抗诉有损既判力理论所带来的法和平性,检察机关应当审慎行事,尤其要避免将再审抗诉权当作一种“控诉支持权力”,而漠视其在控诉救济上的客观义务。
(二)我国检察机关启动再审有法律监督机关地位的理论支持
是否赋予检察官再审申请权与一国的司法语境存在密切联系,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我国允许检察机关提起再审抗诉就是违背诉讼规律的。我国的一个特殊司法国情在于:宪法授权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有学者诟病检察机关独立启动再审程序的权力,主张废止检察机关在再审抗诉中的特殊地位,使抗诉与申诉在引发再审方面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进而将检察机关的再审抗诉改造成为履行公诉职能的诉讼活动。[9]
然而,在笔者看来,只要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再审抗诉,无论抗诉是否必然产生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效力,都是在行使法律监督权,而非单纯的公诉权。在法理上,诉权行使一次就用尽了,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提起公诉并出庭进行指控后,已然用尽其公诉权。一旦法院作出了裁判,检察机关便失去了对同一行为的追诉权。立法赋予被告人上诉权乃至申请再审权,是基于对公民的权利救济理念。检察机关无论是行使二审抗诉还是再审抗诉,都不再是以公诉机关的身份参与刑事诉讼,而是凭借其法律监督机关的身份介入诉讼活动,自然无关控辩平等问题。况且在再审之诉中,检察机关同样要证明原判决、裁定确有错误,而被告人的辩护权相较普通的庭审程序丝毫未减,再审在庭审程序中也并未打破控辩平等的局面。检察机关享有再审抗诉权并非是基于其控方身份,而是来源于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作为诉讼程序的监督者,检察机关自然应当享有进行程序干预的司法权。
(三)检察机关启动再审有助于克服法院与当事人提起再审的缺陷
前文的论述表明,法院主动发起再审恐怕危及其中立地位,也与控审分离原则和刑事既判力理论相左;当事人的申诉则难以对再审程序的启动产生决定性效力。在这样的理论与实践背景下,检察机关无疑成为最适合启动再审的司法主体。为了使刑事再审程序保留基本的诉讼性质,又不对检察机关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地位造成损害,笔者建议对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权力架构进行整合,将法院与检察院的再审启动权加以区分。
因此,法院应当尽量避免主动提起再审,其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的情形宜限定于裁判生效后发现了新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可能被判无罪或被处以更轻的刑罚乃至免除刑罚。这样,那些原审裁判依据上的瑕疵就不能成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理由,即便再审是有利于被判决人的。当然,一旦发现了这种情况,被判决人并非无从救济,被告人可以通过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方式引发再审。由于法院基于控审分离原则一般不主动启动再审程序,再审程序的启动的常规方式便应当是通过检察机关发起,被告人与被害人的申诉也应当向检察机关提出。这样的再审启动方式既凸显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机关地位,又在一定限度上保障了被追诉人的权利,同时维护了法院的中立性。
五、结语
通过上文对我国刑事再审程序提起路径的分析与整合,笔者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法院主动发起再审的情形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法院依职权提起的再审程序不得作出对被告人更为不利的裁判;其次,禁止被害人向法院提起再审申诉,被害人的申诉只能向检察机关提出;最后,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理应在审判监督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检察机关在客观行使本已具有的再审抗诉权之外,还应当接受、审查当事人的申诉,为法院中立性的维护提供外部保障。
将再审程序设置成纠错程序,与我国刑事诉讼追求“客观真实”,坚持“有错必纠”的传统一脉相承。在这种“重实体、轻程序”的理念下,我国的再审程序常常被异化成一种对公民的重复追诉行为,使得我国的被告人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双重危险”,而是来自法院与检察机关的“多重危险”。焉知所谓“客观真实”、有错必纠”,不过是完美主义认识论构建的一个“乌托邦”,而对实体公正的恣意苛求,却实实在在牺牲了程序的正义。
[1](法)贝尔纳·布洛克.法国刑事诉讼法[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2](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张凌,于秀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
[3]李训虎.刑事再审程序改革检讨[J].政法论坛, 2014,(3).
[4]林钰雄.刑事诉讼法(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5]陈光中,郑未媚.论我国审判监督程序之改革[J].中国法学,2005,(2).
[6]陈瑞华.刑诉法:一部民权法,而非治民法[N].南方周末,2011-09-08(31).
[7]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8]陈瑞华.刑事再审程序研究[J].政法论坛,2000, (6).
[9]刘计划,李大伟.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两个司法解释——兼论我国审判监督程序的改革与完善[J].法商研究,2004,(3).
【责任编辑:胡 炜】
D925.3
A
1004-518X(2015)03-016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