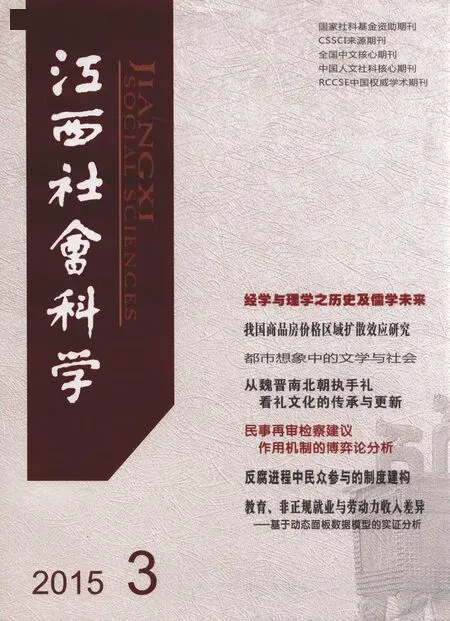论汉代礼学两种趋势的分别与融合
张涛
论汉代礼学两种趋势的分别与融合
张涛
汉代礼学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两种趋向多有分别,在汉代礼学发展中呈现出不同色彩,前人已作了充分论述。同时,汉代礼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礼,很多汉代礼学学者如叔孙通、后苍及庆氏一系经师兼顾古礼与今仪,共同显示出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表征,汉代礼学两种趋向的融合现象同样不能忽视。
汉代;礼学史;叔孙通;后苍;庆氏
张 涛,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后,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235)
汉代礼学存在偏重古礼研究和偏重当代礼制建设的两端,前者可称为汉代礼学的学术性趋向,而后者则是实用性趋向。两种趋向之间,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其区别体现在前者重古礼,而后者重今仪,前者学术性强而后者实用性强;但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融合的。笔者不揣浅陋,对这一现象加以描述分析,并尝试推究其因。
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汉代的礼学主要是指《礼经》学,即专门研究《仪礼》的学问,包括《仪礼》本经,以及当时尚未升格为经的二戴《礼记》等融合了古礼与后师学说的传记,相对于《周礼》为古学来说,又可称“今文《礼》”。由于《周礼》在两汉的大多数时期没有在官学中取得重要地位,汉代《周礼》学仅在私家流传,故本文专门围绕《礼经》学展开,并径称之为礼学。
一、学界对汉代礼学两种不同趋向的区分
《史记》言及汉代礼学发展时,有如下记载:
汉兴,然后诸儒始得修其经罼,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太常,诸生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于是喟然叹兴于学。……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1](P3761-3771)
《汉书》字句略同(唯“容”作“颂”,字通,《史记索隐》云音“容”),并补叙了萧奋以后的礼学传习情况:
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苍、鲁闾丘卿。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平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通汉以太子舍人论石渠,至中山中尉。普授鲁夏侯敬,又传族子咸,为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罽卿,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传业。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杨荣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荣琅邪太守。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桥、杨氏之学。[2](P3615)
历来研讨汉代礼学的学者无不重视《史》、《汉》的记述,主要观点也都由这两条资料生发而来。
现代学者中较早系统论述汉代礼学史者是洪业。1932年,洪氏为其主编的《〈仪礼〉引得》作序,根据《史记·儒林传》的记载对汉代礼学进行了分类:
(司马迁)叙述汉初礼学状况,至可致信。细玩《儒林传》文,礼学盖有三途。一曰,有汉朝廷之仪节;此叔孙通参杂古礼与秦仪之论著也。一曰,鲁人颂貌威仪之礼容;此徐氏父子门徒之所以为礼官大夫者也。一曰在孔子时已不具,迨秦火而益残之《礼经》;此高堂生之所能言,徐襄之所不能通,徐延之所颇能而未善之《士礼》也。[3](P78)
洪业言汉初礼学“盖有三途”:朝廷仪节之学、礼容之学和《礼经》之学。至于后来的礼学发展,他并未再作区分。自此后,少有探讨汉代礼学分类的文章,不过学者一般将之分为两类。
1944年,钱穆发表《两汉博士家法考》,其中第十节“宣元以下博士之增设与家法兴起”对汉代中期的礼学有所论述。在引录《汉书》中与前引《史记》大致相同的一段文字后,钱氏指出:“后苍以前,治《礼》者多善为容而不通经,其人率为大夫,不为博士。大夫与博士同为礼官,同属太常,而自有别。”[4](P209)尽管此处没有专论礼学分类,但观其文意,可以断言钱氏采用的是大夫、博士二分法,他所说的“大夫”对应注重实际操作的礼学学者,而“博士”则对应以传习《礼经》为业的学者。钱氏此处所论可能是受了清儒沈钦韩、王先谦的启发,沈著《汉书疏证》一书曾提出“博士、大夫皆礼官”。王先谦《汉书补注》流传颇广,该书引据沈说,还先于钱穆确认博士一职属于太常[5](P1523)。
1964年《武威汉简》出版,陈梦家所撰叙论谈及汉初礼学情况,也提到“当时只有讲究当世朝廷仪节的和行礼时善为仪容的礼官,少有专治《礼经》如博士伏生之于《尚书》者”[6](P13)。语意和钱穆相似,且已明确将洪业所分的前两项——朝廷仪节之学与礼容之学合并,并统称他们为“礼官”。
1990年,沈文倬发表《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一文,是现代礼学研究领域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下引沈氏语在此文内者,不再出注)[7](P503-558)。此文即采纳了二分法并将之推向极致。沈氏此文的一大目标是:
由于两汉学者对“礼”的认识很模糊,既没有分辨齐、鲁所传古礼与以秦仪为蓝本的新制汉仪有何不同,又与汉仪实行中派生的“容礼”混淆起来,以致史家对今文《礼》的传授,记事颇多失实,家法系统的纠葛亦未一一明辨;而后代礼家又踵误袭谬,罕有提出异议。对这些问题,自应钩沉索隐,切实探讨,力求回复它的本来面目。
沈氏根据汉代礼学前后期的不同特点,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初礼制草创和礼学在民间传授的时期,第二阶段是后苍传习今文《礼》并在征和年间(前92—前89)立为博士的全盛期,第三阶段是庆氏礼学的兴起和衰落。
在第一阶段,沈氏力辟叔孙通所代表的“汉仪”和徐生等代表的“容礼”,认为前者与礼学绝无关联,后者虽“与《礼经》传授颇多瓜葛”,但却分属两个系统。以后者为例,沈氏本来意识到,“从原来的意义上理解,不应该也不可能把礼与容截然分割开来”,因为容貌威仪本为礼典、礼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沈氏坚持认为:“秦、汉以来,古礼典不再举行,残存的在汉初只当作经书供学者们讲说研讨之用;而新创的汉仪尚未具有完备的规模,所用容貌威仪往往从古礼典里移植,善容成了个人的特长,可以不知经而在朝廷任礼官大夫、在郡国任容史。这样,《礼经》书本的传授者和汉仪的善容者分离开来,成为二个并列的系统。”
在第三阶段,沈氏从后苍弟子中割裂出庆普及其后学,认为庆氏一系只是从事汉仪的学者,“本来不应属于今文《礼》范畴”,与闻人通汉、大小戴及其后学徐氏、桥氏、杨氏等不同。章帝、和帝时代的曹褒习庆氏礼,《汉书》本传说他“慕叔孙通为汉礼仪,昼夜研精”,沈氏遂谓此人“完全继承了叔孙通的遗法”,进而推论其父曹充和同习庆氏礼的董钧,“三人是一脉相传的,都是叔孙通定汉仪的继承者。他们都不是今文《礼》的学者”,甚至说连庆普在内,“也属于叔孙通一流人物……都不是今文《礼》经师”。东汉庆氏学经师与其他礼学学者相比,表现出了较重实用的风貌,沈文倬认为庆氏礼学“以修订汉仪为内容”,虽然其师承与《礼经》学者有关,议论汉仪亦用古礼作缘饰。沈氏认为:
班固、范晔等分辨不清汉代礼学同时并存齐、鲁所传《礼经》和当时创制“汉仪”两个部分,又不明白今文官学不应容纳汉仪博士,在他们的书里作了含糊笼统、自相矛盾的记述,以致悬疑千载,一直得不到解决。其实只要辨别两种礼制的对立,这个疑案就涣然冰释了。
这样,沈文倬严格将汉代礼学分为两个系统,一是高堂生所创,后苍、大小戴等传承的今文《礼》经学博士,以古礼经传授为主业,学术性强;一是叔孙通和庆氏后学这样的汉仪博士,以及擅长容礼而未立博士的徐生等人,他们服务于当时朝廷,与古礼关系并不密切。沈氏认为两者必须严加分别。但较之前人,沈文倬之说有两点不同:一,前人论述多局限于汉初,沈氏将礼学二分说下延至东汉。二,前人仅认为汉代礼学存在二分的状况,而沈氏则鲜明提出汉代礼学的两个系统互不相容。前人之所以对两汉中后期礼学二分语焉不详,可能主要是因为《史》、《汉》记载寡少,不易详论,而沈氏则给予大量补正,坐实了礼学二分终两汉之世一直存在的观点,对于汉代礼学二分说是一个重要发展。
其实,沈氏在1982年连载于《文史》的《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一文,已表露出礼学二分思想的远源。在该文中,沈氏将平常笼统所称的礼或礼学划分为“礼典”(包括礼器、礼仪)与“礼书”两个层次,实践性的礼典记录下来,便成为礼书。由于文章重在论述先秦礼典的实际情况和考证礼书文本形成年代,并非为礼学分类而发,又由于所涉时代在汉以前,故所说与汉代礼学类别的用辞指向不一。但将礼学分为礼典与礼书,这一理念可谓给汉代礼学二分说提供了一个学术基点。无论如何,汉代礼学的两大系统区分,至此已划分得异常清晰。
二、汉代礼学两种趋向的融合现象——个案研究
必须指出,从本质上讲,汉代礼学的二分状况,不应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classification)之间的冲突对立,而应看成是汉代礼学学者身上所显示出的各具特色的两种趋向(orientation)。“实用性”与“学术性”常会共同体现在某个汉代礼学学者身上,尽管其人可能偏主一端;所谓的大夫与经师,并不是可排号入座、截然区隔的两个群体,而通常是兼具两种身份,至少能具备两种学养。汉代礼学的实用性与学术性两种趋向存在融合现象。试举两例。
(一)关于叔孙通
叔孙通为汉高祖订礼仪,是汉代礼学实用性的首位代表。不过,叔孙通的礼学含有较强的学术性。
首先,礼制方面,叔孙通采用秦仪,事实俱在,本为学界共识。秦代礼制的创建有很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在此无法详论,但可肯定秦代礼制绝不能凭空撰作。虽然在许多地方秦仪“不合圣制”,可是却必定像汉代一样对前朝有所因袭,《史记·礼书》就承认秦代礼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1](P1368)。非但礼如此,乐也如此,《汉书·礼乐志》记:“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五行舞者,本周舞也,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2](P1043-1044)据《通典》,秦人所谓“五行舞”,即西周《大武》[8](P3592)。采用秦仪绝不意味着必然与古礼乐对立。《史记》本传中言“(叔孙通说上曰)‘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于是叔孙通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1](P3278-3279)。可知制定汉仪时应有鲁地儒生赞划于其间(自然,鲁两生不在其列)。西汉建立后朝廷中尚存鲁地礼容之学,由此不难发现,叔孙通与齐、鲁所传古礼有不可磨灭的因袭关系。事实上,“汉兴,拨乱反正,日不暇给,犹命叔孙通制礼仪,以正君臣之位”[2](P1030),“正君臣之位”与《史记》所言“尊君抑臣”意同,刚好是古代《礼经》学精神的再现,其指向虽是现实,但其本质则极具学术属性。
其次,从礼学系统言,叔孙通本为儒生,初见刘邦时曾着儒服,还是孔子八世孙孔鲋的弟子,叔孙通的知识构成中无疑存在着经学,尤其是《礼经》的成分。叔孙通著作早佚,但从后人所辑的条文中还可以了解到他的礼学修养。如其《汉礼器制度》一书,唐人早有定评,《周礼·天官·凌人》疏称:“叔孙通前汉时作《汉礼器制度》,多得古之周制,故郑君依而用之也。”在三礼注疏中,引《汉礼器制度》来解释经文者尚多有之。叔孙通另一著作《傍章》中有“见羆变不得侍祠”一条,即是效仿《礼记·内则》所谓“夫斋则不入侧室之门”,清末沈家本认为此即“汉法之本于周礼者”,并称“说者谓汉礼全袭秦制,亦未考耳”[9](P1660-1661)。章太炎亦称:“汉律非专刑书,盖与《周官》、《礼经》相邻。”[10](P438)《史记》叔孙通传载惠帝春出游离宫,叔孙通曰:“古者有春尝果,方今樱桃孰,可献,愿陛下出。因取樱桃献宗庙。”[1](P3283)《会注考证》引《正义》曰,《礼记》云:“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荐寝庙。”[11](P1686-1689)语出《月令》,虽有“春”、“夏”字异,然叔孙通所说当即本于此。不论著作还是言行,都显示出叔孙通系统研习过儒家经典。虽然叔孙通后来热衷于政治,多从事礼制建设,而少做传经工作,但从后人的一些评价中可以看出,叔孙通应在礼学谱系中占据特殊位置。如刘向即称赞他“为汉儒宗”[2](P1034);魏张揖《上广雅表》云:“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12](P1276)“文不违古”即是肯定其符合古礼。清陈寿祺《左海经辨》甚至认为叔孙通撰集了《礼记》,“(百三十一篇之)《礼记》乃先秦旧书,圣人及七十子微言大义赖(叔孙)通以不坠”[13](P205)。皮锡瑞《论〈礼记〉始撰于叔孙通》亦因之附会说,今本《礼记》为叔孙通所撰[14](P64-65)。虽清人所论不免穿凿,但叔孙通礼学从古儒而来,其学术性不容抹杀。
洪业曾将叔孙通与徐氏区别开来,其实两者间颇有共通之处。所谓“鲁人颂貌威仪之礼容”应属“朝廷之仪节”的一部分,不可能离开礼仪的操作执行而单独实现,如果将礼容分离出来与“朝廷之仪节”并列,反倒破坏了礼学分类的层次,模糊了分类标准。而且,合并礼容与朝仪,也可在史籍中找到依据。汉成帝时刘向上书言“宜兴辟雍,设庠序,成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攘之容,以风化天下”[2](P1033),即把讲究“揖攘”的礼容纳入朝廷藉以风化天下的礼仪来讲。范晔作《曹褒传论》追述叔孙通定制汉仪,有“先王之容典盖多阙矣”之语,其中“容”“典”联文,“容”为容礼,“典”是指仪式进行时的礼节法则[15](P1205)。《后汉书·刘昆传》记刘昆在王莽时“每春秋乡射,常备列典仪……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云云,又说昆“少习容礼”,李贤注曰:“容,仪也。”两厢比照可知此处所谓“容礼”是以礼容来代指全部礼仪,非限于端正容貌之学[15](P2549-2550)。此外,叔孙通是薛县人,《索隐》云属鲁国,为汉廷制礼时尝“使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更表明叔孙通的礼学和徐氏“鲁人颂貌威仪之礼容”本为同源。他们和高堂生等以《仪礼》文本研究为主要学术内容的学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更侧重把礼学应用于实际操作,文本研究则非所长,至有徐襄甚且“不能通《礼经》”的情况出现。因此,钱穆和陈梦家将叔孙通、高堂生时代礼学分为两类的做法于分类原则更相适宜,也更为通行。
(二)庆氏及其后学、后苍及其师承
庆氏礼学是两汉礼学中颇具实用色彩的一支,但其本身则是两汉礼学学统中重要组成部分。
庆普资料较少,吕思勉言:“庆氏之学与二戴同出后苍。十七篇三家所同,而《礼记》为二戴所独,四十九篇又小戴所独,故(《后汉书·曹褒传》)加‘又’字以别之。陈氏(寿祺)谓褒所传四十九篇亦出庆氏,误矣。”[16](P733)据此可知,庆氏之学与二戴同源,而其后学更兼承小戴一系。东汉董钧、曹充等“习庆氏《礼》”、“持庆氏《礼》”,“于是遂有庆氏学”[15](P1201-1205、P2576)。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命曹充之子曹褒修礼,敕曰:“此制(引者案,指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让曹褒“依准旧典”来“次序礼事”以合于经,其不备者,则“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15](P1203)。这确为实用性汉仪,却又显然与学术性的《礼经》有所关联。
对于庆氏后学,史传多记其礼制建设功绩,但也提及其在经学方面成就。如曹充“作章句辨难”,明显涉及经学博士师法、家法的争斗。曹褒著作甚富,《演经杂论》百二十篇,沈文倬认为必然援引了《礼经》。曹褒授千余弟子,“为儒者宗”。他们参与过汉朝的礼制建设,就像在石渠阁、白虎观争论礼制的经师一样,治学的同时注重实用。
求索庆氏礼学的学统,就必须追到后苍。后苍礼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推士礼而至于天子”[2](P1710),这正说明了后苍礼学从学术出发,以实用为指归的特点。《汉书·儒林传》载:“(后)苍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服虔注:“在曲台校书著记,因以为名。”[2](P3615)《后氏曲台记》,汉志作“《曲台后苍》九篇”。颜注引如淳曰:“行礼射于曲台,后苍为记,故名《曲台记》。《汉官》曰:大射于曲台。”[2](P1709-1710)南朝任碢《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至若曲台之礼,九师之易”句,李善注:“《七略》曰:‘宣皇帝时行射礼,博士后苍为之辞,至今记之,曰《曲台记》。’”[17](P826)刘歆、如淳都点明《曲台记》与汉代射礼有关,与服虔“校书”说有别。《后氏曲台记》应该是结合《仪礼·大射》等经文对汉代礼典所作的传记。庆普后学曹充所立礼仪中,有“大射”一项[15](P1201),应当说绝非偶然,从后苍到庆普,再到曹充,其礼学表现出来的实用性与学术性相融合的现象,前后一脉相承。在融合今文《礼》与汉仪这一点上,庆氏礼学正可谓是渊源于后苍。事实上,汉志“经十七篇”句下班固自注云“后氏、戴氏”[2](P1709),分列后氏、戴氏,显系分家之后,而不数庆氏,可能就是将庆氏视为后氏今文《礼》的传经人;《经典释文序录》有“今庆氏《曲台》久亡”句[18](P107),将《曲台记》归于庆氏,当亦此意。
庆氏礼学出于后苍,后苍出于孟卿,而孟卿又出于萧奋。从郑玄起,学者便多认为萧奋是高堂生的弟子,典型的说法如《礼记正义》大题下疏引:“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亦谓“郑云‘五传弟子’,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戴德戴圣是为五也”。但覆按《史记》原文可见,其实太史公把萧奋放在了言礼为容的徐氏弟子间来叙述。洪业最先发现这一问题,在《〈仪礼〉引得序》中就认为郑玄等人的看法是“未细读《史记》之过”。四年后又作《〈礼记〉引得序——两汉礼学源流考》重申此说。洪氏论据为:
《史记》言,“奋以礼为淮阳太守。”句前,叙徐氏弟子也。句后又云,“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故而推论说,“依《史记》文气观之”,“是奋亦徐氏门徒,所传经亦徐氏之经”。[3](P96)此后一些论著如《西汉经学与政治》等,都延续此论[19](P101)。沈文倬则提出三条依据来反驳洪业:一是徐氏一系皆言“以容”,萧奋言“以礼”,二者不应混为一谈;一是萧奋再传弟子后苍是《礼经》大师,“容与礼既属不同系统,萧奋就不可能属于徐氏弟子”;一是洪业从《史记》文气作出的判断,沈氏给出了相反的解读。谨案,《史记》明言“(徐)延颇能(通《礼经》)”,又说“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表明徐氏学统中确实存在《礼经》学成分。设若认定萧奋是徐氏弟子,兼传礼、容,亦不悖于史文叙事,并能很好地解释萧氏后学既体现出学术性又具实用性的原因。
三、汉代礼学两种趋向融合的原因探析
以上通过考察叔孙通、庆氏后学等所谓“汉仪学者”具有的《礼经》学要素,重在从那些被认为倾向于实用的学者身上寻绎出若干学术性的特征,同时兼及后苍等人,指出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礼制建设,与叔孙通所作所为并无实质不同,两汉《儒林传》中以经义传习为主业的经师,也不乏实用色彩。在某种程度上说,汉代礼学这种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既有分别又有融合的特征,是由礼学特质所预先决定了的。
古代中国,所谓学术多半可称为“治术”。诸子百家之学,汉志谓其源出王官,而儒家尤得前代诗书礼乐以传教。王官之学主于实用,《礼记·王制》云:“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就是要培育可以经济邦国的人才。诸经之中,“礼”的性质尤为特殊。礼与《诗》、《书》等经典不同,本无意义自足的文本可供凭借,流传下来的《仪礼》一书所载皆为现实指向的礼典仪节,难以与实际操作脱钩。《左传》隐公十一年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桓公二年:“礼以体政。”杜注:“政以礼成。”襄公二十一年:“礼,政之舆。”杜注:“政须礼而行。”这些说法都明确显示了礼学与政事的密切关系。而许慎《说文》以“履”训“礼”,更点明礼学的实践意义。《汉书·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2](P1027)也还是突出了礼学的实用性。现代学者对此也有深刻认识,钱玄就曾以“经国济世,实践致用”八个字来概括古代礼学思想[20](P1)。而正是礼,在古代士大夫阶层形态混溶-分化-融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阎步克对此有深入研究。倘若借用阎氏的话语体系,叔孙通与高堂生的不同,便不是文吏与儒生的差距,而仅仅是儒生内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分别。“在两汉四百年的漫长历程之中,儒生与文吏之间既充满了矛盾、冲突,然而对立之中这二者又在日益接近,彼此交融”[21](P451),文吏与儒生尚且如此,更遑论同以礼学为宗旨的诸多汉儒。
汉代儒家经学立为官学,官学的精神并不在于研诵书本、计较文字,而侧重在实际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汉武帝“独尊儒术”,使经术与吏治的扭结大为强化,本质上成为一种划定知识标准基础之上的官方养士行为,标志着汉代在政治推动下学术整合的完成[22](P365-366)。尽管汉代确立了专门传授经学的博士制度,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学术自觉,但当时的学术仍不可能摆脱注重实用的倾向。汉廷一方面“独尊儒术”,促使儒学、经学不断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又每每“以经术缘饰吏治”,任官多选“通于世务,明习文法”的儒者[2](P3623-3624)。其实质即是将经术与吏治相结合,确立统治的合法性。
汉代经学在此氛围下,一开始就带有若干实用特色,并必然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致有学者认为以礼治国的传统肇始西汉。[23](P402-416)演化到极致,就是“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徐复观曾指出:“(汉廷)设置博士的原来目的,在使其以知识参与政治,而不在发展学术。”[24](P58-65)后来博士制度日趋完善,经学传习的作用逐渐加强,但仍未偏离汉廷设置博士的初衷;博士参与朝中礼制的讨论、建设本为份内之事,原无须别立所谓“汉仪博士”。所以,就连被沈文倬认作《礼》学博士正宗的小戴一脉经师也不能局限于《仪礼》的研究与传授,必须对实际政治有所顾及。汉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取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1](P1654),已不纯为古礼,更非《礼经》十七篇的内容,实在难以看出与所谓“汉仪博士”有何分别。倘若洪业对萧奋师承的看法得以成立,那么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情况,在汉初礼学兴起之际便已出现。无论如何,实用性与学术性两种倾向相互交织影响的礼学风貌,正是植根于汉代这一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土壤中。
前辈学者的汉代礼学二分说,为理解汉代礼学发展建立起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采纳汉代礼学二分说,并不意味着必然将汉代礼学经师严格划分为两个系统,应注意到,汉代礼学的两种趋向,既有所区分,又相互融合,不可截然割裂,汉初的叔孙通、西汉中期的后苍、后期的庆普和东汉的董钧、曹充、曹褒都有很具代表性的例证。汉代礼学的两种趋向,经常体现在统一为经世身上,汉代礼学的二分绝不能被视为是两类学术群体、两个学统的对立。班固、范晔看似“含糊笼统”的历史记述,正体现出史家客观如实地反映了汉代礼学的两种趋向。
[1](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洪业.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4]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清)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6]武威汉简·叙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
[7]沈文倬.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A].羈羉文存:宗周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考论[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9](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M].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0]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11](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2](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3](清)阮元.清经解(七)[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14](清)皮锡瑞.经学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54.
[15](南朝)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6]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南朝)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8]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汤志钧.西汉经学与政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0]钱玄.三礼通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21]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2]王刚.学与政:汉代知识与政治互动关系之考察[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
[23]华友根.西汉礼学新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
[24]徐复观.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M].上海:上海书店,2002.
【责任编辑:王立霞】
K203
A
1004-518X(2015)03-0132-07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