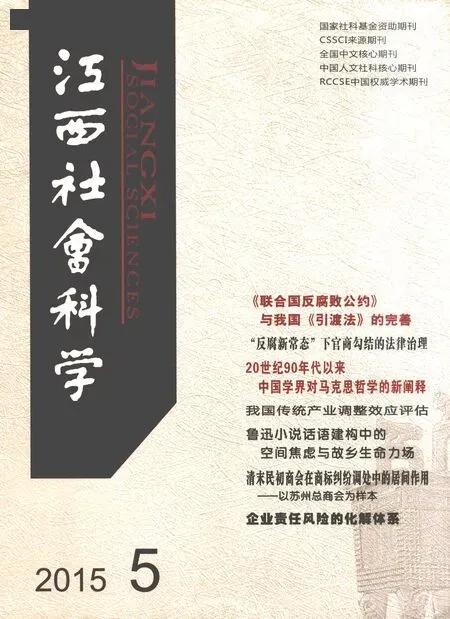史铁生作品中的神性理想及诗意建构
■邓齐平
一
在当代中国新时期作家中,史铁生是对国外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借鉴吸收得较为圆熟的作家。在史铁生的创作中,我们看不出像马原、余华、格非、苏童等作家早期创作中明显的模仿痕迹。在《命若琴弦》《礼拜日》《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中篇1或短篇4》《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等带有浓厚的形式主义探索意味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感受到史铁生扎根于现实土壤之中的鲜活的生命体验。
史铁生的这种圆融自在,来自于他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透彻理解。康定斯基谈到由点、线、面所组成的现代形式主义艺术说:艺术最终通向的是人的灵魂的“内在需要”[1](P45)。史铁生对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他是从人的灵魂的经验事实来理解现代主义的。如对博尔赫斯的理解,史铁生说:“我理解,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是指一个人的感觉、思绪和印象……他强调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作为主观的人的心灵,这才是一座迷宫的全部。”[2](P76)迷宫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史铁生把现实世界看作是心灵的迷宫。时间的交叉,空间的并存,是心灵的感应。所以,在史铁生的文学世界里,感觉是可以错位的,思绪是可以颠倒的,印象是可以混淆的。史铁生对普鲁斯特的理解也是独特的。他说:“普鲁斯特在吃玛德莱小点心时,一瞬间看遍了自己的一生。如普鲁斯特一样的感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过。”[3](P326)史铁生把普鲁斯特瞬间即永恒的生命体验理解为整体性的审美体验,即使是对美味的品尝,也是一种全身心的审美感受。这和史铁生对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的体验一样,他认为只有在审美过程中的体验,才会感受到生命真实的存在。人所占空间有限,玛德莱娜小点心所占空间更是微乎其微,但它能承载整个生命真实存在的感觉信息,它连接着一个人整个一生的漫长经历,它牵动着个体鲜活生命的万千思绪,它所超越的时间和空间是无限度的。
作为审美主体,对往事的回忆,普鲁斯特强调的是确证生命真实存在的喜悦,说明他是现实的;而史铁生看到的却是“脱离现实劳役进入艺术的欣赏”的诗意和美感,这说明他是抒情的。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命若琴弦》中的无字药方、《毒药》中的泡泡糖毒药、《务虚笔记》中的写作之夜、《我的丁一之旅》中的戏剧之夜等,都是可以连接起无限渺茫的宇宙人生的那一个 “奇点”,或者说是“起点”,犹如普鲁斯特审美视野里的马德莱娜小点心。作为艺术符号的象征物,它所唤起的是人的生命整体性的记忆和印象。所以,它能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突然唤醒一个人的全部生命活力和激情,甚至激活整个僵化的、死气沉沉的现实世界。所以,史铁生特别强调文学艺术把握的是每一个个体人的独具的心魂,它连接着纷繁复杂的万千世界。
使个体独具的心魂映现出无限浩渺的现实和历史,史铁生的整体性审美经验的表达必然会选择象征或隐喻的写作技巧,即:以部分象征整体,以具象隐喻抽象。无论是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还是普鲁斯特“玛德莱娜小点心”、加缪的西绪福斯神话、伍尔芙的“心灵漩涡”等,史铁生强调的都是对情感的激发和对灵魂的捕捉。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把这种混沌的情感或灵魂称之为“行魂”①,后来又把它概括为“虚真”。在“虚真”里,包孕着人的善、恶、美、丑等等人性中各种复杂的因素,人的兽性、神性、魔性都存在。因此,在“虚真”的心魂世界里,充满着林林总总的人生疑难和悖谬,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困惑。史铁生的写作,就是试图探秘、揭示“热气腾腾、变幻莫测的心灵漩涡”[4](P177)的奥秘,解开那令人困惑的疑难和荒诞。史铁生说:“写作从来就是去探问一个谜团。灵魂从来就是一个谜团。这一个‘谜’字有两个解:迷茫与
迷恋。”[5]对“行魂”、“谜团”、“心绪”的把握,实际上就是对“空”(“虚真”)的把握。史铁生说:“宇宙诞生前与毁灭后,都不是无,而是空……空不是无,空是有的一种状态。那么死也就不是无,死是生的一个段落。作为整体的人类一直是生生不息的,正如一个音符一个个跳过,方才有了音乐的流传。”[4](P172-173)与中国道家哲学的“空”“势”“造势”“道”等概念相结合,“虚真”也就是灵魂存在的可能性,这也是一种真实。人作为个体性的存在,必然要汇入人类整体之中才能“永恒轮回”地存在下去。“虚真”既是指个体心绪的真实,也是指与整体的人类连接在一起的向上、向善、向美的愿望或理想的真实。在人类整体存在的背景下,对个体心魂的捕捉,也就是以无限召唤有限、以神性引领人性。相对而言,具体的个体是有限的,作为整体的人类是无限的。有限是残缺,无限是圆满。于是,人的残缺和神的圆满就成了史铁生创作思维中的两个极点,人与神既对立又统一的世界就成了史铁生文学世界的基本架构,立足于人的残缺眺望神的圆满,同时又以神的圆满烛照人的残缺,从而形成了史铁生文学创作中独特的审美视野。
二
在史铁生的文学世界里,人与神既对立又统一,但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史铁生认为人与神之间、有限与无限之间、相对与绝对之间存在着永恒的距离,而这种距离由于是残缺与圆满之间的相互观照而形成一种审美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审美心理距离,是一种具有诗意的审美距离感。无论站在哪一个端点上去观照另一个端点,都是审美的观照、诗意的观照。又由于两个端点的绝对存在和不可能重合,使得两个端点之间相互观照的符号化表达,成为二者相互之间的象征或隐喻,即以人显神或以神喻人。以人观神,使史铁生充满对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敬畏之情,同时也使史铁生看到人世间造人为神的悲剧和闹剧;以神观人,使史铁生充满对人世间的悲悯情怀,同时也使史铁生看到造物弄人给人类造成的灾难和人类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命若琴弦》《毒药》《死国幻记》等作品直接采取寓言的形式,在人与神、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之间造成一种审美张力,从而使有形的琴弦和无形的目的、有形的毒药和无形的生命意志以及无声无息的“死灵”和温暖嘈杂的“光明”之间形成一种审美关系,并涵养出各自的审美境界,使具体的物象 (无字药方、毒药、死灵)各自具有抽象的象征和隐喻的丰富内涵,创生出独特的过程美学的审美意义。史铁生在《我的丁一之旅》中谈到西绪福斯神话时说:“有回我走上一条名为西绪福斯的路,那地方才叫荒诞呢!我们从早到晚地把石头推上山去,石头又滚下来,我们从早到晚地再把石头推上山去,石头又滚下来……直到有一天我从落日中看见了西绪福斯的身影,从天幕中读出了一个美丽的注释,那条路途也才变得美丽起来……”[6](P367)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上帝只管交给你这样一个现实,要你从无奈中找出一个美丽的价值,在人与神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建构人生的意义。
在神人冲突和神人融合的审美张力之间,史铁生找到了理想人性的合理限度。理想人性即神性。但由于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神,理想人性永远只能是虚拟的真实,即“虚真”。神或神性只是人在自我完善过程中的想象或虚构。尼采宣告“上帝死了”可人还活着,史铁生宣告上帝活着,但上帝永远在天上,上帝只是作为神灵运行于人世间,上帝活在人的心中。人神分裂是现实,人神同一是理想。史铁生说:“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残缺如人与圆满如神的永恒距离,惟此一条是原版的神说,因其无需人传,不传也是它。绝对的命令就听见了。”[7]这种“听见”是看不见而信的信仰。
树立神的标准和对神的召唤,源自于史铁生对自然人性的不信任。在与神的圆满的对照中,人的残缺的直接表现就是人性恶。史铁生认为真正的人性恶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追求和占有权力的欲望本能。他认为人有一种“控制异体”[8](P136)的古老恨怨,它使人不断地追求无限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造成人与人之间无休止的血腥暴力和精神虐杀。他说:“人性中,原是包含着神性与魔性两种可能,浮士德先生总是在。”[9]人的自然欲望本身无所谓善恶,但它更倾向于受恶的引诱,更容易陷入兽性或魔性的泥淖。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神性对人性的监督和引领是必不可少的。
人性解放的创作模式以揭露现实丑恶,张扬自然人性的合理性为鹄的。从 “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解放自然人性,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但是,没有神性指引的自然人性并不一定走向真善美,也有可能走向假恶丑。史铁生特别强调神性对人性的方向性指引。他说:“中国的文艺复兴,全是人性的解放,没有神性的冲动。‘人性解放’这四个字可不全是褒义呀。人性还有恶呀,全由着人性来,就糟糕了。”[10]树立起人性解放的大旗没错,但矫枉过正也需要警惕。史铁生看到人性解放的负面后果,始终警惕人性被兽性和魔性所控制,担心它使人只追求实利,及时行乐,使人成为行尸走肉。如果人性被魔性控制,出卖灵魂,为虎作伥,或控制他人、征服他人,就将导致极权专制、暴力、霸道等,伤害人类自身。《文革记愧》《她是一片绿叶》《钟声》《务虚笔记》《记忆与印象》《我的丁一之旅》等涉及“文革”的作品,展现的大多是这一时期人性荒诞丑陋的一面,都与史铁生对控制异体的权力意志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既然神人冲突是绝对的,神人融合是相对的,人与神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那么,人就不可能篡改神意,人就不可能僭越神位。史铁生说:“世界是一个整体,人是它的一部分,整体岂能为了部分而改变其整体意图?这大约就是上帝不能有求必应的原因。这也就是人类以及个人永远的困境。”[11]神的“整体意图”不可改变。在神的“整体意图”中,人只能是丑弱、残缺的。因此,在史铁生的创作中,没有伟岸崇高的英雄人物形象,丑弱的人、残缺的人的生命形态成为史铁生倾注全部热情来加以表现的主要对象。如《命若琴弦》中的大、小瞎子,《毒药》中的自杀者,《原罪·宿命》中被“种”在病床上的截瘫者,《钟声》中的“古典派肖像画”似的姑父,《关于一部以电影做背景的舞台戏剧之设想》中死了七天的酗酒者,《务虚笔记》中的自杀者教师O、一夜白头的医生F、残疾人C、Z的异性姐姐M、葵林里的女人,《死国幻记》中的众多死灵,《记忆与印象》中的人形空白的姥姥、姥爷和颤抖的二姥姥、恐惧的老姑娘,《我的丁一之旅》中的姑父等等。我们可以把这种类型的人物形象概括为受难者形象。
史铁生笔下受难者的形象是一群受苦受难的弱者形象,他们的原型是《圣经》中的约伯和圣子耶稣。如《奶奶的星星》中的奶奶,《山顶山的传说》中的瘸子,《命若琴弦》中的老瞎子和小瞎子,《我之舞》中的十八、世启、老孟和路,《原罪·宿命》中的莫非和十叔,《中篇1或短篇4》《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两个故事》中的叛徒、流氓,《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的酗酒者A,《老屋小记》中的B大爷、U师父,《记忆与印象》中的老姑娘、二姥姥、人形空白的姥爷、叛逆的大舅,《老好人》中的老好人等。还有一批是处在父母亲情和自我爱情选择的两难境地之中的受难者形象,如《老屋小记》中的小三子,《务虚笔记》中的导演N和医生F、残疾人C、诗人L等。
在所有受难者形象中,史铁生尤其对叛徒形象的心魂世界予以非同寻常的精细描摹,表现出史铁生对叛徒的深切同情。在史铁生看来,世俗的对叛徒的憎恨和贬斥,表现的正是人性的虚伪和残酷。在神性的视野里,史铁生沉痛地反省有关叛徒的话题,解构的是千万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为野蛮、残酷和虚伪的一面,为叛徒呼吁人道意义上自由、平等的权利,从而使叛徒形象成为史铁生表达神性理想的重要符码。
被损害、丑弱、残缺的受难者形象,在史铁生的创作中不是主要人物的陪衬,更不是插科打诨的小丑,他们本身就是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主要审美对象,是史铁生建构自身文学世界的核心要素,他们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史铁生创作的重大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审美风尚的重大转变。
三
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12](P30-31)雨果把美丑既对立又统一的观念看作是浪漫主义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相区别的标志。他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优美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合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这种天才丰富多彩、形式富有变化,而其创造更是无穷无尽,恰巧和古代天才的单调一色形成对比;我们要指出,正应该由此出发以树立两种文学真正的、根本的区别。”[12](P32)雨果的这一宣言,在文学史上具有开天辟地、开辟蒙荒的意义和价值,此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王尔德的《莎乐美》等,开始直面人类精神的黑洞,揭示人类魔性的恐怖,表现现实多样化的真实,从此开启现代审美的基本范式。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与雨果有着大致一致的说法。他说:“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与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么?……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行为,也都可以统统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会怎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条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13]史铁生的这段文字与雨果一样,也是对单极化的崇高美的否定和对世俗化的美丑并存的现实真实的肯定。所不同的是,雨果借此而肯定了“滑稽丑怪”作为美的存在的合理性,而史铁生则进一步地确立了残缺作为美的存在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宣告了对于完美、圆满的古典美的追求幻象的破灭。既然美人、智者、英雄、佛祖只能相对于丑女、愚氓、懦夫、众生而存在,离开前者就不可能有后者,完美和圆满就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之中,现实生活中永远也不可能单独地存在完美和圆满。
如果说雨果颠覆的是古典主义时代的审美规范,那么,史铁生解构的则是英雄时代的神话。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在审美领域里发现被遮蔽的残酷的现实真实,即“丑的美”②。丑或者残缺美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审美意识从先验观念向经验感性的转变,也标志着人类审美意识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史铁生文学创作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他在经历“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实现了这种转变,从而使他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代表性作家。
残缺美是史铁生以生命为代价感悟和体验到的美感经验,具有触及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但是,当有学者用“残疾主题”、“自卑情结”和“宿命意识”来解读史铁生的创作时[14],却遭到了史铁生委婉的否定。他说:“‘残疾’问题若能再深且广泛研究一下,还可以有更深且广的意蕴,那就是人的广义残疾,即人的命运的局限。”[15]“人的广义残疾,即人的命运的局限”,说的意思是:残疾是人的抽象本质,残缺指的是人命运的局限性。后来,史铁生更明确地说:“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9]从病理学的残疾中剥离出来,抽象地观照人性,史铁生发现人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完全不受限制的存在就只有造物主即神的存在。因此,只有在神的视野里,残疾作为人的抽象本质方能与神的圆满形成对照,从而形成审美距离感,产生审美效果。
用神性烛照人性,史铁生看到的是人性中的兽性和魔性,是人性恶,是人性的残缺,比如造人为神、极权专制、控制异体、人定胜天等等。与受难者形象类型相对应的,在史铁生的创作中还存在着可怕者类型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可怕者人物形象身上,史铁生看到的是人类可怕的兽性和魔性的膨胀。在《奶奶的星星》《务虚笔记》《记忆与印象》《想念地坛》《我的丁一之旅》等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是那个可怕的孩子的形象。可怕的孩子特别擅长于拉拢、打击、孤立对方,擅长于奇迹般地抓住人的弱点加以无情的攻击。他能抓住战神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在古典意义的争斗中,能致他人于死地。可是,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弱点恰恰是人性的表现,攻击他人的弱点、缺陷乃至残疾是极不人道的表现。与斗争哲学相反,神性的关怀恰恰表现在对弱势群体、对人自身的弱点、缺陷和残疾的尊重和呵护上。可怕的孩子的形象是20世纪以来极权专制者的雏形。在《我的丁一之旅》中,史铁生说:那个可怕的孩子获取权力的途径,是“人之罪恶的最初范本”,更令人恐惧的是“那个可怕的孩子已然成长得无比强大,已然漫漶得比比皆是,以致人间的一切歧视、怨恨、防范与争战中,都能看见他的影子”[6](P88-89)。 这是诗人史铁生的敏感,那个可怕的孩子形象已经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小孩,而是诗学意义上的幽灵,它已经飘荡在人世间,成了征服者的象征,也成了炫耀某种神秘力量(如权力、魔力、战争等)的幽灵的象征。
与此同时,史铁生也看到了人性中引人向上和向善的力量。即使是上帝弄人,那也是上帝对人的考验,是神性对人性的检验。比如西绪福斯神话、受难的约伯、受难的圣子耶稣、瞎子的无字药方等等。尽管人性的根基是欲望,但欲望既有可能使人成为魔鬼的代言人,也有可能使人成为上帝(神)的代言人。所以,史铁生一再强调:“人与神有着永恒的距离,因而向神之路是一条朝向尽善尽美的恒途。”[4](P156)“神即是现世的监督,即神性对人性的监督,神又是来世的,是神性对人性的召唤。……神性的取消,恰是宣布恶行的解放,所以任何恶都从中找到了轻松的心理根据。”[4](P49)
维护人与神之间的永恒距离,使神性既是人性的监督,也是人性的牵引。史铁生的写作既否定人欲望丛生的魔性,也否定造人为神的人的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史铁生认为:“人的价值是神定的标准,即人一落生就已被认定的价值。想来,神的标准也有上下线之分,即‘下要保底’——平等的人权,‘上不封顶’——理想或信仰的无限追求。所以,人除了是社会的人,并不只剩下生理的人,人还是享有人权的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人。”[16]这就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狂妄和造人为神的虚伪,也拒绝了人对以社会价值作为衡量标准的所谓成功人士、社会精英的无原则的赞颂。站在神性的高度审视人性,使史铁生对人类兽性、魔性的洞察,异常敏锐,对由于人性的残缺所带来的人的命运的局限,也看得更为清晰。同时,他也对由于神性的牵引所产生人类奇迹,更是惊羡不已。如《命若琴弦》《毒药》《死国幻记》等。
注释:
[1](俄)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M].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史铁生.随想十三[A].史铁生散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史铁生.记忆迷宫[A].史铁生作品集(第3卷)[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4]史铁生.信与问[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5]史铁生.地坛与往事[J].十月,2008,(2).
[6]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7]史铁生.给王朔的信[J].收获,2012,(1).
[8]史铁生.私人大事排行榜[A].史铁生散文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9]史铁生.病隙碎笔2[J].天涯,2000,(3).
[10]史铁生,等.史铁生:扶轮问路的哲人[J].黄河文学,2010,(6).
[11]史铁生.病隙碎笔1[J].花城,1999,(4).
[12](法)雨果.《克伦威尔》序[A].雨果论文学[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3]史铁生.我与地坛[J].上海文学,1991,(1).
[14]吴俊.当代西绪福斯神话:史铁生小说的心理透视[J].文学评论,1989,(1).
[15]史铁生.写给本刊编辑部的信[J].文学评论,1989,(1).
[16]史铁生.日记六篇[J].江南,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