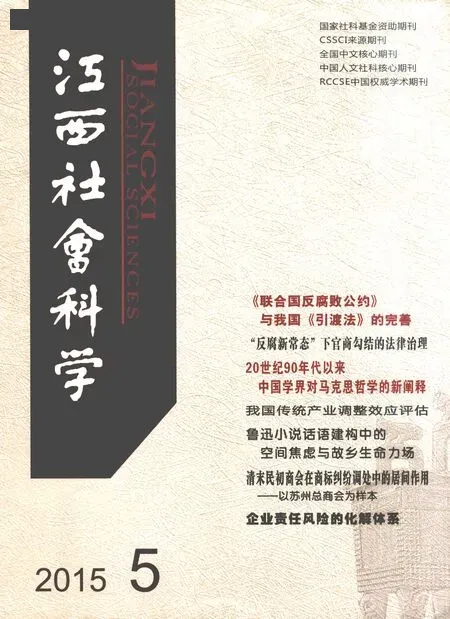鲁迅小说话语建构中的空间焦虑与故乡生命力场
■张春燕
在鲁迅的话语系统中,故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言说立足点。故乡是鲁迅启蒙话语的观照和言说对象,也是鲁迅流寓者身份确立和挣扎的空间、精神参照物,是鲁迅生命体验言说的出发点。它作为鲁迅体验与言说的中枢,辐射出鲁迅话语的基本语汇。于是,故乡成为鲁迅的核心话语点,围绕着这个核心,在不同层次和空间内部形成一种聚集力量,衍生出一个独具鲁迅气质的话语的场域,其中蕴含着鲁迅话语的言说实践和规则。显然,鲁迅的故乡不是一个固定的地域背景或者稳定的空间意象,它的内部既凝聚和衍生着意象、主题、意志,又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话语的生成规则。在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中,空间焦虑内化为主要因子,支撑着故乡话语的成型,甚至决定着这一话语的走向。
鲁迅的小说中,主人公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场域中。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中说:“从一种现实基础开始,在他25篇小说的14篇中,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以S城(显然是绍兴)和鲁镇(她母亲的故乡)为中心的城镇世界。”[1](P66)李欧梵不但注意到鲁迅对于空间的关注,也指出鲁迅作品中的空间建构是以他的故乡为模本的。鲁镇、S城、未庄、平桥村、咸亨酒店、一石居、茶馆、社庙、土谷祠……当我们将这些地理空间并置的时候,凸显出的正是鲁迅话语的一个现实观照点:故乡。鲁迅小说的展开几乎统统依赖于这个以故乡为原型的世界。这是鲁迅故乡话语的初步生成,即作为原型存在的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故乡。它作为小说主人公们的活动背景存在,是鲁迅作品情境建构的出发之处。
鲁迅以密集的空间概念建构了原型故乡的同时,又赋予故乡以内核性的人格,诸如畸形、荒凉、冷漠、残忍、阴暗,生活其间的民众掣于“吃人、观赏吃人、被人吃”的网罗不能自拔,也不自知。这一生存网罗即是故乡自身的人格和生命特质,其实质正是故乡民众的群体性人格。在鲁迅的文本世界中,故乡因为内部众人的群体性人格叠加而有了自己的生命人格,它以自身的生命质与内部主人公们并置为小说的言说对象,从而发出了自身的话语。鲁迅故乡话语的建构过程,实则也是故乡这一空间参与叙事与言说的过程。故乡如何以地理空间意象成为文化建构、价值体系建构的中心,又如何作为文化、价值参照实现言说者自我身份的确立,是本论文要探讨的问题。
故乡作为空间概念,有着自身的层次,它不是单纯的地理空间,是密布着权力关系和价值秩序的社会文化空间。人与空间的关系,人在空间的生存,成为鲁迅故乡话语的着力点。而其间触目惊心的是鲁迅以及他笔下人物的空间焦虑。即,人与生存空间(故乡)不能相容,不能和解的紧张关系。对空间焦虑的直接言说在鲁迅的小说中不胜枚举:
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狂人日记》)
太大的屋子四周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明天》)
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故乡》)
鲁迅笔下的主人公们,狂人、孔乙己、祥林嫂、阿Q、疯子、吕纬甫、魏连殳,几乎无一例外地生存在这逼仄、气闷、秩序环绕、人情冷漠的世界里,时时感受到来自这一空间的威逼和压迫。每一个人身上都带有不安和焦灼感。鲁迅的关注点始终在这些封闭空间内部主人公面临的焦虑。这一以焦虑为核心的关系结构和感受结构就是鲁迅故乡话语的精神本质,也是故乡从地理意象上升到群体性人格象征的内在话语机制,并且暗示着鲁迅对于世界的认知和把握方式。
一、整体上的“囚牢”模式
鲁镇之于祥林嫂、未庄之于阿Q、吉光屯之于疯子、咸亨酒店之于孔乙己、S城和寒石山之于魏连殳……都是一种围困力量。不管物理空间如何转移和置换,始终没有摆脱这一逼人的“囚牢”模式。在这种人与故乡空间的关系中,空间是先在而主动的,人是被动的;空间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是被评判和规约的。孔乙己在咸亨酒店众人的调笑中沦为笑料,祥林嫂是鲁镇人注视中的“陈旧的玩物”,疯子和狂人更是被真实地囚禁在祖屋和社庙里……他们始终处于以囚牢形式出现的空间里,被围困而无力挣脱。故乡就是通过这种令人窒息的囚禁实现对于内部人众的虐杀。这些小说的内部,都传递出黑暗、冷漠、残杀、耻笑、死亡、孤独等体验,糅合的焦灼感在文本中发酵、繁衍、变形、演化。正是这种内在的空间焦虑的影响,故乡在言说过程中演化为鬼域:故乡—社会空间(等级、秩序和文化空间)—牢笼—地狱,通过焦虑情绪的传递,以一系列空间意象的相互置换完成空间概念和空间性质的相互指涉,最终使故乡与鬼域成为同质同构的空间概念。
鲁迅的故乡话语内部,首先突出的是实有的空间,鲁镇、未庄、S城、社庙、祖屋、酒馆、山村、土谷祠,甚至花轿、坟、棺材,鲁迅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些充满桎梏感的意象,以这些具体而封闭的空间营造出逼仄的 “无法呼吸”“艰于呼吸视听”的空间感受,正是这种逼仄产生的焦灼感,将实有意象不断置换为感知意象,从而将具体空间意象变形化,无数涌现的空间意象以一种内在的同质——焦虑——无限推演下去,衍射至不同权力控制的空间内部,渐次演化成了 “高墙上四角的天空”“铁屋子”“地狱”“非人间”“无物之阵”“独头茧”“人肉筵宴的厨房”,甚至“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至此,实有的空间意象经由感知意象的中介,进入到以囚牢为形式、以吃人为内质的象征性意象。从空间对人的囚禁,最后到空间对人的虐杀和吞噬。故乡与鬼域的同质性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意象的置换完成的。这一话语规则是:故乡=地理空间=社会/秩序空间=牢笼=吞噬/吃人=地狱。而从实有的空间意象到感知意象,再到象征意象的转换契机,正是空间焦虑。在这种言说规则中,空间焦虑内化为叙事的主要因子,故乡经由这一因子的内在运作,最终变成鬼域。这一内核性质的感受结构成为故乡与鬼域之间转换的核心规则,并支撑起故乡的生存、文化景观。
故乡的囚牢本质和无形杀伤力作为故乡话语的显在层面,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从叙述者的角度呈现出来的话语,是将故乡作为启蒙对象的空间想象与空间重建。鬼域故乡的建构与启蒙话语的建构是同步的。我们注意到,鬼域故乡的言说者为空间之外的人,他是冷眼旁观者,也是故乡的异己者。即叙事者与故乡的对话关系中潜藏着一个 “文明世界”(理想世界)作为参照,故乡成为鲁迅话语中的“他者”。叙事者与其所在空间的距离感使得他建构的这个众鬼喧嚣的空间成了与他异质的存在,启蒙话语正是经由这异质性提供的言说角度进入到故乡话语系统中。
在“我”这一带有启蒙者眼光的归乡者不出现的文本中,唯有狂人、疯子和夏瑜这种脱离了正常生活轨道的叛逆者,能够跳出生存的空间看到故乡的囚牢性。狂人和疯子出现的意义就在于,以他们的非常态的生存方式和话语方式在故乡话语内部打开非常规的感受维度。这种观察视角和感受维度是故乡自身无法自发出现的。因为故乡话语背后,是文化范式的规约。狂人和疯子的疯言疯语正是以打破规约的方式撕开这密闭的空间的一角,他们不断警示着人们存在场域里的危险性。夏瑜更是对阿义说 “可怜”,他们都因为反常规性而获得与故乡的距离,而同时,狂人被关在祖屋里,疯子被关在社庙里,夏瑜被关在大牢中。他们的身份特征使他们在体验世界里将故乡与监牢这两个意象进行并置。从这个层面看,囚禁意象的设置就具有对故乡整体的象征意义。主人公因为疯癫或者叛逆而获得即使身在故乡也并不属于这一空间的特点,鲁迅反复将这“不在场”身份与囚牢意象并置,实则将囚牢模式的发现纳入到启蒙话语的框架之下,于是,囚牢意象不仅仅是故事事件的呈现,而且是作为一种感受结构去进行意象之外的故乡人格的想象和故乡话语的建构。
二、内部的阻隔模式
如果说囚禁是从叙事者的启蒙观照中生成的故乡话语,那么对于故乡这一“囚牢”的在场者(如阿Q、祥林嫂、孔乙己)而言,故乡又呈现出不同的意味,这一层次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感受结构是阻隔,其内核是被拒斥感。焦虑不仅仅是来自空间的压迫,还来自于人无法进入空间内部,与空间始终隔膜。鲁迅故乡话语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一阻隔模式推动的。《祝福》里祥林嫂的故事对于叙事者“我”来说,是“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由这种整体观照的角度,祥林嫂的一生是被囚禁、被围困的一生。然而推动着这些断片构成小说的内在驱动力,却是由祥林嫂的角度感知到的阻隔以及祥林嫂想要冲破阻隔进入到这个空间的努力。《孔乙己》中咸亨酒店呈现出的阻隔是以曲尺形的柜台将人群分割开来,对于内部的众人而言,取笑孔乙己,成为他们联合一气的途径,他们借此获得一种稳定的团体感或者安全感。孔乙己难堪的失语状态说明他与鲁镇文化空间的疏离。“穿长衫”却只能“站着喝酒”,则意味着他在任何空间中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永远游离于空间之外的焦虑成为孔乙己身上的标签。
如果说从叙事者的角度,以“囚牢”模式展示了故乡在话语中如何变成鬼境,那么,在这个话语层面上,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故乡内部的人如何变成鬼卒。其内在的话语运作机制是空间焦虑迫使下的人的本能挣扎。这种焦虑的运作过程体现的是无数的个人拼死向着群体靠拢。于是,这一层面上的故乡话语沿着这一规律言说和深入:乡民=空间中的人=认同秩序和规则的人=被空间驯化的人(被吃者)=排斥秩序之外的人(吃人者)=鬼众。
以《祝福》为例,祥林嫂的一生浓缩在几个空间之中:鲁镇(初到)、贺家墺(被迫改嫁)、鲁镇(被看、被嘲笑)、阴间(想象与恐惧)。初到鲁镇,地理空间就在四叔的皱眉中成为文化、秩序空间,她做的唯一的努力就是拼命干活以获得认可,进入到这个空间内部;贺家墺是“深山野墺”,象征着空间的隔绝,祥林嫂由改嫁被隔绝在鲁镇社会空间之外,她以死抵抗的心理动因,其实正是她对于所在的社会空间秩序的认同和恐惧;阿毛被狼吃,将她再次送到鲁镇,阿毛的被吃,正是祥林嫂被吃的隐喻,而祥林嫂看到的却不是这个空间的吞噬性,她以不断重复阿毛的故事来获得这个空间的同情和接纳。即便这个空间以注视、鉴赏、嘲笑甚至防备形成密不透风而无法打破的囚牢,她所做的努力也仍旧是捐门槛以期得到救赎,重新获得鲁镇人的接纳。祥林嫂自始至终感受到的,都是阻隔,而不是囚禁,她的所有努力,也都是为了获得空间内的立足之地,而从未想过冲破这个囚牢。
同样,那个虽然满口“之乎者也”却拼命想要与人交流的孔乙己,希望短衣帮对他接纳,结果却是“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那“排出九文大钱”的孔乙己则是以这样“阔绰”的一个举动,想要进入穿长衫的群体。同理,阿Q渴望姓赵、欺负小尼姑,也都有一种打破阻隔,期望与他人融为一体的意愿,也因此,他的革命梦想不是打破铁屋子,冲决出去,获得新生,而是意味深长的“同去同去”,他要的不是“去”,而是“同”。可以说,阿Q的所有生存意志都是进入而不是逃出秩序空间。
我们站在叙事者的角度看到故乡由实有空间渐渐演化为社会空间、牢笼、吃人场、地狱。但这个言说层次中的主人公们却个个茫然而恐慌,他们看到的不是铁屋子,而是阻隔,是“高墙”“厚障壁”……被拒绝的焦虑指引着他们去迎合这个空间内部的所有规范,以此获得自我身份、价值的重构。乡民甘愿被这一空间驯化,其目的是要寻找到自身在这一空间中的位置。正是害怕被空间排斥的焦虑促使他们变成空间的认同者和维护者。于是他们成为相互敌视、防备、既是吃人者也是被吃者的鬼众。故乡这一空间既规约了其间的乡民,使他们成为鬼卒;同时,鬼卒们也不断支持、维护和加强这种空间的压迫力量。于是,经由这种规约与支持的互动,鲁迅在故土言说中营造了人间炼狱,主人公们统统变成游魂。
虽然都有在空间压迫中的焦虑,但在乡者与离乡者(叛逆者)在面对故乡时感受到的自我与空间的关系结构完全不同,其根源在于,个人性的有无。离乡者因为与故乡的距离获得了观照故乡时的整体性视角,带有启蒙视角的离乡者首先关注的是个体与故乡整体的关系。因而他感受到的是自我与空间的对立,以及空间的围困。对于在乡者来说,他们人格中的“自我”、“个人”是缺席的,而甘愿作为鬼卒生存,以此在鬼境中获得立足之地。以狂人为代表的挣脱空间束缚的个人,是以从群体中抽离的方式获得自我的身份认同,甚至是自我的价值和道德上的崇高感。而以祥林嫂为代表的在乡者则是通过不断地将自我放置到群体中这样的努力来寻找安身立命之处。对于在乡者而言,他们惯于以适应空间规则的方式获得存在的舒适感。这一层面上的空间阻隔,指向的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生存的困惑,即人的离群的恐惧。鲁迅这一步走得比囚牢模式中的启蒙观照还要深远,他直接超越了对故乡或传统中国的文化和伦理审视,而直接进入一种现代感知和追问,这一追问针对的不仅仅是生存形式,还是进入到生存逻辑本身的困境:人对于群体的依附所造成的存在困境。
在这种故乡话语的建构过程中,被围困的焦虑和与空间疏离的焦虑并存,成为鲁迅故乡话语无法避开的内在情绪,并以囚禁和阻隔两种模式推动着故乡从原型/背景意义上向着鬼域发展。这种焦虑引导着鲁迅营造压抑别扭的故乡,直指人与鬼相生相克的生死场。
三、还乡模式与自我追问
鲁迅的故乡小说形式上几乎都采取了 “还乡”模式,而“还乡”进入文本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是用以衔接启蒙话语与故乡话语的媒介,不断出现的“我”的离乡与还乡从形式上暗示了在故乡话语系统中启蒙话语的参与。二是话语主体的多重性和自我分裂性媒介于还乡模式得以展现。
离乡者与在乡者的两种不同的感知结构,意味着对生存状况的不同把握方式,也展示着完全不同的生存状态。因而二者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两种相互悖反的认知结构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解决焦虑的途径:穿破阻隔进入秩序空间和从囚牢中突围。鬼域故乡建构的过程,正是自我从传统世界出逃以及自我确立的过程。叙事者的置身事外透露出暗藏信息,即叙事者以自身从故土的抽离将自己变成故乡的旁观者,从而以启蒙的眼光观照故乡,以此完成故乡话语到启蒙话语的转换,同时也完成了自身由故乡的乡民到故乡的异己者、启蒙者的转换。于是,启蒙话语建构的过程可以还原为“我”从故土的出逃过程。鲁迅的矛盾和痛苦在于,他将故乡话语纳入到启蒙话语的解释框架之下,那启蒙话语必然有进入故乡话语内部的需要。而作为启蒙者(故乡的不在场者),他看到囚牢本质之后,他的价值和文化选择是向外突围。可是作为启蒙话语与故乡话语的中介,这个启蒙者在行动选择上又必须是向内的进入。于是,随着鲁迅故乡话语的不断深入,兼具了“离乡者”(不在场者、突围者)和“回乡者”(在场者、进入者)身份的“我”避无可避地进入叙事文本,而还乡成为“我”的自我追问的形式。
从《故乡》开始,鲁迅其后的故乡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出现了一个高度介入的还乡者“我”。言说主体不再是置身事外的叙事者,而是离乡后的返乡者。随着还乡模式在故乡话语中的不断强化,由叙事者、在乡者、故乡构成的对话关系,变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叙事者1(离乡者“我”)、叙事者2(还乡者“我”)、在乡者、故乡之间的对话关系。“我”的分裂性在这种不断强化的对话中凸显:故乡的言说者与面对故乡的失语者、故乡的背叛者与企图进入故乡者、启蒙者与失意者共存一体。“我”的身份在这种对话中丧失了确定性。对于自我的追问在还乡文本中越来越紧逼。不断重复的还乡模式,更像是在为自我认知的追问寻找一个价值的参照。
当离乡者“我”在文本中变成了还乡者(故乡的在场者),叙事过程中“我”的“在场性”就必然导致“我”也深有阻隔体验,而不仅仅是外在观照中看到的囚牢。在还乡模式出现的小说里,还乡者面对故乡的真切感受恰恰是阻隔,无法进入,而且都是以故人相见为场景和契机表现的。在《故乡》中“我”与杨二嫂,象征着还乡者与掌握着乡土话语的在乡者之间的彼此拒斥,“我”始终失语,无法进入这个世界。“我”与闰土的相见,同样是“隔了一层厚障壁”,“四面的高墙将我围困”。《祝福》里“我”与祥林嫂的遭遇更是将“我”甚至是“我”代表的启蒙话语无法进入到故乡内部的现实展示得淋漓尽致。《在酒楼上》“我”访友不得、见旧友而无法亲近、吕纬甫迁葬不见尸骨,处处碰壁,处处被排斥,也凸显了这种阻隔。
还乡者感受到的阻隔有更深层的内在,他们不同于祥林嫂和阿Q的是,他们不是要融入那个世界来获取自身的安全感,而是想通过启蒙言说的介入对其进行改变。这种基于还乡者立场上的阻隔感,在鲁迅的言说中以另一种感知意象出现,那就是“沙漠”和“荒原”:“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2](P439)《故乡》开始的“还乡与失语并存”的模式将“我”与故乡的断裂推送到言说表层。也由《故乡》开始,对于启蒙者自身的存在追问再也无法停止。之后的《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以重复的还乡进入不断的自我审视、自我质疑、自我追问、自我谴责。理性认知将“我”从传统道德和伦理中抽离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给了“我”一个新世界,却只是将“我”变成故乡的异己者,“我”被故乡拒绝和放逐。启蒙者的荒原感未必只有寂寞,还有无地容身的焦虑。“我”的自我意识给“我”的是新的生命形式的衡量标准,却以自我的存在空间的倾覆为代价。《祝福》中祥林嫂的阴间归属的追问实则暗藏着一个关于启蒙者精神和文化归属的问题。无地容身的自我以及自我的分裂开始成为显在话语。鲁迅自身的最大焦虑正是在这一境遇中,迷失了自我身份以及自我的容身之地后,生命主体面临的“我是谁”以及“我在哪里”的双重焦虑。
四、寻路模式与流寓者身份的确立
当故乡话语的展开以鬼域及鬼众的成型收场,话语主体摧毁了自身的容身之地,凸显的问题是:以故乡为参照的这个主体的身份定位是什么,又是以什么方式获得确立?在以故乡为核心的这个多边对话的体系中,分裂的话语主体是如何穿透生存危机,实现分裂自我的重新组合的?其言说的秘密正在于文本中寻路模式的开启。路、行走意象在鲁迅的小说中是与“我”的出现捆绑在一起的。如前所述,“我”从《故乡》出现,正是自我身份焦虑的开始,也是自我分裂的开始。而路、行走作为与“我”捆绑出现的意象,其意义正是以其行动意志实现分裂自我的整合。
与社会空间的不能相容是鲁迅的心理和精神的基本因子。于是,人与空间的对立与不能和解必然成为鲁迅故乡话语的核心语义。在与故乡的对话关系中,作者自身的空间焦虑全部潜伏在文本内部,成为话语意向的牵引力。《孔乙己》中曲尺形的大柜台构成的阻隔感受,几乎无异于少年鲁迅 “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2](P437)所感知到的生存结构。孔乙己和祥林嫂在鲁镇所感受到的阻隔,蕴含着鲁迅对世界基本结构的认知,那就是世界与自我的对立。当他在启蒙话语的框架之中书写这个世界,他能够以不在场的离乡者身份建构故乡的囚牢性,但进入到文本内部之后,他对故乡的判断,无不渗透着自身经历在情感世界中的遗留。
鲁迅在现实中的“走异路,逃异地”,也正是他在被囚禁、被围观的异己空间中无法生存而不得已的出逃。从绍兴到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他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伴有着无法摆脱的空间压迫。汪晖在《反抗绝望》中说:“鲁迅‘反传统’的内在动力还不是对某种价值信仰的追求,而是一种更为深沉、也更为基本的危机感——生存危机。”[3](P58)汪晖所说的“生存危机”是从人与民族的存亡角度阐释的,但鲁迅自身的存在危机也必然是应有之意。所以他的故乡言说过程中始终贯穿着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自身与所在空间的不相容性和对抗性?鲁迅选择的方式是,将他在现实中的一次次出逃带入到文本,这种从异己空间的突围行动进入到言说中,即成型为寻路与行走的文本结构模式。将鲁迅的以寻路、行走作为仪式性动作的精神选择放置在他的故乡话语系统中去观照,所有的行走都意味着与所在空间 (故乡)的龃龉,凸显的正是空间意义上的鲁迅身份:流寓者。它的同质的语汇还有异乡人、过客。行走与寻路的频频出现,既是鲁迅空间焦虑的暗示,也直指言说者鲁迅的生命存在的流寓状态,即始终行走在打破囚禁和寻找立足之地的路上。寻路和行走成为他的故乡话语建构中的潜意识。这意味着他在故乡话语建构中,是将自身在空间里的异化感糅合成精神选择上的主动的拒绝。被摒弃、被放逐与主动告别、主动摒弃交织成近乎悲壮的生命存在方式。这些才是鲁迅精神体验的类似原点性质的语汇。而鲁迅的故乡话语正是在这一个维度上建构和衍生的。
行走意味着拒绝和告别。“我”参与到叙事中之后,鲁迅对于“我是谁”“我在哪里”的追问已经无法停止,这一存在本质的追问愈来愈迫切,当自我无法进行回答的时候,唯一能够确定的,恰恰是“我不是谁”和“我不想在哪里”。于是,这些分裂的自我在所有文本最后都统统选择与故乡告别,行走以其告别性使分裂的自我通过斩除旧我而实现人格的统一。譬如《故乡》文本的言说目的,正是“为了别他而来”。通过书写“我”与故乡这一空间的隔膜,通过“我”与杨二嫂、闰土的对照彻底斩断“我”与故乡的精神联系,从而实现“我”的对于传统世界的拒绝。“这样的还乡作为仪式使现代知识者的文化结构得以真正意义的完形。”[4]“我”最终的离乡虽然仍着笔于“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的焦虑,但是生命存在的意义却通过那段著名的关于“路”的言说而彰显。同样,《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的结尾也是以“我”的“走”而结束。而这一动作的暗示即是通过与所在空间的决裂,所有的“我”都成为故乡的出逃者和新的空间的寻路者,而至此,“我”也彻底成为故乡的游子和过客:“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5](P196)从这种拒绝与告别中浮现出来的,是行为主体流寓者身份选择的自觉性。自我身份的焦虑还不能消除,但是“我”的走,已经将自我变成主体,开始以行动说“我不”。拒绝成为自我潜意识里强有力的人格:“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6](P169)坚决而理智的否定性是生命主体的理性选择。寻路和行走的模式正是以这种否定性解决了鲁迅的问题,使他成为过客反抗精神的践行者。
所以,行走也是内在精神世界迸发出来的意志强力。徐麟认为,从《故乡》的结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种生命的焦虑是如何在行动的契机中释然的:地上本没有路,但大地却是一个坚实的‘有’,他赋予了大地以存在性”[7](P115)。鲁迅的存在焦虑也正是在路的 “无”与大地的“有”之间实现消解。也就是说,鲁迅已经放弃寻路,而更注力于行走。他选择以走为路的生命姿态。即使自我没有容身之地,行走本身会开拓出一个行动场,这个场是人格的立足之地。他已经不再追问“我是谁”和“我在哪里”,而是进入到以行走本身为目的和意义的精神的空间。而言说主体的这一生存姿态在《过客》中得到完整的诠释。来处和终点都不重要,生命的意义和秘密只在于行走本身。他已然超越对现实空间、文化空间的诉求,他以行走这一行动本身建构了生命力量的场,鲁迅正是以此立足的。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2]鲁迅.《呐喊》自序[A].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4]何平.《故乡》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2004,(9).
[5]鲁迅.过客[A].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6]鲁迅.影的告别[A].鲁迅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徐麟.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祥林嫂的悲剧原因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