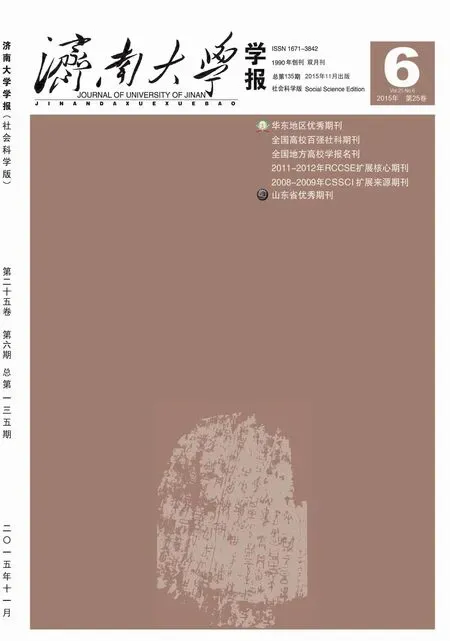鲁迅与左翼乡土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比照研究
田 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鲁迅与左翼乡土小说中的看客形象比照研究
田丰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看客”形象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之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鲁迅影响、指导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左翼乡土小说作家在延续鲁迅“看客”形象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和推进,从而展现出别样的风貌。左翼乡土小说作家在塑造看客形象时,既有意识地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身上汲取养分,同时也依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时代语境变换而有所调整,从而使得看客形象更趋繁复和深化,在给读者带来新鲜体验和感受的同时,也使看客形象得以传达出阶级斗争和时代变幻的讯息。
关键词:看客形象;左翼乡土小说;鲁迅;阶级视阈
“看客”一词在明清典籍中即已出现,然其词义却与今义大相径庭。目前可以查到的在现代意义上使用“看客”一词者始见于《益闻录》1885年第514期《大烧看客》一文,其意为观看戏剧演出者。梁启超在《呵旁观者文》中也曾以 “旁观者”来指称现代意义上的“看客”。然而真正赋予“看客”一词以象征意义,形成具有特定意指和深广内涵的现代语汇的则非鲁迅莫属。以往人们往往依据鲁迅本人的说法,将“幻灯片事件”作为鲁迅形成“看客情结”的原点,然而事实上早在童年时期鲁迅就已经萌发出对于“看客”极其反感、厌恶的情绪。他曾在《呐喊·自序》中感慨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1](P437),此中的“世人”实际上便是周家罹难后冷眼旁观的看客。由此可见,正是童年的苦难记忆和成年时“幻灯片事件”的双重刺激促使鲁迅对于“看客形象”投注相当的注意,为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笔墨,仅《呐喊》《徬徨》两部小说集收入的25篇小说中就有一半涉及到“看客”形象,构建起“看客”人物形象系列,而在其中“凝结着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关系、人际关系及人生价值、命运……最深刻的观察与把握”[2](P1)。由鲁迅开辟出来的“看客”形象对于之后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不乏其例,举凡莫言、余华等当代作家都对“看客”形象有过浓墨重彩的塑造。在鲁迅影响、指导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左翼乡土小说作家更是如此,他们沿着鲁迅开辟出来的创作道路继续前进,在延续鲁迅“看客”人物形象的基础上又有所拓展和推进,从而展现出别样的风貌。
一、延续鲁迅传统的看客形象
鲁迅在《祝福》中透过祥林嫂的悲剧,揭示出看客野蛮、残忍的一面,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经过他们“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而“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3](P10),处境更加悲惨。看客们将自己的欢娱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从他人的悲剧中不断汲取新鲜的观赏体验,而在获得满足后,为他们带来欢乐的悲剧中的“人”却成为不祥之物,祥林嫂正是在这些看客的围观和戏谑之下一步步走上死亡深渊的。尤为可悲的是,这些麻木的看客对由他们所造成的人间惨剧毫无反思和自省意识,仿佛完全凭借本能为之。因而,这样的悲剧非但没能停止,反而一再重复上演着。左翼乡土小说中对此有着诸多的描写,在萧红、柔石、端木蕻良、周文、王统照等作家的小说文本都有所表现。
萧红是在鲁迅大力扶持和帮助下走上文坛的,无论其思想还是行文都深受鲁迅的影响。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对愚昧的看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刻画。在生生死死、毫无波澜的庸常生活中,他人的悲剧和不幸反倒成为人们难得的生活调剂和话题资源,从看死尸、看醉鬼、看泥坑、看跳神、看洗热水澡直到看杀头。小说中的王大姑娘生性开朗、爱说爱笑、身体结实、勤快能干,因而人人都称赞她“膀大腰圆的带点福相”,“将来兴家立业好手”[4](P173)。但自从她和磨官冯歪嘴相好并生下孩子后,却成了不干不净的野老婆,往日的这些优点又改头换面成为恶意攻击她的口实,“说话的声音那么大,一定不是个好东西。哪有姑娘家家的,大说大讲的”,“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没见过一个大姑娘长得和一个扛大个的(扛工)似的”[4](P175)。一时间王大姑娘成了众人注目的焦点,“全院子的人给王大姑娘做论的做论,做传的做传,还有给她做日记的”[4](P177)。看客们甚至在冬天雪夜里也“不辞辛劳”地专门守候在冯歪嘴子的窗前探听消息。老厨子没有听见小孩的哭声,竟“举手舞脚的,他高兴得不得了”,匆忙报告说小孩子已经被冻死了,而一旦发现小孩只是睡着了,他却倍感失望;当有人看到冯歪嘴子炕上有一段绳头时便马上传言说冯歪嘴子可能要上吊;又有人看见冯歪嘴子从街上买了一把菜刀,便又传言说他是要自刎。凡此种种只是为了免费看热闹,“反正也不是去看跑马戏的,又要花钱,又要买票”[4](P179)。实际上也并非单单对王大姑娘如此,而是俨然已经成为呼兰河小城的习俗,以至于每当有人投河或上吊时,就“好像国货展会似的,热闹得车水马龙”[4](P179)。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正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看”与“被看”的悲剧故事,在貌似平静的叙述笔调背后深隐着无限的痛楚和悲哀。
在柔石的《人鬼和他底妻的故事》中,人鬼的妻自从进了人鬼家后,便过着奴隶一般的生活。邻人天赐出于同情,不仅时常接济她一些钱,还替她想方设法解决其生活困难。然而,他却也因此遭受到周围看客的恶毒攻击,纷纷谣传“人鬼的妻已经变做天赐的妻了”。人鬼妻子有孕在身后更是激起轩然大波,连出生后的孩子也在劫难逃,始终被周围的冷笑声包围着。人鬼的同伴更是时常在人鬼面前说孩子不是人鬼的,终而致使孩子在遭到人鬼毒打后染上重病不治而亡,人鬼妻感到希望破灭后上吊自杀。嗜酒如命的人鬼身无分文、无力下葬,天赐主动操办了人鬼妻的后事,却又因此招来看客的冷言冷语。人鬼妻的死像祥林嫂一样非但没有引发人们的同情,反倒成了腾挪于众人之口的生活调料,其悲剧经历在他们看来却只是一件动听的故事。原本善良可亲的天赐经此打击之后,心灰意冷,他已然认定人只有作恶的可以获福,做好人是永远不会获福的。
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则显现出“看客”人性复杂缠绕的一面。一大帮的山东逃荒者来到村上,村人们如临大敌,四门紧闭,到晚上一个老头子牵着一个瞎婆子来到艾老爹门前乞讨,艾老爹慷慨地搬出一大匹黄面豆包要分给他们吃,但当他看到老头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时,竟又鬼使神差般粗暴地将两个老人推出门外。第二天,老头子在村上出卖女儿以求活命,却遭到一大群围观村民的奚落和詈骂,看客们学着老人的山东调哄笑着,“声音透出侮辱的损害的重围来”:
“呣有法子,一把骨头,也管人家要二十站人的(银圆)吗,打的好主意!……”
“你别看,长像还不错呢,至少也比得过猪八戒他二姨不是。”
“你别看,没上食(喂肥猪时,加着米粮,谓之上食)呢,一‘上膘’就好看了……”
“赔账货,到家就得赔口棺材的……”四周的人们又是一阵开心的大笑——[5]
如此粗陋不堪的言语较之封建卫道者四铭而言更令人难以忍受,遭受众人奚落和嘲笑的老人一家此时正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看客们的人性泯灭和精神污浊都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众看客大肆辱骂之际,艾老爹却又良心复苏,出高价将姑娘买了下来。第二天他把许多大饼子塞到老人怀里后又将老人凶恶地赶出村外。在艾老爹将老人赶出门外及逐出村外的两次过程中,作者着重描绘了艾老爹的心理活动。在将老者赶出门外后,他整夜都没有合眼,承受着良心的谴责。而将老人赶出村外后,他也觉得非常难过,孤独地站立半天,直到老人远去后方才返回家中。透过艾老爹这一个体看客,作者将揉作一团的人性矛盾处——善良与恶毒、高尚与卑污一股脑剖示出来,却又在文中并不作褒贬,留给读者自己去进行评判。
在周文的小说《投水》中,陈么要拿家里仅剩的两个银手镯去还高利贷,陈么嫂坚决不依,在遭到痛打后逃出门外,却又偶然听到一直围观着看热闹的孙二嫂、水生嫂、松寿奶奶等人的背后议论。水生嫂奚落她投了三回水都没死成,不过是借投水吓唬男人,简直是在洗澡。陈么嫂难以忍受这样的屈辱,终于在丈夫搜出银手镯并再度毒打她后真的投水自杀了。造成陈么嫂死亡的直接原因固然是由于丈夫的虐待,但看客们也逃脱不了干系,正是她们的恶毒讽刺将她逼上绝路。引人深思的是,孙二嫂、水生嫂与陈么嫂一样都是松寿奶奶高利贷下的受压迫者,然而她们却与逼债的松寿奶奶一道成为陈么嫂悲剧的旁观者,与食利者松寿奶奶相比,她们所给予陈么嫂的伤害反而更大也更致命。她们似乎已经全然忘记了刚被松寿奶奶逼债的情景,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陈么嫂。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鲁迅笔下的柳妈,正是柳妈看似不经意甚或是带着些许善意,提醒改嫁过的祥林嫂到阴间将被两个死鬼男人争夺的恐怖景象,使之成为压垮祥林嫂求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之后捐门槛出路的失败彻底摧毁了祥林嫂残存的生的意念。因此可以说柳妈对祥林嫂的死要比鲁四老爷有着更大也更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柳妈对此不仅不会承认,也是完全不会意识的到的。水生嫂、孙二嫂未必平日里即是如此行事,之所以如此,显然是想借对陈么嫂的谩骂和讽刺来取媚债主松寿奶奶。《祝福》里的看客们对于祥林嫂起初倒也不无哪怕是虚假的同情,镇上的老女人特意寻来听过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后还会“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3](P17),而孙二嫂、水生嫂连这起码的同情心也早已丧失殆尽,生活的磨难摧折已经使得人心极为粗粝和残酷,她们丝毫也没有认识到自身与陈么嫂类似的现实处境,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6](P384)。也正因此,鲁迅曾将此类看客概括为“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7](P129),其杀伤力的确是不可小觑的。蹇先艾作于1934年的《乡间的悲剧》里的祁大娘在得知丈夫在外面又娶妻生子后,便因担心村里人可能随之而来的讥讽而撇下儿女投水自尽。
王统照《父子》里的老铁匠狂吃烂赌,欠下一屁股债,将二儿子小福倾心尽力耕种即将收获的土地典当出去,小福气不过杀了他,上演了一场人伦惨剧。镇上上千的观众围观着公开审讯的过程,有的喊好,有的吐着唾沫,也有人主张即刻将凶犯活埋,还有人提议将这畜类摔死在死尸面前。然而,凶手既不恐惧也不反悔的态度却大大出乎看客们的意料之外,以至于“觉得他的凛然而且直爽的气概,使人想不到是从前那么一个庄稼汉子应该有的态度”[8]。凶手的凛然、直爽反衬出的是看客们心理的猥琐、狭隘,凶手坦然承认了弑父这一事实,使得这一切来临得过于容易,之后凶手的沉默更使得他们觉得“无戏可看”。同样是示众,但《父子》显然与鲁迅的《示众》有所不同,在《示众》中的“看客”单纯为“看”而看,他们并不关心也不去追问犯人到底犯了何罪以至要被示众,而是仅仅满足于“看”这一行为本身,以此来为空虚乏味的生活增添一点补缀和调味而已。然而如此一来,“示众”本身的意义何在便不由得让人怀疑,在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统治者令犯人示众的初衷,在犯人和看客以及看客之间相互的“看/被看”中,犯人被用作工具来吓唬别人的功能设定已经失去了原初的意义。诚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另外一种可能,那便是统治阶层的驯化早已成功,频繁的示众使得看客们早已见怪不怪,失去了初次见到时的新鲜和刺激。如此,透过看客形象不仅揭示了群众的愚昧麻木,也折射出统治阶层的凶残暴戾,因为“示众”本身往往是由统治阶层主导的政治驯化和心理恫吓,经由不断的“政治上的训练”最终使得“人们会从根本上欢迎对他人的公开杀戮”[9](P25)。然而,《示众》中的看客们对于此类行为早已麻木,他们对此早已纯熟于心,因而“看/被看”都已丧失掉具体的意义指向,同样是毫无意义的。而《父子》中的看客则对于犯罪的因由和动机颇为关注,在事后老郭、玉兴、三成等看客们还对此展开过讨论和反思,虽然还浮着在表面,得出的只是似是而非的结论。
二、阶级视阈下的看客形象
在鲁迅塑造的众多看客形象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为民众福祉奔走呼号、抛洒热血的革命者却不幸沦为愚昧看客的观赏行刑的对象。革命者夏瑜被杀头不仅引来了一大群清早便赶来围观的看客,而且连他的血也被当成治病的药给愚民吞食掉。如同郁达夫在追悼鲁迅时所说的那样:“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有英雄而不知尊重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生物之群。”对于此等不仅不顾惜英雄,反倒乐此不疲充当看客的“生物之群”,鲁迅是至为痛心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看客”和统治阶层一道致使革命壮剧蜕变成了一场闹剧和滑稽剧。革命者在被统治阶层剥夺了生的权利的同时,连死的意义和价值也被看客们咀嚼一空,反倒成了被“可怜”的对象。鲁迅曾给这样的看客画了一幅像:“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觫,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10](P170)事实上无论古今中外群众都是看客的主体,过去在国外“处决罪犯似乎总像在庆祝一个公众节日一样”,许多人都“绝对不会愿意放弃在刽子手‘工作’时旁观的机会”[9](P25),就连外表文雅孱弱的贵族小姐们为了观看杀人,也会专门购买视线良好又离刑台足够近的席位以便能看得更清楚些。譬如在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中,断头台即占据着主导地位,老女人们一边织毛线一边观看行刑。鲁迅在散文诗《复仇》(其二)中所描述的即是耶稣为了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们遭受极刑,换来的却只是轻慢和辱骂。
然而,时代的脚步毕竟在不断前进,党领导下革命形势的推进和农民运动的兴起,已经使得底层民众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映现在作品中的看客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变异。与鲁迅一样,左翼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看客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多也都是普通民众。但与鲁迅作品不同的是,左翼乡土小说中的看客们已经逐渐开始以阶级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被看者,对于出身统治阶层的人,如果是真心为民众谋福利的革命者则同情之;对于同一阶级出身的人,甘心做走狗和帮凶的则坚决斗争之;对于那些因生活所迫误入歧途的,只要真心悔过,则仍然有可能得到看客们的谅解和同情。阶级视阈中的“看客”形象可以说是为左翼乡土小说所独具的,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特征。
阶级视阈中的看客形象与鲁迅传统的看客形象相互映衬既可以使我们看到看客形象随着时代的演变情况,构成互补性的存在,同时也大大丰富了“看客”形象的人物画廊,打破了愚昧无知的单色调看客图景。鲁迅着意塑造的是辛亥前后也即新旧时代转换时期的看客形象,其时的民众尚未觉醒,社会上触目可及的都是这些带着旧时代烙印的沉默麻木的看客,他们因袭着传统的重负,尚未能认识自身悲剧命运的缘由,对于那些引领时代风潮的革命先行者也缺乏最起码的认识。同时经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反复灌输,“即使是同一阶级中的人,也存在着隔膜、冷淡、互不关心”[11]。群众非但不能明了自身所处的遭受压迫的屈辱地位,反而会模仿着统治阶层的行为去欺压更弱小者。左翼乡土小说作家笔下的看客经历现实斗争的洗礼和教育后阶级意识已经有所觉醒,对于阶级斗争也有了一些基本认识,但同时那些旧式看客依然存在,因而在作品中便呈现出复杂的看客面貌。
许杰的《七十六岁的祥福》中,出身于有钱人家的革命者方玉山被武装兵士捉住后经过街头时也引发了看客们的围观,但激起的反应却不尽相同。认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看客认为方玉山是强盗;有的则对富家子弟出身的革命者能否为穷人谋取幸福持怀疑态度;有的看客却认为“正是因为不是没有钱出来帮助穷人,才是好人呢”[12]。“好人”和“强盗”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已经表明看客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这也符合实际情形,生活中的看客原本就汇聚了男女老幼、贤与不肖等各色人等。
戴万叶的《激怒》则展现出看客们自发反抗意识的觉醒。文生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只因牵着母牛在恶霸地主李老虎的池塘边饮水时捉小鱼玩就遭致一顿毒打。围观的群众先是慑于李老虎的淫威敢怒不敢言,但“他们的含恨的眼睛,闪着无可奈何的怒火,杂着一些自觉的悲悯”。“人类固有的野性,潜伏在他们的内在的生命里,受这池边的悲剧所激动,已像准备防敌的箭猪竖起了它的身上的毛刺一般,多么紧张而且奋发啊!”[13]终于,群众的怒火爆发了,虽然他们仍不敢直接跟李老虎斗争,指向的只是李老虎的两个帮凶。然而,毕竟群众的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已经开始复苏,在革命者桂叔的指引下他们明白了应该组织起来,去向真正的敌人李老虎作英勇的斗争。
蒋牧良《当家师爷》中的温师爷原本是走江湖的算命先生,靠着穷朋友们你一借我一贷的勉强混个温饱,但当他做了地主家的师爷后却和穷朋友们疏远起来,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孤家寡人。起初温师爷也想到过辞职,但他在地主家过惯了舒服日子,最终为保住饭碗彻底地站到了地主一边。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14](P384),温师爷死心塌地地为主子卖命,整天费心尽力地替东家讨要欠债,以至逼得穷苦人没了活路。他为了维护个人的私利,泯灭了最基本的人性,对于昔日同伴们毫无同情和怜悯,终于在一次讨债逼死新七的女人后惹起众怒,将他家的房子付之一炬。虽然救火的锣声一直敲个不断,但“成百成十的男男女女都野鸭子似地朝东边挤去,可是谁也没带水桶和梯子”,嘴里还都在说着“咱们看去,咱们”[15]。直到整幢屋子烧完了,远处站着的看客们谁也不肯拢来。温师爷落得个屋毁人亡,又遭东家无情辞退的可悲下场。在通常情形下,“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16],看客们对于别人的不幸冷眼旁观,甚而从中获得满足与快感,此种幸灾乐祸的看客心态是极为残忍和恶毒的,但在阶级话语中却反而大快人心,令人拍手称快。对于此类甘愿充当统治阶级爪牙和走狗的人物,鲁迅也是极为鄙视和贬斥的,他在《药》中即刻画过康大叔、红眼睛阿义等兼具奴性和狼性的奴才型人物,在狼面前他们是羊,而在羊面前他们又是狼。
在沙汀的小说《一个绅士的快乐》中,退伍军官出身的绅士不仅和村妇乌花姐姐通奸,还残酷虐待她的丈夫阿发,目睹这一切的窗外偷窥者们为此被深深地激怒了。村人们嚷闹着冲了进来,绅士被乱枪击毙。如同小说中借阿发母亲之口所说的那样,“在这样的年头,农人们早已经不怎样惜疼绅士们的生命了,正如绅士们对他们一样”[17],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实际上早已箭在弦上,一触即发。蒋牧良《赈米》中的赈务委员两度充当看客,第一次是为发放赈米做准备到乡下去视察灾情,他所看到的北乡的水灾实情比宣传照片上的还要凄惨,所经过的五十多里地人烟全无,为此他也感到职责重大,想要及早放粮开赈。然而他终究未能抵过金钱的诱惑,置灾民的生命于不顾,为了二百块钱将赈米转交给商人抵押贷款。年关将至,灾民们苦等救命的赈米迟迟未发放,他们聚在县政府前请愿。作者将本该置于被看者位置的赈务委员放在看者的位置上,触目所及,满街满巷都是清一色的叫花子。隐含的作者及读者则成为赈务委员背后的“看者”,透过赈务委员两次“看”的行为表演,使得赈务委员的伪善暴露无遗,从而达到反讽的效果,让赈务委员在前台充分表演,将其丑态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作者和读者则成为“将这灵魂显示于人”[18](P106)的不动声色的“审问者”。
三、左翼乡土小说与鲁迅作品中看客形象的主要区别
由上文所述不难看出,虽然左翼乡土小说作家承袭着鲁迅开辟的路径,对于看客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也有所展现,但已经开始侧重于从阶级视阈重新打量看客群体,因而左翼乡土小说中所塑造的看客形象与鲁迅作品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
其一,鲁迅在作品中侧重于对国民“劣根性”的暴露,而左翼乡土小说则在揭露国民劣根性的同时着意彰显出国民“优根性”。
从左翼乡土小说作品的表现实质来看,这两者实际上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构成一种和谐互补的关系,“指出劣根,并不等于否定优根”,而“揭示劣根,剪除劣根,正是要保存自己民族特有的优良的根性”[19]。究其本质,鲁迅是持着强烈的“诚与爱”的道德精神来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的,他有意将“看客”现象作为探索国民性问题的一个突破口,像手术刀一样直插进民族精神的病灶。具体而言,童年经历和“幻灯片事件”是触发他剖解看客身上劣根性的原动力,透过这一原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鲁迅会执拗于揭示“看客”人性恶的一面。鲁迅塑造出一系列的看客形象,其目的正是为了剖掘出隐藏在“看客”身上及其现象背后深处的精神弱点和人性悲剧,以此引起读者的省思和感悟。然而,也恰由于此,使得我们在鲁迅的指引下往往单纯瞩目于看客身上所折射出的“国民劣根性”的一面,而忽视了看客依然可能保有的“国民优根性”的另一面。整个1920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基本上都是如此,在这些作品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既是受到同情的对象,同时也是受到集中批判的对象,通过揭示看客身上所附着的封建文化的痼疾以引起疗治的注意。左翼乡土小说作家则在阶级视野下重新打量底层民众,既注重揭示他们所受到的“精神奴役的创伤”,同时也发掘出他们觉醒、抗争的另一面,使得他们身上同时固有的国民“优根性”得到完整的展现。
许杰的小说《贼》即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贼”的故事,由此也塑造出非比寻常的“看客”形象。潜入到普通农家的“贼”被当场捉住后遭受一顿暴打,意犹未尽之下还要将其送官。然而,在贼讲述了他之所以会沦落为“贼”的情由后,围观的看客们却马上转变了态度,原来“贼”也和他们一样是受压迫的穷苦人,看客们反倒开始表同情于他。贼”的凄惨遭遇不仅平息了人们的怨气,他们还找来食物让“贼”充饥,滥腐先生还将两角小洋送给了“贼”。
《贼》中的看客们并非一开始就对“贼”持有同情的态度,而是认识到“贼”所遭受到压迫、屈辱的事实之后方才转换态度的,因此并非仅仅是纯朴的良善心驱使所为,而是基于对反动统治阶层的共同仇恨和恶感方才会导致如此戏剧性结果的出现,因而像《贼》这样致力于揭示看客“国民优根性”的小说并没有降低反思与检讨的力度,同样是有助于启发民众觉悟的。戴平万在《春泉》中也塑造出彰显“国民优根性”的看客群像。一个老婆婆寻找听别人说躲藏在山上的儿子时失脚跌倒在山坑里,一群上山打游击的队员们将她救起,而在救助之先首先问起的便是老婆婆的身份,在确认其为村里的穷人后他们不仅将她救起,还凑钱交给老婆子让她好好生活下去。“我们都是苦人儿,应该帮助着苦人儿呀!”[20]这极为朴素的话语包含着的正是一种真挚朴实的阶级友爱和患难深情。张天翼的《仇恨》里躲避兵灾的村民们在路上看到一个被兵砍伤后伤口上爬满蚂蚁以至变成黑色人的伕子,痛苦难耐的他恳求大家动手结果其性命,但村民们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忙着用水替他擦洗伤口,将他抬下土堆。虽然最终也没能救活,但穷苦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和阶级情愫却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
其二,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多以群体面目出现,左翼乡土小说则开始呈现出众多个性鲜明的单个看客形象。
鲁迅作品中的看客形象往往是众声喧哗却难以瞥见独异者的身影,不像被看者阿Q、祥林嫂、孔乙己那样有着明晰的个性特征,只有在整体的意义上方才赋予看客群体具体、鲜明的群体特征。无论是《阿Q正传》中处决阿Q时的围观人等,抑或是《孔乙己》中的短衣帮都是以群体的面目出现的。尤其是在《示众》这样的文本中,看客们走上前台成为故事的主角,示众者反倒退居到次要地位,“示”众实际上成为了“众”示。不仅如此,鲁迅小说中的看客们还经常处于流动状态中,见有热闹可看便群聚而来,且有新的看客还在不断加入,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如群蜂归巢般乱作一团,每个被拈出的看客均是模糊、片段的感官刻画,作者着意营造的是各式各类无头无脸、无贵无贱的看客云聚的整体场面,呈现出“无主名”的纷乱状态。事实上,这种群体看客形象的塑造正是鲁迅的创作本意,他所要揭示的恰是“看客”的群体人格,注重“以人的群体性格作为一个活动背景对某一人物形象的衬托和深化”[21](P194),从中提炼出有着广泛代表性的“国民劣根性”。
左翼乡土小说中则塑造出众多的个体看客形象,譬如蒋牧良《懒捐》中的老阿培,许杰《贼》中的滥腐先生、吟秋先生等,蒋牧良《赈米》中的赈务委员,沙汀《一个绅士的快乐》的赌徒,戴平万《春泉》中的阿承等等都是个性鲜明的单个看客形象。同时,由于鲁迅作品的看客多以群体面目出现,因而对于看客多以外部行为的展示和面部表情的描摹为主,而左翼乡土小说则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体看客的心理活动。譬如前文所述及的《赈米》的赈务委员即是如此,作者对于其心理演变作了详细的描画和展现。
其三,鲁迅小说中“看客”们与被看者之间几乎没有相互的交流和互动,人与人之间隔着厚厚的障壁,双方所能感受的只是相互间的敌意和隔膜。左翼乡土小说中则开始出现看者和被看者之间的情感交流,所打破的恰是看者与被看者之间的敌意和隔膜。
如同鲁迅所说的那样:“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得自己的足”[22](P83-84)。“看客”看示众者,示众者也在看“看客”,“看客”之间也在相互看,而在此背后隐含的作者则在同时看示众者和看客。这一系列的看者搀杂缠绕在一起,相互之间却并没有言语及思想上的交流,甚而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看,总之只是在看。因而,“看”这一动作本身便具有内在封闭性和自足性,既是意义指涉的起点也是终点,实际上“看客们不在乎看到的是‘什么’,只在乎集体起哄的形式给他们带来‘合群’的快感”[23],以此证明自己不是“被冷落的人”。
而在左翼乡土小说中,看客之间却已经开始有着一定的言语和思想交流。譬如许杰的《贼》从一开始对贼的毒打到讲述因由后的同情和谅解,正是通过双方之间言语和思想的交流方才得以实现的。张天翼的《仇恨》中村民们对于造成他们苦难遭际的兵们深恶痛绝,恨不能生吃他们的肉,恰当此时他们发现了三个败兵,男人们发疯似的直冲过来,拳头冰雹似的落在他们身上,奔在最前头的小伙子没命地咬着其中一个兵的肩头达一两分深。他们以前“老觉得这些兵油子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东西”[24],然而在之后的交谈中却发现兵油子们原本也是跟他们一样的人,也都种过地,每张青黄脸上瞬时都没了先前的兴奋,“满肚子的蹩扭没机会发洩了”,“谁都知道了这三个是跟自己一样的人,似乎该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24]。虽然他们闹不明白为什么本是同一阶级的人竟会成了仇人,但却抛却了先前的怨恨,代之以真诚的关切和帮助,“每个人都想着自己得给这三个人做点什么事”[24](P108),一句“咱们”便彻底拉近了彼此的心。
总而观之,左翼乡土小说作家在塑造看客形象时,既有意识地从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家身上汲取养分,也依据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时代语境转换有所调整,从而使得看客形象更趋繁复和深化,因此在给读者带来新鲜体验和感受的同时,也使得看客形象得以传达出阶级斗争和时代变幻的讯息。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自序[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钱理群,王得后.鲁迅作品全编(小说卷)[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3]鲁迅.祝福[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5]端木蕻良.大地的海[J].文学,1937,9(1).
[6]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7]鲁迅.我之节烈观[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8]王统照.父子[J].文学,1933,1(6).
[9][奥]弗朗茨·乌克提茨.恶为什么这么吸引我们[M]. 万怡,王莺,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0]鲁迅.娜拉走后怎样[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1]陈继会.“看客”:鲁迅独特的形象创造——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J].郑州大学学报,1986,(4).
[12]张子三(许杰).七十六岁的祥福[J].现代小说,1928,1(6).
[13]戴万叶(戴平万).激怒[J].我们月刊,1928,(1).
[14]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5]蒋牧良.当家师爷[J].现代,1934,5(2).
[16]任公(梁启超).本馆论说:呵旁观者文[J].清议报,1900,(36):2313-2321.
[17]沙汀.一个绅士的快乐[J].现代,1934,5(2).
[18]鲁迅.集外集·《穷人》小引[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冯骥才.中国人丑陋吗?——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序言[J].杂文选刊,2008,(6).
[20]戴平万.春泉[J].新流月报,1929,(3).
[21]皇甫晓涛.现代中国新文学与新文化[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
[22]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缪军荣.看客论——试论鲁迅对于另一种“国民劣根性”的批判[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5).
[24]张天翼.仇恨[J].现代,1932,2(1).
责任编辑:张东丽
作者简介:田丰(1981—),男,河南新乡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09-02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5)06-0038-07
doi:10.3969/j.issn.1671-3842.2015.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