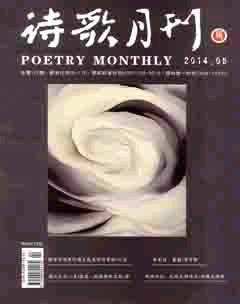在迷魂汤中折腾

这个时代的迷魂汤,花样翻新,但在人性的津唾泅染出的味蕾上,却也有隐约的类型可以辨认。社会文化批判者可能会努力寻找出配方中有些诡异的“药引”,譬如信息高速公路对时空感受的修改,以为就此可以撬开历史和现实的风貌之窍,或者,就此可以神秘地探得时间深海的骊珠;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虚无的烟雾,毫无例外地会抹平这一切。
对于一个沉湎于当代新诗写作的人来说,时光汤汁表面漂浮的青菜叶似乎也别有深意。在他通过语言的触须和这个世界纠缠时,也许会蓦然发现自己竟是独特的那一个。
哪一个?
我们都在狂饮或浅酌时代卷送的迷魂汤,厨子隐约可辨,但谁也不敢肯定他究竟是不是撩开厨房脏兮兮布帘端出汤品的这一个。
化欧化古是一种厨子风格,横眉呵斥是另一种;扮酷剔骨呢,也是一种,慈悲进而垂泪,当然也是……万物在词语的案板和华丽或朴素的刀法之间,被卷进形式铁锅熬制,但它是否较为充分地保留了原材料的口感,是否让迷魂汤也是醒神汤……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每个诗人或多或少在他制作的汤品中流露出他先此被养育的口音,即是说,他先此已经经受过一种更为微妙的迷魂。当然这不是封闭的遗传式密码,而是在时光和事物的摩擦中亮出声音、进而也把自己“糊弄”得清醒的迷魂——无论如何,这还不会让他的舌尖分叉:在汤面漂浮的青菜叶微微的颤动中,在热乎乎的小气泡轻轻涌破之时,诗人已经在那几乎不可见的缕缕青烟中暴露出他的出身,他的地方性。
有时我会惶恐,一如一些朋友早就感受到的那样,我写下的文字,平舌音和卷舌音往往混淆,而元音却自带着不可抑制的喜剧性,即使我曾在疏阔的北方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锤炼过自己的舌头,这一点,也没什么大的改变。当我用卑微的舌尖品尝自己熬制的汤品时,惶恐,有时会突变为一种莫名其妙的窃喜:诺,这词语的汗气。
这,是骄傲吗?
或许,可以试一试:以舌尖为原材料,混合万物熬制?
哑石诗选
暗花
盛夏了,林木早焕新彩一一
你的身体,仍看得见凛冽、蓬勃的雪线。
江间波浪,汹涌如时代。
厌倦了隐喻,羞愧用文字搓出一股股炊烟。
那里,置换露水裹身的朝霞之自我
与众多愣头青的哈戳戳,并非不是件妙事。
又看见:城市埋首,规划胸骨下轰隆隆的地铁
本意献媚女神,却钻了酸楚的牛角尖。
抚摸你冷玉般的背脊,将晴花细辨……
是的,是的,盛夏了,林木早早焕了新彩。
小巫
小巫是个小屁孩。
他爹老巫,头顶四个旋,络腮胡漆黑
蓬乱,硬得像钢渣子。
修锁匠老巫,手艺细致、温婉
上门服务时,从没惊扰过雇主。
老巫莫得生育。不知哪一灭,从何处,
领回了这小屁孩。
人的命也日怪,小巫对老巫
他奶奶的亲得不得了
成天跟在老巫叮叮当当响的勾子后头
爹呀爹的叫唤个没完。
可这小屁孩,有个怪毛病:
没事时,爱把一把铜钥匙,含在嘴里玩一一
说是像热天含着冰块,甚至
还自吹能尝出铜钥匙在不同时段的味道:
早晨酸酸的草莓咪,晌午
则是又甜又稠的蜂糖味,到了晚上
就有点像烧烤摊上,刚烤熟的、还在冒气的
金黄鹌鹑……对此,老巫并不介意
“由他娘去吧?”大家也说
“对着呢,准他娘的没点让人别扭的毛病呢?”
可有些毛病,是不能由他娘去的
一一昨晚夜半,老巫住院了:
他,被人挖了眼睛,作案者正是小巫
一一趁其熟睡,这个小屁孩
用那把已被含得精光闪烁的铜钥匙
噗哧一声,挖掉了,老巫的左眼。
酷刑
读到耶胡达·阿米亥的一句诗:
幸福的人儿,在乌黑的头发上扎条细细的金带。
有点愕然。继而,窥见本地
凉菜大嫂的单车,蝴蝶样掠过筒子楼前。
她嚼着胡椒,尖声尖气朝门房喊:
“嘿,帅哥,今天要买大头莱哇……”
幽晴处,肯定有天使,宽恕了她腰际晃悠的赘肉
一一这也是条细细的金带,一种神秘
一一我的妈呀,饶了我吧
我想,我还分得清什么是天空的盛大,什么
是痛、偶然。譬如,你拖鞋米黄
我睡袍却奇怪地晴蓝。
好在,都还合身,再说了,赌气之时,
不是讨论过那些可爱的酷刑吗?
这,地球人早就经历过。现在,还怕个铲铲!
桌上,从市场买回的车裂果,细圆、红亮
像极了樱桃 我们一起怯怯品尝,用涂蜜之舌尖:
当其时,成都这旮旯,暴雨如注,清凉透骨。
戏剧
于小小弹丸之地翻云覆雨。按理讲
这未免不是场戏剧?
晨曦,挤出薄荷味牙膏……
锦官城一排排舌苔暗集的口腔,被细心打理。
你,连短裤都没来得及穿呢
座于冰冷马桶,悍忪着,那话儿翘得硬梆梆的。
似乎无需对话,无需
翻耕门我。她,蜷于绣榻之中,清明极了
星空红移,揭开你颅骨。窗外
一排翠绿、慈悲的树,手臂挥舞,狂草醉人《史记》。
清粥
晚餐,只喝一碗清粥。
这事可赞美。用哲学,或斜阳下的垂柳。
走进一家粥店,看见老板娘
和两个小妹,正埋头点数一天收获一一
钞票花花绿绿,壹圆归壹圆,贰圆归贰圆
暗花木盒中,不时落进儿枚闪烁、
滚网的硬币。灶台,听了响动,竟一旁淡淡闲着。
这事,毕竟有些喜乐,可赞美。
能否喝上那碗清粥,完全不要紧啊。
她们有的穿红、有的着黄,腰身里有火星
被我惊动,忙不迭跑过来时
多么像一条条破雾而来的河流一一
真的,能否喝上那碗清粥,完全不要紧啊!
一一晚风,吹开胸前大片晦涩的自由
北风
你这糟老头,风卷茅屋时,如何看待言语之妙?
别着急。喝完这杯卡布奇诺,我会
给北风的猫爪发短信。
冰凉、傲慢,蛰伏在苦胆里,弓起细细的闪电形茸毛。
你一直想看清某些东西,譬如它眼眸中
的阴影。那安静、粗暴,那突然
翻脸时星河倒灌之玩笑……
有人成天躲着,像胆怯的保险商,把自己都搞傻了
你运气似乎好点,懂得不妙之妙。
嗨,神会劝它对你更好些一一浊洒入梦时
总该跳出二三风骚猫爪,潜入浣花溪
捞得数条湿漉漉小青鱼一一
小青鱼娃娃一样叫唤着,身体破布般呼呼乱抖
一一醒来时,发现自己就是那猫爪:
山河漶漫的肌汁里,有清凉月光,也有猩红铁锈。
昨晚,我在英特网上搜索,竞看见
成千上万人,仍在化验你胆汁的嗷嗷乱叫
一一某个为“革命”急得流下鼻血的人
悻悻然,于这憋闷、平庸的年代
用6612个汉字,力挺你为“烂醉是生涯”的代表!
他写过诗,毒害了江南空气。
嗨,糟老头,舌尖的铁器上开优昙婆罗花
的糟老头,你之乱劈材、言语之妙
真、真会把我等搞糊涂耶……
山河欲向暖,且读读北风回复的短信吧:
“春口典衣,浓苦即香;瑟瑟幻象,鱼肉清凉。”
辩经会
有人善写冒烟的诗句。其速记簿,转瞬间
就变黑。他的梦境,下着灰烬之雨。
多少世纪前,一个紧要关头,青葱终南山
我还穿着五彩斑斓百纳衣,就曾怂恿弟子
和他扳过手腕。那一天
斋堂闭门熄火。我一直让胃干净地空着。
上山路湿滑,又让我顿悟:一天的大部分光阴
应消耗在对风景的胡思乱想上面!
其实,除了白浆果、消融的山石,几乎没什么
值得我们停下来,理一理微微喘气的
肝、胆。风是凉快的,我知道
涉过那条溪水时,名叫“欢欢”的大黄鱼会蹦出来
尾鳍蒲扇般大小,唇吻蓝得亮晶晶的
一条、两条、三条……就像当地人所说
它们,会模仿出家人热烈诵经。
但我一直认为,那奇异鱼吟当另有出处:
神秘、宽阔、冷峻……赶至约定地点
我们的对手,已在蒲团上盘腿睡着了。
一个弟子,用枯枝碰了碰,他竟噗哧一声闷响
化为一股青烟一一今天,在锦官城
购书中心,我又遇见了他。西服,金丝眼镜
签售一部哈戳戳的诗集:《牛死之间》。
额头上,有道闪电形印痕,晴褐色。
我买了一册,笑眯眯走到他跟前,请他签名一一
这样,扉页上就会留下他龙飞凤舞的容颜。
他抬头看我,似乎想起了什么
又似乎有雾挡在眼前,搞得双眸水汪汪的
一一唉,唉,唉,这迷茫、背时的倒霉蛋……
等待
街边女贞树下,他做扩胸运动。
比小学生课间操还认真:挥臂如桨
嘴紧撮。看不见的波浪中
有点秃的脑袋瓜,一耸一耸向前划。
夏日阵雨,来得猛烈,哗啦拉一阵冲刷
之后,就咽气。凉意未至
却溅起丝丝甜腥,让烦闷更为广大一一
植物比起人类,也许豁达许多。
女贞树又绿又亮,繁盛得有些逼人
风起,那一嘟噜一嘟噜小腰子
好似充盈着用不完的神秘汁液
在头顶闹喳麻了:一个月前
这精致、可爱的宝贝疙瘩们,还是些
枝叶问沉默、细碎的花一一
他,还在树下做扩胸运动。他背湿透了。
而她腰际,有一船形诡秘刺青
如细细抚摸,会涌出真实的海水:
“帕耶罗珀,也是朵细碎的花?”
唉,他很想大呼一口气,让秘密减压。
梦
如其所是。天上有淡墨色积雨云
希望,为它镶上金边一一这样,即使
那些悲观者,小小的悲观者
团身坠下,雨点一般将船坞敲响
你也可收获宽慰之落口。难道不是吗?
太阳心脏,贮满神秘液体。
沙滩,细腻而微凉。一排排海浪
从赤裸足旁,一直铺展到不断蒸腾的远处:
其刹那涌现、刹那芥裂之裙边
于某种颤栗余光中,从深蓝
渐至浅蓝、微黄,进而,璀璨牟金黄!
我们都曾在海浪里呆过,作为
海藻、气泡,抑或清寂而慈祥的海象……
现在,锦官城就是那荒凉船坞?
曲街弯巷,如海底皱褶,塞满咸腥淤泥。
我们却是旱鸭子,嘎嘎摇晃着
瓜兮兮,慢慢托身于榨取体液的伎俩
一一死亡,或许是个颤栗的出口:
向着寂静,侧耳搁浅身体巾的片片海浪。
昨天,我们一同仰望着锦官城上空
淡墨色的积雨云,看她在风中悠悠消失……
晚上,你就不争气地做了梦:
细腻、宽阔的海滩,落霞绚烂至极。
海浪轰鸣声中,两头体形庞大如山的抹香鲸
冲上清凉海滩做爱一一不慌张
不颓唐,优雅性器颤栗着湿润的光一一
从深蓝,至浅蓝、微黄,进而,璀璨到金黄!
青城诗章(选六)
若是大师使你们怯步
不妨请教大自然
——荷尔德林
进山
请相信黄昏的光线有着湿润的
触须。怀揣古老的书本 双臂如桨
我从连绵数里的树荫下走过
远方漫起淡淡的弥撒声。一丛野草
在渐浓的暮色中变成了金黄
坚韧 闪烁 有着难以测度的可能。
而吹拂脸颊的微风带来了琤淙的
泉水、退缩的花香 某种茫茫苍穹的
灰尘。“存这空旷的山谷呆着多好!”
一只麻鹬歇落于眼前滚圆的褐石
寂静、隐秘的热力弯曲它的胸骨
像弯曲料大的磁针。我停下来
看树枝在瞑色四合中恣意伸展一一
火焰真细密 绘出初夜那朦胧的古镜。
满月之夜
现在 我不能说理解了山谷
理解了她花瓣般随风舒展的自白
满月之夜 灌木丛中瓢虫飞舞
如粒粒火星 散落于山谷湿润的皱褶
有人说:“满月会引发一种野蛮的雪……”
我想 这是个简朴的真理:在今夜
在凛冽的沉寂压弯我石屋的时候。
而树枝阴影由窗口潜入 清脆地
使我珍爱的橡木书桌一点点炸裂
(从光滑晴红的肘边到粗糙的远端)
曾经 我晾晒它 于盈盈满月下
希望它能孕育深沉的、细浪翻卷的
血液 一如我被长天唤醒的肉体
游荡于空谷 听山色暗中沛然流泄
雷雨
被一根充满静电的手指缓缓地
抚摸 没有不安。这是先兆:
山谷中的雷雨来得总是那么自然!
微风催促微褐、温存的指头
沙沙地 将万物包裹的细小灵魂
从里到外摸了个遍:黄叶肥大
浆果正把油亮的脂液滴落如绒的苔鲜……
接着 雷雨会在渐渐空阔的身体里
升起、释放 引发出山谷巨大嗡鸣的震颤
也许 这里的雷雨与别处没什么不同
我能肯定的是 幽晴与明亮交错的山谷里
雷雨会使飞鸟的骨骼变得硬朗
而仿佛突然问冒出的花花草草
在喊:“嗨 让我流水般活上一千年!”
黎明
勿需借助孤寂里自我更多的
沉思 勿需在镜巾察看哀老的脸
其实那镜子也和山谷的黎明
一样朦胧。今天的黎明就是
所有的黎明 露水、草霜、清净山石
偶尔会泄露矿脉乌黑的心跳。
“你未来之前它就这样做了。”
现在 你是一粒微尘溶在黎明里
筑一问石屋 只是为了更为完满地
体验肉体的消亡 体验从那以后
灵魂变成一个四而敞开的空间:
昆虫、树木在这里聚会、低语
商议迎接沭风而至的新来者
就像镜子迎接那张光芒四射的脸。
野苹果树林
石屋背后的山坡上 有一片
野苹果树林。大概占了半亩地左右吧
去年 我用山溪里搬来的圆石
垒堆石屋时 还不觉什么异样。
今年春天 一个蓝雾散尽的清晨
山谷才指点给我这美妙的景观:
密密匝匝的白花如浴女羞怯的凝脂
正在屋后摄魂地晃闪……“怎么这样粗心呢
即使作了秘密之美的邻居也不知晓?”
我想:不能随便去探访这片果林
要等到初夏 一个大风骤起的黄昏
当成熟的果子噼噼啪啪坠落屋顶
我会饮着溪水 品尝那赐予我的
直到一种甜涩的滋味溶存骨髓里而……
交谈
今天是个睛和、新鲜的日子
拨开齐腰深的草丛 在山谷里
我找到了那鸟蛋蓝幽幽的声音:
暗褐是野鸽的 银白是雷鸟的。
作为山谷巾万千事物恬静的一员
我站得如此之近 又深深注视着……
或许 我真的领悟了植物们
潦乱中的精确有序 领悟了动物
温顺隐忍、但又迥然桐异的命运——
瞧 山体里潜伏的钨矿正沙哑地
悸动 其额头润泽、坚韧……
而当我试着与周围彻夜地交谈
那双宏大之手就会使一切变得简拙
像流泉 轰的一声将星空、微尘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