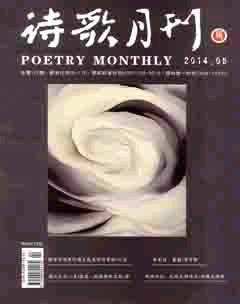一场波逐中的滴水以及她的巫性
他是谁?他从哪里来?
我是他的一部分,更精确的修辞是一粒尘埃。当一束波光显明尘埃的无限运动,我惊异于我对于黑暗深处的迷恋与弃绝。大约是从这里,我初始化,在一场波逐中开启我的诗性,幽速、切入、幻化而成另一个我。我和另一个我,合成一个诗歌生命,他划清我与另一个我的界限,使我悚然有知:他是全部,而我只是一粒微尘。
初始化的我,是青春大草原上的一匹狼。青春作为生命个体的驱动器,把十六岁的我从故土猛掷到苍穹,自下而上,完成首次蜕变。我簇拥着我,不屑于成为他者,有一点点蔑视。驰骋如此疆域的我,必将一瓣瓣撕裂自身,抛向盘旋已久的秃鹰。草原狼在高原鹰的腹部完成生命的X次对话。听觉让我获悉一切,我悄悄把这些碎裂的血肉还原为一具躯体,接通言语的魂脉,吹入诗思的精气,他者就会诞生。诗歌生命,是一个深知他者的人,唤醒字词的巫性而催生的一个生命体,密织环进。当他离我而去,我隐匿,他敞明:执我者死。
必经之径是作为言说的符号 我,穿越作为肉身的迷宫 自我:内置的窍目、节骨和息息相关的附体。恰恰在这里,极大多数人把一生葬送在半途,现代性的垃圾大多源出于此,浊气正在蚕食祖国的少年,只有少数人能在凉风的搀扶下,最终成为凉风的一部分。直觉可以穿越部分黑暗,抵抗垃圾化,但更深的黑暗一定得是经久不熄的燃烧,生命对话由X次修正为N次,单一的方向变得环复,自上而下,由北向南,左冲右突,生命个体完全化为火焰,火焰的内部是全部的黑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苍溟,我在他的深处跃升、返转,与自身同一,他称我为你,我称他为我们。
我曾经在直觉的诱惑下,开始百米冲刺。直觉奠基的跑道,注定不会被杂草荒芜,如果得到硬化,就成了起飞的跑道,云兮鸣吼。被打开的直觉广阔幽深,舒展的云群之上,波光碧透,而我隐匿于一只晨乌的腹部,感受到逐流的眩目与忧伤,随波的困倦与自明。
我真想成为一个随波、逐流的漂流瓶,把充溢其中的骇浪倾泻在麓山脚下,把浮云洗黑,成为沃野,复活是可能的而且必要,这就是幸至。南蛮之地的野性与巫风,生养我于斯,始于一粒受精卯。孕育我的却是一滴水,在新墙河的下游,一滴水在必经的厕所旁,从樟树叶上悄然滴落,把少年的我耸入云端。我写下生平的第一首诗《大树》,至今,我仍徜徉其中。今年六月五号,我莫明的写下《款待》,掏空一滴水,安顿好一场波逐中悦乐与寂寥。
掏空一滴水,做个小房子,
如此不再贫乏,孤单
掏空的一水,是谁的故乡?倘使是我的故乡,说明我的诗歌生命有幸获取了自身的蛹体,我还在,就像我还能在相公岭、三江口、麓山脚下晃悠。倘使是他的故乡,则是盈逸的诗歌生命筑建了自己的家,与我断绝关系。然而你会、司,我到哪里去了?这分明是在质疑:一个人发声的方式,他的腔调,何以在一目了然之后变得形迹可疑?我有别于那个诗人,诗人有别于那些作品,仅仅是一种气息,但明眼人一闻便知。
这就是说,我在某个地域或一个类似栓马桩的地方,得以完成初始化,并接受晦暗的雕刻,愈来愈确凿,以至于成为一张非标准脸孔。这令习惯在格子中囚宿一生的人恼火,更让全球化的格式刷失效。问题出现了,经典化在绞灭种种盎然生机之后,饕餮之光总会扫向下一波菱角、和刚刚溢出的二锅头,鲜活与浓烈,总能让老家伙拿出格式化卡尺,他们仅仅是发明者的影子,使唤一辈子,有模有样,如今却力不从心。不适可以理解并得到尊重,但不能原谅由此而来的狰狞、愚钝和似是而非的庸见。
被格式化中的标准面孔,在地方性中得到化解、拯救。我一次次逃离虎口,重新回到相公岭、三江口和麓山,甚至深冬的青春大草原。我与自己汇合。或者说我肉身所界定的地方性,融入了一种新的生命,那是灵魂的地方性。言说中的颗粒,幽蓝透风,我偷看自己,如此浑浊。
写作的生命或诗歌的生命,安居此地,晦暗的我变得透明、盈逸,成为波逐的云彩。这样的地方性色彩,必将成为光明的一部分。文明正是聚集几乎所有地方性的亮光,令人在目眩之中忘记方向,当他终于在窒息中悠悠醒转,会欣喜于我是他的一部分,一粒尘埃。而我,仅仅是地方性中的造物:唯一不能消融于任何事物的一抹波光,一粒微尘。未能格式化的滴水洞,未能全球化的巫性遗存,令我欣喜,经典化是一百年后,乃至一千年后的无意识运动,与阴谋、盲目和造神术无关。当下正值垃圾化运动的波峰,全民参与,唯有相公岭的凉风,沐我于一滴水的溟空,只有一个深深的母亲!
初始化与格式化之后,我来到故乡,风习与箴言重新把我地方化,触土生根,仿佛我还是原来的我,只不过是浪迹归来。事实却相反,是我被拣选出来,一张非标准的脸孔才是唯一获准通行的入场券。我拥有我,即我最终拥有作为我的资格,我生下我,即我在绝望的深处醒转后,体悟并应和诗歌生命的本真呼吸:抑浊、扬清。生命本身获悉苍天的耳语、如一阵悄然而来的凉风,译出此时、此地、此人的机缘信息,即把捕捉到的波光析出为晶粒。他们嬉戏于我的内心,光芒涌入。敞亮的世界看清每一个人的地方性即他的来路,绝不会误认为从风云(全球化)中来,而成为风云。文明谱系上的每一张标准脸孔,都有一个渐渐隆起的眼睑,恍若新坟,那里埋藏着地方性。他孕育着我、你,都在一场波逐中与波光展开殊死博弈,而永不消逝的幽暗颗粒,是地方性微弱的呼声和他饱含的乳汁,把经由他者而返回的我和你喂养。大地由此重获生机,哦荷哦荷。
2013-6-23,写于北京。
路云诗选
款待
掏空一滴水,做个小房子,
如此不再贫乏,孤单。
一小勺惬意,从内部上升,
渴念结出一层薄冰,庇佑我深入
一场初吻中的酷暑和秋凉。
沉默是冰封之下的河水,往事
自由出入,摆动尾鳍,免除
霜冻的管束和深水中的寂然。
我乐于用指间的风,弹奏露珠中的
四季,你的眉睫成林,结满桨果。
唯有舌尖上的波光,把汗滴追逐,
密切的汗花开满银沙滩,至乐无边。
众人散尽,沙粒发出细小的呼声,
心底里的话,应和着沙沙的海浪,
析出晶粒,倾满盐罐。每一个日子
都是一把小勺,贴心贴肺。
浮光中漂白的倦意,晾在哪,
哪里就有朵朵闲云,摘下来
酿成土家红,黑糯米是她的母亲。
带着微醺中的快意,肩程吧,你,
麓山用一片枫叶包裹好我们,
托付给一阵凉风,哦荷哦荷。
2013-6-5
光虫
角膜与眼帘之间,是我领空。
我有众多发光的儿子一一光虫,
他们密切的飞行,令我的国度
昌明如炽,令我形同虚设。
我的巫婆睡得比春天还香,
她生育的儿子身段柔软,精气充沛。
他们无法无灭,常常掀开我的梦!
咳,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的巫婆啊,你醒来,管管他们。
我用我的眼珠子编好一副光帘,拉上,
仍能辨认家的方向,家在不远处,
是拼着最后一口气可以抵达的地方。
我用记性和想象喂养他们,希望记下,
但更多是徒劳,我的国度百孔干疮。
唯有歌声,至爱的歌声把我灌溉。
我的巫婆,她隐而不见,她的脾性
如同我的缺陷,尘世有多少伤痛!
巫婆,你回来吧,当飞蚊侵入我的国度,
你为何畅悦得一如瀑流?我的错误是
仍未还清的息偾,你只会栖身在它的尽头。
我知道,我不会舍弃药草和她的芬芳,
当有一天,光虫不见,光帘永远拉上,
我相信是睫毛坏了,你会修好她。
是的,你不再撇下我,我会加入飞行中,
守护至福的口夜,如光永在,如影随行。
2011-12
采声者
今夜雨滴是一群挨骂的蜜蜂,她们采集风粉,
风不是一朵一朵的花,更不是一遍遍的园地。
今夜雨滴急急呼呼,在我的耳背停下。
这个菌状地带,没有亲人,没有惊痛,
只有一滴水,成为采声者的旅馆。
众多雨点挤进来,我忙得团团转,幸好有耳朵
可以装下一切。一切并不说明风是一个可以放弃的
念头。如果这个耳朵不属于我,是一片瓦,那片
堂屋顶上的亮瓦。她会不理风,放走不信邪的光。
光在我的耳背上产卵,像鸟一样衔来枯枝,
成为我的同类和伙伴。光和风,
我理解多少,就能走出多远。是光在松涛上,
拿出手电筒,找到风,找到我的耳朵,安顿好那么多雨滴。
2006-6
在郊外我是个小工
在郊外我渴望租用一个窄小的子宫,
生下爱情。郊区是我的初恋,
她的固执不合时宜。在郊外我是个小工,
把某些东西搅拌、碾碎,放进墙体,
墙而摇晃,有时候我被摇下来,
又摇下来,但我不曾动摇。
如果城整个塌陷,我仍会把筋骨挖出来,
那些不能丢,我也不会丢。
我会重新开始搭架,在各种目光中搅拌,
碾碎,放进墙体,墙而晃动,晃动,
我也晃下来,陷落,变迁。
像我一步步后退,随着郊区的节奏,
在某一天,靠着我的出生地和故居。
在这里,我会呆上一阵,当个义工。
那些磨灭的角线与墙体吸引我,我为之
震荡,像我不再谈论我的父亲和他的模架。
有一次,父亲用双手整平一口泥砖,
大拇指顺手一摁,在右上角
摁出一个洒窝,那满盏笑意
印在我心上。那四角四印的砖坯,
比镜子明亮,可以看见我青春的全部。
有一些在暴雨中溜走,他们没有留下姓名,
有一些进入土窑,把水分挤干,
成为基脚,在这里我懂得火是基础。
大部分停在风中,进入墙体,
如果抚摸它,像刚出土的铜镜,
有些事情温热可辨。火与土居于最下面,
土和风在中间,风和水在上面。
那古老的手艺我不曾学会,渐渐废弃,
但我不会忘记,这样的爱和坯子。
他们是一个更大的镜而,照看我的小酒窝,
这隐约的居所,停在右上角,在某个墙体当中
成为空隙,被忽略不计,正是它在等着我。
2007-12
我按揭自身
我从火中搬走,像浓烟冲向天穹
一一她优美的身姿征收了夜色!
影子征收了我,我在黑暗中找不到
我一一一个没有影子的人。
我在哪?我的影子在哪?
当全部的影子聚集,血色殆尽,
如一朵干扁的桅子花,
她何以回到肉身一一凿开一扇小窗?
一只小雀的即兴鸣唱,直抵谎言的
背脊一一她的绝色令我俯手画押。
一代人关在门外,黑暗被加工成方向
趣味和一条死胡同,没有一个跃动的影子!
我默然,我的影子一一颤悠
如一只巾风的手,按不好一个手印。
以今夜的忧伤作为红线,我圈定
一条雀舌的边界,形如一片尿迹。
我按揭自身,把不安的影子赎回。
我和我的影子,加入浓烟的领空,
黑暗中飞行的事物,被典押给烟囱:
她滚烫的舌苔上,放不下一张小床。
2011-12
如何把内心的苍白涂黑
黑发一旦卷成云髻,鹤光就长出翅膀。
当我意识到最初的鹤色是盎然稀落的,
只能贴地爬行,向丛林深处的幽暗。
没有哪一阵风,能扶着她立正、稍息、
向左转,向后转。一眨眼间,她已学会,
挺直腰杆、一言不发,等着岁月的银屑,
从黑发梢头初上。秋霜染白晚风,林中的
丝茅草,轻轻锯我。我在愕然中扑打翅膀,
误入云鬓深处,最初的谎言是绯色的。
她悄然变频,像我的喉结,在多种腔调巾
挺胸、收腹、屏住声息?我早已领悟白发,
并非怯懦者的发明,时光的修辞术。
为着把内心的苍白涂黑,我在云卷中挥毫,
耗尽一生,鹤光惊现。最美的苍老一定是
鹤色的,当我意识到什么,奶奶已藏进西风。
奶奶的满头鹤发,是否变身她的坐骑?
那个清晨,一声老鸦叫波及老婆的耳膜,
耳膜振动她的手,手如芒刺,我如针毡。
一道鹤光目睹我,忽暗忽明,渐渐苍白,
如窗外一粒阔楔形的呜叫。哦,鹤色的光,
穿越惊疑,绘出先于黑暗抵达的形迹,
膝下的麻布垫圈,恍若一团疑云,她彻骨
的眼波把我淹没又捞取,涂黑又涂灰。
2013-6-26
筹码
冬天是一场赌局,大雪用手掌,
沉默用你,把枯荒典押给春草。
亘古的筹码,是一口小小的热气,
岂是百花香?倘使我输得精光,
赤裸如冰霄,你何故唤来秘仪,
化作北风。她寂然的面容清冽,
照见我的硬心肠,是一盘铁索,
恍若一只寒蝉开屏。在哗然中,
我转身凋落,瞥见那张孤独的脸,
皱巴巴一张赌桌而布。一粒骰子,
抛出言辞中的弧光,照见苍白,
恍若鱼肚。波逐其问,一牛何忧?
用平庸制作的外衣,你何必翻卷,
一遍遍在热泪中洗刷,令我溃疡。
恰恰是她,那副特制的翅翼,
庇佑我起飞,穿越庸碌无常,
侧身经过时光的每一个瑕疵。
当我押上一生,你啊,请乘坐
一朵绯云,追上那个大赢家。
他化作一阵阵喘息,你又何必,
何必按住光的气穴,一言不发?
2013-7-1
父亲,我父亲
我相信每一日的行走,都是深入泥土,风沙,
当触及腰身,我看见十字,停在大地当中。
这令我惊讶,泥土是银行,风沙是银行,
我把生命作为定期存进去,取走稻米,蕨类,
和一大早的呜叫。父亲取走一大早的扁担,
那是一个旋转的十字,从上面看从下面看,
从左右两边看,它都在担当着什么,晃悠悠的,
从不走形。当他睡下,有一次,我拿上扁担,
横放在他肚脐眼的上而,又是一个十字?
我猜测父亲不知道,但我错了,父亲一醒来,
双手自然而然拿着它,显明那晃悠悠的十字。
这里面的变化我不懂,父亲明明挑起的是
井水和稻谷,怎么变成了生活、责任和爱?
当母亲把捣衣槌横放在父亲的换洗衣上,
我看见同样的十字,我偷偷看母亲的脸色,
是一个池塘大小的宁静。在夜色中,
母亲由南而北从对门山的菜地回家,
与踏着曙光的父亲不同,父亲从村西头走到东头,
开始一天的劳动。我站在屋前地坪的中间,
位于这个由脚步和小径组成的十字路口,
我徘徊,我相信每一口的行走是沿着父亲的目光,
沿着母亲的目光,通向明天一大早,
通向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当我迷途,我回来,
把那扁担,捣衣槌,随意放在什么地方,
甚至摆成一个十字,我会怔怔地望着,低下头,
想着腰身以上的不安和爱。
2007-12
在云里汇合
一一怀念闻韶
我的太阳穴长满丝茅梗,
准涉其中?我在头顶急急赶路。
风泛白,我独入潜影,割下鼻子,
交差。血液像麻绳,拴住我,
头痛收割一切。把它种在门槛上,
来年,镰刀架上脖子,粒粒盎然。
我不能更大声,它的重量压低嗓音,
像一阵脱臼后。故乡!我悸恸,
如云雀呜叫,春天悄然下沉,
你蓝色的眉睫,那丝茅草!
我沉醉其间,道道血痕,刻下欢乐。
故乡,你宽额敞亮,养育众水,
把我轻轻劫持,波澜不惊。
弯道镜乍现,我在冷汗中盘旋,
在云里汇合!头顶的凉风,
掀开苍茫一角,茅草掠过枯光。
我归来,这一亩三分田,好坟头,
寸草复生,岁岁之父,故乡永无止境,
我听见,我哞叫,我涌现。
2011-3
一只煨罐
存街河口,我看见一把小勺子
像舌尖一样伸进一个樱桃小口。
小勺子在烈口下的阵阵反光,
差点把我煨熟。我一直在寻找
那只煨罐,粗心的父亲找不到,
梦中的母亲纳着鞋底,含笑无言。
两个舌尖传递着柴火的爱,
我在大地深处热气腾腾,
恍若那只失落的小静瓦罐。
她喂养着我,最初用文火,
融洽的汁液灌溉我如良田。
如今,我的几中长满猛火般的牙齿
却咬不碎一个饱嗝中的倦意。
难以下咽的东西,提醒我回过头,
把未来还给未来,而回忆就是
那只小瓦罐,她煨着我,
在另一个舌尖上说出爱。
2013-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