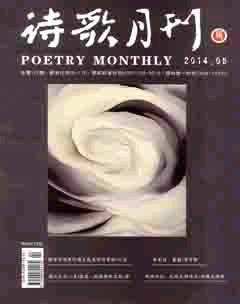关于云南的诗稿

这些年,我的确写了很多关于云南的诗稿,这是因为我认为云南是一个诗歌出没的地方。礼失求诸于野,云南有足够多的野,野外,野草,野山,野水,野之间的人民及其文明,我之写作,类似于古代的采诗官。稍有不同的是,采诗官得到的诗稿,意在建构中国古老诗歌的最初庙宇,我在野地上得到的一切,则意在搭设一个可以体现我诗歌梦想的纸上荒野,并借以反对身边猖狂、霸道的诗歌政治学,以及颠覆了千年文明的工业化的暴力文明。沈浩波曾将我视为腐朽的“乡村才子”之一,殊不知我的内心也藏着猛扑向诗歌未来的干军万马。但我始终觉得,我们这一代汉语诗人的使命并不在于迅速再造神圣的诗歌天堂,而在于在诗歌乱世之后恢复重建一座座塌毁了的诗歌小庙,让诗歌重获良好的文化生态。革命总是静悄悄的,从野外开始的革命,尤其是当这种革命只是基于诗歌精神的重建,它甚至可以视为一个诗人的自虐或自讨没趣!
雷平阳诗选
基诺山上的祷辞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一只大的麂子
神啊,感谢您今天
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
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
荒城
雄鹰来自雪山,住在云朵的宫殿
它是知府。一匹马,到过拉萨
运送布料、茶叶和盐巴,它告老还乡
做了县令。榕树之王,枝叶匝地
满身都是根须,被选举为保长
一一野草的人民,在废弃的街上和府衙
自由地生长,像一群还俗的和尚
大象之死
它送光了巨大身躯里的一切
对没有尽头的雨林,也失去了兴趣
按常理,它对死亡有预知
可以提前上路,独门前往象群埋骨的
圣地,但它对此也不在意了
走过浊世上的山山水水
只为将死亡奉上,在遍野的白骨间
找个空隙,安插自己?它觉得
仪式感高过了命运。现在
它用体内仅剩的一丝气力
将四根世界之柱提起来,走进了溪水
之后,世界倒下。他的灵魂
任由流水,想带到哪儿
就带到哪儿去
穷人啃骨头舞
我的洞察力,已经哀微
想象力和表现力,也已经不能
与怒江边上的傈僳人相比
多年来,我极尽谦卑之能事
委身尘土,与草木称兄道弟
但谁都知道,我的内心装着干山万水
一个骄傲的人,并没有真正地
压弯自己的骨头,向下献出
所有的慈悲,更没有抽出自己的骨头
让穷人啃一啃。那天,路过匹河乡
是他们,几个喝得半醉的傈僳史弟
拦住了我的去路。他们命令我
撕碎通往灭堂的车票,坐在
暴怒的怒江边,看他们存一块
广场一样巨大的石头上,跳起了
《穷人啃骨头舞》。他们拼命争夺着
一根骨头,追逐、斗殴、结仇
准都想张开口,啃一啃那根骨头
都想竖起骨头,抱着骨头往上爬
有人被赶出了石头广场,有人
从骨头上摔下来,落入了怒江
最后,又宽又高的石头广场之上
就剩下一根准也没有啃到的骨头……
他们没有谢幕,我一个人
爬上石头广场,拿起那根骨头道具
发现上面布满了他们争夺时
留下的血丝。在我的眼里
他们洞察到了穷的无底洞的底
并住在了那里:他们想象到了一根
无肉之骨的髓,但却难以获取
当他们表现出了穷人啃骨头时的
贪婪、执著和狰狞,他们
又免不了生出一条江的无奈与阴沉
一一那一夜,我们接着喝酒
说起舞蹈,其中一人脱口而出
“跳舞时,如果真让我尝一口骨髓
我愿意去死!”身边的怒江
大发慈悲,一直响着
骨头与骨头,彼此撞击的声音
集体主义的虫鸣
窃窃私语或鼓腹而鸣,整座森林
没有留下一丝空余。 一听出的是青蛙
它们身体大一点,离人近一点
叫声,相对也更有统治力
整整一个晚上,坐在树上旅馆的床上
我总是觉得,阴差阳错,自己闯入了
昆虫世界愤怒的集中营,四周
无限辽阔的四周,全部高举着密集的
努力张大的嘴,眼睛网睁,胸怀起伏
叫,是大叫,恶狠狠地叫,叫声里
翻飞着带出的心肝和肺。我多次
打开房门,走到外面,想知道
除了蛙,都是些什么在叫,为什么
要这么叫。黑黝黝的森林、夜幕
都由叫声组成,而我休想
在一根树枝上,找到一个叫声的发源地
尽管这根树枝,它的每张叶子,上面
都掉满了舌头和牙齿。我不认为
那是静谧,也非天籁,排除本能
和无意识,排除个体的恐惧和集体的
焦虑,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观点:森林
太大,太黑,每只虫子,只有叫
才能明确自己的身份,也才能
传达自己所在位置。天亮了
虫声式微,离开旅馆的时候,我听到了
一声接一声的猿啼。这些伟大的
体操运动员,在林间,腾挪,飞纵
空翻,然后,叫,也是大叫
一样的不管不顾,一样的撕心裂肺
脸谱
博尚镇制作脸谱的大爷
杀象,制作象脸
杀虎,制作虎脸
他一直想杀人,但他已经老朽
白白地在心里藏着一堆刀斧
杀狗的过程
这应该是杀狗的
唯一方式。今天早上十点二十五分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三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它的头
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色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如此重复了五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十一点二十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山中赶路记
从曼赛镇去阿卡寨,只需要
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却走了整整两天
见到溪水,香堂人光着身子,钻了
进去。时间像一条鱼,在水芹菜
的叶子下面,张合着小小的腮
路边的橄榄已经熟透,克木人知道
有一颗,是悬挂存树上的天堂
时间,在舌面上,缓缓地
由苦变甜。白云是傣族人的表姐
清风是傣族人的姑妈,路边的竹楼上
这一个傣族人,麂子肉和鲜竹笋下洒
喝醉丫了时间,是一张阔大的芭蕉叶
盖着他的脸。基诺人,有着石头
一样的沉默,他的耳朵,却一直关注着
雨林里的动静,不知是什么鸟
叫了一声,他便像一支射出的响箭
时间,被他带走了,很久才从
一只死去的白鹇身上重返人间
整个旅程,只有谦卑的布朗人
静静地守在我身边。我们坐在山头
看落口,看老挝丰沙里烧荒的狼烟
暮投一座古老的缅寺,我睡着了
他才离开,他在我的梦中赕佛
身子紧贴着尘埃。时间,在贝页经里
跪了下来.几双隐形的手,按住了
时针、分针和秒针。我们一行人
还有拉祜和爱伲,山野之上
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相好,时间
奔跑的马蹄,被他们移植到了肺腑里
我这个汉人,多想飞速地抵达阿卡寨啊
催促,埋怨,焦虑,像个疯子
最终的结局,我一个人上路
多次迷途,天黑前,才找到自己的流放地
牧羊记
我在这座山上牧羊
一个老头,穿着一身旧军装
也在这座山上牧羊
山上的两群羊,很少来往
一群在坡地,一群在山梁
一群背阴,一群向阳
山上的草,每天
都被啃两遍。一泓溪水
带走了一群羊,半小时后
又带走另一群羊。它们仿佛
一群是魂魄,一群是羊
那时候,我刚刚学会吹竹笛
常常爬到松树上,一边吹笛
一边盯着夏天的玉米地
锄草的姑娘,花儿一样开放
每天,老头都背着一口
大铁锅,在坟地里
捡来一根根白骨
点燃柴火,熬骨头汤。然后
用一个土碗,喂他的羊
他的羊,又肥又壮
那些白骨,被熬了一次又一次
但每次熬过,他又会将它们
一一放回原地。他知道
它们不同的墓床,从来不会
放错地方。第二天,他又去捡拾
就像第一次那样:扒开草丛
捡起来,鼓起腮帮
吹一下尘土,集中起来
小心翼翼地放入滚沸的铁锅……
我怀疑他知道那些骨头
的主人,却从来不敢与他搭腔
他满脸的阴冷,令我迷茫
而慌张?我曾经发誓
一定要重新找一座山
到别处去牧羊
但我年轻的心,放不下
这座山上,一个穿红衣裳的姑娘
在蛮耗镇
红河边的皂角树上
挂着一把把黑颜色的刀。我的前生
肯定来过这儿。一个农夫
背篓里装满了香蕉,他在树下
坐了会儿,黑色的脸上
藏着我的麻木和安详?他用他的身体
替我,活在了这儿,种植的香蕉
草不像草,树不像树,结出果实却甜如蜜糖
他不是我重逢的,惟一的故人啊
河边的茅草屋,一位老太太
顶着白发而来。流水一样,她说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同样的皂角树下,她打开一个布袋
拿出了一支驳壳枪。暗黑的光
投射到皂角树的一把把刀上
她说起了六十年前的一位团长
那人从这儿骑马北上。那时
她还是一个少女,爱上了团长
之后,她守着一支驳壳机
一晃,就是六十年时光
村庄,村庄集(节选)
拒绝了医生和巫术
也拒绝了一座村庄的奉劝和泪水
一个大雪飘舞的晚上
他把两个儿子,土豆一样
种到了土里。土里的两个儿子
发着高烧,说着胡话
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到了土里……
这个魔鬼,今年八十岁
春天的时候,他顶着一头白晋
跟我打招呼,让我不得安宁
为此,我写下下面这一行字
一一村庄史,因他而冰冷,没有人性
病怏怏的村官,威风八面
他带头烧掉寺庙,把关圣人塑身
丢进了流水。把欧家营改名为爱国村
他指着悲灭河:“以后,谁也不准乱叫
从今天起,它叫胜天河!”
安排工作,他把男人喊上山
女人,好看的几个,喊到仓库择种子
遭他暗算的不少,生下的孩子
一律罗圈腿,也是病怏怏
有一天,他进城开会,疯疯癫癫地回来
口中,全是谵语。碰到女人
马上就脱掉裤子,不干那事
命令女人,不准走开,一定要看他
独自表演。他死的那天,道士说
“这个人,去过地狱里的妓院!”
赶马人路过黄昏的荒原
寒风吹开枯草,露出很多白骨
快马加鞭,他想逃离地府
驱赶了二十多年的马,突然不听使唤
用他的话说,一朵黑云,从地上
升起,散开,一点准备都没有
他就被关进了一部恐怖电影
夹道欢迎他的人.没有头颅,也有的
没有心肝,全是一些身体的残片……
一个好心的盗墓人喊醒了他
他在马车上睡熟了
冬月星空灿烂,荒原霜迹斑斑
四
一只蛤蟆,连续几天
跳到她家门前。不进屋,在门槛外
鼓起肚子,对着神龛,叫得她
心烦意乱。每次,她都用铲子
把它铲起来,丢进了菜园
她始终没有弄懂那只蛤蟆
在喊什么,也没有按照乡下的习俗
烧几份纸钱。黄昏,她进城打工的丈夫
回家来了。由几个工友抬着
一根根骨头,锋利无比
全都钻到丫皮肤外面。一个工友回忆
在三十层的楼顶,脚手架上
他踩空了,像只蛤蟆,笔直地落了下来
五
把一头头猪,杀翻在河边
他的刀,有长的、短的、方的
和圆的。现在,他用牙齿咬住的那把
是红的,滴下的猪血,把草叶打弯
这个老驼背,喜欢开膛破肚
喜欢一刀两断,喜欢提着一副猪心肺
到昭通城换盐。其他人家
门对荒野、河流或良田,他家
高高的围墙,独门独院,与人老死
不相往来。从他围墙外经过
人们每次都听见那磨刀的声音
让人双腿发软。传说,他用乌鸦血
擦过眼睛,晚上,从来不出门
害怕看见村庄里,比人还多的鬼怪
他死的时候,几个侄儿
守在床边,身子躺平了,又撑起来
“我只会杀猪,那边,有没有猪可杀?”
没人回答他,他头一歪
带着疑问,一个人去了那边
六
河流上的堂妹,随水远走
河流的支流,一个堂弟
在水上挖个洞,钻了进去
两个小生命,一个在前,一个在后
一个手中摒着青草,一个口里
含着鸟蛋。一个像清炯,一个像磨盘
那些年的水,清冽、透明、迟缓
那些年的河床,开阔、平坦、干净
我们一直活在岸上,判了死刑的人
手握生机,筹集着不归路上的盘缠
在心上,有时候,为他们修建墓碑
又忍不住羡慕这两个早夭的少年
一一身体鲜美之时,河水清且涟猗之时
他们走了。我们却得继续在岸上
闻着腥臭的河水,一次次将衰败的身体
扶正,拉直,像伺候一堆鱼骨
从来也不敢奢谈湖泊和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