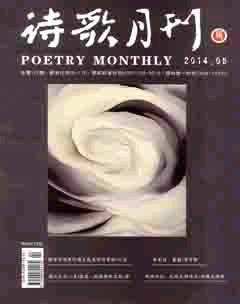城乡结合部的隐喻和宿命

在地球业已成为一个村庄的互联网时代,来谈诗歌写作的“地方性”,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当然,我并非不承认诗歌的“地方性”特征,而是说在我们拥有几乎相近的文化、时代和阅读背景的前提下,“地方性”可能会自然地呈现在各自的诗歌里——如同我们各自不同的表情。
我出生在淮河平原深处,记得我家门口就是一条很宽的河,因为很小就每天帮母亲烧饭,夏天就在烧完饭后跳入河水里去游泳,积累下来就生出了麻烦:高烧不退且浑身疼痛,送到镇上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其中半个月处于昏迷状态;后来总算捡了半条命,但风湿痛从此像梦魇一样缠上了我,让我经常梦到自己不同方式的死亡。我不是宗教信仰者,死亡对我来说不是天堂,而是活生生的梦魇。每次我从梦中逃出来,都会汗水淋漓,半夜睡不着。20岁以前我认定自己活不过30岁,非常恐惧。直到今天,“疼”、“痛”和各种各样的“死亡”场景和记忆仍时时刻刻缠着我,它让我更珍惜人间的小欢乐和小温暖,每天以笑容示人,而把孤独感和宿命的悲伤留给自己,如我在一首诗中所写:“更多的时候,我的欢乐大不过一粒米/我就想办法把它爆成米花,蘸上甜,制成毒药/送给有缘人,击鼓相传。如果这样的想象失于天真/我就把它写成诗篇,对着天空和田野朗诵/这时候,我的心情蕴含着千万种心情/它是无法比喻和形容的,也是无法描述的,只供奉于/我辽阔而不安的内心——”是的,作为中国诗歌曾经的精神家园,作为汉民族文化精神和宗教的乡村,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已经被被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狂飙突进打得支离破碎,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秩序、伦理和完整性被破坏殆尽,它的不断消失和死亡,快要把我的诗歌逼到了无处扎根的地步,所以之于我,诗歌写作的“地方性”除了那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原,还有就是这个无形的疾病了。再进一步说,每一个写作者的“地方性”其实就是它的童年和身体本身,它们共同构成了写作者有限的“个人地域”,我自信。我对它们持之以恒的书写,已经把我和其他优秀的写作者们区分开来。
14年前,我从淮河平原来到了北京,携家在这个叫通州的城乡结合部住下来。但我的父母如今还留在老家那个村子里种田谋生。这真是一个绝妙隐喻,是一种宿命。我在诗里这样写道:“若干年后把住所安置城市的边缘,说明我心向原野/却又被名利的藩篱羁绊/你怀疑我虚伪吧,但请不要怀疑我来自那里/最终还将被它一点点收回。”它说明我是清醒的,矛盾的,纠结的。我是淮河平原的乡村叛徒,我是首都北京的城市贰臣。我的存在就是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我的无形的尾巴一直藏在衣服里。在现实里和精神里,我在两地之间“散步、游走、漫步、奔波”,我是众生的一个,同时也非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通过这样的旁观和介入,试图窥破和理解事物和人的精神世界。但即便不写作,我可能也会这么做。每一个人都有窥破他者的欲望。“他者”即世界,诗人就是世界的偷窥者。在我持续的诗歌写作里,“父亲”一直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我在村子里出生并长到13岁,然后去异地求学、工作,然后越走越远。生产队时代的劳动强度其实并不高,但对血统的歧视无处不在。我的母亲出身三代农民,嫁给我父亲这个富裕中农的儿子后,受到了不可忍受的人格侮辱,这让她非常委屈(我倔强的大伯母干脆直接选择了家门前的老桑树,用绳子了结了生命)。我的母亲没有走极端,但性格渐渐变得非常暴戾,尤其对我这样野小子,几乎动辄以掌相加,再施以饥饿惩罚。以至于我对童年最刻骨的记忆就是饥饿和胖揍。在诗《亲人们》这样写:“四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只把母亲当亲人/三十年前,我九岁,把所有的饭当亲人/二十年前,我十九岁,只把青春当亲人/十年前,我的父母,妻子,儿子和女儿,是我的亲人/踩着四十岁的门槛,所有的敌人和亲人,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当我八十岁,睡在坟墓里/所有的人都视我为亲人,但你们已经找不见我——//……这一撮新土,这大地最潮湿的部分——”可以这么说,母爱的吝啬让我过早体验了人生的孤独,并反过来造成了我对母爱的熟视无睹。我生活中的父亲是中国农民的典型,他性格隐忍、宽仁、与世无争,向亲人和身边的相邻释放着绵绵无尽的爱。“父亲”在我的诗歌里其实早已经“溢出”了“个人”和“血缘”的范畴,从而具有了象征性和寓言性——每个人迟早都会回到屋檐下,成为众多“父亲“中的一个——这就是宿命,它不可逆转。
在城乡结合部活过14年,我不断回望记忆里的平原,为它痛心疾首。返身到眼前,我更多关注和书写的是那些和我一样把各自村庄背在背上、在这里那里挣命奔波的人的命运。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村庄,都是我诗歌写作有限而广大的“地方性”;而童年记忆。忆、身体记忆和“父亲”之爱,则是其立足之根本。至于这座生活了14年的地方,“迄今为止,我鄙视这个城市的/每一片红砖绿瓦(《问自己》)。
2013-06-23
谷禾诗选
小事件
说到车祸,忍不住心慌起来
早晨经过东关路几,望见一辆福田皮卡
横栽在马路中央,车头已经扭成麻花儿
货厢里的旧家具散落一地
肇事者和遇难者都已经不见踪影,
这让留下的大片血迹分外刺眼,也有了更丰富的
想象空间,警察放置了绕行标志,
乘客们议论纷纷,有人还把脑袋伸出窗外。
……也是在这个地方,
大约三个月前,搞装修的雷于挺也不幸丧命
我曾请他吃过一次饭,听他如数家珍
讲述着业主验工的细节,他狠抽了口纸烟
突然说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她下月才满十八岁,
但认识三天就被我搞掉了。”他得意地
笑了,却马上又严肃起来,“我要和她白头偕老?”
他用力挥着拳头。但三天后,
他独自进了火葬场烧红的炉膛。消息传来,
我去东关路口站了很久,但终于没有
碰见他爱上的那个女孩。
这么多年,我已经领教了生命的脆弱
越来越多的死,让我快麻木了
甚至父亲说把我抱大的三爷爷死了.
我也只淡淡地应了一句“噢”,就挂了电话
下午带女儿去看牙医,顺着她手指的方向
突然看见一个失去双腿的男孩在借用两只滑板前行
他的整个身体都趴在滑板上,两只灰黑的手
奋力向后,像一条鱼在人缝里钻游。
女儿问,“他为什么不坐下来乞讨呢?”
我没有同答她一一我又一次目睹了死,
形形色色的死,其实和活着没任何关系
譬如人的死,树的死,田野的死,河流的死
天空的死,爱情的死,性的死。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死
总有一天,我也会静悄悄死去,并且不能选择其一
西海子公园
它是唯一的,夏天我曾去过,
穿过曲里捌弯的两条街,在通州剧场后边,
水面宽阔,浑浊,游艇犁开波浪,独不见莲叶田田。
喝茶的,下棋的,唱戏的,人声鼎沸,
芭蕉扇挥来舞去,占满了廊亭,
城市和它游动的汽车环绕着它,暑假或周末
薄暮时分,这里是孩子的天堂
他们把球踢向空中,自己变成星星,散落进树林,草
丛
直到夜深了,斜月一遍遍催促
但现在是深冬,它的荒凉几乎等同于岁月,落叶
化成泥土,水而结了厚冰,
用力踩卜去,却没有断折的声音传来,
凿开冰层,也不见鱼儿吐出水泡,
喷水池裸出底部的沙砾,四个石狮子表情木然
海子角的土山比草丛还矮,从拱桥上,
能望见栅栏外的满城灯火,但今晚的月光下,
只剩下了我。夏天你和我一起来这里,
但现在,我们天各一方,
公园外匆匆的行人,没有谁停下来,
给我一杯安慰,或者,陪我坐一会儿
现在啊,好像有雪落下来了,并且渐渐
弥漫了我的视线,我冻红的脸
它纷纷扬扬,落在
西海子的冰面上,落在所有的街道、屋顶,
北运河两岸的堤坡,落在向东两公里外的荆棘丛中
当我睡熟,它继续轻柔地,
轻柔地,落在所有牛者和死者身上一一
一个熟睡的老人
一个熟睡的老人
就像一座空荡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
它的内部
黑暗,肃穆,荒凉,蛛网密布
如果一阵风吹过,
逝去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们回来,和他合而为一
它会变得
自然,亲切,带着桃树的端庄和垂柳的慈祥
噢一一,一个熟睡的老人和空荡的房子
接着,河流与村庄诞生了
田野,羊群和炊烟,
女人抱着孩子,沿月光走来一一
我想,这不是幻象
从一个熟睡的老人开始,当他和一座空荡的房子结合
我被允许经常同到屋檐下,成为
众多父亲中的一个
亲人们
四十年前,我还没有出生,只把母亲当亲人
三十年前,我九岁,把所有的饭当亲人
二十年前,我十九岁,只把青春当亲人
十年前,我的父母,妻子,儿子和女儿,是我的亲人
踩着四十岁的门槛,所有的敌人和亲人,你们都是我
的亲人
当我八十岁,睡在坟墓里
所有的人都视我为亲人,但你们已经找不见我一一
……这一撮新土,这大地最潮湿的部分一一
落院
“从八十岁向一岁活,每个人都是
如来……”我父亲絮絮地念叨,日头转过
门框,他脖子以下的枯皮和青筋都没入了
屋檐垂落的阴影。
母亲在当院里捶棉花,木棒落下
蹿起的尘埃在阳光中乱撞。“嘭一一嘭……”
哦,此刻落院的是一对老人的晚年,激情
恍若隔世,而咳喘的
足音不断从暗夜涌来,粘稠的云块
磨损着母亲的乳房,也磨损着父亲的阴茎
五十年的风雨越来越苍茫、邈远……
我从梦中惊醒,但接下来会看见什么
一张随手翻出的旧照片,
我和妻子之间竟隔着另一个人
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了,
留下的空旷多年后却显影出来
我曾经梦游穿过田野、村落和许多城镇
最后又落院回来一一身体里装载着
我父亲和母亲的晚境,
还有我半生的风湿病,我儿子的旱冰鞋
划过水泥路面时打着旋儿的尖叫
原野记
把原野当成生命的温柔地带,我去它
却愈加缈远。当原野上消失了
蓬勃的野草、杂树、荆棘,而只剩下庄稼
沟坎坟畔的花儿在风中加速凋零,请允许我
独自游过田埂时,心中升起
露水大的伤悲。离开村庄3公里
我一步一回的泪光深处
只捉到了电线上的雀点,以及枝头的半片残叶
脚下这青绿的麦苗,头顶着霜露
却并不见老,偶尔有野兔顺着垄沟狂奔去远
似乎它要在惊悚中亡命一生
壕沟里流水不复,哪里还有水草鱼虾的踪迹
蓝天白云凝滞头顶,壕沟对岸
高速公路直穿过围起来的开发区,不用脱去鞋袜
我也能向着灯红酒绿飞去。仿佛
原野已不复为原野,我心已成
齑粉。想起童年时我也曾在原野上迷路
从连片的马齿苋、抓地草间摘下一朵牵牛花放在耳边
隐隐就传来了暴雨般的虫鸣,抬起脸来
看见星辰分外密集而明亮,足以照耀古今
让人平静地睡去,不再想醒来
不再侧耳搜寻亲人的唤归
若干年后把住所安置城市的边缘,说明我心向原野
却又被名利的藩篱羁绊
你怀疑我虚伪吧,但请不要怀疑我来自那里
最终还将被它一点点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