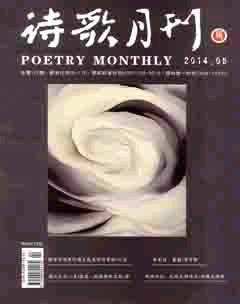如果本土气质有个变种

博尔赫斯有段话我曾稍加整饰为:“万事万物存在于,现世的大地。幽灵与风雨,各有其遗传”。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语言学的本性——写作者都会面临一种追问,即个人语言学的来源与遗传问题。即便读者放弃了这样的追索,真正的写作者也会自我拷问。这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困境:即“我的私人语言气质是怎么形成的”?伟大的作家无时无刻不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气质:世界性惟有作为本土性的对立面时它才是存在的,否则就毫无意义可言。如果说这种气质、司题还有一个深刻的变种,那就不能不涉及写作的地域性或说是地方性这一命题。
如果说写作是建筑于语言学之上的自我觉悟,那么,个体是个容器。在个体所受的种种限制中,他所来自的地域及其附生性因素,既是他的最大限制之一、又分明是真正的个性形成之所,许多作家的无可替代性即来源于此。从表面上看,许多作品、尤其是诗歌绘画音乐一类,出自某种场合中的“一闪念”。然而,本质却是,为这“瞬间”所做的心理资源的准备却懵懂而长久。如同一个泡沫从累积千年的池塘上,突然升起并猛地破裂
谁也讲不清这神秘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瞬间的裂变因某种微不足道的机缘而到来。一闪念,如同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所讲的田纳西山顶的坛子,有了这只微不足道的坛子,就如同建立了某种秩序。由秩序率领的混沌中,深埋着诸如技艺、写作指向、价值观等等语言的附着物。倘你心中没有,它也没办法呈现。这种心理资源的准备,遇到某个“一闪念”的召唤拱出地面。意象等等,都不过是应这种召唤而生的载体。在我讲的这种心理资源的漫长准备中,地域性是最重要的成长因素之一。
比如,我生于安徽桐城:曾经领明清文坛数百年的“桐城派”的源地。桐城文化对我的影响是一种基础性的影响。姚鼐在《谢蕴山诗集序》谈到的“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写作理念,对我的干预是很深的。如果再往下细分,我生于古镇附近的农家。乡村地理、风习的渗透,轮回观念的渗透,在我诗中的痕迹处处可见。陈仲义教授在一篇叫《论陈先发诗歌的汉化》的文章中说,我的诗歌背后中有一个“大部头的”、“潜在的”孔镇。这些地域性因缘累积在血脉里,既有对它的屈从、也催生出种种摆脱的努力:这种对立是我写作的一个基础层面。如果不忠于它,那就不再是我。我的个人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当然,以“地域性”这个钮来固定着的“现实”概念,也并非那么简单。我也多次提到“四个层面的现实”这个说法,是想对当前一些写作者过度轻易解构所谓现实的一种纠偏:一是生活层面的现实,即人的所见、所闻、所触等感觉的综合体。二是被批判、再选择的现实,被诗人之手拎着从世相中截取的现实层面,即“各眼见各花”的现实。三是现实之中的“超现实”。中国本土文化,其实是一种包含着浓重超现实的文化,并不比拉美地区淡,这一点被忽略了,或说是被挖掘得不够深入。每种现存的物象中,都包含着魔幻的部分、“逝去的部分”,如梁祝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诸神及种种变异的特象符号都活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四是语言的现实。从古汉语向白话文的缺陷性过渡,迫使诗写者必须面对如何拓展语言的表现力与形成不可复制的个体语言特性这个问题,这才是每个诗人面临的最大现实。如果不对现实二字进行剥皮式的解读,地域性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我曾提到当代汉诗最醒目的成就,就是一批重要诗人本土意识的觉醒、本土气质的形成。这是个比较宏观的观察。具体到日常写作乃至单独的篇章,其实每个诗人或多或少地都是“一人分饰两角”。诗人的身份于我,首先意味着某种割裂。两种语言形态的割裂。在生活中你得像任何一个普通人那样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得屈从于功用、简明、以沟通为目的的口语系统,而在诗中你又必须完成某种超越。这种超越既是审美的、也是思想的。可以说,这种割裂让所有诗人都苦恼,无论是有了企图统一二者的“口语诗”,还是所谓生涩的学院诗,它们的本质都是要与世界的语言学对抗。诗就是一种对抗,从而达到超越。这种超越的极端形态是宗教、世俗形态便是诗歌。地域性这种话题的开启,有助于写作把根扎入现实的深层,导引出新的局面。
陈先发诗选
丹青见
桤木,白松,榆树和水杉,高于接骨木,紫荆
铁皮桂和香樟。湖水被秋天挽着向上,针叶林高于
阔叶林,野杜仲高于乱蓬蓬的剑麻。如果
湖水暗涨,柞木将高于紫檀。鸟鸣,一声接一声地
溶化着。蛇的舌头如受电击,她从锁眼中窥见的桦树
高于从旋转着的玻璃中,窥见的桦树。
死人眼中的桦树,高于生者眼中的桦树。
被制成棺木的桦树,高于被制成提琴的桦树。
2004年10月
鱼篓令
那几只小鱼儿,死了么?去年夏天在色曲
雪山融解的溪水中,红色的身子一动不动:
我俯身向下,轻唤道:“小翠,悟空!”他们墨绿的
心脏
儿近透明地猛跳了两下。哦,这宇宙核心的寂静。
如果顺流,经炉霍县,道孚县,在瓦多乡境内
遇上雅砻江,再经德巫,木里,盐源,拐个大弯
在攀枝花附近汇入长江。他们的红色将消失。
如果逆流,经色达,泥朵,从达口县直接跃进黄河
中间阻隔的巴颜喀拉群峰,需要飞越
夏口浓荫将掩护这场秘密的飞行。如果向下
穿过淤泥中的清朝,明朝,抵达沙砾下的唐宋
再向下,只能举着骨头加速,过魏晋,汉和秦
回到裸裸哭泣着的半坡之顶。向下吧,鱼儿
悲悯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我坐在十七楼的阳台上
闷头饮洒,不时起身,揪心着千里之处的
这场死活,对住存隔壁的刽子手却浑然不知。
2004年11月
逍遥津公园纪事
下午三点,公园塞满了想变成鸟的孩子
铁笼子锈住,滴滴答答,夹竹佻茂盛得像个
偏执狂。我能说出的鸟有黑鸫、斑鸠、乌鸦
白头翁和黄衫儿。儿子说:“我要变成一只
又聋又哑的鸟,谁都猜不出它住哪儿,
但我要吃完了香蕉、撒完了尿,再变。”
下午四点,湖水蓝得像在说谎。一个吃冰激淋的
小女孩告诉我: “鸟在夜里能穿过镜子
镜子却不会碎掉。如果卧室里有剃须刀
这个咒就不灵了”。她命令我解开辫子上的红头绳儿,
但我发现她系的是绿头绳儿。
下午五点,全家登上鹅形船,儿子发癫
一会儿想变蜘蛛,一会儿想变蟾蜍。
成群扎绿头绳儿的小女孩在空中
飞来飞去。一只肥胖、秃顶的鸟打太极拳
我绕过报亭去买烟,看见它悄悄走进竹林死掉。
下午六点,邪恶的铀矿石依然睡在湖底
桉叶上风声沙沙,许多人从穹形后门出去
踏入轮回。我依然渴望像松桕一样常青。
铃声响了,我们在公共汽车上慢慢地变回自已
2005年4月
孤峰
孤峰独门旋转,在我们每口鞭打的
陀螺之上。
有一张桌子始终不动
铺着它目睹又一直被拒之于外的一切
其历炼,平行于我们的膝盖。
其颜色掩之于晚霞。
称之日孤峰
实则不能跨出这一步
向墙外唤来邋遢的早餐,
为了早已丧失的这一课。
呼之为孤峰
实则已尢春色可看
大陆架在我的洒杯巾退去。
荡漾掩蔽着惶恐。
桌而说峰在其孤
其实是一个人,连转身都不可能
像语言附着于一张白纸。
其实头颅过大
又无法尽废其白
只能说今夜我在京城。一个人。远行无以表达隐身
之难。
2009年3月
游九华山至牯牛降一线
油菜花为何如此让人目眩?
按说
在一个已经丧父的诗人笔下
它应该是小片的、
分裂的,
甚至小到一个农妇有点脏的衣襟上。
从那里
从临近积水而断头的田埂
从她哺育的曲线上,吹过一阵接一阵令人崩溃的花粉
乡亲说,除了出狱者
祖辈们就埋在这地里。
名字只有一个,
生活仅存一种:
稀粥对稀粥的延续。
而尸骨上的油菜花为何如此让我们目眩?
细雨中
喧闹的旅游者鱼贯而入,
远处有黑色的载重货车驶过。
我呆立三小时,只为了看
一个偏执的僧侣在树下刺血写经
为了种种假托,我们沉疴在身。
此刻这假托仅限于
被春雨偶尔击落又
能被我们的语言所捕述的花瓣——
哪怕只是一小瓣,它为何如此让人目眩?
而自九华山到牯牛降,
这假托只有一种:
在它玄学的油菜花下没埋过
一个出狱的人。
没埋过一个以出狱为荣耀的人。
甚至没埋过
一个对着铁窗外的白色浮云想像过监狱的人。
2011年4月
再读《资本论》札记
奢谈一件旧衣服,
不如去谈被榨干的身体。
他说,凡讲暴力的著作常以深嵌的呓语为封面。
第一次枕着它,
是小时候陪父亲溪头垂钓。
老党员搓着手,
把肮脏的诱饵撒向池塘。
我在独木舟上,在大片崩溃的油菜花地里
睡到心跳停止。
日冕之下,偶尔复活过来
记得书中一大堆怒气冲冲的单词
对家族,这是份难以启齿的遗产。
祖母信佛,
而父亲宁愿一把火烧掉十九个州县。
这个莽撞的拖拉机手相信,
灰烬能铸成一张崭新的脸。
他们争吵,
桐互乞求,搏斗,
又在深夜的走廊上抱头大哭。
祖母用白手帕将寺庙和诸神包起来,
藏在日日远去的床底下,
她最终饿死以完成菩萨们泥塑的假托。
而父亲如今也长眠山中,
在那里,
“剥削”仍是一个词。
“均贫富”仍是一个梦想。
坟头杂木被反讽的雨水灌得年年常青
为一本旧书死去,
正是我们应有的方式。
多年以来,我有持镜头写史的怪癖。
只是我不能确知冤魂项上的绞索,
如何溶入
那淅淅沥沥的空山新雨。
因为以旗为饵的城堡早已不复存在。
理当不受惊扰的骨灰,
终不能免于我的再读。
初识时,
那三、两下醒悟的鸟鸣仍在。
像池塘在积攒泡沫只求最终一别。
而危险的尺度正趋于审美的末端
2011年10月
京郊崂山记
连猛虎也迷恋着社交网络
更遑论这些山里的孩子
爱幻想让他们鼻涕清亮
整个下午,夺我们手机去玩尸游戏
滂沱的鼻涕能搭起好儿座天堂
而老人们嘲笑我们这支寻虎的团队。
他们从青檀中榨出染料
令我们画虎
画溪上的鸟儿,揣了满口袋的卵石而飞得缓慢。
画村头的孕妇,邋遢又无忧
画那些柿子树。当
复杂的脑部运动创造出这群山、小院和颜色。
而赤、无须的柿子像老道士前来问候
“你好吗”一一
山里太冷了。我无以作答。废玉米刮痛我们的神经
我能忍受,早年收获的那些
有少数的一部分仍在绽放
一几大锅中,浮出衰老的羊头。
孩子们可等不及了。
而“我们吃掉的每一口中,都焊接着虚无”
在臆想的语法中姑且称称这里为崂山。
饭后的月亮越来越大
我们四肢着地,看鼻涕的群山沸腾
孩子们一直嘲笑直至
暮色剥去我们的人形
2012年11月
正月十五与朋友同游合肥明教寺
散步。
看那人,抱着一口古井走来
吹去泡沫
获得满口袋闪烁的石英的剖面——
我们猜想这个时代,在它之下
井水是均衡的
阻止我们向内张望
也拒绝摄影师随意放大其中的两张脸
而头脑立起四壁
在青苔呈现独特的青色之前。
我们一无所思
只是散步。散步?散步,供每一口的井水形成。
有多年没见了吧
嗯
春风两个拮据的耳朵间传送当年的问候。
散步
绕着亭子
看寺院翻倒在我们的喉咙里
夜里。
井底的稻田爬上我们的脸哭泣
成为又一年的开始
2009年2月
甲壳虫
他们是褐色的甲虫,在棘丛里,有的手持松针
当作干戈,抬高了膝盖,蹬蹬蹬地走来走去。
有的抱着凌晨的露珠发愣,俨然落泊的哲学家
是的,哲学家,在我枯荣易变的庭院中
他们通晓教条又低头认命,是我最敌视的一种。
或许还缺些炼金术士,瓢虫的一族,他们家境良好
在枝头和干粪上消磨终口,大张着嘴,仿佛在
清唱,而我们却一无所闻,这已经形成定律了:
对于缓缓倾注的天籁,我们的心始终是关闭的
我们的耳朵始终是关闭的。这又能怪准呢?
甲虫们有用之不尽的海水,而我却不能共享。
他们短促而冰凉,一牛约等于我的一口,但这般的
厄运反可轻松跨越。在我抵达断头台的这些年
他们说来就来了,挥舞着发光的身子,仿佛要
赠我一杯醇浆,仿佛要教会我死而复生的能力
2005年9月
前世
要逃,就干脆逃到蝴蝶的体内去
不必再咬着牙,打翻父母的阴谋和药汁
不必等到血都吐尽了。
要为敌,就干脆与整个人类为敌。
他哗地一下就脱掉了蘸墨的青袍
脱掉了一层皮
脱掉了内心朝飞暮倦的长亭短亭。
脱掉了云和水
这情节确实令人震悚:他如此轻易地
又脱掉了自已的骨头!
我无限眷恋的最后一幕是:他们纵身一跃
在枝头等了亿年的蝴蝶浑身一颤
暗叫道:来了 !
这一夜明月低于屋檐
碧溪潮生两岸
只有一句尚未忘记
她忍停百感交集的泪水
把左翅朝下压了压,往前一伸
说:梁兄,请了
请了-一一
2004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