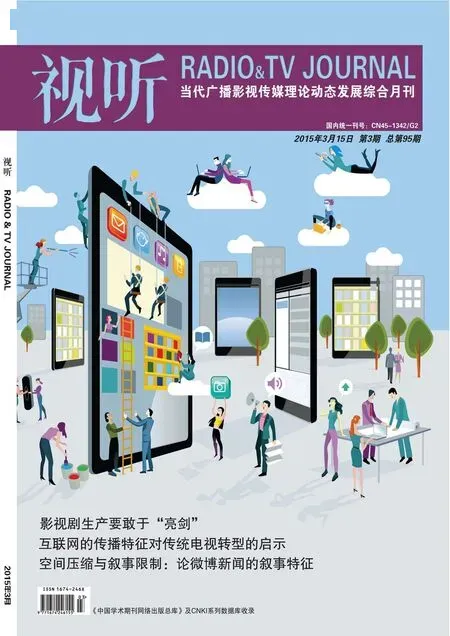浅析议题设置理论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 王鹏飞
浅析议题设置理论对纪录片创作的影响
□ 王鹏飞
随着中国纪录片进入市场化时代,纪录片的创作活动日趋丰富。在带来了市场繁荣的同时,纪录片传播价值的高低成为了决定纪录片是否能占有一定市场、彰显自身文化价值的关键。而与纪录片传播价值息息相关的一个传播学理论就是议题设置理论。因此,在此时对纪录片创作活动与议题设置理论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具有创新性和功效性。本文对议题设置理论进行了阐述,从两个时代下中国不同的议题设置模式入手,着重分析了正向和逆向两种议题设置模式下纪录片创作话语权的不同及其对纪录片创作活动的影响,指出两种议题设置模式各有利弊,互相不能取代,以期在纪录片创作者进行纪录片创作时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纪录片;议题设置模式;话语权;传统;逆向
议题设置理论(theagenda-settingtheory),也称议程安排,是传播学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提出。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认为大众传播对社会某一事件——即议题的着重强调程度和该议题在公众中受重视的程度构成强烈的正比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大众传播媒介中越突出某一事件,对其进行大量、多次的报道,这一事件就会越因此而突出,形成议事日程。进而在一段时间内在受众中形成对这一事件的集中议论,营造出一种舆论、意见的氛围。这方面鲜明的例子可以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在《传播学引论》中的一段话来阐释:“某段时间内媒介把一个大国发生的军事政变当成头号问题对待,醒目的标题、突出的版面、号外、插播等接连不断,于是公众便觉得这场政变是眼下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一时间围绕这个话题议论纷纷。公众之所以重视这场政变,这么热心地、急切地谈论它,并非由于它真是当时最重大的问题,而仅仅是由于媒介给予它以最突出的地位而已。总之媒介报道什么,公众也就越关心什么,这就是议程安排的基本思想。”议题设置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人们对事物的具体思考,但它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活动,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的显著性,从而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重要性的判断。纪录片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上必然担负着议题设置所赋予的媒介舆论导向功能。因此,议题设置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再往深看一步,也就是说谁掌握纪录片议程设置背后的话语权,出于某种传播的目的决定某一议程,谁就给纪录片的传播效果划定了一个限制范围。纪录片创作者或主动或被动地在这个限制范围内进行纪录片创作并传播,完成议题设置的全过程。
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里,纪录片议程设置的话语权是掌握在国家统治阶级手中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一个国家需要在群众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的、向上的主流精神来维护和巩固其政权。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团结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我国的国家政策和历史使命。而纪录片具象真实的受传方式,让其具备了很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进行群众性的、有效性的政治宣传方面时展现出了强大的潜力,使它肩负了向广大人民解释国家政策、宣传国家主张、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任务;另一方面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信息传递单向且封闭,受众的认知范围有限,并没有主动参与到传播中来,往往是消极盲目地被动接受和认知媒介传递来的信息,主体意识受到压迫。两方面原因的综合导致了官方或者政府机构对纪录片议程设置话语权的控制。在此前提下,当统治阶级在一定阶段内想达到特定传播效果时,就通过议题设置过程来达到目的。首先选择、编辑和提供符合议题的信息,给处于大众传播媒介一方的纪录片创作者,然后由创作者根据包含议题的信息,在议题划定的限制范围内选择可表现议题的题材,制作多部纪录片并传播出去产生议事日程。最终达到公众对议题的关注和产生议论,并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发动议程设置一方所希望传播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例如,关于展现历史伟人的纪录片,像《毛泽东》《周恩来的办公室》《忘不了的邓小平》等,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讲述中国的现代发展史,告示后人莫忘革命前辈所作出的艰苦奋斗,珍惜现在;树立先进人物的纪录片,如《人民的好儿女》《永远的先锋战士》《道德之光——全国道德模范人物志》等,是为了展示时代精神,引领人们的行为规范;最多的是记录重大事件的纪录片,诸如《新中国的诞生》《让历史告诉未来》《解放》等,是展现建国过程,弘扬红色精神,《香港沧桑》《澳门岁月》是反映国家政策——一国两制的正确性,《挥师三江》《汶川大地震》都是对突发事件下国家的应急反应及全国人民对受灾群众的热心帮扶的最好例证;即便是自然历史类纪录片,如《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森林之歌》等,也暗含着深沉的民族自豪感的和炙热的爱国精神。所有的这些纪录片,都是在反映国家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传统话语模式下议题设置的正向传播,占据了纪录片市场绝大多份额。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加速转型,这一情况发生了改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积极转型,政府对媒介的严格控制逐渐放开,大众传媒身上的政治气息开始变淡,转为向市场规律靠拢。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众媒介抛弃了其所担负的传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社会使命,而是变得比以往更需要考虑收视率等市场因素对自身发展的切身影响,也就是说考虑受众的消费心理。另一方面,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态度由过去的“圈养控制”到现今的“散养控制”,这导致了舆论环境的开放,受众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放,主体意识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外界塞给他们的信息,而是渴求主动去探寻、去选择自己想要的信息。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让传统话语模式下的议题设置受到了颇大的冲击,新兴话语模式下的逆向议题设置开始兴起。
新兴话语模式下的话语权不再是掌握在官方或者政府机构手中,而是由受众控制。新兴话语模式下纪录片的创作工作从受众产生预期议题中开始,预期议题也就是受众可能会感兴趣的事件或他们正在感兴趣的一类事件,他们想要知道这些议题的后续及更多的信息,但他们却无能力直接影响大众媒介发挥议题设置功能,甚至没有发觉自己正在制造预期议题;然后,纪录片创作者收集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不同预期议题,分析、预判出哪些议题更有吸引力,会在更大的受众群体中找到共鸣、产生议程,亦或是更有力量,与创作者自身心灵产生强烈碰撞,让创作者情不自禁想把该预期议题实现,在这些议题的限制范围内选择题材并拍摄成片;最后传播给受众时是由多部纪录片同时在受众中产生讨论和思考,当不同创作者选择了同一预期议题时,就形成了针对该议题的议程。
从中不难看出,传统话语权模式下纪录片议题设置的产生者和推动者是统治阶级,实行者是纪录片创作者,接受者是议题作用的广大受众。而新兴话语权模式下议题设置的推动者和执行者都是纪录片的创作者,强调了创作者的对预期议题的判断、分析、挖掘的能力,议题的产生者和接受者都是受众,但却是两个不同概念下的受众:一个是产生预期议题的无意识小众群体,一个是接受最终议题的有意识大众群体。这两种议题设置模式更大的区别在于,传统模式下是一个推动者,对多个实行者的正向议题设置,很容易达到议题设置的最终目的,传递某一特定的意识形态,但不易被受众真心喜爱和接受;而新兴模式下是多个推动者,对多个实行者的逆向议题设置,每个受众都很容易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议题,却也因受众的分众选择而让推动者的意识形态难以最大程度地形成议程。在现实社会中,传统的议题设置与新兴的议题设置共同存在,纪录片创作者只是出于自身传播目的、所处位置等的考虑,选择不同话语权下的议题,进而影响到自己的题材选择过程,实际上两者各有其利弊,谁也不能替代谁,共同影响着纪录片的创作过程。
1.唐晨光.新中国60年纪录片美学形态之流变 (之三)转折期(1979-1989):纪录片美学形态及特征[J].电影评介,2010(12).
2.李墨田,王东玲.从《马背谍影》看选题人文观[J].中国电视(纪录),2010(9).
3.鲁佑文.把镜头对准社会及其主流人群——中国纪录片赢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节点 [J].声屏世界,2004 (5).
4.宋继昌,刘敬东.用我们的纪录片到世界上发言[J].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6(1).
5.邵雯艳.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传播视野中的纪录片选题[D].苏州大学,2003.
6.李杨.新世纪历史文化电视纪录片研究[D].广西大学,2008.
7.李斫.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纪录片 [D].东北师范大学,2010.
8.邹毅.当代中国语境下纪录片的发展及其创作原则[J].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5(3).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