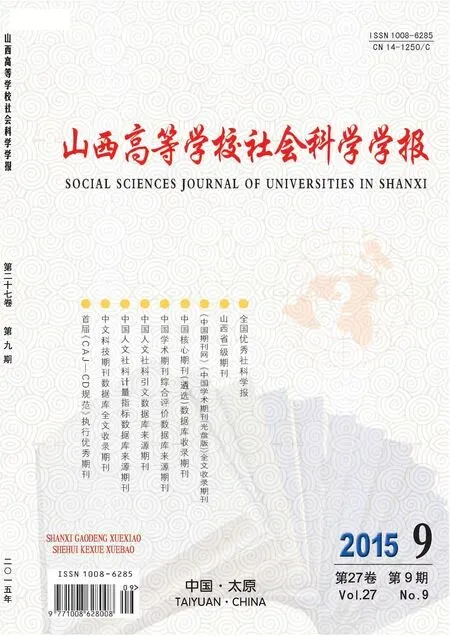孟东野佛教观小议
崔海东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孟东野佛教观小议
崔海东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摘要]孟郊晚年因人生久经苦厄,而儒门修证工夫陵夷无可资借,故转崇佛教以求解脱。但是他对佛教义理并未深入,仅对苦谛有所比附,又期以维摩诘会通儒释,故最终还是恪守了儒士本色。
[关键词]孟东野;佛教观;儒佛互动;儒士
[DOI]10.16396/j.cnki.sxgxskxb.2015.09.028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交游韩愈(退之),二人关系在师友之间。年五十始第进士,调溧阳尉。宪宗元和九年(814),在阌乡(今河南灵宝)因病去世,卒年六十四。东野由于人生之苦厄,于晚年转崇佛教以求解脱,但是他并未深入佛教义理,只是将之当作宣泄痛楚的方式之一,最终还是恪守了儒士本色。
一、东野晚年崇佛之转向
众所周知,退之辟佛,震烁千古。而东野游于韩门,晚年竟然转崇释迦,自言“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自惜》)931,可谓甚不合常理。究其原因,大率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原因在于东野人生异常坎坷。首先,东野个人家庭不幸,前妻早死,三子夭折,一生贫困交加。其次,仕途艰辛。东野早年屡试不第,年至半百始中进士,越四年于贞元十七年(801)方任溧阳县尉。然因性情之忤,不合于时,便索性作诗,不事公务,又被罚半俸,后竟至公务几废,县令乃假尉以代之。元和初,河南尹郑余庆奏为河南水陆转运从事,试协律郎,方定居洛阳。六十岁时,因母死去官。元和九年(814),郑余庆再度招他往兴元府任参军,乃偕妻往赴。然行至阌乡,暴疾而卒,死无分文,还是退之等人凑钱为其营葬,郑余庆又赠钱安顿后事“为遗孀永久之赖”。故同为韩门高士的李翱(习之)为之抱不平云:“郊穷饿,不得安养其亲,周天下无所遇……其穷也甚矣。凡圣人奇士,自以所负,不苟合于世,是以虽见之,难得而知也。”(《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6417正是由于这样坎坷的人生,造就了东野独特、狭窄的人生视角,如云“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937;又如“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胆里生荆棘”(《择友》)930;又如“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同路人”(《伤时》)929等即是真实的写照。
第二个原因是汉唐儒家心性工夫的陵夷。儒家所谓工夫,是针对心性情欲作自我调节、控制与优化的理性的道德实践。简言之,可分下学而上达、上达而存养、存养而践履(再度下学)三大环节。唐代儒学有三种典型:一为注疏,是所谓学问;二为出处,是所谓职业;三为经济,是所谓制度。其最被诟病在于全然不关心性本体与修身工夫,完全偏在发用一路,是为有用而无体,大悖孔门体用一贯之规模。儒门修证工夫黯淡造成三大弊病:一则心性工夫皆失,故多德行之窳;二则不能服膺天命,故罹出处之悲;三则不能解决终极关怀,故囚生死之狱。东野困于命运之多蹇,此时儒门却不能提供有效资源以安身立命,在此精神低谷中,无法安顿灵魂,忧患无可挥拂,其人生即由此转向佛教,即可理解。
其实针对东野这种情况,韩门也作对策,即以儒家传统之天命来破之。如习之即有《命解》,其云:“或曰:‘贵与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也,何命之谓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为?’二子出,或问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对曰:是皆陷人于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盗耕人之田者也;皆以为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无取焉。尔循其方,由其道,虽禄之以千乘之富,举而立诸卿大夫之上,受而不辞。非曰贪也,私于己者寡,而利于天下者多,故不辞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虽一饭之细也,犹不可受,况富贵之大耶?非曰廉也,利于人者鲜,而贼于道者多,故不为也。何智之有焉?然则君子之术,其亦可知也已。”6430习之此文承孟子之义,以为人生所受之天命,有德命、禄命之别,凡求之在我者为德命,求之在外者为禄命,人当凭工夫返回仁性本体之后更提撕上扬,阶及天命流行之境界,从而证其德命,率其禄命。此学理可谓血脉充足、气质澄澈、气象刚正。然东野独不能释怀,亦是当时心性工夫与终级关怀一路未曾真正复兴,士子中高者如习之能独立,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未达自觉而已。
退之更勉励东野不能自甘命运,而要不平则鸣、服膺天命。他专门作了一篇《送孟东野序》欲解决东野思想问题。首先,说明“不平则鸣”是天地万物之规律。其次,说明人既为天地之子,承之不变。人类自开化以来,每朝每代都有不平之人发出不平之鸣,以为时代之强音。最后,勉励东野,要跳出一己之悲欢,而追求国族之永福。文尾更直接点明云:“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从吾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鸣信善矣。抑不知天将和其声,而使鸣国家之盛耶?抑将穷饿其身,思愁其心肠,而使自鸣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则悬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东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释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解之。”241-242退之之意,不可谓不高,然而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东野不仅没有跳出自己诅咒之命运,鸣国之不平,相反地,却转崇释迦,甚至发出了“始惊儒教误,渐与佛乘亲”这样的慨叹。
二、东野佛理的局限——苦的人生与苦谛之比附
东野对佛教主要的切入点为苦谛,但是也仅仅止步于此。东野将其人生的彻痛俱化为诗歌。退之谓其“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29;在《贞曜先生墓志铭》中又称赞其诗“刿目钅术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333。习之认为:“郊为五言诗,自汉李都尉(陵)、苏属国(武)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6417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谈东野诗的语言特色,东野诗所泛射出来的味道,却正是“苦”,故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列东野为“清奇僻苦主”可谓知言。东野诗中,用“苦”字频率甚高,凡四十七见。没有什么题材不是笼罩在此苦之下。我们可将之略作分类来举例。一则描写天气,如《苦寒吟》云:“天寒色青苍,北风叫枯桑。厚冰无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壮阴正夺阳。苦调竟何言,冻吟成此章。”926二则描写身疾,如《路病》云:“病客无主人,艰哉求卧难。飞光赤道路,内火焦肺肝。欲饮井泉竭,欲医囊用单。稚颜能几日,壮志忽已残。人子不言苦,归书但云安。愁环在我肠,宛转终无端。”928《卧病》云:“贫病诚可羞,故床无新裘。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倦寝意蒙昧,强言声幽柔。承颜自俯仰,有泪不敢流。默默寸心中,朝愁续莫愁。”928三则描写羁旅,如《感怀》云:“路傍谁家子,白首离故乡。含酸望松柏,仰面诉穹苍。去去勿复道,苦饥形貌伤。”929四则自述苦学,如《夜感自遣》云:“夜学晓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雠。死辱片时痛,生辱长年羞。清桂无直枝,碧江思旧游。”931五则祭吊亡友,如《吊卢殷》云:“棘针风相号,破碎诸苦哀。苦哀不可闻,掩耳亦入来。哭弦多煎声,恨涕有余摧。噫贫气已焚,噫死心更灰。梦世浮闪闪,泪波深洄洄。薤歌一以去,蒿闭不复开。”947可以说,他的人生时时刻刻每一境遇都向外投射着苦味。另悲、伤、哀、愁、怨等也是连篇累牍,触目皆是。
我们知道,佛教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四谛”,其中第一谛即是苦谛。佛教认为人生为诸苦之集合,如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取蕴等,其中五取蕴即色受想行识——物质、感性、知觉、理性、意识,五蕴会聚故有人身,人们执着自身便有诸苦。佛经中说苦殊众,如《法华经》卷一《方便品》云:“轮回六趣中,备受诸苦毒。”《华严经》卷七三《入法界品》云:“生老病死忧悲恼害,如是诸苦,常所逼迫。”东野对此苦甚有感喟,故频频会之。正是由于苦的人生,东野渐渐开始接解佛教典籍,其《读经》诗云:“垂老抱佛脚,教妻读黄经。经黄名小品,一纸千明星。曾读大般若,细感肸蚃听。”945所谓“大般若”指姚秦鸿摩罗什译《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世称《大品般若》;所谓“小品”指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十卷,世称《小品般若》。《大品般若》《小品般若》和《金刚经》是大乘空宗般若系经典的主要代表作。“垂老抱佛脚”显示了东野在科场、官场苦苦周旋一生而无所得后,开始向释迦求助,以求人生意义之答案。
然东野对佛教四谛亦未有深刻之把握。其只是着重于对人生苦痛的简单比附,而没有继续深入下去,求得真正的解脱之道。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另外三谛。佛教之集谛,探讨苦的原因,人生之所以处处时时充满苦,是由于人们对于佛教真理的无知(无明),不懂得人生本身就是一种幻影,而把人身视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就会产生种种欲望和追求,由欲望驱使,就导致贪嗔痴等烦恼,这些烦恼就是人生痛苦的根源。十大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包括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等)。佛教之“灭谛”,要灭烦恼得解脱,即寂灭、圆寂、涅槃。认识到佛教真理,了悟人生真谛,就会进入一种烦恼灭尽、常乐我净的境界。若只是有余涅槃,断除贪欲、灭尽烦恼,已灭尽生死之因,但作为前世惑业果报的肉身还存在,仍然活在世上,还有思虑活动,是不彻底的。只有到了无余涅槃,不仅灭除生死之因,也灭尽了生死之果,即不仅作为前世惑业果报的肉体不存在了,而且连思虑也没有了,灰身灭智,永无生死,这是佛教中的最高境界。当然,小乘涅槃,视人生为大苦,故把人体消灭、烦恼灭除作为追求的目标,因此其涅槃、圆寂往往是死的代名词。而大乘涅槃则从另一个角度来谈,其视世间与涅槃本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空,也都是妙有,世间的一切都是真如、实相、佛性的体现,如果人们能认识佛教这一真理,反本归原、体证佛性,也就达到了涅槃的境界。最后,“道谛”是求灭烦恼得解脱的方法途径。包括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三十七品;三学(戒定慧),六度等内容。这样一对比,可知东野对佛教只是因为理论基础上的仿佛相似而认同之,也就是说,只是由于苦的人生而产生对佛教苦谛之认同,却并没有真正地去继续深入佛教其他义理,遑论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修行以求解脱。然而也正是对佛教义理的局限性,保证了东野的儒士本色并未因为他的“渐与佛乘亲”而作大幅改变。
三、儒佛会通的努力——维摩诘情怀
《维摩诘所说经》属大乘佛教经典,其主要思想是发挥大乘空观,主张“心净则佛土净”,“入世即是出世”。僧肇在《维摩诘所说经注序》中称:“此经所明,统万行则以权智为主,树德本则以六度为根,济蒙惑则以慈悲为首,语宗极则以不二为门。”其对中土禅宗影响深远。儒家士子往往以之作为会通儒释之桥梁。东野亦视维摩诘为儒佛会通之最佳途径。其有《听蓝溪僧为元居士说维摩经》一诗,诗云:“古树少枝叶,真僧亦相依。山木自曲直,道人无是非。手持维摩偈,心向居士归。空景忽开霁,雪花犹在衣。洗然水溪昼,寒物生光辉。”945“古树”四句是概括蓝溪僧向元居士说经之场景与要义。残冬之古树,枝叶殊寥,然真僧于此说法,亦有何妨。山木随其机缘任其曲直,求道之人又岂能以俗谛之是非而衡定。“手持”两句是说东野我持师偈,不能释手,乃万分向往这种居士的生活。“空景”四句是说听蓝溪僧说经后的感受,本来我的世界,满是污垢,恰来这漫天大雪,一洗尘寰,则雪霁之时,蓝溪之昼,若水洗一新,眼前万物,皆是旧识,然都散发着崭新之光辉,我之人生,亦受此洗礼,将迈向良途欤?
东野又在《赞维摩诘》中云:“貌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饮,在色不淫。非独僧礼,亦使儒钦。感此补亡,书谢悬金。”6997由此赞亦可见,东野对维摩诘的理解是儒家式的,只在入世言,颇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克己复礼”(《论语·颜渊》)之意。只是“补亡”二字,自责过重。维摩诘富贵有余乐,红尘就是孤峰,心净国土净,入世即出世,而东野则奔汲于科举,转促于卑职,乞食于友朋,何时有酒色之累?
我们通过上面对东野的介绍,可知东野崇佛,仅是为了寻求人生苦厄的宣泄,并没有真正直入智地。事实上,如果我们考察他存世的文本,即可发现,对于佛教的欣赏与向往的诗文所占比例甚小,居于主流的还是儒家思想。如其《上常州卢使君书》云:“道德仁义,天地之常也,将有人主张之乎,将无人主张之乎?曰:贤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无其位,则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当时无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书载其言,则周万古而行也,岂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独载其言周万古而行也,前古圣贤得仲尼之道,则其言皆载之周万古而行。阁下道德仁义之言,已闻周天下诵之久矣,其后著书君子,亦当载之周万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仁义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书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让哉?是故不以道德仁义事其君者,以盗贼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义之衣食养其亲者,是盗贼养其亲也。”6996此文堂堂正正,愿求乎吾儒之道德仁义,以为此是人极之基。若我们整体地评介其所作诗歌,亦可看出其纯承儒家之诗教。一则反映时代现实、揭露藩镇罪恶,如《征妇怨》《感怀》《杀气不在边》《伤春》等;二则针砭社会不公与丑恶,如《织妇辞》描写织妇“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927,此类比之白居易《讽喻诗》不遑少让。《寒地百姓吟》则曰“高堂搥钟饮,到晓闻烹炮。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930,比之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亦不逊色。三则描写了人伦之情,如《结爱》之写夫妻,《杏殇》之写父子,《游子吟》之写母子。以上皆是儒家所谓修齐治平之事,故以孟郊为儒士实无问题。所以,我们认为,东野晚年虽转崇佛教,但是其本色还是儒家,此无疑义。也正是因此,有学者认为东野“虽置身佛教盛行之世,亦偶与僧徒相游,惟其思想并未受影响”。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全唐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 董诰.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韩愈.韩愈集.长沙:岳麓书社,2000.
[4] 尤信雄.孟郊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72.
[收稿日期]2015-04-29
[作者简介]崔海东(1975-),男,江苏南京人,江苏科技大学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15)09-0116-04
On Meng Jiao′s View of the Buddhism
Cui Haidong
(SchoolofMarxism,Jiangsu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Zhenjiang212003,China)
[Abstract]Meng Jiao was friend with Buddhism because he wanted to seek comfort for his miserable life in old age. But he learned it superficially, because he was only interested in the truth of suffering and would intercommunica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by Vimaiakirti. Finally, he kept the identity of Confucian.
[Key words]Meng Jiao;view of Buddhism;intercommun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Confucian schola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