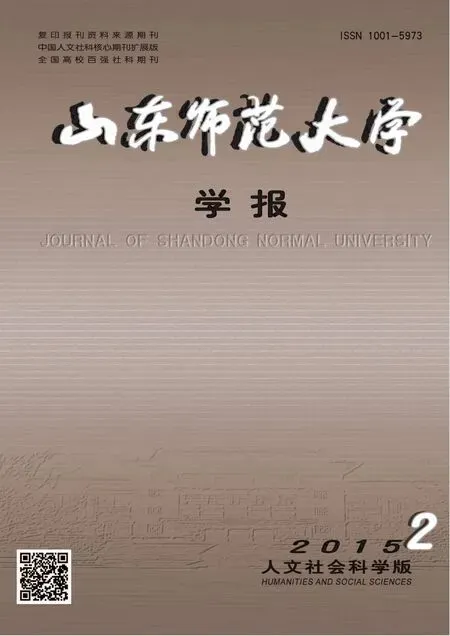梳理、选择和路径展开
——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逻辑理路*①
郭 武
( 1.甘肃政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
梳理、选择和路径展开
——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逻辑理路*①
郭武
( 1.甘肃政法学院 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730070;2.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
经由对环境习惯法内容的梳理和选择,再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具体路径的展开,这一前后关联、依次相递的过程,是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理路。梳理与选择问题主要关乎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环境习惯法规范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意在对环境习惯法进行现代“深加工”之前的“原材料”进行鉴别与选取;环境制定法“自上而下”的主导和环境习惯法“自下而上”的参与,则是为了实现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而构筑的两条上下通达、互补运行的路径。
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梳理;选择;路径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2.010
从习惯到习惯法,再到制定法这一历时性过程既是对法律自身演化规律的客观呈现,同时也暗含着对不同阶段、不同形态法律所具有的价值和功能的主观评价。这一评价便是:制定法作为法律演进的最后阶段和更高形态,必然在价值和功能上具有超越习惯法的优越性。相比较而言,习惯法因松散性、技术性弱等自身特征而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及制定法的缺漏。就环境习惯法这一特殊习惯法类型来说,学者的实证研究同样也证明了这一点。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在某些领域,(环境习惯法)并不是普受欢迎的”,他们“不赞同土著民在本质上必然是环境保护主义者(或天生具有环境保护倾向)的观点”。因为更为真实的情况是,“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存在许多传统观念不能适应的状况”②Neville White, Betty Meehan,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 Lenson Time, in Nancy M. Williams and Graham Baines (ed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Wisdom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entre for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1999,37-38.,“一部分土著民保持有符合环境保护伦理的准则,另外一部分土著民则未必保持”③Michael E. Soule, The Social Siege of Nature,in Michael E. Soule and Gary Lease (eds.), Responses to Postmodern Destruction, 1995,160-161.。诚然,具有自生自发规则属性的环境习惯法在历史演化的某一时间点上会出现收敛于进化博弈模型的非效率均衡点上,以致于出现历时性维度中“很多功能紊乱的习惯(法)”④[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李国庆等译:《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6页。。那么,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即环境习惯法在内容上良莠不齐,有“善恶”之分。而理论上,拟实现现代价值的环境习惯法必然是作为“良法”的环境习惯法,而不是不加区分、鱼龙混杂、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环境习惯法。在这种情况下,“一味盲目地认为环境习惯法都会促进现代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则是幼稚的,……故我们在对环境习惯法作为特定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路径深表关切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任何一项环境习惯法制度应当进行合理性评估后才有意义”。*Fred Bosselman, The Choice of Customary Law, in Peter Orebech, Fred Bosselman, Jes Bjarup, David Callies, Martin Chanock, The Role of Customary Law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435.因此,对环境习惯法进行梳理和选择(鉴别),使其中具有现代环境法治功能的规范或要素凸显出来,同时摒弃其中不合理的部分(如历史“怀旧”、过度民间化、非公平的主导性和排外性等*Fred Bosselman, The Choice of Customary Law, in Peter Orebech, Fred Bosselman, Jes Bjarup, David Callies, Martin Chanock, The Role of Customary Law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438-441。),将是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叙述”得以推陈铺开的必要阶段。
在梳理和选择的基础上,建构合理的路径是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重要步骤。在深刻的现代性背景中,环境制定法取代了环境习惯法的地位,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治”规则,因此以国家环境制定法为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已然成为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主要路径。同时,由于环境制定法在现代环境法治中的“主场”优越性和自我封闭的话语系统,往往使其难以自觉地在“自上而下”路径中主动摄取环境习惯法的有益成分,因而通过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而逐渐展开的“自下而上”的路径必将是其现代价值实现的有力补充。相比较而言,“自上而下”的路径模式“以国家制定法的主导性”和“最优法律制度的唯一性”*William Easterly,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95-99.为立足点,而“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却注重环境习惯法作为规范体系的独立性。而且,环境习惯法更接近于自生自发的内部规则,体现了人类社会规则系统的历史演化与持续发展的属性,所以“自下而上”路径的持续拓展将使大量的内部规则以环境习惯法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供给于现代环境立法,使现代环境法成为以内部规则为基础而建立的外部规则系统。因此,在“自上而下”路径之外拓展“自下而上”路径,进而形成上下通达、互补运行的管道,是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有效途径。
一、环境习惯法的梳理
梳理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对环境习惯法规范群类型化的过程。从逻辑上来说,这一过程是进一步选择环境习惯法的前置程序,因此从方法论角度看,对环境习惯法的梳理是类型化方法的具体应用。尽管如学者所说,类型化方法因概念性和非经验性而在一定意义上存在局限性*任强:《西方法律传统的类型研究及其局限——韦伯法律思想述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但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类型化方法无疑是一种清晰、有效的思维建构模式,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模式,“社会科学工作者才能在纷繁驳杂、经常互相抵牾的经验现象中清理出一个条分缕析的脉络来”*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04-207页。。因此,类型化方法之于梳理环境习惯法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一种清晰的类型框架对各异的环境习惯法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
然而,类型化方法如何展开呢?经典社会科学方法论作家提出了极具洞见的具体范式,它们分别是社会科学方法论大师韦伯的“理想类型”范式、著名法哲学家考夫曼的“事物本质类型”范式以及著名法学方法论作家拉伦茨的“类型分类”范式。韦伯的“理想类型”范式是源于客观实在的概念抽象,将其运用于类型化的具体实践之中,往往会面临主客分离、理论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然而,正是“理想类型”与实在类型之间的偏离又进一步修正了“理想类型”, 避免了类型化实践中“对号入座式的机械化思考方式的影响”*刘士国:《类型化与民法解释》,《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从而使其因时、因事而动,成为更能反映变化中的实在类型的理论构念。因此,“理想类型”范式具有相对性和发展性,虽源于历史实践并用于认识历史,但只能是历史的仆人,而“不应当相反是主人”*[德]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9页。。在考夫曼的“事务本质类型”理论中,法律发现是一种使事实与法律规范相互对应的调适同化过程,因而法律人的主要才能不在认识制定法,而在于有能力在法律的,即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德]亚图·考夫曼著,吴从周译:《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87页。不像许多学者否定规范(应然)与事实(实然)之间的必然联系,考夫曼认为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之间只有在“意义关系”中得到同化、一致,因此“意义”即是二者联系的调和者或二者获得“同一性”的连接纽结。而考夫曼所论述的“意义”就是“事物本质”。可见,以“事物本质”这一“意义”为基础的类推和类型化是发现“真实的法”的关键和基础。“事物本质类型”理论不仅对法律(规范)漏洞的填补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发展“真实的法”所不可或缺的认识论前提。而按照拉伦茨的“类型分类”学说,法律所涉及的类型包括经验的类型和规范的类型。经验的类型产生于真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是人们就认识对象所产生的普遍性的、“典型的”、“平均的”类型,因为这种类型往往符合某类事物的本质,虽然边缘和界限较为模糊,但其中心地带却非常明晰。规范的类型又分为“规范的真实类型”和“规范的理想类型”*[德]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39-340页。。“规范的真实类型”是指“自始就包含规范性因素的类型”,如草场占有人、河流使用人等。“规范的理想类型”则是指基于法律规定,虽不能完全实现,但仍指明方向的“乌托邦”类型。拉伦茨认为,类型化在法学研究中的意义主要在于,相较于“规范的真实类型”和“规范的理想类型”,“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是规范指示应予优先适用的类型,因为这种典型类型始终源于某类事物的本质。
综合以观,除了个别性差异之外,上述三种类型化范式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无论在“理想类型”范式中,还是在“事物本质类型”范式和“类型分类”范式中,类型化的根本性因素都是表现为客观真实的历史实践或事物本质,而作为规范的法律只有在与历史实践或事物本质相调试、一致的时候才具有“真实的法”的规范意义。因此,上述三种范式看似不同,但均可基于历史实践或事物本质作为类型化基础的共同性而化约为在本质上并无二致的类型化方法。
依循上述类型化范式,环境习惯法的梳理过程也就是以客观历史实在和“事物本质”为基础而进行的寻找“真实的法”的过程。按照拉伦茨的规范分类方法,环境习惯法基本可分为“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和“规范的真实类型”两个大类*相比较可以发现,虽然环境习惯法大多以“理想的”或“模范型”的某些“乌托邦”精神或价值为最高指引,但就个体性的环境习惯法规范而言,“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和“规范的真实类型”却是最常见的形式,因为环境习惯法作为一种源于客观实在的规范,从根本上是决定于某类“事物本质”的。在由真实的生活这一“事物本质”所构筑的环境习惯法的适用领域,“规范的理想类型”是大无用处的。环境习惯法中的这种类型存在正好与制定法相反。除了“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和“规范的真实类型”外,“规范的理想类型”也是制定法中常见的规范模型。。在本质主义视角下审视环境习惯法,同样发现环境习惯法可分为具有规定性规范属性但以习惯称谓的环境习惯法和以法称谓的环境习惯法两大类。此处的类型化方法与之完全对应,“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即是具有规定性规范属性的习惯,“规范的真实类型”则是通常意义上以法称谓的环境习惯法。可以说,“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和“规范的真实类型”的二分法在方法论意义上涵括了环境习惯法的所有规范类型。据此,虽冠以环境习惯法之称谓,但不能归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习惯法规范或习惯则不是实质意义上的环境习惯法。以“经验性的经常性类型”和“规范的真实类型”二分法为基础,可比照现代环境法建构的应然模式以具体内容为标准对环境习惯法进行详细梳理,因为按照具体内容的差异性进行梳理的方法不但更接近法的内在构造和规则本质,而且能使环境习惯法的价值和功能在与现代环境法相对应的“角色”中得到确当的体现,为下一步更为合理地选择环境习惯法的有益成分,及为环境习惯法与环境制定法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奠定基础。按此梳理标准,环境习惯法可被类型化为体现环境习惯法价值基础的规范群、体现环境习惯法主要保护对象的规范群、体现环境习惯法特殊规范方式的规范群、体现环境习惯法创制中地方社群元素的规范群以及体现环境习惯法特殊适用方式的规范群五大类。
二、环境习惯法的选择
类型化方法对环境习惯法进行梳理的逻辑延展,便是如何按照合法性检验标准对环境习惯法作出选择的过程了。那么,环境习惯法的合法性检验标准有哪些呢?对这一问题,不同的法学流派对合法性的理解各不相同。自然法学家认为自然法所秉持的自然理性是合法性的基础;法律实证主义侧重于将形式合法性作为合法性的标准;历史法学派却认为特定民族的历史精神是合法性的检验标准。可见,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合法性问题,其标准会各不相同。严存生认为,“合法性一词有多种用法,针对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含义,就对象而言归纳起来有两种:其一是针对个体的行为而言,指的是它合乎法律的规定;其二是针对某种公共权力或政治秩序而言,指的是它的正当性、权威性和实际有效性”*严存生:《法的合法性问题研究》,《法律科学》2002年第3期。。按照此观点,合法性至少存在二元向度上的分野,即“合乎法律规定”的形式合法性和具有“正当性、权威性和实际有效性”特征、“构成习惯法规范存在的基础”*王林敏:《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的基础的实质合法性。向上追溯,社会学大师韦伯提出了以“经验性动机和信念”*[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9页。为基础的经验性合法性。之后,哈贝马斯在韦伯所创立的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的“影响领域”之外又批判性地提出了建立在“商谈理性”基础之上的“重建性”合法性。在哈贝马斯看来,“合法性的意思是说,同一种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的、被认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要求对自身有很好的论证。合法的制度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就意味着某种政治制度的尊严性。这个定义强调的是,合法性是一种有争议的公认的要求,统治制度的稳定性,甚至取决于对这种要求的(起码的)在事实上的承认”*[德]哈贝马斯著,郭官义译:《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总体而言,合法性有经验性合法性、形式合法性和“重建性”合法性三种。经验性合法性是指“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相信官员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具有在道德上良好的品质,并且应该借此而得到承认”*[德]哈贝马斯著,张博树译:《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因而这种合法性是一种“信仰的合法性”*[德]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39页。,是主体对习惯法“内化”的承认。形式合法性是指习惯法在制定法视角下是否具有“合法律性”。形式合法性偏离了习惯法的主体性地位或独立性价值而在制定法的立场对其是否符合预设的制定法规则、目的或立法精神进行“审查”。“重建性”合法性则是指立基于哈贝马斯“视野中作为合法意志集束之平台的公共领域,以及作为合法性来源与基础的商谈民主有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之上,在一个“批判开放的公共领域和交往网络中,通过自由、平等、包容、审慎的公共商谈程序,从而达致理性的共识”*张娟:《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的第三种合法性范式。可见,上述三种合法性范式在内涵上完全不同。
就环境习惯法而言,在“构成社会控制的形式、进而构成秩序的要素这一功能主义”意义上,与环境制定法存在明显的分野,因而其合法性首先且主要地表现为一种自身“正当性”*胡伟:《在经验与规范之间:合法性理论的二元取向及意义》,《学术月刊》1999年第12期。的独立性认同和判断,其次才表现为制定法规范意义上的“合法律性”判断。由于环境习惯法的“正当性”在不同视角下有不同的涵义,经验性合法性所指的内化承认或“信仰合法性”是环境习惯法“正当性”的内在方面(如内心确信之要件),“重建性”合法性据以立基的公共理性则是环境习惯法“正当性”的外在方面(如社群的合意),因此,经验性合法性范式和“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均可统摄在环境习惯法的“正当性”或实质合法性判断之中。继而,环境习惯法的合法性检验标准可分为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和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两个大类。
(一)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
环境习惯法的实质合法性源自不同立场的“正当性”判断或“实质”。结合前文“场域”与此处合法性范式的分别论述,环境习惯法的实质合法性在文化多元论立场、功能论立场、理性演化论立场以及公共商谈理性论立场均可找到立论依据,因而也分别存在文化多元论、功能论、理性演化论以及公共商谈理性论等环境习惯法的检验标准。
第一,文化多元论立场上环境习惯法的实质合法性。在文化多元论立场上,环境习惯法的实质合法性在于它是构成不同民族、区域、历史的文化多样性的载体、事实或要素之一。中国“法律文化论”学者梁治平认为:“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西方法则不能不是西方文化的表征。两种法律建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之上。它们在概念、结构和分类上的技术性差异,实则是有关法律的整套观念形态、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的根本对立”*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9页。。因而,环境习惯法是一种“历史与事实的存在,……是作为与国家法相对应的民间社会中的事实存在且与国家法共同构造社会秩序的规范体系”*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9页。。在国外,霍贝尔、博登海默等人也认为,“法律是文化的一个因素”*[美] E.霍贝尔著,严存生等译:《原始人的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因此,在文化多元论立场看来,环境习惯法在民族、区域和历史等方面的差异不构成对其价值与功能的贬损。当环境习惯法在民族文化的“位育”与系统构成中具有符号意义或不相互“排异”时,即是符合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的法规范。
第二,功能论立场上环境习惯法的实质合法性。功能论认为,在没有国家正式法律的社会中,借助非正式规范而不是法律规则,也能够形成并维系一种“无需法律的秩序”*美埃里克森著,苏力译:《无需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译者序”,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页。。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德克里夫-布朗,以及后来的人类学家均认为,虽然一些“简单的”社会没有国家法律,但“纠纷解决的习惯法机制旨在调节社会生活,它与西方的法律和秩序具有可比性”*Strathern, Marilyn. Discovering Social Control, 1985, in Sack, Peter edited: Law and Anthropolog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2,287.,甚至具有更为显著的作用。在中国研究功能论的诸学者中,以“本土资源”论为代表的朱苏力将习惯法视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资源库存”,认为“中国法制建设主要应该立足于发掘本土固有传统和正在形成的非正式制度,而反对单纯的法律移植”*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21页。。主张“以普适性理念引导中国法治建设”的谢晖却“着力于从民间规范之中萃取价值性支持要素”*魏治勋:《民间法研究范式辨正》,《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以发展习惯法的主体性价值,表达民间规范的权利诉求。从上述论说中可以得知,功能论即不将习惯法视为多样性文化的因子之一,也不倚重规范的形式,仅关注习惯法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资源功能或独立价值要素。据此,在功能论立场上,检验一套环境习惯法规则合法的唯一标准是是否具有建构特定社会秩序的功能。譬如在托拜尔高山草场中,由社群合意而成的“边界规则”、“越冬规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100页。等环境习惯法规范在当地草场资源的使用和管理中长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秩序维系作用,因而这些环境习惯法规范在功能论立场上是符合实质合法性标准的。
第三,理性演化论立场上环境习惯法的合法性。不同于笛卡尔式的理性建构论,以规则演化论大师哈耶克为代表的诸多学者认为,构筑社会秩序的规则有一套类似于生物进化的“社会进化”*[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法律、立法与自由》(第1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系统,“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是自发的进化过程,而非人之主观设计的结果”*Hayek. The Errors of Constructivism,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5.。习惯法等内部规则构成了规则发生、演化的基础,这种自生自发的规则先在于国家法为代表的外部规则,是“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结果”*吴元元:《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从哈耶克的“自发演化论”开始》,《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据此,环境习惯法的合法性在于它是一套不以人为因素而转移的自然进化规则,发挥着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因此,尽管与环境制定法不同甚至完全相悖,但环境习惯法作为社会秩序维系的首要和基础性规则的意义仍不容忽视。在这一意义上,环境习惯法应被看作是一套不同于环境制定法的独立系统,对其合法性的检验更多借助于历史实践中的具体效果。当一套环境习惯法规则在历时性自发演化过程中始终能做出自我调试以适应变化的规范对象(环境、资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时,该套环境习惯法也就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具有规则的合法性。譬如,托拜尔高山草场习惯法历经数个世纪,始终在自我调试中适应着不同的草场管理实践。然而,一些环境习惯法制度则因缺乏弹性机制,虽“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内,环境习惯法能有效发挥作用,但当其所适用的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制度规范往往会土崩瓦解”*Iain J. Davidson-Hunt, Fikret Berkes,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through the Lens of Resilience: Toward a Human-in-Ecosystem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delivery at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on Property Conference, Bloomington, Indiana, May-June, 2000:14-15.。在印度尼西亚东北部马鲁古群岛的摩鹿加群岛上,当地土著民所沿用的渔业管理习惯法规则——Sasi(Sasi规则只将对软体海生生物的捕捞限制在维持生计的范围之中)——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可持续的管理方式,然而针对海洋生物的新型市场模式的发展导致了传统渔业资源管理规则的失败。如此以来,早期在Sasi规则之下的可持续性管理模式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Charles Zerner, Tracking Sasi: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Central Moluccan Reef Management Institution in Indonesia, in Alan T. White, L. Z. Hale (eds.), Collaborative and 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 of Coral Reefs: Lessons from Experience, Kumarian Press, 1994,19-23.而已。摩鹿加渔业习惯法的没落再次印证了哈耶克的观点——“在这种文化进化的过程中,那些被证明有助益于人们作出更有效努力的规则存续了下来,而那些被证明只有助于人们做出较为低效努力的规则则被其他的规则取代了或淘汰了”*[英]哈耶克:《大卫休谟的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哈耶克著,邓正来译:《哈耶克论文集》,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91页。。足以显见,这类环境习惯法在历史实践中的效果只是昙花一现,在变化后的历史实践中显然无法适应新的规制的需要,因此也不具有理性进化论立场上的合法性。
第四,公共商谈理性论立场上环境习惯法的合法性。以公共商谈理性论为基础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是对极具形而上学色彩的“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的匡正与超越”,它“以公共领域和商谈民主理论为背景”,“把合法性译解权和证明权(即检验标准问题)”*张娟:《公共领域、商谈民主与政治合法性——哈贝马斯“重建性”合法性对传统合法性理论的重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建立在民众手中。“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因“主权在民”和理性的商谈建构这两个理论内核而区别于将善良、正义等抽象伦理准则或价值精神作为合法性检验标准的古典规范主义合法性范式,同时也区别于以权力、权威标榜合法性检验标准的主流经验主义合法性范式。“重建性”合法性范式认为,人们在公共领域就某些重要议题或管理内容进行的自由商谈(交往行动)及充分的意见表达“赋予了制度化的意见和意志形式(比如习惯法)以合法化的力量”*[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6-289页。。也就是说,“只有当一项规则让所有的参与者通过理性话语都表示同意,它才可以声称自己具有合法性”*[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包容他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00页。。环境习惯法规范,特别是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一大类环境习惯法规范恰是建立在社群民主商谈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制度化的意志形式”。这类规范虽然与国家环境制定法相去甚远甚至相互矛盾,但在其治理领域却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也正是基于这种合法性地位,环境习惯法在社群范围中的实效也是不言而喻的,以至于在很多环境习惯法发达的区域只见习惯法而不见制定法,环境习惯法在规范实效上远远超出了国家环境制定法。
(二)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
如前文所述,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建立在法律国家中心主义立场之上,不同程度地摒弃了环境习惯法作为法律类型的独立性地位。当环境习惯法符合国家法时,便具有国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进而对国家法具有辅助性价值。*魏治勋:《民间法研究范式辨正》,《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当环境习惯法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标准时,便不具有国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因而也对国家法没有任何价值贡献。虽然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极大地忽视了环境习惯法的独立价值,但在环境制定法运行的某些领域仍具有重要的“法律识别”作用。由于在现代制定法上,公共政策、公共利益也被认可为法律的渊源之一,因而在一般意义上,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不仅包括合制定法标准,也包括合制定法所认可的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标准。
制定法标准要求,环境习惯法在具体规范的内容上应当合乎相关环境制定法的规定或者与环境制定法不冲突。然而,此处环境制定法自身的正当性是不是环境习惯法“合法律性”的前提条件呢?有学者认为,“制定法必须是‘良法’、‘善法’。只有‘良法’、‘善法’才能作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也就是说,必须以‘正当的’法来判断习惯的正当性”*王林敏:《论习惯的合法性检验标准》,《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对此观点,笔者持保留态度。一方面,制定法的正当性是超越制定法中心主义的价值判断问题,且往往与法律的实质合法性相重合,因而将制定法的正当性作为习惯法符合制定法标准的前提,实为习惯法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而非制定法立场上习惯法的“合法律性”检验;另一方面,环境制定法规范是否具有正当性这一问题不能在环境制定法立场上得到回答,尤其是现代环境制定法中大量的技术性规范,如环境标准、环境监测方法等。这些规范往往因价值中立而无法对其作出正当性的判断。
一般而言,环境制定法标准有默示和明示两个方面。默示的环境制定法标准是指环境习惯法在与环境制定规范之间不相互冲突的情况下,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合法性的默示性承认。譬如,对挪威萨米人的渔业习惯法①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e Management: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2001,370.和我国藏区的草场管理习惯法②张济民:《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5-146页。,挪威国家环境立法以及我国环境立法均以默示认可的方式承认这些环境习惯法规范的合法性,而不是以具体规范规定的方式限制或排除环境习惯法的有效性。明示的环境制定法标准通常是指环境习惯法是否合乎具体的环境制定法规范或要义。由于科学技术手段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广泛应用,因而在现代环境制定法中存在大量的技术性规范。而环境习惯法由于历史原因和社群局限而呈现出“简单”的非技术性规范特征,因此往往很难在现代环境法治实践中与环境制定法中的技术性规范相衔接。因此,在环境制定法的技术性规范所适用的领域,环境习惯法因不合法律性而被排除。这也是“合法律性”这一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区别与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的重要特征:实质合法性检验标准是环境习惯法获得自身正当性的标准,而形式合法性检验标准更多是环境习惯法适用的排除性条件。
除制定法标准外,环境制定法所认可的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标准也是环境习惯法“合法律性”的检验标准之一。虽然公共政策、公共利益所承载的正当性或有效性价值是检验环境习惯法实质合法性的标准,但作为环境制定法所认可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它们显然成为了环境制定法的成分之一,而且在我国环境法治领域,公共政策和公共利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合乎公共政策、公共利益也是环境习惯法形式合法性的一种检验标准。
三、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路径展开
(一)环境制定法“自上而下”的主导
环境制定法“自上而下”的主导是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路径之一,是指国家环境制定法依靠国家权威力量及由此而生的强势话语权所主导的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实现途径。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是“以国家制定法的主导性”和“最优法律制度的唯一性”③William Easterly,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2,95-99.为立足点,并在此前提下对作为立法资源的环境习惯法予以制定法化或认可。可见,在“自上而下”的路径模式中,环境习惯法并没有以一套特殊规则系统的独立性“出场”,国家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制定法化或认可完全是环境习惯法被动实现现代价值的过程。那么,“自上而下”的路径模式对于实现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有何优越性呢?在实践中,以环境制定法为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又是如何具体展开的呢?
1.“自上而下”路径的优越性
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对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优越性,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自上而下”模式中环境制定法的主导性符合当下正在深刻发生的现代性对法律制度形态的要求。通过对比发现,环境制定法和环境习惯法分属两种不同的法规范形态。在不同的立足点上,二者均有重要的规范价值。然而从当下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④冯颜利、杨炯:《马克思与吉登斯现代性思想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是我们无法逃脱且不得不深处其中的历史性必然。在当下,现代性无疑造就了这样“一系列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的制度,而这样“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英]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著,尹宏毅译:《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69页。,即这种制度是在吉登斯所说的历史性“断裂”基础上所形成的“异于所有传统秩序的类型”*[英]吉登斯著,田禾译:《现代性的后果》,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3页。,因而是一种“更高的社会秩序”*冯颜利、杨炯:《马克思与吉登斯现代性思想比较》,《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3期。形态。而这种“更高的社会秩序”形态的典型实行就是以现代工具理性为统领的制定法。因此,制定法之于现代性历史条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和产物。作为现代性深入推进所需的制度之一,环境制定法在当下的主导便具有了历史正当性。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当下背景中由环境制定法“自上而下”主导的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方式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因而也是顺应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模式选择。
其次,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模式是克服环境习惯法规则非自足性的重要途径。虽然环境习惯法在社群环境资源管理中是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性规则,但在现代环境法的话语系统中却显现出许多不足之处,如松散性、弱执行力等非自足性特征。悉数现有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态,除村规民约之外,其他诸如口耳相传等形态都表现出了松散性的特征。严格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和关联性来看,许多环境习惯法由于内容的过于分散而无法统合到现代环境法体系之中。另外,长期以来,环境习惯法在运行机制中的社群个体的自愿性参与属性造成环境习惯法执行力较弱的弊端,尤其在现代性语境中,环境制定法的迅猛发展“遮蔽”了环境习惯法的功能空间,同时也使环境习惯法在运行中的执行力被大为削弱。要克服这些弊端,仅在环境习惯法体系之类进行自我完善是根本无法完成的。而环境制定法已经形成的优势却能有效弥合环境习惯法的上述非自足性弊端,如规范的逻辑完备以及以国家权威为后盾的执行力等。因此,在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实现过程中,国家环境制定法“自上而下”主导的路径模式为克服其自身的非自足性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最后,在“自上而下”的路径模式中,环境制定法所赖以为后盾的国家权威力量提高了环境习惯法规范的运行效果。从规范与规范对象的关系角度来看,环境习惯法规范与其规范对象之间有着比环境制定法规范更为显著的相互对应或“匹配”关系。其显著性在社群环境治理与自然资源管理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环境管理中的习惯法是一种通过“学习引导”的自我强化规则。*Westley. Governing desig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systems and ecosystems management. In Barriers and bridges to the renewal of ecosystems and institutions, ed. L. H. Gunderson, C. S. Holling, and S. S. Ligh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391-427.在对“不稳定环境”的不断反应或“持续性试错”*A. Dan Tarlock. The Nonequilibrium Paradigm in Ecology and the Partial Unraveling of Environmental Law, Loyola of Los Angeles Law Review, vol.27, 1994:1121.过程中,环境习惯法“应对环境管理过程中面临的诸多不确定性”*黄宝荣、张慧智、李颖明:《环境管理分区:理论基础及其与环境功能分区的关系》,《生态经济》2010年第9期。的能力不断提高,从而形成了一种极具弹性的适应性管理规则。然而,弹性和适应性特点只从形式上反应了环境习惯法规范与规范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而并不必然导向环境管理实践的高效,因为具体环境管理实践中的实际效果往往取决于管理规则执行力的强弱。显然,环境习惯法规范的弱执行力在当下语境中很难实现高效的环境管理目标。反观环境制定法,情形则大有不同。凭借国家权威力量,环境制定法“在‘自上而下’主导的路径模式中,国家立法者可以做到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弃置旧法而出台新法”*William Easterly,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2,95-99.,使合乎环境管理实际的适应性习惯法规则进入现代环境立法的同时,更能使其实现预期的管理实效。
2.“自上而下”路径的逻辑层次和步骤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由国家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模式在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实现中有诸多优越性。而要想真正实现上述优越性,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模式应当分以下逻辑层次和步骤渐次展开:环境制定法的现代性自省——环境制定法的话语开禁——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积极摄取。
第一,环境制定法的现代性自省。如前所述,环境制定法的产生发展及深处其中的现代性背景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历史性必然。然而在必然性之外,我们需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审视现代性在各个领域中日益凸显出来的弊端。现代性发生在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而工业文明的印迹给现代性烙上了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工具理性”符号。“工具理性”符号却一直是检验包括环境制定法在内的所有现代制度规范是否具有历史正当性的标准。显而易见,现代性因其“工具理性”符号的片面性而先天地具有了“价值理性”不足或被忽视的弊端。因此,深处现代性之中的环境制定法也难逃过度重视组织化和程式化而“价值理性”不足的弊端。于此情形,环境制定法亟待重新审视自身的先天性弊端,以不断从环境习惯法等体系之外的其他规范中获取有益的因素,使自身得到补足和修正。
然而,纵观各级各类现代环境制定法,大部分表现出了规范自身的高度逻辑性和自洽性,但对自身所缺失且需从外部获得的有益供给并未予以足够重视。对我国当下环境制定法进行检索之后,笔者发现仅有极少数立法涉及到对体系外他者规范的关注,如云南省人民政府于2008年制定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若干意见》。该《意见》肯定了传统知识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特殊作用,提倡“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爱护自然、保护环境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习俗,探索并完善社区共管机制,使广大群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得到实惠,更加自觉地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来。发挥民间环保组织的优势,鼓励其依法开展各种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另外,在台湾地区,2007年12月18日制定的《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于划定资源治理区域前,应将计划目的、范围、经营管理及与当地共管事项等计划内容,于治理区域内乡(镇、市)公告阅览及举行公听会,并经当地原住民族同意后,始得划定资源治理区域。” 可以发现,《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若干意见》和台湾地区《原住民族地区资源共同管理办法》都充分考虑到由民族环境习惯法规范形态构成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对国家正式制度规范的补足性价值,是现代环境制定法现代性自省的范例。
第二,环境制定法的话语开禁。与环境制定法的迅猛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一套独立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无论这种话语体系是精英话语还是少数人话语,实践中都表现为少数人凭借环境制定法业已形成的优势地位扩张自己的话语权地盘,同时排挤他者的话语权。随着环境立法活动专业化和技术化的不断加强,环境制定法的话语系统已与大众话语日渐分离。从宏观特征来看,环境制定法的话语系统和大众话语之间的分崩离析只能使现代性所标榜的“工具理性”在环境立法中长驱直入,同时大众话语所承载的实质理性日趋式微,从而使环境立法逐步趋于危险甚至“失控”的危险境地。在实践中,环境制定法的话语系统和大众话语之间的断裂使得少数人在凭借话语霸权地位进行环境制定法的封闭性话语再造的同时,弃置大众意识信念、民众利益诉求于不顾,因而环境制定法与大众生活渐行渐远。为了使大众意识信念、民众利益诉求等大众生活的内容体现在现代环境法之中,在开辟环境习惯法等大众话语机制的同时,必须要抑制环境制定法的话语霸权地位和自我封闭的特点。因此,环境制定法的话语开禁是环境习惯法进入现代环境法不可或缺的步骤之一。
在理论上,环境制定法的话语开禁可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要么摒弃唯制定法是从的少数人的话语霸权,主动接受环境习惯法等其他规范的话语系统;要么以环境制定法自己的话语系统主动影响其他规范的话语系统,使环境制定法与其他规范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优势互补。实践中,常见的情形却是后者。美国印第安人之一纳瓦霍(Navajo)的现代环境立法、澳大利亚土著民环境立法以及台湾地区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即是典范。横跨亚利桑那州、犹他州和新墨西哥州的纳瓦霍印第安人部落在环境与资源立法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环境法话语系统。《纳瓦霍国家法典》(Navajo Nation Code)中的6部环境类立法,如环境(Title 4: Environment)、土地(Title 16: Land)等专门立法*Office of Navajo Government Development, Navajo Nation Government, Fourth Edition, Window Rock, Navajo Nation, http://dine.sanjuan.k12.ut.us/heritage/people/dine/organization/government/tribal_code2.htm.广泛地体现了该部落环境习惯法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精神,均借助于现代环境制定法的话语权优势实现了对古老环境习惯法话语的成功影响和转型。在澳大利亚,情形同样如此。“北部法律改革委员会”就北部昆士兰等地区土著民基于环境习惯法的权利要求展开的环境立法,均体现为制定法话语系统对土著民环境习惯法话语系统的影响直至改造。据该委员会的一份立法背景资料显示,北部地区土著民的土地权利以及狩猎权、捕鱼权和采集权等传统习惯法权利均以澳大利亚国家环境制定法的形式予以立法确认,如1992年制定的《牧场法》(Pastoral Land Act 1992)、1993年制定的《土著民权利法案》(Native Title Act 1993)、1995年制定的《土地基金及土著民土地合作法》(Land Fund and Indigenous Land Corporation Act 1995)、1993年的《渔业法》(Fisheries Act in Native Title Act 1993)等。*Northern Territory Law Reform Committee, BACKGROUND PAPER 3: LEGAL RECOGNITION OF ABORIGINAL CUSTOMARY LAW, 2003,22-24.在台湾,2005年制定的《原住民族基本法》用现代立法语言将原住民的环境习惯法权利予以列举式规定。该法第19条规定:“原住民得在原住民族地区依法从事下列非营利行为:一、猎捕野生动物。二、采集野生植物及菌类。三、采取矿物、土石。四、利用水资源。前项各款,以传统文化、祭仪或自用为限。”
第三,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积极摄取。环境制定法在现代性自省和话语开禁的基础上,对环境习惯法有益成分的积极摄取将是“自上而下”路径模式的最终体现。
在摄取的内容上,环境制定法应从两个角度着手进行。一方面,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摄取是基于对自身规则不足的弥补而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内容摄取必须以制定法上的规则有效性为前提,即符合环境制定法标准。譬如在美国,纳瓦霍部落的《纳瓦霍国家法典》及其组成部分的《纳瓦霍国家环境政策法》等立法对该部落环境习惯法内容的摄取大多以符合现代环境法的价值或内容为标准的。在2005年《纳瓦霍国家法典》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法案18的修订中,纳瓦霍国家委员会在第1310条C款写明:“依据纳瓦霍传统法和习惯法,享有有尊严的且在物质和精神方面均得到良好保护的环境是人们的权利和自由。”*Resources Committee Navajo Nation Council, Proposed Navajo Nation Council Resolution, 20th Navajo Nation Council, 2005.另一方面,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的摄取源于对环境制定法中的空白性漏洞加以补充。不同于前述第一种情况,当环境制定法就某些事项的规定出现空白性漏洞时,对环境习惯法内容的摄取则不是以规则有效性为标准,而是应以符合环境制定法立法目的为标准。如纳瓦霍传统习惯法中的Hozho理念,即“事物各得其所且相互和谐而生”价值意涵虽没有具体的规则标准可循,但同样可被转化为《纳瓦霍国家法典》第201章的原则性条文——“任何事物生而彼此关联又相互独立”*Raymond D. Austin, Navajo Courts and Navajo Common Law: A Tradition of Tribal Self-Governan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42.。
在摄取的方式上,环境制定法对环境习惯法有主动摄取和被动摄取两种途径。两者区别的依据是摄取发生的原因。前者是指环境制定法在自觉地认识到自身规则的不足而主动对环境习惯法有益成分的摄取;后者是指环境制定法在他者力量的推动或刺激下展开的对环境习惯法的摄取。前者如《纳瓦霍国家法典》中6项环境类立法对环境习惯法的摄取;后者则是时间中最为普遍的摄取方式。挪威北部萨米人因对他们传统习惯法权利的要求而导源的国家法对环境习惯法的摄取很好地再现了第二种途径的全貌。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是萨米人(Saami)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园。如今,挪威水电业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萨米人的生产和发展。截止1972年,挪威60%的河流均上马了水电工程的建设,这些工程对萨米人影响极其巨大。*Kleivan, Helge. Incompatible patterns of land use: the controversy over hydro-electric schemes in the heartland of the Saami people. IWGIA Newsletter, 1978,61.1979年,挪威政府在北部芬马克郡(Finnmark Country)境内的阿尔塔河(Alta River)上修建大型水电站(Alta Dam)的动议引起了萨米人和其他非萨米挪威人抗议政府的政策。萨米人认为该工程在社会、文化以及环境保护等意义上均侵害了他们的权益。这次抗议引起政府对萨米人世代相传的习惯法权利的调查,因而改变了政府与萨米人之间的关系,增加了社会对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萨米人法律权利的广泛认同。可以说,这次事件中,萨米人“从公众认同、管理体制革新、宪法性合约以及法律和政府变革等领域收获到了史无前例的成果”*Brantenberg, Odd Terje. The Alta-Kautokeino Conflict, Saami reindeer herding and ethnopolitics, in Brosted, J. 1985,23.。阿尔塔大坝案的结果对驯鹿萨米人的直接影响是:他们被赋予了某些方面,如驯鹿业的独占权以及在驯鹿土地上狩猎和捕鱼的受益权等排他性权利。*Svensson. 1988,78.如今,按照新修订的《驯鹿法》(Reindeer Husbandry Law, 1971年制定,后经1978年和1996年两次修订),在驯鹿萨米人社群中,他们有权就许多事项进行自治。*Susan Joy Hassol. Impact of a Warming Arctic: Arctic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979.
(二)环境习惯法“自下而上”的参与
不同于环境制定法主导的“自上而下”路径,“自下而上”路径模式是发端于环境习惯法内部,以环境习惯法的自我“表达”,尤其是依附于环境习惯法的相关环境资源权利的主张为推动力的现代价值实现过程。笔者将在下文中通过优越性分析和具体展开两个方面对环境习惯法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路径模式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1.“自下而上”路径的优越性
在与“自上而下”路径模式的对比之中,“自下而上”路径模式的优越性便清晰可鉴;从更为微观的规则层面考察,“自下而上”路径模式也无疑是实现环境习惯法的社群参与性和克服环境制定法的非自足性的有效途径。
首先,“自下而上”路径模式的比较优势更为凸显。在“自上而下”路径模式中,由于环境习惯法的被动性和环境制定法的单向性,仅以立法“本土资源”的形式而被国家环境制定法所接受和摄取的环境习惯法寥寥无几。不仅如此,在国家环境制定法“肢解”式的接受和摄取后,不仅环境习惯法自身体系的系统性遭到破坏,造成环境习惯法的系统性功能不复存在的后果,而且在一个由历史、文化、生态、经济等因素相互交错和形成的综合体系中,“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路径只有保护生态多样性的外观,但却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经济的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基础,直接威胁到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再生能力。*Gray, Andrew. Between the Spice of Life and the Melting Po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its Impact on Indigenous Peoples.(IWGIA Document 70).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on Indigenous Affairs, Copenhagen, 1991.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领域,“自上而下”路径模式的弊端更为显见。一般而言,“环境管理的模式因历史条件和具体问题的不同而在优先性选择以及具体目标的设定上有所区别,因此只按照‘自上而下’的单一导向而设计的‘蓝图’在资源管理实践中也会因其缺陷而遭致弃置的命运”*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e Management: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2001,95.。由环境习惯法积极参与的“自下而上”路径模式则不同。在“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中,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与国家环境制定法的认可或承认是这一路径模式得以有效展开的两个基本条件。因此,“自下而上”路径模式的实践是环境习惯法与环境制定法两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体现。这种双向性参与使环境习惯法在充分“表达”自身的同时不失其现代效果。而且,在“自下而上”路径模式中的充分参与使环境习惯法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持其整体性规范功能,避免“自上而下”路径模式中环境习惯法整体性功能被“肢解”的不足。
其次,“自下而上”路径模式使环境习惯法的社群参与机制延展到现代环境法之中。环境习惯法规范本身体现了与其相关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综合性。按照综合地缘政治学说的经典“三螺旋”理论,“由诸如资源区位、资源管理制度等构成的综合性整体被预设为由相互交织的生物物理关系、社会文化关系以及政治经济制度所构筑的‘三线螺旋’结构——表明结构体系中的三要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影响并决定其他方面,同时一方为另一方的更好发展创造条件”*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e Management: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2001,146-148.。同样地,按照“三螺旋”理论,土著民社群以类似的组合将地理的、神话传说的以及社会的景象编制入一个鲜活的体系之中。在这个体系中,昨天、今天、明天以及生命的意识和意志共同构成了一个逼真的整体。*Rose. Nourishing Terrains: Australian Aboriginal Views of Landscape and Wilderness. Australian Heritage Commission, Canberra, 1996a,7.从规范制度角度观察,维系这一综合体系的主要纽带是社群长期而广泛的民主参与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民主参与机制也是环境习惯法能长期保持有效性的根本所在。因此,只有确保民主参与机制的价值优势,环境习惯法的现代价值才能真正实现。“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正是民主参与机制能够在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中实现的有效途径。通过社群“自下而上”的参与性推动,进入现代环境法话语体系的环境习惯法仍不失民主参与的广泛性特征。学者在乌干达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恰当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乌干达西部地区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使用权和管理权保护的实践中,“国家制定法运行的‘自上而下’模式使法治实践与制定法规定相脱节,而且还限制了资源法律制度在监督和实施中的地方社群参与。而实践中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管理途径却是‘自下而上’地来自‘草根’社会,因为‘草根’社会中的所有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都是立足于地方性的广泛参与之中”*Joel Hartter, Sadie J. Ryan,Top-down or bottom-up? Decentralizati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usufruct rights in the forests and wetlands of western Uganda, Land Use Policy, 2010,27:815-826.。
最后,“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是克服环境制定法非自足性的有效途径。统一规定、一体遵行,是制定法的规定性和主要特征。环境制定法也概莫能外,统一化的立法特点往往使规范的共性与具体规范对象的个性之间产生严重的不适应。即使在地方立法层面有专门针对地方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特殊性的相关立法,但地方性环境法律规范在实践中仍然无法具备与环境习惯法一样的弹性特征和适应性功能。因此,在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实现途径中,“在‘自上而下’路径模式时制定法的统一性无法与规范对象和相关权利的不确定性特征相匹配”*Kipaya Kapiga, Bottom-up and Top-down approaches to development, June 26, 2011, See from, http://global_se.scotblogs.wooster.edu/2011/06/26/bottom-up-and-top-down-approaches-to-development/.。基于祛除制定法统一化科层运行模式中僵硬且繁琐的局限,“用更为合理的‘自下而上’模式替换复杂的‘自上而下’模式的观点在逻辑上是完全自洽的”*Peter Orebech, Fred Bosselman, Jes Bjarup, David Callies, Martin Chanock, The Role of Customary Law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439.,因为“‘自下而上’的路径模式将现有(环境习惯法)制度视为受制于历史制度,因而逐渐变迁、演进而非革命性变迁的过程”*William Easterly, Institutions: Top Down or Bottom Up?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 Proceedings, 2008,2,95-99.。在这一渐进式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环境习惯法制度规范与具体规范对象之间的相互适应。新西兰毛利人环境习惯法的现代转型、美国纳瓦霍印第安人环境习惯法的现代化过程以及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环境习惯法权利的现代立法确认等实践均例证了“自下而上”路径模式之于克服环境制定法非自足性的有效性和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实现的合理性。即使在阿富汗这样政治动荡的国家,习惯法仍被认为是具有重要规范价值的法律形态。阿富汗国家司法部认为,“习惯法是一种具有弹性和适应性,且与地方性信仰和特殊情况相符合的法律治理手段”*Amy Senier, Rebuilding the Judicial Sector in Afghanistan: The Role of Customary Law, The Fletcher School Online Journal for issues related to Southwest Asia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Spring 2006.。因此,结合前文关于“自上而下”路径模式的优越性,基于实现本土民众的社群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并置的目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模式应当在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中并行不悖。*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e Management: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2001,96-97.如此以来,“自下而上”路径模式中环境习惯法规则的弹性与适应性属性与前述“自上而下”路径模式中统一性环境制定法的强执行力特征相呼应,形成了规范外观与规范实效在现代环境法“场域”中的完美契合。
2.“自下而上”路径的展开
“自下而上”路径模式的核心内容是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在现代环境法语境中,环境习惯法的参与在范围和方式上有特殊的要求。
第一,环境习惯法的参与范围。在现代性语境中,制定法在国家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管理领域,环境制定法同样是主要的制度规范。因此,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应当只限于一定的范围。纵观现代环境立法的规范类型,技术性规范和权利义务性规范是其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其中,技术性规范与现代文明发展所取得的科技成果相关联,显然,环境习惯法因民间性和大众话语的特点而缺乏必要的技术性知识基础,也无法与现代环境法中的技术性规范衔接起来。这一现象无论在弱化环境习惯法的我国环境立法中,还是在利用环境习惯法规则构建地方性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美国纳瓦霍部落和澳大利亚北方土著民聚居区的实践中都具有共同性。所以,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因技术性知识的缺乏而无法触及到现代环境立法的技术性规范领域。
与前述情形不同的是,在各国环境习惯法现代立法转型的成功实践中,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权利义务性规范领域展开。究其原因,环境习惯法的参与并不是形式上的规则“进入”或转化的实现,而是由环境习惯法所承载和确认的环境资源权利获得现代国家环境法认可的过程。因此从形式来看,环境习惯法的参与更多地以土著民、部落等地方社群以争取传统习惯法权利的活动表现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有影响的抗议活动。比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克里族印第安人(Cree)和因纽特人(Inuit)在政府发起的一系列水电站建设项目中为争取自己的传统土著权利而进行了许多抗议和斗争,对土著民(国家)主权主义的复兴,以及在加拿大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倡导土著民自治的政治和习惯法制度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McCutcheon, Sean. Electric Rivers: The Story of the James Bay Project. Black Rose, Montreal, 1991; Jhappan, C. Radha. Global community? Supranational strategies of Canada’s aboriginal peoples.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1992.3(1):59-97.
长期以来,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工业化发展一直与水电业的发展紧密相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魁北克省更是以空前的速度发展水电业。1971年,当地主要的水电企业——魁北克水电(Hydro-Quebec)宣布了一项新的建设规划——詹姆斯海湾项目(James Bay Proposal)。这项建设规划包括建设4座水电站、4座大坝、18条泄洪和防控设施以及80英里防洪堤。*O’Reilly, James. The role of the courts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James Bay Hydro-electric Project, in Vincent, Sylvie and Bowers, Garry (eds) Baie James et Nord Quebecois: Dix ans Apres/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Ten Years After. Recherches amerindiennes au Quebec, Montreal, 1988,33.同年7月,克里族印第安人开始对该项目进行抗议,认为他们“使用土地的权利、狩猎的权利、捕鱼的权利以及维系克里族人生存的权利都是基本人权”*Richard Howitt, Rethinking Resource Management: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Indigenous Peoples. Routledge, 2001,302.,因而加拿大和魁北克政府无权干涉和对其施以影响。之后,生活在更远北方地区的因纽特人也就詹姆斯海湾项目提出抗议。魁北克省政府最初的态度十分强硬,拒绝与克里族印第安人以及因纽特人进行谈判,认为“水电项目不容谈判,印第安人没有特殊的权利”*Awashish, Philip. The Stakes for the Cree of Quebec, 1988:43, in Vincent, Sylvie and Bowers, Garry (eds) Baie James et Nord Quebecois: Dix Ans Apres/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Ten Years After. Recherches Amerindiennes au quebec, Montreal:42-5.。于是,克里族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启动了司法程序以图终止该项目。马卢夫法官在初审判决中认为,“克里族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在他们生活的领土上显然具有相关权利”,因而发出了一份停止工程后续进行的禁令。虽然初审判决后来被高级法院的判决所推翻,但初审判决无疑是“魁北克政府态度的极大转折点”*Awashish, Philip. The Stakes for the Cree of Quebec, 1988:43, in Vincent, Sylvie and Bowers, Garry (eds) Baie James et Nord Quebecois: Dix Ans Apres/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Ten Years After. Recherches Amerindiennes au quebec, Montreal:42-5.,因此意义重大。此后,魁北克省对土著民传统习惯法权利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任命了专门的谈判人员与克里族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接洽处理相关事宜。这一谈判进程直接导致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份“现代条约”——1975年《詹姆斯海湾项目和北魁北克协议》(James Bay and Northern Quebec Agreement, JBNQA)的诞生。该《协议》建立了有关环境保护、土著民社群发展以及区域治理的长效法律制度框架,并就项目建设对土著民权利造成侵害的赔偿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加拿大克里族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以实现他们的传统习惯法权利为主张,最终使他们的传统习惯法进入到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之中,是环境习惯法以“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方式实现现代价值的重要范例。当然,此类案例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地区、斯堪的纳维亚北部萨米人聚居地区均有发生。
第二,环境习惯法的持续参与。在前述引用的加拿大案例中,环境习惯法及相关环境资源权利获得国家认可是一持续时间较长的谈判过程。诚然,大多数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通过环境习惯法的积极参与而引起环境制定法的被动认可都以持续性的权利主张而最终实现。在现代国家,立法者已然混淆了制定法的重要性与法律正当性之间的界限。在技术立法更为显著的现代国家环境立法中,设计科学、精美细致的制定法条款往往被认为是现代法治唯一有效的制度依据,因而忽视了其他民间规则的价值。于是,立法者长期形成的固定思维无法接纳环境习惯法作为另外一套明显不同的规则系统进入现代环境法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环境习惯法“在下而上”的参与不易打破立法者的思维桎梏。而只有持续性参与才是实现其现代价值的可能方式。因此,持续性参与是实现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有效方式。
不仅如此,持续参与也是确保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持续有效的条件。因弹性特征和适应性属性,环境习惯法规范能有效地根据环境的变迁做出调整,从而在历时性角度始终保持规范的连续性和有效性。与环境习惯法不同,环境制定法规范对环境变迁的调试则是通过立法修订程序或创制新法的方式实现的。显然,修订前后的法律规范之间没有任何历时性关联。循此,尽管环境习惯法在之前某一时刻因积极参与而获得了国家环境制定法的认可,但很有可能在环境制定法频频修订的过程中被搁置一边。从这一意义上看,持续性参与是确保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持续有效的重要条件。通过“自下而上”的持续参与,环境习惯法将持续供给现代环境立法,在维持环境习惯法现代价值的持续有效性的同时也使现代环境立法在环境习惯法的持续供给中日臻完善。
澳大利亚的实践为我们理解持续性参与的重要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1992年昆士兰地区的马博案之后,澳大利亚基廷工党政府通过了《土著民权利法案》,作为对该案件以及土著民土地等权利的要求。该法实施两年后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一份违背《土著民权利法案》的判决引起了各界的关注。1996年12月23日,高等法院就维克土著民诉昆士兰州案(Wik Peoples v. the State of Queensland)作出法庭判决。案件的争议焦点是,依制定法而达成的租约能否对抗土著民权利。围绕这一问题,法院的判决认为,依制定法而达成的租约不能赋予租约权利人以排他性所有权,故土著民权利可依照合同条款和特定目的与租约权利人的权利共存。但是,当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依制定法达成的租约可以对抗土著民权利的存续。*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2000) Wik People v State of Queensland 2000 FCA 1443 (3 October 2000).之后在政治领域和公众领域的激烈反应中,联邦政府提出“维克10项计划”以回应该项离奇判决,要点如下:第一,国家土著民权利委员会在土著民权利申请事项上具有绝对的管辖权;第二,基于国家利益,州政府可根据法律授权解除就王室土地上的土著民权利;第三,提供公共设施的土地属于土著民权利申请的例外;第四,矿业和牧业租约可被允许与土著民权利共存;第五,国家土著民权利委员会只对获取传统土地权利创造条件,而不是针对所有的土著民权利;第六,登记审查是所有申请的强制条件;第七,取消都市之中或周边地区的申请权;第八,政府有权管理任何区域的土地、水和大气;第九,所有申请均被规定以严格的时间限制;第十,通过创设土著民土地使用协议的方式达到权利的共存。“维克10项计划”成为修改完善1993年《土著民权利法案》并形成1998年《土著民权利法案(修订本)》的重要基础。*据澳大利亚土著民权利委员会的立法动态显示,1998年之后,《土著民权利法案》又分别于2007年、2009年、2010年、2011年进行了多次修订。1998年之后,“维克10项计划”成为了昆士兰地区《土著民土地使用协议》长效实施的重要依据,大量土著民开始了他们以环境习惯法权利为基础的土地权利。仅2011年1月1日到6月30日的半年时间内,就有15名新的申请者申请了《土著民土地使用协议》。*National Native Title Tribunal of Australia, National Report: Native Title, August 2011:1.可以说,在从《土著民权利法案》的制定到修订,再到《土著民土地使用协议》的长效实施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土著民依据传统习惯法对土地权利的持续主张一直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Classification, Selection and Path: Logic Approach to Achieve Modern Values of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Guo Wu
(1.Gansu Institute of Politics and Law, Gansu, Lanzhou 730070;2.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From class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articl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to its establishment by way of the two practical paths, i.e. the “from-top-to-bottom” path and the “from-bottom-to-top” path are interrelated and successive with each other. This is just the logic approach to bring about modern values of the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Classification and selection involves mainly how to take the essence and discard the dregs from the tremendous amount of the gauge groups of the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with an eye to the identification and selection of the “raw material” of the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before its “deep processing”, whereas the “from-top-to-bottom” domination and the “from-bottom-to-top” participation in its drawing-up are the two unobstructed and complimentary paths to realize its modern values.
environmental customary law; modern values; classification; selection; path
2015-03-10
郭武(1980—),男,甘肃通渭人,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
①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文明视域中我国西部地区民族环境习惯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DF0-052
A
1001-5973(2015)02-0102-17
责任编辑:寇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