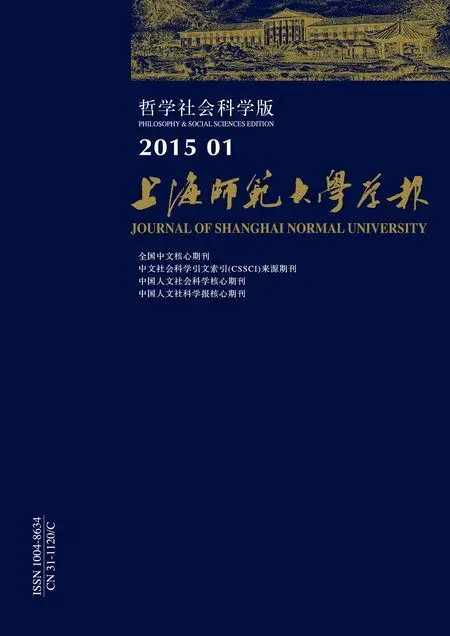同意的涵义及其中国式表达
吕耀怀
(苏州科技学院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在西方学界,有一种通常被用来阐释政治义务之根源、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的理论叫作同意理论,而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同意概念是这种理论的基础或核心。当然,同意概念并非仅仅具有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证成的功能,在商业领域、医疗领域乃至家庭生活领域,都有涉及个人同意或集体同意的问题,只不过在政治学领域同意理论相对成熟且更为丰富。随着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同意概念也逐渐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和讨论。中国社会对于同意概念的认知,最初是通过在医疗领域中得到广泛讨论的知情同意概念而实现的,此后,同意概念又为政治学界、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所使用,其他领域中同意概念现在正处于准备或偶尔使用的阶段。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现代化,同意概念的影响将会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然而,对于同意这一源自西方的理论范畴,人们的认识存在着诸多模糊、不确定之处,有待学界的进一步澄清和阐释。为此,本文在梳理和审视西方学界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同意概念予以初步的辨析,并考察其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达,以期引起更多的探讨和争鸣。
一、同意的基本涵义
关于什么是“同意”,曾有国内学者指出:“所谓‘同意’指的是行为者用来在自已与同意对象之间创立一种特定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1]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其将同意定位于一种行为而不是或不单纯是一种心理状态,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西方学者的某些有益的研究成果。在西方学术界,尽管历史上曾有不少学者探讨过同意问题,但关于同意概念的涵义,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迄今最具权威性的解释,也许是当代西方学者劳伦斯(Lawrence)和夏洛特·贝克(Charlotte Becker)主编的《伦理学百科全书》中专门设立的“同意”词条给出的定义:“同意是一种行为,一个人通过这种行为改变了其与他人相处之涉及他们可能做什么的日常关系。日常关系是由权利、职责、义务、权益等等来制约的那些关系。一般而言,如果某人X同意Y做行为A,那么,在X(或处于X位置的另一人)没有同意的情况下,Y就无权或仅有极有限的权利去做A。通常情况下,X所同意的是Y发起的某个提议,或至少可推测是Y想做的事情。”①由于该词条为克雷尼格(John Kleinig)所撰写,因此,克雷尼格当然也就很可能是当代在同意之界定问题上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为使讨论简便起见,仅就同意之最一般涵义而言,我更倾向于采用克雷尼格在《同意的伦理学》中给出的说法:同意“是响应他人提议并借以分担其中责任的一种合作形式”。[2]
克雷尼格在给出这种界定时,首先论证了同意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行为,是个人明确地倾向于配合他人提议的行为。克雷尼格指出:“‘同意’的词源及其语义范围内的观念,使得某些论者认为它的主要功能或至少是基本功能就在于确认一种心理、态度或信任的状态。同意被认为是与他人‘有同样意向的状态’,被认为表达了一种‘心理上的赞成态度’或表明情感与意见方面的一致。更具体地说,它被认为是表达与他人之行为或计划的相符,或成功完成这些行为或计划的愿望。”[2]克雷尼格认为,在评价这种观点时,我们不必否认同意往往反映了某种一致或相符。而且我们尤其指望这是事实,尽管所同意的事情并非都需要同意者做出实质性的努力。但以此为首要的或基本的关注点却意味着关注点方面的重大误导。在他看来,对于同意来说,态度一致或意向一致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当同意伴有这些因素时,往往可以称之为“全心全意的”或“完全的”同意。在其他情况下,同意则可能是不情愿的、勉强的、轻率的、内疚的或半心半意的。[2]这就是说,即使在没有“心理上的赞成态度”或这种态度不明朗、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也可能做出同意的表示。
克雷尼格以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同意这一事例,说明心理上的赞成态度对于同意来说并非必要条件。一般而言,父母的同意是与其内心的情愿相一致的。但事情却并非必定如此。父母可能认为他们的某些愿望不会在拟议的子女婚姻中得到实现或他们的孩子还没有形成对恋爱关系的成熟且稳定的认识。然而,他们可能会表示,尽管他们不喜欢孩子的这次婚约,但他们不会阻碍孩子与对方的结合。虽然不情愿,他们仍然会表示同意。这种同意的前提条件,不是他们内心的情愿,而是他们处于能够以某些实际的方式(要么不给予必要的支持,要么出面阻止或阻碍他们的结合)单方面地影响其子女婚姻计划的地位。
接下来,克雷尼格逐一反驳了另外三种对同意的解释,即:(1)作为制度化概念的同意;(2)作为自我承担性义务(self-assumed obligation)概念的同意;(3)作为一种承诺的同意。
所谓作为制度化概念的同意,是指将“X同意Y之做a”分析为“X赞成/授权Y之做a”这样的解释。在克雷尼格之前,普拉梅纳茨(Plamenatz)与西蒙斯(A. John Simmons)曾以这种方式表达他们自己对同意概念的理解。但在克雷尼格看来,赞成与授权是制度化行为。而普拉梅纳茨与西蒙斯预设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有与许可、认可、批准、允许、委任、准许、合法化等概念相关的职位与义务、角色与责任、权利与权力以及赞成与授权。克雷尼格认为,这种分析的错误之处,就在于他们不适当地将某些有限的语境中同意所产生的效果推演为同意的一般作用。签署一份同意表格确实授予大夫以做特定手术的权利,但现在同意其孩子的婚姻的父母没有任何授权而是表明(在最低限度上)他们不会为难他们的婚姻,倘若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话。寻求同意的必要条件是被征求同意者的优越地位,而且尽管这种优越性有时通过制度化地位表现出来,但其并非总是如此。[2]
所谓作为自我承担性义务的同意,通常指这样的情形:如果X同意Y之做a,那么,X就承担了一项至少不能干涉Y之提议行为的义务。从这一点可推出:同意行为之最有成效的含义就是承担义务。西蒙斯曾对此提出批评,他指出:由同意形成的义务仅仅是第二位的;同意的主要目的是授予他人以行动的权利,而在这样做时,为另一方产生或授予另一方一项特定权利。[3](P276)威尔(Weale)用涉及第三方的同意案例(即X同意Y对Z做a)表明了西蒙斯观点的不足之处。[4]如果无论是X还是Y都无权对Z做a,那么,X就不能通过同意如此做来授权。但威尔也还是赞同包含在同意中的义务仅仅是第二位的这样的观点。他认为,最好不要将同意理解为承担义务的言外行为,而是理解为有意诱导他方信任己方的言后行为。②与威尔的主张不同,克雷尼格认为,我们必须将同意理解为一种言外行为。X在同意Y之做a时所为,就是为与Y分担做a的责任而行动。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关于X是否同意Y之做a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关于X之共谋的问题。
所谓作为一种承诺的同意,是指威尔和许多其他人将同意视为承诺的一种形式——一种消极的承诺。在这种承诺中,一个人在他方有提议时答应做或克制不做某些事情。毫无疑问,这是人们为什么认为同意将自己置于一种义务之下的一个原因,一般将承诺视为将自己置于一种义务之下的典型情况。虽然克雷尼格不认同佩特曼(Pateman)对消极承诺(好像在承诺时,一个人没有表明自己有“独立判断和理性思考的能力”)的怀疑,但他接受承诺是“义务关系的自由生成”这个观点。在克雷尼格 看来,“我承诺”这种表达的关键之处(如果是自由表达的话)是对说者的约束,而这不是同意的关键之所在。“你承诺做a吗?”与“你同意做a吗?”这两个问题的意义很不一样,在前面那个问题中,接受提问者被要求通过将他自己约束于做a而参与一种社会实践;而在后面这个问题中,所寻求的则是接受提问者之自由参与做a。[2]
由上述分析可知,克雷尼格的同意概念,与对同意的其他解释相比较,最为明显的特征或特殊意义就在于,凸显了作为同意方的X的责任。X不是简单地表示同意,不是因为X同意Y做或不做某事,就将做或不做某事的责任完全转移到了被同意方Y那里;X在表示同意后,仍然应当承担Y做或不做某事所导致之后果的某些责任。对于同意之其他解释的不足或缺陷,就在于其他解释一般都缺省了这种责任。此外,克雷尼格对同意概念的解析,在深度、细致性、周全性及概括力等方面都明显超越了其他西方学者的相关诠释。
二、明示同意、默示同意与假设同意
同意概念作为一种理论之要素的情形,其最早的典范出现于洛克的《政府论》(下篇)。洛克将同意视为论证政治社会的起源和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甚至是其政府理论的核心之所在。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尽管他并没有给出同意的确切内涵。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5](P59)一般认为,在洛克的论述中,同意至少有两种形式:明示同意(express consent)与默示同意(tacit consent)。虽然洛克认为人们对默示同意的理解要比对明示同意的理解更为困难,因而他以更多的篇幅讨论默示同意问题,但在洛克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却始终存在着不仅对默示同意也对明示同意之理解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对同意的这两种形式都给以说明。
爱德华·哈里斯(Edward A. Harris)曾经指出:“明示同意是指个体对于其放弃自然权利与自由、成为这个国家的一份子并服从它的法律的意图的自愿宣示。该个体与其所在文明社会的其他成员达成了一项服从其法律的事实上的协议,回报是其人身与财产得到可靠保护。洛克认为,这种形式的同意将‘永久性的、绝对必要的’义务加于给出这种同意的个体,而这些义务只有在该政府解散之后或在该国抛弃这一个体后才终止。”[6]爱德华·哈里斯对明示同意的这种解释,显然是因应了洛克以同意来论证政治社会之起源和政治权力之合法性的思路。因此,这里的明示同意局限于政治领域的情形,其严格的意义并不适用于其他领域。尽管如此,但从爱德华·哈里斯对明示同意的这种解释中,至少可以推知:明示同意的特点就在于其为公开宣示的同意。对此,爱德华·哈里斯有进一步的说明:“知情个体在公共场所有意识地作出的服从法律的承诺就成为明示同意的表征,个体因这种表征而可以被认为获得了政治义务。”[6]“在公共场所”这一短语规定了明示同意之宣示的公开性;对于政治领域的明示同意来说,这种公开性往往是非常重要的。但若明示同意用于私人交往、私人关系,则未必要有公开性。
卡西内利(C. W. Cassinelli)认为,理论家们为了证明明示同意的存在,就“必须找到一种特定行为,这种行为表现出一部分公民对于另一部分公民(这通常是由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所组成)所做出的某种或某些特定行为的自愿赞同或认同。……古老的社会契约论是明示同意的原型:通过自愿给出对一份协议的明确赞同(可能以说话或文字的形式),协议的条款约定了将是之公民同意接受将是之政府的控制,这个政府以后的行为已经得到明确的同意。在这种社会契约的案例中,那些给出同意的人随后将成为被统治者,而他们所同意的行为则由政府官员做出且这些行为处于该协议所明确陈述的范围之内”。[6]卡西内利的这段话,说明了明示同意具有正式性、明确性的特征。尤其在社会契约论之明示同意的原型中,赞同之同意的意思表达,采取的是正式的言语或文字的形式,而且这种意思是明确表达出来的。
在洛克那里,明示同意似乎指的是“通过明文的约定以及正式的承诺和契约,确实地加入一个国家”的行为。[5](P76)爱德华·哈里斯和卡西内利对于明示同意的理解,大体上与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的思想相吻合。但以洛克为代表的这种关于明示同意的观点,却一直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明示同意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除了假设的签订原始契约的情况之外,现实中很少有人曾有过对其政府的明示同意。爱德华·哈里斯指出:“明示同意的问题在于,对政治义务的解释被严格地限制在仅仅涉及实际作出这种同意表征的极少数人的范围内;例如,那些为成为公民而宣誓的人或为就职而宣誓的人。作为对于政治义务和合法权威的一般性解释,明示同意这个概念完全难以胜任。”[7]西蒙斯也认为,“十分明显,明示同意者的人数很少;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从没有面临适宜于对政府权威做出明示同意的情况,更不用说实际做出这样的行为”。[6]既然只有极少数人实际做出过明示同意的表示,那就很难以明示同意来解释相对于所有公民(至少是大多数人)而言的政治义务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的正当性。洛克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他提出了默示同意的概念。
最初的默示同意,在洛克那里是这样表述的:“只要一个人占有任何土地或享用任何政府的领地的任何部分,他就因此表示他的默认的同意,从而在他同属于那个政府的任何人一样享用的期间,他必须服从那个政府的法律。这不管他所占有的是属于他和他的子子孙孙的土地,或只是一星期的住处,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事实上,只要身在那个政府的领土范围以内,就构成某种程度的默认。”[5](P74~75)洛克对默示同意的这种解释,表现出某种偏狭性,即仅仅将居住在某国或只是在公路上自由地旅行作为默示同意的形式。
爱德华·哈里斯根据洛克及其之后西方学者的观点,对默示同意的各种表达做了进一步的归纳,“无论什么样的被当作是默示同意的行为,都必定不会是明确表达的同意。相反,这种同意是从某些其他的表达、行为甚或是沉默中推导出来的”;“默示同意行为必须是几乎每个人都做的事情。根据这一普遍性条件,可以确定这么几点:居留在某国,接受该国提供的好处,交税及通过投票等参与这个国家的事务”。[8]哈里斯的这种归纳,既以洛克的观点为基点,又反映了洛克之后西方思想家们对洛克默示同意观点的某些修正或完善,实际上扩展了洛克对默示同意的界定,其中不仅将“居留在某国”而且还将“接受该国提供的好处,交税及通过投票等参与这个国家的事务”作为默示同意的表达。
然而,早在18世纪,休谟就对洛克的默示同意提出了批评。休谟认为,“隐含的同意只有在一个人想象事情可由他自己抉择的地方才有存在的余地”。[9](P126)而许多人之所以持续居留在某个国家,其实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财产来自由地选择移民(休谟问:“一个贫穷的农民有离开他的国家的自由吗?”),故将居留作为默示同意的表征就显得理由不充分。当代一些西方学者进一步扩展了休谟的这种批评,认为即使具备移民的条件,持续居留也不一定是默示同意的表征。例如,西蒙斯指出,虽然往往可以得到帮助贫困者移民的生活物资,但似乎没有任何生活物资能够补偿一个人通常必须将其与他所居住的国家联系起来且不能带离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有价值的所有物。[3](P99)与此类似,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也指出,“如果不能够更自由地有所得,且有更真实的选择机会,而不只是下降到在外国旗帜下的一无所有中开始生活”,一个国家的国民之所谓同意通常就不会有重要意义。[10](P193)
接受国家提供的好处,也难以认作是默示同意的表征。爱德华·哈里斯 认为,“当合法权威和政治义务的范围限于那些自愿从这个国家接受好处的个体时,这种权威和义务在程度上也是有限的。一种基于接受好处之默示同意的对于义务的解释,面临着要表明个体服从这个国家的法律的义务超越仅仅服从导致其所接受的好处的那些法律这一困难”[7]。这里的困难在于,如果以接受国家提供的好处来证成服从国家法律的义务,那么,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某公民有义务服从的法律,就仅仅是与他所接受的好处有关联的法律,而对于与他所接受的好处无关联的法律就似乎没有服从的义务。例如,自愿接受使用国家高速公路系统的个体本应有服从并非直接关联到这种好处的法律的义务,但若以接受好处作为服从法律之义务的理由,则只接受使用高速公路这种好处的个体,似乎就仅仅负有服从管理高速公路的法律(如速度限制、汽车重量和尺寸限制)的义务以及服从要求他交税和付费(用于修建和维护公路)的法律的义务,而该个体与服从管理如处置有毒废物等的法律的义务之间就似乎没有任何关系。问题的实质是,公民遵守国家一切法律之义务的普遍性、一般性与公民接受特定好处之事实的特殊性、个别性之间是不对等的。
还有西方学者对将参与国家事务视为默示同意之表达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卡西内利着重分析了视参与选举为同意表达的观点。[8]他认为,这种诉诸选举的同意理论的第一个缺陷是:不仅同意可能仅仅由小部分人给出,而且还总是有相当比例的明显持异议者。这样,这种选举行为实际上最多只能被视为部分人的同意行为,因而无法证成所有公民都应有的服从法律之义务;第二个缺陷与选举制度本身有关。在选举到来时,投票者面临着一个涉及政府性质的既成事实:全部情境的最重要方面是选举制度自身已存在,而且没有人曾给予投票者以赞同它的机会。这就意味着,参加选举的个体是在一个未经其同意的制度框架内投票或进行选择的。这大概属于制度本身的合法性问题,而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在此种制度下的选举或投票本身也可能还有未决的合法性问题。尽管卡西内利的分析所直接针对的是明示同意,但他明确指出:“这里提出的反对同意的论证也适用于默示同意。”[7]这就意味着,他所说的诉诸选举的同意理论的两个缺陷,不仅为明示同意所具有,而且也是默示同意的问题。
除了明示同意、默示同意之外,另有人提出了假设同意的概念。汉纳·皮特金(Hanna Pitkin)在评论洛克的同意观念及特斯曼(Tussman)对洛克之同意观念的研究时指出:“相关的同意似乎最好被解释为假设的或推定的——出自理性人的抽象的同意。如同洛克一样,特斯曼可能被推回到这一位置:你所负有的义务既不是源自你自己的同意也不是来自多数人的同意,而是由假设的‘自然状态’中的理性人不得不做出的同意所决定的。一个在这样的假设同意的范围内行动的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从而我们都负有服从这样的政府的义务。一个蓄意践踏这样的同意所设立之边界的政府是专制政府,从而我们有反抗这种政府的自由。”[11]皮特金在这里所说的假设同意,主要是指称社会契约论所设想的原初状态中的同意。而亚瑟·卡夫列克(Arthur Kuflik)则将假设同意扩展到现实世界,在他看来,虽然与日常对话中的常见表达相比较,哲学讨论中有更多的专门术语,但“假设同意”这一短语的确表达了一种对我们来说并非完全不熟悉的思路。在许多情况下,虽然没有感觉到已经给出了同意,但似乎有理由推论且以某种方式关联到认为:如果某些条件(1)已经获得,(2)将会获得,或(3)尚待获得,那么,某人的同意就(1)已经获得,(2)将会获得,或(3)尚待获得。[12](P131~161)从卡夫列克的这种表述中可以知道,所谓假设同意,是一种虽然并未实际做出或发生,但却可以在满足某些条件的情况下合理推出的同意。例如,一个先前有但现在缺乏决策能力的人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可能的治疗方案——会(或不会)延长生命、改善健康条件、避免残疾和/或减轻不适的治疗方案——产生了一些问题。人们假设,如果该个体重新获得了决策能力并知道、了解这种治疗的预后、治疗的选项、预期好处和相关风险等,那么,该个体就会批准家庭成员和/或医生采取(或阻止采取)某些措施。又如,道德哲学或政治哲学中的理想化的契约理论:人们设想了一个纯属虚构的(也是高度理想化的)审议过程,而参与这种过程的各方将(或将不)同意用以控制社会最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设计的某些一般原则。从这些事例来看,假设同意的确不仅可能具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现实价值。但正如卡夫列克所表明的,假设同意只在某些熟悉且重要的语境中起作用,而在另外一些语境中,假设同意要么是无关紧要的,要么就是不必要的。[12](P131~161)
三、西方的同意困境与同意观念的中国式表达
明示同意、默示同意在解释政治义务或合法权威时表现出的局限性,使得一些当代西方学者逐渐降低了对其在这方面之应用的热情。例如,罗尔斯在其政治哲学中,就用社会契约作为工具来生成和建构原初位置,而不是通过明示同意或默示同意的自愿表达来订立一项社会契约。罗尔斯说:“我认为,至少对于宪政民主下对政治义务的解释来说,最合适的构想是作为我们许多的政治思想之根源的社会契约论的构想。如果我们用一种适当普遍的方式对它予以谨慎的阐发,那么,我认为这个原则就为政治理论甚至伦理理论本身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基础……我建议的阐发是这样的:社会安排必须遵循的原则,尤其是正义原则,是处于同等自由之原初状态的自由且理性的人们将会同意的原则;同样,管理人们对机构之关系并规定他们的自然责任与义务的原则,是他们在处于如此情境中时将会予以同意的原则。应当马上指出,根据这种对于契约理论的解释,正义原则被认为是假设协议的结果。”[13](P240~242)这里,罗尔斯诉诸近似于假设同意的假设协议概念,但即使使用这个概念,也没有真正解决政治义务的解释问题,以致罗尔斯自己都认为,“……严格地说,公民没有政治义务”。[14](P333~391)因此,将罗尔斯的假设契约作为对于政治义务的一般性解释的基础,是没有多大用处的。[15]
虽然明示同意、默示同意及假设同意在解释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利之合法性时都因其自身局限而陷入了困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意概念就因此而丧失其存在意义或其重要性已经不复存在。即使是声称“同意”是一个虚幻概念的卡西内利,其具体所指的“同意”,也是与解释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相关的“被统治者的同意”,而没有在其他意义上否定同意的价值和意义。卡西内利这样说:“即使同意并非为民主国家所独有,但正如某些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代议制政体下仍然可能比任何其他政体有更多的同意”;“代议制政体允许最大多数的人参与政治决策,而且,这种政体中的制宪权为最大比例的社会阶级所拥有。这些特征表明,在所有国家中,只有民主国家要求有其最大多数人的同意”。[7]由此可见,卡西内利甚至还有些强调民主政体下最大多数人的同意,只是不赞成将“被统治者的同意”作为区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指标。即使是饱受争议的默示同意概念,人们感到困惑的也主要是其在解释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之合法性方面的应用,“但我们不必受这些困惑的影响而认为不存在默示同意这样的事情;相反,至少在非政治学的领域中,真正的默示同意的事例是相当多的”。[8]这样看来,西方学界在同意问题上所产生的困境,主要存在于用同意观念为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的辩护或论证方面;如果不是将同意作为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论述同意观念在政治领域其他方面或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其他领域中的应用,则可能不至于引起多大的争议。事实上,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对同意概念的质疑,也主要存在于与政治义务或政治权威之合法性相关的方面;同意概念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如医疗、医学研究领域中的知情同意概念,不仅没有被质疑声所遏制,反而越来越走向深入且影响越来越广泛。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没有当代意义上的同意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与深入,西方的同意观念逐渐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和重视。最早在中国社会得到关注并得以广泛应用的,是同意概念的一个种概念——具体的知情同意概念。今天的中国社会,不仅有许多专业人士研究知情同意概念(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所有对同意概念的研究中最多且关注度最高的),而且这个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普通中国人也经常接触到并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如何应用这个概念。这里,我们不打算展开对这一人们已经有丰富认识的知情同意概念的论述,而主要就同意观念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种重要表达——人民满意不满意,给出一些初步的分析。
众所周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是我国政府原则上用来衡量其工作的基本标准。这一标准,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的根据是群众路线。然而,从更广泛的国际视角来看,从政治哲学、政治学一般理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这一标准是同意观念的内在要求,是同意概念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一种特殊表达。这就是说,同意观念可以作为“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这一标准的理论基础,可以用同意观念来对这一标准予以合理性解释。
同意观念突出的是人民主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现代政治就是同意的政治。而“作为认可和辩护统一的现代政治正当性,实际上就是人民同意的道德认可原则与人民主权理论的辩护形式的统一,即人民同意是现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石”。[16]任何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其权力的合法性或道德上之正当性的获得,都无疑应基于人民的同意。政府是否具备运用公共权力的道德资格,从根本上说,就是看其是否得到了人民的同意。公共权力理应服务于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则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如果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为民众谋利益,人民就会满意;反之,如果政府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为小集团谋取私利,人民当然就不会满意。就此而言,“人民满意不满意”,是人民群众是否同意赋予政府以运用公共权力之资格的基础标准。“满意”蕴含着同意,而“不满意”则显示出不同意。如果政府(或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之所作所为不为人民所满意,那么,人民就有理由否定政府(或政府部门、政府工作人员)运用公共权力的资格。
“人民满意不满意”,不仅是人民群众是否同意赋予政府以运用公共权力之资格的基础标准,而且还是政府工作的评价尺度。“满意不满意”,在很多情况下体现出人民对政府工作之效能、效率的评价。政府的工作做得好,效能突出,效率高,人民就会感到满意,就会继续拥护政府;而如果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好,无效能,低效率,则人民会感到不满意,甚至感到失望。公共资源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无限的,往往是稀缺的有限资源。公共权力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利用和消耗公共资源,如果政府的工作无效能、低效率,就会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最终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受损。人民满意,意味着人民同意政府以其当下的方式利用和消耗公共资源,这只有在政府对公共权力的使用具有效能和效率从而能最大限度地为人民谋利益的情况下才可能;人民不满意,意味着人民不同意政府以其当下的方式利用和消耗公共资源,而这往往发生在政府对公共权力的使用无效能、低效率从而使得人民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
由此可知,在中国语境中,同意观念通过“人民满意不满意”这一表达,不仅某种程度上曲折地复现了西方政治学传统中曾经最为关注的政府之赋权问题,而且给予经赋权后的政府工作的评价以十分深刻、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中国语境中的另一种说法“人民答应不答应”,则更为直接地显示出同意不同意的意味,因为“答应”通常等同于“认可”(也有时用“人民认可不认可”这样的表达),而“认可”则是同意概念的传统涵义之一。克雷尼格所界定的同意概念,在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认可”。例如,他对父母同意子女之婚姻的说明中,父母的这种同意就是认可的意思。[2]如果关于“人民满意不满意”的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人民答应不答应”或“人民认可不认可”的同意蕴含就更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对同意观念的中国式表达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在当代中国社会,蕴含同意的“人民满意不满意”这样的标准,与西方政治学界传统上主要将同意理论用于证成公民政治义务的取向无关。这样,就避开了西方政治学家用以解释公民政治义务的明示同意、默示同意概念所遭遇的种种麻烦。此外,虽然“人民满意不满意”标准也涉及人民授权问题,但“人民满意不满意”是对现实状况的描述,而不是一种理论的虚构,无需原初状态中的假设协议或假设同意,无需根据虚构的社会契约的预设,从而与西方政治领域的类似思想相比较似乎更具有合理性、现实性。
当代中国在同意问题上的不足,主要不在于没有相似的、相关的、相近的或完全一致的同意观念。因为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当代中国社会,同意观念至少找到了某些适应本土语境的表达方式,同意概念所内含的某些要求也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以富有特色的语言呈现出来。这里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反映同意观念、同意概念内含要求的制度建设问题。例如,人民代表制度从理论上看、从理念上分析,应该是一种符合人民同意之要求的很好的制度;如果人民代表真能代表人民说话,真能体现人民意志,那么,人民代表所行使的表决权,就能充分表达人民同意还是不同意的真实意志状态。然而,尽管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种根本制度形式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但在这种制度的运行中却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并非全部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人,有些所谓“人民代表”利用这样的头衔或利用人民赋予的代表权谋私利。我们知道,在当代中国社会,表达人民同意的最重要的场合或最有影响、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就是人民代表大会,而人民代表的表决权是人民主权的实际运用。因此,如果人民代表不能代表人民,那么,理论上不错、理念上先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会因这些不能代表人民的代表们的存在及其作用而不能产生应有的结果。作为一种根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符合人民同意的理念,符合同意观念的内含要求,这里的问题不是根本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根本制度在运行中所需要的某些具体制度的不足或缺失导致的。例如,人民代表的产生制度是否可以进一步改进,以提高所产生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的概率和可能性?是否需要有专门的人民代表问责制度,对人民代表给予必要的制度性约束?人民代表名额的分布是否合理,是否能平等地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给予充分关注并有效解决的具体制度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不会对作为根本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带来任何损害,反而更有利于人民代表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因为解决这些具体制度方面的问题,有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人民同意的要求、人民主权的观念落到实处,从而成为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制度。而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治制度,人民一定会由衷地赞成、认可、拥护,即,人民一定会同意。
注释:
①该词条以前通过谷歌从网上获取,但现在谷歌暂不可用,故只能利用原来保存的PDF文档,无法提供来源网址。
②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施事行为是通过一定的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通过协定的步骤与协定的力而取得效果,所以施事行为是协定的(eonventional);而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取效行为取决于境况,取效行为不一定通过话语就能取得,所以,取效行为不是协定的,它包括意图或者非意图,常常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往往是在特定情况下的特定话语所引起的。参见王正元:《间接言语行为取效》,《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年第3期。
[1] 毛兴贵.同意、政治合法性与政治义务[J]. 哲学动态,2009,(8).
[2] John Kleinig. The Ethics of Consent[J].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Supplementary Volume VIII), 1982.
[3] Simmons A J. Moral Principles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s[M].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4] Weale A. Consent[J]. Political Studies, 1978,(26).
[5] 洛克. 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 Edward A. Harris. From Social Contract to Hypothetical Agreement: Consent and the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J]. Columbia Law Review, 1992,92(3): 651-683.
[7] Cassinelli C W.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J].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1959,12(2): 391-409.
[8] Simmons A T. Tacit Consent and Political Obligation[J].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976,5(3): 274-291.
[9] 休谟. 休谟政治论文选[M]. 张若衡,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10] Ronald Dworkin. Law’s Empir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11] Hanna Pitkin. Obligation and Consent-1[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65,59(4): 990-999.
[12] Arthur Kuflik. Hypothetical Consent[A]. Frankling Mill, Alan Wertheimer. The Ethics of Consent[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3] John Rawls. The Justifica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A]. Hugo A. Bedau ed., Civil Disobedience:Theory and Practice[C].1969.
[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114 (1971)[A]. Civil Disobed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C].1969.
[15] Edward A. Harris. From Social Contract to Hypothetical Agreement:Consent and the Obligation to Obey the Law[J]. Columbia Law Review, 1992,92(3): 651-683.
[16] 郭为桂.人民同意:现代政治正当性的道德基石[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