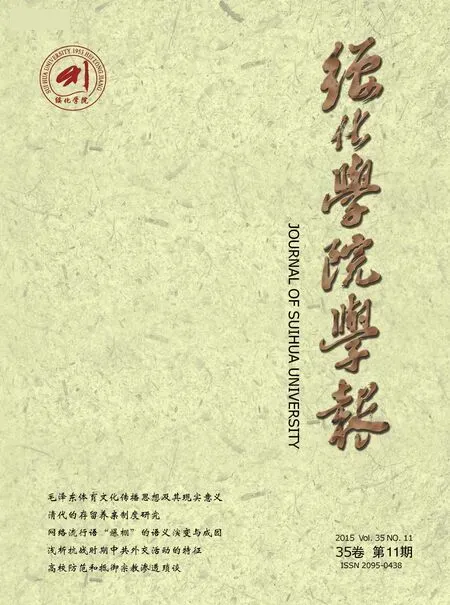原汁原味“说”故事
——读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
白雪(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00)
原汁原味“说”故事
——读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
白雪
(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黑龙江绥化 152000)
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作为述史文学的又一部力作,平淡一“说”是其重要的叙事特征。“说”本身不着任何色彩,内化于故事;“说”是作者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淌;无有拘束、说得随意,便是姜老本色无华、疏放自然的内心格调的写照。
姜淑梅;说;故事
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是继《乱时候,穷时候》之后的又一部原生态作品,一“苦”一“甘”道尽人生心酸,一“花”一“芽”述尽人生百态。姜淑梅老人的作品与其说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从心里淌出来的,虔敬质朴的情感,强悍无华的生命力,平淡一“说”间喷薄而出,感悦人心,无可以数。
一
姜淑梅老人用地地道道的一方语言讲说她的人生故事,这语言精准、平实、简单、真切,虽说是语言,其实就是故事,说了就是说了,读了就是读了,除了故事似乎不着一点痕迹,这便是姜老“说”故事最大的魅力。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说,真正的语言让你感受不到语言及语法的存在,“语言越是生动,我们就越不能意识到语言。这样从语言的自我遗忘性中引出的结论就是,语言的实际存在就在它所说的东西里面。”[1]当我们听到语言时,会立刻接受它所说的内容,并参与到这一内容中去。语言必然要指向它为之表现的世界,即指向它自身,这是语言存在的辩证法。语言消失在所说的故事中,语言与意义同在。姜老正是用这样的语言明证故事本身的价值,从老家女人到老家男人,从百时屯到东北,从爱莲、小妹、三嫂子到我爹、家族长、四大爷,从打架、感会到小时候咋玩,从逃荒、盖房到忆苦思甜会,这一切的一切,激荡心神的不再是语言的力量,而是故事的力量。语言在此消失,正是故事与意义复活的开始,也是姜老无意而得的艺术的境界。
整部作品说了61则故事,61种人生,女人的隐忍,男人的顽强,老人与孩子的坚韧与脆弱,生存的不易,生命的无常,生活的乐观,无不力透纸背。这些故事与其说是故事,不如说是时间让历史与我们拉开了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背后,是一种永远也讲说不完的生命的轮回。战争、贫穷、疾病、生存与死亡,爱与恨、奋斗与挣扎,人性的光辉与暗淡,一切都真实得可触可碰。故事中赤裸的情感犹如面对面的宣泄,偶尔使人猝不及防,偶尔使人心神激荡,偶尔使人涕笑无由。然而,作者姜淑梅在此却异常平静,平静得像上帝观看他的臣民,了然一说在此成了唯一的解释。介于高度的放纵与高度的控制之间,这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姜老的情感在故事中得到无限放纵,在讲说中却平静内敛、控制得体,这收放自如的叙说增强了作品理解的弹性,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参与创作的空间,更彰显出姜老无有修饰、本色无华、疏放自然的内心格调。
历史不都是故事,但故事已成为历史,说出那段历史是姜老的夙愿,她认认真真地说着说着,我们认认真真地听着听着,语言于此不再重要,佛陀拈花一笑的禅意我们可与姜老心领神会了。
二
姜淑梅老人没上过几天学,没读过几本书,没有经过正规的语言训练,她的语言不是来自于外在的世界,而是内心世界自然而然的书写,来自对遥远过去的回忆。
柏拉图说“理想国”中的哲学家是能回忆起真实世界的第一等人,也就是说能回忆起真实世界进行“灵魂转向”的人是第一等人,是哲学家。[2]可见,回忆如此重要,回忆不仅能让人反思、沉淀,回忆还能让人警醒——过去与现实之间到底哪个更为真实。作家的创作无非就是回忆的梳理,《苦菜花,甘蔗芽》正是姜淑梅老人的回忆录。作品中老人津津有味地讲说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儿时的贫穷、战争;青年时期的奋斗、拼搏;老年的安稳、享乐;百时屯的记忆与逃荒东北的辗转流离。这些故事,广大无边,却细致有味,一个一个读来,就像走在一条通往记忆深处的小路,却突见人生百态,不禁驻足观望,留恋凄惶。姜老回忆的魅力不只是故事多样、情节周详,更重要的是故事具有历史真实与情感真实的双重性。历史的真实使作品蕴藉厚重,情感的真实不仅使作品感人至深,还会发人深省。历史、现实、人生;生命、存在、意义,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没有沉淀就没有提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姜老的叙说勾连着一个沉重而永恒的话题:有限与无限,时间与空间,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和谐与悖论。回忆不都是美好的,但回忆可以成为艺术,回忆如果超越一段回忆,这便是人性由于匮乏而始终不渝追寻的补偿。
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给我们最直接的启示就是,艺术的味道最该源于平静的回忆。姜老作品的语言解读的正是这样的艺术情怀。她的“说”淡到让人无法描述,无法渲染,甚至无法体会。
那年,来云他娘十八岁,大辫子过腿弯。听说爹让人弄死了,她把大辫子往头上缠了几道,骑着马就去了东里湖,给爹报仇。(《女老缺》)
这三个闺女都是大个,模样也好,不少媒人来说媒。不管啥样的人家,老杨头都横挑鼻子竖挑眼,不同意。(《赔钱货》)
再往外送,俺刚进门,那家狗就咬,俺跑它就追,追了老远,把俺吓哭,哭着回家了。剩下的苹果是二哥送出去的。(《吃苹果》)
深远的回忆使语言无色可着,剩下的只是纯粹的生活原型。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提醒我们注意“原型”在艺术作品中的创生作用,[3]而我们似乎在姜老的作品中已经感受到了这一神秘理论的现实版本。因为原型最伟大的艺术力量就是喷薄而出的生命力,虽然姜老作品中“原型”并非是荣格直指的“原型”,但《苦菜花,甘蔗芽》力透纸背的就是这种种生活原型中震撼人心的生命之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对生命的捍卫,对生活的探求,对理想的追寻,无不彰显着人性的强悍与坚韧,这不是看得见的那段历史可以完全书写的,我们说姜老的故事呈现那段历史,更呈现那段历史之外的远自洪荒而来的人性自身的一切冲动。
回忆的力量超越了自我,更超越了有限语言的意义世界,在“住”与“不住”,“说”与“不说”之间,故事绵长而深远的力量将直击未来的精神世界。
三
姜淑梅老人的《苦菜花,甘蔗芽》叙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语言在此虽不重要,但“说”却成了故事衍生的重要动作。没有说,便没有作品,虽然我们很难感受到姜老在作品中的情感倾向,这源于她几十年的沉淀与洒脱,但她平静的叙说却是一种的无形力量,一直牵引着我们于故事中行走。
在语言与事物和思想之间,语言的局促不安与捉襟见肘是早就被古人说破点明的,姜老似乎对此深有感悟,她不着力于语言的运用,而只是在一说中巧妙地开发原生态的故事情节。淡化语言色彩而来说故事凸显了“说”的重要意义。平心而论,说故事正是姜老本色人生的最恰切的表达方式,如果“说”被看成是一种技巧的运用,那么这也是无技之技的表达。庄子深谙此道,他的庖丁解牛,佝偻承蜩的故事都在寓言着这样一种思想,所谓真正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没有技巧就是外在的技巧转化为一种内在心智的能力,不以“目视”而以“神遇”,才能“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庄子·养生主》),看似无技实则大技。由外向内的这种转化正是姜淑梅老人一“说”中所呈现出的无上智慧:水流九曲,花开四季,来兮来兮,归去归去。
姜老人生经历坎坷丰富,心理沉淀厚重大气,性情安稳禅静,心态开放洒脱,这弥足珍贵的个性气质造就了作品真实、简单、纯粹、自然的艺术风格。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的构思说,正是对创作主体进行艺术构思时的心理要求,也是对创作主体日常个性修养的要求。动静的辩证关系在这里十分紧要,极静才能极动。姜老的人生修养直接地气,平实厚朴,纯净少欲,“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庄子·大宗师》)其嗜欲浅者,其天机深,天机深的人方能于极静中极动,艺术的创作体现的正是这样的游戏规则。姜老平静的叙说,不是有意为之的技巧,而是自性流淌的写作,她的故事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体,似乎不受作者的制约,大有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自然悠闲之境。无有拘束,说得随意、听得自然,便是姜老作品的最好写照。
佛家讲最上乘的智慧是般若菠萝蜜,即关照自性。写作也是关照的一种,关照内心最真实的涌动,并将其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这就是艺术。
结语
姜淑梅老人是一位历经沧桑、阅人无数的讲说者,她的讲说没有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没有不期而至、突如其来的灵感,她娓娓道来,原汁原味地说着自己内心的故事。沉淀的经历,平淡的心境,超然物外的洒脱,造就了这样平静、亲切、温暖、柔和的叙说风格,我们听闻故事,听的就是这样一份真意。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朱立元,张德兴,等.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206.2
A
2095-0438(2015)11-0045-02
2015-06-30
白雪(1973-),女,蒙古族,辽宁铁岭人,绥化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文艺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学视域下的民间述史研究”(14YJA7510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