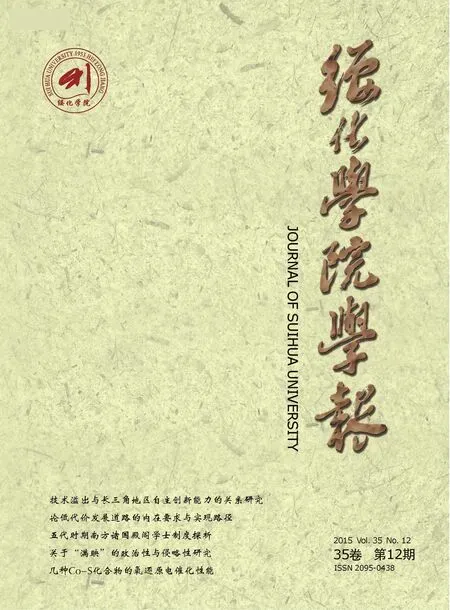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想……》中的时间话语对讽刺意向的表征
蓝庆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想……》中的时间话语对讽刺意向的表征
蓝庆
(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无锡 214122)
《想……》中的科学家拉尔夫崇尚“科学主义”,认为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只有科学知识才能解决困扰学术界已久的“意识问题”。洛奇对此进行了讽刺,并将这一讽刺意向渗透到故事的时间话语中,通过对时序、时距、频率的调整,使时间话语为小说的讽刺主题服务。而利用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分析《想……》中的时间话语特点,能清楚地阐释洛奇派生到时间话语中的讽刺意向。
《想……》;时间话语;意向性理论;讽刺意向
一、引言
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戴维·洛奇对小说的时间话语颇为关注。在理论层面,洛奇对小说的时间话语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他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分多个章节,结合具体例子,就小说中的时序、时距、频率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洛奇认为,时间的转换造成的空白可以刺激读者的阅读欲,让读者自己“领悟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讽刺意义”[1](P85);时间跨度则会影响叙事节奏与主题表达;而在频率方面,洛奇着重论述了重复的多种表达效果。在小说创作层面,洛奇践行了他的时间话语理论观点,他对小说时间话语的处理往往谨慎用心,使时间话语在最大程度上为小说主题服务,《想……》(2001)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想……》的背景设置在虚构的格洛斯特大学(UniversityofGloucester)。该校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拉尔夫与新来的文学课代课教师海伦在一次聚会上相遇。二人因对人类“意识问题”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吸引,并在交往过程中对意识研究问题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探讨。故事中的拉尔夫傲慢自大,是现实中科学家的一个缩影,他拥护“科学主义”(scientism),坚信“只有自然科学是权威的知识,凌驾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知识之上”[2](P181),当今学术界面临的意识难题也只能靠科学知识才能解决。洛奇让《想……》延续了学院小说“一脉相承的讽刺模式”[3](P109),对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进行了讽刺。而故事的时间话语对这一讽刺意向的表征起到了关键作用,洛奇有意将这种讽刺意向渗透到故事的时间话语中,通过对时序、时距、频率的调整,使时间话语为小说的讽刺主题服务。本文将结合约翰·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分析《想……》中的时间话语特点,探究时间话语在讽刺意向的表征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约翰·塞尔的意向性与小说的时间话语
约翰·塞尔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灵哲学家之一,他将人类的言语行为归结为心灵意向的派生形式,并系统地阐释了心灵的意向性与言语行为之间的内在关系。他在《意向性——论心灵哲学》一书中解释了意向性的含义:“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direct at)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4](P1)心灵所具有的这种“指向、关于、涉及”的特征就是意向性,比如信念、害怕、希望等心理状态都是意向性的。塞尔进一步指出,哲学中的意向性实际上就相当于认知科学中被称为“信息”的东西。[5](P145)通过意向性的这种关涉能力,心灵才得以与外界发生联系、交流。意向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思考某事时头脑中所具有的初源的意向性或内在的意向性(original intentionality),属于心理状态。另一类是人们将自己的想法写在纸上时,纸上的文字符号所具有的衍生的意向性或派生的意向性(derived intentionality)。[5](P25)换言之,语言符号是属于物理层面的,并非本质上就是意向性的,这种言说出来的意向性实际上是派生出来的。[4](P26)因此,话语的意义是由初源的意向决定的。说话人思想的初源的或内在的意向被转化成语词、语句、符号等,并被有意义地表达出来,它们便具有了从说话人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而语言就是表征意义的媒介,是初源意向的寄生场所。
小说的时间话语就是小说家独有的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常规的文字符号,而是一套系统的叙事规则。小说家对这套规则的操作行为类似于人们对常规语言的使用。因此,小说家对时间话语的运用是一种特殊、抽象的言语行为,必然会表现出小说家某种相应的意向状态。小说家可以通过不同形式的时间话语来传达不同的内在意向,表征不同的意义。通常这种意义意向有两层结构,一层是表征意向(theintention torepresent),另一层是交流意向(the intention to communicate)。小说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对小说的内容进行表征,而且要实现一种交流意向,即希望这种表征能被读者识别出来并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完成向读者表征小说主题意义的意向。具体而言,小说里发生的故事被假设为具有自身的时间(自然时间),事件的序列按照自然时间先后发生、发展。[6](P113)但是,小说家通常打破自然时间的常规,通过时序、时距、频率等话语技巧对时间进行调整。时间话语的重组、调整实际上衍生于小说家的初源意向,即在叙述故事内容的同时,能清楚地表征小说的主题意义,实现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意向。
三、《想……》中的时间话语意向
小说的故事时间遵守不可逆的自然时间规律,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依次进行,而在《想……》中,洛奇有意打破了时间的线性特征,通过倒叙、重复、停顿等技巧对时间进行了有意的操作。正如他本人谈及《想……》时所说:“如果你想写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你必须要提示你的读者你在操作某种规则。”[7](P296)洛奇通过对时间话语的操控,充分表征了他对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的讽刺意向。
(一)时间倒错。小说中的时间倒错是指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这“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8](P17)。倒叙常常引起故事时间的“错位”。热奈特明确指出:“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8](P17)事件发生的时间先于叙述事件的时间,叙事者站在“现在”的角度对过去的事件进行追忆。倒叙的目的在于解答读者脑中对在时间间隙发生了什么的所有疑问,对不完整的故事情节进行补充说明,揭示事物因果关系,表明作者的态度。[9](P119)
《想……》共34章,海伦的日记内容占12章,拉尔夫的录音内容占9章。需要指出的是,拉尔夫的录音内容也是对所见所闻的记录,可以看作是一种“录音日记”,这让小说的时序方面有了一些日记体小说的特征。日记是对现在正在发生或者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转述。因此,人物心理活动的内容必然会让现在时和过去时不断交叉、重叠,造成时间上的“错位”现象,而这种“错位”会刺激读者的意识,增强小说主题意义的表达效果。小说的第十一章是拉尔夫的“录音日记”。通过前几章,读者已经了解到拉尔夫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认知中心,借助办公室的电脑秘密录下自己的思维活动,作为自己研究“意识问题”的材料,但近来拉尔夫新买的录音设备让他可以不用受制于电脑,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录音。“现在是三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五点半……我现在正在录音,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更准确地说被堵在路上……再也不用为了继续这个实验而在星期天早上跑到认知中心去录音了……那绝不再是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了(现在时),因为我上个星期天正要从那里回家的时候碰见了道格斯(过去时)……”[10](P113)拉尔夫先描述了当下自己正在经历的事件,继而便转向了对偶遇道格斯一事的追忆,将故事时间一下拉到“上个星期天(三月五日)”,接着录音就进入了“过去时”的倒叙。通过这段回忆,我们得知道格斯和拉尔夫在中心门口相遇时,道格斯态度十分冷淡。由于这种“冷淡”,拉尔夫的思绪陷入了更久之前与道格斯第一次见面时的回忆:道格斯本是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他的学术成就比拉尔夫高,他的研究项目比拉尔夫的更具创新性,多年来一直埋头苦干,连星期天也不肯休息,只因欠缺领导才能才输给了拉尔夫。尽管道格斯不太友善,但在拉尔夫心中,他确实是一个兢兢业业,沉醉于学术研究的科学家。与自己满脑子的男女之情相比,拉尔夫不禁有点自惭形秽,他感叹,像道格斯这样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脑子里只会想着他的科学,科学就是他的生命,就是他的呼吸,他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分散自己对科学的注意力。”[10](P115)拉尔夫觉得要是让道格斯录下自己的意识活动,内容肯定都与科学研究相关。
拉尔夫通过对往事的追忆,向读者传达了他眼中真正的科学家道格斯的形象。而在故事的最后,道格斯的真正面目才浮出水面:他的脑子里装的并不都是和科学有关的事情,他的思想内容比拉尔夫所想的要肮脏得多,他甚至是色情狂魔,通过学校的网站下载了大量的儿童不雅照。回忆里的道格斯和现实中的道格斯相差甚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是对拉尔夫自己的一种讽刺。拉尔夫这位自负的科学家,曾想发明一种可以植入人体的微型电脑,来了解被植入者身体里的一切信息,包括思想。然而,他最终也没能像他所期望的那样能够看穿人心,就连自己同事的真面目都无法识破。这是对“科学主义者”狂妄自大的讽刺,同时也向我们暗示,意识具有不可忽视的人文主义特征,光靠科学知识恐怕无法解开意识的奥秘。
(二)重复叙述。申丹对重复叙述的定义较为简洁,即“讲述数次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6](P124)。希利斯·弥勒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着重探讨了小说的意义是怎样从“重复发生作用的某些方式”[11](P3)中推衍出来的,他指出:“无论什么样的读者,他们对小说那样的大部头作品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得通过这一途径来实现:识别作品中那些重复出现的现象,并进而理解由这些现象衍生的意义。”[11](P1)
《想……》中一共出现了三个叙事者,海伦、拉尔夫以及第三人称叙事者。叙事者的不同引起叙事角度的切换,使得小说中出现了不同叙事者在重复叙述同一事件的现象。在第三章,第三人称叙事者讲述了海伦和拉尔夫第一次在职工大楼相遇时的场景:
“……午饭时间,拉尔夫·麦信哲和海伦·里德在职工大楼巧遇。海伦在大厅里欣赏一个当地画家展出的画作。拉尔夫通过旋转门进来时看见了她,就走到她的背后。‘觉得这些画怎么样?’他把头凑到她的肩膀说道,吓了她一大跳。
‘哦!你好……我在想,如果他们很便宜,我会买一幅来装饰我的客厅。’”[10](P32)
从这里看,这段巧遇似乎非常地真实、浪漫。通过海伦被吓了一大跳时断断续续的语言和手足无措的样子,读者似乎能体会到她偶遇拉尔夫时又惊又喜的心情。随后,拉尔夫在自己的录音中也提到了这段巧遇,丝毫没有发现其中的掺假成分。最后,海伦在日记里坦白了自己对这场“巧遇”的策划:“昨天中午,我在职工大厅里碰见了拉尔夫·麦信哲。好吧,老实说(为什么不说实话呢?这日记只有我自己可以看见),我从卫生间出来时,透过玻璃窗看见他沿着楼梯走进来,于是我有意在大厅里的一些丑陋的图画又或者说是图画展览前徘徊,希望他走进来时能够看见我——结果他真的看见我了,然后我们一起共进午餐。”[10](P61)海伦的日记让读者恍然大悟:站在大厅里的她透过玻璃窗早就看见了正要走进来的拉尔夫,并故意站在显眼的地方等着拉尔夫来打招呼,制造出巧遇的假象,可见拉尔夫心中这场美丽的巧遇实际上只是海伦的一个小计谋。在第三十章,故事接近尾声,海伦和拉尔夫再次在职工大楼就餐,海伦把那次巧遇的实情告诉了拉尔夫,“我向他袒露实情的时候他微微一笑,似乎有点恼怒。”[10](P303)显然,真相让这位傲慢的科学家有种受辱的感觉,他的科学知识根本无法识破人类的谎言,轻而易举地便被一个女人使了花招。这一事件的四次重述,一方面让读者有机会进入不同人物的内心,对事件进行全面了解,另一方面,不同角度的叙事“画面”形成鲜明对比,假象与真相的强烈反差恰恰增强了小说的讽刺意义。
(三)嵌入式的停顿。停顿是指当故事外的叙述者为了向读者提供某些信息,对某个对象进行描述而造成故事时间停滞不前的情况。[6](P123)《想……》中的停顿是通过嵌入学生的戏仿作文来实现的。戏仿(parody)是后现代派小说的常用手法之一,“它突出被戏仿对象的弱点,具有破坏性,是一种意图明显、分析清楚的文学手法。被戏仿对象的范围很广,既可以是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一种创作手法等,也可以是作家的立场、观点。”[12](P297)通过戏仿,作者在事物原型的基础上对被戏仿对象的某些特征进行放大、扭曲,使之显得滑稽可笑,从而达到讽刺、批判的目的。海伦学生的戏仿作文虽然引起了情节的停滞,但是这种停滞反而促进了主题意义的升华。洛奇借助戏仿手法向读者展示了“意识问题”的争论焦点,再一次对傲慢的科学界进行了讽刺。
《想……》中的两次长时间停顿分别出现在第八章和第十六章。其中,第十六章展示了三篇学生作文,是对脑神经科学家弗兰克·杰克逊提出的一个思想实验的戏仿。杰克逊设想了这样一个实验:神经生物学家玛丽从小到大被囚禁在一个完全黑白的环境中,从未见过除了黑色、白色以及灰色以外的任何颜色,但她掌握了关于人类颜色认知机制的所有知识以及所有的光学知识。这意味着玛丽即使没见过真正的色彩也能对每一种颜色给出功能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说明。问题是当她有一天真正看到一种真实的颜色如红色时,她是否能获得一种新的体验?这一实验争论的焦点在于,感受性质问题是否真的存在。如果玛丽获得了新的体验,那么说明玛丽得到的关于颜色的物理知识是不完全的,遗漏了诸如“看到红色时所体验到的主观的质的经验”[13](P82),即感受性质(qualia)。
三篇戏仿作文均以滑稽的结尾告终。第一篇《玛丽走出来了》中的玛丽走出黑白房间,第一次看到鲜红的玫瑰后,“她那脆弱的心因无法承受视觉上的强大刺激而停止了跳动。”[10](P157)第二篇《玛丽的玫瑰》中,玛丽第一次看见真实的玫瑰后激动不已,她对焦急等待实验结果的科学家们说,“我不在乎它是什么颜色”,并以捷尔特茹德·斯坦因的一句诗结尾:“玫瑰之所以为玫瑰,正因为它是玫瑰。”[10](P161)这两个滑稽的结局与严肃的科学实验形成对比,似乎是对科学家们的一种调侃。而第三篇《玛丽看到了红色》的结局还在这种调侃中添加了伦理层面的批判。玛丽一直生活在与色彩隔绝的世界里,但让科学家们没想到的是,女性的生理周期早就让她体验到了红色的视觉经验,这显然是对科学家自以为是、忽略常识的嘲讽。而且,这一实验也显现出认知科学家们的冷酷无情,他们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就残忍地囚禁他人,应该受到道德上的谴责。洛奇使用三种不同结局,将矛头一起指向以拉尔夫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批判了认知科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荒谬的一面。[14](P45)
四、结语
在《想……》中,拉尔夫的形象影射出了现实中那些“科学主义者”的狂妄自大。洛奇将对“科学主义”的讽刺意向派生到时间话语层面,通过对时间话语的有意重组、调整,有力地表征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在故事的最后,洛奇通过情节的安排,使拉尔夫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谦卑,这或许也表达了洛奇对科学界的美好期许:“最优秀的科学家事实上也总是对人文学科有浓厚的兴趣。”[3](P108)自然科学家应该放下傲慢的姿态,与人文科学家携手并进,共同解决意识难题。
[1]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2]Barnett,S.Anthony.The Pale Cast of Thought:An Essay ReviewofThinks...byDavid Lodge[J].InterdisciplinaryScience Reviews,2003(3).
[3]罗贻荣.戴维·洛奇访谈录[J].外国文学,2009(6).
[4]约翰·塞尔.意向性——论心灵哲学[M].刘叶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5]约翰·塞尔.心灵导论[M].徐英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7]Lodge,David.Consciousnessand theNovel[M].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2.
[8]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9]刘巍,吕明臣.从“郑伯克段于鄢”看《左传》的叙事时间[J].湖北社会科学,2013(4).
[10]Lodge,David.Thinks… [M].New York:Viking Penguin, 2001.
[11]J.希利斯·米勒.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M].王宏图,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12]杨仁敬等.美国后现代派小说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4.
[13]高新民.人心与人生——广义心灵哲学论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4]董燕萍.与“两种文化”的对话——谈戴维·洛奇的小说《想》[J].外国文学评论,2004(1).
[责任编辑 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5)12-0053-04
2015-07-31
蓝庆(1989-),畲族,浙江丽水人,江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