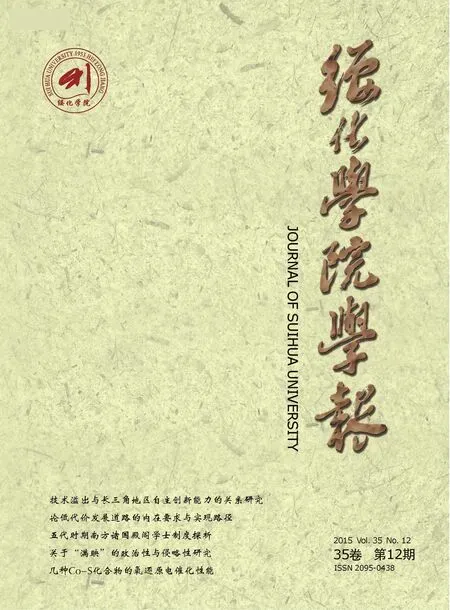《第七天》:现实背后的关于底层国民宿命的透视
沈文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第七天》:现实背后的关于底层国民宿命的透视
沈文平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重庆 401331)
《第七天》是当代著名作家余华于201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作者用犀利直白荒诞的语言将残酷的现实勾勒出来,但小说当中塑造的众多底层国民的悲剧形象,承载着更为复杂深厚的情感,作者借底层国民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于人命运地深切思考和终极关怀。
余华;第七天;国民宿命;叙述距离;透视
同《兄弟》出版初期一样,他的新作《第七天》在出版之后,招来各路人士地积极讨伐,但毋庸置疑,余华作为当今为数不多的具有鲁迅气质的作家,其新作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让人再次体验到了类似当初《兄弟》出版时引起的文坛盛况。
就目前批评界的主流来看,众多的批评者将目光停留在《第七天》的文学趣味上,用目前较为广泛流行的说法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余华的新作是新闻串烧或微博杂烩,文学趣味极淡。但无论哪一种说法,我认为这都是对余华创作的极大中伤。作为余华七年磨一剑的力作,《第七天》用直抵现实的荒诞笔法,将阴间与阳间并置对比,并以一个亡灵视角反观现世,将残酷冷漠的现实境况一针见血般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背后,隐含了作家对国民命运深层次的透视和关怀。
一、叙述距离的无限抵近
对于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汪晖在其名噪一时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中做了较为恰当地论述,他在书中的序言中写到,“我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从而也是反思性文化和民间文化边缘化的时代。”[1](P43)我认为汪晖的这种说法,无疑是对当今整个文化界的恰当概括,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大多数学者和作家已经成为学院制的牺牲品,作为当今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往往都走向了与鲁迅时代众多具有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相反的道路。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秉持一个具有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姿态,他们的方式和行为,逐渐造成了当代人文精神的失落。缺乏批判的勇气是当今文化界的通病,尽管在当今,没有人会否认现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也日渐有人发现,新的社会关系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干预和限制人的生活,这种干预和限制的方式经常像是非社会事件,以至任何一个对其合法性进行质疑的人都被视为没有理性的人。然而,《第七天》的出版发行让我看到,余华就是这样一个没有“理性”的人。在视非现实主义为原罪的当代中国文学,余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与现实进行了对话。而这种特殊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他在新作当中的叙述距离,而这种叙述距离在这里则具体理解和展现为作品本身与现实的互动关系。
余华本人在答《京华时报》记者问时说出了他的叙述距离:“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欲望,将我们生活中看似荒诞其实真实的故事集中写出来,让一位刚刚死去的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让现实世界像倒影一样出现。”[2]在这里,余华间接地向人们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即试图同时塑造死者世界与现实世界,并通过死者来描写现实世界,用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展现现实社会的残酷和荒寒。他还说:“在《第七天》里,用一个死者世界的角度来描写现实世界,这是我的叙述距离。《第七天》是我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以后可能不会有这么近了,因为我觉得不会再找到这样既近又远的方式。”[2]很明显,余华在处理作品与现实关系时采用的既近又远的叙述距离存在其在叙事上的某种策略。就作品而言,在《第七天》中,余华在描写现实时,引用的事例很多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实,诸如小说当中的政府强拆的情节在现实社会当中就经常见到,这种直接从现实生活当中取材并直接让其作为小说情节进行书写的方式,稍显粗暴,但他给人带来的现实逼仄感却尤其强烈。这也是“近”距离带给我们的直接效果。而余华在展现现实的这种惨淡时,主要是将阴阳世界并置对比,并借亡灵的口吻将现实境况呈现出来,二者之间的强烈反差让人将现实世界看的更为彻底。而阴阳之间的频繁转换似乎又将叙述形式的粗暴弱化了,在这里这种弱化实际就可以理解为余华所说的叙述距离的“远”。总的而言,余华的这种处理现实与作品的方式,实际上饱含了作家关于现实的多重思考。余华通过叙述距离上的“近”“远”之间的并置交叉,实现了其直抵现实,揭露现实的目的。而这种叙述形式,除了直观揭露现实之外,带给我们的还有直抵心灵的震撼。鲁迅曾说:“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了”。[3](P457)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在表达自己的某种社会批判时往往会采取比较委婉的方式。这在鲁迅的很多文章当中可以看到,例如在《狂人日记》当中,鲁迅在表达自己对封建礼教的不满时巧借虚构的狂人之口,但故事情节的书写就显得更加隐晦含蓄了。与之不同,余华的《第七天》在情节地设置上,就显得直白粗暴,他直接将社会事件纳入到书写的范围而不予想象和虚构,他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表达了他与鲁迅同样的批判思想,但在叙述距离上,余华则显得更为极端。在媒体新闻发达的今天,余华以他独特的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真”的世界,他是让社会知道他在攻击而不惧。这在当今学术界文化界缺乏勇猛的批判的今天,显得极为珍贵,这完完全全就是以孤独者的身份去触碰和挑战这个社会的公,揭示出现实世界最惨痛的一面。
尽管他的叙述距离成为诸多批评家口诛笔伐的对象,但在我看来,他选择的与现实对话的方式在我看来也是值得一些批评家们反思的,如上文所说,他以一种极为贴近现实的方式处理了他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表达方式上存在着极大差异,这种体现在叙述距离上的直白赤裸既是当今的许多文人作家所不能拥有的,也常为众多的批评家所诟病。他们普遍认为,文学是人学。这点没错,站在文学自身角度来讲,中国文学一直都主张作家要宣扬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基于“人”这个点必须在很多方面都要呈现关注现实的一面,但在文本与现实间的关系处理上,方式无疑显得极为单一。就大多数文学作品而言,作家在处理作品和现实的关系时,惯用虚构的方式来拉开作品与现实的距离,情节的漫想虚构带给读者以意识感官上的疏离,这可以被认作是一种好的处理作家作品与现实的方式,但此种方式并不一定就存在其表达上的持续优越性,诚然,这是众多中外作家秉持已久也更为让读者接受的一条标准,余华的前期创作也基本是以虚构的方式来处理作品与现实的关系,这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已有众多成熟作品的作家来说,余华完全有能力凭借其深邃的思想和丰富的想象虚构继续创作一个更加符合他个人风格的故事来呈现现实的困境,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粗暴直白的方式,肯定是想要表达一种更为明显的东西,就如同他自己所说,他写的很多东西,已经不是新闻,其中很多被认为是新闻的东西早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这种直接地暴露和阐释给人直接强烈的冲击感,余华的这种以毫厘抵近现实的方式在当今中国的文学界可谓是鹤立鸡群,我认为这也是对他自己在叙述距离方面的尝试甚至超越。当你习以为常地认为文学在处理与现实之间关系时,应该采取更为向内的虚构的方式来表述的时候,对余华这种表达无疑会大肆抨击。但毫无疑问,他的尝试,在我看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哪怕这是一次在后来被视为莽撞的方式。但余华在叙述距离层面的探寻,我认为也是值得的。
二、残酷背后的宿命透视
凭借着无限抵近现实的叙述,余华的《第七天》向读者展现了一幅残酷冷漠荒诞的现实景观。小说以死者杨飞阴阳互换的视角,讲述了杨飞死后七日的见闻,余华利用虚构的两个世界的对比的方式,向世人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关心。余华的真实意图,乃是借死者杨飞来再现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而将现实社会中真实发生的新闻事件集中汇聚在一起,则在某种程度上将现实社会的荒诞感进一步增强了。《第七天》承袭了余华一以贯之的苦难意识和对小人物命运地关注和同情,而贯穿在其小说当中的温情叙事,也展现了余华对现实的尖锐批判立场。
米兰·昆德拉认为,写作就是写那些无人敢写之事,讲那些无人敢言之语,这,就意味着要反一般人之常态。余华以一腔澎湃热血,如此直白地记录这浮生乱象,不加隐晦地直指社会积弊,着实勇气可嘉。《第七天》当中对现实世界有这样的几段描述,“我意识到四周充满欢声笑语,他们都在快乐地吃着喝着,同时快乐地数落起那个离去世界里的毒大米、毒奶粉、毒馒头、假鸡蛋、皮革奶、石膏面条、化学火锅、大便臭豆腐、苏丹红、地沟油。”[4](P155)这样的一段描写,将现实世界存在的诸多问题具体地呈现出来。在谈到人们的生存境遇时,小说当中又有这样一段描述,“这里没有公安、消防、卫生、工商、税务这些部门,在那边开一家餐馆,消防会拖上你一两年,说你的餐馆有火灾隐患;卫生会拖上你一两年,说你卫生条件不合格。你只有给他们送钱送礼了,他们才允许你开业。”[4](P157)试想,这不正是发生在身边赤裸裸的事实吗?这种描写,就犹如明镜一般将险恶的现实困境倒影出来一般。并且这种书写在小说当中俯首皆是,比如作品中还记叙了一位老太太流着眼泪说她只是出门去买菜,回家后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他还以为走错了地方。还谈到了另外一些人遭遇深夜强拆的恐怖,他们在睡梦中被阵阵巨响惊醒,房屋摇晃不止,仓皇逃出来时才看到推土机和挖掘机正在摧毁他们的家园。《第七天》当中的这一系列地描述,让人清醒地意识到这才是我们真实生活着的世界。不仅是余华的《第七天》,他的众多小说,比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乃至《兄弟》都描绘了底层人民的悲苦与艰难,从《活着》当中的福贵到《兄弟》当中的李光,再到当今的杨飞,鼠妹以至于伍超,他们都是社会底层人民的代表,却总是遭受命运世事的作弄,无不让人对底层民众的命运感到悲哀。古有苛政猛于虎,近代有白毛女,再到今天被政府强拆暴打的民众,如此等等,底层民众的悲剧从古到今从未消失。
从造物主开始创造出人以来,一些文化名人就一直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人人生而平等”,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当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除此之外,美国的独立宣言当中也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包括我们国家同样宣扬民主,人权无国界,这种平等的权利只要是这个世界的子民,都应该享有。其实不然,这种说法从它被提出的那一天就是一个伪命题,是统治者,政治家,上层社会人士用来愚弄大众和统治下层人民的工具。真实情况是,处在社会上层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占有和享受着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而处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则不断地遭受来自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的压迫和剥削,始终享受不到作为人而本该享有的平等的权利。余华的小说正是发觉到了这种虚伪地宣扬,故而以解剖的方式逼近现实,审视现实,反思现实。向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社会存在。对此,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则认为今天中国的现实并不是中国作家能够击穿的,但是中国有一批作家尽管他们对现实表现不是那么尽如人意,但是他们有一份对现实顽强不屈的责任。余华作为这批作家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文化人,凭着巨大的勇气将矛头指向了当今的政府,指出了一些相关部门滥用职权,强拆,瞒报、胡乱判案,余华用文学夸张的形式为世人展现了人们所生存的惨淡社会。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民众,凭借自己微薄的力量,是难以撼动这种不对等的格局的,否则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不会从古至今都存在,即使撼动了,也不过是位置置换而已,那种不平等的关系依旧存在,这不得不让我想到有关宿命论的问题。这种无法摆脱的宿命,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底层民众身上轮番上演着,并且,这种宿命时常在底层民众身上发生。
宿命论是指人生中早已注定的遭遇,包括生死祸福、贫富贵贱等,或者相信一切事情,都是由人无法控制的力量所促成的。相信宿命论的人认为人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是注定的,由上天,上帝或未知的力量预先安排,是人无法改变的。而结合小说,处于底层的社会民众,只要他是处在底层这样一个位置,他就必然要遭受社会的种种不公,无论压迫,冷漠,还是欺骗或虚伪,他们只要是处在那个位置,就必然无法逃脱这样的一种宿命安排。哪怕你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即便成了王,也只是让他人处在底层的位置,这种难以改变的宿命仍旧在蔓延和持续。具体到小说当中就是政府的强拆事件,小说中的老太太出门买菜回来后发现自己的房子没有了,作为平民的郑小敏的父母也在强拆中丧生,而与之相反的,是一些政府高官贪图享受,住五星级宾馆,与嫩模搞暧昧,死在床上还被冠以工作操劳过度突发心脏病去世的噱头。还有政府瞒报火灾的死亡人数,威胁一些死亡者家属,死者到死都没有受到公平的待遇,除此之外,故事中的李月珍也是蹊跷地死亡,据说与政府的暗箱操作有关。再者,鼠妹的男朋友伍超在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跳楼自杀之后,一直后悔,为了给鼠妹买上一块墓地,他卖了自己的一个肾,身体随之越来越差,最终死亡。小说中,几乎所有主人公,都以一种命中注定的方式走向死亡,他们或者不想,不愿,但却最终都奔上了黄泉路,是世人为鼠妹选自杀场地的冷漠,是医院将婴儿视为垃圾的无情,是政府为官员的死编造的工作操劳过度的虚伪,这是作为底层的他们所无法改变的,这就是宿命,难以抗拒和改变,是上天为他们注定的结局。
三、透视潜存的作家情怀
这种通过近距离展现社会现实,并透过残酷现实引发的作家对于宿命的透视,显示了余华作为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勇气和担当,他的这种叙述,犹如厉风迎面扑来,引人警醒。基于这种宿命地思考和透视,展现了余华对于国民命运的关怀。余华的意图也绝非向人们展示这样的一幅宿命图卷,更多的是向外界表达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旁观者”内心的不屈,他寄托的是宿命之上地不闻战叫。
就《第七天》而言,余华“写的”不是小说,倒是可以当做是现实社会的反光镜,而余华更像是一个意志清醒的持镜人,他立于尘世之外,冷眼注视观察着这个冰冷无情的世界。他将自己冷眼看到的事实一五一十、不加修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小说的书名“第七天”在我看来也隐含着作家的某种情感价值取向。根据小说的内容,作家从第一天一直写到第七天,既写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也在残酷当中夹着了绵绵温情,但无论是冷漠无情还是来自亲情的温存,都在小说的扉页得到了终结。余华在小说的扉页附上了《旧约·创世纪》当中的一句话:“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4]这句话在我看来是有明显的情感渗入的,“歇了他一切的工”实际上是作家在面对现实困境,面对底层人的悲剧宿命时,意图借这样的一句话表达作家希望这种困境得到改善或者终结。而在当今社会,当全球都采用一周七天的时间规则之下,再结合作品,我们很容易想到,七天之后便意味着苦难困境的终止,新世界的始端。而新的开始,毫无疑问也是余华作为当代知识分子对社会,对人民大众的一种人文关怀,是其博大情怀的展现。正如作家苏童在与王宏图的谈话当中所说:“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社会现实,在知识分子眼里永远是该受到批判的。只有这样才能构成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生存。”[5](P12)而这种批判,在深处无疑是作家情怀的聚焦和展现。当俗文学,俗文化在一点点蚕食仅有的反思文学、反思文化时,这种作家独有的情怀无疑更像是浊泥中的白莲,暗夜的星光,在混沌和黑暗中做着无声地抵抗。
[1]汪晖.反抗绝望[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于丽丽.余华《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N].北京:新京报·书评周刊,2013.
[3]鲁迅.鲁迅全集(16卷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余华.第七天(第一版)[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5]苏童,王宏图.苏童王宏图对话录(第一版)[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王占峰]
“The Seventh Days”:the Reality of the National Fate of the Bottom
Shen Wenping
(The College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
“The Seventh Day”was published in 2013,written by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Yu Hua. In the novel,the author sketched the reality with sharp straightforward absurd language,but many of the underlying national tragedy images in the novel carry more complex deep feeling.The author,through the tragic fate of the underlying national,expressed intellectuals’deep thinking and ultimate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bottom.
Yu Hua;seventh days;national fate;narrative distance;perspective
I206.7
A
2095-0438(2015)12-0045-04
2015-07-31
沈文平(1989-),男,江西抚州人,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