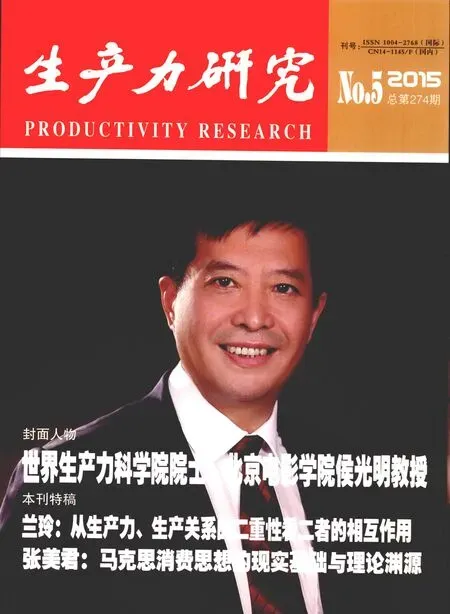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循环累积因果”效应研究
浮莉萍 ,王 超 ,李 琰
(1.兰州工业学院 会计金融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2.西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人力资本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决定因素,理论界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之间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Mincer(1957,1958)最先在人力资本的框架下研究了收入分配问题,提出并发展了收入分配的人力资本模型。Viaene和Zileha(2001)利用一个三阶段“世代交迭模型”(OLG)对人力资本与收入分配以及内生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Shankha和Mausumi(2003)研究了人力资本在收入差距的代际关联和持续性间题中所起的作用。Guvenen和 Kuruseu(2007a,2007b)分别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积累的世代交叠模型,并利用他们的模型很好地解释了1970—2000年间美国收入分配的演进。陈琳和袁志刚(2012)实证研究了中国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对中国代际收入传递具有重要作用。方亚(2012)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实证研究了收入与健康人力资本的关系,结果显示低收入人群因经济困难而被严重地限制了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本文正是在这些理论研究的框架下,分析我国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人力资本与收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探寻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后机理。
一、我国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
据统计,全国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国际上衡量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基尼系数 0.4,中国这一指标在 1991年是 0.282,2001年为 0.459,2008年达 0.470,2013年则上升到了0.473。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61(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①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报告》,http://www.chfsdata.org/data/2012-12.。这些数据都说明一个不争的事实: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都处在国际警戒线以上,并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除了基尼系数外,衡量收入分配的指标还有:库茨涅兹指数(下称:库氏指数)是以最富有的20%人口的收入比重表示;阿鲁瓦利亚指数(下称:阿鲁指数)是以最贫穷的40%人口的收入比重表示;绝对极比指最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最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根据王传仕的计算,中国城镇居民近几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 1985—2001年,基尼系数增加了57.14%,库茨涅兹指数增加了19.32%,同期的阿鲁瓦利亚指数降低了-23.99%,绝对极比增加了87.33%,两极分化情况很明显。②王传仕:《收入分配非均等性对经济与消费增长的制约关系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04)》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财富差距达到32倍。而根据2010年国际知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现在已有67万个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位列全球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这一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2%,报告指出0.4%的中国家庭已经占有70%的国民财富。③时学成、张彤玉:《我国高收入阶层的影响因素分析与对策》,学识探索,2011年第2期。这还没有包括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如果把这两项考虑在内的话收入差距会更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教授认为,考虑到灰色收入我国城镇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31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9倍。而全国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1倍。④王小鲁:《高低阶层居民收入差距达55倍 灰色收入是主因》,凤凰网财经,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00201/1780543.shtml.2010-02-01.这些数据都充分说明,我国高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巨大,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造成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但一个不可否定的事实是人力资本投资是我国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人力资本投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收入分配状况,人力资本投资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互为因果的累积效应:收入分配差距大——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不同——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这种累积效应会不断的极化收入分配,形成收入差距的“人力资本陷阱”,导致收入差距存在自我扩张的内在机制。
二、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效应分析
据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联合建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家庭中,健康状况良好的家庭年收入为46 636元,健康水平一般的家庭年收入为33 614元,健康水平较差的家庭年收入仅为16 996元,健康水平较好的家庭收入是健康状况较差家庭收入的2.7倍。户主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其以上的家庭平均收入为195 282/年,而户主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其以下的家庭平均收入仅30 415/年,本科学历家庭收入是小学学历家庭6.4倍。⑤《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http://www.chfsdata.org/data/.谢周亮(2010)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人教育年限增加1年,平均来说可以使个人收入增加11.4%,而健康水平每提高1个等级可使收入提高5%(根据调查数据把健康状况分为5级)。陈琳和袁志刚(2012)以及张车伟(2006)等人的研究,也都得出类似结论。可以看出,人力资本对于收入分配具有重要的影响,具体来说其作用机制如下:
(一)人力资本状况对居民就业状况的影响
1.教育状况决定着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一方面,受教育程度影响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者,信息的来源渠道较少,搜集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较弱,从而搜寻工作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同时,文化素质较低的劳动者,学习能力较弱,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难度较大,从而导致其就业领域较窄、职业转换较难。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也会导致劳动者就业的领域不同。一般来说,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意味着较高的学习能力及工作能力,其从事复杂工作、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因而其从事较高收入职业的可能性也就越高。大量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受教育水平与职业分布之间具有程度较高的相关性,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的就业者往往集中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技能行业;随着教育水平提高到初中、高中水平,从事商业、服务业以及办事人员的比例上升,在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就业人员中,单位负责人及专业人员的比例大大提高。
2.健康状况也影响劳动者的就业。健康状况与劳动者就业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良好的健康状况直接决定着劳动者较高的劳动参与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好坏影响着劳动者的寿命预期及就业心态,进而影响着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决策。一般而言,健康状况较好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更强,更愿意进入高风险的就业领域。刘生龙(2008)的实证研究得出健康状况每提高一个等级,农村居民劳动参与的可能性将提高3.48%。另一方面,健康状况还影响着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一般而言,健康状况较好的劳动者,其所能从事的职业所受限制较小,就业领域更广,从而获取就业难度较小、机会较多。
(二)人力资本状况对居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取决于其边际生产力,意味着劳动者的收入与其劳动生产率直接相关。一方面,良好的健康状况,将使得劳动者的有效劳动时间更长,工作积极性较高,劳动强度更大,从而其劳动生产率也相对较高。而较差的健康状况,不仅限制着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而且也会严重影响其他人力资本的正常发挥,导致劳动时间减少、劳动生产率降低,进而严重影响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其学习能力、技能水平、工作能力等方面都会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者具有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在按要素贡献的分配体制下,就会表现出差异性的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愈高,其利用科学技术、操作先进设备的能力愈强,从而也就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刘丁蓉(2013)的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她认为人力资本变量对劳动生产率起到显著性影响,在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比重较高地区的劳动生产率较高,人群中健康更高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也会更高。
(三)人力资本状况对居民非劳动收入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推进,非劳动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特别是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对收入差距拉大的贡献较大。王书华和苏剑(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户金融资产的配置差异确实对农户的收入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琳和袁志刚(2012)的研究则表明金融资产对于代际收入弹性的贡献较大。而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则影响着居民金融资产的投资决策。一方面,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居民,对于市场经济以及金融市场的理解力较强,能够较为正确地理解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因而具有更为理性的投资冲动及投资决策。另一方面,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居民,其信息来源广、加工信息的能力较强,因而其对于金融产品的理解更为准确,从而能够降低金融投资中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而人力资本素质较低的居民,由于所获信息的劣质性,更容易导致盲目投资。另外,人力资本较高的居民,具有较高的开拓精神及创新意识,也能更好地阅读市场、理解市场,使得这部分居民能够更好地获得并利用市场机会,因而这部分居民具有较高的创业冲动及创业能力,能够获得更高的经营性收入。
三、收入分配差距对不同收入阶层人力资本差距的累积效应分析
(一)不同收入阶层的家庭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不同
我国收入分配之间的巨大差距,意味着低收入阶层本身能够用于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智力投资和健康投资等方面)的绝对收入,要远远小于高收入阶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总是先满足较低层次的需求之后,才会去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其较低的收入除去满足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后,能够用于较高层次——求知需求等方面人力资本的投资就微乎极微了。因而,低收入阶层不仅能够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绝对收入与高收入阶层相差巨大,而且收入中能够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比重也相差较大;这两方面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低收入阶层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严重不足,使得高低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要素的质量不断被拉大。
(二)不同收入阶层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观欲望(动机)不同
1.各收入阶层之间的时间偏好率不同。所谓时间偏好率测量的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对现在的事情比未来的事情看得更重要。时间偏好率越强,意味着人们对于当前利益看得越重,反之则相反。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健康状况较差,生活压力较大,对未来的预期更加悲观。因而,低收入阶层的时间偏好率一般要高于高收入阶层,这也就意味着低收入阶层对于未来效用的贴现率更高,更加重视当前消费,短期行为较为严重,从而对于见效慢、期限长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要远远低于高收入阶层。
2.各收入阶层的经济决策时间视野不同。经济决策时间视野的长短,是投资决策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低收入阶层文化素质较低、进行合理决策的能力有限、对未来普遍缺乏理性预期,再加上我国劳权改革仍不到位、劳动力市场仍不完善等方面的原因,这就导致我国低收入阶层的经济决策时间视野较短,在决策中更加重视眼前利益。而人力资本投资只能在较长时间的连续投资后才能获取收益,时间跨度较长;在家庭较短的经济时间视野内,就会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期限长、收益慢而成为不恰当、不可取的方案。因此,低收入阶层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经济决策时间视野较短,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也就相对不足。
3.各收入阶层对于未来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由于我国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过低(甚至有些居民仍处在生存的边缘),所能享受到的各种社会保障严重不足,再加上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的失业压力加大、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使得我国低收入阶层居民抗风险能力较弱而趋于保守,“风险最小”取代“收益最大”成为其经济决策的首要目标。众所周知,人力资本投资的时间跨度较长,所面对的未来不确定性(风险)更大。因而,相对于高收入阶层而言,我国低收入阶层居民对于风险较大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求相对较小。
(三)不同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的代际积累不同
根据Viaene和Zileha(2001)的三阶段“世代交迭模型”(OLG),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被分解为两种形式:父母所提供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所提供的“公共教育”,其中:家庭教育取决于父母自身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状况,而公共教育则对于同一时代中的每个劳动者都近乎是相同的。低收入阶层由于其本人的人力资本要素较低,其能够提供给子女的“家庭教育”质量也就相应较低;再加上低收入阶层学习的能力较弱,其通过自身再学习而向子女提供“家庭教育”的能力也远远劣于高收入阶层。因而,低收入阶层“家庭教育”的劣质性导致其人力资本的代际积累速度较慢,进一步拉大其与高收入阶层人力资本的差距。另外,低收入阶层由于健康状况较差,通过遗传的作用也会导致其后代健康状况先天性较差,通过代际之间的交叠作用拉大与高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差距。
四、政策建议
(一)短期主要采取“激励相容”的福利政策
1.改变补贴方式。要改变传统单纯“给予式”的单向补贴方式,大力开展以项目为依托的“开发式”补贴方式(例如:以工代赈),使得福利支出在弥补收入差距的同时也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获得持久、可持续增长,鼓励低收入家庭进入劳动领域和项目创业。
2.变传统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为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府在设计现金转移支付政策时,可以借鉴美国“有条件现金支付项目”(CCT),鼓励低收入家庭在获取现金补贴的同时增加健康和教育投资,激励低收入阶层居民积极参加各种现代职业技能培训、市场经济知识普及以及科学技术培训。通过实施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在给予低收入阶层一定生活补贴的同时也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科学文化素质以及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能力,使其能够更好、更容易进入现代产业部门就业、创业,从根本上解决他们收入过低的状况。
3.建立劳动所得抵免制度。劳动所得抵免政策只向愿意工作的“勤劳者”进行抵免,抵免额随着纳税人收入状况和家庭成员状况而变化,当抵免额超过纳税人的应纳税额时,政府就会对纳税额进行财政补贴,这时相当于纳税人所承担的所得税税率为负税率。在弥补收入差距时,劳动所得抵免政策不仅可以有效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而且由于这项政策的对象是愿意工作的“勤劳者”(只有他们努力工作后才能够获得补助),从而能够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而不至于像传统的福利制度那样增加社会失业、损害社会效率。
(二)长期路径要以改善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为主
1.政府应制定长期规划,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一是,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出生干预以及婴幼儿的营养补贴。为了提高我国的人口质量,降低低收入阶层健康状况的恶性循环,从根本上杜绝在出生环节而出现的身体、生理缺陷,国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出生干预。并且,低收入阶层的婴幼儿由于营养不良,生长发育缓慢、机体萎缩,这种状况就会对其产生长期的影响,导致身体素质较差。因而,政府要要加强对于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出生干预计划和婴幼儿营养加强计划,以提高低收入阶层人口的基本素质。二是,继续加大并改善现行针对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的营养补助。三是,扩大医疗保障的覆盖范围,特别是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保障程度。目前,我国医疗保险仍然没有覆盖全体居民,而保障程度的差距较大。2011年,全国2 853个县(市、区)中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为2 637个,新农合报销比例仅为26%(而城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为50%)。因此,政府增加医疗保障投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保障程度,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身体健康水平。
2.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建立公平有效的教育体系。现有教育体系的教育资源更多地倾向于城市、倾向于高收入阶层,使得各收入阶层之间由于所能获得教育资源的差异,而导致人力资本质量的差距逐渐扩大。因而,在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政策中,教育政策应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以逐渐缩小各收入阶层之间人力资本质量上的差距。一是,要切实改善我国目前教育投资结构失调的状况,继续加大国家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二是,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地区教师的收入水平,引导素质相对较高的人才流向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教育事业,解决目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三是,加快经济转型,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向技术密集型增加方式,提高知识的收益率,才会有效的改善大学生的就业状况。从而增加社会公众对于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收益,引导低收入阶层增加对于教育的投资。
[1]刘金贺,马兹晖,李牧群,等.2010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展望[J].当代经理人,2010(7).
[2]黄世贤.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中国的贫困问题[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2).
[3]张学仁.对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现状的分析与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7(15).
[4]赵荣,王斌,张结魁.西安市国内游客旅游行为研究[J].西北大学学报,2002(4).
[5]郭旭新.经济转型中制度变迁的动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6(2).
[6]刘晓路.论政府在改善收入分配状况中的作用[J].财贸经济,2003(8).
[7]夏莉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成因分析和对策思考[J].生产力研究,2004(10).
[8]孙立平.贫富差距的几个新特征[J].理论与实践,2003(5).
[9]阮扬,陆铭,陈钊.经济转型中的就业重构与收入分配[J].新华文摘,2003(2).
[10]肖行.我国社会保障问题讨论综述[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10).
[11]刘凤良,吕志华.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影响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8(6).
[12]张要杰,徐毅.“链环路径”:构筑我国收入分配公平之“桥”[J].重庆社会科学,2006(12).
[13]平新乔.关于中国财政税制改革的若干看法[J].经济研究资料,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