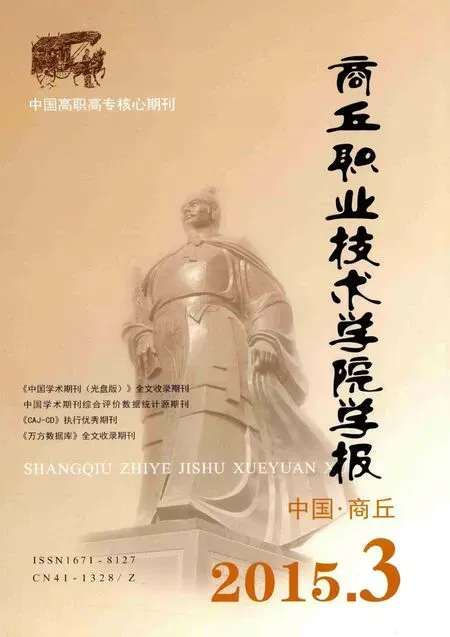女性主义批评课程设置难点及应对策略
赵思奇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一
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权政治运动深入到文化领域的产物。它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1791年妇女领袖奥伦比·德·古日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与此差不多时间,在与法国一水之隔的英国,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在1790年写了《为人权一辩》,这些理论上的先导为日后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铺下了坚实的基础。自19世纪晚期以后,出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弗吉尼亚·伍尔夫、波伏娃、凯特·米利特、贝尔·胡克斯等人。弗吉尼亚·伍尔夫致力发掘独立的女性文学传统,从男性垄断的文学史中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女性文学脉络;波伏娃批判了男性作家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误读,并对这些女性形象给予重新评价;凯特·米利特将两性关系与男权社会权力结构联系起来,对文学中的父权制进行了全面的批判,通过将男性作家劳伦斯、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的作品与同性恋作家让·热内作品的比较,指责男性作家文本中的性别歧视;贝尔·胡克斯则从黑人群体的立场,批判了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对种族问题的忽视。上述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女性主义批评的不同纬度和层面,虽然立足点各有侧重,但无一例外开拓了传统文学领域研究的另一维。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用女性意识关照文学作品,凸显女性视角和女性审美追求的文学批评方法。作为西方文论流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它在对男性中心诗学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纠正单一男性视角建构文学史的偏差,模塑新型两性关系的未来趋向。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登陆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演变成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流派。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促进了中国女性研究的兴起和女性文学的繁荣,它从性别的角度打开了一个沉睡千年的女性世界,构筑了文学研究的新层面。
二
正是鉴于女性主义批评的重要价值,目前,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性别研究课程。其中,讲授方法各有不同,要么以讲述女性主义批评家的批评思想为主,要么用性别视角解读国内外文学作品,要么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阐释女作家生平与创作。可见,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目前国内从事性别研究的人员数量庞大,专业繁多,使得女性主义批评在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的层面,都存在着概念误用的状况,甚至出现概念的含混不清、阐释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等问题。鉴于此,开设女性主义批评课程,不仅对于帮助学生厘清女性主义批评的一系列概念至关重要,对于完善大学生的知识体系大有裨益,同时,对于引导他们以一种新的视角解读文学作品,培养他们敏锐的性别视角和性别意识,纠正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偏差有着现实意义。鉴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流派的纷杂以及批评家的众多,且女性主义批评和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都有密切联系,不同专业研究者研究的切入点各有不同,即使同在文学领域,不同方向的研究者也会有各自的研究视角,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给学生梳理出女性主义批评的主体框架和脉络,课程设置的立足点至关重要。而且,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把这门课程核心脉络讲述清楚,时间的把握也非常重要,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教学资源浪费,成了女性主义批评课程设置的首要问题。如果采取传统的以批评家为主体的教学方法,虽然知识面很普及,但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同一个理论问题会反复地讲。
以“姐妹情谊”这个理论问题来说,“姐妹情谊是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批评的基本原则,也是女性文学乐于建构的理想国,它的动因在于女性作家、批评家争取女性团结以获得力量的愿望,也基于女性四分五裂而无力反抗压迫的实际”[1]89,对于这个理论话题,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探讨过,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探讨过,如果以批评家为主体来讲,倒是可以讲清楚各自对这个问题不同的看法,但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之间有什么差异?白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不同?很显然,这种教学方法缺乏一种纵向的比较,造成学期课程结束后,学生掌握的知识点犹如一盘散沙,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知识体系和清晰的知识脉络。而关键词的课程设置恰恰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不仅让课程条理清晰,而且学理性强,节约教学资源,彰显文艺理论专业特色。鉴于此,以“关键词”作为入手点,以点带面,进而让学生了解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全貌,掌握女性主义批评的本质内涵,是一种有效且可行的授课方法。具体而言,梳理出女性主义批评的关键词汇,包括“女性文学传统”、“女性写作”、“女性形象”、“姐妹情谊”、“双性同体”等,以上述关键词作为专题,分课时给学生讲述。在授课过程中,先从理论的角度入手,厘清概念,然后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发展历程中,不同批评家对这个概念的各自看法,归纳出她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挖掘出产生分歧的深层原因。
以“女性文学传统”为例来说明,英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女人的职业》一文开头中写道:“多年以前,范妮·伯妮、阿芙拉·贝恩、哈丽雅特·马蒂诺、简·奥斯汀、乔治·爱略特等人就已开拓出一条道路——许多著名的女人,和更多不知名、被人们遗忘的女人都曾先于我,铺平道路,规范我的脚步”[2]1366。很显然,她提出了一个女性主义批评中重要的话题——即探寻女性文学传统的问题。自伍尔夫之后,英美后世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就没有放弃过建构传统的努力,虽然各自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肖瓦尔特提出“女性亚文化群”,从文化层面上凸显女性传统的独特性;爱伦·莫尔斯将女性文学史作为与主流文学并行的潜流;吉尔伯特和古芭用现代批评理论阐释女性文学传统存在的原因等,她们侧重于“建构”,树立一种传统和规范。而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则采取“解构”的立场,她们认为“传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女性的写作身份才是关键,“哪里有压制,哪里就有女性”[3]8。由上可见,英美派和法国派虽立场不同,但基本都将讨论的立足点放在女性写作的领域内,这是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相应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也提出了建构“文学传统”的命题,主旨和英美派一致,侧重于“立”,但突破了写作的领域,而深入到文化范围,将音乐、建筑、花草树木包括黑人女性的生理特征等都纳入到传统之内,对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是一个补充。在此基础上分析不同的女性主义流派产生上述分歧的原因。
每一个论题都采取上述授课方法,不仅能让学生准确地把握理论内涵,而且清楚每一个概念流变的来龙去脉。上述关键词汇讲述结束后,学生就会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有一个宏观且细致的把握,实现教学目的。具体到教学过程,女性主义批评关键词之间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有内在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把握好先后次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可让教学过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具体而言,将“女性文学传统”放到首位,因为它是总纲性的论题,牵涉到对“女性文学”的定义;然后由此发散出“女性形象”这个理论话题,因为“女性形象”来源于“女性文学”对于文学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由此可以洞见男性文本和女性文本在塑造女性形象时的性别意识差异;在此基础上引出“女性写作”这个论题,分析女性写作的含义,挖掘隐藏于其中的女性视角、女性身份以及女性心理;个体女性在女性心理、女性视角等要素之间存在差异,导致“姐妹情谊”建构的困境,就此引出“姐妹情谊”这个论题,如此递进。抓住关键词这条线索,依照教学规律,由知识点入手,由点及面,向学生呈现出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全貌。鉴于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特性,在授课过程中,将课堂板书与多媒体结合起来,运用图片和视频,使课程充满活力。以问卷调研的方式,了解学生的兴趣点所在,融入教学中,真正做到让书本知识活起来,而不再是枯燥的理论。最后以论文考察的形式,检测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掌握情况。
三
具体到教学过程,首先注重女性主义批评的本土化阐释。女性主义批评作为西方文论的重要流派,属于外来理论,其内容和话语形式具有明显的异域色彩,造成了学生接受的陌生感和艰涩感,总感觉与课程“隔着一层”。这就需要教师尽可能用本土理论去包容、去覆盖这些外来理论。当然,这种阐释不是生硬地把外来理论变成中国理论,中国的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已经有了独立的学科和独立的研究范式,所以用本土理论去统领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相通的部分,是行得通的。比如“女性写作”,白人女性主义批评执着于在写作领域对性别权力的占有,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则倾向于通过写作达到男女两性的和谐。这些问题,中国的女性作家也会遇到,因此借用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可以实现中西理论的有效对接。对于那些在本质上与本土理论不相容的批评,自然可以另换一种方式来阐释。其次,将鲜活的感性知识融入课堂中,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理论话语,本身缺少栩栩如生的文学文本作为感性支撑,而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量少是本科生的通病,这会造成他们接受上的困难。因此,在讲解每个论题的过程中,将一些生动鲜活的文学作品融入课程的各个知识点,让学生从感受作品出发,去领悟女性主义批评的内涵,降低理论的难度,培养学生的兴趣。比如,在讲述女性形象这个理论问题时,可以将《傲慢与偏见》、《阳光下的葡萄干》、《最蓝的眼睛》等西方女性主义文本纳入到课堂中,白人女作家和黑人女作家都会谈到女性形象,她们笔下所塑造的女性类型,必然不同。白人女作家一般擅长描绘“天使”与“妖妇”,黑人女作家一般描绘“女保姆”、“女家长”等等,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必然结果。这些女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反映了什么深层问题。从文学作品入手,让学生在形象思维中接受理论知识。再次,将小组讨论融入课堂中。借鉴西方女性主义团体注重开展讨论小组的方式,将课堂分组讨论和小组交流与教学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增强师生互动,让理论有生命力,而不再是枯燥的书本知识。
[1]魏天真.“姐妹情谊”如何可能?读书[J].2003(06).
[2]弗吉尼亚·伍尔芙.伍尔芙随笔全集[M].王 斌,王保令,胡龙彪,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3]玛丽·伊格尔顿.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胡 敏,陈彩霞,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