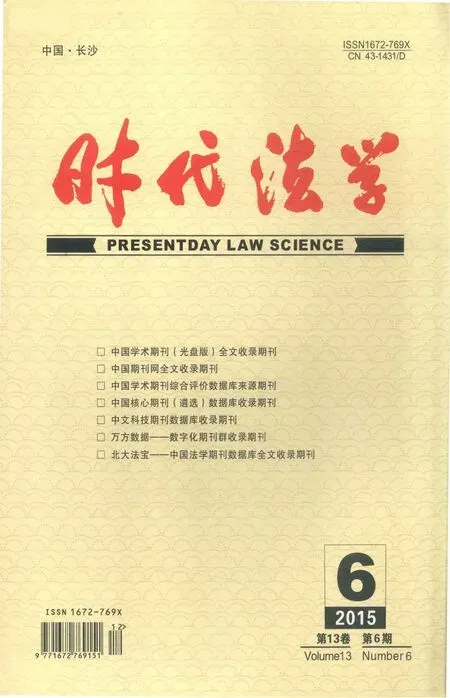日本“情况证据”理论及其借鉴*
帅清华,郭小亮
(1.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南昌 330029;2.江西警察学院,江西南昌 330100)
证据的审查判断,是审判权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判实践中,运用间接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要比直接证据更为复杂,也更具研究价值。间接证据在日本亦称为情况证据,其理论来源于英美法,但又有别于英美法,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研究日本的情况证据理论,发现和甄别其中可以为我国所借鉴的地方,对于完善我国证据制度、规范审判权的运行,庶几可以裨补阙漏,有所广益。
一、日本“情况证据”理论概观
(一)情况证据中的“情况”
情况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又称情势证据、环境证据,指的是“间接证据以及由此认定的间接事实合在一起的总称”〔1〕[日]松尾浩也.刑事诉讼法的争点[M].东京:有斐阁,2002.156.。按照这一定义,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是有一定区别的。但是,日本的司法实务并不严格区分两者,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的,两者仅具有语源上的差别,即:“间接证据”来源于德国法,“情况证据”来源于英美法〔2〕[日]石丸俊彦.刑事诉讼实务(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规出版株式会社,2005.41.。
情况证据一词,在英美法上是来自于“情况不会说谎(Circumstances don't lie)”的格言〔3〕[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35.40.。按照这一格言,情况证据中的“情况”是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事物性质、痕迹、环境以及人的行为等客观资料和信息。这些客观资料和信息的存在具有客观实在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云“不会说谎”。但客观资料和信息并不能直接地证明犯罪构成要件事实存在与否,只能证明某些间接事实,然后才能根据间接事实推导出犯罪构成要件事实。所以,日本刑事证据法一般将情况证据中的“情况”理解为不属于待证事实,但又与待证事实具有密切联系的事实,这些事实可以间接地推认待证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4〕[日]平野龙一.刑事诉讼法概说[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0.201.。在这一意义上,“情况”就是间接事实,因此将情况证据等同于间接证据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情况证据的存在形态
1.情况证据的常规形态
日本的刑事证据理论一般把情况证据的常规形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物依存型,一种是非实物依存型。
所谓实物依存型,就是以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的情况证据。如凶器、药物、现场遗留的碎片、钥匙孔的破损、各种痕迹、指纹、脚印、笔迹、账簿、会议记录等。实物依存型的情况证据相当于我国的物证和书证,比较容易理解。
所谓非实物依存型,指的是以实物之外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情况证据。最常见的是各种言辞,如证人陈述被告人于某一时间不在现场的证言(日本司法实务一般套用英美法用语称为「アリバイ」,即Alibi)。此外,人的生理、心理变化、行为、状态等,也可以成为情况证据。例如哭泣、哀叫、性格、疾病、可能用于犯罪的知识和经验、财产的转移和处分、工作变动、社会交往关系等。日本法院的判例还明确指出,说话的声调、语气、发抖、出汗等表现人的心理变化的情况,也可以通过录音、录像、检验笔录等形式固定化为情况证据〔5〕[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35.40.。
2.情况证据的特殊形态
情况证据的特殊形态,主要有四种。
一是作为辅助证据的情况证据。这种情况证据要证明的对象不是待证事实,而是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即所谓“证据的证据”。例如,会议记录记载董事长甲在公司董事会上暗示要挪用和侵占客户资金的发言,该会议记录是一种情况证据,而证人乙作证陈述甲当天在美国旅游,不可能出席该次会议,乙的证言不能证明甲是否实施了侵占行为,但能够间接地证明会议记录的可信度,此时乙的证言就是一种作为辅助证据的情况证据。
二是关于可能性的情况证据。这种情况证据不能确实证明待证事实的有无,只能证明有无该事实的可能性。例如案发现场的环境、构造、通风、采光等情况,只可证明被告人是否有作案条件或证人是否有目击条件,其证明的结果仅为一定程度的可能性。大阪高等法院2001年10月24日的判例指出,被害人尸体无法找到,不能确实查明其年龄,但从其案发前不久的照片上的容貌、体格、发育情况等,可以认定其系未成年人的可能性较大,此时,该照片可作为情况证据使用。
三是关于被告人作案后实施特定行为的情况证据。即通过被告人在作案后的毁灭隐匿证据、栽赃嫁祸、整容、逃亡等异常表现,推认其就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例如,东京高等法院2000年8月17日的判例认为,被告人在其女友失踪之后,立即搬家到外地、不与女友家人联系、不去参与寻找、将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剪下来收藏、不出席葬礼和法事,这些异常的间接事实可以作为推认被告人杀死其女友的情况证据〔6〕[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35.43.61.。
四是控辩双方当事人特定的诉讼行为也可能成为情况证据。例如,日本最高法院的判例指出,在检察官初步证明了待证事实后,被告人可以提出反驳,如果被告人提不出证据进行反驳,就可以认定检察官指控的事实成立。此时,被告人提不出证据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情况证据,法院可以据此认定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同样,对于被告人的反驳,检察官可以提出再反驳,如果检察官无法提出再反驳,也可以作为情况证据认定对检察官不利的事实〔7〕[日]石丸俊彦.刑事诉讼实务(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规出版株式会社,2005.55.。
(三)情况证据的分类
情况证据有多种分类,实务中常用的是两种。一是分为肯定指控内容的积极情况证据和否定指控内容的消极情况证据。二是分为并存的情况证据、预见的情况证据、溯及的情况证据。
并存的情况证据,指的是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过程中的情况证据。最常见的如现场残留的被告人指纹、脚印、血痕等。此外,日本法院的判例认为,Alibi以及被告人提出的犯罪行为系第三人实施的主张,也属于并存的情况证据。
预见的情况证据,指的是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证据。日本法院明确认定的预见的情况证据有:被告人具有制造毒品的知识和经验、向他人购买用于印制假钞的机器、与被害人的矛盾纠纷、对藏有银行金条的特殊隐密场所的认知、业务侵占行为被揭发前经营不善而出现资金紧缺的情况等。
溯及的情况证据,指的是产生于犯罪行为实施之后,可以证明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证据。前述情况证据的特殊形态已涉及到溯及的情况证据。此外,溯及的情况证据还包括:犯罪发生后第二天,被告人持有作案用的工具;被害人财物被盗窃后,被告人的银行卡上忽然多出与被盗金额相近的存款,并在数天之内挥霍一空;杀人现场留有被告人血迹,而被告人在案发当晚曾到医院治疗伤口〔8〕[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35.43.61.。
(四)情况证据认定的构造
1.实体性构造
按照前述的定义,情况证据是间接证据以及根据间接证据认定的间接事实的总称。据此,运用情况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基本构造,也就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根据间接证据认定间接事实,第二步是根据间接事实推认出待证事实。日本证据法理论上说的“情况证据认定的构造”,指的主要就是根据间接事实推认出待证事实的过程和方法。
曾任东京高等法院法官的木谷明教授把情况证据认定的构造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即“分别检讨、综合评价、过程说明”〔9〕[日]木谷明.刑事事实认定的基本问题[M].东京:成文堂,2008.259.。分别检讨,指的是对每一个间接证据和每一项间接事实都要单独拿出来进行分析,判断其与待证事实的逻辑关系,重点审查其证据能力(关联性)。综合评价,指的是在肯定情况证据关联性的基础上,将全案的情况证据作为一个整体,判断其对待证事实的推认能否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过程说明,指的是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详尽地说明推理过程。从间接事实到待证事实,需要在判决书中有意识地展示推理过程。如果推理过程的说明不能排除被告人辩解提出的合理假说,就需要对认定的事实进行重新审视〔10〕[日]木谷明.刑事事实认定的基本问题[M].东京:成文堂,2008.259-261.。
2.程序性构造
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一审开庭之前要进行庭前整理程序,目的是交换和开示证据,在尽量早期的阶段明确争议焦点,以便庭审时集中进行证据调查和法庭辩论。在庭前整理程序中,检察官应提出记载预定证明事实的书面材料,在充分进行证据开示的基础上,向被告方表明主张。这要求检察官在书面材料中明确提示情况证据的运用以及举证计划。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的防御而言,一般可以从排除情况证据本身、主张相反的间接事实、反驳推理过程这三个方面着手,这些主张应在庭前整理程序中明确提出,需要提交证据的,应充分开示。如果被告人认为检察官开示的证据和举证计划有不够清晰的地方,可以通过法院要求检察官释明。对法官而言,应“准确地把握检察官举证构造的整体状况,对照着斟酌被告方的主张,在此基础上整理争议焦点,确定审理思路。”〔11〕[日]木谷明.刑事事实认定的基本问题[M].东京:成文堂,2008.259-261.
(五)日本法院判例中情况证据的运用
在日本法院的历代判例中,情况证据的运用非常广泛,最常见的是用于对被告人同一性和对故意、目的等主观要件事实的认定〔12〕[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从情况证据的观点看事实认定[M].东京:法曹会,1994.3.。
检察官指控被告人犯罪,首先要证明被告人与作案人的同一性,即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实施。在日本,运用情况证据来证明被告人与作案人同一性的著名判例是最高法院2000年2月21日关于“乌头碱杀人事件”的判决。在该案中,检察官以杀人罪、诈骗未遂罪起诉被告人神谷某,指控其于1986年5月20日与妻子神谷佐利子(被害人)及女友二人一起到冲绳县石垣岛旅游,期间被告人将一枚含有乌头碱的胶囊交给被害人服下,被害人于当晚出现不适,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因心肌梗塞而死亡。被告人坚决否认自己下毒杀人,因此没有口供或其他直接证据。检察官提交的情况证据主要通过动机、作案条件、被告人的专业特长、行为习惯、在短期内为被害人购买巨额人身保险、曾购买乌头草和河豚等间接事实来证明被告人的同一性。与此相对,被告人提出的辩解是:乌头碱为急性剧毒,5毫克左右可立即致命,而被害人出现不适症状时,自己已离开被害人3个多小时,因此否认检察官的指控。检察官对此进行反驳,认为被告人所用的毒药是乌头碱与河豚毒的混合物,河豚毒是慢性毒物,可缓解乌头碱毒发的时间。本案由东京地方法院一审,经综合考虑认为检察官提出的假说具有较高的盖然性,且足以否定被告人的辩解假说,遂认定被告人构成杀人罪和诈骗未遂罪,判处无期惩役。案件经东京高等法院二审、最高法院三审,均维持原判。此判例没有明确指出被告人实施犯罪的事实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是从具体时空条件下杀害被害人的可能性的角度来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性,从而认定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这被认为是没有直接证据的场合完全依靠情况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较为成功的典型判例〔13〕[日]石井一正著.刑事事实认定入门[M].东京:判例时代社,2005.117.。
在杀人案件中,被告人经常以没有杀人意图作为辩解理由。为此,能否运用情况证据来证明杀人的故意,是事实认定的关键。按照日本法院的判例,认定杀人意图的存在,主要是从凶器、创口、行为形态、动机这四个方面来着手。东京高等法院1994年11月16日判决中对根据凶器来认定杀人故意的做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在该案中,被告人用华丽的锦盒装住一把刃长68厘米的忍者刀,伪装成礼品,进入被害人的办公室,将被害人砍伤,对此,被告人辩解称自己仅有伤害的故意,没有杀人意图。法院认为,在使用刃物杀人的案件中,刃部的长度、形状、攻击的部位、角度、方法等,均可成为认定杀人意图的积极要素或消极要素,关键是看凶器及其使用是否具有致命的危险性,根据本案案情,凶器忍者刀为精炼花纹钢材质,刃口较长而且十分锋利,被害人受伤的几处部位均足以致命,被告人将凶器精心伪装,则表现出计划性,因此可以认定被告人具有杀人的直接故意。另一方面,正如上述判例指出,凶器的性状也可以成为消极的情况证据,例如福冈地方法院宫崎分院的一个判例认为,被告人使用刃长仅4.5厘米的水果刀捅被害人腰部,最多只能在伤害的程度上认定犯罪故意〔14〕[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124.。
根据凶器来认定杀人故意,还要考虑被告人的认知,在这一点上与过失犯罪相区别。例如,对于药物、爆炸物、机械、弓弩等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物品,其本身虽有高度危险性,但如果被告人不可能认识到危险性,则不应认定被告人具有杀人故意,根据案情应认定为过失或无罪〔15〕[日]植村立郎.实践的刑事事实认定与情况证据[M].东京:立花书房,2008.132.。
二、日本“情况证据”的若干特色
与我国的间接证据理论相比,日本的情况证据理论更是具有鲜明的特色,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渊源判例,具有显著的实践性
日本的判例制度十分独特,一方面它坚持成文法主义,另一方面,它又规定法院的判例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法官在审判案件时有遵循判例的规范性义务〔16〕[日]团藤重光.法学的基础[M].东京:有斐阁,2007.167.。日本刑事诉讼法典对情况证据的规定很少,学者的教科书和专著中对情况证据的论述大多也很简略。但由于情况证据在审判实务中的重要性,很多法官都非常注重对情况证据的研究和实践,由此形成了很多经典判例。自1947年日本现行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通过数十年的判例积累,形成了一套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情况证据理论。情况证据理论的大部分内容,可以说主要不是依靠纯粹的学者,而是依靠法官,尤其是学者型法官来完成总结和表述的任务的。前面论及的研究者,石丸俊彦、植村立郎、石井一正、木谷明等皆是享誉司法界的学者型法官,他们的论述常常大量引用各级法院的判例,使得情况证据理论的很多内容与具体案情直接相关。
(二)分类独特,具有广泛运用性
日本将情况证据按时间序列区分为并存的、预见的、溯及的三种,这种分类未见于英美法,为日本所特有。一般来说,并存的情况证据产生于犯罪过程中,与犯罪行为有密切的因果联系,证明力相对较强。预见的情况证据和溯及的情况证据,其证明力则十分微妙:一是其结论的或然性也比较低;二是其不能单独定案。对此,日本最高法院的中川武隆法官把预见的情况证据和溯及的情况证据称为“危险的证据”,并指出,“对于这些情况证据,法官往往容易过度地肯定其可信度和推定力,因此,在判断这些情况证据的时候,应当慎重地分析其含义和相互联系,在适当的范围内认定其证明力。”〔17〕[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从情况证据的观点看事实认定[M].东京:法曹会,1994.36.在日本的刑事判例中,因为没有直接证据而完全依靠情况证据定罪的案件非常多,前述的“乌头碱杀人事件”就是近年来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此类案件之一。同时,运用情况证据判决被告人无罪的案件也占无罪案件的多数〔18〕[日]法务省法务综合研究所.平成21年版犯罪白皮书[EB/OL].http://www.moj.go.jp/content/000010214.pdf.。
(三)恪守程序,存疑有利于被告人
日本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原则,证据的证明力主要由法官依据自己的心证裁量。但基于情况证据需经过推理这一特殊性,为了防止自由裁量权行使超越应有边界,法律和判例确定了一系列制约性程序。值得一提的是疑罪从无原则的适用。情况证据只能得出或然性的结论,虽然允许被告人提出反驳,但实践中仍难以避免因判断失误造成冤案的情况。为此,曾任东京高等法院院长的石丸俊彦法官在其著作中深有感触地写道:“由于法官的过于自信,情况证据往往变成危险的证据。有了情况证据后,法官在面对各种压力时,就容易倾向于考虑报应感情的满足和社会秩序的维持,通过处罚被告人来缓和被害人与舆论的指责。对此,情况证据最重要的注意规则,莫过于坚持‘存疑则有利于被告’这一刑事审判的铁的法则。”〔19〕[日]石丸俊彦.刑事诉讼实务(下)[M].名古屋:新日本法规出版株式会社,2005.90.
(四)公开心证,展示事实认定过程
自由心证主义在现代被要求具备可检验性,而可检验的前提正是法官将心证形成的过程予以公开。木谷明教授认为,“裁判文书的制作是事实认定过程的一种反馈。将事实认定过程包含的各种信息完整地传达给受众,是裁判文书的基本功能。”还有法官指出,“裁判文书不是诉讼档案,不应该要求裁判文书能够详细到可以独立于案卷和证据而存在的程度。”因此,详尽的说明并不等于冗长的文字,就判决书的写作而言,日本法官也反对单纯地罗列间接事实而使文书显得繁琐,“说明的详略程度,应视案情而定,在全面的基础上兼顾精练。过于简略或过于冗长,都会使判决丧失说服力。”〔20〕[日]最高法院司法研修所.从情况证据的观点看事实认定[M].东京:法曹会,1994.127.
三、我国刑事审判对间接证据的运用:以日本“情况证据”理论为借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制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别,日本的刑事诉讼和刑事证据理论的很多内容,对于我们来说仅具有参考意义,不宜直接移植。例如日本法院根据传闻规则通常否认侦查笔录和庭外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与我国司法实践的做法大不相同。但是,由于审判权运行的普遍规律和证据运用规则所具有的共性,中日两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证据理论还是有很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的。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我国刑事审判对间接证据的运用可以借鉴日本情况证据理论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一)总结经验,确立间接证据运用规则
日本的情况证据理论在总体上给我们一个启示:证据法具有浓厚的实践性色彩,光靠单纯的理论思辨和哲学玄想很难在证据法研究上有所作为。判例的积累和法官的思考,是证据法理论发展和完善不可缺少的路径。目前我国关于间接证据的研究,有几个值得商榷的倾向:一是介绍英美国家法律的多,结合本土资源的少;二是研究立法规定的多,关注司法运用的少;三是抽象论述的多,个案实证研究的少。要改变此种现状,唯有以广大法官为研究主体,以典型案件为研究素材,以实证分析为研究方法,不断总结审判实践运用间接证据的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既要切合司法实践,也要防止就案论案,使司法审判中法官的智慧和经验转化为普适性的原则和规范。期待我国尽早建立全国统一的案例指导制度,为审判实践运用间接证据的经验总结提供制度支持。
(二)谨慎判断,发挥间接证据的独立定罪机能
日本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经济发达国家之一,这种情况被归结于其刑事司法制度的成功运作,同时,法院审判刑事案件的有罪率很高,一般都维持在99.8%左右。由于存在沉默权,实践中经常出现没有口供和直接证据的案件,可见日本法官对运用情况证据定罪是非常“大胆”的。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明确规定了自由心证主义,法官对证据证明力拥有较大的裁量余地,另一方面,日本法官享有良好的职业保障和社会威望,在作出裁判时面临的案外压力相对较小。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理论虽然也承认可以完全运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21〕徐静村.刑事诉讼法(上)[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68.,但在司法实践中,单凭间接证据就定罪的案件可谓少之又少,而大量地取得直接证据在很多案件中是不可能的。这种二律背反已经演变为司法实务的一种困境,有学者称之为刑事诉讼的“证明危机”〔22〕龙宗智.印证与自由心证——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模式[J].法学研究,2004,(2).。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1)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过于理想化,要求证明结论具有唯一性,并“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23〕陈光中.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66.,而间接证据必须经过推理,推理结论仅具有或然性,不可能绝对地“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2)“口供情结”在很多法官的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未能克服传统司法“罪从供定”的思维模式,对没有口供的案件不敢作出判断;(3)我国侦查机关技术落后,侦查人员素质不高,很多间接证据未能及时收集、固定,或存在严重瑕疵,影响了证明力;(4)我国实行严厉的错案追究责任制度,法官在作出判决的时候常常不得不有所保留;(5)我国法官的司法能力和社会公信力仍有待提高,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的社会压力较大,缺乏运用间接证据定案的底气和自信;(6)司法体制有待改正,我国实际行使审判权的往往是审判委员会,真正审案法官往往只是将自己的意见交由审判委员会裁决,审判委员会成员由于不是实际的审判经历者,而只是根据法官报告来形成意见,在只有间接证据的场合,难以形成明确意见。
2010年6月,我国的“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第33条放弃了“排除其他一切可能性”的理论标准,代之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此“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被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再次确认,为独立运用间接证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关于合理怀疑以及如何排除存在纷争,且现今正处于司法体制阶段,要解决解决间接证据司法困境和证明危机,还有待于实践的继续探索和司法环境的根本改善。
(三)疑罪从无,尊重和保障被告人权利
日本司法机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曾标榜“精密司法”,即通过严密的社会管理机制和细致的侦查手段来追究和指控犯罪,大量运用科学化的证据准确认定犯罪。但是,80年代以来,日本连续出现了财田川事件、白鸟事件等著名的冤案,通过媒体的放大宣传,导致“精密司法”的神话成为历史,曾经得到国民高度信任的法官威望面临空前挑战。这促使日本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存疑则有利于被告’这一刑事审判的铁的法则”。还有法官明确主张“刑事审判中第一重要的不是追究和惩罚犯罪,而是阻止冤案的发生,保障无辜者不受处罚。”〔24〕[日]木谷明.刑事事实认定的基本问题[M].东京:成文堂,2008.2.
我国媒体高度关注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强奸杀人案、浙江张高平和张辉叔侄强奸案、安徽于英生故意杀人案等近年改判的刑事案件,这些冤错案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严重影响国民心中尚未树立牢固的司法权威。我国与日本的司法体制大相径庭,造成冤案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间接证据运用不当应是共同原因。对于间接证据的运用,应当以证据链的真实、完整、协调为标准,在极其谨慎的基础上进行缜密的逻辑推理。当公诉机关提出的证据不能使推定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时,应当严格依照程序,从保障人权,维护被告人权利的角度出发,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裁判。
(四)详尽说理,明确裁判文书证据推认过程
过去我国法院的裁判文书长期流于简略,事实和理由均以数笔概括,曾被学者诟为“简单归摄模式”〔25〕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25.。近年来此种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洋洋万言的判决书已是司空见惯。但是仔细考察这些篇幅较长的裁判文书,其大部分篇幅并非用于说理,而是用于罗列证据,这些证据已载于案卷,法官在裁判文书中概括转述,不仅显得重复,而且可能存在人为剪裁、断章取义的危险。在证据的分析和说明方面,目前我国的裁判文书较为注重证据个别分析,即在罗列证据的同时说明每个证据的来源、证明对象、是否采信等事项,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运用间接证据得出待证事实的推理过程,仍鲜见详尽的论述,往往是在大量罗列证据之后,直接得出最后的整体结论,其思维和推理过程如何则不得而知,给人印象十分唐突。裁判文书缺乏推理过程,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事后检验,在上诉和再审程序中容易造成上下级法院的认识分歧,导致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
对此,应该借鉴日本的“裁判文书不是诉讼档案”、“不要求裁判文书能够独立于案卷”的观点,即裁判文书不必将大量的篇幅用于重复叙述证据的内容,而应将重点置于“说理”,公开展示对证据的评价和推理过程。为此,法官在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中,最好能够详细地分析每一个推理步骤,层层展开,使证据链中的空隙都得到填补,形成环环相扣的完整的逻辑思维过程。法官对于推理所使用的经验法则、逻辑规则、生活知识、专业知识等,都应大胆予以明确的揭示,通过裁判文书的文字载体,尽量公开自己形成心证和内心确信的全部过程,以接受上级法院和社会公众的事后检验和监督。
——以“被告人会见权”为切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