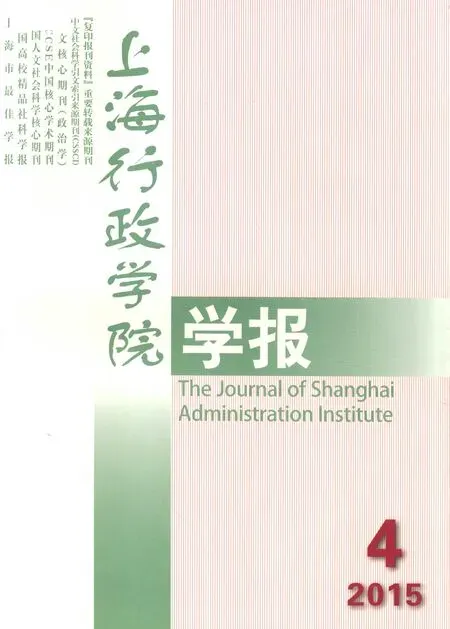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丁长艳
(上海行政学院 上海 200233)
从世界文明发展进程看,现代化已经从简单阶段进入复杂阶段,现代政治风险容易将国家治理带入更多不确定性中,个人、组织、社会与国家如何实现不同程度的自我保护,个人认同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都是现代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随着信息化技术日益渗透政治生活,重塑了权力、权利与民主间的关系,国家治理形态及其结构也发生本质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看,权威理性化、结构分化、政治参与扩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并成功地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从20世纪末到现在,关于市场化与全球化给中国国家治理带来的现实风险,在理论层面主要有“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两种不同争论。前者认为,局部危机容易导致国家治理的全面问题,就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执政能力而言,中国共产党不一定是处在即将崩溃的危险中,但是它却面临严重的治理危机①;后者认为,中国国家结构仍具有相当程度的弹性与适应性②,两者聚焦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可持续。
针对上述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两种争论,转换成现实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发展逻辑议题,即从缘起于革命年代、定型于改革年代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具有典型的结构性依赖特征,能否成功建构国家治理的制度性认同决定了中国能否有效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从应对国家体系的外部风险与解决内部问题两个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中国日益融入全球治理的进程,越来越需要建构稳定的制度性认同,适应现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发展趋势,一个具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化、回应性、有效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与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条件。
一、制度性认同: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现代国家不仅包含对法律的共同认识和一致利益的观念,还包括蕴含共同利益的政治制度,这些制度赋予共同目标新的意义,因为政治制度是道德一致性与共同利益在行为上的表现,政治制度的形态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治理结构与治理绩效。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三大基本特点:“以现代社会为基础,以构成国家的每个人拥有政治平等的政治解放为历史和逻辑前提;以现代国家主权为核心,以建构全体人民能够共享并获得发展保障的国家制度体系为基本的组织框架;以公民权的保障为机制,将社会的全体成员聚合为具有共同纽带的共同体。”③只有以社会、国家和公民权保障为中心,建构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同制度层次,并形成一套稳定和有效的制度体系,进而有效地产生稳定而持续的国家认同,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因此,构建以制度性认同为核心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因素。
从制度性认同蕴含的层次看,现代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两类属性与分层的认同形式,具有双元结构④:一类是归属性的国家认同。指公民对同胞-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这是公民文化-心理归属的国家/民族认同;另一类是赞同性的国家认同。指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赞同、支持,即公民在将自己视为公民-民族成员的基础上,基于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有所肯定所产生的政治性认同”⑤,这两类认同分别依托于不同的制度层次与制度形式。现实中这两类认同常会产生紧张关系,因为,“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和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⑥在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集中表现为:不同的国家认同需要塑造上述两类公民身份与公民行为,两者在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交叉与融合造就了现代国家的治理形态。
第一,宪法体系主导国家生活塑造一种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正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对所有的公民都保持开放状态,使得宪法体系为公民提供政治-法律上的开放性身份,因为,“在多元社会中,宪法表达的是一种形式上的共识。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系列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⑦宪法渗透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塑造了形式上与实质上的现代国家。通过宪法体系确认了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公民与共同体的新的文化-心理身份,塑造了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归属性国家认同。同时,运行于宪法体系下的一套法律体系也在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使得公民认同指向一套国家制度体系,依托于宪法体系生成两类不同身份的国家认同,使得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趋于成熟和稳定。
第二,政治制度满足公共需求促成一种赞成性的国家认同。除了宪法塑造混合型国家认同外,政治制度化的过程能否满足公共需求,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国家认同的实践效果,“制度的精进与否遂成为合理爱国心与合理国家认同的最佳指标。”⑧因为,制度不仅塑造公民的政治行为,也确认与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进而生成赞成性的国家认同。这是现代国家认同的制度基础,相比归属性的国家认同,赞成性的国家认同比较容易实现,它已经成功突破民族的心理界限与地域的地理界限,在一个新的公共空间中塑造了一种共同的与平等的政治-法律身份,它基于普遍化的政治制度化过程,将传统的特殊治理方式转换成一种现代与平等的国家行为。
第三,国家福利的一体化建设塑造一种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对于国家而言,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决定基础层面的国家认同,而归属性的国家认同则是一种更高层面的心理认同,不仅取决于国家制度的满足情况,还需要公民对国家形成结构性的依赖与支持关系,而现代国家福利的一体化建设构建了这种持续性的结构化关系。“一个全面覆盖而富有成效的国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将极大地提升公民日常生活的质量和抗击社会风险的能力,从而强化公民对国家的依赖与信任,推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⑨因为,从现实来看,建立一体化的国家福利体系能够实现公民的心理安全与文化需要方面的满足。
上述以政治-法律的公民身份形成的赞成性的国家认同、以文化-心理的公民身份生成的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两种类型,贯穿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两种认同在国家治理层面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种制度性认同。因而,对于像中国这一类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构建一体化的、稳定的与系统的制度性认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向和发展特征。
二、结构性依赖:中国传统“政党-国家”体制的治理逻辑
国家的治理结构与形态取决于时空等综合要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国家治理模式决定其政治运行特定的优势、负荷、困难和挑战。国家治理模式不是任意选择的,常与国家的历史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关系,中国国家治理的历史基础、转型条件与现实需要三者共同决定当前的结构形态。中国国家治理涉及三大主要内容:一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般性规律与发展特点;二是社会主义因素及其政治体制对中国国家治理的约束;三是传统文化因素对中国国家治理、转化与继承的影响。这三大因素形成一种复杂的结构性约束路径。但是从决定性程度看未来中国国家治理如何转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政党-国家”体制的结构性依赖特征的影响和支配。
中国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源于革命的行动和逻辑,并形成对应的集权式国家治理结构。从制度学习的来源方面看,这种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是与对苏联共产主义体制的模仿与借鉴有很大关系。在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体制中,国家被建构成为一个具有高度权威与权力的政党领导下的全能主义型的控制体系,通过控制与支配市场、国家、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生存与发展资源,形成以政党领导为中心的一套国家治理模式的支持性结构。“政党科层、国家科层、国有经济以及结构内可供攫取和分配的资源、政党科层与国家科层包括经济之间的互联线、可用于更深地融入该结构的结构性反馈”⑩,这种政党领导国家的政治逻辑在中国国家治理的实践中主要生成四类嵌入的结构关系⑪:与国家系统的“政策领导”或“执行合一”关系;与社会领域的“有限控制”与“选择适应”关系;与市场经济(主要指国有企业)的“人事嵌入”与“权力支配”关系;对价值体系的“大众引导”与“选择收缩”关系。
相当长时期内,这种政党与不同领域之间嵌入式的支配关系,是决定中国国家治理的结构性基础与体制性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国家治理行为与模式的改革则是对这一体制进行变革与优化。尤其是拓展到执政党内部的改革,政党执政重新制度化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政治方面进行“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体制”的政治建设计划⑫,这个过程分别在国家发展模式以及行为方式方面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类“发展型政体”⑬,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产生新的社会阶层,中国共产党通过适度开放意识形态领域和增加体制的包容性,与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进行持续的沟通融合,个人与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国家体制表达利益诉求和在公共政策导向中形成特定的政治偏好,有限度地吸纳社会力量。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特殊主义和政治化的利益诉求又是受到限制的,从而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这就分别在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国家治理的不同层面,形成了特定的模式与结构。
第一,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对于发展型国家而言,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成就,从发展策略及其成型模式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发展型国家的大部分特征。中国依赖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与发展机遇,特定阶段中形成了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事实上形成了一套实践性较强的经济政策适应机制。既突破传统政党-国家体制内意识形态的硬约束,也没有为自己设置特定的制度性框架。在不同区域和不同领域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而且,这些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缘起于灵活的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而非中央政府事先有意识的政策设计⑭,这是中国成为发展型国家的重要特点之一。然而,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留下了后遗症,尤其是政府行为的企业化取向,将官员的政治经济利益和市场化改革紧密联系起来,容易形成不正常的政商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区域快速发展与官员腐败的高度相关性。
第二,有限度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⑮治理方式。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必然产生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和参与需求,面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时,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策略不一样。其中,新生的社会阶层如私营企业主群体是其重要的吸纳对象。新社会群体在经济方面的崛起必然会反映到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方面,参与政治过程,与体制进行合作成为一种常见的形态。因此,处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治理战略和策略,需要考虑“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阶层的社会与政治功能”⑯的现实问题。因为,从建国以来的传统政商关系看,企业家只有当他们(或许也包括其他阶层)被“嵌入”政党-国家体制中,而不是与之分离时,他们才会感到安全⑰。针对新生社会阶层与社会力量,他们与国家之间是一种适应的依赖与监管关系,因为它们不断增强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力,所以“企业家阶层”成为国家体制吸纳的重要对象,并在政策与社会地位方面得到优待和享有特定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参与通道,同时,这种依赖与保护型的体制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他们进行监管。
第三,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上述经济、社会两个领域的国家治理过程表明,传统的政党-国家体制形成的结构性依赖特征已经发生变迁,既利用原有体制的结构性依赖关系,在经济与社会领域有限度地进行变革,并逐渐形成新的国家认同模式。同时,这种新模式并未完全瓦解原来的结构性依赖关系,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模式。一方面,中国的普通公众因经济发展绩效产生新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能否形成长期与稳定的认同关系,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绩效的持续性。同时,这种认同会部分转化为赞成性的国家认同,但是,要形成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应的支持条件。另一方面,针对社会领域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公民对国家的体制性依赖与心理归属都存在,但是能否通过制度化过程促使公民形成稳定的政治-法律身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众在文化-心理层面认同的巩固。
在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中,上述三类领域的国家治理形态,主要是通过强化中国共产党与经济治理、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的现实关联性实现的。从体制与现实两个方面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是优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的核心问题,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同时期改革的中心议题。因而,通过怎样的战略与策略塑造中国国家治理的新模式,关键是如何将基于传统革命逻辑形成的政党领导结构、后来高度体制化的领导结构,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形成适应性的制度化关系,进而转化为高度稳定的国家政治认同。从当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来看,尽管革命秩序下的中国国家治理模式正在深度变迁,但是国家秩序赖以生存的核心治理结构仍然完好地保持。中国共产党通过重新塑造组织系统的“吸收”战略,形成一个使中国共产党得以重建、维持执政地位的“适应的非正式机制”的变体⑱,它依赖于执政党领导与治理的结构及其治理绩效,这种治理逻辑仍是支配当前与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与关键。
三、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征
一定阶段中,中国国家治理需要依赖经济治理的绩效,但是,从制度性认同的角度看,长期的国家认同依托于优化国家治理体系与提升治理能力,两者的协调性关系主要涉及三大关键性因素:一是国家权力属性的现代转变;二是国家权力的体系性与制度化的结构安排;三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协调性。现代国家发展的历史与实践表明,国家治理模式是自上而下分层的,它是在巩固公民的国家认同过程中走向成熟与完善。这种分层分别形成四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认同:国家主权与宪法认同层面、文化信仰与价值认同层面、法律和制度认同层面、福利与政策认同层面。对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法律与制度、文化与价值层面的认同要先于其他两类,其中国家主权与宪法认同早于福利与政策认同,这一类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然而,对于处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几大要素的构建被容纳进同一个时空中,建构整体的国家认同与优化国家治理模式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
从建构国家认同的角度看,现代国家治理必须是国家制度建设与国家结构体系优化的有机统一。国家结构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关系是制约中国国家治理的核心矛盾之一。在民主成为国家治理重要目标的前提下,国家制度建设必须要围绕优化国家结构体系展开⑲:以提升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优化国家治理结构体系;同时要通过国家治理结构体系的整体优化,稳定与巩固国家制度,民主才有可能成为有利的国家治理因素,进而成为正向的治理资源。从优化治理的路径看,毫无疑问,现实问题——对应性改革措施——系统性顶层设计的逻辑关联是优化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治理思路⑳。中国的国家建设主要包括横向的公共授权体系和垂直的政府体系两大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府和公众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中国共产党和社会力量这三组治理结构之间的关系,在现实中能否形成有效的治理能力,宏观层面取决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大关系的结构化与制度化的现实形态。对于超大规模的中国社会,利益代表的逻辑与实践过程就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政治治理结构上要充分塑造与完善各项制度的结构与功能,使政治治理结构与多元的经济社会治理需求适应,将多元的社会利益转化为统一的行动。从实践角度看,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已经具备了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与共识性。治理价值的文明化是现代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对人类共同体生活与优秀文明价值的追求是现代国家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一般情况下,对于一个正常的国家而言,成熟的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的输入与转化之间不存在本质矛盾。有选择地学习与融入以西方国家为表现形式的成熟的“国家产品”,及其背后的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有助于中国更好地融入人类文明与现代化的进程。这并非要将中国政治秩序西方化,而是要在制度治理与秩序建构方面,为变化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律。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与大众化是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因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要兼顾一般发展规律和中国的主体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兼顾与均衡二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国家治理体系、国家制度之间形成契合与支持的关系,价值层面既要凸显国家治理的主体性,同时,实践层面制度体系要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因而,意识形态领域内复合式的引导与治理十分重要。
第二,公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因为现代国家的两大治理主题即发展与秩序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正在探索一条更安全的政治改革之路能带来更多责任、透明度和回应性的制度改革,由此构建更有效、更具合法性的治理体系。”[21]民主执政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大目标之一,治理体系民主化与治理结构的透明化是同一过程的两面。法律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与机制保障公众能分享政治决策权。虽然,治理有效与否和民主之间并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要解决权力过大导致的治理失效问题,必须要依赖民主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过程。民主治理不仅需要拥有共同的制度平台,还需要基于多元利益和平等的对话协商的机制。以当前中国的公众参与现状而言,依托于政治制度与组织构建适应中国国家发展需要的政治治理结构是关键。因为,民主政治中有机会参与到协商活动中的行动者接受集体决策,这是合法性的核心,是合法性表达的开端。[22]制度化的公众参与能够塑造有序的公共生活,通过民主参与治理的技术手段,不仅能提升官僚体系的理性化程度,也在塑造一种新型的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形态。
第三,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技术化。从制度化角度看,现代化过程中成熟的国家治理模式应该是建立了政治主体与环境之间稳定的制度化关系。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了一个从总体支配向技术治理[23]、从直接治理向间接治理转变的过程。在行政体制内部集中表现为一种“治官权与治民权分设、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24]。这种结构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官僚体系内部的弹性与地方创新,但是,也造成了实践中地方政府或部门主义的权力过大的乱象等问题。权力责任清单的生成是其理性化与技术化的集中表现。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与四中全会决定针对这一突出的现实问题,从重塑官僚体系的权责关系出发,围绕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化与技术化趋势,通过司法改革启动以程序主义为中心的官僚制的改革。因为,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不仅对界定复杂社会中的利益、决定这些利益的活动战略发挥重要作用,保障规范公共权力和保障社会稳定在法律方面的公平正义。
上述三大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发展特征,从实践层面看,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绩效不仅依赖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协调,更依赖国家、社会与公众间的复合治理形态。复合治理的特点是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的协调关系和权力的多维运行,将中国的政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等形态有效结合起来,塑造自律型的政党治理是关键。制度性认同主要是通过不同层面的治理结构,实现国家公权与个体私权间稳定的制度化关系。中国在国家层面的建制化进程不仅取决于制度化的基础,更取决于在治理体系内部形成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凝聚力和整合情况。一般而言,处于转型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一种暂时的过渡性政治权威的需要是存在的,关键是能否将对权威的依赖与服从关系转移到制度体系上,形成稳定的制度性认同结构。制度性认同对于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的积极影响已是基本常识,因为这种依赖是最稳定和持续性的。
四、制度性认同发展进程中中国国家治理的价值维度与支持性条件
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主导国家治理的核心因素,它决定中国国家治理的过程。“东亚社会一般都有一个弱小的‘市民社会’:很少独立于国家或有能力向国家提出要求的有影响和有力量的第二团体……东亚社会确实有走向非个人化的合理性的要求;但在许多方面,这个地区的现代化选择了另一种路径。”[25]东亚区域内的国家不可能发展为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不同的国家发展路径塑造了不同形态的治理体系与治理制度,更确切地讲,“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26]这些制约性规则是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普遍性共识,并在国家内部塑造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因而,要完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价值原则、制度规范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旧有关系形态,进而重塑与优化一种新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关系形态。
1.制度性认同进程中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维度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能够解决国家组织结构与制度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即将现代国家与人类的基本价值合理地嵌入特定的历史、经济与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内化为公众的日常行为习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与推动发展的背景下,深度了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的价值导向、行为变迁及其发展重心,尤其是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在价值层面需要解决的特殊性问题,它们共同决定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内在特质与未来走向。
第一,善治原则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外的转化与运用。中国语境中的治理是“运用权威维持秩序以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7]通过中国学者们的本土化努力,传入中国后的治理概念以及变形后的治理理论,成为正在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有效治理工具。善治概念的价值导向既为中国的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提供了伦理支持,同时,通过社会力量介入国家治理与政府治理的过程,既调整了政府与公众间的治理结构,也缓和了公众和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的国家治理通过在价值导向方面塑造公民对国家层面的制度性认同,善治原则及其过程提供了一种现实的可能性。
第二,重新制度化塑造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协调性。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当前与未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有明确的发展定位:“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8]从目标、维度与特征方面明确了国家治理有效性、制度治理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关联性,同时,突出制度治理的有效性是当前决定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核心问题。围绕现代国家治理的技术层面、民主层面和法治层面的发展导向,从重新塑造执政党、国家机构、社会力量以及公众各自的权责体系、以及相互之间新的治理关系出发,优化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主体关系,从整体上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能力,形成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趋势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第三,塑造一种新政治伦理与建构公民对国家的一体化认同。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两者结合的方式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属性、形态与实践形式。从国家治理的思想层面看,与现代政治发展契合的价值伦理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发展导向。这种伦理是政治精英层面对国家治理及其权力的一种整体规划,“统治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与对国家整体性的思考紧密相关。”[29]对国家整体性的思考是建构公民对国家的一体化认同的前提与基础,新政治伦理的形成不仅依赖于上述重新制度化塑造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间协调关系的结果,而且公民对国家的一体化认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新伦理。同时,建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也是塑造新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时期,重新制度化的过程塑造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以及文化-心理身份,生成公民对国家持久的政治认同。
2.制度性认同与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支持性条件的培育
当国家治理打上文明模式的烙印时,中国国家转型的结构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往往是迟缓的,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适应性难题。只有从国家治理的一般趋势与中国的特殊内涵两个角度考察,摒弃国家治理的中西对峙的二元思维,在接受、融通、学习与转化中,促使中国的国家治理朝着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方向发展。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的三维角度看中国的国家治理,“轴心-外围”的政党领导结构与中心治理路径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点。国家治理中的制度性认同一般依赖于两大社会类资本的构建,一是结构性社会资本。通过规则、程序以及惯例建立某种社会网络,赋予确定的组织角色,促进信息分享,达成集体行动,制定政策,形成对国家的特定性支持;二是认知型社会资本。通过共享的价值观、规范、信任、态度或信仰等,影响个体的行为选择,形成对政治体系的普遍性支持。前者依赖于后者的心理与文化基础,后者又建立在前者形成的制度性规范与认同基础上。从培育制度性认同角度看,无论是价值导向还是过程结果都需要相应的支持性条件,主要有四大关键性因素。
第一,塑造与优化现代公民教育体系。一个成熟的国家治理体系保持其社会、思想与国家的一体性是国家认同的基本任务,“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30]这种整体性不同于革命年代国家与公众间的关系,也区别于改革之初通过经济绩效塑造公众对国家的结构性依赖,而是将正在不断伴随着经济社会变迁的公民教育定型化与公共化,将公民对国家的认同引导到稳定的制度性认同框架内。前述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现代公民教育是塑造现代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体两面,没有理性的公民教育体系,也就难以有效运行理性化的官僚体系。
第二,提供一体化的福利保障体系。当前中国国家治理领域中引发诸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诱因是公民权与公民福利保障缺失。结构性依赖的国家治理结构下,中国国家领域内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结构存在主体单一化的问题,导致治理过程容易出现公共权力的权责失衡,国家责任的“缺场”与政府责任的“缺位”十分常见,造成中国公民的政治-法律身份塑造出现困难,难以生成赞成性的国家认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建立适合国情的一体化的福利保障体系与网络,从国家认同层次看,一体化的福利保障体系是公民认同的基本物质条件,为公民的政策认同提供现实基础,进而才有可能产生制度层面与更高层次的认同。
第三,培育与生成现代理性的公共空间。上述现代公民教育体系只是塑造理性公民的一个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对于国家认同而言,治理体系内部的权力结构均衡对公共空间有更高要求。因为,“一种潜在的、参与性的公民对精英的自主施加了有力的限制。这些限制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逻辑要求(呼唤)越来越多样化的、富有知识的、复杂的、要求严格的公民。”[31]公共空间是训练与培育“公共人”的必备条件,现代国家治理过程提供稳定与畅通的沟通制度与渠道。理性公共空间为理性化政府与公民提供长期联系的纽带。
第四,网络化的治理技术嵌入国家治理。从形式上看,现代国家治理必然也是一种网络化的治理形态。任何投身于集体行动组织都需要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进行资源交换和合作实现共同目标,于是网络者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和基于规则的互动模式。[32]处于不同社会网络与政治网络中的个体,通过现代信息技术被“网罗”成相互交织的独立主体。既改变了国家治理领域内不同主体的交往关系,也塑造了一种立体式的治理需求网络,为现代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可供利用的技术资源与治理形式。
综合看,中国从结构性依赖的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国家治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制度性认同是解决中国实践中的发展问题的关键,也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有效治理路径。鉴于中国实践中已经出现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和局部特征。如何形成一体化的现代国家认同,重塑制度与建构认同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体两面,对于超大型中国的国家治理而言十分关键。
注释:
①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81,No,5,2002,pp.96-109;Minxin Pei,Beijing Drama:China's Governance Crisis and Bush's New Challenge,Policy Brief,No.21,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
②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
③⑲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
④肖滨:《两种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双元结构》,《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⑤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6页。
⑥[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5页。
⑦[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三联书店,2003年,第660页。
⑧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10页。
⑨李友梅:《社会认同:一种结构性视野的分析——以美、德、日三国为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第16-17页。
⑩[匈]乔纳蒂:《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⑪丁长艳:《现代化转型中国家治理的风险治理与秩序建构》,《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⑫Joseph Fewsmith,The Communist Party in Evolu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40th Anniversary Conference of the 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er,Hong Kong.January 2003.
⑬Pempel,T.J.,The Development Regime in a Changing World Ecomomy.In Meredith Woo Cumings ed.,The Developmental State.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⑭So,Alvin Y.,Rethinking the Chinese Developmental Miracle,in Ho-Fung ed.,Chin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9.
⑮Kanishka,Jayasuriya.Beyond Institutional Fetishism from the Developmental to Regulatory State,New Political Economy.2005,10(3),p:381-87.
⑯[德]海贝勒:《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
⑰Bruce Dickson,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⑱Kellee S.Tsai,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The politics of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7.
⑳程竹汝:《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1][美]戴蒙德:《评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2012年第1期。
[22]John S.Dryzek,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143.
[23]梁渠东、周飞周、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4]曹正汉:《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及其稳定机制》,《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25][美]霍华德·威亚尔达:《非西方发展理论——地区模式与全球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6页。
[26][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页。
[27]俞可平等:《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1页。
[28]习近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华网2014年2月17日。
[29][法]皮埃尔·卡蓝默等:《破碎的民主——试论治理的革命》,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第14页。
[3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524页。
[31][美]贾恩·弗朗哥:《国家:本质、发展与前景》,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第78页。
[32]Stoker,Governance as Theory:Five Proposi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Journal,Vol.50,1998,p.1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