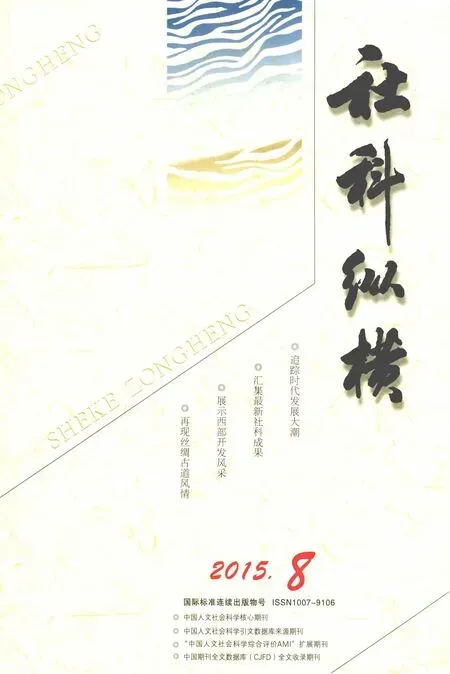豪门叙事与都市现代性的隐喻:《上海的金枝玉叶》与《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之比较
丁 琪
(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天津 300191)
陈丹燕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怀旧热”的一位主要推动者,林希是当代津味小说“双帜”之一(另一个是冯骥才),非常巧合的是二者在1999年先后推出了都市文化系列代表作,即陈丹燕的《上海的金枝玉叶》与林希的《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两部作品都运用“城与人”相互指涉的文学构思模式:豪门贵族的命运沉浮映现着城市文化的历史与未来,金枝玉叶的绽放与凋零讲述着一种地域文明的前世今生,这种共同的隐喻思维使南北两位作家不期然的邂逅在类似的命名中。然而一位被认为是具有中产阶级文化特征的“小资教母”,一位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走来经历了时代剧变与政治风波的文化启蒙者,他们对现代化发祥地的南北两个大都市有怎样的文化共识与认知差异,他们的作品在哪些层面可以对话和交流,这些相关问题对当今的都市文化与文学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城与人”的隐喻思维与东方史诗特征
上海和天津在近代相继开埠通商,从而开启了早期的城市现代化进程。接近百年的殖民历史形成了两个城市中西合璧的文化特征,也孕育了具有相似文化特征的都市文学。早在上世纪30、40年代上海和天津就成为南北派通俗文学的重镇,涌现出了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等一大批擅长描写市民生活境遇的通俗小说大家,海派和津派的文学旗帜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树立起来。80、90年代这种渗透着地域文化的都市文学思潮在对现代性的追逐中重新抬头,陈丹燕和林希就是当代海派和津派都市文学的代表。陈丹燕因为一系列书写老上海的作品备受关注,其中《上海的金枝玉叶》是她的都市三部曲之一,讲述了上海永安公司郭家四小姐黛西在历史大变迁中的命运沉浮:六岁的时候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跟随父亲从澳大利亚回到上海,1930年代在家族鼎盛之际经历繁华旧梦,1949年以后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变得一无所有,1990年代在一个人的独居生活中旧梦重圆。尽管生活大起大落,但黛西始终安之若素、不惧不惊,以难以想象的坚韧和宽容展示着一个大家闺秀的气质和尊严。因而作者送给她的挽联是“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1](P 263)林希在同一年推出的《天津卫的金枝玉叶》同样讲述了一个津沽世家的衰落和少爷小姐们的命运遭遇,一个津城豪富之家在历史动荡中渐渐涣散,然而家国不幸却激发了金枝玉叶们的坚强品质,有的为民族解放走上革命道路,有的为匡扶一个完整的家庭牺牲着自我,这里的金枝玉叶不仅指那些出身高贵的人,而是泛指一切表现出高贵品质与人性光华的年轻生命,如母亲的贴身丫鬟桃儿,她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坚强勇敢以及对六叔萌之这个革命青年坚贞含蓄的爱情,都散发着金枝玉叶般的华彩。可以看出这两个作品都是以“人”的悲剧命运为结构线索,在豪富之家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清晰的展现财富、权势、完美、高贵等完整的东西被历史的浪潮撞得七零八落的悲壮情景,因而“豪门叙事”渲染的不是都市豪门的财富和权势,而是展现人在失去这些东西之后显现的高贵人格。
由于创作者的地域文化自觉,两个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核心的文本都内含着“城与人”相互指涉的隐喻思维,以“人”的成长与命运勾勒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孕育着独特的地域性格与文化心理,探寻二者之间的传承积淀与历史突变乃是这类作品的重要主旨。陈丹燕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上海精神”的芯子,她曾说:“我对别人笔下的上海没有意见,我自己笔下的上海,是为了挖掘这个城市的精神,我认为,这是这个城市最容易被遮蔽,也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在它的混乱,嘈杂,时髦,欲望,梦想,失败,迷失,奋斗,林林总总之下,有一种恒定的、宽广的、痛苦的、公允的东西存在,我想那就是我要寻找和表现的这座沧海桑田的东方城市的精神。”[2]城市的精神沉淀在城市历史里,体现在一个个人物的命运中,她就是要挖掘出这种城与人缠绕生长中的“上海特性”。林希的小说创作也浸透着浓郁的天津味,他的市井小说和家族系列都意在重塑天津文化。他认为天津文化的精髓是基于海河地理和独特历史形成的一种兼容并包的地域文化,天津人的性格融汇“北方人的粗犷豪爽与南方人的精明干练”,同时还兼具本土码头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3]但是他不满意文学对天津精神的表现,“老实讲,天津的地域特色和天津人的文化心态一直没有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公正的反映,多年来不少人写天津,但都写天津的粗野、蛮横和愚昧无知,虽说有人也曾将此类作品称之是津味小说,但这类作品不具有较高的文学品位和较高的文化品位,所以也就不具有艺术魅力……”[4]强调对城市表现的文学品位和文化品位的提升,是对文学审美表现力和思考深度的高要求。因而作者沉潜在城市历史深处,观察那些特定的历史进展和社会转折如何锤炼了天津人的性格与文化心理,并把这些思考化作一个个鲜活丰满的文学形象,试图在文学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复活一个城市和那些顽强的生命。
创作者强烈的地域文化自觉以及南北两座城市共同的殖民历史背景形成了两个作品共同的“东方史诗性”的美学追求。上海和天津都因为殖民历史而较早的开启了现代化城市进程,都市豪门以社会地位和财富的优先性较早地享受到了西方文明的成果,无尽的财富、特权、便利、舒适,但是在经历了物质的奢靡繁华和生活剧变之后他们都坚守着东方民族的精神气韵和价值操守,并以此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磨砺出珍珠般的光华。基于这种整体文学象征,作者都退回到民国历史中来展开金枝玉叶们的命运,作者需要在那种多元文化激烈碰撞、无序竞争中凸显出历史结构性的文化支撑,在西方文化最为强盛、霸权地侵略到东方古国的历史时刻找到中国历史与城市的心性,东方的、民族的、城市地理的情感和价值观念得到了最为完整生动的呈现。
陈丹燕笔下的黛西小姐骨子里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性,虽然童年在澳大利亚度过,回到上海后一直生活在父亲以雄厚资本创造的摩登世界里,她的语言、教育背景、生活习惯都已经西化了,但作者突出她的思想信仰和文化根脉却在中国。她终生只穿中式服装,这不仅是一个审美习惯,还表明了自己的精神寄寓和文化立场。她凭着东方女性的坚韧和宽容美德接受了一切磨难,这包括1949年以后接踵而至的丧夫、抄家、劳改、文革中被羞辱和打骂等。经历大风大浪之后她依然热爱中国和上海,直到晚年也没有随兄弟姐妹和后代移民海外,八十多岁还靠教授外语独立生活,在上海弄堂的一间屋子里度过一个人的晚年,面对别人不解的询问,她说:“我是中国人”[1](P263),“我的整个生活在上海”[1](P251)。她的坚强勇敢、不抱怨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美德,她表面的西化生活方式背后深藏着对于国家与故土的眷恋,而她表现出的这一切都是作者要挖掘的上海精神:在摩登时尚中透着一丝传统的精致优雅,在混杂拼接中联结着坚韧和密实,在殖民西化的情调装饰下埋藏着东方风骨。在林希的创作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比附关系,金枝玉叶们的命运映现着天津“九国租界”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内外交困中自我救赎。府佑大街的侯家大院是遵从儒家伦理的津门望族,随着近代天津开埠通商这个家族逐渐走向了“买办之家”,大家族的爷爷和父亲都依靠在外国企业做代理而给这个家族带来经济利益和数不尽的财富,但金钱和利益也带来了奢靡和堕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这个大家族土崩瓦解失去道德约束力。随之而来的是血腥的民族战争,是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你死我活的领土争夺。这个时候,民族和国家的正义以及人性光华在这些侯门子弟、金枝玉叶中显现出来。“我”母亲在见证了这个大家族的败落、忍受情感打击之后仍然坚信“人类爱人的天性是不会泯灭的”,她仍然以一己之力保护她的丈夫、孩子、侄女、仆人,无论自己遭受多少经济损失和情感创伤,她都无私无畏、无怨无悔地付出。母亲象征着这个买办之家的传统文化肌理,代表着东方文化精髓在西方文化入侵时的强大的生存能力。包括桃儿、菊儿以及我的六叔萌之、松哥这些在豪富之家长大的金枝玉叶,他们都体验过租界小洋楼的西式奢华生活,但是都恪守着中国诗礼之家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堂堂正正做人的伦理价值观和传统美德。
由此可见,大都市里的“豪门叙事”是对一个世纪以来东西方文明等级观念的一种质疑和颠覆,这种文明等级观自从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以来一直存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曾指出的,“所有的文明一个一个地承认它们中的某一个具有优越性,这个优越的文明就是西方文明。”[5](P37)它助推了落后国家的文化殖民和同质化现象,挤压一些弱势的部落文化和差异性文明几乎失去了生存空间。当然对这种文明等级观念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的地域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同时觉醒便是质疑和反抗的表现,陈丹燕和林希的作品就是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讲述东方城市和民族的史诗,是在东西方文化激烈碰撞交融时期对东方文明特征的重新历史化和审美化。因而陈丹燕的上海怀旧不是简单地怀念过去,而是应对新时代背景的文化前瞻,林希的津味也不是简单地写天津,而是以天津为镜像反观民族与与世界的对话,他们都有全球化的宽阔文化视野和文明多样性的思考深度。
二、重塑与检视:两座城市中投射的情感价值差异
产生在同一个时代与历史背景下的两部“金枝玉叶”,读来感受更多的是作者讲述方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上海的金枝玉叶》采取的是个人精神史讲述方式,以编年体方式结构章节,每一章以老照片为线索讲述黛西的精神成长史,同时作者习惯把不同年代的故事与感受交叠在一起来增强人物精神性格的饱满度和立体感。这种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调动了大量精美图片配以诗意的解释文字的呈现方式十分新颖前卫,突破了传统文体界限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文体形式的先锋实验性质与传主“黛西小姐”表现出的文化多元、深邃神秘的精神境界也十分协调;《天津卫的金枝玉叶》则运用家族小说模式,是有一定历史原型的虚构性小说文本。与个人传记的一个中心人物相比,它是群像式的时代与社会的“史诗性”呈现,从年老的家仆到年轻的侍女,从父辈们荒淫无度的奢侈生活到家庭青年叛逆者的革命之路,从捍卫传统儒家伦理的大少奶奶到热心公益、走向革命前线的新式妇女,不同人物代表不同的文化立场,不同文化立场的碰撞交融构成了一个色调丰富多元、交错重叠的大时代。以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展开一个时代的生活细节,品味一段动荡历史中糅合的振奋昂扬与伤痛滋味,应该是这个具有历史感的家族小说追求的微观美学。因而它雄伟恢弘的家族史诗结构下是细腻的家庭生活和情感描写,是对各色人物的鲜活刻画。
除了文体与讲述方式不同,最根本的还是作者对待上海和天津这两座古老而现代的城市差异化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念。《上海的金枝玉叶》中作者以城与人的比附关系重塑了老上海的魅力,它华贵、精致、典雅、开放、多元、时尚,一如那个中西合璧又风华正茂的少女黛西。作者借助她的生活经历描写了大上海南京路上的新潮百货公司,详尽介绍享有盛名的新式贵族学校“中西女塾”,1930年代才子佳人在私家花园草坪上的浪漫订婚仪式,以及贵妇们如何准备一顿丰富的西式早餐,在有着薄薄的阳光的午后在淮海中路逛街购物。作者还借助黛西的生活说明这座城市的富裕豪华没有使金枝玉叶们沉沦堕落,反而练就了他们抵御诱惑的能力和成熟的思想气质。“有时候,真的让人怀疑,是不是一个人的品质是童年生活中就确立了的,而且很可能,富裕的明亮的生活,才是一个人纯净坚韧品质的最好营养。”[1](P23)黛西人到中年之后经历的风风雨雨一如上海这座老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相同的是他们都以宽容开放的胸怀安然处之、淡定自若。作者由衷的赞美黛西,也深切怀念与之相似的老上海城市精神,借助城与人的融合表达了她温情脉脉的中产阶级文化认同观念。“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含混的概念,并且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涵义不尽相同,它既可以指涉遵循特定文化价值规范的社会富裕阶层,也可以指涉那些在吃穿用度以及闲暇娱乐方面讲究的普通市民。当代文学提供了一整套关于中产阶级生存状态的想象,“这些想象包含着对丰裕的物质生活的追求,也覆盖着诸如体面、品位等精神价值,甚至还勾连出了对日常闲暇时间的令人兴奋的规划”,[6]在陈丹燕笔下,上海这座城市具有这样一种“中产阶级文化特征”,它算不上多么高尚,但精于实际生活的追求,她以充满灵性和睿智的笔触在营造着“中产阶级文化”氛围的城市,描绘着那些与之气质相匹配协调的古老建筑、富家小姐和上海故事,作者、主人公与城市三者之间已然形成了相互映衬的稳定统一的认同情感和价值观念。
但是在《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作者对他所塑造的人物以及城市文化特征有一种严厉的解剖和审视,他以那些充满了矛盾性格和时代弱点的“金枝玉叶”们来凸显一个并不完美的都市与时代,它充满了混乱、嘈杂、阴谋、欲望、拜金,连同那些华丽、精致、革命、激情、文明一起,构成了一个近代“九国租界”时期藏污纳垢、鱼龙混杂的旧天津。作者摒弃小资情调坚持文化精英立场和启蒙姿态,并且怀有鲁迅式的揭开伤疤、治病救人的批判意识。所以作者以人的弱点来写城市与时代的某种局限,戳穿了传统家族文化、革命以及现代西方文明的种种谎言和虚妄。比如在新的文化观念冲击下传统儒家伦理文化逐渐被边缘化,然而我的“母亲”仍然固执地要维护传统家族的和谐完整;我的六叔萌之、松哥和三婶娘苏燕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但他们的革命道路似乎讲述了革命的脆弱幼稚、功利无情的一面。六叔和松哥只是充满革命热情而手无寸铁的热血青年,他们除了在家庭中爱上侍女或者在学校排演话剧并不能做任何实际的事情,南下参加抗战的六叔萌之面黄肌瘦的回来了,松哥遵从母命没有娶到情投意合的人而是进了富家小姐的“情感圈套”,婚后及其失意沮丧。三婶娘苏燕是思想新潮的女革命者,逃出旧家庭的婚姻牢笼到了抗战前线,通过革命婚姻飞黄腾达之后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敢认,不过是个功利思想严重的革命投机者。在租界里拥有一幢小洋楼成为多少中国人的梦想,因为那象征着财富、特权和西式文明生活。但是作者写侯家搬到租界别墅后,渐渐发现这里隐藏着中国军阀政治的仇恨、中国民族商人的穷困潦倒和他们处于中西夹缝中的尴尬处境。这些描述表明曾经的殖民主义席卷到天津后带来的是畸形繁荣、残酷的战争和影响几代人的心理创伤。林希作品中人物与城市的内在矛盾分裂感、作者无情的审视批判与陈丹燕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所表现出来的温情默默和文化认同有根本区别,这导致两位作者对历史与城市进行了符合他们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选择性的截取、修饰和雕琢,造成了两个城市文化形态的差别,一个精致一个粗粝;一个时尚一个乡土;一个完整光滑,一个矛盾分裂。
三、上海与天津:都市现代性的双城差异
上海和天津在近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将近百年殖民历史,这段特殊的城市经历在它们各自的文学书写中留下深刻痕迹,西方、殖民以及迎拒问题成为文化因子性质的重要介质,环绕流淌在它们各自的文学世界里。“西方”到底是文明、强大、进步的民族,还是野蛮、霸权、凶残的帝国主义,到底中西文明在相互过滤中彼此曲折渗透还是在交错缝合中最终断裂,这样的西方想象有一个历史衍变轨迹:晚清帝国遭受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击后中国的“家天下”观念瓦解,现代世界地理观逐渐成型,西方不再是遥远的极乐世界或佛教圣地,而是一种近代世界关系体系的符号,一种凌驾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非西方世界之上的霸权。之后的历史文献中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全盘西化”的争论从未停歇,依据时代和社会需要而给出不同的回应,正如萨义德所言“东方”“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是西方世界根据自己的利益建构出来的“相当微妙甚至是精心谋划的差异”[7](P16-17),同样道理,“西方”也从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自然”,它有很强的时代、民族和地域认知差异。《上海的金枝玉叶》和《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两个描绘都市现代性的文学作品恰恰说明,即使在同一个时代因为创作主体思想差异和地域区别,对“何为西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充满差异性,两位作者给出了不同的“西方想象”和它对中国大都市影响的描述。
在《上海的金枝玉叶》中,近代的上海充满了殖民现代性特征,即它的都市现代性是西方文明和本土文化的杂交结果,从外在的建筑、街区到内在的日常生活方式、市民的文化心理都发生了融合他者的蜕变,这种融合了宗主国和属地的文化与单一文化相比显得多元、摩登、时尚和国际化。因为这时的“西方”在想象中是先进的政治体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具有普世意义的人文精神的集合体。它对落后的东方民族实施了经济和领土的掠夺,但同时也让东方民族在沉睡中惊醒,揭开了他们轰轰烈烈的现代化进程。被殖民的区域因为对“先进西方”的学习、模仿和借用而对其他落后地区具有话语霸权和文化优先性。被殖民的“上海”这时就成为一个先进、文明、发达、时尚的符号,而金枝玉叶的生活是对这种涵义的细节化和画面性呈现。郭家小姐和少爷们开着豪华汽车在马路上兜风、参加上海小姐竞选和举办时装表演的新潮观念、以及在自家花园身着优雅白裙、笔挺西装的浪漫婚礼,都是这个城市西化的表现,黛西父亲雄厚的经济资本、举家从澳大利亚回来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完整的西式教育培育出的贵族气质,都在诠释一个抽象的“西方”渗透上海之后的具体内涵。当然西方文化并不能取代上海原来的城市特性和民族特性,这也正是作者根据自己文化设想的需要对西方与上海关系想象的另一个层面。上海“西化”的只是物质文明,它镶嵌在城市的表层,而精神上它依然保持着东方性和民族特征,它融化在每一个中国人/上海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它支撑着黛西度过艰难的后半生,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难她也不悲愤、不抱怨,作者认为这个成熟、坚韧、独立的黛西才是真正的她的心,那个青春、华贵、时尚的少女不过是外表。黛西小姐的塑造说明西方殖民文化只是在物质的、外在的层面融进上海,而在精神上、骨子里上海从来都是自己,它有极强的包容性和自我主体性,这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不同于上海殖民现代性的都市文化特征,天津的都市现代性“长期以来呈某种二元对立式的并置状态甚至是冲突状态”[8],即本土文化对西方文明有强烈的排斥和对抗,如历史上有名的“火烧望海楼”,义和团与洋人及教民的流血冲突。“九国租界”在天津相继建立后,更加剧了两种文明形态在地理空间、城市规划、建筑风格、语言系统和阶层的区隔分界状态,一种是老城厢、“三不管”等尊崇中国传统文化和码头文化的华界,一种是五大道、小洋楼所体现的西方现代文明的租界,两者矛盾并存或者是融而不和。在《天津卫的金枝玉叶》中作者是在华洋交错的时代氛围中写了一个传统聚族而居的大家庭逐渐衰落的故事,这个家族具有典型的传统儒家文化特征,它是在与西洋文化、中国新兴买办文化的斗争中被放逐到了时代边缘,但是它一直在顽强的坚守着诗礼传家的古训,不为金钱堕落,不为个人利益出卖国家,在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那个家庭的空架子散落一地,但是它的生命被侯门的金枝玉叶带到了新的时代中去,仍然生生不息。作者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是显而易见的,对这个家族曾经经历的一段西式生活也进行了详尽的描写,作者带着戏谑的口吻在描述一个传统中国家庭的“全盘西化”,但是它只限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其后就是爷爷以“守旧宣言”终止了这场家庭变革,这个供职于美孚油行的总会计师虽然挣着洋人的钱,但要求他的子孙们不能变质:
别以为住到租界来了,我们诗书人家的家风就要改变了,不能够。我们说仁义道德,他们讲平等博爱,这是看似相似,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两种信条,他们对,还是我们对?用不着我们去管,反正我们是不相信他们那一套。[9](P211)
抗日战争胜利后侯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回府佑大街的老宅院,作者以居住空间的感受表达了对殖民文化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中“西方”是物质层面的刻板、异样、单调,它们的侵入给这个城市带来了灾难、战争和心理恐慌,因而传统与“西方”是互不相容的隔膜甚至是斗争状态。
上海的郭家和天津的侯家一样都是大都市的豪富之家,都有雄厚的资本在这个城市里过他们想要的生活,但是郭家处处新潮,侯门却总是固执守旧,其实是反映了在殖民地环境中都市“现代性”诉求差异,对于对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认知,一种是认同,追求文化共性与融合;一种是认别,强调差异与自我。因而在中国近现代城市史上上海与天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着都市现代性发生的复杂经验和多种可能,它们各自的都市文学本文参与了这种复杂经验的描述,带着创作主体的各自人生阅历、差异化的思想观念和美学趣味重新建构了一座城市,并在城市历史与想象之间建构了一套新的历史发展逻辑和文化意识形态,在全球化与地域文化激烈争夺城市空间的时代背景下,他们意在回顾城市的过往,以谋划城市的未来。
[1]陈丹燕.上海的金枝玉叶[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9.
[2]陈丹燕.城与人——陈丹燕自述[J].小说评论,2005(4).
[3]林希.天津离精神大都会尚远[J].小康,2007(9).
[4]林希.津味小说浅见[J].小说月报,1992(9).
[5]列维 -斯特劳斯.种族与历史·种族与文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董丽敏.“上海想象”:“中产阶级”+“怀旧政治”?[J].南方文坛,2009(6).
[7][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8]藏策.“津味”到底什么味儿[J].小说评论,2008(4).
[9]林希.天津卫的金枝玉叶[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