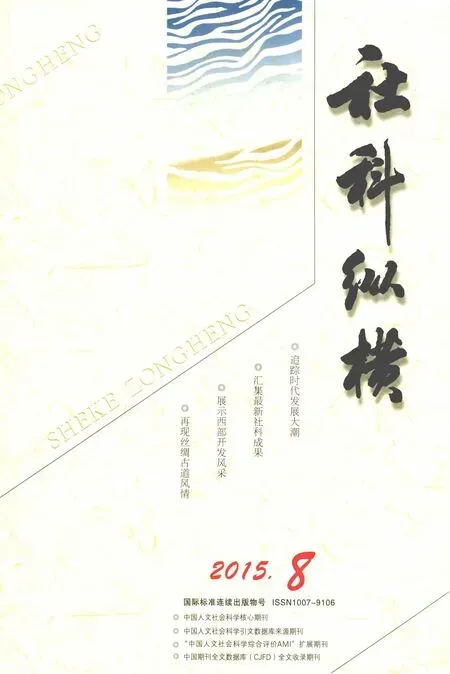移动互联技术影响社会生活方式的新趋势及应对
张丽红
(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所 天津 300191)
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已经有20多个年头了。从最初的培养用户、培育市场,到1997年以后上网人数的快速增长,再到如今网络应用的高度普及,互联网对大众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在潜移默化中不断推进。近几年,移动互联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化、移动化更是全面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大众的社交方式、传播方式、文化方式和消费方式等出现了一些新趋势。把握住这些新趋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使移动互联技术更好地服务大众是当务之急要做的。
一、移动互联技术影响社会生活方式新趋势
1.网络社交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交往方式,但客观上也加剧了现实的人际疏离
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员流动的愈加频繁以及人际信任状况的不断恶化,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际交往变得越来越匮乏,身边能宣泄的朋友越来越少。这样的社会背景,给了网络社交“横空出世”的机会,网络的超时空性、虚拟性、匿名性和网络中地位的平等性,正好迎合了人们对人际交往的需要。它不仅能克服时间、距离的阻隔,还能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身份、年龄、性别、职业等影响人际交往的因素统统隐匿掉,ID代号成为每个人的标识。人们可以依兴趣、爱好组成不同的群落,合则聚,不合立马走人。人们通过互联网交朋友似乎变得轻松容易,一些在现实社会中不善于人际交往的人,在网络中也可能成为“交际达人”。因此,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社交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型交往方式,它在拓展人际交际领域和扩大交际范围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网络社交并非完美,网络社交迎合了人们交往快速、简单和公平的需求,但客观上也加剧了现实的人际疏离。在一项关于网络新媒体对青年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影响调查中,当问及“自从接触新媒体后,您认为自己社交活动、户外活动的变化”时,认为没什么变化的受访者达到54.1%,同时,回答活动时间和活动频率大大缩短的人占到了36.2%,还有9.7%选择了能不参加的社交活动和户外活动就不参加。统计结果表明,虽然有一半的被调查青年人感觉,他们的社交活动和户外活动没有受到影响,但是,依然有三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感受到了网络新媒体对他们现实交往的冲击,更有近10%的人已因此变成了不适应现实生活交流的宅男宅女。在访谈中有人谈到,我腻味了就会上网和网友聊天,聊得特别热闹,可是真的到了见了面,发现根本就没有什么好聊的,特别的尴尬。[1]这种“微信近,隔壁远”[2]的现象恐怕在许多年轻人身上都存在。更糟糕的是,以手机为载体的移动互联网对父母子女之间亲情沟通交流的冲击。许多人沉溺于网络,忽略了与亲人之间的沟通交流。羊年春节的“抢红包”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也多是对这方面的深层忧虑。一些人为抢红包甚至没有和亲人说上几句称心的话语,没有来得及和爸妈唠唠知心嗑。因此,有人惊呼,抢红包这个春节的“伴奏曲”盖过了亲情的“主题歌”,抢红包正在毁掉春节。[3]
2.网状发散结构的信息传播方式实现了信息传播形态的革命,但人们也不得不面对信息选择的困扰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互联网之父伯纳斯先生在电脑屏幕上敲下这样的文字:THIS IS FOR EVERYONE,即:这是每个人的。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网络传播降低了信息传播准入的门槛,每一个普通大众都可以以个体身份参与信息传播,构成网络节点。每一个网络节点既可以是信息的发布者,也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每一个用户既是节点的实体,用户以自己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激活每一个节点;同时又是节点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其他节点的互动产生新的信息。[4]而手机等移动互联技术的发展,更为网络传播“锦上添花”,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传递和接收信息。网络环境下传播节点数量巨大、纷繁复杂和动态多变的特点,造就了网络传播的网状发散结构,这是对传统媒体信息流动线性结构的巨大突破,实现了信息传播形态的革命。
网状发散结构的信息传播方式离不开技术和人,技术实现了网络自身的复杂建构,而人是技术的操控者。然而对于网络这样复杂的建构和建构中所包含的形形色色的内容,许多人都在反思:人是否还有能力或在多大程度上能进行自我操控。当前,电脑、互联网、手机,数字化处理器等高速、高清、高容量信息传输工具的涌现,标明了现代社会的高信息化程度。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信息并不一定是越多越好,过剩甚至泛滥的信息,将会使人们更加无所适从,不得不面对信息选择的困扰。“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至于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一句话,有朝一日,选择将是超选择的选择,自由将成为太自由的不自由。”[5]
3.媒介新技术给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但也催生了“速度文化”
人类的每一次科技进步,都会给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力量。媒介新技术凭借瞬息到达、即时互动的传播能力,打破了国家和地域的时空界限,为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创造了条件,不同的文化传播、不同的风俗习惯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念在网络中交织、互容和碰撞,不仅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对于既有社会的习俗、传统、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的认知和评价。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媒介新技术所具有的文化影响是显著的,它不仅冲击文化中那些相对稳定、持久的意义结构,带来特定价值、观念及信仰的暂时性断裂,而且还引发了既有社会网络的分化和解体,促成新型意义结构的生成和巩固。[6]
然而媒介新技术对文化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推动文化整合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催生“速度文化”。数字化特征以及对模拟资源的处理,导致新媒介内容的碎片化,由此产生了媒介文化的拼贴化趋势,即通过无规则地组合各种图像、信息和符号,以为人们提供最浅表、感官化的体验为要义。“抓眼球”是所有媒介传播的首要任务,为了吸引高度分化和善变的目标人群,媒介不得不反复借用那些最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引发人们的兴趣和吸引人们眼球的拼接方式,这又造成了媒介文化的同质化。媒介文化拼贴化与同质化的结果就是媒介内容的浅表化表现形式——“速度文化”或者说“快餐文化”。“速度文化”或“快餐文化”,带来的表面现象是:信息数量高速增长,传播活动日趋频繁,文化主体更加活跃,文化内容更加丰富,文化取向更加多元。但实际上,对于社会文化整体来说,知识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明显的加快,信息的社会影响力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弱的倾向。
4.网购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方兴未艾,但网络消费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发展物流快递,把以互联网为载体、线上线下互动的新兴消费搞得红红火火。实际上,这一政策正是为了迎合我国目前网购飞速发展的需要而提出的。2014年5月,国家邮政局发展与研究中心与德勤最新发布的联合报告《中国快递行业发展报告2014》指出,2008年我国网购人数为0.7亿人,到2013年迅速增加到3.0亿人,线上零售额在整个零售业中所占的比重由2008年的1.3%提升至2013年的7.4%,网购渗透率也由24.9%提升至47.4%。网络人数和网购频次的不断提升,使得中国网络零售额迅速赶超美国,2013年达到1.84万亿元人民币,成为世界第一网络零售大国。据预测,未来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仍将维持在30%以上。[7]因此,不容置疑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便利、效率、节省的网络消费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方兴未艾,正在确确实实地改变着我们的消费方式。
诚然,网络购物存在着诸多优势,它可以满足一些人低价买进高档消费品的省钱愿望,可以给那些因工作繁忙而无暇去商店购物的人享受足不出户购物的便捷,可以通过轻点鼠标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商品瞬间呈现在面前。但是,网络购物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购物方式,由于我们还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和措施,因此在网购轻松、便捷的背后,还存有诸多的不规范,如:宣传与实物差距大、商品质量良莠不齐、物流配送问题频出、货款支付存在风险、售后服务争议突出、欺诈行为屡禁不止、信息安全亟须加强等,急需出台相关法律和法规予以规范,网络消费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应对措施
面对移动互联技术影响社会生活方式的这些新趋势,过分迎合和一味逃避都是不可取的。要在把握上述新趋势的基础上,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
1.加强网络文化宣传和引导
网络上一切与观念意识相关的文化活动,都会直接投射到社会文化和民众的心灵深处,影响和重塑现实社会的价值观。[8]在移动互联时代,网络空间已成为各种文化和各种社会思潮交流、交锋、交融的平台。要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优势,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使之成为弘扬先进文化、主流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渠道。当前,要想占领网上思想舆论阵地,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必须深入研究网络舆论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必须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中汲取文化精华。唯有如此,才能唱响网络文化的主旋律,避免网络文化的“浮躁”和“短视”。
2.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教育
要教育和引导广大网民,在网络环境中自我约束、道德自律,而且这不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网络用户的责任,不仅包括普通网民,也包括大V等意见领袖。信息网络人际交往的匿名性和“去身份化”,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从某种程度上降低甚至剥夺了我们对现实生活的责任感,贬低了我们作为人的身份。责任感的缺乏,必然对我们的人际交往产生消极影响,引发现实的人际交往障碍。通过加强网络伦理道德的教育与自我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网络交往的健康发展。另外,加强在网下各类正式和非正式社会组织中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努力使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由“同质、机械结合”向“异质、有机结合”方向转变,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或降低网络给人际交流带来的“孤独感”、“机械感”和“ 异化感”。[9]
3.净化网络空间
要通过技术、行政、法律等多种途径,净化网络空间,有效遏制信息垃圾的生产和传播。通过相关技术,层层设置关卡,对有害信息进行有效过滤,阻止其入网。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规范化网络运作,敦促网站加强行业自律,坚持依法办网、文明办网,积极承担应负的社会责任,对纵容网络水军、为网络水军活动提供方便的网站,进行严肃的处理,让不良网络信息失去生存的土壤。同时,要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化的法制化,立法执法,对信息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4.加大网络监管力度
要制定相关及配套的移动电子商务监管法规,对网络交易市场的信息发布、准入资格、买卖细节、电子支付、各方责任等方面都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强化社会惩戒机制,凡是违法违规经营的电子商务者一经投诉、举报并经监管、执法部门确认事实后,要在其主管部门的网站上公布,以便网民上网查询或验证,令其无可遁形。另外,还要对消费者加强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
[1]张丽红.网络新媒体对青年人工作、生活状态的主要影响及建议[J].前沿,2014(5).
[2]余平.微信近,隔壁远[N].中国青年报,2015-03-23(02版).
[3]评论:莫让抢红包毁掉春节[OE/0L].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02/id/1558087.shtml,2015-02-26.
[4]喻国明等著.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3.
[5][美]阿尔温·托夫勒著,任小明译.未来的震荡[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313.
[6]石义彬,熊慧.从几个不同向度看媒介新技术的文化影响[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
[7]中国去年网购额1.84万亿元,超美国成世界第一[OE/0L].http://money.163.com/14/0527/10/9T8BG167002526O3.html,2014-05-27.
[8]黄桂清.论网络在社会文化重塑中的作用[J].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学报,2011(6).
[9]宋巨盛.互联网对现代人际交往影响的社会学分析[J].江淮论坛,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