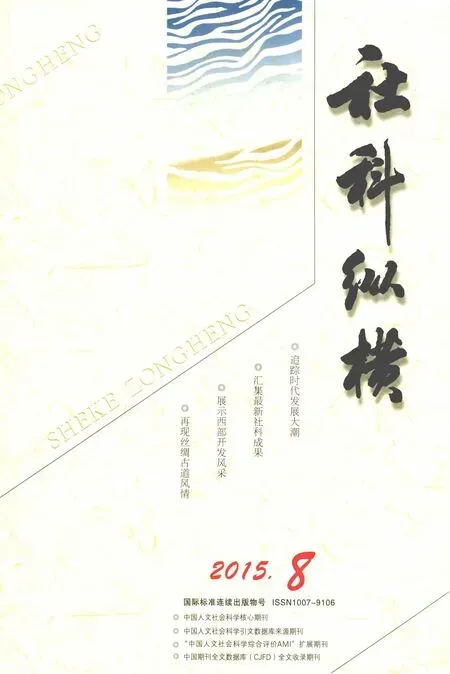中国梦与中国外交战略转型
刘 颖
(广东财经大学 广东 广州 510320)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后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他对这个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中国梦的提出不仅为攻克国内社会转型难题凝聚人心提供了强大动力,也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
近年来,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关于中国外交转型问题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焦点。一般来说,国外学者大都把中国外交看作为战略主动转变的结果,一个颇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大国间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旦中国具备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后,中国必定对现有国际秩序及领导提出挑战[1]。而国内学者一般关注中国外交的被动转型,主要论点可以概括为:由于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产生忧虑和疑惧,进而各自进行对外政策的调整,致使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发生变化,中国既往的外交战略正在失效,因此,中国外交必须转型。[2]
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壮大,中国外交将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前所未有挑战和压力。确实,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包含许多变量,情境(situation)的变化是其中之一,中国国力提升带来国家利益的拓展及国际地位的变化都会导致外交政策发生变迁。而国家作为复杂的组织,内部动态也会对国际行为起影响作用。从新中国外交走向看,外交战略的历次演变都深深地打上了领导人的烙印。从上世纪50-70年代的一边倒和一条线、80年代的真正不结盟,到90年代的韬光养晦、新世纪初的和平崛起,这些外交战略体现出了几代领导人各自理念。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两个百年的中国梦。中国梦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声与愿景,是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大共识。这一伟大目标的提出,不仅为攻克国内社会转型难题凝聚人心提供了强大动力,也对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和转型提供了契机与依据。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外交战略经历了两大阶段。1978年底之前为第一阶段。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政权,面对日益复杂的周边环境和不断加剧的美苏争霸紧张局势,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国家独立和主权不受侵犯。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历史经验出发,认为结成广泛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是维护新中国独立主权的最佳途径,从上世纪50年代的一边倒战略到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都是这一思想的产物,而毛泽东关于世界革命的理念更加重了这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的政治诉求的色彩。1978年之后为第二阶段,邓小平改变了对时代特征的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成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时代主题。在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或推迟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发生了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大幕就此拉开。在此背景下,外交战略也围绕着经济建设中心而发生转型,即使是对外政策中国家安全目标也开始被赋予非常清晰的经济性质的动机: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3]正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是第一位的,一旦国家的安全和生存得到保障,国家就开始寻求尊严、价值观、稳定、发展等其他目标。[4]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首先是内向型外交。本着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要服务于内政的传统观念,在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外交强调的是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的理念,即: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依靠的是内部努力,外交从基本功能上起着为国内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具体来看包括:一是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有一个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二是保障外部资本、技术、原料和能源的输入,三是保障中国的产品和企业走向世界。可以说这是一种着眼于内部的外交。其次是内敛外交。强烈的国家建设偏好使中国外交战略呈现出谨慎而内敛的风格。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后,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实施的种种制裁措施,中国政府坚持了韬光养晦的方针。在面临突发外交危机如1999年的“炸馆事件”和2001年的“撞机事件”时,中国政府采取了“冷处理”,没有让这些外交危机干扰国内经济建设。最后是被动型外交。由于把自己作为国际社会的“接收者”,中国主动参与国际体系的热情不高,往往是采取被动应对的态度,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不涉及中国内政的相关问题上常常投弃权票。
二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安全压力和国内发展压力均呈现急剧上升的态势,外交面临着更多难以预测的不确定因素,战略调整已经逐渐展开。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思想,为中国外交的转型进一步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一,实现中国梦需要外交从内向型向内外均衡型转变。内政与外交同属上层建筑,都应该服从与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2013年5月31日习近平在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时提出中国梦的中长期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这说明中国梦,不仅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目标,也包括了使中华民族重享泱泱大国的国际尊严与地位、实现民族中兴的目标。现代化是指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现代化,而民族复兴是指中华民族通过和平发展再次走在世界前列。如果说前一个目标主要是靠亿万中华儿女通过自力更生的国内建设而实现的话,那么后一个目标的获得则需要更多的外交参与和贡献。因为在这个目标阶段,外交的基本任务除了继续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有利总体国际环境外,还包括在国际舞台为中国谋取相应国际地位的内容。从前者来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中国面临的国际及周边环境将愈加复杂,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发生将是对中国外交严峻的挑战。从后者看,这要求中国在国际舞台恰当与准确地运用与展示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威望与能力,并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学会并适应担当负责任的国际领导角色,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成为一个令世界尊敬的国家。为达到这两个目标,必须转变单向的外交为内政服务和外交是内政延伸的传统观念,树立外交与内政同等重要的战略观念,统筹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推动中国外交由更多受制于内政向内外平衡、良性互构方面转型,营造一个内外有机互动的外交战略。
第二,实现中国梦需要外交从内敛型向自信型转变。民族复兴的重任将驱使中国在保卫国家安全利益时更为自信与坚决。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地区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正在逐渐改变,客观上引起了某些国家的猜疑与担忧,它们相继调整其军事外交战略,致使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益复杂。特别是2009年美国启动“重返亚洲”战略后,不断强化与韩国、日本、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盟国关系,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近两年中国在周边地区遭遇的外交困境,从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中菲之间的南海岛礁争议,都与美国的这一战略调整不无关系。对于近代以来饱受丧权辱国经历的中华民族而言,领土主权不仅涉及国家物质利益,更与民族的尊严与荣誉相关。美国学者理查德·勒博认为,与追求财富与安全一样,追求自尊也是国家行为的动力之一。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于群体身份与认同具有“强烈的渴望”,因为这种身份和认同能给予“提升自尊的层次”。当人们的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国籍或国家时,就会因为国家的胜利而感同身受并增加自尊,如果国家遭受挫折,人们的自尊则会遭遇相应的折损,甚至感到屈辱。[6]因此民族复兴的重任必然要求政府在有关领土安全问题上采取更为坚决与自信的政策以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就如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7]
第三,实现中国梦需要外交从被动型向责任型转变。习近平在阐述中国梦时多次表示中国梦“不仅致力于中国自身发展,也强调对世界的责任和贡献;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人民”。[6]中国梦中包含的为世界作贡献的使命感将驱使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更有担当。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自身需要与利益出发,希望中国在政治上成为制衡国际霸权在经济上帮助南方国家的有效力量,而一些发达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从实际来看,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期许往往超出了中国现有国力使中国力不从心,而西方发达国家“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又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中国也不可能照单全接。在未来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本着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美好愿望和梦想,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更为主动地参与现有国际体系并积极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治理结构的改革,为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外交实践中逐步学会并适应担当负责任的国际领导角色。
三
1959年肯尼思·沃尔兹出版了《人、国家与战争》,明确提出了分析研究国际关系的三个层次:个人、国家、国际社会。1979年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沃尔兹进一步精炼了其思想,将国际社会的结构归纳为两组重要的关系:体系与单位,结构与过程。从结构层次分析法上看,中国梦外交应该具有以下内容:
从体系层面看,中国梦外交要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持猜疑与敌视的态度,甚至一度倡导世界革命,让世界改天换地。1978年后为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打开国门逐渐参与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作为一个国际体系的后来者,中国在参与体系的过程中确实感受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敌意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种种不公,认为这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并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8]但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中国并没有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方面有太大作为。习近平在向世界阐述中国梦时同样提到了公平与正义问题,“国家应该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9]。但同时他又反复强调中国将追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实现中国梦:“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因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始终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7]并表示中国“将坚定不移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7]。可见,在未来中国并不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中国梦追求的国际秩序,既不是“安于现状”的秩序,也不是“另起炉灶”的秩序,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框架内,发挥中国的大国作用与国际责任,通过强调国际规范,强调制度规则和体制机制的公平正义,重点支持和照顾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从单位层面看,中国梦外交要构建一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国家间关系。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两极激烈对峙的冷战格局影响和求生存的压力下,求和平成为中国处理国家关系首要及基本目标。80年代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依次展开,为推进国内经济建设的进行,求发展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在不断加大,一国的和平安全与经济发展皆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因而求合作也逐渐进入中国外交的议事日程并成为重要目标。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时说“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中国梦的实现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周边环境。中国将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中,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10]因此新时期中国外交要在和平发展合作的基础上寻求共赢互利。求共赢,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世界做出的郑重承诺,复兴后的中国把将发展自己与发展人类文明和谐地统一起来,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互利共生,共同应对挑战,体现出了中国惠济天下的大国胸怀和担当,展现了受“和合”文化影响的新兴大国的特殊襟怀。这种新型国家间关系至少包括两个重要内容: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摒弃了传统大国关系模式,开创了崛起国与既成国之间处理冲突与矛盾的新方式:双方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亲诚惠容的周边国家关系是在睦邻友好政策的基础上,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我国发展更好地惠及周边,也使我国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同时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回应周边国家期待,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
从个人层面看,中国梦外交是以人为本的“为民外交”。中国梦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梦想,“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11]。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要求外交改变过去只为“国家”服务的习惯性思维,确立“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观念。从传统上看,中国外交过去基本上都是礼宾外交、首脑外交,精英外交,在“外交为国”的思路影响下,外交主要保障的是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利益。在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日益密切,有越来越多的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中国海外的利益日益多元化。这要求外交在确保国家安全的同时,确立“为民服务”的理念,有效维护我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人身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生活工作学习提供更多的便利,为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提供更多的服务,尤其是要妥善应对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遭遇的一些突发性事件和纠纷。
综上所述,外交是现代国家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方式。既然中国梦要求的民族复兴是和平的复兴,是打破以往大国崛起定律的复兴,这要求中国外交谨慎重新审视崛起中的国家利益,缜密谋划外交战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为自信的角色,最终以中国力量推动“世界梦”的演进和实现。
[1]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王逸舟.论中国外交转型[J].学习与探索,2008(5);庄虔友,杨束芳.和平发展战略与中国外交转型[J].理论研究,2008(4);刘胜湘.中国外交周期与外交转型[J].现代国际关系,2010(1);赵可金.“建设性领导与中国外交转型”[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5).
[3]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R].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http://News.xinhuanet.com/zilai/2003_01/20/content/_696989.htm.
[4]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p.91
[5]习近平接受拉美三国媒体联合书面采访[N].人民日报,2013-6-1.
[6]理查德·内德·勒博.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4.
[7]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N].人民日报,2013-1-30.
[8]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R].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11/17/content_632296.htm.
[9]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164113-23549058.html[EB].
[10]人民网.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7)[RB].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05/c40555-23756883-7.html.
[11]人民网.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2)[EB].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205/c40555-2375688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