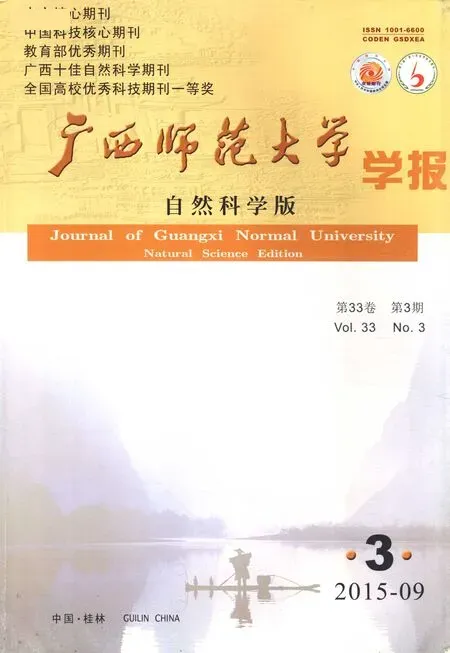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立法研究
蒋 科,叶胜宇
(1.湖南警察学院法律系, 湖南 长沙 410138;2.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湖南 长沙 410008)
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立法研究
蒋 科1,叶胜宇2
(1.湖南警察学院法律系, 湖南 长沙 410138;2.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湖南 长沙 410008)
公司中经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事与监事,负有公法上特定的国资经营监督职责,实质为国资委代表国家委派的公务代表,其激励当符合国家公职人员的相关原理及规则。然而,当前的制度设计基于其公司董监事的私法身份,依据经济学上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了以市场化激励为主导的激励机制,使其异化为公司的普通董监事而丧失了应有的功能。对此,需从法学的视角反思其理论基础,明确国资委与其董监事代表人之间公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构建以履行公务职责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回归对其公务激励的本来面目。
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立法完善
在公司的语境中,所谓国家出资人代表,是指由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以下简称国资委)依法直接委派,或经国有股权支持当选的公司董事及监事。从现行相关国资立法看,其负有公法上特定的国资经营监督职责,对其实施合法公允的激励,可促使其积极履行公务职责,防止国资流失并保障国家出资目的的实现。然而,当前理论及实务界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主流价值导向下,忽视了国企与私企的区别,混淆了国有股董监事与普通董监事的界限,主张对其市场化激励。但正如学者所言:“有关私企的规范性结论在推广到国企时会变得复杂起来,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理念尽管在发挥作用,但由于涉及垄断的社会成本和公共服务义务,价值最大化很难赢得民众的支持。”*Prichard J R .Crown Corporations in Canada, Butterworths, Toronto. 1983,65而在缺乏严格的绩效衡量标准时,增加激励性报酬会鼓励其最大化垄断租金,导致其与执政当局官员的合谋,最终损害委托人即全民的利益*Dixit A K.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erspective, London:MIT Press, 1996,33。因此,在当前我国明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国企改革新形势下,有必要对国资委委派或推选董监事的法律性质予以明晰,探究其激励的法理依据并合法构建其制度,以实现激励应有的功能。
一、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的立法原理
依出资人股东与公司法人分离之法理,公司的董监事为其自身法人机关成员而绝非出资人股东的代表。但国家作为出资人时,基于出资资产的全民性及其法律人格的虚拟性,有必要通过公司机制推选其自然人代表担任公司的董监事,同时委以相应的国资经营监督职责。此时该自然人代表实际是国资委借助私法机制实现国资行政监管职能的手段,二者当为一种公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故该类董监事作为国家出资人代表是符合法理的。因此,我们只有揭开其董监事私法身份的“面纱”,还原其公法上的本来面目,方能从本源上揭示该类董监事激励机制的内在法理,为合法构建其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一)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的理论依据
在经济学理论上,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过程,从最初委托人(全民)到最终代理人(国有产权代表)是层层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偏离导致了代理问题,故需激励代理人以降低代理成本。西方学者詹森等人曾指出,现代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入到经营者手中,经营者可能利用其实际控制权为自己谋利而损害股东的利益*M Jesen,W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Managerial Behavior,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76, (3): 66-75。我国经济学者张维迎则把企业的所有权解释为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认为在企业内部权力的最优配置即是二者的对应,把剩余索取权分配给经营者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张维迎.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的权利斗争[J].经济研究,2000,(6):50.。因此,我国经济学者主张对包括国有产权代表在内的国企经营者,实施以业绩回报为核心的显性激励,从而实现其代理行为与企业目标的利益兼容。
然而,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只能说明国资授权经营中“代理成本”的存在,而其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是否适用于国有产权代表则不无疑问。从法学的视角看,私人出资者对其推选董监事的激励纯属私权的范畴,可在公司法框架下依其自由意志行事;而国家出资人对其董监事代表人的激励却受制于相关国资立法的规定,其原因则在于国有股权之源泉——国家所有权的公共性。
众所周知,国家所有权的真实主体为全民,由于全民无法直接行使所有权,故只能由国家代表全民为着公共利益统一行使。国家利用国有财产出资,其目的在于将国家所有权转换为国有股权,通过公司经营的方式实现全民的利益。而国家所有权转化为国有股权后其公共性并未丧失,只是公共性的实现机制发生了变化:如国有股权的具体行使主体国资委,其对国有股权的资产收益及处分须遵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股权转让等方面的规定;其行使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权时,须服从国家宏观调控意图、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等强制性规定;其行使选择企业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时,对董监事代表人须先会同组织部门按内部程序选拔,然后再依公司程序选举和任命,对其管理也需遵从相关国资立法的规定。可见,国家所有权转换为国有股权后,国资委对国有股权的行使无不受到国家立法及政策的约束,而其目的即在于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公共性。
正是由于国有股权沿袭了国家所有权的公共性,对国有股权支持当选的董监事的激励也就不能照搬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委托代理理论。从我国国资授权经营体制看,全民是通过国家立法,授权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并享有出资人权益,政府再授权国资委代表政府履行相同的职责,再由其选派自然人担任公司的董监事从而在微观层面保障了国家出资目的的实现。可见,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实际是国家所有权间接行使环节上的末端代表,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理论仅说明了对其激励的必要性,而其制度构建的法学基础则在于国家所有权行使理论。
(二)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的立法基础
虽前已述明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的理论依据,但其具体制度的构建却属立法的范畴,故当以其所处具体法律关系中的法律地位为基础构建。鉴于国家出资人代表兼具公司董监事的双重身份,其实际参与了两种法律关系:即在国资授权经营体制上与国资委的法律关系及其在公司法上与所在公司的法律关系。那么,该两种法律关系性质为何,又当以何种法律关系为基础构建其制度?以下试析之。
1.国资授权经营体制上国家出资人代表与国资委的法律关系。根据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规定,国资委是经政府“授权”而“代表”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从其职能定位看,实际包括了代表政府对国资经营公法上的监管职责与私法上作为出资人股东的职责。一方面,作为监管主体,其负有代表政府对企业国资经营管理职责:一是以政府的预算编制为基础的投资预算决策;二是投资的具体执行;三是对投资执行及国资经营、收益等进行的全程监管。这三方面管理职责均是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应有之义*顾功耘.国有资产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4.。另一方面,作为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权利的机构,其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出资人权利。那么,国资委与其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之间,基于其职能定位到底是何种法律关系?从该类董监事承担的职责来看,二者实为公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如董监事代表人应当在企业中执行国家有关国有资产投资、转让、收益及基础管理等方面的规定;监督企业在主业范围内经营、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并及时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对企业重大事项及时向国资委报告等等*国资委委派或推选董监事的公务性职责难以详尽列举,散见于相关国资行政立法之中。具体参见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投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财政部与国资委《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地方性国资委对国有产权代表管理的相关规定等等。。这些行政性职责明显体现了二者之间是公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
2.公司法框架下国家出资人代表与所在公司的法律关系。国家出资人代表作为公司的董监事,其与公司当为私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其一,从职位来源上看,其是全体股东选举产生的公司法人机关成员,而不是国资委个别股东的代表。其二,从公司法上的职权看,国资委推选的董监事也是代表着公司行使相应的职权。有学者曾言:“董事会是公司对外的代表机关,国有股董事仅是这一机关成员,即使国有股董事充当了公司董事长,其对外代表的名义也必是公司而不是国有股股东。”*肖海军.国有股权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39.同理,国有股监事亦如此。可见,在公司法上,国资委推选董监事的职权均是基于公司的授权而不是国资委股东的授权,其基于董监事身份的职权均是代表公司行使。其三,从法律责任上看,国资委推选的董监事依公司法或公司章程履行职务的行为均由公司承担责任。因此,国家出资人代表作为公司的董监事,其与公司当为一种基于其董监事私法身份的职务代表关系。
3.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依托之法律关系。既然国家出资人代表同时参与了两种法律关系,那么对其激励当以何种法律关系为依据?本文认为,国家出资人代表外在的董监事身份仅是便利其在公司中履行公务职责,对其激励当以其内在的与国资委公法上的委任与代表关系为依据。如前所述,国家所有权是通过层层“授权与代表”机制实现的,而国家所有权转化为国有股权后该“授权与代表”关系并未断裂。从授权主体上看,国资委作为直接代表政府间接代表国家的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其与国家及其政府乃一体关系,其授权行为即国家的行为;从授权对象上看,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均具潜在的公职身份,其可依现行《公务员法》在党政企事业单位之间交流;从授权内容上看,根据目前国资行政立法,其是分别在董事会与监事会中利用其董监事身份履行相应的国资经营监督职责。可见,国家所有权转化为国有股权后,公法上的“授权与代表”机制仍在公司延续,其原因则在于国有股权是对国家所有权实现机制的升华,而非对国家所有权的否定。“国有产权是一个国家通过公共权力分配收益和风险的宪政机制,而不能如私人产权一样以公司治理机制为媒介。”*胡海涛.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实现机制若干理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37.如果对董监事代表人按公司普通董监事对待,则会“激励”其“积极”履行私法上董监事的职责,追求公司利益最大化而脱离国家出资本应承担的公共性目标。尤其是在当前国家股东“虚位”而国有股董事普遍兼任经理层职务的现实情况下,依其私法身份的激励会加剧其沦为公司的内部人,继而丧失其作为国家出资人代表应有的作用。
(三)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的立法要素
1.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主体。在国资授权经营体制上,国资委是国家立法授权政府专设的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而国家出资人代表又是受国资委委派在企业中履行国资经营监督职责的公务代表,故国资委当依法对其履行公务职责的情况进行考评并作为其激励主体。
2.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目的与依据。基于国家出资人代表承担着国资经营监督职责,国资委对其激励目的即在于促使其积极履行公务职责,防止国资流失并保障国家出资目的的实现,而其激励依据也当以其履行公务职责的考评结果来衡量。当然,对具体企业中的国家出资人代表,应根据其所处企业功能定位及董监事岗位职责的不同,分类设定其考评标准。但总体而言,作为激励依据的考评标准当以其公务职责为中心设定,以此达到对其公务激励的目的。
3.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方式与程序。基于国家出资人代表实质上的公职身份,其激励方式与程序当参照国家公职人员的相关规定并结合企业特性来确定。如其激励当贯彻依法、公开、公平公正等原则,采取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的方式,按法定权限与程序等进行。
4.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的监督与法律责任。首先,应当明确激励的监督主体与监督对象。基于激励环节牵涉到激励主体国资委是否依法激励,激励对象董监事代表人是否如实提供相关信息资料,第三方社会中介机构是否客观提供审计或鉴证报告,故其均为激励环节中的监督对象。而相关监督主体,对国资委而言,应当包括同级政府审计、监察及人事部门等依职权的监督,社会中介机构的专业监督以及社会公众的监督等;对董监事代表人而言,应主要确定企业职工的民主监督机制;对社会中介机构而言,则应包括聘用单位的监督以及行业监督等。此外,应明确激励监督的内容、方式与程序并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只有明确了上述内容,方能实现激励机制的规范化与法治化。
二、国家出资人代表现行激励机制的立法缺陷
针对国资委委派或推选董监事的激励,我国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不同效力层级的制度规范*激励性规范主要包括:国务院国资委《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2003年通过并历经2006、2009、2012年三次修订),《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及其《实施细则》(2004),《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2006);人力资源部会同国资委等六部委联合颁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2009);中组部《中央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2009);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2009);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和《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2014)。此外,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2000)、《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2003)等行政法规以及《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等对此也作了原则性规定。。然而,现行激励机制主要建立在国资委相关部门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行政法规及《企业国有资产法》等对其仅作了原则性规定,故难免部门立法的弊端且有效性不够稳定。虽然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对其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该方案毕竟尚未转化为相关立法而难以依法执行。而国资委现行规范主要规定了对其委派董事的激励但无对监事的具体规定,对其推选董监事的激励则交给了公司自行处理。因现行激励性规范未得到国家立法授权且制定过程不够规范,其科学性与合法性均难以保障。具体而言,现行激励机制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
(一) 激励权主体错位且责任虚化
根据我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7条规定:国家建立国家出资企业管理者经营业绩考核制度,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应当对其任命的企业管理者进行年度和任期考核,并依据考核结果决定对其奖惩。而根据我国《公司法》,公司股东大会享有审批董事会与监事会报告,决定董事及监事报酬等职权。可见,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主体区分为两种情形:在国有独资公司,国资委委派的董监事其激励主体为国资委;而在国有资本控参股公司,国资委推选的董监事其激励主体则为公司本身。
但如前所述,国家出资人代表外在的董监事身份仅是便利其在公司中履行公务职责,对其激励当以其内在的公职身份为依据,现行公司法上公司的激励权实际仅当适用于公司的普通董监事。由于目前公司制国企一般为国有独资或控股,在国家出资人股东主体虚位的现实情况下,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极易借助公司独立法人地位的保护,利用其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和公司自治机制,为自己设定所谓与市场接轨的激励机制,产生“天价年薪”与畸高福利等问题。尽管国资委规定,投资主体多元化企业由其推选董事的薪酬应当报国资委“备案”,但无实质性的约束作用;而在国有独资公司,企业负责人(含董事)的年度薪酬方案由企业拟定再报国资委审核,其中法定代表人的薪酬由国资委批复,其他负责人则仅需备案。可见,目前激励对象实际主导了激励权,激励权主体错位。
同时,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的规定:国资委等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不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予以处分;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可见,在现行立法上,国资委相关人员不依法行使激励权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处分,而目前国资委相关规范并未规定其自身的法律责任,所谓“依法”给予其处分依据何在不得而知。而在公司作为激励主体的情形下,对公司董监事的激励由股东大会决定,但股东大会作为责任主体欠缺主体性条件。可见,在目前激励机制国家立法缺失的现实条件下,激励主体的法律责任虚化,激励机制的运行缺乏法律责任保障。
(二)激励依据片面化且激励方式过度市场化
一方面,激励依据片面化。根据现行考评与薪酬管理规定,国资委委派董事的薪酬结构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和任期激励三部分构成。其中,基本年薪是年度基本收入并按月支付,绩效年薪与任期激励则与年度和任期经营业绩挂钩。对国有控参股公司中国资委推选的董监事,其薪酬方案则由公司依其经营业绩决定并报国资委备案。可见,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与其“经营业绩”紧密相关。而目前对其“经营业绩”的考评,无不是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对其考评的首要标准。即使对军工企业和主要承担国家政策性业务等特殊企业,也仅规定年度与任期考评“可以”而不是“必须”优先考虑政策性目标的完成情况。可见,现行以“经济绩效”为中心的考评指标导致其激励依据的片面化,其“经营业绩”中本当包含的公共性目标被“经济绩效”覆盖,国家出资应当承担的公共性职责被弱化,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激励方式过度市场化。对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事,目前的激励方式主要体现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在国有上市公司还包括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此外职务消费以及福利补贴等事实上也为其隐性激励方式。然而,年薪制以人力资本理论为依据,其实施的前提是必须存在一个完善的企业家市场。但目前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并非市场机制选择的结果,而是其任命或推选的“官员董事”与“官员监事”。而股权激励方式在目前国有公司普遍欠缺客观的价值评价标准且内部人控制严重的现实条件下,极易被董事等公司管理层操纵而侵蚀国家出资人等股东的利益。至于职务消费与福利补贴等隐性激励,因其由企业自行确定再报国资委备案,其标准更是畸高离谱。依法学之视角,目前所谓的年薪制等实际符合关联交易的特征,国家股东的“虚位”以及董事会和经理层实质上的人员混同加剧了其激励机制的扭曲,而其根本原因还在于董监事代表人的私法定位。但如此一来,其一方面享受着企业的高薪,另一方面又享受着官员的待遇,随时转换于“官场”与“市场”,在企业经营中通过短期行为提高其“经营业绩”而获得巨额回报,忽视了其本当承担的公务职责。
(三)激励程序封闭化且激励监督弱化
其一,从基本年薪的确定程序看,目前规定国资委委派董事的基本年薪与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但如何联系却无具体可操作性的规定。其一般由企业自行制定方案并报国资委审核或备案,仅需企业与国资委双方认可即可。其二,从绩效年薪的确定程序看,国资委按照先考核后兑现的原则,根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由企业一次性提取并分期兑现:其中绩效薪金的70%在年度考核结束后当期兑现,其余30%根据任期考核结果延期到任期考核结束后兑现。而在此过程中,国资委对激励的依据即年度与任期考核结果,仅向企业主要负责人及本人反馈而无需向企业职工公开,且绩效年薪由企业自行提取并兑现,可见其激励仍只在企业与国资委双方之间进行。其三,从任期激励的确定程序看,目前规定在综合考虑中央企业负责人整体薪酬和考核对象薪酬水平的基础上,根据任期考核结果给予相应的任期激励。但何谓“相应的”任期激励当前并无规定,那么其也只能在国资委与其激励对象之间内部确定。此外,作为中长期激励方式的股权激励计划、职务消费和福利补贴等隐性激励方式,目前规定由企业自行确定后报国资委备案再实施,显然也为企业所主导。总之,目前各项激励措施的制定及实施均只在国资委与其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其激励程序的封闭化导致了激励监督的弱化,难以避免过度激励而侵蚀国家出资人等股东的利益。
综上,目前我国对企业中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因激励依据仅限于国资委部门规章及相关政策性文件,尚未经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激励制度,其立法的科学性及合法性均存在问题。尤其是对董监事代表人私法定位的激励措施,无法督促其在企业中积极履行国资经营监督之公务职责,丧失了其作为国家出资人代表的基本作用。因此,我们只有基于其公务职责的职能定位,构建基于其公法身份的激励机制,才能克服现行立法的弊端,实现对其公务激励的目的。
三、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机制的立法完善
国家出资人代表作为在企业中履行国资经营监督职责的公务代表,其激励机制当以此身份定位为基础构建。而现行以董监事私法身份建立的激励机制显然与其公法性定位不符,这也是当前激励机制存在诸多矛盾与问题的根源所在。为此,我们应当在遵循《企业国有资产法》原则性规定的前提下,借鉴《公务员法》及党政领导干部管理相关规定,结合企业特性,将国资委对董事代表人的现行考评与激励规范和国务院有关对外派监事的规定进行整合,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化为专门性行政法规,以解决激励机制国家立法缺失的问题。具体而言,可从激励主体、激励依据与方式、激励的监督与法律责任三个方面予以立法完善。
(一)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主体的立法完善
1.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权由国资委统一行使。目前在国有资本控参股公司,国资委推选董监事的激励权由公司享有,这显然与其承担的公务职责相悖。对此,应当根据现行《公务员法》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对国家公职人员转任或调任企业担任国家出资人代表的董监事,明确其公职身份,以此确定国资委对该类董监事的激励权。同时,应当修改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与《公司法》相关条款,对国资委委派或推选的董监事,其考评与激励等当参照国家公职人员的相关规定。此外,为配合该公务激励机制,立法应明确禁止国家出资人代表兼任公司经理层职务,限定其仅在公司董事会与监事会中履行国资经营监督职责,避免经营监督主体与具体经营者身份混同导致的利益冲突。
2.在国资委内设国家出资人代表管理局行使激励权。目前在国资委内部,对委派董事的经营业绩考评由财务监督与考核评价局负责,其薪酬激励则归企业分配局负责;对委派监事的日常管理则由监事会工作局负责。可见,国资委对其委派董监事代表人的激励权尚未统一行使,更谈不上对控参股公司中推选的董监事代表人激励的归口管理。此外,国资委作为法定的履行出资人职责机构,其是代表国家统一行使激励权,而董监事代表人作为“官员董事”与“官员监事”,其最为关键的职位晋升激励权却为上级党政机关享有,国资委实际仅享有“经营业绩”的物质激励权,难以对董监事代表人实施归口管理并有效激励。为此,可在国资委内设行政级别仅低国资委半级的国家出资人代表管理局,将党政机关的激励权纳入该局,同时建立党政组织人事部门及监察部门人员派驻制度,以实现国资委统一代表国家行使激励权,并解决对其推选董监事代表人归口激励的问题。当然,国家出资人代表管理局作为专门管理机构,可在内部分设人事、考评、薪酬与监察等职能机构,由其分别行使相应的职权。具体到激励而言,由该局薪酬部门执行,其职责在于依法定程序及方式激励董监事代表人。
(二)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依据与方式的立法完善
1.激励依据的立法完善。对国家出资人代表的激励当以其考评结果为依据,而考评结果又依赖于其考评标准的设定。如前所述,由于目前考评标准存在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且分类不明的弊端,故需首先确定其考评标准才能解决其激励依据的问题。在考评标准的确定方面,立法应当以其履行公务职责为中心,对董监事代表人的“业绩”作扩大化解释,并依据其所处企业的功能定位及董监事岗位职责的不同分类设定。具体而言,对公益类国企中的国家出资人代表,当确立以公共产品为核心的考评指标体系,保值增值仅作为次要指标;对营利类国企中的国家出资人代表,当确立以保值增值为主兼顾落实国家经济政策的考评指标,以实现财政增收与其他公共性目标的有机融合。此外,对董事代表人应重点考核其在董事会决策中是否监督企业在主业范围内经营以实现国家出资目的;对监事代表人则重点考核其在监事会中是否履行了相应的国资经营监督职责,包括对董事代表人的监督等等。当然,在立法确定以上原则性考评标准的基础上,对董事代表人可通过现行“经营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晰其含公务职责在内的考评标准;对监事代表人则可针对董事代表人“经营目标责任书”的内容,设定其监督业绩考评指标。总之,应当通过立法明确国家出资人代表以公务职责为中心的考评标准,为其激励提供客观依据。
2.激励方式的立法完善。目前过度市场化的激励方式,使得国家出资人代表不仅忽视了企业的一般社会责任,对国企应当承担的公共性目标也未予重视:如在宏观上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与经济调控意图,在微观上监督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等等。因此,基于国家出资人代表实质上的公职身份,对其激励当采公职人员的激励方式,即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励为辅。在当今市场经济国家,当国家机构官员被任命到董事会或监事会时,除其得到官员薪俸之外不能在企业获得薪酬,可给予官员的企业薪酬则转为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预算。如在新加坡政府淡马锡公司,董事会中的官员董事兼职不兼薪,薪水由政府支付,但经营业绩好的可以升迁*吴越.公司治理:国企所有权与治理目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129.。而我国现行所谓与市场接轨的年薪与股票期权等激励方式,实际模糊了国家出资人代表的官员身份,使其得以接受双重激励并逐步丧失其公务特性。因此,立法应当明确对国家出资人代表出任的公司董监事,其激励当以《公务员法》为基本依据,主要采嘉奖、记功、授予荣誉称号及职位晋升等激励方式,并结合企业特性予以适当经济补贴,以实现对国家出资人代表公务激励的理性回归。
(三)国家出资人代表激励的监督与法律责任的立法完善
1.健全审计监督机制。因国资委对董监事代表人的激励主要依赖于考评结果,而考评结果又有赖于相关部门或机构的审计是否客观真实,故审计监督至关重要。从目前的审计机制看,其主要依靠企业自身审计,国资委在必要时可聘请第三方机构审计。可见,现行审计机制为企业与国资委所主导,激励的审计监督弱化。对此,需立法明确企业内部审计、独立第三方机构审计与国资委审计并行不悖的“三方审计”机制,结合现行政府审计机关对国企法定代表人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对董事代表人的经营业绩进行全方位审计,从而保障激励依据的客观化。
2.建立司法监督机制。一般而言,公司董监事的薪酬激励属于公司自治的范畴,但就国有公司而言,因国家出资人股东主体虚位,含董监事代表人在内的公司管理层往往利用公司机制为自己设定较高的薪酬激励方案,导致公司及出资人股东的利益受损。因此,在公司自治功能弱化或失衡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司法介入的监督机制。从法理上讲,股东享有对董监事激励提出异议的权利,在其制定程序存在瑕疵或激励标准过高等情形下,有权请求法院及时干预或进行事后公正性裁判。但国资委作为股东仅是代表国家行使股东权,在国家独资或控股的情形下,只要其不行使该项权利则该类诉讼难以提起。而且,国资委与其董监事代表人本为公法上的一体关系,其也不可能提起诉讼。因此,可以考虑由法律监督机关即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公益诉讼,解决国家股东主体虚位的问题,并以此监督国资委依法行使激励权。
3.完善民主监督机制。一方面,完善企业职工参与董监事代表人薪酬激励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职工董监事的作用,赋予其在董事会与监事会中相应的监督职权;另一方面,建立强制性的信息公开制度。对董监事代表人的薪酬激励方案、业绩考评结果及薪酬激励的执行情况等,立法应当要求国资委依法定程序向企业职工等法定对象公开,并确定相应的异议与救济机制。
4.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一是明确激励主体国资委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国资委内部与激励相关的直接责任人及国资委机构负责人,应根据现行《企业国有资产法》、《公务员法》及党政领导干部管理等相关规定,在国务院专项立法中明确其行政责任及承担责任的具体情形。对情节严重构成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行政处分取代其本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二是明确激励对象董监事代表人的法律责任。对虚报业绩骗取激励的,除依法取消该项激励外,还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与经济处罚。三是明确激励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对社会中介机构等虚假提供审计或鉴证报告的,除依法予以经济处罚、吊销营业执照及相关责任人的职业资格外,还应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
The Legislation on Prompting Institution of Representatives of State investors in Enterprise
JIANG Ke1,YE Sheng-yu2
(1.LawDepartment,HunanPoliceAcademy,Changsha,Hunan410138,China; 2.People’sProcuratorateofKaifuDistrict,Changsha,Hunan410008,China)
The prompting of the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who are elected by States’ stock holders and have special responsibility on operating and supervising the national asset in enterprises, should follow the rules and principles of that of national officer. However, the running prompting institution is based on the private statues and the authorizing theory by marketing, which makes them only burden the obligation of ordinary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We should rethink the theoretical bases, identify the relation between States’ stock holders and directors and supervisors, and erect the prompting system focus on public duty to fulfill the duty of public promp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tate investors in enterprise; prompting institution; legislation
2015-06-1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董事法律制度研究”(15BFX169)阶段性研究成果,民商法学湖南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HNPR-2012-03001)。
蒋科,男,湖南警察学院教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学;叶胜宇,男,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院。
DF411.91
A
1672-769X(2015)05-006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