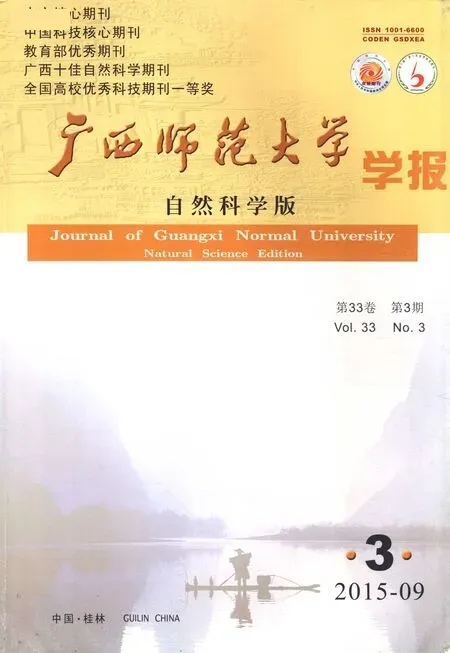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新论
李冠煜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新论
李冠煜
(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某种危害环境行为构成犯罪后,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即为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是环境犯罪的法律后果,也是对环境犯罪适用刑罚或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前提。在追究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应当奉行责任谦抑原则、责任前置原则和经济制裁原则。相比德国、日本,我国《刑法》为环境犯罪配置的刑罚整体偏重,不能完全满足预防性环保的刑事政策的要求,不利于合理追究其刑事责任。
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概念;特征;原则;实现方式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人民日报》评论员.引领民族复兴的战略布局——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N].人民日报,2015-02-25(1).。其中,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因此,深刻领会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立足于当下国情再次研究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一般认为,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受的、由司法机关根据刑事法律对该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的谴责。据此,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因其危害环境行为所应承受的、由司法机关根据环境刑法对该行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对行为人进行的谴责。
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与一般犯罪的刑事责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是刑事责任的种概念,必须符合刑事责任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即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本质在于,体现了国家对环境犯罪的否定性评价以及对环境犯罪人的谴责。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同样只能因环境犯罪行为而产生,由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强制环境犯罪主体承担,以对环境犯罪的否定性评价和对环境犯罪人的严厉谴责为内容。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危害环境的作用原理和发生经过明显不同于一般犯罪,所以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应当根据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来研究。那么,环境犯罪刑事责任自然就表现出区别于普通犯罪刑事责任的特征。
一方面,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内容除了否定环境犯罪和谴责环境犯罪人以外,还包括恢复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和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环境权。换言之,当把预防性环保的刑事政策的目标引入环境刑法之后,环境犯罪刑事责任不再只着眼于惩罚环境犯罪,使判处的刑罚和行为的责任相均衡;还要在有利于预防环境犯罪的目标下,检讨追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必要性和妥当性。在此,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内容不仅包括对环境犯罪人的刑事负担,还包括服务于预防环境犯罪必要性的其他途径。可见,提倡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二元构造,有以下根据:一是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根据我国的环境政策和刑法目的,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目的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运用各种刑事和非刑事方法,预防和控制环境犯罪,保护被害人的环境权和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追究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时,必须以预防环境犯罪为导向,当对环境犯罪科处刑罚不利于实现这一目的时,就不应当科处刑罚,而应当采取刑罚之外的其他途径。二是目的论的、刑事政策性的责任概念的要求。当把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贯彻到刑法中去时,犯罪的非难可能性和预防必要性就结合在一起,责任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这种“责任”,也被称作“答责性”(Verantworlichkeit)。答责性这一范畴,是回答在刑事政策的观点下,个别案件中刑法上的制裁必要性的问题*[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中的责任和预防[M].宫泽浩一监译.日本东京:成文堂,1984.88.。这种责任必须取决于两种现实才能够加到不法上去:行为人的罪责和应当从法律中提取出来的刑法威胁的预防必要性*[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57.。所以,罪责和预防必要性是答责性的两个要素,只有罪责和预防必要性才能共同决定是否予以刑罚处罚。尽管预防必要性体现了刑事政策和刑法的目的,但它不是没有限制的。预防必要性不能超过罪责限度的范围,使功利追求凌驾于正义价值之上。预防考虑是实现罪责的最终目的,但罪责也是限制预防的有效手段。所以,只要将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选择引入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事责任自然就包含了严厉惩罚环境犯罪和有效预防环境犯罪的内容。
另一方面,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除了继续广泛适用自由刑外,还把罚金刑作为一种主要手段。而且,在确立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的环境刑罚体系的同时,赔偿经济损失、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目的对环境刑法体系的影响,必然导致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有三种类型:一是刑罚的多元化。根据我国《刑法》第338条至第346条之规定,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主刑中的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均可用于处罚环境犯罪,附加刑中的罚金、没收财产和驱逐出境也能适用于环境犯罪。值得注意的是,立法者为每个犯罪都配置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刑。二是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多元化。根据我国《刑法》第36条和第37条之规定,非刑罚处理方法有判处赔偿经济损失、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这几种。当危害环境行为已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不需要运用刑事处罚,或者单纯适用刑罚不足以实现刑罚目的、需要刑罚以外的方法配合适用时,可以考虑采用这些非刑罚处理方法。三是行政处罚的多元化。例如,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行政法规定了警告、罚款、责令停止生产或使用、责令停业、关闭、责令拆除或没收等多种行政处罚,作为“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这一非刑罚处理方法的具体化,对刑罚制裁起到了有力的补充作用。总之,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多元化,表现出惩罚性和预防性并重、人身性和经济性并重、剥夺性和补偿性并重的特点。
只有在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引下,才能完成环境刑法的机能化、体系化的任务,这其中就包括了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体系化。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体系化,需要提炼出某些归责原则,并厘清这些原则组合之间的关系,作为完善环境犯罪责任论乃至整个环境刑法学的“指导性要点”(Leitgesichtspunkte)*[德]克劳斯·罗克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M].蔡桂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5.。
二、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
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是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在产生、确认和发展各阶段应当普遍遵守的指导准则。它是环境犯罪刑事政策渗透到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发展阶段的结果,进而对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化、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的构建、环境犯罪的刑罚适用及执行产生很大影响。关于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应当包括哪些原则,学界至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包括标本兼治原则、多元处罚原则、区别对待原则、与民事、行政措施相协调原则*付立忠.环境刑法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253-256.。还有学者提出,确定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时除了应该考虑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应坚持如下原则:刑罚节俭原则(轻刑化原则)、财产刑与自由刑并用原则、刑罚与非刑罚方法并用原则*蒋兰香.环境刑法[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78.。最近,又有学者主张,基于环境犯罪的特殊性,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除了刑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外,还应包括以下原则:刑罚谦抑性原则、财产刑、资格刑与自由刑并用原则、刑罚与非刑罚方法并用原则*吴献萍.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68.。笔者认为,在归纳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之前,首先要认识到,这些原则是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所特有的,必须区别于一般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和刑法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在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被挑选出来的,必须符合环境犯罪刑事政策的目的;这些原则能够在环境刑法领域发挥作用,不仅有利于完善环境刑法,还能推动环境刑法学的发展。因此,基于上文对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概念和特征的分析,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原则应当包括责任谦抑原则、责任前置原则和经济制裁原则。
(一)责任谦抑原则
刑法谦抑主义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原则,也是刑法解释的指导原理,在制定和适用环境刑法时,也应当坚守刑法谦抑主义。换言之,环境刑法具有谦抑性,“并非所有的环境侵害必须受到刑罚的制裁”*[日]町野朔.环境刑法的综合研究[M].信山社,2003.7-8.。只有其他的社会统制方式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时,才能动用环境刑法这一最后的手段。现代社会重视人权保障,环境刑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应当限于最小限度的领域。为了保护重要的环境权,环境刑法还必须重视宽容精神而慎重处罚。所以,环境刑法不应全面介入环境保护领域,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应当具有自制的品格。
首先,环境刑事立法应当贯彻责任谦抑原则。不是所有的危害环境行为必须入罪,也不是所有的危害环境行为必须被追究刑事责任。责任谦抑原则通过限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惩罚必要性,从而限制了环境犯罪法定化的界限。日本的公害刑法、环境刑法是各种法律的处罚规定的集合体,并不一定在体系上整然有序。尽管位于其中心的是《公害罪法》(1970年),但实际运用中重要的是被害发生时的《日本刑法典》第211条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作为事前规制问题的《大气污染防止法》和《水质污浊防止法》等有关环境行政法的罚则*[日]中山研一,神山敏雄,齐藤丰治,浅田和茂.环境刑法概说[M].日本东京:成文堂,2003.33.。然而,在以行政从属型为主的环境刑法法制中,以上各种处罚规定的适用是受到各种条件限制的:《公害罪法》规定的排放有害物质罪及其结果加重犯,以公众的生命、身体为保护客体,在没有产生侵害这种法益的危险或实际结果时,不构成本罪,从而在特别刑法中排除了没有造成生命、身体法益侵害危险的排放有害物质行为的责任。与此相似的是,《日本刑法典》中的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也旨在保护人的生命、健康,即使存在业务上的过失,但没有导致这一结果时,也不会被处以5年以下惩役、监禁或50万日元以下罚金,从而在普通刑法中否定了没有发生致人死伤后果的业务上过失危害环境行为的责任。而在行政刑法中,行政法规从属性主要被反映在间接罚方式中,即刑罚权的发动从属于行政命令,只有在违反行政机关发出的改正命令后,才能被追究刑法上的责任。即使在导入直罚方式以后,只要行为违反行政法规,就可直接进行刑罚处罚,但是这种直罚制度仅被用于规制违反排放基准的犯罪行为。因此,无论是间接罚方式还是直罚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事责任的谦抑性。
其次,环境刑事司法应当贯彻责任谦抑原则。在环境刑法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若选择较轻刑种和较短刑期就能满足预防环境犯罪目的的,就没有必要选择较重刑种和较长刑期。这既是出于预防环境犯罪、保障环境犯罪者人权的需要,也是考虑到环境犯罪在客观上存在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一面。同时,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以直接造成不特定或多数人的伤亡为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经营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中间接导致人身伤亡或破坏生态平衡等严重后果。所以,无论是从追求预防还是从注重罪责的角度看,都没有必要对其适用重刑。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在对环境犯罪的自然人主体量刑时,情节较轻,能够判处拘役的,就不要判处略高于6个月的有期徒刑;情节较重,能够判处中等严重程度有期徒刑的,就不要在接近法定最高刑的区域判处有期徒刑;只有情节严重,必须在接近法定最高刑的区域量刑或选择更高档次的法定刑幅度的,才能根据罪责轻重判处严厉的刑罚。而且,在工业社会,单位实施环境犯罪的现象并不鲜见。在对环境犯罪的单位主体量刑时,所判处的罚金应与犯罪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尽量限制在犯罪单位的资本范围内,不能为了剥夺其再犯能力而处以高额罚金,使单位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当然,在刑事司法中贯彻责任谦抑原则,并不表明不能科处重刑。当环境犯罪对生态环境和他人的环境权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可以判处长期自由刑或高额罚金的。
最后,环境刑法执行应当贯彻责任谦抑原则。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环境犯罪,通过灵活运用各种刑罚执行制度,更有利于发挥刑罚的积极功能。例如,对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滥伐林木的自然人,通过宣告缓刑,并责令其赔偿损失或重新栽种树木,不仅会唤醒其规范意识,而且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这种开放的执行效果就大大优于收监执行的封闭效果。再如,对被判处高额罚金的污染环境的单位,若该单位在某行业占据重要地位,规模较大且有一定的盈利能力,但一次缴纳罚金确有困难,为保证其正常的资金周转,可以考虑判决其分期缴纳,以获得惩罚单位犯罪和保护单位合法财产之间的平衡。这种弹性的分期执行效果同样明显优于僵硬的一次执行效果。
(二)责任前置原则
鉴于工业发展对人类生活和生态环境带来的各种危险,有必要在实际的污染环境和破坏资源的后果发生之前,运用刑法抑制这些危险。因为,一旦这些危险变为现实,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将是永久的、不可逆转的、无法恢复的。所以,刑法不仅应当介入环保领域,而且要适当地提前介入。各国环境刑法普遍依靠危险犯立法,不仅在更早的阶段创设环境犯罪的罪责,而且使刑罚权的边界延伸到以前不曾涉足的地方。“处罚的早期化、处罚的严罚化、处罚的扩大化是危险社会的刑法表现出的特征。”*[日]高桥则夫.刑法保护的早期化与刑法的界限[J].法律时报,2003,75(2):16.同样,环境犯罪的责任前置带来的直接后果,也表现为处罚的早期化、严厉化和扩大化。
所谓环境犯罪处罚的早期化,是指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观向生态、环境本位主义的法益观的变化,应当对危害环境行为在更早的危险发生阶段处罚。为满足处罚早期化的需要,环境刑法在规定具体危险犯的同时,还创设了大量的抽象危险犯,以此强调应对环境犯罪的策略应当从事后处理向事前预防转移,更加积极地发挥刑罚的预防效果。例如,《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无权处理废弃物的犯罪构成要件(第326条第1项),是“绝对不以结果发生为必要的(危险犯!)”。在此,人类和动物的保护以各自分别选择所为的形式,单独地与水、大气和土壤的保护相并列*[德]克劳斯·梯德曼.德国及欧共体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M].西原春夫,宫泽浩一监译.日本东京:成文堂,1990.197.。换言之,该项既保护人类的生命、身体法益,也保护生态、环境法益,是一种双重的法益保护。而且,只要产生侵害双重法益的具体危险,就可根据该项进行处罚。日本行政刑法中也规定了许多类似的抽象危险犯。
所谓环境犯罪处罚的严厉化,是指由于公民环保意识的提高和保护自身环境权的迫切需求,即使对不太严重的危害环境行为也可予以刑罚处罚。相对以前对该行为不处罚的刑法而言,这种处罚规定的设置就体现了严厉化的倾向。处罚的严厉化,是为了唤醒或强化公民的环保意识,号召公民忠诚于刑法,使公民最终信赖刑法的实施效果,强化对部分危害环境行为的刑罚处罚。处罚的严厉化,在抑制危险发生的意义上,与“处罚的严罚化”具有相同的意义;但在防止结果发生的意义上,与“处罚的重罚化”的含义不同。即为了预防危害环境危险的发生,可以对违反环保标准或限制条件的行为处以一定的刑罚,但无需科处重刑。相反,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前置要求配置较轻的刑罚,以贯彻预防性环保的刑事政策和责任谦抑原则。简言之,责任的前置化应当带来处罚的轻缓化,而非处罚的重刑化;处罚的严厉化应体现在刑罚的必然性、适度性和及时性上,而非刑罚的残酷性上。
所谓环境犯罪处罚的扩大化,是指为了更有效地预防环境犯罪,刑事处罚的界限被扩张到以往没有作为环境犯罪论处的领域。一方面,处罚的扩大化会导致环境犯罪圈的扩张。即立法者通过继续对危害环境行为的犯罪化或修改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将刑罚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以前属于行政权规制的领域。例如,美国环保署对其认为属于有毒的废物都会列表公布,数量达几百种,从1984年起,对其进行多次修改,同时法院在审理时通过不断的解释把一些新型的废物纳入到《资源保护与回收法》(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的调控范围,所以适用范围越来越宽*肖松平.美国环境刑法研究[D].湘潭大学,2002.17.。另一方面,处罚的扩大化还会造成刑罚体系的膨胀。即立法者通过对新增的环境犯罪配置法定刑,在刑种和刑量方面丰富了原有的刑罚体系。例如,为应对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中由于放射性物质的扩散所造成的环境污染,日本专门制定了《放射性物质污染应对特别措施法》。根据该法第7章“罚则”的内容,对违法丢弃污染废弃物等的人,可处以5年以下惩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将其并科(第60条第1项)。不仅如此,其余各条项还对多种违法行为规定了惩役刑或罚金刑。
(三)经济制裁原则
根据“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人类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必须对生态系统予以适当照顾,在现实社会中就表现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兼顾;由于环境犯罪会损害环境的经济价值,通过运用罚金刑、没收财产、损害赔偿等经济性的制裁方式,可以实现刑罚的报应正义和满足罪刑均衡的要求;鉴于环境犯罪的利弊同体性,在追究其刑事责任时必须考虑到对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经济制裁方式将是抑制犯罪动机和实现刑罚目的的最佳方案。据此,经济制裁原则是指出于现代环境伦理观、环境权的经济内容和环境犯罪的经济特征的考虑,在追究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时,可以适当地多运用经济性的制裁方式,在弥补环境犯罪造成的物质损失的同时,也引导行为人进行理性的经济分析,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减少环境犯罪,实现刑法公正和刑法效益的统一。
第一,该原则以刑法的经济分析作为立论基础。所以,为了减少环境犯罪、防范环境风险,应当使罪犯承担的刑罚成本大于犯罪收益,从而鼓励其选择合法的行为模式(不去实施环境犯罪)或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措(尽量恢复被破坏的环境资源)。在此,“成本——收益”的比例关系不仅是分析环境犯罪人心理的模型,也是设计环境刑罚体系应当遵守的原则。
第二,该原则重视财产刑的制定和运用。环境是人类共有的财富,环境犯罪在破坏环境媒介物的同时,最终会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其中就包括经济发展条件。所以,无论是从经济损害方式还是从侵害整体经济的角度看,环境犯罪都可被视为一种经济犯罪。对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可谓是罚当其罪。因此,财产刑通过剥夺环境犯罪人一定的财产权益,使其负担较重的金钱给付义务,成为惩治环境犯罪的一种主要手段。
第三,该原则也注意发挥其他经济性制裁方式的作用。除了财产刑外,经济性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也成为环境犯罪制裁体系的有力补充,在我国《刑法》中主要有赔偿损失和行政罚款两种。这种处罚实际上体现了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结合。应当注意的是,尽管经济性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对惩罚和预防环境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经济性处理方法的功能同样不容小觑。
三、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
环境犯罪的刑事责任主要通过刑罚和非刑罚处理方法来实现。下文将结合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环境刑事立法的最新动向,探讨其刑罚配置的利弊得失和完善途径。
(一)德国环境犯罪责任的实现方式
在德国,环境犯罪都被规定在其刑法典第29章“危害环境”中,环境行政法只对违反秩序行为进行处罚。本章是1980年新增加的,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规定在单行刑法中了。而且,1994年颁布的《第二部环境犯罪防治法》扩大了环境刑法的范围,并加重了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德]汉斯·海茵里希·耶赛克.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刑法典序[A].德国刑法典(2002年修订)[C].徐久生,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27.。另外,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不仅是人的生命健康应当通过环境得到保护,使之免收危险的威胁,而且保护动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以及保护一个完整的自然,也都是属于一个符合人类尊严的生活内容的,因此是能够融入一个与人类需要相关的法益概念之中的(因此,今天在环境刑法中产生了生态性——人类中心的法益概念)*[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
在上述法益观的指导下,《德国刑法典》就环境罪刑规范作出了一些颇具特色的规定。例如,第326条(未经许可的垃圾处理)规定:“(1)未经许可在规划范围以外或背离规定的或许可的程序,存放、储存、排放或去除下列垃圾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1.可能含有或产生对人或动物具有公共危险且能传播毒剂或病原体的,2.具有致癌、严重危害或改变遗传基因的,3.具有爆炸、自燃或严重放射性的,或4.依其性质、特点或数量,足以持久地污染水域、空气或土地,或对此作其他不利改变的或危害动物、植物生存的垃圾。(2)违反禁令或缺乏必要的许可,将第1款所述垃圾运入、运出或运输途经本法效力范围的,处与前款相同之刑罚。(3)违反行政法义务,不将具有放射性的垃圾运走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4)犯第1款和第2款之罪而未遂的,亦应处罚。(5)过失犯本罪的,1.在第1款和第2款情形下,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2.在第3款情形下,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6)由于垃圾数量小,显然排除对环境,尤其是对人、水域、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植物的有害影响的,该行为不处罚。”该条的特点在于:其一,注重保护个人法益和非个人法益,形成了对生态法益的完整保护。其二,刑罚法规内部存在基本犯(Grunddelikt)和(加重的或减轻的)变形犯(Abwandlung)的关系,形成了构成要件群*[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326.。其三,根据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在构成要件之后规定了轻重不同的法定刑。这也明显体现在第330条(危害环境的特别严重情形)中。基于不同的危害环境情形,该条设置了“6个月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或3年以上自由刑”、“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或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三个幅度的法定刑。
(二)日本环境犯罪责任的实现方式
在日本,大多数环境犯罪被规定在刑法典之外的特别刑法、行政刑法中。由于所涉及到的罪名和罚则数量庞大,在此仅选取有代表性的公害刑法和环境刑法中的部分规范进行比较。
《日本刑法典》和《公害罪法》主要侧重对个人法益的保护,即环境犯罪侵害了人的生命、身体时,才会受到刑罚处罚。例如,《日本刑法典》第143条(污染水道)规定:“污染由水道供公众饮用的净水或者其水源,因而导致不能饮用的,处6个月以上7年以下惩役。”第144条(将毒物等混入净水)规定:“将毒物或者其他足以危害他人健康的物质混入供人引用的净水的,处3年以下惩役。”而第146条(将毒物等混入水道和将毒物等混入水道致死)规定:“将毒物或者其他足以危害他人健康的物质混入由水道供公众饮用的净水或者其水源的,处2年以上有期惩役;因而致人死亡的,处死刑、无期或者5年以上惩役。”可见,当发生死亡结果时,本罪是第143条、第144条规定之罪的结果加重犯*[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第六版)[M].日本东京:成文堂,2012.326.。与之相比,《公害罪法》的特色在于,并不需要具体地特定每个被害人。只要对公众的生命、身体产生危险的,就可处罚排放有毒物质的企业*[日]藤木英雄.公害犯罪[M].日本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 1975.17.。第2条(故意犯)和第3条(过失犯)即为适例。其中,第2条规定:“伴随工厂或事业厂的事业活动,排放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包括累积于身体内部的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下同),对公众的生命或者身体产生危险的,处3年以下惩役或者300万日元以下罚金。犯前项之罪,因而致人死伤的,处7年以下惩役或者500万日元以下罚金。”第3条采取了与该条同样的罪刑结构,只是处罚上略轻。总体而言,《日本刑法典》和《公害罪法》规定的都是属于刑事犯的环境犯罪。
作为行政犯的环境犯罪被规定在行政刑法中,即严格来说,在行政法规中对违反行政法义务的行为规定刑罚*[日]福田平.行政刑法[M].日本东京:有斐阁,1959.1.。日本行政刑法的特色在于:其一,基于某种行政管理的目的而制定,具有很强的目的性。其二,修改程序相对简便,能够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不断变化。其三,独立于刑法典存在,可以规定不同于刑法典的罪刑规范。其四,不仅处罚自然人犯罪,而且处罚法人犯罪。其五,涵盖行政管理的重要领域,行政刑罚规范分散在各种行政法中。在此,日本环境刑法侧重对生态法益的保护。例如,《放射性物质污染应对特别措施法》于2011年8月30日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除附则外,该法有7章,共计63条,分别为:第1章“总则”(第1条至第6条)、第2章“基本方针”(第7条)、第3章“监视及测定的实施”(第8条)、第4章“由事故的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废弃物的处理及清除放射污染等的措施等”(第9条至第42条)、第5章“费用”(第43条至第45条)、第6章“杂则”(第46条至第59条)和第7章“罚则”(第60条至第63条)。本法规定了多种违法处置放射性物质的行为,并配置了相应的法定刑。其中,第60条第1项第1号至第5号分别规定了违法丢弃污染废弃物等、违法焚烧特定废弃物、违法以特定废弃物的收集、搬运、保管或处分为业、违法以清除放射污染土壤的收集、搬运、保管或处分为业、违反适当保管特定废弃物等的措施命令五种类型的行为,法定刑均为“5年以下惩役或10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将其并科”。除了自然人实施上述行为会受到处罚外,法人也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第63条第1项第1号明确指出,实施第60条第1项第1号至第4号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对法人科处3亿日元以下的罚金刑,对自然人科处各本条的罚金刑。相对于《放射性物质污染应对特别措施法》设置的重刑,《水质污浊防止法》规定的刑罚较轻。其中,第32条规定,对特定设施等的设置或其构造等的变更不提出申请或提出虚假申请的,处3个月以下惩役或30万日元以下罚金。第33条第1项第2号也规定,违法设置特定设施或有害物质储藏指定设施,或者变更其构造、设备、使用方法或处理方法的,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这鲜明地体现了日本行政刑法不同于德国环境刑法之处。
(三)环境犯罪刑事责任实现方式的应然选择
可见,德国环境犯罪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限于自由刑和罚金刑两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德国废除了死刑,自由刑和罚金刑成为现代德国刑罚体系的支柱,另一方面是由于人道主义原则(Grundsatz der Humanitaet)这一刑事政策的基础要求减少刑罚的适用,并为罪犯回归社会尽量提供帮助,于是,刑罚和保安处分的双轨制(die Zweispurigkeit der Strafe und Massregeln)被确立。在现有刑罚体系下,环境犯罪者最重可被处以终身自由刑,最轻可被处以5欧元罚金。同时,出于再社会化的考虑,也可对其适用矫正措施中的保安监督和职业禁止。德国环境刑法同时保护生命、身体法益和生态、环境法益,对侵害不同法益的犯罪配置的法定刑也不同。总的来看,对主要侵害生命、身体法益的犯罪(第28章危害公共安全之罪)配置的法定刑偏重,也只有对这类犯罪才能适用终身自由刑,且较少规定罚金刑;对主要侵害生态、环境法益的犯罪(第29章危害环境之罪)配置的法定刑较轻,最高刑为10年自由刑,且基本上都规定了罚金刑。所以,德国环境刑法在整体上较为轻缓,以非长期自由刑和明确的罚金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值得借鉴。但是,能够适用于环境犯罪的保安处分的种类很少,其实际效果令人怀疑,所以,不得不指出,缺少专门针对环境犯罪的非刑罚措施,是德国环境刑法的一大漏洞。
而日本环境犯罪责任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惩役刑和罚金刑,对毒物等混入水道及其致死伤罪规定死刑和无期惩役是一个例外。《日本刑法典》中规定的环境犯罪数量和刑罚比重远不及其他法律中的环境刑罚法规,所以,可以认为,环境刑法的立法中心已经从普通刑法转移到特别刑法和行政刑法。在现有刑罚体系下,环境犯罪者一般会被处以较短的惩役刑或较少的罚金刑。但是,特别刑法和行政刑法引入了两罚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人环境犯罪的责任,这比起德国只能通过处罚违反秩序行为来追究法人责任的做法,无疑是一大进步。《日本刑法典》是传统的刑事刑法,规制环境犯罪的效果有限。《公害罪法》带有明显的应急性质,其适用领域随着人们对各环境要素保护的重视而迅速缩小。所以,只有《水质污浊防止法》等行政刑法才真正预示了日本今后环境刑法的立法方向。由于法益保护的早期化,这些行政刑法将部分违法行为升格为犯罪行为,并配置了相当轻缓的法定刑。所以,适度犯罪化和刑罚轻缓化依然是日本环境刑法的主要特征。而且,适度犯罪化必然导致刑罚轻缓化,刑罚轻缓化以适度犯罪化为前提。这对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颇具启发意义。
反观我国《刑法》为环境犯罪配置的法定刑,主刑中除了死刑和无期徒刑,附加刑中除了剥夺政治权利,环境犯罪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涵盖了其余所有的刑种。刑法典对每种环境犯罪都规定了有期徒刑、拘役和罚金刑,突出了自由刑和财产刑的重要作用,值得称道。法定最高刑为15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四个,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一个,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六个,法定最高刑为5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两个,法定最高刑为3年有期徒刑的犯罪两个,刑罚整体偏重,需要反思。根本原因在于,立法机关将环境犯罪视为一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被置于社会管理的必要性之下,由此极大地贬损了环境的生态价值和精神价值。所以,如果危害环境行为没有严重威胁或侵害人类社会的话,就无需动用刑罚规制;一旦严重侵害人类利益,自然要运用重刑惩治。因此,重刑结构与环境伦理观和法益观密不可分。显然,现行刑罚体系不能完全满足预防性环保的刑事政策的要求,刑法应当提前介入,对生态环境给予更加周全的保护。即使在维持现行环境犯罪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对犯罪构成进行实质的解释以及完善刑罚体系和非刑措施,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
A New Study on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LI Guan-yu
(LawSchoolofCentralChinaNormalUniversityWuhan,Wuhan,Hubei430079,China)
When some harmful behavior against the environment had constituted a crime, it must bear the corresponding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which is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It is not only the legal consequences, but also the premise of application of penalty or non-penalty methods. On investigating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t should pursue the principles of modesty, preposition and economic sanctions. Compared to Germany and Japan, the whole punishment in our criminal law for environmental crimes tends to severe, that can negatively affect preventive criminal policy and appropriat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environmental crimes; conception; property; principle; Implementation
2015-05-27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公害犯罪的惩治与传统刑法理论的创新研究”(批准号:13BFX051))以及中国法学会2014年度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污染环境罪的客观归责研究”(课题编号:CLS(2014)D038)之阶段性成果。
李冠煜,男,华中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刑法学。
DF611
A
1672-769X(2015)05-004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