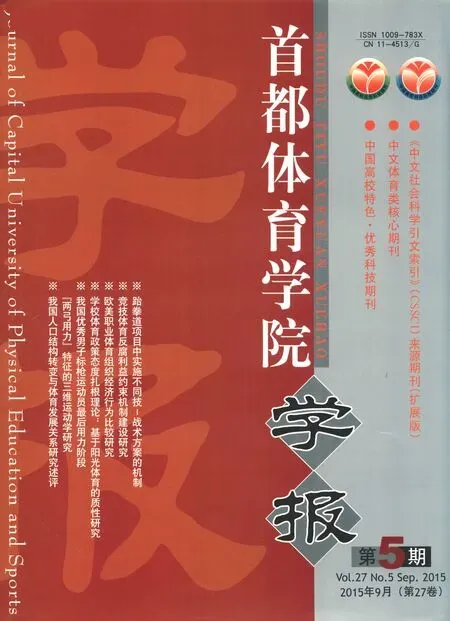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体育思想研究
刘 晖
清末以来,西方各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消了昔日清政府“天朝上国”的迷梦,昔日经济繁荣、江山一统、文化强盛的大清帝国苟延残喘于西方列强的铁蹄下,呈现出经济凋敝、政治衰败、文化落后的末世凄景。于是在清政府内部洋务派筹办洋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救国宣告破产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承担起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时代重任。救国救民首先在于“强我种族”,而强我种族,要以提倡体育为本。康有为认为,“列强之所以能够称霸称雄,是由于他们尚武;严复引进了优胜劣汰、自强保种的进化论思想,主张以尚武强国精神来鼓起中国人的斗志。在维新派志士的提倡下,尚武思潮在思想界广泛传播,由此国人无不思强健体魄,以改固有文明之陋习”[1]。为此,梁启超和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本着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先后发出了借体育强种强国的时代呼喊。
梁启超的体育思想集中展现在他的作品和言论中,他在《论尚武》(见《新民说》一文)一章中所称赞的“尚武以强种、保国”等体育主张,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提倡武勇、推崇体育的著作,为近代中国体育的萌芽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前提和理论根据。
孙中山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体制,其光辉的历史业绩和壮烈的人生事迹足以彪炳史册。孙中山以“民族、民权、民生”为自己毕生的行动纲领:他心忧民族命运,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心系民族权力,反对满洲贵族的统治;他不忘民生艰难,积极提倡健体的体育。孙中山提出的强种、保国的体育思想,把历来为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所不耻的体育的意义提高到了“民族存亡”和“国家兴衰”的历史高度,可谓“国家兴亡,体育有责”。
时至今日,重新翻开记载梁启超和孙中山体育主张与见解的字句篇章,不仅能够使人洞见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领袖的体育思想的全貌,也依然能够给今人以诸多有益的启发。
1 尚武以“强种”: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
传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着“文德为上,武德为下”的重文轻武的文化心理习俗,人民大众根据“好铁不打钉”的生产经验,进而形成了“好男儿不当兵”的文化偏见。为此,梁启超认为:我国人因喜好和平,缺乏尚武民风,而拒斥战争导致屡被列强欺凌的悲惨境遇,实则是我华夏民族之“奇耻大辱”。由于 “苟无尚武之国民,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众民,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2]。据此,他进而提出了“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侍以成立,而文明所以赖以维持者也”[2]的论断。一个国家的国民若是缺乏刚强的意志力量,即使有超人的智慧和德行,也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尚武精神”是一个国家之所以能够立国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武士精神和尚力思潮是梁启超“民族思想”的中心内容,二者都是国家安全和民族生息的内在要求,而民族精神中的尚武习俗,必须通过艰苦的军事操练和国民体育来养成。为此,梁启超极力推崇尚武的体育精神,以养成体格健壮的国民。他在《新民说》的《论尚武》一节中,高度赞扬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军国民教育”和“全民体育”的教育方式,文中描述了斯巴达人从幼年时期一直到老年阶段所受到的军事体育教育,“斯巴达人自幼从军,刻苦练习跑跳投等各种体育技能;饮食粗糙,近乎野蛮,以养成勤奋耐劳、不怕寒暑的生活作风和豪侠勇敢、不惧危亡的精神气度;经历此种近乎残酷训练的斯巴达人,不论老幼,无不把生死置之度外,无不勇敢好胜”[3]。
梁启超指出,西欧诸国无不曾经效仿古希腊时期斯巴达城邦的军事体育制度,实行“军国民教育”,重视体育在国民素质和国民品格养成中的作用,“除‘军事体操’外,击剑、跑马、足球、游泳、竞渡诸戏,俱得提倡,必使国人无不有‘军国民’之健壮体质”[4]。实施“军国民教育”是欧洲列强国力强大的重要原因,为此,积贫积弱的华夏民族,必须借体育之力,以提高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和精神状态,而梁启超这种尚武以“强种”的体育思想正是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
孙中山诞生在广东省中山县(原香山县)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生活在农村的幼年孙中山喜好各种体育游戏,经常与儿时的玩伴们一起泅水、踢毽球、登山、钓鱼、捉蛐蛐,同时也对传统武术情有独钟。青年时代的孙中山,精力充沛,喜欢各种体育运动,在维持身体健康的同时,注意营养饮食的有机搭配,曾研习一种流传于日本的“抵抗养生术”。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孙中山赴美就读于夏威夷州的意奥兰尼书院和奥阿胡书院,期间系统接受了西式近代教育。作为留学生的孙中山不但立下了“变革祖国,拯救受难同胞”的鸿鹄之志,还系统学习了近代西方学校的体育运动项目。这对孙中山形成“强种”的体育观念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孙中山青年时期所生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江河日下、国势衰微,内忧外患不断,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着深重的生存危局。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引起国人强烈的生存危机感,我国民纷纷意识到“自强保种”迫在眉睫,于是知识阶层中的先进人物纷纷发出了以体育为手段“富国强兵、健体强种”的时代呼喊。
孙中山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提出“强种保国、强民自卫”的号召,他认为“体格健壮,才能实施有效的防卫,也才能保家卫国;国民身体的强健才能保证国家的生生不息”[5]。在上海精武体育会积极活动的1915年,孙中山在“精武会”的毕业典礼上,极力提倡我国固有之技击术,“技击术为中国国粹,自枪炮发明之后国技遂微”[5],他接着举例论证技击术在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通过此次欧洲战争的实践证明,枪炮为冲锋之用,肉搏则非技击术不可”[5],并预测“随着科学日益进步,枪炮终将穷于用,而中国将来与列强相周旋最后五分钟必藉于技击术为强有力之后盾”[5]。孙中山从救国救民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尚武以强种的体育思想,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依然闪烁着先哲的智慧光芒,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 强身以“保国”: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
梁启超受到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著《原强》和《天演论》的启发,认为:“人格包括品行、智识和体力;国民、新民和现代人包括民权、民智和民力;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新民权、开民智和鼓民力”。从梁启超的思想来看,他提倡“德”“智”“体”“美”共同发展的全面教育。梁启超将兴办新式学堂、培育变法人才作为变法图强的关键。他认为中国遭受外族欺凌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才”匮乏、“民智”愚昧、“教育”落后。梁启超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顽强的变法热情,指出欲使中国从贫弱走向富强,必须摒弃祖宗成法,摒弃祖宗成法,就要从变革教育、启迪民智、养成新民开始。在解释鼓民力的“力”时,梁启超指出,力指的是人的“生命力”“意志力”“体力”和“军力”。而旺盛的生命力是国民个体实现救国理想的必备物质条件,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生发出坚定的报国之心,也才能有相应的实际行动;因此,梁启超不止一次地指出:“身子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越,所以要给他种种体育。”[6]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在他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设计出“儿童教育”的课程内容,其中有“每天下午上课前习体操,略依幼学操身之法,或一月或二月尽一课,由教师指导,操毕听其玩耍不禁”[7]4的有关儿童体育的专门规定。
梁启超肯定进行智力游戏、参与体育运动对儿童身心的积极影响,并且提议尽可能地缩短儿童的学时,将儿童剩余的精力用于培养各种体育技能的课外活动。儿童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希望,儿童的身体健康是国民素质提高、强种强国的前提。梁启超以体育为手段,形成国民顽强的生命力和“培养健壮幼儿”来实现保存民族血脉、国家命脉的强身以“保国”的体育思想是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
1896年,英国人在一篇文章中称道,“中国人实为东方‘病夫’”,而且其思想状态,“麻木不仁久矣”(《中国实情》)。至此之后,“东方病夫”就成为了欧美诸国对我国民的挑衅性称呼。孙中山不无愤慨地写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东亚病夫’的中国,自然而然地成了这样一块用以满足欧洲野心的地方”。为了尽快摆脱“东亚病夫”的称号,中国的知识阶层普遍把振我民风、强我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我国固有的技击术上。由此,孙中山号召国民,“要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就要去学习技击术”,同时,“还要去学欧美之长”。1905年,在孙中山的提议和领导下,同盟会会员在日本东京建立了“体育会”,将体育技能和军事技术相融合,举办各种形式的训练,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时,孙中山指出,千百年以前的中国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方面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而贫困落后的今日中国要想富强,则有赖于“一跃之功”。他积极鼓励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练习体育的学生们要以“一跃之功”,证明“东亚病夫”实则是列强对我国家的歧视和蔑称。孙中山深感于我国所面临的深刻的国家生存危机和自鸦片输入后国民身体羸弱的客观现实,极力肯定体育对于国家强盛和民族体质提升的重要意义,“体育是我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根本”,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国民教育,体育先行”。先生在国民身体素质的提高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力图把每一个流淌着华夏民族血液的人塑造成为人格健全的“文明人”,进而实现他体育强国的目的。否则,就会使“堂堂中国人”失去发愤图强的机会。处在弱肉强食、生存竞争极为惨烈的时代,倘若“不知求自卫自强之道,则难以立足于世界”[7]4;因此,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体现了在民族激烈竞争之时他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他提倡以体育为手段强身以“保国”的体育思想是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
3 健体以“摄生”:个体生命意识的关照
梁启超接受过系统的西式教育,能够用西方科学的观点认识世界,坚持世界是由永恒变动的物质构成的观点,坚信宇宙万物无不是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动中;同时,他吸收中国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精华,确信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还是作为集体的国家的生存都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因此,梁启超尖锐地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不通,道德不达,人的智体堵塞,国势日弱一日,积弊深重”的原因在于“喜静不动”[8],而这种喜静不动和宇宙“无时不动”的运行规律恰好相反。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揭示了中国国势日弱、积重难返的深层社会原因:“学者以束身自好为第一流,语以变武科,恐民挟兵器以为乱,生此一念,百度不张”[9]。力主社会变革的梁启超对我国延续已久的喜静传统深恶痛绝,他说:“无动也,皆天下最可耻之事也”[9];因此,国家必须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国家要“大变动”,也只有进行社会变革,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相应地,每一个国民作为构成国家整体的生命个体,也需要“动”,由于动可以强身健体,个人以“动”健体“摄生”才能保证国家机体的强健和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梁启超从生理学的角度认为,“动”对于人体血管系统的畅通,大脑的灵活运转都有莫大的益处。他撰文指出动力(即体育运动)对于人体气血运行、生命意识提升等方面的功效“不可思议”,反之,若没有“动力”,人体则“为麻木瘩痹,而体魄之弱随之”[8]。梁启超否定“主静克动”的传统陋习(我国古传有静功,它也是修心养体的练功方法之一。梁启超在否定静时,未能将俗指的“静”与“静功”分别清楚(这是梁启超认识的局限性),提倡健体以“摄生”的体育思想,是梁氏作为社会改革家在关注国家整体命运的同时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照。
1923年上海的一家报纸(4月18日《民国日报》)刊载了一则名为“孙文介绍名医—孙中山刊登的一则广告”的文章,文章中称:“……原来吾国人民极嗜油肉,伤害天质,国民体质改良,非行高野主义不可。”[10]“高野”为孙中山使用过的化名,“高野主义”在这里指孙中山的主张。从这篇警醒国人提高个体生命意识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我国人民作为生命个体的深切关照,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国人不行“高野主义”及“嗜食油肉”对身体健康的危害,指出要提高国人身心素质“非行高野主义不可”。社会经验告诉人们,要提高个体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必须提高个体的生命意识,使体育运动和日常保健紧密地联系起来。
在“摄生”方面,孙中山除积极坚持体育运动外,尤其看重通过卫生方式维持身体的健康。他在《建国方略》一文中对“摄生”有独到的见解:“人间之疾病,多半从饮食不节而来。通常饮食养生之大要,则不外乎有节而已。不为过量之食即为养生第一要诀也”[10]。孙中山按照人体生理学的原理,指出人不宜饮食过量,过量则对人体的器官造成压力,日久必生病,也不能“少食”“少食”则不能供给健康人体日常生活及从事体育运动所需要的营养和能量,因此,饮食应该以适量为要。综上所述,孙中山提倡通过体育运动和健康饮食健体,而以“摄生”的体育思想则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照。
4 结束语
重新翻开记载梁启超和孙中山体育主张与见解的字句篇章,不仅能够使人洞见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政治领袖的体育思想的全貌,也依然能够给今人以诸多有益的启发。
梁启超极力推崇尚武的体育精神,他这种尚武以“强种”的体育思想正是民族忧患意识的体现。孙中山从救国救民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尚武以强种的体育思想,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忧患意识。梁启超的尚武,主要是推崇西方由武力而强盛,“外看”的成分多;孙中山的尚武,主要是提倡我国固有的技击术,“内看”的成分占优势。梁启超作为理论大家,有《新民说·论尚武》存世;孙中山是革命家,注重身体力行。
梁启超以体育为手段,形成国民顽强的生命力和“培养健壮幼儿”来实现保存民族血脉、国家命脉的强身以“保国”的体育思想是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体现了在民族激烈竞争之时他对于民族生存发展的思考”,他提倡以体育为手段强身“保国”的体育思想也是民族生存意识的彰显。梁启超主要从“新民”的角度出发,主张培养健壮婴儿,保存民族血脉;孙中山从国家富强角度,提倡技击术,以脱掉“病夫”的耻辱帽子。
梁启超否定“主静克动”的传统陋习,提倡健体以“摄生”的体育思想,是他作为社会改革家在关注国家整体命运时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照。孙中山提倡通过体育运动和健康饮食的健体以“摄生”的体育思想,这也是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关照。
[1]胡玉玺,安汝杰.试论清代少林武术发展的社会环境[J].体育文化导刊,2014(6):163.
[2]李杰,李龙洙.简论梁启超的“尚武”体育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1):21-22.
[3]胡超,律海涛.梁启超的体育思想[J].体育世界·学术,2008(2):4-5.
[4]周敏.论梁启超的体育思想与实践[J].山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学报,1998,13(1):96-97.
[5]律海涛.梁启超新民思想与当代体育教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12):341-342.
[6]陈亮.孙中山体育思想刍议[J].南方论刊,2012(9):58.
[7]沈先金.孙中山的足迹[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5.
[8]刘云朝,刘丽,曾丽君.论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与实践[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12,28(2):5.
[9]杨昆普.孙中山的体育思想与实践[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9):34.
[10]胡惠芳,邹政.论孙中山的体育思想[J].池州学院学报,2010,24(5):108.
-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的其它文章
- 竞技体育反腐利益约束机制建设研究
- 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体育发展关系研究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