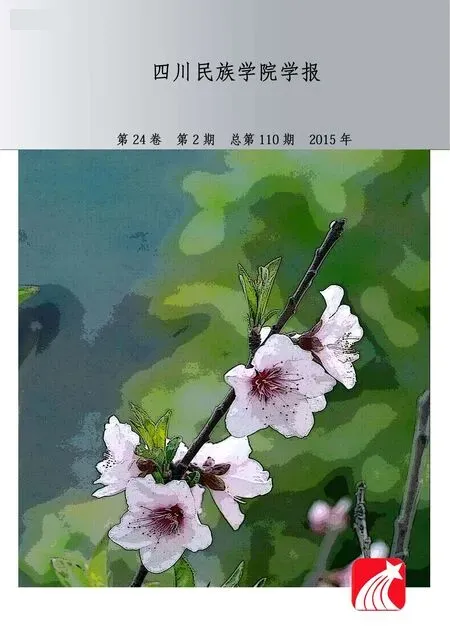“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特点与属性
焦虎三 仲昭铭
★民族研究★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特点与属性
焦虎三 仲昭铭
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时期的人形彩陶艺术品,是中国彩陶文化的一大特色。以上文化类型与古羌有所关联或存在源流关系。本文分析了这一时期人形彩陶艺术品艺术、文化与工艺的特点,并对其属性进行了剖析,认为历史与社会属性、实践与实用属性、精神与信仰属性共同促成了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出现与发展。
马家窑;羌族;人形彩陶;特点
彩陶,亦称陶瓷绘画,是指在打磨光滑的橙红色陶坯上,以天然的矿物质颜料进行描绘,用赭石和氧化锰作呈色元素,然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高度统一,达到装饰美化效果的陶器。中国彩陶虽发现较晚,但考古证明其彩陶的历史十分久远,彩陶文化分布广泛,延续时间很长,并且在世界彩陶历史中艺术成就最高。“在已发掘出的数以千计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有数以万计的彩陶碎片和美不胜收的彩陶器物。据统计,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七千余个,大多都有陶器遗存,其中有二千多处有彩陶或彩陶片,每处数量不等,但其总数可以万计。”[1]
中国原始彩陶因时间的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其中,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半山时期的彩陶器,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阶段,显示博大、成熟和完美的特色;至马厂时期、齐家文化、辛店文化、诺木洪文化等遗址中,彩陶在数量与规模上虽有所递减,但在造型与纹样上都有所发展和创新。而这些文化类型,现大多认为与古羌有所关联或存在源流关系。[2]
将彩陶器制成人形,或在彩陶上通过塑、刻、绘等手法塑造和表现人面 (头)与人身 (像),是中国彩陶文化的一大特色,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其中,尤以黄河中、上流域更为普遍。这一区域彩陶与人像、人形有关的艺术演化历史,从陶绘的角度而言,可以师赵村文化序列为例加以说明,即:彩陶从大地湾一期文化开始,直至第六期。其间延续发展不问断,各期都有数量不等的彩陶,一般而言,彩陶数量是从少到多,发展至第七期后便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彩纹各期均以几何彩图案为主。但各期具体内容不同,并且各有各的主纹,如大地湾一期与师赵村一期皆为简单的宽带纹,第二期为直边三角形;第三期为弧边三角纹或涡纹,第四、五期为波浪纹或旋涡纹,第六期为齿带纹与圆圈纹等为主要花纹。象征性花纹亦表现出各自的特征与风貌:如第二期以鱼纹为主,第三、四期为鸟纹或变形鸟纹:第五期为全蛙纹;第六期为人像纹,而动物纹却较罕见。可见,与人像、人形有关的彩纹艺术,应成形与成熟于第六期,即在半山-马厂文化时期。而从陶塑的角度而言,在以上众多文化类型的原始彩陶艺术品中,陶塑的人物像,即人物形的陶器皿,较早见于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 (陶塑人头像更早见于秦安大地湾),其后,人像彩陶壶首见于半山-马厂文化时期,其中不乏精品,也给后来者解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如马厂时期出土的裸体人像彩陶壶:“在这个彩陶壶的颈腹部有一个捏塑成的裸体全身人像,头部五官俱全,小眼、人口、高鼻梁,双臂捧腹,形态可掬。尤其是袒露的乳房和性器官,既有男性的特征,又有女性的特征,在性别问题上.学术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女性,有人认为是男性,还有人认为是男女复合体。”[3]故我们将之称为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
从艺术类形的角度而言,人物形陶器皿,可细分为 “单独塑 (绘)人体像”与 “装饰于陶器皿上的人头像”两大类。[4]这些宝贵而真实的人体造像,为我们今天从人种学、民族学、宗教学与艺术学等诸方面研究古羌的人种特征、社会生活、文化面貌与原始宗教信仰都提供了形象而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原古羌人在西北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存中出土的与此相关的文物,其数量与种类,均为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所罕见。
一、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特点
彩陶不仅是原始先民器用的产品,也是他们精神世界的物化产品。程金城就认为:“原始先民将人对自身的感受投射于彩陶的造型过程之中,以人的形体作为彩陶造型的参照,或者说,人的形体被无意间作为 ‘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最直接的参照体系。人形与器形或隐或现的对应关系,在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彩陶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1]他同时认为,器形人形化表明“原始先民有了将彩陶视为人自身的意识”。[1]
(一)“古羌人形彩陶艺术”艺术特色鲜明,表现对象独特而具体,生动而形象,极富艺术感染力
从艺术角度而言,“人形彩陶艺术”因其形制独特,表现力与其他彩陶艺术有明显区别,事实上已成为我国丰富多彩的彩陶艺术中的单独门类。“人形陶制艺术”专注于 “人”的表现,专注于对人精神世界的探索,是对彩陶艺术在思想境界与艺术表达力上的深化与提升。
(二)“古羌人形彩陶艺术”是人类对自身认知提高的产物,它不同于一般的装饰图案,文化色彩强烈,表达思想与信仰的倾向明显,是属于思想与文化、艺术与宗教合一的产物
从文化角度而言,“人形彩陶艺术”据有强烈的文化意味,信仰色彩浓郁,甚至不排除有些陶器本身就是巫术的器物。“这一时期的人物雕塑除了个别胸像、坐像和立像外,绝大于部分为头像。这表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人类对自身有了更深刻认识,因为头乃 ‘六阳’所聚之处,人的智慧、力量和美都集中在头部。同时也说明原始雕塑家的技艺此时已有了很大提高,已能对人的外貌和精神进行比较深入的刻画。”[5]
又如在对乐都柳湾出土的马厂-半山文化时期人像彩陶壶解读时,有学者就认为:附着陶瓶首部的 “女性人物雕塑”是原始宗教活动的产物:“塑造出来的作为陶瓶的器首的人头像即可以认为是祖先形象的象征。从实用角度来看,这些人头形的陶瓶的实用功能远远比不上那些陶盆等的功能,他们无法作为盛装的工具,而如果认为它们是被制作出来作为欣赏的装饰品则显然有些不太实际。将瓶口塑造为人头形状显然是刻意的,其中秦安大地湾陶瓶的瓶身有被修补过的痕迹,显然陶瓶的拥有者是很珍视陶瓶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陶瓶的顶部都有一些小孔,这些小孔和陶罐葬盆盖子上的小孔很相似,陶罐盆葬盖上的小孔据推测是用于灵魂的出入只用。那么,这些陶瓶可看作是祖先灵魂的栖息地,祖先的灵魂通过这些小气孔出入,因此这些人头像无疑是祖先形象的象征。”[6]
(三)“古羌人形彩陶艺术”工艺精细,刻绘传神,手法多样,充分代表了我国原始彩陶艺术的最高技艺水准
从工艺角度而言,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中的 “人形彩陶艺术”类别多样,手法多变,工艺多彩。工艺手法有雕、塑、刻、绘等,光雕就有圆雕、浮雕与贴雕、镂空等数种,而且这几种手法有时还综合运用;塑造人物形象有头形、半身和全身几种,有面、有像、有形,形象丰富而多变。如:马家窑文化彩陶本身就流行器皿上的浮雕和捏塑相结合,人头形陶瓮、人面形器盖等大物用此工艺塑造并烧制。上文谈及的柳湾裸体人像彩陶壶最为典型。这件陶壶器形唇微侈,腹稍鼓,双腹耳,颈肩部无明显分界,陶壶正面和后面原均绘人形纹,双腹耳上方绘两大圆圈纹,填充网格。正面中部人形纹后被略去,另加浮雕人头像及人体部。整个作品手法多样,融烧制、彩绘、浮雕与捏塑为一体,浑然天成。在材质与原材的运用上,这一时期也多种多样:“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分析、x射线衍射仪综合分析,结果表明该陶片黑色颜料以磁铁矿、软锰矿、黑锰矿等为主,陶衣则是由较细的陶土制成,以白云石、石英、赤铁矿和钙长石为主,胎体是以高岭土、蒙脱石为主的粘土。”[7]
二、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属性
属性是事物的性质与关系,它与事物密不可分。事物都是有属性的事物,属性也都是事物的属性。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特点,源于其特质的属性。
(一)历史与社会属性是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存在的基础
恩格斯1844年在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 “过去和现在”》一文中言及:“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 ‘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8]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来,宗教与艺术的发生与发展的根源都在于唯物主义原则下人与自然界的原始关系,也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原则下人与社会的原始关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
在我们对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属性的分析,首先必须认识到这一切不仅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历史与社会属性是产生这一独特艺术形态的基础。“古羌人形彩陶艺术”始于马家窑文化,普遍于马厂-半山文化时期,是和这一时期生产发展与历史进步密不可分的。
就马家窑文化而言,东乡林家遗址说明其已进入铜器时代,F20:18出土有一件合范铸成的铜刀,长12.5厘米,弧背直刃,前尖微翘,条形短柄,柄上留有镶柄痕迹。这在当时中国所有新石器时代可谓 “鹤立鸡群”。在石器种类上,马家窑文化中林家有22种之多,比起石岭下类型多出一倍,“而石锛、石钻头、条形石匕等,都是大地湾石岭下类型所没有的。特别是石锛,一直是大地湾的带半坡因素期,带庙底沟因素期、石岭下类型所没有的。”[9]考古发现已证明,林家已有较发达的农业,有稷、粟和大麻籽,“从小穗的花序的细枝割断痕迹,证明是用锋利的刀类割下来的。”[9]
至马厂-半山文化时期,社会经济事业发展更进了一步,当时原始居民以原始农业为土,种植物主要是粟,次为糜子。粟在各遗址或墓地都有较多的发现,如柳湾马厂类划墓中随葬的粗陶瓮内普遍装有粟,M339中14件粗陶瓮都满盛粟粒。鸳鸯池M34内一件大陶瓮中所盛粟,按陶瓮容积计算可达66.9公斤。出土这些数量可观的粟遗存说明当时居民是以粟为土要粮食,而且有了相当多的粮食剩余可用作随葬品,这也进一步说明农业与相关的手工业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制陶业发达,发现半山、马厂类型的陶器数量位居史前文化诸类型之首。据柳湾、阳山、地巴坪、土谷台、鸳鸯池、花寨子、张家台7处遗址统计,共出土陶器17396件.如加上陶纺轮等制品,达2万余件,其中彩陶约占2/3。生产陶器已有专门的制陶窑场。在兰州白道沟坪遗址发现较完整的窑址12座。从窑场可看出制陶业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可生产数量可观的陶器”。[10]
在社会属性方面,柳湾出土的马厂-半山文化时期人像彩陶壶,有学者就释为 “裸体人像彩陶壶”,认为其是原始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这种作法是原始宗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这种两性同体崇拜,是母权同父权斗争的产物。”[3]这一点,在相关遗址也得到印证,如:兰州花寨子男性墓中多有石斧,女性墓中多有石纺轮;土谷台男性墓中多有石斧、石锛,女性墓中多有石纺轮。[11]证明马厂-半山文化时期已有男女性别的分工,面对经济的发展与,男、女之间的社会性别身份已经形成,我们今天俗称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身份与家庭身份已据有初形,这毫无疑问,会影响到母权至父权的过渡。又如甘肃宁定半山遗址曾出土几件彩陶人头饰器盖,人头上画满横、竖、斜各种不同的线条,人们一般认为那是原始人类文身的遗痕;甘肃省马厂文化的人首彩绘陶塑表现了 “披发剔面”的习俗,这都是当时的社会实践与现实生活在“人形彩陶艺术”中的真实再现。这一切综合说明,历史与社会属性是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存在的基础,也是促使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产生的物质基础。
(二)实践与实用属性是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产生的条件
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古羌人形彩陶艺术”来源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社会生活的实践以及实践中产生的意识与思想,通过艺术的手法得以表现和升华,通过手工制作来加以完成,可见,手工实践与实用的属性是产生这一独特艺术形态的条件。如陈文华在 《农业考古》便刊文指出:“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类孕妇裸体像是依附在陶器上,结合为完美的整体。这类文物多发现于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女性塑像的陶器虽然都着重表现孕妇的形象,都有祈求人口繁殖、农业丰收的宗教或巫术的意义,但其用途应有所不同。前一类是独立的女性偶像,具有单一的被人供奉膜拜的用途,是女神的化身。后一类是附属在实用容器上,其中空的腹腔可以容纳物品,通常是装纳谷物之类,多用于贮种、孕种和祈殖等农事巫术场合,有一定的阶段性和时间性。”[12]“实用容器”从巫术法器中的分离,说明在实践中,人们已开始考虑器物的实用价值。
(三)精神与信仰属性是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表达的方向
在约翰·B·诺斯等人看来,绘画雕塑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宗教用途的巫术,“无论萨满是否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也许主持过一种仪式,造成了巫术在绘画和泥人中的运用。”[13]现今研究证明,“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出现的确与巫术与宗教行为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裸体人像彩陶壶的出土,证实了史前时期本地区母权制氏族社会的存在,说明了女性崇拜在史前人类信仰中的崇高地位:“柳湾裸体人像正是青蛙图腾崇拜朝着女娲造人神话过渡时期的一种文化形象,如果说柳湾裸体人像就是寓意着女娲形象,那么女娲形象至少在我国新石器时代便已产生。”[14]
更重要之处在于,如宋兆麟在针对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出土小型石雕刻人像品分析指出的那样,这是巫觋执行巫术的手段。[15]同理,“古羌人形彩陶制品”部分也可以视为巫术的产物与用器,这说时,此一时期,古羌人的精神与信仰世界已经有了较复杂与多样的显现形态,而巫术实践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或生产活动之中。这在同期出土文物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如:师赵村六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一件 “人像彩陶罐”:泥质红陶。质地细致,侈口短颈,深腹平底。黑彩绘、口侧绘一宽带纹,肩部饰五道平行条纹。在肩部浮塑一完整人首,雕塑出眼、口、鼻等器官。头顶上塑有半圆形发髻,中间穿儿,当是插发笄的。在头部下面用黒彩画出人的躯体及四肢,两手掌还勾画出手指。颈部两侧各画一 “⊕”形符号,头部两侧画有齿边的羽毛纹,左在遥相对应。人身躯左侧画纵行齿带纹,右侧遍布十字纹,腹部中失绘一树枝纹,背部画纵行排列整齐的波浪纹。器形完整,口径14.3厘米,高23厘米,底径9.9厘米。“该陶罐整个塑画似富有神秘的宗教色彩,推测该人像可能象征氏族中具有某种特殊身份或属于巫师一类的人物。”[16]师赵村六期文化遗存相当于半山-马厂文化期,该头像头部有饰,颈部、身躯布绘有⊕纹和十字纹,这两种符号在原始文化中都是带有生殖崇拜意义的巫符,⊕纹也有指代太阳的意义,人像全身布满各种纹饰,像文身之状,认定为 “巫师一类的人物”也并非言之无据。又如甘肃省永昌县鸳鸯池51号墓出土的石雕人面饰,其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全器于稚拙中透露出几分神秘,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其精湛特异的制作工艺反映了原始人类的智慧和技巧。鸳鸯池51号墓还出土了若干陶、石、骨器以及400多颗骨珠,表明墓主是一个具有较高身份的人物,或者是一个巫师。因此有的学者认为该面饰 ‘可能是神像,也可能是巫师的灵物。’”[5]
对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的研判也证明了此点,即图腾崇拜行为在彩陶纹饰中的神显,早期如甘肃甘谷县西坪和武山傳家门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的人面鲵鱼纹,中、晚期如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大量带巫术性质的绘制符号;靑海柳湾出土的马厂文化彩陶壶上的变体人形状;半山-马厂文化中出现的带生殖崇拜性质的蛙纹。这些人兽相合的装饰纹样,都是图腾崇拜与巫术信仰的产物,“如果我们把这位彩陶壶上的两性人与其壶上同时绘有蛙肢纹这一事实联系起来看,那么初民们的用心就已经很清楚了:蛙是高产多育的象征和神灵,显然这彩陶上的浮雕阴阳人就是初民心目中具有神力魔法的萨满巫师,也是主管多育的生殖神,即多产的 ‘达其布离’式的女神。”[17]同时,彩陶饰纹中常见的日、月纹与星辰纹图,水纹与火纹和云纹,如庙底沟类型彩陶中常见的 “太阳纹与月牙纹组合的几何形花纹”,马家窑文化中代表太阳与女性的 “万字符”,青海东都柳湾出土的马厂时期的绘有四组太阳纹的彩陶壶;这些也都是当时人们信仰生活中万物有灵观的具体呈现。
而远古羌人的信仰体系,也在这种精神与信仰属性的双重组合中,逐渐形成。除了本文分析的 “人形彩陶制品”外,最明显的便是白石崇拜习俗的出现,如:在属于马厂类型的甘肃兰州红古下海石遗址墓葬中出土白石珠85枚,[18]随葬石串项链珠 (M25:22,M30;8),1组9枚,1组46枚,均由灰色白石料磨制而成;[18]西宁朱家寨遗址墓葬中多次发现大理石珠,多数为白色,“收集珠子最多的是图三标为 ‘H’点的发掘遗址。在一个0.4×0.3×0.3立方米的狭窄空间里,发现的珠子不少于560颗”,[19]五号墓还出土一项链,上串有白色的大理石珠50颗,有些石珠磨损得很薄,[19]这应是佩带者长期使用磨损所致。
综上所述,马家窑文化与半山-马厂文化时期的人形彩陶艺术品,是中国彩陶文化的一大特色。其人形彩陶艺术品在艺术、文化与工艺方面各具特点,丰富多元,而历史与社会属性、实践与实用属性、精神与信仰属性的共同作用,最终促成了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出现,也促成了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发展。
(基金项目: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科研项目—— “古羌人形彩陶艺术的运用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CWYB201401。)
[1]程金城.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p155、p156
[2]段小强.马家窑文化的渊源与属性 [J].东方考古,2012年
[3]青海省文物管理处编.青海彩陶纹饰 [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 [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
[5]顾朴光.中国面具史[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p86,p90
[6]王晓婷.中国新石器时代女性人物雕塑及其功能分析[J].大众文艺,2013年第2期,p278
[7]严小琴、刘逸垄、李立等.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科技分析 [J].电子显微学报,2013年第5期,p408
[8]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宗教问题 [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p108
[9]佟柱臣.中国新石器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p1143、p1145
[10]谢端琚.甘青地区史前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p98
[11]张朋川、周广济、阎渭清.兰州花寨子 “半山类型”墓葬 [J].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
[1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 [J].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另参见:曲石,孙倩.我国新石器时代雕塑人像的研究 [J].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
[13][美]约翰·B·诺斯、[美]戴维·S·诺斯著,江熙泰译.人类的宗教 (7版)[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
[14]柳春诚.青海彩陶上的史前 “维纳斯”——柳湾 “裸体人像彩陶壶”解读 [J].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p147
[15]宋兆麟.后洼遗址雕塑品中的巫术寓意[J].文物,1989年第12期
[16]孙新周.中国原始艺术符号的文化破译[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p28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师赵村与西山坪 [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p148
[18]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红古下海石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p55、p162
[19][瑞典]安特生著,刘竟文译.西宁朱家寨遗址 [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p88
[责任编辑:古 卿]
The Features of Humanoid Painted Pottery from Anicent Qiang
Jiao Husan Zhong Zhaoming
The Humanoid Painted Pottery unearthed from Majiayao and Banshan-Machang sites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Painted-pottery culture in China,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ncient Qiang culture.Therefore,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artisitic,cultural and technical features of this kind of pottery,and then holds on that the historicality,sociality,practicality,spirit and belief…etc.,all have some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oid Painted Pottery in anient Qiang.
Majiayao pottery site;Qiang;Humanoid Painted Pottery;feature
J187
A
1674-8824(2015)02-0030-06
焦虎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院羌文化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四川绵阳,邮编:621000)
仲昭铭,四川文化艺术学院。(四川绵阳,邮编:621000)
——马厂炮台及兵营旧址的调查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