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国资难入国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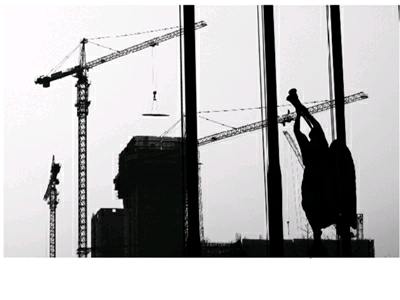
高达数千亿元的国有金融资本经营收入,始终未能明确纳入中央政府预算之中,背后是金融国资的“所有人困境”。
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张玥
发自深圳、北京
“高达数千亿元的金融国资收益,在预算里几乎完全看不到。”吴君亮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政府预算公开。
但变化正在出现。他办公桌上摆着的一份最新的预算报告,由财政部编制、近400页,是新预算法实施后公布的第一份“国家账本”。
这份日趋透明的政府“全口径预算”中,依然笼罩着一些“迷雾”。2015年,中央政府预算报告中的“2014年全国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执行情况表”之下,国有金融资本等项目依然没有明确体现,仅有一项预算金额才3亿元的“金融企业利润收入(地方部分)”。
但此项下方多了一行说明,称2015年中央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将首度被纳入政府收支预算。
不过100亿元的预算收支金额,仍与现实中的金融国资体量差额巨大。
根据上市银行公告等公开数据所做的初步统计显示,仅中央汇金公司所持有的工农中建及光大银行股权,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累计分红便高达4823亿元人民币,而财政部所持有的所有上市银行股权累计分红也达2559亿元人民币。
国资账本中的计算难题
国账中缺失的不仅仅是国有金融资本,早在2013年两会期间,吴君亮便撰文指出,当年国家预算收入里总计为970亿元的“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包括金融、房地产及邮政、军工在内的8大行业的收入为零,或者说成了“迷失的数据”——并未在政府预算报告中得以体现。
面对国资账本预算中的重重迷雾,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身为中央政府大管家的财政部并非不想把它们纳入政府预算,而是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一些技术性难题。
“比如中国邮政现在还承担着某些政策性职能,同时在经营中处于亏损状态,而我们现在提交人大审议的国资经营收入,只是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的企业,亏损企业自然没有国资经营收益预算。”文宗瑜表示,在未纳入国资经营预算的行业中,这种由于政策性职能未剥离而带来经营亏损的企业占相当比例,未来只能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渐理清。
另一部分如房地产企业等,由于它们大多是属于112家国资委直属央企的下属子公司,因此在预算征收时被并入了相关央企的报表,“比如中石油、华润都有房地产业务,但在预算征收时都合并到母公司报表中了。”文宗瑜强调。
文宗瑜的这一解释,也得到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的佐证,“承担着政策性的公共服务功能的企业,自身盈利能力薄弱,如果再向国库缴纳利润,会减少自我投资的能力。并非不需要纳入国资预算,但在企业收益与社会贡献之间的计算和管理难度,确实使问题复杂化了。”
“政府与其控制的国有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过其他任何行业,”王雍君说,“进而金融国有资本纳入预算的困难也超过其他行业。”
不过,也有意见认为,事情也许并不那么复杂,只是,中国国有金融机构面临的一个困局,是它们仍然受到政府直接或者间接的干预。例如金融危机以后4万亿的刺激政策,直接导致金融机构的呆坏账。因此很难判断损失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执行了政策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把国有金融机构直接纳入预算,逻辑上有问题。“所以未来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实现国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运作,免除它们的政策性功能。”世界银行全球金融与市场局首席金融专家王君表示。
金融国资独有难题
在与其他“政策性国资”面临着共同的计算难题的同时,体量庞大的金融国资还面临着另一个独有的难题,那就是双重交叉的“国资所有人”。
当下金融国资的“国有股东”有两个,财政部和中央汇金公司(下称汇金),其中由财政部直接持有的国资股权比例并不高。
根据今年的全国预算草案,从2015年起,中央国有资本中将纳入金融企业收入,预算100亿元,它的范围是“财政部直接持股的部分金融企业”。
2013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显示,财政部从直接持股的工行、农行和交行所获得的分红为571亿元,也就是说,即将纳入央企国资预算的收入不到财政部股利、股息收入的20%。
然而,财政部收入在整个金融国资收入中仍是“小头”,同年汇金从五家上市银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光大)获得的分红是1362亿。仅从五大行的分红来看,汇金所得是财政部的2.4倍,而财政部上交国资预算的又不足其所得的五分之一。
在2007年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中,被纳入中国投资责任有限公司(下称中投)的汇金,其分红所获的金融国资收益,并未被纳入财政部所制定的国资经营预算内。
不过,现行国资管理体系中这一体量庞大的预算外金融国资,并未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管理视线之外,而是形成了与现行国资管理体系并存的“金融国资”管理模式。
中国“金融国资”形态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以“拨改贷”为标志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由国家拨款的基建项目和国企投资,分别由此后陆续成立的建行、工行等国有银行贷款解决。
但在多年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下,早期的国有银行体系实际上变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出纳”,并因此而形成大规模的银行坏账,部分银行与金融机构甚至处于技术破产边缘。
在这一背景下,21世纪初,中国开始对国有商业银行实施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理不良资产、充实资本金并创造条件上市。中央政府经过反复论证,提出了一个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见的以外汇储备注资再造国有银行的政策思路。
在相关的救助方案设计中,以“特殊目的载体”(SPV)角色出现的汇金,通过向央行借入外汇储备并注资中行、建行等国有重点金融企业,在推动国有银行改制上市的过程中,成为了获中央授权的“国有出资人代表”。
这一过程中,财政部所持有的国有银行权益,除了工商银行保留50%(计入特别账户)之外,全部被用于冲销坏账,由此形成了汇金控股四大国有银行的特殊结构。
在金融体制改革的同时,以国资委成立为标志的国资管理体系改革也于2003年启动:在国资委整合国企资产的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过去多年银行与国企责权不分而带来大量坏账的教训;另一方面也由于央行外汇储备并非国有资产而是央行负债的现实,新成立的国资管理体系将国资金融资产和实体资产做了划分,并明确国资委只管理国资“实体企业”部分。
从此时开始,中国的国资管理体系中便形成了国资委管实体企业,汇金管金融企业的“双轨制”——原本作为外汇注资过渡性载体的汇金,也因此而变成了国有银行们的实质性控股股东。
外储注资的“所有人困境”
1998年国内银行资本金总额5151亿元,而到2007年末,中央金融企业国有资本总额已达1.2万亿元,管理资产总额超过40万亿元。这一轮金融国资改革的成效可见一斑。
然而,这一巨额的国有金融资本及其收益,却面临着一个法理上的“所有人困境”: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汇储备负有投资管理和保值增值的职能。而资本金全部来自外汇储备的汇金,依法只能向外管局负责。
如果汇金所管理的金融国资要划归财政部主管,要么修改法律,要么财政部自筹资金还清央行负债并“赎买”汇金股权。
这一“所有人困境”成为了2007年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的争议焦点,并直接影响到了金融体制改革后的金融国资管理模式。
在2007年之后所建立起来的金融管理体系中,以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形态创建的中投,成为了汇金的母公司。而中投的注册资本,则来自财政部以其所发行的1.55万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向央行购入的2000亿美元外汇。
在中投所获的2000亿美元注册资金中,三分之一用于置换汇金前期借用的外储出资;三分之一注资国开行与农行,剩余三分之一则投入海外投资业务。
此时已经管理着近70%国有金融资产的汇金,由此再度将国开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纳入麾下,成为了国有金融企业们名副其实的控股股东。
财政部在通过特别国债置换了汇金对金融机构的外储注资后,终于恢复了其“金融国资出资人”的合理角色。
在此前一直力主设立“金融国资委”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看来,当时已经初具金融国资委的管理结构,而且在多年管理实践中完成了从管资产到管资本这一重要角色蜕变的汇金公司,本应就此纳入财政部管辖,并明确其“金融国资管理者”的身份。
但现实并非如此,与中投的设立初衷有关。
据南方周末记者在此前报道中获悉的资料显示,2007年中央政府创建中投的初衷,远非仅为解决“金融国资”的所有者身份,而是为了另一个迫在眉睫的货币政策难题:在连续多年大幅贸易顺差下所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成为央行难以承担的管理重负。
这一背景下,财政部以特别国债购买央行外汇,并注资成立主权财富投资机构中投的举措,可谓“一石二鸟”之举:一方面以人民币长期国债“置换”央行外储以缓解市场流动性管理的压力;另一方面则通过中投的多元化投资尝试,为外汇储备寻找更多的投资保值途径。
但在这一“资产互换”式的政策设计中,由于央行依然是财政部特别国债最大的“债主”,此前因外储注资带来的金融国资“所有人缺位”现象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理论上,央行依然是这1.55万亿元资产的“债主”,身为“欠债方”的财政部有义务在未来10至15年内,将这笔“欠款”连本带息还给央行。
因此在新的金融国资管理体系中,财政部这个“借钱注资”做成的金融国资股东,索性将汇金纳入中投的外储投资管理体系:财政部将金融机构收益通过中投向央行“还本付息”;央行外汇管理部门则将汇金股权收益视为其庞大外储的“国内投资收益”,承担银行法的监管要求。
王君表示,从股权关系来看,汇金其实是财政部的孙子公司,因为中投拥有汇金100%的股权,而财政部又是中投的全资控股股东。在这样的格局下,财政部和汇金同时持有某一家国有控股银行的股份,等于祖孙两辈拥有同样的孩子,其中的职能交叉与冲突显而易见。
▶下转第16版
◀上接第15版
争议金融国资委
在2013年汇金成立十周年之际,中投在其年报中表示,探索并创立了市场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汇金模式”,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创新的重要实践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层面对现行“金融国资”管理体制——汇金模式的肯定。但一场延续多年关于国资管理体制的争论,远未落下帷幕。
发端于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此后伴随着中央政府换届而五年召开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无论在金融体制改革还是国资管理改革方面,均有着特殊的“制度设计”功能。
正是在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期间,金融体制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两条改革主线发生了碰撞:围绕着“谁来掌管金融国资”这一主题,市场和政府各方在金融国资委的设立问题上争议激烈,令原本预定于2006年底召开的会议不得不一再延期至2007年初。
作为国家财政的大管家,当时的财政部提出应参照国资委管理模式,设立由财政部金融司所管辖的金融国资委,对国有金融企业“管人管事管资产”。
但财政部的这一政策建议遭到作为金融监管当局的一行三会反对,据财新网引述央行人士观点认为,当时已成立五年的汇金公司不但与国资委一样扮演着金融国资“出资人代表”的角色,而且其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比起行政化的国资委管理模式,也更加符合高效和公平的市场化原则。
在学术界内,支持建立金融国资委的李曙光等人,更关心的是在市场制度设计中如何保障“国资经营者”和“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分离。
“无论是金融国资委,还是国资委,都应该只管经营而不能介入市场监管。”李曙光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种“裁判下场踢足球”的角色混乱,是导致今天市场管理机制混乱的关键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对于长期未能获得国资管理授权的财政部门,在面对复杂的预算内外资金管理和央地财政博弈关系中,能否有效行使对金融国资的出资人管理职能,也有着诸多不同的看法。
重重争议之下,设立金融国资委的动议被搁置,直到2012年的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期间,金融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也依然悬而未决。
就在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身为金融国资管理者的楼继伟卸任中投董事长,进入新一届中央政府担任财政部长,由此为包括金融国资在内的整个国资管理体制改革开启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自此,财政部推出了新预算法修订后的首部“全口径政府预算报告”,启动了规模空前的地方债置换计划;同时也在包括金融国资在内的国企资产产权登记、国资经营预算编制以及央企海外资产调查等多个领域展开工作。
随着2015年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市场各方人士推测新一轮国资管理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即将出台。参与了此轮国资体制改革方案设计的文宗瑜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现阶段的国资改革中,当务之急是要把已经纳入国资预算的垄断企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电信和航空铁路等“个头大”的资产摸清家底,并真正纳入国资经营预算。
相比之下,已经在汇金模式下逐渐形成市场化管理机制的金融国资定位,“估计今、明两年还提不上议事日程”。
目前可以观察到的,是财政部门正在加紧进行国有金融企业的产权及股权登记,并明确提出应当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我们在金融国资的管理关系上还是乱。”李曙光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无论是国资经营与市场监管的关系,还是出资人与管理人的责权划分,没有完全理清楚,“期盼看到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出现真正的顶层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