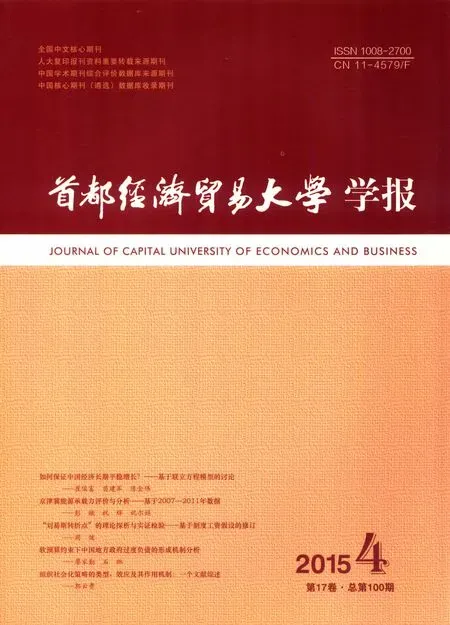“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周 健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探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周 健
(辽宁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刘易斯转折点”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时点。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进而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中国要顺利地跨越“刘易斯转折点”,解决其面临的严峻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唯一的出路。
刘易斯转折点;边际生产率;平均生产率;制度工资;生存工资
引言
“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国家从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如何判定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呢?一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从零转变为正的临界点就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而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边际生产率相等时,“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高铁梅和范晓非(2011)、吴海民(2012)通过农业总产出曲线计算农业劳动边际产出说明中国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大约出现在2005年,“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大约在2043年[1-2]。二是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蔡昉(2007)估算得出2005年农村40岁以下剩余劳动力约为5 8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因此“刘易斯转折点”大约在2009年出现[3]。而樊纲(2007)认为,中国现在还有2.5亿~3亿的农民处于劳动力过剩阶段,还未到达“刘易斯转折点”[4]。三是现代部门实际工资显著持续上升。吴要武(2007)发现,2003年和2006年企业工资支付水平较2002年有明显提高,由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5]。袁志刚(2010)则指出,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并不全是“刘易斯转折点”带来的,因而不能从中得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的结论[6]。四是通过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三次产业产值结构、城市化率和工业化等结构性指标等来判断。黎煦(2007)认为,人均GDP在300~500美元且农业劳动力比重为40%~50%时会出现“刘易斯第一转折点”[7]。李德伟(2008)则指出,“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开始进入一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相对更加稳定的发展状态[8]。
以上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作出了判断。产值结构、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等指标都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外在变化,属间接衡量标准,而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变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工资上涨等属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内在变化,其作为衡量指标是直接标准,会更为准确。而这三个指标作为“刘易斯转折点”的内在变化都与制度工资的假定紧密相关,因而本文以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为基础,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从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这一经济增长概念和生存工资这一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概念两个方面提出“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标准,强调只有这两个标准同步实现,才是真正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
一、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与制度工资[9]
图1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一部分,横轴OA从左向右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纵轴OB从下到上表示农业部门的总产出,ORCX代表农业部门总产出曲线。
1.制度工资。在E点之前的农业部门的工资不是由劳动的边际产出决定的,而是由平均产出决定的,称之为制度工资,它等于维持农业部门劳动者生存水平的平均产出。不变的制度工资由图1中OX斜率表示。这种工资是一种分享形式的工资。现代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给传统农业部门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平均产出的工资就能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
2.制度工资与农业劳动的边际产出。在D点,传统农业部门的MPL=0,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这时,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出于生存的需要,其工资不可能取决于边际产出,而完全受制于制度工资。农业劳动力从D点转移到E点,相应地,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从C到R。CR部分的农业劳动边际产出虽大于零,但小于平均产出。这时由于边际产出决定的工资还难以完全满足农业劳动力的生存需求,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配置也难以完全商品化,其工资依然取决于制度工资。在R点,农业劳动边际产量等于平均产量,即R点的斜率与OX的斜率相等,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都是由相同的劳动边际产出决定的。通常认为,在R点,制度工资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约束必然被打破,现代工业部门支付给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由劳动边际产出决定。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相等是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判定标准。
3.制度工资与农业剩余劳动力。AD部分的劳动力(MPL<0)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对农业产量没有影响,这一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称为绝对剩余。但到达D点后,如果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将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但还没有超越E点,农业劳动力依然剩余,被称为相对剩余。无论是相对剩余还是绝对剩余,只要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配置商品化必然是有限的,制度工资就会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起决定作用。只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完毕,制度工资对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约束才会被打破。
4.制度工资与工资上涨。到达D点后,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短缺,此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以及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超过人口的增长,其工资开始上升,但还没有超越E点,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仍由制度工资决定。当到达E点时,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现代工业部门工资进一步上涨,传统农业部门的工资也超越了制度工资,最终将会上升。
二、“刘易斯转折点”的理论辨析——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修订
(一)基于制度工资假设的理论辨析
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制度工资被界定为维持农业部门劳动者生存水平的平均产出。但是必须认识到,一是分享制假定不符合现实。制度工资作为生存工资和平均产出统一的概念的依据是分享制。正是由于农业部门内部的生产者之间可以实现分享,才使得生存工资等于平均产出。而现实是,大多数农业部门内部的生产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在家庭内部可以实现分享,但不同家庭之间基本上是经济利益关系,很难实现分享。因此,实际上,在农业部门内部存在着收入分层的生产者结构,而制度工资的平均产出下的生存工资界定只是一个总体上的收入平均化的概念。二是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不等于平均产出。生存工资一般是指这种工资水平仅够其维持生存,如果平均产出等于生存工资,也即意味着,如果不能实行分享制,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维持生存,这一部分人只能凭借被平均而活着。因此,现实中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不等于平均产出,两者不能做同一解释。
生存工资在这里有四方面的意义:第一,图1中X点表示与劳动力总量OX相对应的平均产出,这是一个基准的生存工资水平,此时整个农业部门中各个家庭的生产方式都较为传统和统一,因此平均产出也大致相等。但是如果一些家庭的平均产出小于生存工资,则这个家庭就会承受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之苦,劳动力转移便成为寻求生存之路。此时,农业劳动力转移更多地表现为无序的逃荒, 其也无法提供工业部门发展所需的农业剩余。如果各个家庭的平均产出大于生存工资,农业劳动力在满足生存需要之后,还会有剩余,此时的转移好像“每个工人都背着自己的食物包离开农村[10]”,将会呈现出有序的流动,并逐渐形成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持续稳定下降的趋势。由此,农业部门平均产出等于生存工资的临界点也就成为迈向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起点,也即图1中的A点。
第三,费景汉和拉尼斯假定农业部门的平均消费水平是由平均产出决定的,因此,劳动力转移的每一数量上可以得到的平均农业剩余就等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每一数量上的ORCX和OX之差。随着AD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的每一数量上可以得到的平均农业剩余是不断增长的。但随着DE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来,劳动力转移的每一数量上可以得到的平均农业剩余是不断下降的。而这一转换过程的临界点就是C点,此时MPL=0,即“刘易斯第一转折点”。那么此时是否会出现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点呢?短缺点意味着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这一界定是基于以下假设: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可以快速全面市民化,而不存在工资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歧视,但现实中这种歧视是普遍存在的[11]。二是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要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因而其消费水平也必然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消费水平。因此,如果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农业劳动力也按制度工资消费粮食的话,就难以保障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消费到满足其需要的粮食数量。而事实上,“背着生存数量食物包离开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可以但有时又不得不接受的工资和消费水平,只要比其在农业部门时高就行,其一般不会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水平和平均消费水平*即使是“背着较多数量食物包离开农村”的农业劳动力,其在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也大多不会高于原有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而这一工资水平只能供其在工业部门获得维持自身生存必需的生活资料,却难以获得足够的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及劳动者的教育和训练费用。这样工业部门消费的粮食可以按低于制度工资的水平满足这部分工人的需要,既使这时农业剩余下降,也不会产生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因此,虽然MPL>0,但在一定时期内,也不会出现短缺点,而直到MPL=APL时为止,即R点。这时,农业劳动力再继续转移时,其工资要求要高于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水平,消费也要高于工业部门原工人的生存消费水平,也就是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工资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产出,消费水平也高于农业部门的平均消费水平。因而在这个临界点,实现了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和消费水平与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和消费水平相一致,城乡一体化初步形成,而这一临界点正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第四,如果作为生存工资和平均产出统一的概念的话,一是OX斜率表示的生存工资实际上是“离开农村的每个工人背着的不同数量食物包”的一个平均;二是制度工资实际上决定的是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而不是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给农业部门的工人的工资略高于平均产出的工资就能吸引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而这一工资实际上就是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但“略高于”一般很难明确界定,而其与制度工资又极为接近,有时甚至完全相同,因此,平均产出可以看作是工业部门生存工资的底限;三是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假定,不变的制度工资在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前与农业劳动力转移没有关系,是一个静态点。然而事实上,制度工资作为平均产出的概念会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和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因此,动态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要比传统静态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达得晚一些。
(二)结论
本文以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为基础,对制度工资的假设进行修订,得出基本判定条件,一是“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是MPL=0的临界点,其表示劳动力转移的每一数量上可以得到的平均农业剩余从上升到下降的转换过程的临界点,但并不意味着粮食短缺点的形成;二是“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的根本条件是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与平均产出动态均衡的临界点,即MPL=APL,其表示的是经济增长的概念。为什么“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判断标准不是通常认为的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呢?因为此时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可能只是取得瞬时平衡,这种平衡未必相等,可能是工农业部门之间边际生产率的差异达到最小,并且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变化的状态。而之后,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并不会沿着传统假设一直平衡下去,这也就意味着工农业之间并未实现真正的平衡,因此,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乡城迁移还未结束[12]。而且许多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国家也没有真正实现工农业之间边际生产率的相等。这表明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相等并不是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判定标准,农业部门内部实现MPL=APL,才是判断“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的标准[13]。
除了MPL=APL这一标准外,还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与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基本相等这一标准,表示的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成果分享的概念。关注这一判断标准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低收入者的相对贫困甚至绝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只有低收入群体更好地分享了社会经济增长成果才能表明全面实现了小康,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在低收入群体中,农民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但是中国大多数农民远远没有合理且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具体来看,一是农业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广大农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获得持续加速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农业经济增长对于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较小,农民从农业经济增长过程中直接获益的能力有限[14];二是贫困农户往往无力克服迁移障碍,难以从劳动力转移中获益[15];三是城乡居民的生存工资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四是这种差距的形成是建立在城乡居民的生存工资水平都十分低的基础之上的。
三、“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的实证检验
用MPL=0的判断方法对“刘易斯第一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的文献很多,而对“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进行实证检验的较少,因此,这里主要对“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做实证检验。
通过MPL=APL这一判断标准计算得出中国“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的时间大约在2026年[13]。下面主要通过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生存工资相等的临界点来判断“刘易斯第二转折点”,这里采用两种生存工资的概念加以分析。
(一)作为生活费用概念的生存工资
生存工资等于最低生活费用,因此更多的是一个生活消费的概念,因此本文选用农村低收入户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这一指标来测算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存工资,城镇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作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存工资的指标。由表1可见,2002—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年均增长14.15%,城镇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11.64%。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静态估计下,如果两者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农村的生存工资赶上城镇需要30年,也就是2041年。这与由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在2026年左右到来相去甚远。
(二)作为收入概念的生存工资
生存工资作为收入概念,选用城镇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工业部门生存工资的测算指标,农村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作为农业部门生存工资的测算指标。由表2可见,2003—2011年,农村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03%,城镇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2.98%。在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的静态估计下,如果两者的增长速度保持不变,农业部门的生存工资赶上工业部门则是遥遥无期。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相关数据计算得出。后表同。
(三)结论
通过表1和表2的指标比较可见,城乡居民的生存工资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甚至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尤为明显的是农村中等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低于城镇最低收入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中高收入户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也低于城镇最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城乡生存工资水平低且存在一个较大的差异固然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乡城迁移,但如果城乡之间在消费和收入上巨大的且不断扩大的差距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则难以实现农村与城镇部门的生存工资相等,也不可能实现城乡一体化,更不可能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使经济增长概念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到来了,也是虚假的,没有实现真正的跨越。只有由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和由生存工资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同步到来,即农民切实合理且同步分享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才能真正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由此可见,201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在‘收入倍增’中着力促进农民增收,农民收入至少应与城镇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并力争超过”的政策主张蔚为重要,必须切实保证农村居民合理且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样由农业劳动边际产出和平均产出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和由生存工资决定的“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才能同步到来,才能真正跨越“刘易斯第二转折点”。
四、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对策建议
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困难是在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的经济发展。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的生存工资的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中国接近及跨越 “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农村居民生存工资的不断提升,而且这一趋势在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接近的过程中依然存在,甚至会以加速度不断向前推进,其必然会带来更为严峻的压力与挑战:一是催动一般性劳动力工资的全面上涨。农村居民的生存工资一直制约着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形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低人工成本优势。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重要提供者之一,是支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随着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农业劳动力转移进入全面加速时期,农村居民生存工资的快速提高也必然会催动一般性劳动力工资的全面上涨,“人口红利”很快就会消耗殆尽,原有的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二是制约现代部门发展。农村居民生存工资的提高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给现代工业部门的农业剩余不断减少,而要实现原有不变生存工资下的现代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升到相同水平则需要更多的资本积累,由此,将农业部门作为主要发展资源提供者的现代工业部门则会陷入困境,一方面需要更大幅度的“掠夺”,另一方面又存在难以不断持续“掠夺”的“资本积累瓶颈”。三是农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危机。农村居民生存工资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其转移能力在加强。如果说最初转移到城市现代部门的是传统农业发展需要的体力劳动意义上的边际产出水平较高的农业劳动力,而后则是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脑力劳动或知识劳动意义上的边际产出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城乡之间的资源竞争逐渐转移到人力资本的争夺上。这些优质的农业劳动力的流出,极易造成“农业空心化”,这将为农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埋下危机的隐患。一旦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极易出现固定生产要素的闲置,农村中出现土地撂荒的现象。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大面积的土地甚至于更多生产工具也会随之闲置,因而小农经济状态下的耕地高度分散经营的土地制度也必然要加快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农业规模化生产也必须加快推进。四是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亟待完善与提升。中国以家庭为基本社会层级结构单位的农村生存保障能力和水平无疑是低下的。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后的最低要求就是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生存工资水平,全面摆脱贫困。完善与提升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对实现这一目标蔚为重要,但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五是如果转移到城市的农业劳动力无法真正实现市民化,无法消除歧视,那么其会一直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游走在城市边缘,被压榨在低端劳动力市场,拿着可怜的工资,过着悲惨的生活,这会使得他们生活在城市而又无法达到城市的生存工资水平,具有农村身份而又不能提升农村的生存工资水平[13]。
以上这些问题对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来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无疑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一方面要实现城乡生存工资全面提升,不断趋于相等;另一方面要化解城乡生存工资快速提升所带来的压力与挑战。而要解决这一矛盾,需采取以下措施:第一,转变中国原有的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为此,要促进产业转型,实现优化升级;加快生产要素和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等。第二,要提高农村居民的生存工资水平,保障与提升生存能力。为此,要加快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实现真正的市民化;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实现城乡一体化[12]。
[1]高铁梅,范晓非.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与供求拐点[J].财经问题研究,2011(1):22-31.
[2]吴海民.我国刘易斯拐点的新检验——基于1990—2010年农业和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考察[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3):6-11.
[3]蔡昉,都阳.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8——刘易斯转折点及其政策挑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樊纲.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就业[EB/OL].[2007-11-05].http://www.cq.xinhuanet.com/2007/2007-11/05/content-11588833.htm.
[5]吴要武.“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J].开放导报,2007(6):50-56.
[6]袁志刚.三问“刘易斯拐点”[N].解放日报,2010-09-12.
[7]黎煦.刘易斯转折点与劳动力保护[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7(4):60-66.
[8]李德伟.中国将迎来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转折点”吗?[J].理论前沿,2008(12):37-38.
[9]费景汉,古斯塔夫·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M].洪银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对若干重大体制改革问题的认识与政策建议[J].中国社会科学,2013(7):59-76.
[12]张桂文.二元转型及其动态演进下的刘易斯转折点讨论[J].中国人口科学,2012(4):59-67.
[13]周健,邵珠琼.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测定及其对策研究[J].西北人口,2014(1):23-26.
[14]刘浩澜.农民对经济增长成果分享的实证——基于社会效益层面的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30):9788-9789.
[15]蔡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探寻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源泉[M].北京:社会文献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宛恬伊)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Lewis Turning Point:Based on the Revised Hypothesis of Institutional Wage
ZHOU Jian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Lewis turning point”is an important time point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Here the hypothesis of institutional wage is revised,and puts forward the two aspects of criteria——the agricultural labor marginal output and average output which belong to the concept of economic growth,and the living wage which belongs to the concept of benefit share of economic growth.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only with the synchronous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aspects of criteria China can truely cross the“Lewis turning point”.In order to successfully across “Lewis turning point”,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best choice.
Lewis turning point;marginal productivity;average productivity;institutional wage;survival wage
2015-04-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研究”(11&ZD146);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辽宁劳动份额提升的适度水平及其实现路径——基于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的分析”(w2013005);辽宁大学省级重点学科中央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周健(1976—),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
F249.2
A
1008-2700(2015)04-006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