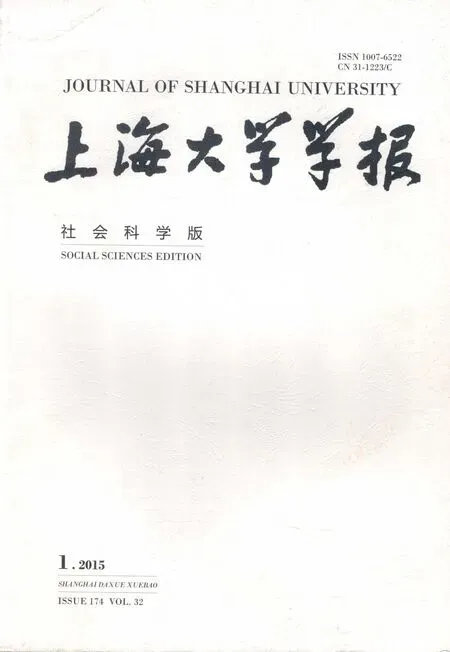叙事视野下的义山七绝
李 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叙事视野下的义山七绝
李 翰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论义山七绝,以叙事为视角,以时空关系、叙述行为、叙述风格、诗歌意境、句法语式等为观测点,以艺术评鉴为旨趣。管见所及,其叙述时空远近交织、虚实互映、真幻相夺;叙述风格含蓄隐约、欲吐还吞、曲折绵密;叙述笔法千丝密网、层进勾连、潜引暗逗。遂使篇幅极短之七绝,而有容涵极大之意蕴、包孕极深之情理。叙事分析于“百宝流苏,千丝密网”之义山诗,不惟能了然其诗境之所以然,且能洞烛其诗心诗意之深微幽曲、层进衍展。借助叙事分析,对古典诗歌研究走向深入,当不无裨益。
李商隐;七绝;叙事;叙述时空;叙述留白
尽管李商隐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抒情诗人,其大部分诗歌被视为抒情诗,却非常适合从叙事的角度来考察。从叙事的角度考察,也有助于深入认识其文学价值之所在,这既因为“在人类文化活动中,‘故事’是最基本的(世上一切,不论是事实上发生的事,还是人们内心的不同体验,都是以某种叙事形式展现其存在)”,[1]193又因为义山诗有“百宝流苏,千丝密网”(《臞翁诗评》)之特点。
从叙事视角考察义山七绝,还基于这样一种认知,即文学史的本质为形式演进。①对形式主义批评家来说,文学作品是纯粹的形式,是材料关系的组合。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性,亦即使一部著作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这对观照中国文学确有启迪。首先,思想、内容并不天然属于文学范畴;其次,自《诗经》时代到清、民,思想、内容根本上的新创远远比不上重复,尤其是就天然最具文学性的人类情感来说,事起或异,而不出七情之域。只是表现的形式、方法,从四言到五言、七言,从骈文到散文,到戏剧、小说,才构成文学史演进的基本内容。前人从文体的角度导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其实就是文学史为文学形式史的观念。李商隐以近体律、绝最擅胜场:七律继轨杜甫,卓然为诗史又一高峰;七绝则与杜牧一起,颉颃盛唐李白、王昌龄。其所以能达到这一高度,即因语言词汇、意象境界、表达方式、表现手法等形式上的新创,拓展、深化了这一传统诗体的艺术空间,从而无愧于传统诗艺总结者的历史使命。①董乃斌教授认为,李商隐对文学史的贡献,在于他“充当了中国诗艺的一名总结者”,并“以超人的才力,漂亮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见《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0、93页。
王蒙先生有《〈锦瑟〉的野狐禅》一文[2],将义山七律最具代表性的《锦瑟》,在语言、词汇上做过多番组合,最大程度上考验了其在形式结构、语言意象上的强大张力。王氏之文,事实上就是带有结构主义性质的文本分析。
七律如此,七绝也不例外,亦具叙事学分析价值,或者说也适宜作叙事分析。此前的七绝圣手李白与王昌龄,以情韵悠长、风神畅达取胜,语俊意新而诗境却相对单纯清浅。如李白《早发白帝城》、《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峨眉山月歌》,王昌龄《从军行》、《出塞》、《芙蓉楼送辛渐》等名篇,在文本结构上,皆多呈线性平面化特征,较少层次叠折与迂进。王昌龄部分七绝稍添迂回,如《闺怨》(闺中少妇不知愁)、《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而李白则完全是一派天机,元气淋漓。义山七绝,迂回处承王昌龄,而用意更曲、措辞更婉、层次更密,借助叙事分析,庶几勉窥堂奥。
一、叠映穿梭、真幻相夺的叙述时空
叙述时空包括话语时空与故事时空,话语时间是叙述行为发生、花费的时间,话语空间是叙述发生的空间;故事时空则为故事中人物的活动时间、空间。[3]112-143七绝的艺术张力就在于以有限的话语时空,展开无限的故事时空,形成所谓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话语时间是烟花三月,空间是长江、黄鹤楼;故事时间与空间则不仅包括上述作为辞别时间、地点的烟花三月、黄鹤楼,还有故人即将要去的地方——扬州。烟花三月的扬州,以及故人在那个美丽的城市的将来活动,都没有在诗歌文本中提及,却包含在诗意之中。扬州作为一座著名的城市,相应的历史文化信息,也为本诗提供了意蕴丰富的故事空间。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是老杜七绝中罕有的神品:
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就话语时空来看,不过短短二十八字,时为江南春暮,事为劫后故友重逢。就故事时空来看,唐王朝由开、天盛世经安史之乱而劫后余生,无数黎庶的颠沛流离、亲故凋散,包含了几十年朝野变故,巨细无遗。这其中,还有对世事变幻的沧桑体验,构筑了深邃复杂的心理空间。话语时空的紧缩与故事时空的扩张,使一首诗成为一部史,数十言超过数万言。
上举李、杜二首七绝,一由当下向前,联及未来;一由当下向后,回溯过去,未来与过去作为故事时空,并没有呈现为完整的叙述文本。话语时空与故事时空既有明显的界分,又有确切的串联。故事时空虽远远溢出话语时空,但基本指向比较清晰。总体上看,两首诗具有七绝语短情遥、隽永含蓄的特色,但时空关系其实并不复杂,不过二重协奏而已。
义山七绝有类似者,如《咏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
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间同晓梦,
钟山何处有龙盘。
在玄武湖漫漫水波中,三百年王朝兴废、成王败寇,悠悠而过。北湖南埭为眼前实景,而幻化出三百年漫长光阴中王朝兴废的虚景。“一片降旗百尺竿”,既是话语层面的意象定格,又是故事层面意象延伸的开始,其间多少历史人物、事件,都以画外音画的形式,蕴涵在故事时空之中。话语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来说无穷缩短,最大程度上增大了故事的容涵,使诗歌表现出高度的概括力。如果说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涵盖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唐代史,李商隐的这首诗则超出了数十倍,囊括了从吴、晋至南朝宋、齐、梁、陈三百年的政治史。
再如《楚吟》:
山上离宫宫上楼,
楼前宫畔暮江流。
楚天长短黄昏雨,
宋玉无愁亦自愁。
这首诗咏怀古迹,诗人以所处、所见之时空,写所想之历史时空。历史时空的容量,取决于读者的历史文化修养,但指向相对明确。所不同的是,《楚吟》所咏宋玉多含自况,则历史时空又返回映射到现实时空,使二者缠杂在一起。如果说杜甫咏宋玉“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在感怀兴慨之际,诗人(叙述者)与古人(被叙述者)尚有明确分界,而在义山的《楚吟》中,强烈的代入感就使二者混融难分了。因此,本诗在当下、历史的二重时空之外,又有相互叠映、交融的第三重时空,即叙述者的自传时空。
《北齐》二首以全知视角写北齐后主与冯小怜事,通过巧妙的剪裁、组合,将多重历史时空相叠映,不仅大大增强了叙事含量,也使叙述主题得到鲜明的表达。如其中的第一首:
一笑相倾国便亡,
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入晋阳。
“何劳荆棘始堪伤”将西晋索靖叹荆棘铜驼事植入叙事中;具有象征与对照意味的历史背景,这是本诗的第一层时空。在这层时空下,又并列组织了两层时空:小怜获宠与周师攻陷晋阳。据史料,周师入晋阳在北齐后主武平八年(577),而于此前,冯小怜玉体横陈、备受宠爱已经多年。两件不同时空中的事件,被拼合到一起,达到蒙太奇式的叙述效果,形成叙事因果链。再结合荆棘铜驼故事,一层底景,两层显景,三段时空,粘连措合,叠映互释,诗旨就变得格外显豁。
如果在物理时空的措置中叠加心理时空(有些情况下,物理时空本身也就蕴含着心理时空),则诗歌的时空关系就更为丰富。美国学者沃尔特·费希尔(Walter·Fisher)在《作为人际交往的叙事》中曾指出:作为“内心体验”的情感,其表达过程与方式,必然是叙事的。[1]而七绝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体式,其情感的表达,很多是通过心理空间的构建来完成的。
上述引诗中(包括李白、杜甫诗)其实也都有心理时空,或为对友人的留恋,或为对岁月流逝的感慨,或为对历代兴亡的沉思……这种心理时空是与诗俱来、客观存在的,究其实,乃作者之心理时空。在有些诗歌中,如《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作者即为诗中送行者,《楚吟》作者与所咏宋玉混而为一,则作者之心理时空与叙述者、被叙述者(作为诗中人物的作者)之心理时空叠映互补。而在另一些诗中,心理时空直接作为主体,被多方面、多层次叙述,如《嫦娥》:
云母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
华贵深幽的居室,从窗外望过去,星沉月落,长夜将曙,这是诗中的现实时空。由之而想到月宫嫦娥,于是就出现嫦娥窃药奔月的神话空间。现实时空与神话时空平行对应,则嫦娥之寂寞凄凉与云母屏风的深宅幽人两相映照,寂寞嫦娥就有了象征的意味。这种象征,就是根据心理空间的设置来完成的。本诗的所有场景、意象,皆为心理空间之象征写照,而“应悔”更是直接对嫦娥心理活动的分析。从叙述逻辑来看,心理空间更是有三层叠加:作者对叙述者、嫦娥寂寞心理空间的领会,叙述者对嫦娥寂寞心理空间的领会,嫦娥寂寞的心理空间。在这首诗中,物理时空导引心理时空的建构与穿越,并成为心理时空的显像,叙述逻辑则将多重心理时空有机统一在一起,使诗歌的意蕴变得尤其丰厚。
再如《柳》:
柳映江潭底有情,
望中频遣客心惊。
巴雷隐隐千山外,
更作章台走马声。
钱钟书言后两句为义山“醒时之想因结合,心能造境”,[4]即谓其为心造之幻境。雷声隐隐为今日江潭摇落、天涯飘零之真实处境,车声隆隆为昔日长安游冶、走马章台之旧境,因其音声类似,心中之昔日遂叠映于眼前之时空。真而为幻,幻而转真,真幻并存,且在画面中轮回,犹如电影中的叠影镜头,将其章台走马的故事渲染于柳映江潭的背景中。
物理时空与心理时空最为丰富的是《夜雨寄北》:
君问归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涨秋池。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话语时空为秋夜巴山、夜雨中的寓所,这也是写作时的当下情境。作为写作情境的话语时空,同时也是故事时空,并随故事发展在空间、时态上不断发生变化。如后半句“却话巴山夜雨”,实即此刻之雨,但在“何当共剪西窗烛”的未来想像中,又变成了旧时之雨。诗人在当下的凄风苦雨中,悬想着未来的某一天,在风雨过后的宁静夜晚,与友人细话凄风苦雨的当年。随着语境的变化,当年的凄风苦雨,在若干年后的回忆中,时间的距离也许会改变些许凄苦的颜色,为其抹上一缕温馨。但我们又要注意,故事时空中的未来,未来时空中的回忆,都是当下的悬想,皆为心理时空。诗人幻想着早日摆脱当下的凄苦处境,幻想着在摆脱这苦境的某一日,能用时间把凄苦稀释出温馨,而当其从心理时空回到当下,依然还是巴山夜雨、客舍秋风。对未来美好而迫切的向往,反衬着当下境遇的凄苦,而所有向往又只能是心理空间终归寂灭的幻想,则加倍映衬出当下境遇不仅凄苦,并且凄惶而无助。
诗在未来时空中,穿插着对过去的回忆,这个过去,就是写诗的此刻。至此,诗之故事时空分裂为三个:当下、未来、过去,而当下和过去其实是叠映在一起的,只是随故事演变而改变其时态。在同一时空的时态变化背后,是情感、意境的改变,本诗以其叠映穿梭、真幻相夺的时空,将苦涩流离的悲剧人生,表达得凄彻入骨。
二、引而不发、言外蓄事的叙述留白
“留白”,是创造诗歌隐性时空、增加诗歌叙述意涵的重要方式。话语时空与故事时空的关系,其实就已牵涉到叙述留白,如前面所说的话语时间相对于故事时间无限缩短,实即构成叙述留白。叙事学中,有叙述时距的概念,指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差距。热奈特将其大致分为四类:“概要”(summary):叙述(话语)时间短于故事时间;“停顿”(pause):叙述(话语)时间无穷大,故事时间为零;“省略”(ellipsis):叙述(话语)时间为零,故事时间无穷大;“场景”(scene):叙述(话语)时间基本等于故事时间。[3]119[5]其中,“概要”、“省略”都是故事时间长于叙述时间,这也正是大部分七绝的特点,因篇幅限制,话语时间在客观上大都短于故事时间。叙述留白所生成的隐性时空,正是叙述时距综合应用的结果。
如《龙池》:
龙池赐酒敞云屏,
羯鼓声高众乐停。
夜半宴归宫漏永,
薛王沉醉寿王醒。
皇帝在龙池赐宴,参加宴会的有薛王、寿王及其他一些大臣和勋贵。鼓乐齐鸣,尤以羯鼓敲打得最欢。宴会持续到半夜,不少人都喝醉了,比如薛王。不过,相伴而去的寿王因没有怎么喝酒,一直很清醒。从叙述行为来看,这是一段“场景”,话语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但故事是系统完整的因果链,而这里只叙述了结果,原因则省略了。实际上,本诗是两段故事同时上演,台上美酒歌舞、君臣尽欢,而在台下,却掩盖着一段浪漫而又荒悖的翁媳恋。台上的故事,以“场景”来表现,却只能说是一个序幕。而台下被“省略”的,文本中叙述时间为零的,才是正剧。诗人打开序幕,以富有意味的细节稍作剧透,意在引导读者自己去看正剧。“薛王沉醉寿王醒”的“场景”,在诗中提示勾连,以引起读者追索下去的兴趣,而作为原因的另一段故事,于省略处生动展开。
再如《瑶池》:
瑶池阿母绮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骏日行三万里,
穆王何事不重来。
这首诗前二句所叙为“场景”,但并未构成故事。故事在“省略”中,以“穆王何事不重来”引出。而这一句同时充当着“概要”的功能,指向《穆天子传》所记周穆王与西王母事,并规定着诗歌的主旨走向。当然,在阅读中完成的“省略”,重在“何事不重来”之上,在《穆天子传》中也没有现成蓝本。所以,诗中的“省略”既有其方向与范围,同时又呈现出开放性的特征。
前述李商隐《咏史》“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结尾的句式结构与《瑶池》一致,但形象性更强。三百年间的“一片降旗”,作为一种“场景”,话语层面所叙述的内容是自足的。至于这三百年间成王败寇的具体情况,并未详细展开。诗中二十八个字,在此仅充当着“概要”的叙述功能。这一“概要”不仅概括了三百年兴亡相续的故事,也概括其间的因果得失。“概要”之外的话语空白处,一是客观存在的史实,所指确定,但具体内容的多少与深浅,则依赖读者的历史文化积累;二是对这一史实的再现、想像,则开放而不确定;三是情感与认识,由于“概要”规范,大致不出“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之范畴,又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据此可见,在义山不少七绝的写作中,其实是综合了“概要”、“省略”与“场景”三种叙述行为,“概要”与“省略”都是以“场景”来呈现,“概要”规定了故事大致走向,而“省略”则须在阅读过程中来完成,“概要”与“省略”在话语层面组成自足的“场景”,并引导故事在阅读中进一步展开。“场景”的自足性说明诗歌话语的完整性,而具有延伸性与引导性的“省略”,又使得“场景”不是静止与固化的,而是不断生成的。
留白作为诗歌的隐性时空,正是这种不断生成的“省略”。留白的创造,也就是“概要”、“场景”指向“省略”、规范“省略”与激活“省略”的过程。从上引诸例中我们能够看到,一是“场景”所叙述的故事,包含或关联着未曾叙述的故事,如《龙池》,再如“平明每幸长生殿,不从金舆惟寿王” (《骊山有感》)、“莫向尊前奏花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宫词》)、“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为有》),等等,皆属此类。二是通过“场景”自身意蕴,自然衍生出丰富的隐性时空,如《夜雨寄北》;另外,“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鹦鹉对红蔷薇”(《日射》)、“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柳》),等等,皆属此类。三是以假设、推问等形式,在逻辑或判断上引导、延展隐性时空,如“何事不重来”、“何处有龙盘”,等等。此类还有“君王若解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马嵬二首》其一)、“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代应二首》其一)、“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鸳鸯》)、“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华岳下题西王母庙》),等等。
在第一种情况中,留白所生成的“省略”,是另一段故事,如《龙池》、《骊山有感》所生成的唐明皇、杨玉环故事,《宫词》所生成的宫女失宠,《为有》所生成的独守空闺,等等,在文本话语中,都是含而不露或点到即止。第二种情况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场景”直接关联到另一段故事,如《齐宫词》,“风摇九子铃”的留白,是齐、梁荒淫亡国故事;另一种则仅暗示情绪、感情,留白生成的是心理时空,如《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日射》。不过,心理时空中必有本事,只是本事被虚化了。但虚化的过程,也就是泛化的过程。为什么这类诗的感染力最强?因为诗中人与事在虚化的同时,取得了广泛的针对性与适应性。第三种以句法、语式为导向,留白所生成的隐性时空包括前述各种情况,可以是隐性故事,如《瑶池》“穆王何事不重来”,对穆王不重来的追问,关联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各种故事;可以偏向于“场景”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如《代应》“十二楼中空更空”;也可以导向理性时空,这是前述几种情况中所缺乏的。如“玉辇何由过马嵬”、“锁向金笼始两全”之类,对于话语及其所叙述的故事来说,是以追问或判断作结,但对于阅读接受来说,正是理性思考的开始。由所叙故事及判断、追问获取经验教训,最终形成对叙事中所含理性的规律性与普遍性认知。由于思考结果带有规律性与普遍性,也就同时具有广泛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这与心理时空所具有的广泛适应性类似。正是这种针对性与适应性,在文本叙事外,自然关联更为广泛的类似人和事。
留白的制造,可以是故事,可以是场景,也可以是语词句法的逻辑结构,更多的,则是上述几种的混合。如上引“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场景与故事中,也有理性认识;而“君王若解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马嵬二首》其一)、“离鸾别凤今何在,十二玉楼空更空”(《代应二首》其一),追问与判断中,其实也有场景与故事。但要使留白生成有意义的隐性时空,叙述时距的把握和应用至关重要。正是“概要”、“场景”与“省略”三种叙述行为,打开广阔的隐性时空,从技术上成就了留白艺术,克服了七绝体制上的局限。留白生成的言外蕴蓄,有的直接是另一个相关故事,有的是情感心理或理性认识,但这些情感心理或理性认识,只有与“事”关联才有所附依和落实。情、理、事,实际上总是以三位一体的形式存在于诗歌中。
三、层进勾连、包蕴密致的修辞技巧
宋人敖陶孙评李商隐诗云“百宝流苏,千丝密网”(《臞翁诗评》),“百宝流苏”谓辞藻、意象之华靡,“千丝密网”谓构思、用意之深曲。一偏向于遣词造句,一偏重于结构技巧,二者结合,具有鲜明的修辞性叙事学的示范意义。①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认为文字叙事作品的艺术形式有两个不同层面:一为结构技巧,二为遣词造句,叙事学和文体学各聚焦于其中的一个层面:叙事学聚焦于结构形式,而文体学则聚焦于遣词造句,两者构成一种对照和互补的关系。研究修辞格的修辞学构成现代文体学的一个源头,而研究话语劝服力的修辞学与叙事学相结合,就产生了“修辞性叙事学”。见该书第1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不过,表面看来,修辞性叙事学在讨论叙事如何运作的时候,多集中于讨论作者、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关系,但文本的语言分析,无疑是讨论的客观前提。
就义山七绝来说,用意之深微曲折,使得“本意”隐曲,就牵涉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的问题。②关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不可靠叙述等文体,可参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第二、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其实是义山诗最大的问题,义山的苦恼在此,义山诗的魅力也在此。义山在《上河东公启》中自辩云:“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那么,又是什么使其诗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发生错位,使义山诗成为一种“不可靠叙述”呢?根本上还是文本结构、叙述方式有其特点。上节论叙述时距与留白之关系,如果能将“省略”的开放性与“概要”的指向性、“场景”的包容性相结合,则既不失诗意的丰富,又不迷失于这种丰富。本节探讨结构、语式、句法、修辞等文本形式,从具体的遣词造句,进一步明前论之所以然,既欲抉幽发微,又欲一窥其飞彩金针。
长篇叙事诗,以时间、地点、人物等构成叙述要素,以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形成自然的叙述次序与结构,并有足够的容量展开叙述。而七绝统共二十八个字,若欲承担长篇的叙述容量,乃至要以少许胜多许,则尤须讲究叙述技巧。故就叙事学而言,七绝的标本意义不言自明。义山《咏史》“三百年间同晓梦”的时空与喻象,《嫦娥》“碧海青天夜夜心”的心理活动,《齐宫词》“犹自风摇九子铃”的象征与留白,等等,都是成功的叙述修辞,无限拓展了诗歌的叙述容量。不过,这些在其他诗人那里也会见到;李商隐对扩展七绝叙述容量的贡献,主要是语法意义上的修辞与结构,如实词之锤炼、虚词之承接转折、语义之层进衍展、句法与语序之组措,等等。杜甫七律曾对此多有开拓,李商隐七律学杜也主要表现于此,但义山将此应用到七绝之中,则独创无匹。
仍以具体诗例来说明。
一,顺承推进。《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其二“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江水东流,与诗人作别,即便诗人位置不变,也当愈去愈远。然而,江水向东,诗人向南,就将离别之旷远与相会之无期,推进一层。“相送…后”、“犹自…更”,纯为行为、时态之描述,却构成叙述上的层进关系,“犹自”兼有对心态的揭示。同样的句式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花下醉》),“客散”、“酒醒”、“深夜”,连续三层掘进,后一句加一“更”字,再推进一层,然后“持烛赏花”就带有一种喜剧般的滑稽之感,而“花”是“残花”,“烛”是“红烛”,两相对比,视觉之残酷,又是一层推进。如此层层推进,则持烛赏花人,可笑更可悲,可悲更可怜悯,其寂寞无奈、凄清无告之境,淋漓尽致而怵目惊心。再如“如何雪月交光夜,更在瑶台十二层”(《无题》),“雪月之夜”一层,“瑶台”一层,“十二层”又是一层;“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残阳又带蝉”(《柳》),“清秋日”一层,“残阳”一层,“蝉”又是一层,而“如何”、“肯”,“已”、“又”,贯穿推进的意脉,如抽丝剥笋般,掘发出深微诗意。
顺承推进的语序不一定都是顺叙。如《西亭》“梧桐莫更翻清露,孤鹤从来不得眠”,换“更”为“莫更”,将句式前后调整,其意即是“孤鹤从来不得眠,梧桐更自翻清露”。语序的更换,等于在顺叙推进中又多一层推进,如本句,“莫更翻清露”,所叙之事实即“更翻清露”,“不眠”、“翻清露”已构成一种递进,本不得眠,而露滴梧桐,愈增入眠之难。用“莫更”调整语序,将客观的陈述变成主观的祈使,丝毫无损于对事实的叙述,却增加了对心理空间的刻画。又如《旧顿》“犹锁平时旧行殿,尽无宫户有宫鸦(一作“宫花”、“飞鸦”)”,本为“尽无”、“犹锁”之递进,语序颠倒后,强调之重点在“犹锁”,就显示了本诗之微意在于批判而非感慨。
二,逆转推进。两句或当句构成前后逻辑上的否定,在对比中产生强烈落差,使诗意向深微处推进。期待、转折、否定,一波三折,可以说是一种极具戏剧性的叙述方式。如名作《贾生》“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夜半虚席”构成叙事期待,这一期待当然的逻辑指向是“苍生”。而作者没有满足我们的期待,“苍生”被“不问”而抛弃,“鬼神”却被“问”而唤醒,一弃一取间,不但期待成空,且向着相反的方向演进,不可思议的阅读感受油然而生。“可怜”、“虚”、“不问”、“问”,或肯定或否定的叙述所组成的逻辑推进、逆转,形成有效的叙述干预,呈现出对事实的判断立场,深化了与之相应的认知情感,并支配着阅读接受的向度。再如“秦中已久乌头白,却是君王未备知”(《人欲》)、“伶伦吹裂孤生竹,却为知音不得听”(《钧天》)、相如解作长门赋,却用文君取酒金(《戏题友人壁》),等等,语词转折与句意推进,相得益彰。也有在语词上无转折而仅在逻辑上推进句意的,如《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
梓潼不见马相如,
更欲南行问酒垆。
行到巴西觅谯秀,
巴西惟是有寒芜。
表面看起来是顺承推进,其实一路否定逆转。先是在梓潼觅司马相如不得,于是南行继续寻找。走到巴西,还是没有司马相如的影迹,退而求谯秀,依然不能如愿。一路寻找,一路失望,巴西觅谯秀,所得是“寒芜”,欲觅者不可得,不欲觅者不可避,人生之窘迫,莫过于此。
再如《谒山》:
从来系日乏长绳,
水去云回恨不胜。
欲就麻姑买沧海,
一杯春露冷如冰。
“系日”肯定,“乏长绳”否定,一句中完成一次逆转;“水去云回”承“乏长绳”,是否定层的推进,“恨不胜”承“系日乏长绳”及“水去云回”,是总体上又一次推进。“欲就麻姑买沧海”为转折,事实上系日不得,退而买海,对前二句而言,也构成一种否定。然而,买沧海仅得一杯春露,且春露又成冰,一层肯定,以两层推进式否定来逆转。系日不得,水去云回无可奈何,买沧海而仅得春露,春露又成冰,一路追求,一路失败,一路憧憬,一瞬成空。短短四句,叙述人生之不如意,达到无可如何的境地。其思想寓含及对生存的哲思,与卡夫卡、乔伊斯等人的小说不相上下。
三,潜转推进。最为典型的是一句双绾,即通过句法、语汇,使一句暗含几层意思,句意得到深化扩展。如“宋玉无愁亦自愁”(《楚吟》),同时包含“有愁则更愁”的意思;“自是明时不巡幸”(《过华清内厩门》),同时包含“昏时才巡幸”,即昏君才多游玩巡幸之举;“未必圆时即有情”(《月》),包含“缺时便有情”之意;“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樱桃花下》),所见要么未开,要么已败,良辰美景之二美难并,以所见关合所不见;“金徽却是无情物,不许文君忆故夫”(《寄蜀客》),“不许忆故夫”,包含着“难免忆故夫”,“金徽无情”,包含着“文君有情”。上述诗例,皆属一句双绾,一支笔写几家话,相克者可相生,极有叙述技法上的标本意义。
双绾句法如果再熔铸语典、事典,则进一步增加句意内涵。如“壶中若是有天地,又向壶中伤别离”(《赠白道者》)。“壶中若是有天地”,实为“壶中本无天地”。在此认知下,以“若是”让步,诗意便推进一层:壶中即便有天地,也会因离别而忧伤,何况壶中本无天地呢?“壶中天地”典出《后汉书·方术列传》费长房事,指道士的方外生涯,李白有“壶中别有日月天”(《下途归石门旧居》)、“寥落壶中天”(《赠饶阳张司户燧》)之句,但和义山诗让步推进的句法比起来,意思就过于直白了。义山用此典故,并采用假设句式让步推进,谓仙家原本超脱,却依然不免为情所苦。那么凡人又当如何呢?这一层意思虽在言外,实亦寓言内。再如“武昌若有山头石,为拂苍苔检泪痕”(《妓席暗记送同年独孤云之武昌》),用《幽明录》所叙武昌北山望夫石故事,但同样采用让步推进的句法,诗意尤增深曲。“武昌若有山头石”,即“武昌本无山头石”。若有山头石,则石上当泪痕斑斑,而其实并无此石。那么,忧伤的刀斧刻在石头上的斑斑痕迹,只好在离人的心头刻削,而且无人可见。掩泪入心,泣血自咽,这是何等的忧伤啊!
以上分解述说义山诗层进推衍的几种方式,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义山七绝包含着多种叙述技巧,是层进勾连而达成其包蕴密致之艺术效果的。且以《夕阳楼》为例。
花明柳暗绕天愁,
上尽重城更上楼。
欲问孤鸿归何处,
不知身世自悠悠。
①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79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如本文所论,刘先生这里说“不自知其可怜”,或欠准确。
②实际上,西方叙事学的很多概念,也一直处于争论中,并未得到绝对统一。如“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叙述视角”,等等,在不同的叙事学家那里,其内涵、外延不尽相同,有些更是有歧议。
此为义山少作,而婉曲细密,已令人叹为观止。“花明柳暗”与“绕天愁”,属句内逆转。“花明柳暗”正是春光明媚,正常逻辑当是心情愉快,而本句却接以“绕天愁”。愁而绕天,于逆转中再加以渲染推进。第二句紧承第一句,构成叙事因果链,因其“愁”而登城上楼。先登城,再上楼,不过是以时间为顺序的行为,而诗用“上尽”、“更”来串联,逻辑上的层进,就变一般性叙述为修辞描述。在行为方式、行为结果之外,将行为心理揭示出来了。因此,第二句对第一句而言,构成的是层进曲折的转承,而非简单的顺承。后两句承第二句,写登楼所见,意蕴更为丰富曲折。“欲问”句,一写孤鸿之飞,二写叙述者之心理。“欲问”其实并未问,也是一笔双绾。将“问”之具体行为转为“问而不问”、“不问而又欲问”之复杂心理,形成巨大的叙述留白,增加了诗句的容涵。最后一句承“欲问”句,再次形成叙事因果链,以“不知”与“自”串联,将欲问不问之缘由表达得曲折无比。“欲问”是因“身世悠悠”的同病相怜,抑或是“不知身世悠悠”的泥人救溺?紧接以一“自”,看来还是知道身世悠悠。故“不知”就是“知”,亦为一笔双绾。而“自悠悠”者,说明“知”只是“自知”,而对外来说,是“不知”也,这也包括叙述者所欲问不问之孤鸿。人与孤鸿构成富有寓言意味的单向度对话。人知孤鸿飘零之苦,故欲有问,其欲问时,浑然忘记“自悠悠”之身世;待其见孤鸿飞远,忽然醒悟“自悠悠”之身世,则终于问不出口。人对鸿虽未问而欲问,鸿对人则未答而终不欲答,人知鸿飘零之苦,而鸿却不知人之身世悠悠。“怜人者正须被怜,而竟不自知其可怜,亦无人复怜之也”,①诗意之曲折细腻,一至如此。“身世自悠悠”收篇,又回应首句之“绕天愁”,形成本诗所有叙事因果链的终极之因,使本篇成为闭合完整的叙事体。
从对本诗的分析可以看到,词语、句法、结构等的精确使用、灵活组合,形成各种层进勾合的叙述关系,使一首诗丰富深曲的内涵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
四、对义山七绝叙事的思考
以上从三大方面对李商隐七绝作试验性之叙事分析,有几点需要作出说明。第一,本文借助西方叙事学的一些概念、术语,但有自己的理解与应用,故不尽符合所借用学术概念之原始意义。②本文也审慎地使用“叙事视野”、“叙事分析”等说法而非“叙事学视野”、“叙事学方法”。第二,分解分析义山七绝叙事特点,实为肢解混沌。很多诗例,在不同的小节中,都可以作符合该节需要的解读。比如第三节从语词逻辑上分析义山七绝层进曲折的特点,其实前两节的时空叠映、事外有事,同样促成这种层进曲折。本文在各节的分解中,时有混同,就说明很难做到绝对肢解。实际上,义山七绝丰富复杂,分而为肢,合而为体,然肢即体,体即肢,其间血脉贯连,乃一以语言为元件的生命有机体。第三,因为第二点,本文对义山七绝叙事的分析远远不够,如叙事干预、叙事视角、隐含作(读)者与真实(读)作者、不可靠叙述、戏剧性叙述思维,等等,间有涉及,却未曾展开。这也说明从叙事角度,对义山七绝的艺术研究,空间极大,难以用几篇文章完成。
对义山七绝作叙事分析,文首略有论及,在此稍作补充。一是义山七绝自身的特点。本身即具故事情节,为叙事学之当然对象者,可不必论;除此之外,“千丝密网”的逻辑结构、“包蕴曲折”的文本空间,对叙事而言都极具魅力。二是义山七绝所体现出的艺术思维,适合作叙事分析对象,它有这样突出的两点:戏剧思维与影像思维。戏剧思维既包括诗歌所叙内容本身具有戏剧性,如《北齐二首》、《龙池》,也包括戏剧化的写作方式,如《贾生》、《谒山》、《夕阳楼》。冯浩谓义山诗“总因不肯直叙,易令人迷”[6],而“不直叙”恰恰是叙事作品制造诱人情节的不二法门。影像思维,实即意象、意境之营造,如《咏史》“一片降旗百尺竿”。这是对传统诗歌思维的继承,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叙事学对诗歌分析有适用性。三是叙事学本身的特点。正如米克·巴尔在《叙述学》中所说:“叙述学有效地适用于每一种文化对象。并非一切‘是’叙事,而是在实践上,文化中的一切相对于它具有叙事的层面,或者至少可以作为叙事被感知与阐释。”[7]“作为叙事被感知与阐释”,可以是将“事”本身进行泛化,“事”是一切对象的客观存在形式,也可以是将叙述看成万能的阐释手段。即便是想当然的纯粹抒情作品,当你在讨论它如何抒情的时候,实质上就是在分析它如何叙述。此外,对于被认为是“抒情”的作品,“叙事”能被阐释还在于它可以成为抒情的有效功能,即作为修辞方式而存在。以李商隐《无题》为例:
白道萦回入暮霞,
斑骓嘶断七香车。
春风自共何人笑,
枉破阳城十万家。
“枉破阳城十万家”用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故事,情节丰富,极具戏剧性,是典型叙事作品。而在这里,不过是用以形容车中人之美艳无比。即便不认同叙事学家对叙事的扩大化,依然坚持七绝本质为抒情诗体,也不得不承认,叙事是可以作为修辞方式,参与抒情并深化抒情的。
实际上,叙事学研究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发展而来,注重语言、形式、结构等文本要素,致力于对文学性的揭示,对当前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具针砭意义。当前古典文学研究中,多偏向于文献、史料,这些当然极其重要,但这不过是通向正桥的引桥而已,究其性质实为史学。真正的文学研究的正桥上,一直车马冷落,偶有三两辆,也是蹇驴牛车,缺乏深度与气象。这与研究视野与思维的局限,如将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歌仅视为单一的抒情文学有很大关系。在此背景下,寻找并激活古典诗歌固有的叙事传统,应用叙事视野来观照古典诗歌,对古典文学研究走向深入,当不无裨益。
[1] Walter F. (1987). Human Communication as Narration: Toward a Philosophy of Reason,Value and Action[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 王蒙文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45-448.
[3]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4]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569.
[5] [法]热奈特.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60-70.
[6] 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97.
[7] [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63.
(责任编辑:梁临川)
Yishan’s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LI Han
(SchoolofLiberalArts,Shanghai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Yishan’s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in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 terms of time and space relations, narrative behavior, narrative style, poetic context, syntax and grammar, aiming at artistic evaluation. In Yishan’s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the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features the intertwining of remoteness and closeness, the reflection of emptiness and concreteness, the contention of reality and imagination; The narrative style is characterized with subtleness, implicitness and intricacy;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include entangling plots, gradual mapping of structures and extricate suspense. All of this makes Yishan’s quatrains rich in contents and ideas with logic and deep feelings at extremely short length. By applying narrative analysis to Yishan’s quatrains which are praised as “flowing treasures with silk net-like constructions”, we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ir poetic context, but also grasp the subtleness and development of poetic heart and poetic connotations. The introduction of nar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is conducive to the return of its research to original literature studies and possibly in an in-depth manner.
Li Shang-yin; seven-character quatrains; narration;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narrative white space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1.008
2014-11-25
李 翰(1974- ),男,安徽桐城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魏晋隋唐文学与文论。
I206
A
1007-6522(2015)01-01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