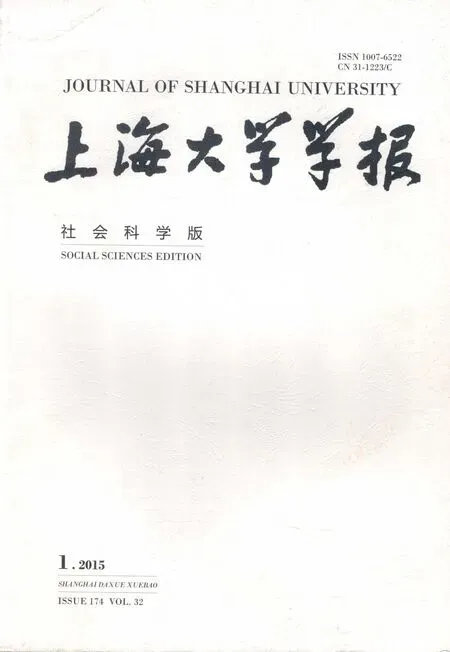环顾影像:德勒兹影像分类理论释读
聂 欣 如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环顾影像:德勒兹影像分类理论释读
聂 欣 如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理解德勒兹电影分类理论的关键在于对其差异哲学的了解,凭借差异哲学的思想,德勒兹将电影影像分成了两个大类,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这两种影像都被德勒兹置于了差异化的思考之中,影像一方面是实际的,一方面又是潜在的;一方面是客体,一方面又是自主的存在。在关照影像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中,德勒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影像分类系统。这一系统基本上是以空间和时间为原则来区分影像的,但高度抽象的哲学命题很难切入现实的电影影像,对其实施有效的“管理”,德勒兹显然是在哲学化影像的同时兼顾了电影的纪实美学,才建立起了自身的电影理论体系。因此,分类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纪实美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过渡也就成为了观察(阐释描述)和哲思之间微妙的博弈。
电影理论;影像;德勒兹
德勒兹电影理论是出名的难读,巴迪欧曾将其称为“双重苦行”。①巴迪欧的“双重苦行”并不仅指德勒兹的电影理论,也包括其他方面。可参见陈永国主编的《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213页。尽管国内已经出版和发表了不少相关的专著、译著和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们对于德勒兹电影理论的陌生感,但离清晰的了解还是有相当距离。这篇文章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读解德勒兹的电影分类理论,尝试一种新的维度,意在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德勒兹对于电影的想法。
影像如何被“环顾”
一般理解“环顾”,特别是影像的被“环顾”,是将影像看成对象,我们作为主体,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和研究“影像”这一事物,类似于一种地球环日的“公转”。而对于德勒兹来说则不是这样,德勒兹把影像等同于运动,运动无处不在,因此影像也就无处不在。他说:“就电影而言,是世界变成为它特有的影像,而不是一个变成世界的影像。”[1]119这也就是说,整个的世界都可以是影像,甚至包括我们在内。这样一来,便没有可能区分出主体和客体了,你的四周都是影像,你所要讨论的问题在你的四面八方。因此对于德勒兹来说,他的环顾与我们的理解相反,我们认为是围绕着对象转圈,他认为是自身旋转,类似于“自转”,把目光投向我们绝对不会看到的身后。
德勒兹电影理论的这一立足点从何而来?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哲学而来,他认为对于电影来说,“不应该再问说‘何为电影?’而是‘何为哲学?’”。[2]751这是什么意思呢,电影何以能够变成哲学?这是因为他认为哲学的立场不同于一般所谓科学的立场,科学的观念是为人们提供清晰的、可理解的对象事物,而不是那些模棱两可、尚处在未知混沌中的事物。柏格森用万花筒作比喻来说明这点:“我们每个行动的目的都是:以某种方式将我们的意志插入现实。我们的身体与其他的实体之间,存在一种安排,它就如同构成万花筒图案的那些碎玻璃片的安排一样。我们的活动从一种安排走向一种重新安排,而每次都无疑使万花筒产生新的摇动,我们的活动对摇动本身并无兴趣,而仅仅对新图案感兴趣。”[3]德勒兹延伸了柏格森的这一思想,提出了许多复杂的论证,这里不再复述。德勒兹也有一个比喻很好地说明了自己的意思,他把哲学对于事件的展示比喻成《爱丽丝漫游仙境》中的隐身猫,它在消失后会把自己的笑容留在空中,而科学则是将事件“实显化”,因此德勒兹的结论是:“科学和哲学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4]所有的麻烦均来自于此。作为一般人,而非哲学家,我们的思考和想象基本上都是“科学”化的,那些非科学的成分都被驱赶至潜意识和梦境之中,而德勒兹的电影理论是从一个非科学化的哲学立场和角度出发,专门针对一般人无法想象的混沌世界,这就难怪一般人难以理解了。
我们在此碰到的麻烦是,我们应该怎样来阐释德勒兹的电影分类理论,如果我们站在德勒兹的哲学立场上,那么我们写出来的东西会和德勒兹一样佶屈聱牙,难以被理解;如果我们站在自身的立场上,那么我们的解读就难免会曲解、误读德勒兹的本意,这也是当今国内电影理论释读德勒兹最大的问题。①这样的问题我自己也很难避免,我在《电影的语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版)一书中有关德勒兹的部分,亦有表述不够准确之处。在此,我打算采用一种折中的立场,既非德勒兹的哲学,亦非我们的“科学”,而是设法“改造”德勒兹的视点,从我们的立场加以理解。用一个形象的说法,我们既不跟随德勒兹像陀螺似地自转(我们不是哲学家,我们会“晕”),也不像地球环日那样面对客体公转(只有克服这一惯性,才有可能理解德勒兹),而是将我们的观察方法,施之于德勒兹,也就是把德勒兹作为我们的对象,让我们来看他的“旋转”,从而理解他的变成了影像的世界。
影像的源起及其理论
既然在德勒兹看来影像就是世界,或者说就是这个世界无所不在的运动的一份子,那么影像的起源就会是个问题,它不再是科学技术的问题,也不再与1895年法国的卢米埃尔兄弟有什么关系,它和运动同在,与物质同在,早在生命诞生之前的洪荒远古就已存在。这听起来有些荒诞,但德勒兹就是这么认为的。他把影像写成“运动-物质-影像”,以示其由来和身份,他向我们描述的最古老的感知、动作影像,是远在生命生成之前的混沌世界之中。就如同中国古人所说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那样,在一片混沌之中,开始逐步出现“核心化”的感知和“蜷曲化”的动作。德勒兹说:“生物学家谈到一种可能创生生命体的‘前生物态溶液’,其中所谓右旋与左旋物质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就如同这样的状况一般,在无中心世界里会出现坐标与原点的雏形,一右一左,一高一低;即使在前生物态混合液中也必要孕含着微区间,但由于生物学家还说过这样的状况只有在地表高热时才可能发生,所以必要孕含有某种内运平面的冷却,这平面是同制造光照障碍物的最初不透光性与最初银幕相关联的平面,而固体、刚体与几何体的最初雏型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1]126德勒兹当然不是对电影技术诞生于19世纪一无所知,他对于“影像”概念的使用源于柏格森,柏格森将事物切分至极其微薄(光波粒子的厚度)的剖面之后,事物便成为了“影像”,但是此“影像”非彼“影像”(电影影像),同为“影像”却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具有巨大的差异,促使德勒兹将两者联系起来的便是他的哲学。
德勒兹的这一哲学被称为“差异”哲学,这一哲学与众不同,它强调的是经验与先验的差异,外在与内在的差异,清晰与混沌的差异。德勒兹举例说,如果笛卡尔要我们思考三角形,便不可能超越三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但是,“那种真理都是假设的,因为它们预设了所论的一切问题,因此不能在思想中激发思考的行为。事实上,概念只能表示可能性。它们缺乏绝对必然性的爪——也就是施加于思想之上的原始暴力;怪异的利爪或敌意的利爪,只这一点就能把思想从自然倦怠中或从永恒的或然性中唤醒:所唤醒的只是无意识的但却被束缚在思想之内的思想,而且愈加绝对必要地非法地产生于世界的偶然性”。[5]39这段话引自德勒兹的《重复与差异》(又译《差异与重复》),了解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思想是了解德勒兹电影理论(也是其所有艺术相关理论)的关键,只有从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他相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这一理论指向了一个对我们而言陌生的世界,在那里不再有“清晰”、“逻辑”这些为一般人所熟知的概念,那里似乎只是一个怪兽咆哮的荒原。因此,有人将这一理论形容为“革命”:“由于德勒兹坚持差异性与多元性是首要范畴,颠覆了同一性的思想霸权的传统,因此,‘差异与重复’的哲学观念无异于哲学上的一场革命。”[6]显然,面对一个不停旋转的德勒兹,我们既要习惯于他面对我们,也要习惯于他背对我们——如同快速旋转中消失了的形体,因为当德勒兹在强调差异时,其一端便置身于太虚的混沌,既没有客体也没有主体。差异理论将我们带入了一个虚拟的世界,在那里不能指望舒适地依赖你的本能和经验,德勒兹并不讳言虚拟,他说:“虚拟不是与真实相对立,而是与实际相对立。虚拟仅就其虚拟性而言完全是真实的。”[5]66因此,德勒兹的电影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虚而言”,他不停地将具有实体意味的影像导向虚拟的世界,在那里,“普通意义上的实在不再是主体,成为倾向的一种表达,这样差异本体就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一元实在本体,实在只是差异的一种外在表达而已”。[7]差异哲学所标示的不仅是学术上的标新立异,同时也是现代社会催生的对于我们自身和社会的思考,人在世界中不甘屈从于物,有必要从最本源的基础上对自身的存在进行再思考。德勒兹说:“我们在此并不是为了建立有关能力的某种学说。我们只是想确定其各种要求的性质。在这方面,柏拉图的决定因素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能够使能力发展到各自极限的并不是已经中介过的和与再现有关的外形,而反倒是差异本身自由的未驯服的状态;不是可感事物内部质的对立,而是本身就是差异的一个因素;它既创造了可感事物内部的性质,又创造了感性内部的先验运用。”[5]44不过,我们在研究德勒兹的电影分类理论时发现,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追求差异而“背对”影像,而是不时地转过身面对影像,有时还打量得特别仔细。
当德勒兹将他的差异哲学运用于电影理论的时候,电影便与整个世界发生了关系,电影影像对于德勒兹来说只不过是这个整体的一个局部,“运动自身就作为发生变化之全体的活动切面”。[1]55这一理论被直接使用在了电影镜头的制作上,柏格森的超薄影像切面概念通过时间向度增厚成为实体(这一过程被称为“时延”),变成了电影的镜头影像,并与生成它的世界保持着关系。德勒兹说:“镜头就如同不断进行转换及循环的运动,它根据组成整体集合的客体们对于时延进行分化即再细分,并将客体与整体集合重新整合为单一的新时延;它不断地将时延分化为彼此异质的次时延,并将这些次时延整合到作为世界全体的内运时延里。”[1]57蒙太奇的情况也是如此,也被与非影像的全体世界联系在一起,“蒙太奇其实就是镜头的一体两面:一边作为不再仅仅满足于单一镜头的入镜整体集合,它还展示着在度量单元(意即在多重取镜中)产生变化的续列中的相对运动,而另一边则是影片的全体,这全体不再满足于作为一种影像续列,而企图在必须于此刻寻获本质的绝对运动中自显”。[1]96由此,我们对德勒兹的差异哲学有了一个概念化的了解,不论我们是否能够全面深入地理解,至少是有了心理上的准备,这样我们便可以跨入德勒兹的影像分类理论了。
德勒兹将电影影像分成两个大类:“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见下表),下面我们分别进行讨论。

运动-影像时间-影像时间间接时间直接时间感知经验先验心理外在内在运动相对运动纯运动情境感官机能情境纯声光情境
生命起源式的“运动-影像”
按照德勒兹的说法,他的分类是按照生命起源(或者说宇宙起源)的模式来进行的:在洪荒太古,世界尚处在一片混沌之中,没有生命,物质处于一种散漫无序的状态,然而,就在这无序之中,开始出现了一种“核心化”的趋向运动,并伴随着“蜷曲化”的运动形态,物质开始分出彼此,有了区间。这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感知”,这样一种“感知”与“运动”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动作”相伴而生,区分彼此也就是分出主客,“动情”于是也就顺理成章地介乎于感知与动作之间。所以,德勒兹的感知-影像、动情-影像和动作-影像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诞生的,并且是在一个无人之境中的自身生成,这也就是他所称的“以己影像”,[1]123显然,该影像不存在“被看”的问题。可见,德勒兹从一开始便是“背对”我们所谓的一般影像,因此他能够在两者(原始影像与银幕影像)的“重复”之中区分出彼此之间巨大的“差异”。
比如,在感知-影像中,德勒兹注意到的是一种“半主观影像”[1]143现象,这一现象一直是电影叙事和电影语言研究中的难题。最初可能是由欧达以“缝合理论”[8]的方式提出来的。欧达在研究“正反打”的时候发现,有一种“过肩”的拍摄,既不能用主观的视点来解释,又不能用客观的视点来解释,于是自己想象了一个解释的理由,这一理由后来遭到波德维尔的有力批驳。后来的研究发现,这样的表现方法竟然不是电影语言的偶然现象,而是常态,不仅在“正反打”的方式中出现,也在其他的表现手法中出现。[9]经由这一现象,德勒兹将感知-影像从我们的视野中拔出,赋予其完全自主的地位,他说:“的确,我们在电影里可以看到那些自称为客观或主观的影像,可是除此之外还有着另外一回事,它涉及越出主、客观而朝向某种自主性内容视像的纯粹形式;我们不再身处于主观或客观的影像前,而被卷入感知-影像与某种转化着感知-影像的摄影机-意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至此,问题已不再是知晓孰为主观或孰为客观)。”[1]145德勒兹认为,感知-影像与一般影像的差异便在于它是一种“间接自由主观”,“它就像是化身摄影机之意识里的影像反思”。[1]147“间接自由主观”的概念从帕索里尼而来,帕索里尼对于“自由间接话语”的解释是:“作者完全深入其人物的内心,他不仅采纳人物心理,而且也采纳其语言。”[10]与帕索里尼不同的是,德勒兹将话语权完全给予了影像的本身,从而排除了主客体参与其中的可能,感知-影像因而悬浮脱离现实世界。除此之外,德勒兹还把感知-影像细分成固态、气态、液态等不同的虚拟形态,这里不再详述。
动情-影像和动作-影像也是如此。对于动情-影像来说,德勒兹强调的是其作为身处感知-影像与动作-影像之间的中介功能,因此其本身的影像属性被高度抽象化,成为一种“动情力”,动情力具有“质”和“力”两种不同的属性,简单来说,力的作用在于促成动作的产生,质的作用则是将局部抽象出来与全体联系在一起。“质性变成某客体的‘化质’,力量变成动作或激情”,“至于动情-影像,就是将它带入事物状态的时空坐标的抽象物,并在这状态中将属于该人物的容貌给抽象化”。[1]178德勒兹把动情-影像分成两种,一种是人(面容)的特写,一种是物的特写,两者在功能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德勒兹在谈到伊文思的作品《雨》的时候说:“至于雨,既不是雨的概念,也不是降雨的时间或空间状态,而是使得雨自显为纯粹质性、纯粹力量的独特性所构成的集合,它毫不抽象地将所有可能的雨调和在一起,并构成了相应的任意空间。”[1]198-199德勒兹对于动作-影像的思考,同样也不在动作的本身,而是在动作与非动作的间隙,这可以从他对于动作-影像的具体分类命名看出。德勒兹将动作-影像分成两种:一种是“大形式”(ASA),即情境-动作-情境;一种是“小形式”(SAS),即动作-情境-动作,对于动作和情境之间关系的考虑成为了动作-影像的核心。德勒兹说:“在情境与即将发生的动作之间必须存在一个巨大间隔,而这个巨大的间隔为的就是酝酿,酝酿一段有进有退、高潮迭起的过程。”[1]263思考“间隔”,便是思考差异,思考影像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影像的本身并不包含物理性的间隔,“间隔”仅存在于思考之中。
感知、动情和动作这三种影像,都被德勒兹置于了差异性的思考之中,也正是因为看到了差异化的另一端,这些影像呈现出了脱离具体影像的非主体化的特征,它们互为结构,形成了一种“以己影像”的自然化生成状态,影像的这种状态是非经差异化哲学所难以揭示的一面,它指向非现实和虚拟的范畴,存在于一个被德勒兹称作的“内在性平面”①参见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迦塔利的《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版,第247页。在《电影1》(第126页)中“内在性平面”被译作“内运平面”,参见前面引文。之上。
写实关照中的“运动-影像”
不过,德勒兹以生命起源、生成的方式来讨论电影影像的分类并不充分,因为这样的方式只是一种类比化描述,只能构筑一个粗略的框架,不可能将讨论深入到影像的内部(对于德勒兹来说或许应该是“外部”),正如我们在类比的情况下所看到的,只能涉及三种不同的影像类别,而不是六种。[2]414-415因此,德勒兹必须借助另外的工具,以一种不同于生命起源方式的规则来框架影像,才能够使他的影像理论从洪荒远古回到今天,也就是使他必须时常转过身来关照现实的而非先验的、内在的影像,一个作为客体而非主体的影像,也就是作为差异的另一端必然会被视见、被看的那个影像。这个工具显然与皮尔士的指号学(也被称为符号学)相关。

运动-影像分类皮尔士指号学景别影片类型1、感知-影像0度全景2、动情-影像第一度特写3、冲动-影像(过渡)自然主义和原貌世界4、动作-影像第二度中景纪录片、剧情片、喜剧片5、反映-影像(过渡)6、关系-影像第三度推理电影、新好莱坞电影
德勒兹使用皮尔士的指号学似乎有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意味,因为他并没有严格按照皮尔士的指号学来规划自己的影像符号分类,但是对于整个影像的分类系统来说,皮尔士的影响又似乎无处不在。我们知道,皮尔士的指号学与索绪尔的符号学大不相同:索绪尔的符号学严格限定在语言符号的范畴之内,其符号的所指并不指向实在之物,而是指向物之概念;[11]“而在皮尔士那里,指号的根本功能则是作为对实在世界的指称”。[12]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德勒兹不仅把影像作为一种存在于洪荒太古的想象之物,同时也把影像当做一种“实在”,并把影像的“实在”与其本身的纪实功能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纪实性,影像的“实在”便只剩下赛璐珞和感光化学涂层了,这显然不符合电影的概念。
现在我们再来看在电影纪实美学观念影响下德勒兹的影像分类系统。
首先,感知-影像消失不见了。感知-影像因为自身无所不在,既可以是主观的,也可以是客观的,[1]148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基础性的存在,使其自身的特点消失于无所不在之中,德勒兹将其称为一种“0度”的存在,他说:“严格来说,感知就等同于影像。”[2]414这也就是说,只要是影像,它就是一个感知。这就如同空气对于我们生存的必要性,我们每时每刻都需要空气,但我们一般不会表达这种需要,我们可能需要水、食物,但很少有人会表述需要空气的欲望。感知-影像贯通内外,勾连主客,往来于全体世界的这样一种一般化的存在,使其在具体的影像分类中不再能够发挥作用,或者说,当德勒兹转身面对实存影像的时候,他脑后那个在混沌世界中被生成的虚拟化影像便不再能够被看见了。
其次,空间概念被引入。当德勒兹把感知-影像、动情-影像、动作-影像分别对应于全景、特写、中景的时候,已经是结合空间的概念来思考影像了。空间与时间不同,按照柏格森的说法,人们在对事物进行思考和计算的时候,一定是以空间作为依托的:“倘若我们把时间解释为一种媒介并在其中区别东西和计算东西,则时间不是旁的而只是空间而已”。因而他得出结论说:“我们相信空间是实在的东西。”[13]67,68正是在空间的概念中,德勒兹面对影像,或者也可以说,德勒兹面对影像思考时,便进入了空间。
如果说动情-影像因为空间的局促不具备拓展的余地的话,那么动作-影像便是完全凭借实在的空间来思考问题了。德勒兹对此说道:“质性与力量不再展现在任意空间里,也不再盘踞于原貌世界中,而直接就在由地理、历史、社会等因素下决定的确定时空里生成;动情力与冲动也只能体现在用感动与激情形式加以调整或扭曲的行为表现上,就是写实主义。……构成写实主义的是地点与行为表现,或者说形成的地点与成形的行为,而动作-影像就是两者间的连系以及这些连系所产生的诸多变化。”[1]245-246显然,在动作-影像中,德勒兹已经完全转向一般意义上的影像,但是他对于空间意义的理解,仍然与一般人保持着距离。在他有关动作-影像的论述中,空间首先被呈现为实录的影像空间,也就是纪录片;然后是社会心理剧、黑色电影、西部片、战争片等(大形式);在与之“逆反”的小形式中,则主要被呈现为喜剧片,也包括一些警匪片和带喜剧色彩的西部片。显而易见的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动作-影像的区分在于现实性和非现实性。那么,具有写实性的剧情空间又是如何向着非写实的喜剧空间逆转的呢?它们又是如何被置于同一个影像类型之中的呢?德勒兹在原则上将两者都置于了“写实”的原则之下,不过喜剧的写实是一种内在的、与非现实表面逆反的写实,是要通过“细微差异开凿成两种无法调和、彼此对立的相异情境”,[1]289其实质还是要提出尖锐的社会现实问题。因此,德勒兹对于卓别林那些深入触及社会现实的喜剧电影赞赏有加:“卓别林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将两者充分混融,越是好笑就越是触动内心深处。”[1]287不同的外部形式并不能掩盖内部的一致性,这样便使类型的归属有了逻辑性。至于外部形式的改变,德勒兹使用了一个“拓扑”的概念将两者联系在一起。其中最为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西部片。同为西部片,既可以是非常严肃的《双虎屠龙》,也可以是带喜剧色彩的《小巨人》。《双虎屠龙》严肃到不像一般的西部片,其中既没有除暴安良的英雄,也没有货真价实的决斗;《小巨人》中的男主人公既是印第安人,又是白人,在白人追杀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奋起反抗的年代里,他不停地变换着自己的身份角色。从严谨的写实到荒诞喜剧的渐变,被统一于西部片追求真理神话的内涵之中,①有关西部片的“神话”说可参见安德烈·巴赞的《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4月版。拓扑的含义便在于一致性之下的互反渐变。
最后,在生命起源模式中,感知、动情、动作三种影像形态是同时生成的,彼此依傍而存在,不需要附加的过渡性事物;而实存的影像是一个叙事的过程,不同影像类型的出现不可能是同时的,因此彼此之间需要过渡,从静止状态的“动情”到动作,从动作到叙事整体,不可能跳跃性地生成。所以,我们在德勒兹的影像分类中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过渡类型以及并非具有生命起源状态的关系-影像。
德勒兹罗列了两种不同的过渡性质的影像类型,但却只对其中的一种,即“冲动-影像”展开讨论。皮尔士在论述现象范畴过渡的时候提到过“冲击”[14]181-182的概念,德勒兹显然受其影响。尽管德勒兹所有对于冲动-影像的描述都在说这是一种介乎于动情-影像与动作-影像的过渡形式,但是在我看来,他却是在不停地言说从具有内在性的影像到具有外在形式的影像的过渡,也就是从生命起源模式到写实模式的过渡。冲动-影像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自然主义”和“原貌世界”,自然主义似乎是一种“静态的暴力”,而原貌世界则表现了残忍的“原始暴力”,这两者的背后都是写实的地点,超现实的原始暴力必须被压抑方能够过渡到动作-影像。在德勒兹所举的例子中,既有《娜娜》、《女仆日记》这样表现自然欲望的作品,也有《科学怪人的新娘》、《金刚》这样的超现实作品。德勒兹显然是认为人类暴力欲望差异的两端必须通过综合平衡才能够成为“正宗”的影像类型,否则便永远只能是一种类型形式的“过渡”。
关系-影像的概念显然也是来自于皮尔士,但与皮尔士不同的是,皮尔士的“第三性”或者“第三范畴”(即德勒兹《电影1》、《电影2》译本中的“第三度”)概念尽管也是一种“实在”,但却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它必须建立在与第一性、第二性的关系之上,是一种“把时间连接起来的综合意识、学习感、思维”。[14]188然而,在德勒兹的相关论述中,时间性的观念被刻意强调了出来,他认为这就是直接的时间因素出现后“动作-影像的危机”。[1]325德勒兹认为,关系-影像主要对应的是新影像类型(新好莱坞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出现,而不是与前面两种不同层次影像类型,即第一度的动情-影像和第二度的动作-影像的综合,正是因为新的影像因素的出现,所以造成了传统动作-影像的危机。这一危机的实质指向时间,与皮尔士的实用主义背道而驰。德勒兹对这一点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与皮尔士分道扬镳。他说:在皮尔士的分级存在理论中“不免可以见到一种辩证关系的存在,可是辩证法是否得以涵盖这种区分下的所有运动则有待斟酌,所以我们只能说辩证关系在这里只是一种诠释、一种极为匮乏的诠释”。[1]326-327可见,德勒兹并不愿意把自己束缚在强调“实用主义”的皮尔士指号学理论之中,他要在影像的“实在性”与“虚拟性”之间保持平衡,不停地“旋转”。
从重复和差异完全不同的两端来认识德勒兹的运动-影像,能够使我们建立起一个相对立体的印象,不至于迷失在混沌或实在之中。
“时间-影像”的三种样态
要了解时间-影像,首先需要了解“间接时间”和“直接时间”的概念,因为时间无所不在,所以只有区分出时间的不同属性才有可能了解时间-影像。一般来说,我们经验中的时间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无视它的存在,这就是德勒兹所谓的间接时间。顾名思义,它在我们的意识中被忽略,只是一种“间接”的存在。时间的这种存在因为与人无涉,因而具有科学的性质。柏格森说:“科学要把那主要的、性质的因素先行去掉,即从时间里去掉绵延,从运动中去掉可动性。”[13]85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直接时间与间接时间的不同所在,直接时间必须呈现为“绵延”,也就是为我们所意识到、知觉到。人们对于绵延的知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柏格森解释说:“无论我们假定纯粹知觉有多么短暂,其实它都要占据一定深度的绵延,因此,我们的连续知觉从来就不是事物的真实运动(像我们迄今所假设的那样),而是我们意识的一个个瞬间。从理论角度看,我们说:意识在外部知觉中的作用应当是不间断地穿过记忆,将真实的即时幻象结为一体。”[15]54换句话说,绵延与人们的记忆直接相关。那么,这种与记忆相关的时间理论又是怎样被德勒兹加以利用而改造成时间-影像中的直接时间呢?
德勒兹分两步走。首先,从影像形态的分析入手,将某一种类型的影像析出,将其重新命名,“透过这种一连串出于平常无奇、日常性情境的毫无所指,但却更符合单纯感官机能图式的姿态,一种纯视效情境骤然浮现”。[2]372德勒兹认为:那些平淡无奇日常生活的影像不同于一般影像强烈的视听效果,因而脱离了诉诸“感官机能”的情境,进入了“纯声光情境”。德勒兹说:“纯声光情境→直接时间-影像这种无法界定的关系取代了感官机能情境→时间的间接影像的连系。”[2]425这里所说的“纯”很难从影像自身的纯粹性来理解,实际上是德勒兹转身背对影像进入虚拟化范畴的一种状态。其次,单独的纯声光影像并不能构成直接时间,只有在记忆的参与下,纯声光影像开始扭曲、变形产生绵延,方能够使直接时间得以呈现。德勒兹说:“纯声光情境(描绘)是一种实际影像,但它并没有延伸为运动,而是同某种潜在影像串联,并以这潜在影像形成一个廻圈。”[2]437那么,什么是潜在影像呢?“回忆,即柏格森称为‘纯粹回忆’者,则相反地作为一潜在影像。”[2]448德勒兹借用了柏格森的倒锥平面图,[15]144构成了时间-影像的理论模型。
参照倒锥平面图,我们便可以讨论德勒兹时间-影像的第一种样态了,这就是“晶体”。柏格森的倒锥平面图是由一个倒立的圆锥体和一个平面组成的,倒锥立于平面之上,倒锥代表过去的记忆,平面代表现在时态。当回忆经由圆锥体下降到与片面相交的那个“点”,便是晶体。因此,晶体具有两个不同的属性:现在时和过去时。两者在一个点上交汇,形成一种在时态上的“不可区辨点”,“这个不可区辨点就是由最小圆圈所组成,即实际影像与潜在影像的嵌合,一种同时具有实际与潜在的双面影像”。[2]486在此,我们来到了德勒兹影像理论的难点,因为德勒兹坚称,潜在影像与实际影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不可混淆。他说:“实际影像及其潜在影像组成了直逼尖端或点的最细微内在廻圈,但却是一种仍然拥有不同元素的物理点(有点近似于伊壁鸠鲁的原子)。”[2]470这也就是说,潜在影像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潜在性,并没有成为一种“实在”。对于一般的理解来说,如果事物不存在于外部的世界,那么便只能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人作为主体,观看作为客体的影像,除此之外,似乎没有第三个可以立足的空间。但是德勒兹明确否认了这样的想法,他说:“真实与想象物、当刻与过去、实际与潜在之间的不可区辨性并没有发生在脑袋瓜或精神里,而是某些实存的双重影像的客观特性。”[2]469在此,我们显然不能从将影像作为客体的“公转”立场来理解德勒兹的晶体,而只能从德勒兹的“自转”立场来理解他的想法。对于德勒兹来说,影像,特别是呈现直接时间的影像,并不是一个客体,他本身在环顾四周时也不是一个主体,而是在一个内在性的平面之上(这一平面不存在主客之分),这样,晶体便可以既不是外部,也不是内部的事物。德勒兹借用普鲁斯特的话说:“时间并非存于我们内在,而是我们置身于时间内在”,“主体性从来就不是我们的主体性,而是时间的”。[2]484这样,我们便随同德勒兹一起降落在了时间的荒芜星球上,如果事情就此了结,成为直接时间的孤魂野鬼倒也干脆,但是,一旦涉及具体的电影,德勒兹还是不得不转过身来面对影像,这样一来,习惯于“公转”的我们便不得不跟随德勒兹“自转”。
德勒兹将晶体分成三种不同的形式:“实际与潜在(或说两两相向的镜子),清澈与不透明,种子与地点。”[2]471这一两两相对、彼此循环的形式,说明的正是晶体回旋不可区辨的两个方面,时间在实际的存在和潜在的存在之中分成两个不同的面向,一个朝向过去,一个朝向未来。走向过去的影像就如同镜子映照着未来。德勒兹用电影《乌鸦》作为例子来说明实际与潜在,他说:“公众角色的潜在影像变为实际,相对地他个人犯罪的潜在影像也会变为实际,甚至取代前一种影像。”[2]472德勒兹对于这种实际与潜在循环的晶体描述并不难理解,影片中的罪犯是个主教,开始所有人(包括观众)都将其认同为好人,这就是“好”的潜在性变成实际。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主教邪恶的身份一点一点被揭示出来,于是这一层面上的潜在也会变成实际。从一般的认识来看,影片中逝去的影像总是在不停地成为观众的记忆,并伴随影片的进展成为潜在的影像(时间朝向过去),它映照着实际的影像,让观众能够理解故事和人物的进展变化(时间朝向未来)。拥有回忆-影像的影片也是如此,“《萝拉·蒙戴丝》可以包含倒叙:如果需要,该影片只需要确定在何时倒叙只是作为进行深化的次要程序,因为真正重要的并非实际悲惨的当刻(马戏团)跟过去美好当刻的回忆-影像之间的关联。回想的确存在,但它更为深刻揭露的却是时间的分化,它使得所有当刻成为过往,一方面朝向过去的马戏团,另一方面则投向未来,同时它也保留下所有的过去,置放在马戏团上,就像是潜在影像或纯粹回忆”。[2]486需要注意的是,这段话中提到的“过去的马戏团”和“马戏团”是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马戏团。“过去的马戏团”是影片女主人公蒙戴丝的马戏团,她是老板;“马戏团”则是蒙戴丝落魄后在其中充当演员的那个马戏团。萝拉·蒙戴丝曾是欧洲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她以姿色征服过德国国王和欧洲各国政坛的许多王公大臣,但是她作为一个身份低下的马戏团女演员,最后的结局却十分悲惨,为了生计,她不得不屈从于将她的艳遇编成马戏节目来吸引观众的马戏团老板。影片以现在时与回忆的交叉呈现了这个人物的一生。我们在观看这部影片时,当然是越往后集聚在记忆中的潜在影像越多,从而影响我们对于这个人物的判断。德勒兹轮廓分明地描述了实际与潜在晶体。
清晰与不透明的晶体形式是指一种在强烈戏剧化氛围中生成的晶体,“廻圈就像是试验角色的过程,一直试到找出最好的角色,以求通过它们逃向一种澄清的现实”。[2]488德勒兹用来举例的影片是《游戏规则》,这部影片嘲讽了资产阶级的虚伪和空虚,他们将爱情视为游戏,一位年轻的飞行员不谙其道,真情投入,结果却被误杀。实存和潜在的因素在一个似真而假的虚伪层面上反复循环,清晰与不透明的晦暗交替闪烁,德勒兹将这样一种在强烈戏剧化中暴露出社会残酷真实的形式称为“晶体的裂缝”,只有晶体的破碎方能够将这一真实暴露出来。所谓“破碎”便是循环戛然而止,一切虚伪的掩饰都暴露无遗。我们在《游戏规则》的结尾看到,那位声称“爱”着飞行员且要与他私奔的贵妇,在飞行员被打死后,面带笑容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种子和地点的晶体形式比较特别,这种晶体是一种孕育生成过程中的晶体,因此其交替循环的实存与潜在两个方面不是特别的明显,而是难以辨认,用德勒兹的话来说:“在费里尼那儿,是当刻,逝去当刻的轴线编织成骷髅舞,它们流动,但却是朝向墓穴而非未来。”[2]494尽管这样一种象征化的表达不是很好理解,但是我们从费里尼的作品中(如《八又二分之一》)却可以感受到,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无从判断费里尼作品剧情的发展,因为他的作品是碎片化的、非线性的,这种观影过程中的无从判断性也就是无从辨认故事发展的轨迹,故无法朝向未来(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是“朝向墓穴”)。德勒兹认为费里尼作品所拥有的超现实形式尽管描述的是“沉沦的严酷过程”,但“必然伴随该过程的清新与创新的可能性”。[2]493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晶体的形式理解成具有先锋特色作品的时间-影像样式。
如果说德勒兹的晶体时间-影像就是如此这般的话,我们就要怀疑德勒兹是否改弦易辙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德勒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强调说,对于晶体的讨论只不过是对于时间-影像第一种样态的“描绘”,这种描绘是需要进一步“调整”的。他说:“我们指称‘晶体’者是一种专为客体而存在的描绘,它会取代客体、创造客体并同时如霍格里耶说的擦拭掉客体,不断地移让给下一个具冲突性的描绘,它转移并调整之前的描绘。”[2]547这样一种对之前影像描述的调整和校正,就是德勒兹的第二种时间-影像样态。
第二种时间-影像样态对晶体描述中实际与潜在影像两两相对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将时间朝向未来和过去的两分岔调整为三分岔:“未来的当刻、现在的当刻和过去的当刻。”[2]512不要认为这样的修正是为了强调“现在”,恰恰相反,这是为了强调“过去”,“未来”的概念被“作为普遍先行存在的过去”给取代,“现在”成为了“无限收缩过去的当刻”,而“过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两者之间的“所有廻圈”。[2]510这样一种理论上修正的目的显而易见,在一个无限膨胀的过去时态中,没有主体的位置,因为主体必然是一个现在的主体,根据他者确认自身的主体,在一片茫茫然的过去之中,主体只能趋于消失。德勒兹借用柏格森的话说:“记忆并不存于我身,而是我们在一种存在-记忆、世界-记忆中游动。”[2]510德勒兹终于再一次无情地转过身去。
晶体的基础理论被修正之后,相关的其他细节也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有关回忆-影像的性质。在晶体的描述中,可以说回忆-影像直接承担了潜在影像的功能,因为它在影片中的出现直接造就了观众心目中的潜在记忆,[2]486但是现在德勒兹开始否认这一点了,他以《公民凯恩》为例说:“调查员以个案探访的方式进行调查,每一个见证者都足以作为肯一生的某个切面、潜在过去的某个廻圈或时层、某种连续体。……的确,就是通过这些时层,这些见证人才得以召唤回忆-影像、组成古老当刻;但它们终究跟将之实际化的回忆-影像有所差别,纯粹过去并不能等同于它曾是的古老当刻。”德勒兹在此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纯粹过去”,以区别于以前所使用的“过去”。两者的区别在于一个不能被实际化,而另一个能够,能够成为影像中的“古老当刻”。德勒兹说“过去”只不过是一种回忆,而“纯粹过去”则“不完全是回忆,而是‘一种回忆的邀约’”。[2]522两者区别的关键在于,前者是一个回忆者的回忆,而后者,主体消失在回忆温馨的邀约之中。为了理论上的一致,德勒兹将回忆分成了两个不同的端点:一端是影像的实际化,与晶体的描绘保持基本的一致,德勒兹称其为“压缩”,是一种将回忆压缩成实际的“共存在的时层或区域”;[2]522另一端则与当刻无关,是一种在回忆之中的“天问”,如《公民凯恩》中的对于“玫瑰花蕾”的追问。德勒兹说:“我们很清楚回忆-影像自身在此并无多大意义,但它却提示了两个足以超越它的事物:一为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回忆-影像的纯粹过去的时层变幻,另一则为不断重新追忆的当刻实际的压缩。”[2]52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时间-影像的第二样态实际上是第一样态中未充分表达的晶体差异的另一端,指向虚拟和非现实范畴的一端。
时间-影像的第三种样态与晶体没有关系,而是换了一个全新的“晶体叙事”的角度关照那些在晶体相关讨论中没有被提到的影片类型。按照德勒兹的说法:“前两种时间-影像涉及的是时序,换言之,连系的共存或时间内的元素的同步性。第三种则是时间系列,将之前与之后整合在流变之中,不再将它们分开:它的吊诡之处就是引入时刻中延续的区间。”[2]578其实在我看来,德勒兹在有关时间-影像研究的一开始便声称时间-影像来自于一种平淡无奇日常生活的纯声光情境,而在有关晶体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豪门历史(实际与潜在)便是强烈戏剧性(清晰与不透明)和超现实表现(种子和地点),似乎与时间-影像概念建立的初衷相去甚远,以致不得不借用某一种理论将那些游离在晶体之外的影片聚拢过来。由此,我们看到了在这一部分不但有有关新浪潮、新德国电影、新好莱坞电影、苏联电影的讨论,甚至还有关于纪录片和日本电影的讨论。这些影片共同的特点是在叙事上拥有“非历时性的时间性时间,它制造出必要‘不正常’的运动、根本‘造假’的运动”。[2]551“叙事不再是一种同(感官机能)真实描绘相串联的忠实叙事,而是描绘完全成为它自己的客体,而叙事变成是暂时且伪造的。”[2]553这里所提到的描绘“成为它自己的客体”,是说主客的浑然一体,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主体匿身不见,影像变得虚幻。
德勒兹在时间-影像的三种不同样态中表述了他对于时间-影像的想象,这一想象将某些类型的影像置于了浩瀚时空的虚实之间,与一般所谓的影像,也与他的运动-影像拉开了距离。
“时间-影像”的边缘
在德勒兹有关时间-影像的论述中,边缘的形态是放在典型形态前面论述的,所谓从边缘到中心。由于德勒兹电影理论对一般人来说有理解的困难,如果不对其核心的观念有所知晓,是不容易把边缘形态区分清楚的,因为边缘本身便具有似是而非的两可形态,所以,我们把对于边缘形态的讨论放在了最后。德勒兹把处于时间-影像边缘地带的影像分成了三种:回忆-影像、梦境-影像、世界-影像。[2]467
我们先来看回忆-影像。由于回忆牵涉到时间,德勒兹首先区分了回忆的两种不同形态,一种是感官机能的确认,另一种是关注性的确认。后者属于纯视效(音效)影像,因而与直接时间相关。正是由于回忆-影像的这种双向确认的可能性,因此其究竟属于哪一种影像形式需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仅从其自身的形式无法对其属性进行判定。一般来说,回忆-影像会涉及一段闪回或者倒叙,而闪回和倒叙并不必然地与潜在影像的循环联系在一起,因此,“回忆-影像并不属于潜在影像,它只是为其所需而去实现某种潜在性(即柏格森称为‘纯粹回忆’者)。因此回忆-影像并不能提供过去,它仅能再现的并非‘曾经存在’的过去,而是一个古老的当刻;回忆-影像是一个被现实化的影像或说正值实现的影像而没有同实际影像或当刻影像形成某个不可区辨彼此的廻圈”。[2]445但是,德勒兹又从理论上论证了回忆-影像与感知机能确认的不同,他说:“因为回忆-影像,而出现了一种主体性的新意义……因此主体性具有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意义,它不再是机能性或物质性的,而是时间性与精神性的:即‘附加’于物质上者,而不再是将物质变得蓬松者;属于回忆-影像而不再是运动-影像。”[2]437从内容上看,以上援引的两段文字是彼此矛盾的,前者认为回忆-影像并不属于潜在影像,因此也就不能进入循环构成时间-影像;而后者则明确宣告其不再属于运动-影像。因此,在我们的理解中,既不属于时间-影像亦不属于运动-影像的,只能是一种中间形态,——或者说,它能够同时属于两者。这也是德勒兹在后面有关晶体的讨论中以《公民凯恩》为例所说的,回忆-影像在大部分情况下作为实际的影像(运动-影像)出现,但是也能够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成为时间-影像,其条件是回忆不再属于某个主体,而是回忆成为“邀约”。
梦境-影像与回忆-影像的情况相类似,也是一种骑墙的中间状态。不过所牵涉的对象有所不同,我们看到德勒兹所举的一些例子涉及许多先锋派电影作品,如著名的《幕间休息》、《一条安达鲁狗》等。应该说直接时间的呈现在这些影片中是最清晰不过了,因此德勒兹会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它们的时间性‘敞视’、一种流光回忆的不稳定整体、一些令人晕眩快速通过的普遍过去的影像,仿佛时间征服了一种更为深刻的自由”。[2]447不过,德勒兹讨论的对象并非都是先锋电影,在一般影片中,梦境的机制显然无法与潜在影像联系起来。因为本体并非处于一种清醒的意识状态,因此德勒兹会说:“潜在影像的现实化并非直接发生在原影像上,而是在另一影像中现实化,该另一影像亦扮演同样角色现实化于第三个影像,直到无限。”[2]448我们看到,时间-影像循环的基础在这一情境下被改变了,它“又回到了运动;可是已经不是对情境作出反应的人物,而是一种世界化的运动取代了人物的失败运动。因此出现了一种世界化或说‘网络化’、去人称化、失落与受阻运动的代词化。”[2]451如同回忆-影像一样,德勒兹在这里完成的也是一个从面对到背对的旋转,现实世界在这里变形虚化,成为了另一个世界。德勒兹指出:梦境-影像“跟回忆-影像一样无法保证真实与想象物之间的不可区辨性”。[2]450不可区辨性不能得到保证,即是说时间-影像并非一定能够出现,这也就是说,梦境-影像是否能够作为时间-影像还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如果说梦境-影像在另一个不同于一般世界的基础之上达到了时间-影像要求的实存与潜在的循环,那么它还不能算是最典型的,因为它仅呈现在为数不多的先锋派电影之中。德勒兹认为最为典型的影片类型是音乐歌舞片,那里是整体化的另一个世界,德勒兹称其为世界-影像。前面我们提到过,德勒兹的电影理论是在差异哲学和纪实美学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结合这一点,我们便能够轻而易举地理解何为世界-影像。我们可以看到,德勒兹的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所针对的基本上是纪实美学影响下的电影,但一般所谓的先锋电影、音乐歌舞片、喜剧片、魔幻片等不属于纪实美学的范畴,前面已经提到,喜剧片的主要部分已经通过主题与一般纪实化影片的“同一性”被纳入了动作-影像,其他的以及纪实美学所不能涵盖的各种影像样式将在另一个理论系统中被收纳,这就是世界-影像。世界-影像的运动是一种非现实化的运动,德勒兹将其比喻为动画片,人物的运动与背景的运动脱节,两不相干。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另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将主体不再能够或者根本不能进行的运动揽在身上”。德勒兹认为,这就是“潜在运动,唯有产生整个空间扩张或时间延展时才得以现实化的潜在运动,也是最大廻圈的限制所在”。[2]451相对于音乐歌舞片来说,是舞者改变了现实的世界,“重要的是舞者个体创造力(即主体性)从一种个人模态跨越到超-个人的元素,再臻至舞者即将穿越的世界运动”。[2]453非现实的运动被作为了潜在的因素。不过,不能因此而认为所有的音乐歌舞片都属于时间-影像,德勒兹指出,“我们拥有两种呈现事物的方法,一种认为歌舞片所提供的是最为普通的感官机能影像”,而另一种则属于“已然失去机能延伸的纯声光情境”,[2]454也就是从根本上便失去了与感官机能的联系。只有后者才是所谓的时间-影像。
有必要指出的是,德勒兹在使用回忆-影像、梦境-影像以及世界-影像这些概念时,并没有将其等同于先锋电影、喜剧电影、音乐歌舞电影、魔幻电影以及其他的现实主义影像类型,而是将这些影片中与时间-影像相关的部分标示出来,这特别是在有关梦境-影像和世界-影像的讨论中。德勒兹之所以在他的论述中使用了大量篇幅讨论这些影像成为时间-影像的可能,是因为大部分的类型化商业制作影像都具有强烈的视听效果,属于德勒兹所谓的“感官机能情境”,难以进入时间-影像的范畴,因此必须作出充分的论证。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类型化商业电影都能够成为时间-影像。同时,即便是这类影像中具有直接时间的因素,也与典型的、晶体化的时间-影像有所不同,这可以从德勒兹将其称为“最大廻圈”看出,而晶体化的时间-影像则是“最小廻圈”。
通过对德勒兹影像分类理论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影像基本上是以空间作为原则来区分的,而时间-影像则是以直接时间作为原则来区分的。空间和时间都是哲学上高度抽象的命题,一般来说很难用这些“软绵绵”的概念来切割“坚硬”的现实影像。德勒兹的做法是将电影纪实美学作为“固化剂”,使之与抽象概念混合,这样便能够防止抽象概念的泛滥,将不同类型影像的范围囿于一定的范围之中。因此,我们对于类型之间关系的分辨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哲学与电影美学之间的来回奔忙,文章中经常提到的“面对”和“背对”影像,便是这一瞻前顾后的比喻。希望这样一种解读的方式能够更为趋近德勒兹的本意,并给对德勒兹电影理论感兴趣的同仁带来新鲜的感受。
[1] [法]吉尔·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M].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
[2] [法]吉尔·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M].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3.
[3] [法]亨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64.
[4] [法]吉尔·德勒兹,菲利克斯·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379.
[5] [法]吉尔·德勒兹.哲学的客体:德勒兹读本[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6] 麦永雄.德勒兹差异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举隅[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5):50-56.
[7] 景君学,黎志强.差异与游牧:乌托邦的微型学[J].社会科学研究,2011(3):117-122.
[8] [法]让-皮埃尔·乌达尔.电影与缝合[M]//鲁显生,译.张红军.电影与新方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59-273.
[9] 聂欣如.电影的语言[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204-213.
[10] [意]皮·保·帕索里尼.诗的电影[M]//桑重,姜洪涛,译.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465-487.
[11] [瑞士]菲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 张留华.皮尔士哲学的逻辑面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164.
[13] [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4] 涂纪亮.皮尔斯文选[M].涂纪亮,周兆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5] [法]亨利·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魏 琼)
Looking around Images—An Interpretation of Gilles Deleuze’s Image Classification Theory
NIE Xin-ru
(SchoolofJournalism&Communi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241,China)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Deleuze’s film classification theory is to comprehend his philosophy of differentiation. In the light of this philosophy, Deleuze classifies film images into two categories: motion images and time images. As the two set of images are placed in differentiated thinking, images appear to be realistic and objective on one hand, and potential and subjective on the other. Rightly in the sense of attending to the two conflicting sides Deleuze develops his unique film image classific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which images are basically classifi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ime and space. Nevertheless, the highly abstract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s are hard to be integrated into real-life film images, not to say conduct effect “management”. It is evident that Deleuze establishes his own film theory system by taking account of documentary aesthetics while 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images. In view of this, the relations of classification is in some sense the relation between documentary 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 and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two is the result of subtle coordination between observation (or interpretive description) and philosophical thinking.
film theory; images; Deleuze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1.005
2014-09-01
聂欣如(1953- ),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J912
A
1007-6522(2015)01-007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