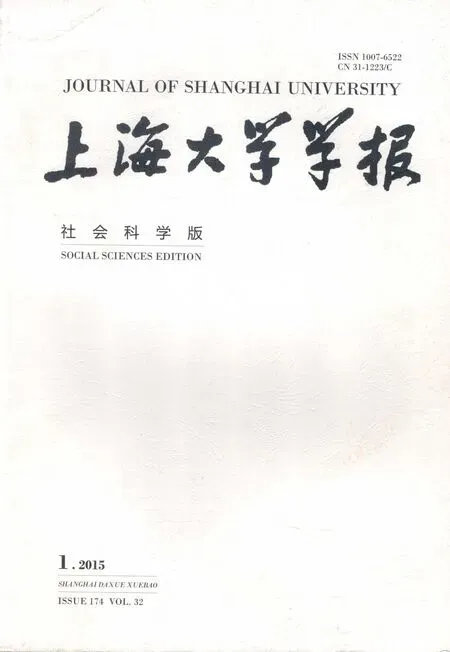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
周 剑 之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论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
周 剑 之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意境说”并不能包容诗歌的所有特质,在面对古典诗歌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传统时,我们应拥有与“意境说”不同的阐释工具。经由明清诗学的酝酿,尤其是翁方纲、方东树等人的运用,“事境说”逐渐得以凸显。“事境说”反映着古典诗学中的一条重要思路,即对“事”这一要素的重视和思考,是古典诗学对“事”的正面应对。以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为基础,进而建构“事境说”的现代学术体系,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事境;意境;诗境
中国古典诗学中有许多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一些概念术语,在经过现代学理阐释之后,可能被激发出鲜活的生命力,“意境”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历经古典诗学的长期酝酿,又经由王国维、朱光潜、宗白华及众多学者的现代建构,“意境”遂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概念。不过,对越是看上去深刻的认识,我们越是应当有一种警醒:在这深刻的背后,是否存在被遮蔽的事物?拿古典诗歌研究来说,“意境”一词被无限制地复制,被用于各种场合——无论恰当与否,这种现象本身都足以使我们反思:我们是否过度依赖“意境说”?是否把古典诗歌的发展脉络、古典诗学的丰富内涵简单化了?①不少学者已对“意境说”进行反思,如陶文鹏《意象与意境关系之我见》(《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论文,皆有高见。然而在短时间内,仍难以扭转整个局面。
已有学者指出,“意境”并非“中国古代诗学的核心范畴”②对于这一点,蒋寅《原始与会通——“意境”概念的古与今》、罗钢《学说的神话——评“中国古代意境说”》(《文史哲》2012年第1期)、《意境说是德国美学的中国变体》(《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等论文中有详细精彩的论述。。在古典诗学中,它远没有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重要,“意境”实为诗境之一种,既无法覆盖所有的诗歌类型,也难以包容诗歌的所有特质。即便是经由现代阐释的“意境”概念,仍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原因是,在20世纪学界的论述中,“意境”几乎始终与“抒情传统”绑在一起。关于“意境”的各种定义,大都离不开对诗歌抒情的本质认定①如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认为“意境”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是“情”与“景”的结晶品。李泽厚《意境杂谈》认为:“意境”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统一。”袁行霈《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也说“意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在具体操作中,往往把重点放在“情”上,重点讨论对“情”的抒发、或对“主观情意”的表达。。对抒情传统、对“意境”的强大认同,使得古典诗歌的其他许多特质在无意间被遮蔽了,尤其有代表性的,是注重记录情境、记述事实、忠实呈现外在世界的这一脉络②张晖《中国“诗史”传统》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传统诗学中强调作品对于外部世界忠实的模仿很有可能突破抒情传统。”(《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70页):《诗经》中的赋法,汉乐府的“缘事而发”,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史”的“善陈时事”,以至宋诗中对纪事的追求③参见拙文《宋诗纪事的发达与宋代诗学的叙事性转向》(《文学遗产》2012年第5期),清诗中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呈现等④参见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发表于“越界与融合:清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南京大学与《文学遗产》编辑部合办,2014年8月)。。这些内容,在围绕“意境”建构起来的诗学体系中,是失位的。而这样一条时间悠久且影响深远的脉络,如若忽视,将是古典诗学的重大缺失。
为了纠正这片面的深刻,我们要朝两方面努力。一方面,让“意境”走下神坛,还原为诗境的一种类型;另一方面,则应进一步探求诗境的其他类型,寻找堪与“意境”并行,且符合古代诗歌传统的有效阐释方式。前者破,后者立。前者目前已有一些成果;而后者,仍需要艰难的摸索。
当我们从“意境”中跳脱出来,重新审视古典诗歌与诗学,关注记录情境、记述事实、忠实呈现外在世界的这一脉络时,“事境”一词走入了我们的视野。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有这样一条论述:
凡诗写事境宜近,写意境宜远。近则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1]504
把“事境”与“意境”并提,并对二者的特点作了简明而精到的叙述。“事境”“意境”的具体含义,方东树语焉不详。但二者并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当我们考察与“意境”相区别、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诗歌传统时,我们能否以“事境”为基点,来构筑一条新的诗学阐释的路径?
一、“事境”的历史渊源
从古典诗学中借鉴资源,固然是一条颇为理想的路径。但如何从丰富的古典资源中选择适用的概念、对其发展演变进行合乎实际的梳理,并进行现代学理的合理转化、使之真正能为当下所用,则又是非常不易解决的问题。比较理想的情况,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吸纳一些关键的、已在历代学人手中经过一定积累、并且具备应用潜力的语词和概念。“事境”一词就是如此。“事境”之说,绝非无源之水,而已有了时间与学理的积淀。
“境”在古代诗论中颇为常见。唐代即有王昌龄《诗格》中的“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诗学中的“境”固然有着中国自有的含义,但在发展中也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①萧驰《佛法与诗境》(中华书局2005年版)对此有系统论述。。“事”“境”连用,唐以来的佛家典籍已频繁出现,但往往是两个词而非一个完整的概念,如《五灯会元》载西余拱辰禅师语:“理因事有,心逐境生,事境俱忘,千山万水。”[2]不过,佛家的“境”有着专门的含义,与诗学多无直接关涉,可暂不列入考察范围。
就目前所见材料看来,宋人已用“事境”来表示身处的境遇和状况。如许景衡《与吕守》中所言:“京居久客,事境纷乱,讫贻不早之愧,尚倚神明有以谅之耳。”[3]卷十六叙述自己客居京城、诸事纷繁的处境,这是未能及时拜访吕守的原因。许景衡又有《祭刘元修文》,中有:“事境纷然,错节盘根。至于元修,一扫剧烦。”[3]卷十八意谓刘元修善于处事,能将繁杂事务处理得当。两处“事境”意思相似。相比于具体的“事情”或“事件”,“事境”显得更为复杂,往往含有“境况”和“遭遇”的意思。这种用法在后世也颇为常见,如:
若土风人情,随叩随识,洒然有当于心,即历历若在事境。(祝以豳《代贺观察大夫讷庵苏公寿序·代作》[4])
人生少壮而老,事境参差百出,转相纠缠。其得从容无为、委身于问学者,常无几时。(方苞《与徐贻孙书》[5])
世尽人子,谁不悲慕其亲者。及寒暑改节,事境移情,截然如两世人者有之。(李世熊《伍君某甫六十寿序》[6])
先生举于乡,而文弨亦以是年举顺天乡试,为同岁生,情亲矣,而事境龃龉,亦不获常会聚。(卢文弨《陈祇园先生家传》[7])
在这类用法中,“事境”往往包含“境遇”、“境况”之意,是人所处的各种具体情状、各类事项的总和。
在使用中,“事境”偏重于客观的实际存在,而与偏重主观的心、理等相区别。如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里仁篇》:“事境分明,入目不乱,亦可谓之审。心境泰定,顺物无逆,亦可谓之安。”[8]又如明代袁黄《游艺塾文规》:“遇理境则忘理以观妙也,涉事境则因事以冥心也。”[9]70“王家植云:‘吾人纷驰于事境,未若自有之灵明。灵明启而事境融,人品学术称纯备焉。’”[9]311“灵明”指个人之心智,“事境”则是具体的、纷繁的事件情境,与“灵明”相对应。《说文解字句读》在解释“忼慨:壮士不得志于心,情愤恚也”一句时说:“不得志者,事境也;于心者,心境也;愤恚者,忼慨之未发者也。”[10]“不得志”属于具体的事实,心有所感,方属心境。由此可见,“事境”在使用过程中,侧重于客观具体的事实情状。
值得注意的是,“事境”一词还常常应用于与学术,尤其是与儒学相关的著述中。明葛寅亮《四书湖南讲》在讲解《孟子》中的一段时,有这样的表述:
季子不将“吾敬”二字体认,于外边事境上执着,故孟子亦只得在事境上剖析,未免多费葛藤。[11]
《孟子·告子上》有云,孟季子问公都子:“何以谓义内也?”公都子回答:“行吾敬,故谓之内也。”孟季子却进一步追问:“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酌则谁先”?公都子不能答,只好请教孟子。孟子据此有“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的回答。由此可知,葛寅亮所谓的“事境”,即孟季子给出的“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酌则谁先”这样具体的事件情境。清代孙奇逢《四书近指》对《孟子》的这一段时,同样用到了“事境”一词:
就事境上看,不独冬日夏日,汤水在外,即饮亦在外,然因冬饮汤,因夏饮水,自然裁制合宜处,皆由中出,义岂不在内?[12]
《孟子》中,公都子在听了孟子的回答之后,又对孟季子说过这样的话:“冬日则饮汤,夏日则饮水,然则饮食亦在外也?”孙奇逢的解释即是对此而发。可见,孙奇逢的“事境”具体指的是饮汤饮水之事。葛寅亮与孙奇逢的“事境”具体所指虽有不同,但都是针对某种事件情境而言。在具体“事境”中体悟道理、利用具体“事境”来进行学术的分析和阐释,使得“事境”一词具有了学理上的意义。
既然“事境”一词可用于儒学等学术方面的阐释,那么应用于诗学也就顺理成章。将“事境”直接用于诗学,比较早并且比较典型的,是明代张鼐。在《题孙叔倩百花屿稿叙》一文中,张鼐提到了“事境”对于诗人的意义:
苏长公喜和渊明诗,其弟子由称其精深华妙,直与渊明比。今读其和篇,只坡老本色语耳,非不能肖,政不必肖也。秦汉间歌谣不必尽合三百篇,曹刘鲍谢不必尽合秦汉歌谣也。少陵而下,抑可知已。古之人得于中,而口不能喻,乃借事境以达之。其达之也,与委巷妇女同其口,而不必与古作者同其解。乃后人读之者,悠然穆然,其旦暮遇之也。所谓不能肖,亦不必肖,政肖其人耳。[13]
在这篇文章中,张鼐的主要观点是,每一时代之诗、每一诗人之诗,都有自己的面貌。后人之诗不必与古人尽同。秦汉歌谣不必与《诗经》同,鲍照、谢灵运也不必与秦汉歌谣同。关键在于,将“得于中”的内容“借事境以达之”,使后来读者能够感同身受,有“旦暮遇之”之感。因此苏轼《和陶诗》仍是苏轼本色,“非不能肖,政不必肖也”。基于这样的观念,张鼐继而认为,孙叔倩之诗虽有杜甫之风调,但仍是“叔倩所自得者”。“夫人各有本,各自肖焉。”因此“少陵自肖少陵,叔倩亦宁不自肖叔倩哉?”[13]从而肯定孙叔倩诗歌的成就。
从张鼐的叙述脉络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认识:一、古人借“事境”来传达心内之所得;二、每个诗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事境”,通过“事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不必与前人相同;三、后人读到这些包含独特“事境”的作品时,会产生“悠然穆然”、“旦暮遇之”的感受,由此可见,“事境”对读者具有切实的感染力。
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张鼐才会最后得出“夫人各有本,各自肖焉”的结论。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对诗人个性化体验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与张鼐对于“事境”的体认是相关联的。尽管“事境”在这篇文章中并非论述的核心,却是张鼐理论建构的基石。
“事境”作为一个概念,至此已进入诗学范畴。
二、清代诗学中“事境说”
“事境”得到相对系统的应用、真正可视为一“说”,是在翁方纲那里。翁方纲的诗学固然以“肌理说”最为著名,但在翁氏诗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事境”是颇为重要的关节。翁方纲多次提及“事境”,视“事境”为诗歌的要素之一,使之具备了相当丰富的诗学内涵。在对翁方纲诗学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关注到“事境”的特殊价值。如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五章《从虚到实》一节中,专设一个部分“理味与事境:唐诗的虚境以实为基础”加以讨论,认为对“事境”的强调,是翁方纲从“实”的角度来认识诗歌本质的结果[14]。叶倬玮则在《翁方纲诗学研究》中指出,翁氏重视“事境”,“认为这是诗人自成一格的必要条件”。[15]这些研究多以翁方纲诗学整体为研究对象,在这一大框架下观照“事境”。本文则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事境”为核心进行再度梳理,考察翁方纲对“事境”的认识及其理论建树。
翁方纲的“事境”有着比较明晰的内涵。尽管翁氏并未专门对“事境”一词进行解释,但他使用“事境”的语境基本相似,“事境”的意义也基本一致。翁氏所谓的“事境”,其实是诗人身处的具体时空。“事境”的重要特点,是具体性和独特性。它是每个诗人在写作每一首诗的当下所面对的那一特定时空、特定境遇的总和,因此既是具体的,又是独一无二的。诗歌应写出这样一种独一无二,不可移为他人,不可移至他时、他地。
翁方纲认为,“事境”是诗歌达成“温柔敦厚”、诗之所以为诗的必要条件之一。《石洲诗话》卷八云:
若以诗论,则诗教温柔敦厚之旨,自必以理味事境为节制。即使以神兴空旷为至,亦必于实际出之也。风人最初为送别之祖,其曰“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必衷之以“其心塞渊”、“淑慎其身”也。《雅》什至《东山》,曰“零雨其濛”、“我心西悲”,亦必实之以“鹳鸣于垤”、“有敦瓜苦”也。况至唐右丞、少陵,事境益实,理味益至。后有作者,岂得复空举弦外之音,以为高挹群言者乎?[16]
翁方纲在探寻诗之本质的过程中,对于神韵说有深刻的反思。他发现以空寂谈神韵,容易陷入空言,“神韵说”需要“以肌理之说实之”(《神韵论上》)。在他看来,就本质来说,诗应当是“实”的;即便神兴空旷,也“必于实际出之”,自《诗经》以来就是如此。“温柔敦厚”的达成,需要有“理味”、有“事境”。“理味”即“肌理说”所看重的“理”,“事境”则是具体的情境。故又列举《邶风·燕燕》、《豳风·东山》为例,前一例用于说明诗歌应衷之以理味,后一例说明诗歌当实之以事境。并认为后来名家如王维、杜甫,无不如此。如此一来,在翁氏诗学体系中,“事境”就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
《延晖阁集序》同样体现了翁氏对“事境”的重视:
泥于言法者,或为绳墨所窘;矜言才藻者,或外绳墨而驰。是皆不知文词与事境合而一之者也。”[17]52
空谈诗“法”的人,最后不过困窘于规矩,而追求词采的人,则又失了规矩。其实“事境”与“文词”是统一的,从具体“事境”中孕育而出的诗歌,才能有自己的面貌。如果只懂得模拟前人,就会成为“为诗文徒袭格调,而不得其真际者”(《延晖阁集序》)。看重“真际”、反对袭仿,有“事境”,才能有所谓的“真”诗。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切事境”就成为诗歌的一大弊端。《神韵论下》:
渔洋之诗……如《咏焦山鼎》,只知铺陈钟鼎款识之料;如《咏汉碑》,只知叙说汉末事,此皆习作套语。所以事境偶有未能深切者,则未知铺陈排比之即连城玉璞也……若赵秋谷之议渔洋,谓其不切事境,则亦何尝不中其弊乎?[17]87
这一段举出王士禛诗作的具体例子,来说明“不切事境”之弊。翁氏认为,钟鼎款识之料、汉末故事,都不过是“习作套语”,其实未能“深切”“事境”,这正是王士禛诗的弊端所在,也是赵执信(秋谷)所批评的。就现存材料来看,赵执信似未直接说过王士禛“不切事境”。但从倾向上看,赵执信主张“诗之中须有人在”,认为王士禛“诗中无人”、所写诗歌不能符合自己所处的现实情况①赵执信《谈龙录》:“司寇(即王士禛)昔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讲学士,奉使祭告南海,著《南海集》。其首章《留别相送诸子》……云:‘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不识谪宦迁客,更作何语!其次章《与友夜话》云:‘寒宵共杯酒,一笑失穷途。’穷途定何许?非所谓诗中无人者耶?”参见赵蔚芝《赵执信和王渔洋在诗学上的分歧》,《文史哲》1982年第5期。,其实也就是“不切事境”的表现。
切于“事境”,具体来说,就是要“切人、切时、切地”。《神韵论中》就提到:
诗必能切己、切时、切事、一一具有实地,而后渐能几于化也。未有不有诸己、不充实诸己而遽议神化者也。[17]86
诗歌必须“实”,需要“切己切时切事”,否则不可能达到化境。在《苏斋笔记》中,翁氏同样以王士禛诗为例,对这一点还有更为细致的解释:
渔洋集有《冒辟疆水绘园修禊》十首,众所称也。一日有友读此诗,议其不工。予闻而竦然,意此友必知诗者。及叩其所以不工,则曰:“此题须切,如皋冒氏之不可与他处景事相似,乃工耳。”予笑曰:“君误矣。渔洋篇篇皆然,何尝有某一诗切其人其地,而独议此为不工耶?”盖渔洋通集之诗皆若摹范唐人题境为之者耳,如赵秋谷所举即其类也。[18]8726
翁方纲在看来,不切其人其地、不切事境,是王士禛诗作的通病。比起“工”来,“切”更为重要[15]113。若不能“切”,就只是对前人的单纯模仿,即便能做到工,却缺少了诗的内核。因此翁方纲在归结王士禛诗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其失何也?曰:不切也。诗必切人、切时、切地,然后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渔洋之诗所以未能餍惬于人心者,实在于此。[18]8725
“性情出焉”、“事境合焉”,是作诗的基本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切人、切时、切地”,也就是要充分凸显每一事境的独特性,由此凸显每一诗的独特性。
综合来看,翁方纲对“事境说”的贡献至少有这样几点:一是基本明确了“事境”的内涵;二是在诗学建构中赋予“事境”极其重要的地位;三是提出了切于“事境”的具体方法。可以说,“事境”说在翁方纲手里有了基本轮廓。
比翁方纲稍晚的方东树,是又一位对“事境说”有重要贡献的论者。他对“事境”的直接论述虽不多,却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即本文开头所引的几句:“凡诗写事境宜近,写意境宜远。近则亲切不泛,远则想味不尽。”在方东树看来,诗歌中存在着“事境”与“意境”两种类型的“境”。它们具有不同的审美旨趣,前者要“亲切不泛”,后者要“想味不尽”。因而在营造这两种“境”时,前者宜“近”,要具体而仔细地叙写、摹画,让人看得清、看得真;后者宜“远”,要拉开距离,让人去联想、去体悟。我们可以看方东树对谢灵运《七里濑》的分析:
中间以“遭物”二句,由上事境引入,横锁为章法,以逼出己情。[1]155
《七里濑》诗云:
羁心积秋晨,晨积展游眺。孤客伤逝湍,徒旅苦奔峭。石浅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首四句叙写“孤客”途径七里濑。接下来的四句,是对景物的细致描画。再往下即方东树所谓“遭物”二句。按方东树分析,此诗“遭物”两句以前,有“事境”。这一“事境”,其实正是谢灵运当时境遇的整体,既包含了前往外地赴任、旅途孤苦的境遇,也包含了行旅间所见所闻所感。其中对山石、水流、落日、荒林的描画,极其细腻。从谢灵运此诗可以看出,“事境”的呈现,确实是具体的、亲切的。由这一事境“逼出己情”,则是“遭物”两句之后的重点。由“遭物”引发概叹,抒写内心。末四句从眼前的严子濑,联系严子陵与任公子的典故,引出自己的志趣。方氏评云:“后半心目中借一严陵,与己作指点比照。兴象情文涌见,栩栩然蝶也,而已化为周矣,是为神到之作。”据方氏的理论,可推断,诗的后半部分属于“意境”,能令人“想味不尽”。
方氏所论之“事境”、“意境”,对于诗歌研究来说,极有参考价值。在此论述框架下,“意境”亦不过是诗境之一种类型,“事境”恰可以与之形成对照。若再往进一步推论,那么“事境”的旨趣在于“实”,“意境”的旨趣在于“虚”。如此一来,有“实”有“虚”,虚实相生。方东树的这一归纳,概括了虚、实两种典型诗境,其实是对古典诗歌颇为全面的认识。
明清诗论家对于“事境”的开掘,其实并非偶然,而有特定的诗学背景。明清时期逐渐兴起一种诗学倾向:越来越看重诗歌的独特性、看重诗歌与诗人个人经历的密切程度。在诗歌创作领域,日常化与私域化的倾向日益突出,在诗歌中对时间、地名、事件的交代都更加明晰,今典和自注现象增多,诗集后还常附入年谱等,使诗歌带上了私人心灵史和生活史的意味①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对明清诗歌“日常化与私域化”的问题有详细论述。。与此同时,诗论家评判诗歌时,也往往强调个人经历、个人境遇对于诗歌的必要性。
如方东树评《七里濑》还引申出这样的论述:
古人作诗,自己有事,因题发兴,故脱手欲活。后人自己胸次本无诗,偶值一题,先已忙乱,没奈他何,因苦向题索故事,支给发付,敷衍成诗。其能者只了题而已,于己无涉。试掩作者名氏,则一部姓族谱中人人皆可承冒为其所作。其不能者,则并题不能了。且如此题,亦古今之恒题耳,惟此诗乃是谢公过此而作也。此时康乐若非真遭迁斥,则虽能为此二句,亦属陈言泛剩语矣。欲作诗,先须洗清面目,与天下相见,此岂寻常所及哉。[1]155
假如掩去作者姓名后,人人皆可承冒,又如何能算是“诗”。诗应当是每个人自己的诗,不能是对一个题目的刻意敷衍,也不能是对前人诗作的刻板因袭。在这一点上,方东树与翁方纲、赵执信论王士禛诗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
在这样的诗学倾向影响下,“事境说”的凸显也就不足为奇,而“事境说”之意义也昭然可揭。“事境”可以使每一首诗成为“唯一的诗”。诗人的所思所感,原本就产生于特定的语境之内。他们从某一个时空境遇的总和中获得了独特的感悟,而这独特的感悟,也试图通过在诗歌中表现这个“事境”来传达。因此,每一首诗的“事境”都是不同的。诗歌切于“事境”,有助于诗人传达在特定语境中的复杂内心。只有切于“事境”,才能使诗歌具备独一无二的价值,超越因袭模仿的层次。诗法可授,“事境”却不可授。在写作中保有独特的事境,以及在独特事境中生发的情志,才可使作者自成一家[15]150。
三、“事境说”的学术潜力与现代价值
通过对“事境说”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事境说”反映着古典诗学中的一条重要思路,即对“事”的重视和思考。“事境说”的本质,可以理解为古典诗学对“事”这一要素的正面应对。
在古典诗学中,“事”向来是诗歌的要素之一。在许多情况下,古人是将“事”与“情”并列的。旧题贾岛所撰的《二南密旨》提出的“诗有三格”,其中就包括“情格”、“意格”、“事格”。唐代《本事诗》分七个部分,其中两部分是“情感”和“事感”。叶燮《原诗》则云:“于以发为文章、形为诗赋,其道万千,余得以三语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也许“诗言志”的理念确实对古代诗学有很大影响,但从未阻遏诗人对“事”的思索。诗论家们在许多场合都显露了对“事”的热情。《本事诗·序目》虽有“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传统论调,随即又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19],由具体的事引发的诗,最是凝聚着深刻的情感,由此引发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而有必要对那些“事”有所解释和发挥。“事”的重要,可见一斑。更不用说“缘事而发”、“歌诗合为事而作”、“诗史”、“善陈时事”等诗歌史上影响颇深的提法。
对事境的强调,也并非明清才有。前人早已看到诗歌中事件情境的重要性,只是表述中未必使用“事境”的表述。钟嵘《诗品序》中曾提及引发诗歌创作的各种因素:
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这些内容,都可以说是某种类型的事境,故董乃斌先生将这段表述总结为“事感说”[20]。宋代则有“事贵详,情贵隐”的观点。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乌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况厚人伦,美教化,动天地,感鬼神乎?[21]
要实现诗歌的感人,则需要以事来承载情感。理想的做法,应当是“述事以寄情”,将情感隐含在诗中,让人“缘事以审情”,才是感人至深的好诗。魏泰虽未使用“事境”一词,但这一论断反映了古人作诗的一种倾向,即充分凸显“述事”在诗歌中的作用,将读者带入事境之中,力求使人“感会于心”。
明清时期对“事”的认识则更为深入。除了翁方纲、方东树等注重“事境”的学者,即便一些看重抒情的诗论家,也无法忽视“事”对于诗歌的重要性。王夫之主张“情景交融”,但在对诗歌的具体分析中,也有“情、景、事合成一片,无不奇丽绝世”的判断[22]902;即便是站在“情”的角度强调诗歌是“即事生情”[22]651,实际上也充分肯定了事对诗歌的触发作用。又如推重比兴的陈沆,也有“俾情与事附,则志随词显”[23]89等观点。
古人对诗中之“事”的思考成果其实相当丰富。然而近年来,抒情诗学的大行其道,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古典诗歌关于“事”的这条传统脉络。现代学术中的“抒情”、“叙事”等提法,又往往有浓厚的西学影响,假如未经仔细辨析,便用于衡量古代诗歌和诗论,容易出现许多问题。比如,从西方的叙事理念来看,中国古代诗歌叙事性并不发达。但若从古典诗学对“事”的理解来看,古人何曾忽视过“事”的意义?古代诗歌又何曾缺少叙事性?中国古典诗学不过是拥有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叙事”罢了。
在古人眼中,“叙事”不等于讲故事、说过程,而“事境”也明显不等同于“事件”。“事件”不过是一件特定的事情,有头有尾有过程。“事境”远比“事件”复杂。其所提及的“事”,指的是事实性的存在。其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宽泛,既包含“事件”,也包含非“事件”的许多其他内容。而“境”强调立体的、多层次、复合的空间。当“事”与“境”相结合,其所指涉的就是特定的事实性的时空,是诗人当下所遇、所为、所知、所感的总和。
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当我们面对古典诗歌注重纪实与叙事的这条传统时,我们应当拥有与“意境”不同的阐释工具。这套阐释工具应该是与古典诗学相契合的。与其生搬硬套一个异域的概念,抑或生造一个未必恰当的新概念,倒不如合理利用既有的概念。“意境”原本就脱胎于古典诗学资源,既然如此,同样从古典诗学中孕育而出的“事境”,理应能在现代学术视野中焕发新的生机。在此基础上回思“事境说”,可以更清楚地发现其价值所在。“事境”适合于分析这样一类诗歌,它们注重对现实境遇的呈现,能够给人以具体真实、亲切可感的印象,有利于还原诗人当时所处的整体情境,让人从具体的情境中去体会作者的所思所感。“事境”可与“意境”并行,作为诗境的两种类型,分别展示古典诗歌多方面的面貌和成就。许多无法用“意境”解释的诗歌现象,可以从“事境”的视角得到解决。
当然,将“事境”引入诗学研究,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两方面基础工作是必需的:一方面,须对古典诗学中关于“事境”的论说做系统的梳理,从中发掘“事境”的历史内涵,这正是本文努力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须从具体的作家作品出发,探寻“事境”在古典诗歌中的阐释效力。二者结合,互动互促,是为建构“事境”阐释体系的基石。
针对某些个案,笔者有过一些粗浅的思索,也曾在对宋诗的探究中初步尝试过“事境”角度的分析方式①参见拙著《宋诗叙事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这些尝试的基础上得以明确,欲建构“事境”体系,至少需要在如下几个环节做出努力:
第一,应给“事境”以恰当的定义,这是首要的一步。定义既要符合古典诗歌发展的实际,又要具备现代学理的规范性。基于对古典诗学与古典诗歌的双重考察,“事境”可初步定义为:古典诗歌所创造的一种诗境;它包含着鲜明的事的因素,是基于某一时刻、某一地点的特殊情境而产生,含括了背景、境遇、见闻、事件过程、乃至诗人的所思所感等多种内容;它强调对现实存在的各种要素的具体呈现。随着研究的深入,“事境”的定义还将进一步修正和完善。
第二,应为“事境”的运用探寻一套可践行的方法。想要援用“事境”对诗歌进行分析,必然要找到一条可反复操作、具有阐释效力的路径。“事境”作为一种诗境,是由诗人创造出来的。诗人在创造过程中需要使用相应的素材,对这些素材的选择和处理,是构成不同“事境”的关键所在。为此,我们可以引入另一个概念——“事象”,以与“事境”相配合。选择这一概念,并非对于“意象”一词的仿制,而是出自学理上的考虑。古典诗歌在表现“事”时,很少采用完整而详细的叙述,多以片段的形式出现,体现为对事的要素的提取和捕捉,并且在诗性提炼后呈现出许多“象”的形象性特点。但这类“象”与“意象”又是不同的,它们凝聚着“事”的要素,可以呈现动态的、历时的行为和现象。因此,以“事象”来指称这类诗歌表现形态,有其合理性和便利性。“事象”即是构成“事境”的关键。诗人通过对不同“事象”的选择、组合、表现,从而形成“事境”。因此,对诗歌“事境”的深入剖析,可以通过对“事象”的考察来实现。
第三,在明确定义、探寻方法之外,还应当确立以“事境”为中心的审美评价体系。对诗歌的认识和评价应当是多元的。从“意境”角度进入诗歌,可以产生以之为基础的审美评价,而从“事境”角度进入诗歌,自然也应有与之相应的审美理想和评价标准,这是不能以“意境”标准来取代的。诗人们追求的是怎样的“事境”?何种“事境”是好的“事境”?这些问题应在“事境”研究中得到相应回答。这一过程同样需要引入一些相关概念。“事境”在古代诗学中并不是孤立的,它牵连着一系列范畴和术语。比如宋诗中强调的“实”,又比如翁方纲反复提及的“切”。若能以“事境”为核心,充分开掘古典诗学中一些颇为常见,却未曾被理论化的术语,建构一套以“事境”为中心的评价体系,就可为认识古代诗歌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定义、方法、评价,若能将这几方面问题通贯处理,当可获得“事境”的现代再生。
诚然,以古典诗学中的“事境说”为基础,进而实现“事境说”的现代学术建构,这并非一项轻松的工作,恐怕也无法在短期内完成。然而“事境说”所拥有的学术潜力,定会为古典诗歌研究带来良性的影响;对于打破“意境”过度使用的局面、重理古典诗歌纪实叙事的发展脉络,也必能有所贡献。
(本文撰写深受张剑先生启发,谨致谢忱。)
[1] 方东树.昭昧詹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 普济.五灯会元[M].北京:中华书局,1984:754.
[3] 许景衡.横塘集[M].北京图书馆藏清乾隆翰林院抄本.
[4] 祝以豳.诒美堂集:卷十一[M].北京图书馆藏明天启刻本.
[5] 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76.
[6] 李世熊.寒支集:二集卷二[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初檀河精舍刻本.
[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395.
[8]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237.
[9] 袁黄.游艺塾文规[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10] 王筠.说文解字句读[M].北京:中华书局,1988:401.
[11] 葛寅亮.四书湖南讲·孟子湖南讲:卷三[M].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
[12] 孙奇逢.四书近指[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805.
[13] 张鼐.宝日堂初集:卷十二[M].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二年刻本.
[14] 张健.清代诗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5] 叶倬玮.翁方纲诗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16] 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41-242.
[17]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8] 翁方纲.苏斋笔记[M]//复初斋文集手稿影印本.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19] 孟棨.本事诗[M]//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2.
[20] 董乃斌.古典诗词研究的叙事视角[J].文学评论,2010(1):25-32.
[21] 魏泰.临汉隐居诗话[M]//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1:322.
[22] 王夫之.唐诗评选[M]//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9.
[23] 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89.
(责任编辑:梁临川)
On “Circumstance-oriented Theory” in Classical Poetics
ZHOU Jian-zh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Poetic imagery theory” can by no means account for all features in poetr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when the tradition of on-the-spot recording and narration is emphasized in classical poetry, thus calling for a different interpretive tool. “Circumstance-oriented theory” gained gradual prominence after the brewing of poetic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specially after the employment by figures like Weng Fang-gang and Fang Dong-shu. “Circumstance-oriented theory” reflects an important train of thought in classical poetics which highlights and reflects on “circumstance”, and address “circumstance” head on. Therefore, it is worthwhile to construct contemporary academic system of “circumstance-oriented theory” based on its development in classical poetics.
circumstance; poetic imagery; poetic context
10.3969/j.issn 1007-6522.2015.01.007
2014-10-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青年项目(13YJC751084)
周剑之(1984- ),女,广西桂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唐宋文学。
I206
A
1007-6522(2015)01-0103-11
——翁方纲定武《兰亭》的收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