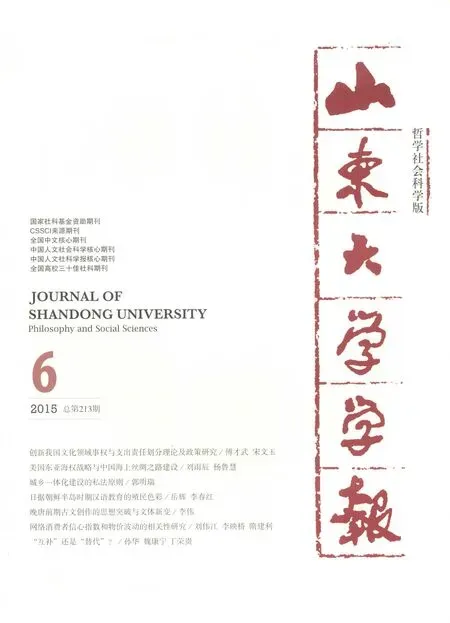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与审美生成
网络艺术的传播途径和审美方式有别于传统艺术,它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观看主体的观看方式,打破了传统艺术中二元对立的审美价值观。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界限消失,形成了新的审美方式。网络艺术不断撕裂二者之间的裂隙,造成一个虚空的地带,使一切艺术陷入不确定的虚拟世界。因此,如何正确看待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网络艺术;观看方式;观看主体;观看对象;审美生成
信息科技的发展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它借助互联网为观看主体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形态——网络艺术。互联网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介被广泛运用到网络艺术,其价值和意义也随之被推到风口浪尖。正如本雅明所说:“照相机与电影的怪异之处在于,它们消解了存在于人类与机械之间的疆界。”①瓦尔特·本雅明:《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胡适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6页。信息科技的出现,消解了人与机器的二元对立,使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变革成为可能,并推动了新的审美生成。
网络艺术只能通过互联网来体验艺术作品,具体有网络装置艺术、网络动漫艺术、网络数字诗歌艺术等类型。在互联网这个特有的平台,网络艺术的形成是经过数字化处理、再以超文本②参见范尼瓦·布什:《如我们所想(As We May Think)》,《大西洋月刊》1945年7月。(Hpertext)的形式显现艺术作品,分两类:一类是传统艺术迁移到互联网虚拟空间的艺术作品;一类是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原创艺术。在新语境中,观看主体的观看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发生了相应改变。网络艺术改变着观看主体的思维、感知以及心理等精神活动,打破了传统艺术中二元对立的审美价值观。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数字信息造就了网络艺术传播机制的改变,产生了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交互式的沟通与交流。在艺术接受过程中,观看主体被提升到优越的位置,并且参与网络艺术的传播,这使得如何正确看待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网络艺术没有一个定型的样式,它集文字、声音、图像等于一体,形成了一种虚拟艺术,使观看主体的审美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网络艺术不再满足于单调的文本或图像,而是通过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交互来改变人们的观看方式。它以拟真性取代了再现性,以观看主体的互动性取代二元对立性。网络艺术的直接性、互动性和即时性,改变了观看主体的观看方式,从而建立起新的视觉观念与审美模式。
一、观看方式的交互性
从达达艺术、波普艺术到观念艺术,它们的出现无不伴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图像的自由结合及重复使用等因素都预示着网络艺术的到来。一是超文本的应用。超文本的特点就是非线性结构,它通过节点之间自由链接,按照创作者的创作意图组织信息和文本,其中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独立的要素。超文本颠覆了纸质文本的阅读方式,可以自由切换阅读位置。二是多媒体软件的应用。艺术文本将单词、短语、符号、图像、音乐等元素标示出来,通过多媒体软件进行相应的整合和处理,生成文字、声音、图像等多元融合的艺术作品,产生虚拟现实的场景。换句话说,借助网络出现的各种艺术作品,与信息科技的完美融合有紧密关系。如20世纪60年代,西方较早着眼于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动态艺术、早期电脑艺术;又如20世纪70年代,北美地区的“艺术与科技实验”的艺术团体,陆续研发网络科技给艺术带来的审美改变。这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是如何进入观看主体视野的呢?
网络的数字化将各种艺术信息统一成二进制的数字代码,并且根据个人意愿自由组合,逐渐成为一种全新的艺术形态。借助于网络,艺术家不再拘泥于有形的物质世界,而是进入了一个虚拟世界。传统艺术与网络艺术的相互结合,使观看者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选择。正如德里达对传统的二元对立命题解构得那样,要在“一定的时机,把它的等级秩序颠倒过来”①J.Derrida,Positions.Paris,Minuit.1972,p.57.。观看主体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助视觉、听觉与触觉等,增加了与观看对象的连接与互动,“为他们接纳新式思想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②李宗刚:《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文史哲》2014年第6期。。网络技术的日臻成熟,使艺术创作带有强烈科技色彩和机械烙印,人们更容易陷入信息技术误区。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网络艺术以虚拟现实为准则,以超文本和多媒体为创作和表达手段,并以复制性图像、符号性语言、虚拟性空间等为审美因素,这都对观看方式的转变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对观看主体而言,观看方式的转向昭示着一场深刻的视觉革命。艺术与信息科技的融合,消除了人类与机械的距离,而信息科技的介入,使传统的艺术形式被眼前的虚拟艺术所取代。创作者更加注重当下的审美感受,在空间上拉近了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关系,并且使这两个关键角色产生互动甚至互换。在虚拟世界里,观看主体与观看客体的关系完全是一种交互式的关系。在网络艺术中,观看主体与观看客体的关系变得不再固定,其文化载体逐渐消失,进而演变为一种“虚无主义”的艺术表征。在虚拟的环境中,网络艺术虽然偏离现实世界的认知方式,但是给予观看主体的审美体验却是实实在在的,它既吸收一切因素,又被一切因素吸收,人们获得的不仅是审美快感,更是一种对自由的觉醒与反思。在这种虚拟环境下,观看主体表现出审美感知的内在需求,为与互联网对话、交流和沟通提供了话语权。对此,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说道:“在诸如电脑这样的表征性机器中,界面问题尤为突出,因为人/机分野的这一边是牛顿式的物理空间,而那一边则是赛博空间。高品质的界面容许人们毫无痕迹地穿梭于两个世界,因此有助于促成这两个世界间差异的消失,同时也改变了这两个世界的联系类型。界面是人类与机器之间进行协商的敏感边界区域,同时也是一套新兴的人/机新关系的枢纽。”③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页。这里提到的“高品质的界面”,与超文本空间的互动平台成对等关系。超文本空间的互动性链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为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改变了传统艺术的互动方式。至于观看主体的参与过程,则需要进一步阐释。
第一,观看主体可以是创作者、传播者和接受者,他们无法以单一身份进入虚拟世界,其观看方式永远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观看主体正处于“看什么”向“怎样看”的视觉转型。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距离消失,所以观看主体可以直接进入观看对象,或成为观看对象的一部分。对观看与被观看关系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的哲学认识论:一方面,要厘清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二者如何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等问题;另一方面,观看主体从自身去感知“意识与身体联接”的统一性,产生一种更高层面的审美认知。正如胡塞尔所说:“其他自我在我之中的意义是在哪些意向性上,哪些综合以及哪些动机之中被构造出来的,并且在一致的陌生经验的名义中又是如何以他自己的方式被证实为本身在此的。”④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ons:An Introdiction to Phenomenology,Trans.By Dorian Cairns,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60,p.123.这里所说的陌生经验正是观看主体需要审美体验的过程。这种意向性体验意味着观看主体与尚未观看的事物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即意味着预先拥有某种东西。胡塞尔提出的“意识的意向性”正试图沟通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二者的直接联系。观看主体通过意向体验在观念与思维的相互作用,感受并呈现在视觉模式中。
第二,面对互联网的实时交互的传播机制,观看主体更直观地参与到作品的审美体验中。这种直观性包含了观看主体的知觉与想象,是目光中隐含着未知体验。正如胡塞尔所说:“‘一切体验都是被意识的’,因为这些特别意味着与意向体验有关的东西,这些体验不只是对某物的意识,而且不只是作为当它们本身是一个反思意识的客体时作为呈现者,而且同样也是未被反思地作为‘背景’存在着,因而本质上在类似于下述意义上是‘有待知觉’(Wahrnehmungsbereit)即如同我们的外部视线中尚未被注意的物是有待于被知觉的一样。”①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25页。“有待知觉”正是通过人们的观看方式去表达未知的体验。人们的观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由直观的知觉体验构成:一方面,直观使观看方式从外界对象向主观感受转变,它所带来的主观意向性体验适用于网络艺术的互动原则;另一方面,直观与观看对象直接关联,克服了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传统的认识论认为,直观只能用感官直接感知事物,但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对直观的认识,恰恰在于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即 “本质直观”。观看主体在审美体验过程中,主动地将视线投射在与观看对象的互动上。交互性的网络平台突破了传统艺术的单向传播方式,具有随机生成性,所以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必然带有主动性与互动性。就像媒体理论家尼葛洛旁帝所说:“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世代,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观信号。”②胡泳、范海燕:《网络为王》,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47页。在传播和体验的过程中,新的审美模式也会随机生成。
二、观看主体的审美生成
马克·波斯特(M.Poster)将单向传播的时代称为“第一媒介时代”,而网络时代则进入了“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第二媒介时代。媒介的发展改变了媒介本身与人类的关系,网络艺术结束了传统艺术的私密性空间,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审美生成的特有属性。弗·杰姆逊曾说:“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的模式,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空间性的模式,从时间向空间的转变使得时间的历史感被挤压到平面中导致历史深度感的消失。”③弗·杰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87页。后现代主义的这种空间模式取决于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相互作用的关系。网络艺术可以从二者的相互关系中寻找一种能动的观看方式,前提是观看主体用在线空间实现与观看对象的交互共享,这与传统艺术的审美方式大相径庭。有学者说:“传统艺术观众处于两极的身份是对抗性的,但在网络艺术中,两极的对抗得到了消解,两极身份向中间流动,尖锐的对抗变成和谐的身份融合。”④刘晗:《论网络艺术的美学精神》,《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在网络艺术里,观看主体的目的在于传播、参与及交流艺术作品,从而获得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而不是传统艺术中被动地接受艺术,这确立了其参与性与共享性。这种时空观变化召唤着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交互演绎。一方面,观看主体强调审美体验的开放性与实时性;另一方面,观看主体将这种瞬间碎片式参与转换为在线空间的互动,具有极强的主动性。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二者的关系,由封闭性的接受模式转变为开放性的互动模式。这就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何合理地观看,才能使观看主体需要从观看方式中去获得新的审美生成,并参与到审美体验中去呢?
网络艺术是一种多元整合的传播媒体,它通过虚拟现实造型语言(Virtual Reality Modeling Language,简称VRML),综合全感官的多媒体软件,可以逼真地模拟三维现实空间。观看主体置身其中,在传播信息与接收信息之间相互转换,仿佛成为虚拟现实的一部分。这种拟真成为一种开放性的自由空间,表现出强大的兼容性。在审美生成过程中,观看主体采用实时在线的交互审美方式,在虚拟环境中增强了网络艺术的现实感。虚拟环境在外观上并不背离现实,而是一种超真实的图像世界,这与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揭示的“超真实”(hyprereality)理念不谋而合。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虚拟之境被模仿到极度真实,就成为一种超真实的真实。鲍德里亚强调真实与再现的关系,是通过真实去探寻超真实,其奥秘在于“拟真”(simulation)的出现。拟真是从实物向符号过渡的产物,被称为一种审美幻觉。这种审美幻觉打破了传统的审美原则,试图借助想象和意象等心理活动来抑制现实世界。
在超真实的虚拟环境中,艺术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观看主体的审美意识。观看主体审美意识的形成,则很大程度上源于后现代所描绘的图像世界;观看主体的目的和价值不仅是为了审美的愉悦,而是转向文化与社会的意义上来,这也是网络艺术审美的意义所在。网络艺术用大量拟真的形象构筑了一个视觉的动态过程,其拟真性隐藏于虚拟环境,并制约了观看主体的视觉观念。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声音、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帅了观众。”①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56页。视觉观念将虚拟的真实与现实的真实混淆起来,从而使观看主体在虚拟环境中体会真实的审美快感。因此,观看主体的审美体验也成为一个超真实的过程,并且“整个现实从现在起都与超真实的拟真维度结为一体,我们的生活处处都已经浸染在对现实的‘审美’幻觉之中”②Jean Baudrillard,Simulations,London,Sage Publicatious,1995,pp.147 148.。在虚拟的审美幻觉中,观看方式俨然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审美模式。
如果大量拟真的视觉形象是为了承载虚拟之境的话,那么想象则成为通往超真实的审美路径。想象与观看主体的审美感知、情感、心理趋向等具有密切关系。在审美心理上,网络艺术体现为一种排除功利、排除主客分离的审美体验。这种审美体验将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紧密相连,它不仅涉及到审美空间置换和视角转变,而且涉及到视觉观念的转换。鲍德里亚曾说:“想象既表现出人超脱现实的渴望,又成为人追求乌托邦境界的一种动力。想象的认识论价值在于它的主观认知和创造。”③戴阿宝:《鲍德里亚:超真实的后现代视界》,《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想象的目的在于寻找观看主体的某种自由的审美境界,其价值在于观看主体的主动性与参与性。作为观看主体,他们用自己的观看方式作用于网络艺术,用想象构筑艺术的每一处细节,其目的是为了体现观看背后的思想观念,以便在超真实审美路径中寻求想象和幻想的延宕。观看主体用直观的形式反映了视觉循环逻辑,建构了真实与虚构、能指与所指的审美模式。正如鲍德里亚所说:“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再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④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王为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页。这种虚拟的实在造成观看的再循环,而观看循环逻辑的形成,意味着一种动态的线性结构。网络艺术借助视觉观念对观看主体思维的渗透,产生了“看”与“被看”的权力运作形式:一方面,这种流动性有助于艺术生活化的审美生成;另一方面,它将封闭性审美空间转换为在线审美空间,将深度审美体验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形象。
网络艺术将观看主体带入了一个超真实的图像世界,并将观看主体的审美模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法国学者米歇尔·德赛图指出:“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如同癌症一样疯狂生长的视觉形象,所有的东西价值均取决于这些形象显示或者被显示的能力,谈话也可能被转化为一个视觉化的过程。”⑤曾庆香、张楠、王肖邦:《网络符号:视觉时代的交流》,《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视觉形象的意义在于,观看主体审美意识的外化。在观看主体审美意识的外化过程中,网络艺术打破了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二元论观念,取消了二者之间的审美距离,消弭了审美想象中介。在视觉的直观作用下,观看主体寻找身份认同,产生了开放性与参与性的审美意识。
三、观看方式的审美异化
网络艺术蕴含着庞大的信息量,通过数字化技术生成逼真的虚拟形象。这种虚拟的形象通过强烈的感观刺激,主导着观看主体的审美意识,让其在一瞬间获得一种直观的审美体验。与传统艺术不同的是,网络艺术利用高科技手段,产生了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让观看主体的审美生成更加虚拟化和弥散化。观看主体的审美体验演变为对现实世界的遮蔽,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视觉异化现象。有学者指出:“虚拟世界的审美体验紧密关联着生理的美感,或愉悦或痛苦,或快乐或伤心,或喜忧参半或悲喜交加。”①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文史哲》2004年第5期。这种审美体验建立在虚拟环境中,很可能失去主动的审美意识,完全被视觉感官所控制,它所产生的生理快感会引起视觉观念的异化。网络艺术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采用互联网这个物质载体进行创作。从审美层面来说,虚拟环境与现实世界之间有一道天然屏障。观看主体的视觉异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审美观念的异化,必须要在社会和文化本源中质疑与反思。
当代审美由一维向多维发展,由本位向多元渗透,审美需求往往由精神领域向物质层面渗透,由此产生的视觉异化现象日益凸显。网络艺术是一种“第二自然”,这种超真实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它容易使观看主体陷入泛审美交流,而拒绝挖掘其内在深意。这种审美泛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审美缺失:观看主体在寻求观看价值的过程中失去了还原艺术本真的能力,从而导致了观看对象的审美泛化。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关系打破了主客体的原有认识,从不同角度唤醒人们对观看主体与观看客体二者关系的重新审视。一方面,人们试图寻找观看主体存在的独立意义;另一方面,人们却不得不受制于“非自身”因素的控制。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这种“冲击——反应”模式,成为隐藏在审美背后的话语权,控制并影响着视觉观念的合理表述。
面对庞杂繁多的艺术作品,观看主体不再专注于观看背后的审美体验与文化思考,而转化为一种“消遣”。关于消遣和凝神专注这两种审美态度的不同,本雅明曾解释道:“消遣和凝神专注作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可表述如下: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去注视自己的杰作时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②瓦尔特·本雅明:《经验与贫乏》,王炳军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8页。这里说的“消遣的大众”,实则是对观看主体的一种认知。在后现代社会,观看主体看待艺术作品已经不再具有神圣感和新奇感,而成为一种纯粹的视觉享受。面对网络艺术中各种各样的形象和符号,观看主体的心理和行为拒绝深层的审美体验和深度思考,审美目的则仅仅是为了抓取一个个动态的瞬间,从中获取自我欣赏的快感,达到一种自娱的观看目的。
这种观看方式造成了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诱发了网络艺术的解构与变异,使审美体验肆意化、碎片化。视觉形象遭到了解构,这就消解了虚拟与现实的关联性,以致审美泛化,并对观看主体的视觉观念造成冲击,进一步深化了网络艺术的审美解构过程。观看主体以直观的方式参与到观看对象中为审美的第一要义,与观看对象之间的距离随之“消解”与“分化”,完全沉浸到直观感应中,是即时性的审美生成。关于“消解分化”,费瑟斯通解释说:“距离的消解有益于对那些被置于常规的审美对象之外的物体与体验进行观察。这种审美方式表明了与客体的直接融合,通过表达欲望来投入到直接的体验之中。的确,它具有解除情感控制发展的能力,它把审美主体本身裸露在客体能够表现出来的一切可能的直观感应面前。”③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南京译林出版,2000年,第104页。“消解分化”准确地揭示出主体与客体审美方式的直观性。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的二元对立,其“消解分化”更倾向于一种碎片化的审美体验,这正是网络艺术不求完整性、不确定性的视觉异化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观看主体即便意识到二元对立的错误,也会重新掉入主体性的陷阱中,这是因为观看的过程是一种单维指向而非双向互动的视觉行为。正如鲍德里亚说的那样:“整个既存媒介都将自身建筑于这种界定之上:它们总是阻止回应,让所有相互交流成为不可能。”①让·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在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之间,网络艺术失去了连接性与交互性。这仿佛在摄影中,焦距始终处于模糊状态,观看主体无法获得观看的稳定角度,如何“认识你自己”成为消除观看主体焦虑的核心问题。观看主体的身份无法确认,导致了审美观念的模糊与不确定。这似乎掉进了互联网编程高手诡异的异态虚拟空间。观看主体沉迷于完美程序的幻象,可能导致信息科技的肆意发展,影响甚至取代人类思想及社会文化。
综上,网络艺术是融合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之间的在线交流艺术。与传统艺术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网络艺术旨在通过观看主体与观看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消除对立和隔绝,建构出连接性与交互性的审美模式。在网络艺术中,人与机器可以毫无痕迹地相互穿梭,把视觉的虚拟性发展到极致,使人们的视觉观念获得想象空间,不再拘泥于信息技术等有形物质,而是通过想象链接各种虚拟之境与现实世界。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本质上源于观看主体的审美体验。观看方式的改变,使网络艺术的价值与审美都有所迁移,并加深了观看主体对网络艺术的认识与理解。观看主体进入一个互动的审美空间,在提升想象的同时,承担视觉观念改变所引发的思考。
网络艺术的观看方式与审美生成
张嫣格
The Viewing Method of Internet Arts and Emergence of Aesthetic
ZHANG Yan-g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faculties of Arts,Jinan 250014,P.R.China)
The transmission route and the aesthetic method of Internet arts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raditional arts,which have changed the viewing method of the viewing subjects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have broken traditional arts’aesthetic value of binary opposition.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ostmodernism,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viewing subjects and objects has disappeared,by which a new aesthetic method has formed.Internet arts keep tearing the fracture between the two parts,creating a void zone and making all arts fall into the uncertain virtual world.Therefore,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to treat the viewing method of internet arts properly.
network arts;viewing method;viewing subjects;viewing object;emergence of aesthetic
[责任编辑:以 沫]
2015- 06- 30
张嫣格,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