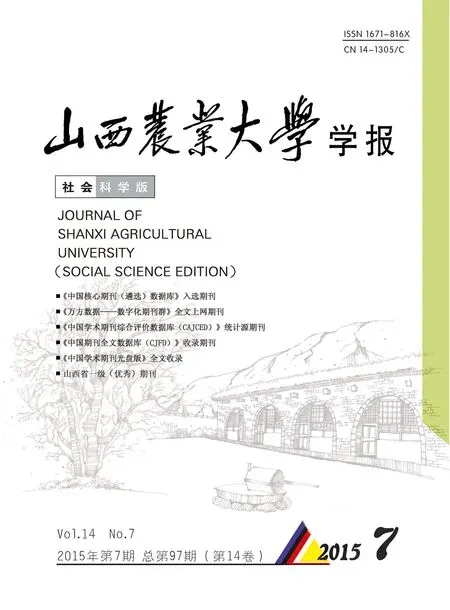延安文艺大众化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
张仁竞
(忻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山西 忻州034000)
延安文艺大众化 (下称文艺大众化)是20世纪文学思潮演变过程中一个关键词。从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到左联文艺大众化运动,从解放区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到建国以来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对文艺大众化这个命题的争论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厘清文艺大众化的运行机制,就要确定大众化的主体归属。主体的定位与归属直接决定了文艺大众化内部权力运行机制的形成。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学界也集中力量对大众化的主体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如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地位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及文艺大众化的文学史生成深入挖掘,以期从发生、发展的进程方面分析大众化的主体演变、形成过程及主体归属。问题是,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武断地判定文艺大众化的主体归属,一劳永逸地解决知识分子的地位与定位,那是一厢情愿的假设。以传统方法从宏观角度论述文艺大众化只能 “研究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相对的,有经济过程和上层建筑史。而对于各种权力机制中的权力却未被研究过。”[1]基于政治和文艺在现代文学史中的特别亲密的关系,学界的文艺大众化研究大多热衷于对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的研究,以宏观视野分析政治权力对文艺的干预,通过对大众化的宏观生成机制的追溯,分析大众化生成的背景和条件,探索知识分子在文艺大众化过程的作用和贡献,为文艺大众化的成功实践提供合理的依据,证明其内在的合法性。
然而宏观权力对文艺大众化的分析仅局限于政治和文艺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直接导致结论的简单化:政治对艺术的绝对领导,强调政治的作用是学界对文艺成功实践的共识。问题真是如此简单吗?政治对艺术的粗暴统治可以促成文艺的 “大众化”吗?即使政治的作用是巨大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的因素不应该考虑吗?难道作为五四一代启蒙主体的知识分子在文艺大众化过程中竟然主动放下自我缴械投降?这里忽视的恰恰是福柯所关注和思考的权力关系和机制的研究,他的理由在于:宏观权力是建立在这些权力的微观动作上的。他认为,权力是从最小单位、以零散的方式形成的,具体来说是从个人的身体发生的。身体和主体是研究权力的主要因素。福柯强调权力是一种关系,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权力是不稳定的,是动态的。权力的动作不是发号施令,也不是强制或压迫,而是各种力量之间的角逐,力量关系对比的描述。因此,文艺 “大众化”的过程是一种微观权力力量之间的变化对比和相互作用。分析文艺大众化的内部运行机制,须从大众化主体和相关关系入手,只有认清主体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找出话语权的归属、总结出权力在文艺大众化内部的运行机制。如果说宏观权力在政治层面和经济层面剖析了文艺大众化的生成机制,那么微观权力将以权力在主体身上的动作为中心研究文艺大众化问题的生成史。宏观权力注重社会运动,微观权力关注单一身体。所以,在对文艺大众化进行微观机制的考察中,“身体”处于核心位置。如何利用 “身体”内部各种权力关系的相互转化分析文艺 “大众化”和 “化大众”运行机制在 “身体”中的形成史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首先,文艺大众化的主体界定。大众化的主客体研究非常多,它们大多把知识分子作为大众化的主体,把群众认定为客体。其实学界的讨论针对的并非文艺大众化的主体问题,关注点更多的集中于主体背后隐藏的政治属性和阶级意识,而非主体本身。五四以降,大众化的主体不断发生着变化。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 “人的文学”和 “平民文学”,倡行以人性和人道主义研究社会人生诸问题,把知识分子当作理所当然的启蒙者和主体,平民作为启蒙的对象和客体,此时的平民指的是普通民众。[2]左联的文艺大众化运动,把大众定义为工农大众,是可以通过 “号召组织起来的社会性力量和政治性集团”。[2]知识分子依然以绝对的知识优势启蒙着大众。延安文艺期间人民群众包含所有工人、农民、士兵等无产阶级,且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发生逆转,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被工农群众取代。许多学者在论述主体性时,往往讨论的是知识分子的归属问题而非身份的论证,是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而非身体定位。学者们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他们引导并启蒙着工农群众,但在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却成为需要改变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被启蒙者。由此看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引起的化大众的启蒙运动和与工农群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的大众化运动是势不两立的。前者所指是知识分子 “化大众”,后者所指是被大众所 “化”。知识分子的定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直高居于主体地位的知识分子成了被大众 “化”的对象,有些无所适从。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到底谁是主体?判断这个命题的标准是什么?传统观点往往从启蒙的角度来判断主体的归属。但从延安时期文学实践的成功经过分析,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文艺大众化无疑是不能透彻的剖析其主体的归属问题。原因如下:一是延安时期工农群众处于启蒙的地位,无可争议的是工农群众不具备启蒙的素质。以工农的知识水平和能力启蒙处于先锋地位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二是毛泽东启发知识分子应该主动到工农群众之间改造自身,毛泽东深知工农群众是不可能改造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而要知识分子主动放弃自我,从此可以解读出工农群众没有启蒙的潜质。知识分子的启蒙者不是其他,而是自我,是经过毛泽东所代表的政治启蒙过的知识分子 “自我”,知识分子启蒙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本身被他者化的过程。所以,文艺大众化的主体从来不是工农群众,而是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被政治化的自我之间的一种权力较量。分析文艺大众化的主体就是对知识分子与其本身所代表的权力关系的分析。
知识分子是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权力关系和秩序。负载知识分子属性的身体才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身体在福柯的眼中不再是一个政治人,经济人,而是一个单一的载体,无任何文化意义。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认识到知识和权力在身体上发生的强有力的结合,将生物学与政治学联系在一起,推导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权力机制。他让 “肉体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打上标记,训练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那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3]以延安文艺为例,只有在知识分子的身体被政治化的驯服机制驯化之后,知识分子的身体才会转化成启蒙的力量,比如十七年写作和文革文学中知识分子作为启蒙的主体代表的仅仅是隐藏于其身后的政治权力。知识分子的自我已经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知识分子的思想通过政治的过滤净化后才能公之于众。知识分子作为卷入政治的肉体,代表的是权力关系中占有主动地位的主体,与普罗的关系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在有关启蒙者地位的征服机制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政党和集团。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时期,权力关系发生了流变。战争使工农成为了国家的主体,知识分子只占少数,在武力威胁面前只有工农才能完成守卫国土的使命。工农和知识分子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折。一切为了战争服务的口号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写实。战时权力关系相应的规训机制和征服机制也生产出大众化的知识分子和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两种身体。在被大众化的知识分子中,他们的身体被分割成各个部分,权力在其上分割出具体的控制范围、控制对象和控制方式,这是一种典型的微分权力。通过对身体各部分的控制和训诫,政治、文化和经济分别控制了身体的各个部位。
所以知识分子不是主体,群众也不是主体,主体是其背后隐藏的权力关系的相互作用中胜利的一方。
其次,通过对知识分子身体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分析,主体的定位已然明确。但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知识分子与群众的关系,一方面党要领导知识分子对工农群众进行基本的启蒙;另一方面党明确表态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要接受工农群众的情感改造。知识分子不但受党的政策束缚,而且要受工农群众的情感约束。知识分子被打上政治权力的 “烙印”,执行党的意志启蒙工农群众;工农群众被党提上主体的地位,承担着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任务。两种权力关系放置在一起必然会产生矛盾。但也可以看出二者都在政党的领导下为新生政权服务,二者统一在党的领导之下。即使如此,两个 “伪主体”之间在争夺话语权上也要一决高下。政治化的知识分子身体和政治化的工农群众情感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党在某种程度上更倾向于以工农群众群体改造知识分子群体。党认为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 “劳动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想感情、兴趣爱好和政治诉求”[4]不同于工农群众,是典型的中间派,既不属于党的认识论中资产阶级的范畴,更不属于工农群众的范畴。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知识分子属性的认识,以政治归属和政治表现划分立场的做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站在工农群众的立场上,感受他们的思想情感、工作方式、劳动方式等成为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内容。五四启蒙一代的主体在瞬间被打回原形,成了一个比普通劳动者还要低下的 “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有着自觉而强烈的自我意识。那么,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完成身份的自我超越呢?世界观改造的依据是什么?党是如何帮助他们完成世界观改造的?
这要从现代权力的特征说起。现代权力和传统权力不同,传统权力体现在君主身上,而现代权力是一种关系集合,这些关系不是单向的,充满了各种冲突和斗争。19世纪英国思想家边沁发明了一种叫做 “全景敞视建筑”[5]的环形牢房,环形中心部位是一座监视塔,环形建筑被分割成若干囚室,每个囚室的窗户正对监视塔。这种建筑的隐喻在于犯人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收入眼中,监视塔在囚犯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能够确保权力无形中发挥作用。处于大众语境下的知识分子就象是被置入一种 “全景敞视建筑”。他们处处受到一种眼光的注视,这种目光是大众的目光,这种目光促使他们开展自我审视,意识到自我是被监视的身体,这种机制会把权力应用于自我,还会对其他主体实施权力的传播和说服,使每个知识分子主体都纳入环形建筑的 “凝视”之下,把权力关系 “烙印”于自我和他者的身体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也是被监视和囚禁的过程。他们的思想处于被凝视的状态。自此,外在权力抛弃了身体的物理性(知识分子身体本身),而趋向于非肉体性 (知识分子自我),而且越接近自我,被凝视效应越稳定、越深入。党的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关系的论证其实正是建立在这一现代权力的凝视效应之上。
第三,确定了文艺大众化的主体,厘清了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的关系,那么 “大众化”和 “化大众”的过程中,大众话语是如何产生的?其内部运行机制是什么?根据对文艺大众化主体的认定和党、知识分子、工农群众三者关系的认识,笔者认为,大众话语的产生应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的驯服功能;二是工农群众的凝视效应;三是知识分子的自我超越。其运行机制也是以政治驯服、凝视效应及自我超越为基础的。
文艺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大众话语产生的过程,同时又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政治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话语分别代表自身所属的利益集团,政治话语因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存在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改造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话语是政治话语组织生产话语为其政权服务的基本目的。 “在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是根据一定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再分配的。这些程序的功能就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5]话语的生产程序依靠的就是政治力量的驯服功能,工农群众的凝视效应和知识分子自我的超越性。话语不再具有纯粹的表意特征,而要受到历史、文化、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的束缚和限制。文艺大众化运动的语境使知识分子被 “大众化”这一程序所规约,知识分子话语被放置于各种话语中,话语之间相互作用。话语体现权力关系,话语的相互作用体现权力关系的消长。
依上所述,文艺大众化其实是在政治话语的领导下,以大众化程序为条件,以驯服的知识分子自我为主体,生产符合政治话语引导的工农群众话语的话语机制。文艺大众化是一种话语生产机制,生产工具是政治的驯服、群众的凝视和知识分子自我的超越。在各种话语的纠缠中,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是最关键的二个,因为知识分子话语的先锋性地位是无可取代的,政治话语最终要实现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并为我所用。政治话语的驯服主要体现在话语的审查机制和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排斥上。知识分子话语的声音要经过政治话语警察的审查才能传播,而且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归属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虽然同为国家命运的组成部分,不可否认的是知识分子话语一直处于受控的地位,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话语的排斥一直存在。知识分子话语被禁锢在同盟者的身份里。即使如此,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意志也会被逐一甄别,话语的陈述受语言机制警察的审查,一旦被视为敌对势力,这些话语即被说成无意义的声音给予排除。话语的权力机制简单而明了,话语权的发放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内容,而在于 “谁在说”和 “如何说”的形式。权力意志通常会向其他形式的话语施加一种压力,产生排斥异己的力量。
在政治话语的领导下,工农群众也充当了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主体。作为全景中心塔的守护者,大众话语扮演着监视者的角色。这是除政治话语警察之外又一个话语审查者。在话语生产过程中,政治话语和大众话语都在凝视着知识分子自我,知识分子自我在监视中成长,这种权力关系无处不在,隐遁在周围像无形的手一样发挥着作用。它们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自我监视和权力传播一起构成了大众话语生产的大众化程序。在各种秩序的凝视下,知识分子自我的信心被摧毁,寻找一种被大众所 “化”的方式是其实现自我的最佳选择,也是其实现超越的唯一出路。
综上所述,知识分子话语被放置于包括大众话语、政治话语、经济话语等语境中与此形成权力消长关系,政治话语通过对知识分子话语和身份的认定和排斥,把知识分子定性为小资产阶级,与工农阶级和无产阶级处于对立状态,最终毛泽东通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政治话语把知识分子放逐于大众话语之下,产生一种附属于工农思想感情的代表无产阶级的大众话语。在大众话语的生成过程中,知识分子的身体先被甄别、排斥出无产阶级的队伍,然后被确定为改造对象,始终处在被监视的处境之中,知识分子自我最终在压抑中实现了超越,完成了被政治话语大众化的自我救赎。
[1]王治柯.福柯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192.
[2]王爱松.“大众化”与 “化大众”——三十年代一个文学话题的反思 [J].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2):24-32.
[3]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缨译.规训与惩罚 [M].北京:三联书店,2001:25.
[4]赵睿.从 “化大众”到 “大众化”看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变化 [J].学术论坛,2007(4):48-51.
[5]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