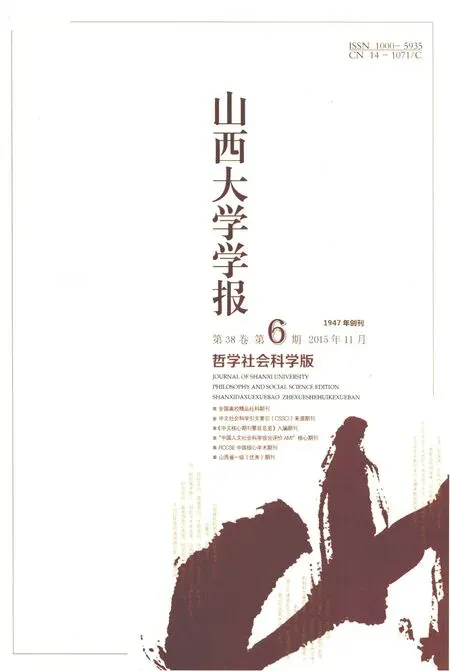论新闻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表现及其社会影响
姜 华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上海 200241)
民粹与民主仅一步之遥。当民主制度正常运转、社会秩序井然的时候,民粹主义隐而不显;反之,民粹思想激荡鼓动,民粹运动风起云涌。英国学者玛格丽特·卡诺婉(Margaret Canovan)认为:“民粹主义并非落后的表现,而是民主自身投射下来的一种阴影。”[1]民粹主义思想虽不及民主的观念那般源远流长,但作为一种时隐时现的社会思潮,也已经历数百年的历史。新闻业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深受诸多社会思潮的影响,民粹主义思潮虽然是阵发性的,但对新闻业发展之影响亦不容忽视。本文拟从民粹主义的历史及理论起源谈起,进而勾勒出民粹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思想根源与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民粹主义是如何影响新闻活动、新闻民粹主义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客观性等传统新闻价值观念构成的诸多挑战等问题。
一 新闻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一——政治民粹主义
从现象发生的角度看,政治民粹主义公认有两个源头:一是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运动及其革命宣传活动;二是19 世纪90年代到20 世纪初期的美国平民党运动。至20 世纪,在拉丁美洲、欧洲诸国、东亚等地,民粹运动都有表现。尤其是欧洲,民粹主义往往与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结合,这种被称为当代欧洲新民粹主义的思潮,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新闻媒体当然也不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闻生产与受众观念。
其实,如果依照宽泛的争取下层民众权益、对抗精英暴力统治的民粹含义来看,它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即已初露端倪,至工业革命时,社会矛盾激化,民粹思潮更加彰显。①(英)吉姆·麦克盖根认为,如果追本溯源,民粹主义的事例可以追溯到“14 世纪英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2]15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几乎同时出现的平均派和掘地派争取下层民众权利的运动,从某种程度上隐含了民粹之义。平均派是在1647年左右出现的,其领导者是约翰·利尔本和理查德·奥弗顿,成员多是克伦威尔军中的普通士兵,这些士兵在革命前原本是英国社会中的小商人、工匠和农民,谋求的是代表自身利益的激进改革(与英国社会的富裕阶层的诉求有很大差异,后者设想的仅仅是保守的改革)。利尔本本人常常以人民的代表自居——“当别的人争论有关国王和议会的权利时,他总是谈人民的权利”。虽然在军方的高压之下,平均派归于失败,但是“他们的思想在许多方面对后来的民主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和纲领起到了先导作用”,[3]541民粹主义恰恰是此处所说民主激进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与平均派的活动相比,掘地派运动着眼于将部分公有土地分给农民,但影响甚小,一年左右就以失败告终。[3]550
作为学界公认的民粹主义源头之一的俄国民粹主义,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 世纪20年代致力于推翻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参与者俱是沙俄贵族,遭到残酷镇压。别尔嘉耶夫认为,民粹主义乃是“彼得大帝时期历史的非有机性的产物,是大量俄罗斯贵族的寄生性的产物。相当小部分的最优秀的俄罗斯贵族获得了很大的荣誉,在他们中产生了民粹主义意识”。[4]103“十二月党人”起义正是这种少部分优秀贵族民粹主义意识爆发的结果。第二个阶段是19 世纪四五十年代,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思想动员。有研究者认为,“民粹主义的理论体系,是由赫尔岑建立,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并由不同时期的各主要派别的思想家充实”。[5]二人之所以被俄国民粹派尊为思想旗帜和精神领袖,主要是他们在19 世纪40年代提出的将“将俄国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肯定俄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论点与三十年后俄国民粹派的基本思想理论保持了一致。[6]1除此之外,民粹派更加看重的恐怕还是二人在当时俄国社会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当中的巨大影响力。其实,就思想倾向而言,赫尔岑更倾向于个人自由,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俄国民粹派的主流思想是不太契合的。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张也与民粹派未尽相同,二者皆是民粹主义者,但俱非民粹派。在第一、二两个阶段,参与民粹活动的,以贵族知识分子为主,到了第三阶段,许多平民知识分子加入其中,影响面进一步扩大。第三个阶段即是民粹派风起云涌的19 世纪最后三十年。民粹派的真正彰显是1874年前后,数千名青年学生在“到民间去”口号的鼓舞下深入到俄国“村社”中去,“力图通过发动农民来推翻沙皇政府的反动统治,从而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粹派的名称也正是由此而来”。[6]2此事发生的社会背景是1861年解放农奴制改革的失败。但是由于内部充满分歧,又没有富有成效的协商机制与明确目标,19 世纪末期,民粹派的运动走向衰落。
从俄国民粹派及民粹主义思想传播的过程来看,其主要特点如下:第一是对“人民”的推崇,认为“人民”是社会的精粹,是社会变革的动力。无论是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后期的民粹派,他们都将生活在具有俄国特色的“村社”中的农民看作道德高尚的社会群体,是推翻沙皇旧制、建立社会主义的主要力量。恰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不同于西方各民族国家的特殊性)、赫尔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70年代的革命者都是民粹主义者,他们“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4]102这里的人民其实主要是指当时的俄国农民,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正确指出的,俄国民粹派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出以农民之名”。[7]由于当时的俄国,农业人口占社会的绝大多数,因此农民从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的代名词。第二是对人类平等的追求。民粹主义者认为专制的政府腐败不堪,侵吞了广大农民的劳动成果,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剥削。在19 世纪80年代的一份《民粹派基本纲领》中,首先提到的就是:“民粹派学说的出发点是人类平等”。[8]而在“到民间去”的民粹派成员多尔古申的作于1873年的传单中,又再次重申了平等的重要性:“只有当人们处于平等的地位,当一个人不能随便欺负别人,当没有那种迫使人服从不公正的制度的难堪的贫困,当人们都沐浴着文化和科学的光辉时,人们才能自由”。[9]值得一提的是,民粹派的此种平等观念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尤其是雅克·卢梭的思想在俄罗斯的传播有密切关系。第三,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对农民自治的崇信。俄国民粹主义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斯拉夫主义者,与当时俄国境内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俄国也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同,他们认为俄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即可实现村社社会主义,而农民是道德最崇高的群体,俄国传统的村社组织与社会主义的结合,完全可以使农民实现自治。因此,不必迷信代议制制度。第四是对精英知识阶层充满敌意。俄国民粹派运动的发动者,大多是知识分子(贵族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对自身曾是剥削阶层感到愧疚,他们到“民间去”的举动,既有发动农民参与革命的诉求成分,同时也有以自身行动向农民表达忏悔之意。在民粹派的思想中,知识分子只有将自身与农民的利益紧密联合在一起,才是有价值的。在一份传单中,多尔古申写道:“你们知识分子都非常了解目前极不正常的世道,所以我们号召并请你们到民间去,以唤起人民为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而进行反抗。谁只要能够,谁就应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献给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必考虑,不论做出什么牺牲对他来说都不会代价太高。”[6]257-258在民粹派的纲领中,亦将此作为重要的方面:“知识分子的作用在不同时代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当知识分子代表被奴役群众的利益并为反抗被奴役群众的压迫而进行斗争时,他们的思想和道德水准最高。”[6]554
在俄国民粹派走向衰弱的同时,在19 世纪末期的1890年,美国西部和南部的劳工和农场主联盟组建了平民党,继而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浓重民粹主义色彩的平民运动,借以对抗世纪之交美国垄断大企业等少数特权阶层对自身利益的侵害。美国平民党运动兴起的背景是,19 世纪末期,美国经济萧条,普通民众,尤其是西南部农民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失。伴随运动的发展,参与者逐渐超出农民、农场主的范围,大型企业的产业工人亦加入其中,声势日渐浩大,成员达数百万人之巨。平民党的民粹诉求集中体现在1892年发布的奥马哈宣言中。宣言主要纲领有三条:第一,在货币政策上,国家管理货币,摆脱银行系统,限制税收,制定切实可行的所得税政策等。第二,交通方面,政府拥有铁路所有权和管理权。第三,遏制土地的投机买卖,被铁路公司或者其他大公司侵占的超出其实际用途的土地应该交还政府或当地居民。[10]44美国平民党运动与俄国民粹派革命活动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从道德价值层面看,二者都将下层民众(“农民”、“下层产业工人”)看作道德高尚的群体,美国民粹主义者的思想“印证了农民作为富有成效的尽职尽责的公民和堪称美国革命思想源泉的宝库,以及创建一个农民自治的共和政体的形象”。[10]48与之相关,二者都倚重下层农民(农场主)或者底层劳工,与俄国民粹派不重视城市工人的思想相似,美国平民党运动也未能成功动员城市工人加盟。与此同时,他们都将特权阶层看作想象的敌人。在美国平民党运动中,其所属报刊就一再宣称:“阶级的权力或者说大公司的权力,在与日俱增。…在所有最基本的方面,我们父辈建立的那个共和国已经死了。”[11]813
但是细心分辨可以发现,美国平民党运动与俄国民粹派毕竟不同。例如,俄国民粹派的革命色彩非常突出,目标是推翻沙皇政府,而美国平民党并无推翻政府之意,仅仅是要求社会改革;俄国民粹派反对西方的代议制政府形式,看重的是某种程度的“直接自治”,更有少数民粹派成员(如巴枯宁)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色彩,而美国平民党曾参与19 世纪末的美国总统竞选,他们并无反对代议制的诉求。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自此一直保留下来,直至整个20 世纪,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中一道别样的风景。
除了俄国民粹派和美国平民党以外,受这两种民粹思潮的影响,20 世纪中后期,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民粹主义运动逐步兴起,在继承基本的民粹信条之外,亦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他们或与本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融合,或与民族主义甚至是极端种族主义勾连,掀起一次次的民粹浪潮,影响及于社会的方方面面。①拉丁美洲和欧洲民粹主义新变化的相关论述,可参见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保罗·塔格特著,袁旭明译《民粹主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两位作者在实证和实例部分,对此有详细评述。这些流变中的民粹思想和发展中的民粹运动,有些民粹主义思想家自身积极参与新闻业活动而直接举起了新闻民粹主义的大旗,另外还有些新闻从业者因受民粹思潮启发,亦在新闻活动中采取民粹主义的价值取向,使所在新闻媒体乃至本国、本地区本国新闻媒体亦沾染浓烈的“民粹”色彩。
二 新闻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之二——文化民粹主义
文化民粹主义的出现与雷蒙德·威廉斯等几代英国文化研究学者扭转精英文化论的努力有紧密关系。谈及现代文化的精英论,一般都会论及法兰克福学派,凡是论及法兰克福学派,必会引述该派学者对文化工业的猛烈批判。事实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也是渊源有自: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谈及现代文化时,曾提出“合理性”的概念,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合理性有双重内涵:一为实质合理性,强调内容本身,具有解放意义,关心的是终极目的和价值目标,一为形式合理性,看重形式,具有实用价值,关心的是功利目的和效率取向。现代文化无疑深受形式合理性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工具性。但是,正如陆扬、王毅指出的那样,“形式合理性完善了资本主义的主要机制及其实践,完善了自由市场和它的管理机制,然而却是以牺牲这些领域自身内在最根本的东西为代价的”,“韦伯对现代性的悲观态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开启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先声”。[12]48-50韦伯之前,德国哲学家尼采亦持有显著的文化精英论点,在《上帝之死》中,尼采提出,健全的社会有三种类型的人构成:第一类是具有卓越精神的精英,第二类是具有强健体魄和顽强性格的个体,第三类是占大多数的什么方面都不突出的普通人。[2]50依循这样的思路,尼采认为现代文化具有做戏和激情的特征,完全是为了迎合毫无教养的愚昧大众的,是现代“病态社会”的产物,“真正的文化成就日益被如火如荼的商业主义和大众民主蚕食”。[12]86-87换言之,以尼采的观念,真正的文化是由精神卓越的少数精英创造的,而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却是在大众民主的浪潮中,由那些愚昧的普通人粗制滥造的结果,这是文化的沦丧。在吸收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本雅明等人先后著文对文化工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现代文化已经丧失了批判功能,堕落为商品法则的产物;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工业不顾公众的真正需求,生产的产品都是为了自身利益和公众的虚假需求。但是,即使是法兰克福学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对文化工业批判最为激烈的阿多诺最先注意到了文化工业自身所蕴含的潜在批判力量,而本雅明更是注意到了文化工业的进步意义,他认为艺术作品有两种价值,一为膜拜价值,一为展示价值,文化工业通过机械复制把艺术品的展示价值释放出来,供大众鉴赏。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对文化工业作了非常积极的评价。
与法兰克福学派总体上把文化工业的作用简单化不同,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持精英文化态度的学者根本就是置若罔闻、不屑一顾。在英国学者阿诺德的眼里,人可以分为三类,即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野蛮人也就是贵族,他们闭目塞听、自高自大——“其过度则表现为桀骜不驯”,然而其缺陷又“表现为不够勇武高尚,过分的怯懦,逆来顺受”;非利士人指中产阶级,他们陷于功利主义的物质泥潭中,积重难返——“他们喜欢的就是工具,诸如生意啦,小教堂啦,茶话会啦”;群氓指劳工阶级,他们不是追随中产阶级生活——“他只想工具手段,满脑子转的念头都是发展工业、执掌权力、成就卓著、还有别的外在的能耐等等”,就是自甘沉沦、粗野无知——“严厉时喜欢大喊大叫,推推搡搡,打打砸砸,轻松起来则喜欢喝啤酒”。[13]在三类人中,只有小部分人能够成为有思想、有修养的知识精英,成为人类文明和思想的传承者。剑桥大学的利维斯继承了阿诺德的文化传统,认为文化是少数人的事情,工业化使文化范畴扩大,但也导致了文化的堕落。在传统的精英知识分子看来,社会的构成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有文化的少数人类精英,他们使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深邃的思想得以传播、发展,另一类人则是占人口大多数的“群氓”,他们生活贫困、举止粗鲁,没有文化。对此,利维斯解释说:“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数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众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12]72这是典型的英国式的精英文化观,与德国思想家的从哲学角度切入不同,以上英国学者大都以文学为文本,论述精英文化的价值,针砭大众文化的粗俗不堪。
成立于1964年、崛起于20 世纪80年代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颠覆了英国传统的精英文化思想,反思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使文化走下了神坛,走向了民间与大众。在对大众文化的认识问题上,伯明翰学派的思想家们的观点与传统精英思想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他们的研究都表现出英国中心主义的倾向,同时又把文本分析作为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传统精英思想不同,伯明翰学派的思想家认为,文化是人们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是大多数人的事情;传统精英思想只以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伯明翰学者则把研究领域大大地扩展了。例如,在雷蒙德·威廉斯看来,文化至少应该包含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用来描述18 世纪以来思想、精神与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二是表示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关于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全体人类;三是用来描述关于知性的作品与活动。[14]102-103将特殊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考察,无疑极大地突破了精英文化的“文化视域”,亚文化、次文化等多元的文化视角成为其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看来,文化工业几乎是十恶不赦的“恶棍”,他们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引向堕落和黑暗,使人们被迫接受他们并不需要的精神垃圾,而且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还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分子的姿态,他们把受众当成了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和辨别力的“文化群氓”,认为文化工业拥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在解释“popular”一词时,特意指出“popular culture”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地下的工作(如popular press 意指通俗新闻,与优质新闻——quality press 相对);二是指刻意讨人欢心的工作(如popular journalism 意指大众新闻,与民主的新闻——democratic journalism 相对)。紧接着,他进一步指出,“populism”(平民主义、民粹主义)包含了“popular”一词的上述各种含义,同时仍然强调“民众的利益与价值”。[14]357威廉斯没有直接提出文化民粹主义的概念,但是他认为大众文化之中已经天然含有民粹之义。虽然在定义“文化”一词时,为避免陷入民粹之中,他特意从历史的视角阐明文化的三种不同含义(其中既有精英文化观,亦有大众文化观),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看重大众文化面向广大民众的价值,此论实际上开启了伯明翰学派后世的文化民粹之风。
伯明翰学派的学者第一次真正把大众和大众文化当成了研究的对象,他们充分肯定了大众文化的意义和大众的主观能动作用。该派的领军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是被压迫者反对权力支配的“斗争场所”,大众在这个竞技场中有较大的自主性,而不是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霍尔在《编码,解码》一文中指出,信息生产的权利关系与消费的权利关系并不是完全吻合的,并提出受众的三种解码方式:即“支配-霸权立场”,受众立场与传者立场完全一致;“协商立场”,受众不完全同意也不完全反对传者立场;“对立立场”,受众有自己的解码方式。[15]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使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期占优势的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受到重创。传统的经验学派始终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关注受众研究和效果分析,以为借此就可以把传者的意图传递给受众并使其接受,获得意想中的传播效果。霍尔的理论把受众彻底解放出来,使人们对这种被动的受众观有了新的认识。换句话说,他认为,民众是有能力从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念来解读文本的。与霍尔的理论有某种相似之处,约翰·菲斯克通过“两种经济”的学说,将文化民粹主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他所谓的两种经济,一为金融经济,一为文化经济。在文化经济中,本来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的观众转而成为文化意义的生产者,通过对文化产品的解读,创造出体现其个性的意义与思想。霍尔和菲斯克的理论,使大众文化的供应者明白文化传播终端的重要作用及其价值。从而也从一个角度开启了迎合民众趣味的大众文化风潮(这正是精英文化论者对现代大众文化的最不满之处)。在他们看来,这些“普通百姓的符号式经验与活动比大写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费思量”。[2]4
而事实上,从新闻业本身看,与政治民粹主义强调“人民”的政治意涵不同,文化民粹主义看重的是“普通的、底层的、广泛的普通人”,而在强调市场和竞争的欧美新闻业巨头那里,这个普通人无疑悄然演变成了“尽可能多的受众”。从欧美新闻巨头的新闻实践活动看,绵延不绝并在一定时期愈演愈烈的通俗新闻、“黄色新闻”、新闻的“小报化”风格,无疑都有“文化民粹主义”的影子。当然,这是一种变质了“文化民粹主义”。
三 传统新闻业中的新闻民粹主义
(一)新闻民粹主义:政治民粹与文化民粹的融合
关于民粹主义,学界一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思潮或政治运动,相关的研究文献也以政治学领域居多。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Jim McGuigan)曾言,相比在文化讨论中而言,“民粹主义”一词在政治学的研讨中显然更加普遍。①有关民粹主义著作,较有影响的著作如:GhitaIonescu,Ernest Gellner.Populism.Macmillan Pub Co,1969;Lawrence Goodwyn.The Populist Moment:A Short History of the Agrarian Revolt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Margaret Canovan.Populism.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1981;Jeffrey Bell.Populism and Elitism:Politics in the Age of Equality.Regnery Publishing,1992;Francisco Panizza (Editor).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Verso,2005.;John Lukacs.Democracy and Populism:Fear and Hatred.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Francisco Panizza (Editor).Populism and the Mirror of Democracy.Verso,2005;CasMudde,Crist?balRoviraKaltwasser (Editor).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Threat or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确实大都是在政治范畴内进行讨论。其实近年来,作为一个指涉广泛的概念,民粹主义早已超越政治学范畴,成为文化乃至传媒领域内被用来分析相关现象的重要理论概念。如:Michael Shamiyeh (Editor).What People Want:Populism i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Birkhäuser Basel,2005;Cher Krause Knight.Public Art:Theory,Practice,and Populism.Wiley-Blackwell,2007;Charles Postel.The Populist Vis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15也正是这位麦克盖根,以一部“文化民粹主义”为题的著作,将民粹主义引入到文化研究甚至大众传媒的分析中。此后,欧美诸多学者开始借助民粹主义这一有力的分析工具,对新闻传媒、影视作品等进行分析。就连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著名学者、作家翁贝托·艾柯也曾撰文谈及新闻传媒的民粹主义与意大利政局的相互关系。民粹主义,不仅仅是将自身看作一种政治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新闻民粹主义承继了两种民粹主义的价值观念,是二者思想的有机结合。上文对政治民粹主义及文化民粹主义的来龙去脉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述,意在表明以上两种民粹思想对于新闻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价值追求在当时及后世乃至当今的新闻活动中不断再现。
以新闻发展的眼光看,新闻的民粹主义首先体现在民粹主义者为民粹思想传播和民粹运动动员所创办的一些新闻评论杂志和报刊中。在俄国的民粹运动过程中,赫尔岑流亡英国后,曾与友人创办了《北极星》和《钟声》。尤其是《钟声》,通过大量叙述生动、知识性强的时政评论,赫尔岑不仅传播了民粹主义思想,还“利用从秘密通信和私人消息获得的大量信息,讲述俄国官僚的种种劣迹,揭露具体的丑闻——各种行贿案、司法腐败、官员和大人物的专横与虚伪”。[16]在美国平民党运动期间,为了传播其思想和观念,平民党人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小册子,同时还创办了1 000 多份地方报纸,这些报纸面向社区,为民粹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11]812
除了民粹派自身创办的报刊之外,新闻的民粹主义在劳工报刊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在英国劳工报刊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劳工报业的风云人物亨利·海瑟尔顿(Henry Hetherington)曾在其报纸上宣称:“我们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痛击政府。”在其创办的《穷人卫报》上更是抨击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不公:政治将社会分成两个阶层——奴隶与强盗;前者包括穷人和没有知识的人,后者则是富人和狡诈者…这些抢劫是通过政治活动实现的,也只能凭借政治活动禁止…而且,所有的政府运作,都将人民排除在外。在这种体系下,所有的政府运作都是如此。[17]海瑟尔顿的政治态度在当时的劳工报刊中较为普遍。劳工报刊的表现具有两面性,当它在议会制民主制度下争取劳工权益的时候,它是争取民主的舆论工具;当它宣扬大多数的穷人与少数富有者的对立,将这些富有者称为抢劫者和狡诈之徒,将劳工阶层看作社会的良心和一切进步的根源的时候,则恰恰是民粹思想的直接体现。
新闻民粹主义在美国大众化报业中也不鲜见。当平民党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恰恰是美国大众化报业兴起之时。当时客观性的新闻理念尚未完全形成,在不同的报纸之间,新闻活动的日常操作也存在千差万别。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党派性报纸、大众化报纸并存,虽然报业的逐步独立,使得报纸逐渐有意识地承担起为民主服务的职责,但在此过程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报纸为了谋求迅速发展,吸引更多读者,办报活动中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以挖掘社会黑暗和为劳动阶层代言主导新闻报道,代表了大众化报业发展中的一种民粹主义价值指向。与英国激进的劳工报刊主要呈现出更多政治诉求、对抗执政精英阶层不同,美国大众化报业兴起过程中的表现,对抗政府的意味淡薄,主要的是提供更多适合社会底层公众阅读的新闻,文化民粹的意味更重些。
从政治的角度看,在政治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新闻民粹主义选择了民众;从文化角度看,在高雅与通俗之间,新闻民粹主义更看重通俗。与新闻民主观念强调自治观念抑或是精英式的程序性代议制民主不同(代议制民主并未否定普通公众的民主权利,在他们看来,从政治现实的角度考量,普通公众的民主权利主要表现在通过选举权的行使,选出适合的人进行国家或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新闻民粹主义是一种“二选一”的模式,强调少数社会精英与多数社会大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存在极为对立的价值观念和利益之争,其崇尚的是社会底层大众道德观的优越,传达的是社会底层的声音,传播的是深受社会底层偏好的新闻资讯,代表的是社会底层的利益,处处表现出对精英阶层的不信任,对精英层次及其价值观念始终存有贬抑之意。概言之,新闻民粹主义是新闻活动主体极端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平衡性等理念不同,在民粹主义的新闻观念中,是价值先行,价值判断和情感偏向远比新闻的客观呈现更重要。
(二)政治色彩浓郁的拉丁美洲新闻业:“民粹核心区”的新闻民粹主义
拉丁美洲是当代民粹主义最为突出的地区,称之为“民粹核心区”毫不为过,因此该地区新闻媒体的民粹主义倾向也最引人瞩目。由于历史上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曾长时间沦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其政治、经济、文化带有明显的欧洲烙印,在此背景下,其“新闻文化长期受到欧洲的影响”。[18]60同时,拉丁美洲又毗邻北美大陆,亦受到美、加尤其是美国自由主义新闻理念及其实践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拉丁美洲的新闻业,既与欧洲大陆不同,更与北美自由新闻业有异。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英美自由主义新闻模式的标志是以市场为中心,公民社会和国家介入有限。民主化公民媒体则以公民社会为中心,对市场和国家的介入多有限制。”但是拉丁美洲的新闻业显然与上述情况都不一样,它将国家置于媒介系统的中心,这种模式以代表“大众-民族”利益还是代表“寡头——外国”利益作为划分新闻业的标准。[19]拉丁美洲的新闻媒体重视市场,但是更看重自身与政府如何建立密切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又与英美和欧洲大陆各国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迥然有异,其典型表现是媒介与政府是“合作而非对抗、互利而非自治”,而“政府官员们常常会直接(或通过家庭关系)加入到媒介所有者的行列”。[18]61即使有的新闻媒体没有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参与,但也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从20 世纪30年代开始,拉美主要国家政府陆续制定了通过媒介宣传公共政策和传达一些事项的法规,以不同的方式规定,征用各民营广播电台和电视台1 小时或半小时的黄金时间,播出由政府提供的新闻和娱乐节目(包括电视剧)”。[20]作为回报,拉美各国政府会在这些媒体上投放政府广告。事实上,拉美各国的许多媒体恰恰是依靠政府投放的广告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鉴于以上特点,无论是自由主义模式还是法团主义模式,都不足以解释拉丁美洲的新闻业,采用民粹主义的分析视角,却能够较好地对其进行解释。
既然拉美各国政府的政治运作表现出明显的民粹主义色彩,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拉美各国新闻业在运作中凸显民粹主义也就不足为奇。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执政的巴西总统热图利奥·瓦加斯(Getúlio Vargas)就非常注意利用广播推行其民粹主义政策。为此,他还下令于1931年设立宣传部(State Department of Propaganda,后来改为新闻与宣传部——Press and Propaganda Department)。1935年7月22日,巴西新闻与宣传部制作了一档节目——“巴西时间”(Hora do Brasil),用于宣传瓦加斯政府在国家发展中取得的成绩。随后,强令全国各地的广播公司在每个工作日的黄金时间段下午6:45-7:30(中波)和下午7:30-7:45(短波)播放这档节目。[21]由于历史上巴西长期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经济发展滞后。瓦加斯执政的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恰恰是巴西现代化起步的阶段,城市人口激增。为了赢得大众支持,瓦加斯提出了遏制跨国垄断企业,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在利用新闻媒体宣传时,上述政策又以“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赢得了巴西绝大多数中低阶层民众的支持。
1945年以来,民粹主义政治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全面复兴。阿根廷的庇隆主义乃至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在政治活动中无不诉诸民粹主义,这昭示着民粹主义思潮始终是影响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拉丁美洲国家的新闻业一个明显特征是以国家为中心,因此,伴随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不能说其他模式的新闻理念对拉丁美洲新闻业没有影响,但是瓦加斯时代兴起的新闻民粹主义显然依旧是上述国家新闻业的典型特征。在拉丁美洲,民粹主义新闻业有不同的名称。在阿根廷,它被称作“激进新闻业”(militant journalism);在委内瑞拉,它被称作“迫切需要的新闻业”(necessary journalism);在尼加拉瓜,它被称作“桑地诺新闻业”(Sandinista journalism,桑地诺是尼加拉瓜20 世纪30年代民族革命领袖);在厄瓜多尔,它被称作“忠诚的新闻业”(committed journalism)。[19]在拉丁美洲各个国家,民粹主义新闻业的理念受到新闻从业者的认可。阿根廷的一名新闻工作者马丁·加西亚(Martin Garcia)对激进新闻的理念就颇为认同——“我首先是激进分子,其次才是记者。对谁客观?在另一面,有些人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致使儿童受到绑架。对于他们,不能有客观性。”[22]尼加拉瓜的记者康斯韦洛·桑德瓦(Consuelo Sandoval)是“桑地诺记者论坛”的创办人之一,他认为民粹主义的新闻业有助于打破商业媒体的束缚,因为这些商业媒体以往常常假借独立、公平与客观之名,利用我们维护党派利益。[23]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拉丁美洲的新闻民粹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独特的规制特征。首先,从新闻修辞上讲,诸多具有民粹倾向的拉丁美洲新闻媒体,都将“人民”置于新闻理念的核心地带。恰如别尔嘉耶夫所言:“把人民看作真理的支柱,这种信念一直是民粹主义的基础”。[4]102将“人民”作为价值诉求的主体,是一切形式的民粹主义共有的特征,拉丁美洲形式各样的民粹主义亦如此。“人民”成了拉美媒体新闻活动的最终价值指向。在拉丁美洲新闻业的话语系统中,“人民”是受到跨国公司寡头剥削的下层民众,而那些掌握大多数人命运的寡头或者国外形形色色的利益群体在本国的代言人,则是“人民的敌人”。凡是对于人民“有利”的,就毫无保留的支持,而对于损害人民利益的群体或者个人则大加挞伐。其次,新闻媒体的民粹“偏见”与民粹主义政治领袖的相辅相成。依照马克斯·韦伯的分析,历来合法的统治可以分作三种类型,分别是合法型的统治、传统型的统治和魅力型的统治。合法型统治的基础是统治者建立的合法性的章程规定的制度和指令,传统型统治的基础是历来的传统的神圣性。与二者不同,魅力型统治“(建立在)非凡的献身于一个人以及由他所默示和创立的制度的神圣性,或者英雄气概,或者楷模样板之上”。[24]反观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的政治,无论是阿根廷、秘鲁,还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其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诉诸个别政治人物个人魅力的基础之上的。泰勒·博厄斯(TaylorC.Boas)曾以巴西和秘鲁为例,研究了拉丁美洲电视与新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博厄斯看来,与传统民粹主义通过严密的组织(政党或者商业组织)对下层劳工进行动员不同,新民粹主义是一种非组织化的面向所有原子式的贫困阶层的民粹新形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电视成为新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博厄斯发现,1989年的巴西选举中,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将1985年刚刚获得选举权的穷人和文盲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诉诸民粹的路线赢得了巴西电视的广泛报道。2000年秘鲁总统选举中,民粹主义者藤森更是赢得该国电视的一致支持。从新闻报道数量上看,藤森占有电视报道总量的66%以上,而他的竞争者仅仅占23%,其被报道的时间更是占总报道时间的78%-89%。从新闻报道的内容方面看,藤森的所有反对者在新闻中100%是负面报道,而针对他本人的报道97%是正面的,仅有3%是中立的。[25]由此可见,在拉丁美洲,新闻媒体在报道活动中,采取一种自觉地带有民粹倾向的偏向性报道,已成为其新闻活动的常态,在政治活动和政治人物的报道中尤其如此。再次,拉丁美洲的新闻媒体,常常受到统治当局的严厉管制,自觉或被迫与当局的“民粹”策略保持一致。当局常常对个人拥有的媒体和记者进行点名批评,指责其背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利益阶层效劳。更有甚者,对敢于作对的新闻媒体,有时候还会没收其财产。
(三)欧美等国的新闻民粹表现——从政治民粹主义到市场民粹主义
在传统的民粹主义话语中,民粹主义有两种较为清晰的指向:一是“以民为粹”,这种修辞表达的是“大众是精英的力量源泉,大众是不容忽视、不容污蔑和至高无上的,而精英应该服务大众,为大众谋福利,大众支持的目标应该是民粹主义者的目标,大众反对的就是民粹主义者的敌人,一切对上层、对统治阶层的妥协和宽容都有违人民意志”;二是“民之精粹”,这种修改表达的是“部分精英一方面承认人民利益的重要和人民支持的意义,另一方面又认为人民是消极落后和愚昧保守,因此他们自视为人民的精粹,认为自己在历史发展中应起到决定性作用”。[26]4220 世纪50年代以前,农民在世界各国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成为民粹主义者心目中的“中心地带”。伴随社会的发展,城市劳工阶层等成为与农民一样,成为具有合法性的“人民”的一部分。拉丁美洲各国新闻媒体的民粹思想即是如此,它将农民、城市劳工以及代表这些群体利益的少数政治人物看作社会公正和统治合法的力量来源,积极报道维护下层利益的社会政策与社会运动,支持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这体现了“民之精粹”的思想。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也是从这个层面上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的。他认为,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而不是人民本身的运动,虽然它更大程度上是为人民的。[26]42考察世界各国新闻业,新闻记者将自己看作人民的代言人,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底层民众代言的观念一直存在。在新闻活动中,新闻记者一方面将社会底层看作报道对象,将呈现其价值指向作为自身的自觉追求(以民为粹),同时又将自身看作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民之精粹),巧妙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依此凸显新闻话语的合法性和道德追求。
在丹麦,虽然新闻业没有像拉丁美洲那样受到政府当局的严密控制,但是民粹主义的倾向依然突出,而且成为新闻记者日常工作中一种自觉追求。首先,在记者的信息来源上,丹麦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记者对精英阶层极其排斥。一项针对丹麦800 名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新闻记者的全国性调查表明,97%的受访者认为新闻记者应该有政治责任解决社会问题;94%的受访者认为记者应该在民主进程中帮助公民参与社会事务。这样的思想具有公民新闻的色彩,但是在新闻活动中,却滑向了民粹主义。在丹麦,至少有31%的记者认为他们是没有任何政治影响的人民或社会群体的代言人。[27]当认为自身代表人民的声音时,丹麦新闻组织(记者)的日常新闻报道就会围绕市民展开,不太关注政治机构;他们通常将普通市民作为新闻的基本信息来源,政治人物、专家和其他精英人物的言论与观点在其报道中则甚少出现。其次,丹麦新闻媒体的民粹主义趋向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20 世纪90年代,丹麦地方媒体与首都媒体存在明显差异。历史上的丹麦新闻媒体曾长期与政党保持密切关系,接收其津贴,成为政党喉舌。20 世纪以来,公然以党派面目出现的新闻媒体少之又少,但是首都哥本哈根地区的新闻媒体仍然与政府、政党关系密切,传播社会精英阶层的声音是其主要特征。而丹麦地方媒体(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的新闻记者崇尚直接民主,对政党、政治人物及专家等持抵制态度,具有显著的民粹主义色彩。哈亚沃德(Hjarvad)注意到,与哥本哈根新闻媒体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新闻报道不同,在一些社会亟须解决的问题上,首都媒体将政治精英作为报道对象,而在地方媒体新闻记者的报道中,往往求助于普通市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的报道方面也逐渐对首都哥本哈根的广播电视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很多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新闻栏目像地方媒体一样,日益表现出民粹化倾向。[27]
与拉丁美洲新闻媒体的上述表现以及它们艰难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左右为难并常常受制于当局的严厉管制不同,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体则基本上沿着自由主义的轨迹发展。虽然明目张胆的倾向性不多见,但是带有民粹色彩的新闻报道依然时有显现。只不过,在这种新闻民粹主义中,想象中的“中心地带”——人民已不是其强调的重点,争取更多的受众则成为追求的目标。换言之,这是一种具有突出的市场化导向的新闻民粹主义,往往采用小报化、名流化的文化民粹主义策略迎合读者和观众。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是此类新闻的典型。在日常实践中,他首先强调本人及新闻集团的“反主流”色彩。20 世纪90年代,当福克斯新闻网创办的时候,这种反主流的民粹主义即成为其出奇制胜的商业策略。当时,默多克敏锐地利用美国民众的政治疏离感和对美国主流媒体的极端不信任感,将福克斯新闻网打造成了“一种‘反媒体’(主流媒体)的新型媒体”。[28]与主流媒体将新闻来源锁定社会主流群体、恪守传统的客观性理念不同,福克斯新闻网声称代表普通的美国人,日常新闻活动中观点和评论尤为突出。其次,民粹主义深深扎根于小报传统中,通过小报化的办报风格“反精英”。所谓的“小报风格”是指一种以追求趣味性为主的模式化的新闻叙述风格,同时因片面追求叙事生动而常常偏离了新闻业的客观性标准。小报的内容以名流新闻和流言蜚语取代了严肃新闻,以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趣闻轶事替代了重要的国际性事件。[29]自从1969年购买《世界新闻报》之后,默多克就竭力鼓吹它的平民化色彩,将揭露精英化的社会名流的丑恶一面作为一直坚持的立场,从而赢得了英国民众的喜爱。“民粹”路线,《世界新闻报》在日常新闻实践中是一再宣称的,但事实上,却与民粹主义的思想观念相去甚远,它看重的仅仅是“民粹主义”中“人民”(对于《世界新闻报》而言,这些是它的受众)规模巨大,有利可图而已。恰如媒体人Jeff Sparrow 指出的,默多克经常通过他的新闻帝国标榜他傲慢的“民粹主义”,宣称普通人像他的计算机主管一样出色;他也经常在旗下小报上表达对新移民和拦路抢劫者的愤怒,故意与他旗下的高档报纸和电视唱对台戏,即使在他与传统的保守人士(一般都是社会精英人士——引者注)结成联盟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名声在外的“民粹主义”并非通过直接鼓动读者反对新移民、同性恋者和黑人,而是通过鼓动激起他们的反抗之情。[30]为了达到吸引民众的目的,新闻集团往往无所不用其极,2011年《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事件爆发之前,新闻集团的窃听事件就屡有发生。早在2002年,16 岁的英国流行歌手夏洛特·丘琪(Charlotte Church)就曾遭新闻集团旗下的《太阳报》电话窃听,将其怀孕的消息公之于众。但是事实上,这种表面上的“反精英”、“平民化”、“大众化”却具有两面性。有研究者指出,英国《太阳报》其实比一般的严肃报纸更倾向于精英化,而其所声称的激进的民粹主义仅仅是陪衬而已。[31]这无疑再次表明,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的“民粹化”的最终指向仍然是市场。虽然,政治、文化与市场的要素密不可分,但是从新闻民粹主义的视角看,我们会发现,在欧美新闻业,为了赢得更多受众,获得产业发展,其“新闻民粹主义”已经悄悄地经历了“政治——文化——市场”的逐步演变。
即使是在美国这样“自由主义新闻业的大本营”,带有明显政治倾向性的新闻民粹主义依然存在。20 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天主教神父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先后在底特律的WJR电台、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自己创办的电台主持新闻评论和谈话节目,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迈克·斯考特(Mark Scott)和拉斯·林博(Rush Limbaugh)主持同类节目。前者赢得了4 000 多万听众,后者的听众也有2 000 万之多。三位主持人在新闻评论中,运用多种策略对美国包括总统在内的精英阶层进行讽刺和评论。例如,考夫林就曾在新闻评论中称跨国银行家是“隐藏的、全世界人民的对头”,是“拦在伊甸园入口处的恶魔”。[32]这些评论迎合了特殊历史时期美国民众对利益阶层的愤恨情绪,民粹化的策略使其在普通民众中广受追捧。其实不仅是这些政治意图明显的新闻评论节目,就是上述提到的默多克及其新闻集团,其市场化的新闻民粹主义背后仍然能看到媒体巨头左右政治的强烈意图。
四 新媒体与新闻民粹主义
(一)新媒体的特性使其成为民粹思潮产生的土壤
新媒体是一个歧义纷呈的概念。多伦多大学的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认为,“新媒体允许使用者广泛参与,使用者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而是信息和内容的积极生产者。今天所说的新媒体是指数字化的交互性的媒体,与麦克卢汉所说的电子媒体截然不同。”“总体而言,新媒体是指交互的、双向传播并包含了信息处理技术的数字媒体,是与电话、广播、电视等旧媒体相对而言的。”[33]4-6他认为,新媒体携带了14 种“信息”:“(1)双向传播。(2)易于接近和扩散信息。(3)持续学习。(4)排列与集成。(5)共同体的创建。(6)便携与弹性时间。(7)媒介融合。(8)媒介互用性。(9)内容聚合。(10)多样化、可选择、长尾。(11)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再聚合。(12)社会集体与赛博合作。(13)混合文化。(14)变迁:从产品到服务”。[33]49-72
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杰森教授(Klaus Bruhn Jensen)看来,数字媒体对传播实践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影响:第一,实现了传播面对面;第二,通过技术模拟大众传播;第三,数字技术使网络交互实现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34]
以西英格兰大学的马丁·李斯特(Martin Lister)等学者的观点,新媒体的出现与以下诸多变化密切相连:“第一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化。第二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第三是西方实现了从机械工业时代到后工业信息时代的转变。第四是去中心化和地缘政治秩序的出现。”“20 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传媒看上去与以往非常不同,尽管这种变化在不同媒体间的表现有所不同,但新媒体一词试图抓住迅速变化的这种感觉”。新媒体通常可以表示如下状况:“(1)新的体验。(2)表现世界的新方式。(3)主体(使用者和消费者)和媒介技术之间的新关系。(4)个体、身份和共同体之间的新体验。(5)身体与技术媒体关系的新界定。(6)组织和生产的新模式。”基于以上考虑,李斯特等人认为新媒体具有“数字的、交互的、超文本的、虚拟的、网络的和模仿性的”等诸特点。[35]
依照洛根、杰森、李斯特等人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新媒体的首要特点是可以实现即时相应与即时互动。与单一的传统媒体单向传播、很难实现即时互动的特征不同,利用新媒体,人们很容易及时接收和发送信息,改变了过去被动的信息接收者的地位,成为集信息消费者和生产者于一身的传播主体。
第二,新媒体实现了信息传播的无中介化。在传统媒介环境中,信息传播工具掌握在媒体组织手中,信息传播必须经过传媒组织。因此,各个层级的传媒人既是信息的把关人,也是信息的中介者。新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在新媒体的传播环境中,组织中的传媒人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其用武之地。
第三,新媒体使信息流动加快。当今时代是新旧媒体共存的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使传统媒体上的信息增加了一个信息迅捷扩散的绝佳渠道。人们使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上的新闻和信息加以个性化地改造,同时也在利用身边的新媒体随时生产和发布新闻和信息。
第四,新媒体使传播网络整体表现出信息传播的去中心化现象。以往传播主体(使用者和消费者)和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信息生产者占有主导地位,媒介消费者往往是信息接收者,处于被动境况;传播形态以“点对面”形式为主。然而,在新媒体上,这个中心化的“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数个点,实现了传播的“点对点”、“点对面”和“面对面”的交互式、网格化传播格局。
最后,新媒体促成了传播共同体的出现。虽然詹姆斯·凯瑞推崇“社会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36]3的观点,提出了传播的仪式观,认为研究传播就是为了“考察各种有意义的符号形态被创造、理解和使用这一实实在在的社会过程”[36]16。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不是信息,而是戏剧”。[36]10但是参与仪式的人在何方?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如何与他们共享“参与仪式”的感受?在传统媒体环境中,这些问题虽然并非一定不能解决,但是实现起来确实非常不易。可以说,新媒体的出现,真正使凯瑞所提的“传播仪式”有了现实意义。人们通过新媒体,不仅可以共享意义,而且可以分享参与的感受,可以为了共同的兴趣、目标和所遇到的诸多不同类型的问题,极为便利地与五湖四海的“同好”结为共同体,协同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从传播的角度讲,新媒体是实现传播平等化的最有力工具,也为民粹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在塔格特看来,“民粹主义之中有一个暗示性的中心地区的构想,人民位居于中心地区,民粹主义者赋予了人民以创造性和依靠性的作用”,[10]4而这个“人民”,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在于“它的数量”。新媒体使原本在旧的传统格局中鲜有表现机会的普通民众获得了表达、传播(新闻)信息、个人观点的契机,打破了精英垄断新闻传播的局面。当社会分化严重、不同阶层严重对立的时候,民粹主义随即产生,而新媒体成为培育和扩散民粹思潮的温床。
(二)公民新闻、社会动员与民粹主义
新媒体的特征,促进了人际传播的发展,对于信息流的迅速扩散亦提供了便利。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新闻应运而生。在新媒体环境中,公民新闻既可以单独传播新闻,在具有社会公共性的话题上,又极有可能与社会运动紧密结合。
公民新闻首先具有很强的民间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者杨保军将这种“民众或社会大众以他们自己的兴趣、需求自主传播的新闻”称为“民间新闻”,与组织化的“职业新闻”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经过新闻组织或机构的编辑、过滤”,[37]因此更多民间色彩,更有平民意味。民间、平民不仅是一种社会身份和社会阶层的符号标识,它同时意味着这个群体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是“人民”的合法来源。此种含义使它与民粹主义的想象中心——“人民”不谋而合。
其次,新媒体的开放性使公民新闻具有广泛的参与性。新媒体出现前,在组织化的职业新闻生产、传播过程中几无权力的普通民众自是其主力,而各式各样的社会精英(包括在传统的新闻组织中任职的传播精英)亦成为公民新闻的一部分。在传统的新闻传播中,出于种种限制,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在新闻事件的传播上,存有鲜明的裂缝与鸿沟。但是在公民新闻中,二者却极有可能依照多数人的意愿达成某种共识。
再次,新媒体使信息流动加速、极易聚合的特征,使公民新闻从具有极强的传递效应和扩散性质(微博新闻在这方面表现尤为充分),这无疑使其具备了社会动员的能力。杨保军就认为:“民间新闻的传播者开始超越私人化的传播角色,正在转变为社会化、公共化的传播角色;普通人作为私人和作为公民的角色在新的传播时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身份统一的时代;更能引起人们兴奋的是,普通大众在信息传播领域身份公共化的机会的增多,也为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37]这段话精确地概括了新媒体条件下,公民新闻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无限潜力。
其实在历史上,新闻媒介就曾经为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研究社会运动的权威查尔斯·蒂利就认为:
自18 世纪社会运动刚刚兴起,报纸、杂志、小册子以及其他印刷传媒就在传播运动的消息,它们宣告即将开始的行动,评价这些行动,并对这些行动的成败得失予以报道。当然,20 世纪传播媒介的变革与扩展,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展示。广播、电视、电报、民意测验以及遍布全球的新闻业,都在促使运动、社会运动的表演和WUNC(指的是社会运动中的价 值——worthiness;统 一——unity;规模——numbers;参与者和支持者的奉献——commitment。——引者注)展示发生转型。[38]
与蒂利相似,赵鼎新也将新闻媒体与语言、符号性行为和情感,运动动员结构,政治机会结构一同作为社会运动分析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39]但是在传统媒体的传播环境中,虽然社会运动和新闻报道是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是社会运动的走向和新闻呈现更多地受控于新闻媒体,而不是相反。托德·吉特林在对媒体如何报道20 世纪60年代美国“新左派”学生运动时,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一开始,媒体并不怎么重视运动,继而开始关注运动,接着与之合作,最后以固定的模式来对运动加以表现,这些模式的性质和倾向是不断变化的。”[40]值得一提的是,社会运动,无论政治性的还是非政治性的,有相当一部分都带有民粹色彩。俄国民粹派发动的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运动、美国的平民党运动、欧洲右翼势力的政治运动,乃至美国2009年崭露头角的茶党运动(The Tea Party Movement)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粹化倾向。即使是广为人知的法国大革命,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卢梭的民粹思想是其重要思想资源之一),还是运动过程,诉诸民粹,俱是其显著特征。但是,这些运动在传统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新闻呈现中,却未必彰显运动自身的民粹倾向。这是因为,在新闻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中,无论新闻记者的态度和报道方式如何变化,媒体力图保持和维护的仍然是传统的、保守的、主流的价值观念。但是公民新闻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在异常情况下,公民新闻往往能够成为社会运动的导火索。新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虚拟动员和现实运动的结合,二是新媒体上的虚拟串联。2007年,当PX 项目即将上马的消息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翔鹭集团已在海沧区动工投资(苯)项目,这种剧毒化工品一旦生产,厦门全岛意味着放了一颗原子弹,厦门人民以后的生活将在白血病、畸形儿中度过。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健康!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100 公里以外开发,我们厦门距此项目才16 公里啊!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行动吧!参加万人游行,时间6月1日上午8 点起由所在地向市政府进发!手绑黄色丝带!见短信群发给厦门所有朋友!”[41]这既是一条动员信息,也是一条关于当地民众反对PX 项目运动最新进展的公民新闻。这条新闻随后通过手机和互联网迅速流传,推动了运动的发展,最终促成事件的解决。童兵教授将这种对社会公众有直接影响、参与者众多同时又有强烈利益诉求的事件称为突发群体性事件。[42]西方学界一般将这类突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进行研究。在国内外的此类事件中,虚拟动员和现实运动的结合已经成为常态。值得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社会运动都是民粹主义的,只不过民粹主义在实现诉求的过程中,为求目标实现,常常诉诸社会运动。
相比虚拟动员和现实运动相结合的社会运动,虚拟串联更为常见,也更容易走向极端。互联网等虚拟空间,实际上就是一个狂欢广场。在欧洲,狂欢节的传统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时代。“在狂欢节期间,人们享有可以把平时常常想的事情一股脑儿说出来却不受惩罚的特权”,[43]因此,参与者身份的平等(无等级),情感的尽情抒发(宣泄),颠覆现实、重构理想(颠覆性),与宫廷文化对立、强调民间性(大众化)就成为狂欢节的最主要特点。[44]在狂欢节上,人们(尤其是贵族、教士等特权阶层以外的普通民众)尽情释放自己,抒发个人对现实世界的种种不满,表达对特权阶层的愤恨。虚拟世界里的公民新闻会在传递、转发的过程中不断被重写、修改、评论、放大,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参与者会因观念相似而逐渐串联在一起,最终导致凯斯·桑斯坦所谓的“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极化的群体排除异己、达成一致,对于不同的信息和意见恶语相向,客观上对参与信息生产的人做出“我们”、“他们”的二元划分。恰如当年俄国民粹派所宣称的那样:“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加以消灭。”[45]在现实语境中,越是与权力阶层充满对抗、言辞激烈的新闻信息和极端言论,越容易在虚拟空间获得认可、赞誉和转发。在这些人看来,“我们”来自社会的草根阶层,是代表着人民的正义一方,充满道德优越性,而作为“假想敌”的“他们”则是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特权人物。杰克·凯等人曾经概括了考夫林等人在进行民粹主义式的新闻评论时,通常使用“洗牌作弊”、“感同身受”、寻找“替罪羊”、“谩骂及偏狭”、“简化及歪曲”[32]等手段和方法吸引更多公众,陈龙也认为,民粹主义者会有意识地采用“扣帽子”、“谎言”、“谩骂”、“渲染”、“限制不同声音”[46]等手法实现话语垄断的目的。这些民粹主义的话语方式在当前的虚拟空间中可谓司空见惯、比比皆是。
客观地讲,公民新闻引发的虚拟串联有其积极的一面。在虚拟世界中,公民新闻有时候表现为对主流新闻的解构,这种解构充分体现了公民新闻的创造性和价值观。2009年的“天价烟局长”、2012年发生的延安重大交通事故中的“微笑局长”等社会事件,当事人本来是作为普通新闻人物被呈现的,但是公民新闻的生产者却通过自己的经验对其重新解读,将“天价烟”、“天价表”、“微笑”等传统新闻媒体不予关注的新闻要素通过互联网进行传播。而且有数量可观的人参与其中,将发掘出新的信息,不断地进行整合和汇聚。注意到常规新闻要素以外的“枝节”的背后,映射的是普通公民对特殊阶层的不满。由此可见,公民新闻和社会运动并非必然是民粹主义的,它既可以成为促进舆论监督和民主发展的利器,而在极端情绪的渲染下,也可以成为潜伏着巨大危害的民粹主义运动。
五 结语
拉克劳(Ernesto Laclau)认为,“民粹主义”概念中有“我们”和“一再发生”的含义。它既可以从运动和意识形态混合的层面进行理解,也可以单纯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分析。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民粹主义表达了一种对现状不满的情绪,对政治人物充满不信任感,反对精英,具有非理智化的倾向,以上诉求对人民充满了吸引力。[47]“我们”当然指的就是“人民”,是与精英对立的平民——农民、城市下层劳动、边缘社会群体。之所以强调精英与平民的二元对立,是因为民粹主义者看到了二者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更多的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平等观,即“作为取消权力和财富分配差异的结果平等观”;而非权力平等观——“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尊严和价值的平等观”。[48]相比权利的不平等或平等的隐而不彰,结果的不平等和平等更加显而易见,民粹主义者诉诸结果平等的思想,赢得了更多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民粹主义的民主观颇多理想色彩,强调主权在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而不是仅仅拥有选举权利,听任政治精英的摆布。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视野中的“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对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民主则是坚决拒斥。
正是在以上民粹思想的影响下,产生了新闻民粹主义。新闻民粹主义是新闻活动主体极端价值观念的体现,与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客观性、中立性、平衡性等理念不同,它“天然地排斥受过专业训练、掌握专业知识、拥有专业权威的人,其核心在于要求新闻业体现与普通公众的联系,一是代表公众,反映底层人民的疾苦;二是参与社会行动,帮助底层人民解决实际问题。”[49]在它的观念中,是价值先行,价值偏向和情感偏向远比新闻的客观呈现更重要,因此,新闻民粹主义者喊出“首先是激进分子,其次才是记者”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日常新闻采写中,常常将社会精英阶层尤其是专家作为权威的新闻来源不同,新闻民粹主义则将以上权威看作是现行体制的合谋者,统统将其排斥在外,而是以传达底层声音作为工作的核心。
新闻民粹主义的形态:(一)如果从媒体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两类:第一是作为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工具的新闻民粹主义。拉丁美洲的新闻业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此外,德国、荷兰、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右翼色彩的新闻媒体亦表现出民粹倾向。其中,尤其以迎合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民粹主义新闻最为引人瞩目。第二种是作为商业手段以市场为导向的新闻民粹主义。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新闻媒体遭遇了严重的发展危机,在这样的情况下,欧美发达国家的报纸、广播电视有意识地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商业策略,以迎合广大受众,企图依此改变传统新闻业萎靡不振的现状。但是,这种民粹主义也非单纯仅具商业色彩,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报纸中推行的市场化民粹路线,就潜藏着明显的政治意图。(二)如果从直接的传播主体的角度看,亦可分为两类,第一是以知识分子面目出现的少量新闻记者的民粹主义。俞可平认为,“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地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产生民粹主义的直接原因通常是社会的不公正,政府的腐败,政府的无能,特别是公民对政府的失望”。[50]其实从英美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报业民粹实践看,新闻民粹并非一定要排斥现代化尤其是市场化。但是在现代化进程尚未完成,社会转型正在进行中的很多国家而言,现代化和转型意味着社会阶层的重新划分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此过程中,社会底层的利益极易受到侵害,普通民众心中充满不确定感,民粹主义情绪随之潜滋暗长。有知识分子道义追求的少量新闻记者对这样的社会转型感觉尤为敏锐,常常自觉地将底层利益和价值诉求作为新闻活动的主要目标。第二是新媒体上普通公民新闻中的民粹主义。如果说,在传统媒体上,新闻民粹主义表现为精英分子(政治精英、社会精英、媒体精英)的有意识设计和规划的话,那么在新媒体上,个体的公民却代表“人民”进行新闻生产,与社会运动结合的公民新闻具有较强的民粹倾向。
概而言之,新闻民粹主义既有很强的价值观指向,又有很强的工具色彩。这使它成为各个场域积极争取的话语资源。虽然我们都知道,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新闻理念,新闻专业主义在国际新闻业中赢得了普遍的认同并成为部分新闻从业者内在的不懈追求,但我们依然清楚,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与挑战,民粹主义即是其中之一,它挑战的不仅是新闻业的理想,也对其日常实践构成了威胁。从这个角度看,深入探讨新闻民粹主义,对于促进全球新闻业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J].Political Studies,Volume 47,Number 1,March 1999:2-16.
[2]吉姆·麦克盖根.文化民粹主义[M].桂万先,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著,[美]托马斯·兰敦·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M].刘 山,等译.南木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4][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M].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5]陈 龙.Web2.0 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J].国际新闻界,2009(8):77.
[6]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M].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56.
[8]佚名.民粹派基本纲领[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553.
[9][俄]亚·瓦·多尔古申.致俄罗斯人民[M]∥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43.
[10][英]保罗·塔格特.民粹主义[M].袁旭明,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11][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下卷[M].王 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2]陆 扬,王 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3][英]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3-75.
[14]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02-103.
[15]霍 尔.编码,解码[M]∥罗 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356-358.
[16][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240.
[17]Mitchell Stephens.A History of News[M].Fort Worth: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7:191.
[18]西尔维奥·韦斯波得.南美洲的媒介:在政府和市场间左右为难[M]∥[英]詹姆斯·卡伦,[韩]朴明珍编.去西方化媒介研究[M].卢家银,崔明伍,杜俊伟,王雷,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19]Silvio Waisbord.Democracy,journalism,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J].Journalism,2012(10):1-18.
[20]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161.
[21]Doris FagundesHaussen.Radio and Populism in Brazil:The 1930s and 1940s[J].Television New Media,2005(6):251.
[22]Rosenberg.Martín García,el cruzado K quedirige la agenciaestatal de noticias.La Nación (Argentina),21 November,2010.转引 自Silvio Waisbord.Democracy,journalism,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J].Journalism,2012(10):1-18.
[23]Sandoval.Somosperiodistassandinistas.el19digital.com,11 September,2009.转引自Silvio Waisbord.Democracy,journalism,and Latin American populism.Journalism,2012(10):1-18.
[2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约翰内斯·温克尔曼整理,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
[25]Taylor C.Boas.Television and Neo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Media Effects in Brazil and Peru[J].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2005,40(2):27-49.
[26]林 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42.
[27]TanniHaas.Importing Journalistic Ideals and Practices?The Case of Public Journalismin Denmark[J].The Har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2003(8):90-103.
[28]David McKnight.The market populism of Rupert Murdoch[J].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2012(8):5-12.
[29]姜 华.市场新闻业与传媒边界[J].新闻记者,2011(9):8-12.
[30]Jeff Sparrow,Australiaand the Dirty Digger:The Phony Populism of Rupert Murdoch[OL].http:∥www.greanvillepost.com/2011/07/15/australia-and-the-dirty-digger-the-phony-populism-of-rupert-murdoch/.
[31]Tjitske,Akkerman.Friend or foe?Right-wing populism and the popular press in Britain and the Netherlands[J].Journalism,2011(12):931-945.
[32][美]杰克·凯,乔治·W·西盖尔穆勒,凯文·M·敏奇.从考夫林到当代谈话电台:美国民粹主义电台的宣传策略[J].夏倩芳,译.新闻与传播研究,1999(4):84-95.
[33]Robert K.Logan.Understanding New Media Extending Marshall McLuhan[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Inc.2010.
[34]Klaus Bruhn Jensen.Media Convergence The three degrees of network,mass,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New York:Routledge,2010:4-5.
[35]Martin Lister,Jon Dovey,Seth Giddings,Iain Grant & Kieran Kelly.New Media A Critical Introduction,Routledge,2009:10-12.
[36]詹姆斯·凯瑞.作为文化的传播:“媒介与社会”论文集[M].丁 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37]杨保军.新闻的社会构成:民间新闻与职业新闻[J].国际新闻界,2008(2):30-34.
[38][美]查尔斯·蒂利.社会运动:1768-2004[M].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6-117.
[39]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7-45.
[40][美]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M].张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5.
[41]张晓娟.厦门PX 危机中的新媒体力量[J].国际公关,2007(5):46-47.
[42]童 兵.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与大众传媒社会责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
[43][英]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M].杨豫,王海良,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21.
[4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264.
[45]苏 文.不要民粹主义,但能要“精英主义”吗[J].读书,1997(10):43-47.
[46]陈 龙.网络民粹主义的话语垄断策略[J].苏州大学学报,2011(6):157-162.
[47]Ernesto 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Capitalism,Fascism,Populism[M].New York:Verso Books,2012:143-147.
[48]刘军宁.平等的理想精英的现实[M]∥巴特摩尔,著.尤卫军,译.平等还是精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
[49]谢 静.民粹主义:中国新闻场域的一种话语策略[J].国际新闻界,2008(3)34.
[50]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J].战略与管理,199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