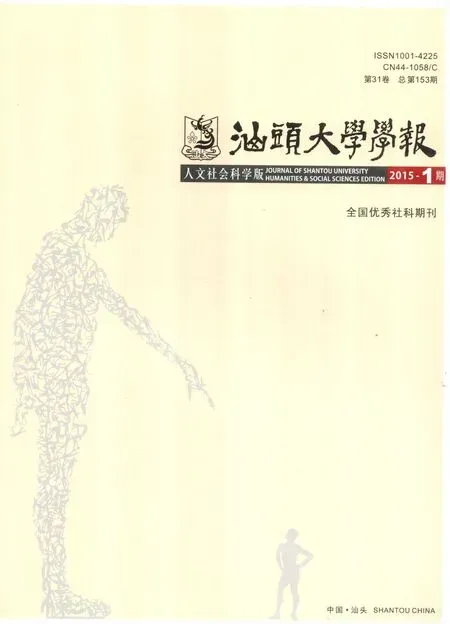论周朴园的精神救赎之路
陈旭东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合肥 241003)
论周朴园的精神救赎之路
陈旭东
(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安徽合肥241003)
《雷雨》中主人公周朴园的生命历程是宗教性的救赎之路。借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宗教精神就是超越现实自我的自由超我,周朴园的情欲就代表着本我,儒家规范代表自我,基督教的博爱与自由代表超我。以儒家伦理为代表的传统无力化解与升华恶的欲望,这样个体中内在的情欲没有合适的实现途径。周朴园先是在自我与本我的斗争中痛苦挣扎,再经过乱伦与绝种这种对自我的彻底摧毁,最后进入博爱的宗教境界,获得精神上的新生与自由。周朴园的救赎之路也体现了《雷雨》对具有文化原罪的传统如何拯救的思考。
《雷雨》;周朴园;宗教精神;救赎
一、引言
曹禺的经典话剧《雷雨》通常被看作是一部伦理压迫或命运捉弄下的悲剧,其主人公周朴园则作为一个专制家长的负面形象出现。评论者要么从社会政治的层面把周朴园定性为导致悲剧的凶手,要么从道德审判的角度谴责其虚伪与邪恶。即使对他有所同情的评论,也主要是因为他最后忏悔了。但很少对他给予深刻的同情式理解,很少从超越道德的精神的高度来评价。这种对周朴园的不全面把握很容易误解《雷雨》的主题,因为“理解《雷雨》全部意义的关键在于明确意识到周朴园的存在并对他的典型意义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离开他,全剧就会变色;离开他,就将失去评判所有其他人物的主要客观依据。”[1]本文在王富仁这个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周朴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家长形象的体现,他的种种罪错体现着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问题,他的结局是《雷雨》对当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传统如何找到出路的探求。周萍、周冲、鲁大海喻示着周朴园自己人性的不同方面朝各自方向发展的可能结果,他们三人的死亡或失踪表明周朴园只有一条宗教意义上的救赎之路可走。最终他成为基督徒象征着他精神的复活,即从儒家的名教束缚中走向博爱,走向摆脱一切世俗羁绊的精神自由。于是,周朴园的救赎之路也是《雷雨》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可能出路的思考。
1945年时吕荧就曾提出“超然的社会学立场”与“纯正的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立场”两种理解《雷雨》的视角。张耀杰提出用前一种视角可以“从高层次、高境界上解读《雷雨》”,他通过这种“超然的社会学立场”让我们看到了在“天地间残忍主宰的施虐”下周朴园脆弱的一面。[2]150而从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角度来理解《雷雨》就更具体地体现了这种超现实视角。宋剑华曾从基督教道德层面来描述与曹禺作品的关系,他认为,《雷雨》悲惨的结局是《圣经》劝善惩恶教义的体现,并引用了许多《圣经》原文作为依据。[3]248但这些只是宗教与《雷雨》表层的经验意义上的联系。其实,宗教精神并不同于世俗意义上的宗教,它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本文就是从这种宗教精神的角度来讨论作品与宗教的深层次联系。笔者认为,贯穿《雷雨》始终的是周朴园的精神救赎过程。这种宗教救赎是超越实用主义的,序幕与尾声就起到了这种超越作用,它使《雷雨》提升了精神境界,从而使周朴园具有了宗教救赎的意义。
二、《雷雨》中的三重人格结构
对于宗教精神在神学与哲学上有着众多的阐释角度。本文试图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宗教观来谈周朴园的救赎。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了理性神学理论,他认为信仰是建立在理性与道德之上的。而理性与道德以自由意志的运用为基础,人可以凭借自身自由意志的运用可以不受感性冲动与现实利益的束缚,不断趋向至善,也就是趋向自由。所以康德把基督教解释为一种自由宗教。进而康德认为,人可以通过自由宗教达到超越世俗羁绊的超我境界。相比于道德上的惩恶扬善,宗教使人提升为超我境界的作用显然更具有意义。
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儒家的自我很难产生超我。本文所说的儒教是指长期统治国人的思想,与社会一体的建制化的名教与礼教,而不是指存在于文本中理想化的儒学。这种儒教对大多数中国人起着准宗教作用,其统治下的人都缺乏独立人格,所谓的人只是在纲常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并按相应的名分来服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周朴园对周萍说:“那我请你为你的生母,你把现在的行为完全改过来。”对儿子用了“请”,似乎在尊重他,但改过是为了长辈,其根据在纲常关系。他还说:“苦的事你成么?要做就做到底。我不愿意我的儿子叫旁人说闲话的。”“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不让旁人说闲话成了判断行为的标准。
而且,儒家的忏悔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实用主义式的反省,其目的是为了剔除良心的不安,而非更高意义上的自我提升或拯救。周朴园自己说得很清楚:“这于我的心也安一点”,“算是弥补我一点罪过”。于是,内心的痛苦和矛盾就最终消解在对外在伦理规范的认同与肯定中。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基督教视所有的人为上帝的子民,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名分与等级的差异。原罪、忏悔都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每个人天生都有罪,基督教的忏悔不同于儒家的内省,它讲究直面内心的痛苦,忏悔的人内心经常有灵魂的激烈搏斗。这种对世俗自我的否定就容易产生精神上的超越。所以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把基督教称为自由宗教。
我们还可以用弗洛伊德的人格三结构学说,即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的冲突与协调来理解这种超越精神。于是,《雷雨》中的情欲冲动代表本我,儒家规范代表自我,基督教所象征的超越世俗的自由博爱精神代表超我。在这种视角下,蘩漪是情欲本我大于现实自我的象征;周萍是在本我与自我之间摇摆;周朴园是自我压抑住本我;鲁大海是被左翼的阶级规范所主导的自我,而看不到本我的影子。这些人身上都是没有超我的,只有周冲有点超我的影子。我们知道,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有着政治实用主义的倾向,儒家自我伪装成超我,导致自我与超我的同一,所以儒教成为皇权专制的思想基础不是偶然的。当然,周朴园的罪错并不应该完全由儒家来独自承担。儒家的伦理规范压制了自然的本我,同时又产生不出自由的超我。儒家伦理无力化解与升华恶的欲望,这样个体中内在的情欲没有合适的实现途径,而没有超我的要求,自我看起来很稳定,其实内部有着根本矛盾。
这种矛盾在周朴园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他苦心维护着夫权、父权、体面秩序等儒家核心价值,换来的结果却是子女乱伦与绝种。周朴园训斥周萍时曾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我的儿子我也认为是健全的子弟”。儒教非常注重家族内部的秩序与外部形象的体面,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当然也是周朴园的理想。而且他积极入世进取,从容应付乱局。比如他在处理罢工事件时,很善于玩弄权谋,采取了镇压、收买、开除、分化瓦解等措施,很快使工人复工。但在这种家庭里是没有感情交流的。所以《雷雨》中有着婚姻关系的,不管是周朴园与蘩漪还是侍萍与鲁贵,都只有夫妻的名分而没有真情。这并不是说婚姻关系里就没有真情了,而是说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束缚下,原本应该感情最深的夫妻之间变得有名无实。反而像周朴园与侍萍、蘩漪与周萍、四凤与周萍之间被儒教认为不合法的关系都有真挚的爱情。在儒教统治下,人与人之间丧失了自然感情,只有名分上的感情。所以第四幕开头周冲对周朴园少见的关心感到意外:“您平时总像不愿意见我们似的。您今天有点奇怪”。这也反过来说明周朴园平时很少关心儿子。
强迫侍萍喝药一节精彩地描述了儒家父权主义道德的真面目。周朴园一再强调说这是为妻子好、为家庭好,并对周冲说,“你同你母亲都不知道自己的病在哪儿。”最后让周萍跪劝她喝药。这种以一己之欲强加于人的思想正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体现。他们“以仁慈、宽厚、体贴的面目,体现着中国传统伦理的专制性和任意性。父母和父母官对儿女和子民们滥施淫威,均可振振有词地说成是为你们好”。[4]150而且这种父权主义不仅严重伤害了周萍蘩漪周冲三个人的心,最终其实伤了自己,使自己一步步走向孤立,也是导致蘩漪后来激烈反抗的关键环节。
《雷雨》中的罪魁是周朴园,最初他与侍萍未婚私通,然后赶走侍萍才发生了后来一连串的悲剧。然而,他又经历了最多的苦难,自己的妻子与儿子乱伦,妻子与情人发疯,两个儿子死亡,还有一个儿子公开与他作对后失踪。对一个儒家文化下以家庭体面秩序和传宗接代为重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受的苦难更重呢?所以说周朴园既是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又是它的受害者。《雷雨》不仅把他刻画成一个恶人,更是一个罪人,甚至富有悲剧色彩而值得同情。在他里面包含着最多的内心冲突,但他又无可奈何,所以曹禺才说他“遇事希望着妥协、缓冲、敷衍”。只有彻底的罪孽与苦难才能迫使他颠覆自己原来的一切,逼得他寻找一条新路,这只有通过赎罪。曹禺让周朴园不死,而且独自一人清醒地活了下来,也是为了有赎罪的机会。周朴园最后昄依基督教,成为教徒象征着他得到了救赎。所以耶稣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圣经·以西结书》33章)
三、可能的救赎之路
周朴园的救赎过程并不是受到打击后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层层积累与递进,最后水到渠成的过程。《雷雨》的深刻性在于,它不是简单地判断周朴园的结果只能如此,而是先为我们提供了几种可能的出路,并表明了它们都将失败。具体来说,周朴园的三个儿子周萍、周冲、鲁大海分别代表了周朴园出路的三种可能路径。
周萍如同年轻时的周朴园一样,开始很有激情,正如蘩漪所说:“你说你恨父亲,你说过,你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但后来周萍的回答说明了一切:“你忘了,那是我年轻,我的热叫我说出来这样糊涂的话。”“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这时周萍又成了儒家的顺民。他为了摆脱与蘩漪的畸恋,希望携四凤私奔来实现自我救赎。结果从与后母偷情到与妹妹乱伦,罪越陷越深,只有以自杀了结。周萍只能在本我与自我之间动摇,根本没有超越自我的可能。
周冲有很多不同于周公馆氛围的幻想,也有些实际行动,比如试图与鲁大海握手,慷慨地让四凤跟着周萍。但年轻时的周朴园也不会比周冲逊色,他在德国留过学,他训斥周冲的一句话说明了一切:“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对于这方面,自命比你这半瓶醋的社会思想要彻底得多。”表面看周冲之路的失败是脱离现实的幻想,没有韧性,所以很容易被现实击碎。其实是没有对儒家自我之根作彻底的反思与转化,想绕过“自我”的“超我”只是美好而脆弱的“夏天里的一个春梦”,失败是必然的。
鲁大海与周冲的耽于幻想正相反,他与周朴园一样有强大的自我,而且构成其自我的似乎不是儒家规范。比如他注重通过现实斗争来改变世界,阶级性明确,一开始就要四凤离开周公馆,对她说,“这不是你住的地方”。周冲因为是周家的人,所以他一定要把钱还周冲,还说他“虚伪,假慈悲”。他还喜欢用枪解决问题,多次用枪命令鲁贵。受了周萍一巴掌后就想用枪打死他,报复心重,做事彻底,骂周朴园“绝子绝孙”,身上充满刻毒的恨。表面上看,鲁大海与周朴园有着截然相反的理念,但他明确的阶级性不是儒家重名份重等级的体现吗?他只重现实斗争不也是“外王”过度发达的结果吗?他从来不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更是专制精神的体现。作为建制性的儒教早已渗透进了最有反抗性的鲁大海的骨子里。在他身上最不可能有超我出现,所以他最后失踪迷失了方向,出走后十年间连自己的母亲也不回来看望。联系当时的现实,这似乎显示了曹禺潜意识里表达了对左翼道路的担忧,隐约中预言了日后左翼运动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蘩漪其实是周朴园心中被压抑的作为情欲的本我。从赶走侍萍开始,周朴园心中的本我一直被自我压抑着,但时不时的会起来反抗,他要以纪念侍萍的方式来安抚一下本我的要求。但他又不能让情欲太过份,要采取压制措施,所以周朴园曾多次说蘩漪有病,通过给她看病吃药的方式来压制本我。病象征着对秩序的破坏和对自我的反抗。他还说周冲有病,这似乎很不讲道理,周冲非常青春健康怎么会有病?但我们知道周冲是周朴园潜意识里超我的象征。自我要控制一切就不能让超我太活跃。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让蘩漪看病吃药是他专制性的体现,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常常是复杂的。最后蘩漪固执地要让本我胜利结果却落得个发疯的下场,就表明没有超我只靠本我来战胜自我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喝药这一情节显示了周朴园自己已觉察到内心的激烈冲突,他似乎在想办法找到出路。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吃药看病这么在乎。而且中医不够还要请西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鲁迅的小说《药》,其效果正如华老栓用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一样会注定失败。在保持儒家自我不变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达到和谐?不过周朴园这位留德人士当然比华老栓高明,他或许已感觉到中医所代表的传统并不那么可靠,所以又请德国的西医克大夫来看病。这喻示了周朴园由中向西的求索以及接受西方传教士所传基督救赎之路的可能。还有《雷雨》序幕里说,周公馆屋中间的“门身很笨重,上面雕着半西洋化的旧花纹。”这似乎显示了周朴园留学德国受到的西方文化熏陶只是装饰,影响是外在的,他身上流着的还是儒家文化的血,笨重的传统才是生命的根。
周萍、周冲、鲁大海、蘩漪的失败表明,“超我”不是那么容易产生的,这几条道路都绕过或越过了儒教“自我”,所以都走不通,只有对这个根本性的“原罪”进行彻底清理才是希望之路。
四、痛苦与挣扎
周朴园的大半生都是在儒家自我与情欲本我之间的挣扎中度过的。现实行为上是自我占据优势;而内心则受到本我的不断反攻。他年轻时与侍萍相恋后因家长压迫与门第观念赶走侍萍,情感就处于压制状态。作为心理补偿他一心按儒教入世要求专注于事业,情感世界就渐渐封闭,所以冷漠地对待妻子儿子。这种对人对己的情感压制是为了证实自己当年选择的正确性,又是一种精神自杀过程,这就是礼教杀人杀己的必然逻辑。
周朴园对侍萍的感情是不是虚伪的?对这一问题一直有很多争论,原来多数都认为他的感情是虚伪的,但陈思和等研究者指出周朴园对其是有深厚感情的。从常理来看,把儿子取名为萍来纪念生母,多次搬家仍按侍萍当时的原样陈设,把她的照片放在桌上,保留着她夏天关窗的生活习惯,还有重逢时告诉侍萍的话,这些言行表明周朴园当初决不是出于玩弄而始乱终弃的。侍萍说,“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可见侍萍也承认是“你们”,即周家的长辈的集体行为。当侍萍说她能抱走第二个孩子是“你们老太太看着孩子快死了,才叫我带走的”,我们可以知道周朴园的母亲可能起了关键作用,当然并不意味着周朴园就没有责任了。正因为周朴园知道自己对不起侍萍,才会采取种种方式来进行心理补偿。对两任妻子的冷漠与心里忘不了侍萍有重大关系。因此四凤才说“我怕老爷念经吃素,不喜欢我们侍候他,听说老爷是一向讨厌女人家的”。既然有这么多证据表明周朴园的真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认为他虚伪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周朴园怀念侍萍的方式是外在的、仪式性的。周朴园出于真心的怀念走向了不自觉的虚伪,实际上转化成了虚情假意的行为。这是因为他是按照传统儒家礼的规范来行事的,所谓礼到即可,这种礼容易沦为维持身份与面子的做戏,结果却丧失了内心的实质感情。在儒家伦理的渗透和参与下,“用道德内省的方法处理忏悔往往让灵魂的拷问沦为肤浅的道德表演”。[5]297这有点类似某种传统故事原型,老二篡位杀了老大之后,再给予他风光下葬的仪式来作为补偿。这种补偿企图去消除篡位谋杀所带来的负罪感,让自己相信自己不是忘恩负义之徒,而是有道德的。这种礼的仪式之所以广受欢迎,在于它不仅欺人,而且可以自欺,让人似乎可以心安理得一生。
在儒家礼教的统治下,周朴园对侍萍的怀念与愧疚无法向人诉说。所以他“除了会客,念念经,打打坐,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人性与非人礼教的冲突一直潜伏着,内心的孤独痛苦体现了一个儒家思想受害者的形象。周朴园30年来一直在对侍萍的怀念、良心的不安、维护个人与家庭的体面之间挣扎,所以他有很多矛盾行为。周朴园心里虽然怀念侍萍,但意外见到她时却又是一连串的严厉质问“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里来了”。因为觉得侍萍的出现是对自己体面的冲击,反应才如此强烈。体面最重要,所以儒家式的反省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但平静下来后,他问道:“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么?你看这些家具都是你从前顶喜欢的东西,多少年我总是留着,为着纪念你。”“一切都是照着你是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这些话当然有可能出于稳定侍萍情绪的策略考虑,也的确表达了真实想法。接下来又要把鲁贵和四凤辞退,“以后鲁家的人永远不许再到周家来”。这是他30年前赶走侍萍以来一贯以体面为重的做法。在顺利处理完这个意外后,半夜周朴园“无意中又望见侍萍的相片,拿起,戴上眼镜看”。他独处时又流露了真实的自我。半夜两点时他还不放心询问仆人给侍萍寄钱是否办妥。然后感到很寂寞,“怎么这屋子一个人也没有?”看到周冲马上面露喜色,知道周冲找母亲转而失望,用很多问题来关心周冲。后来他又教育周萍好好照顾侍萍,“我对不起你的地方,他会补上的”。
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发现,原来周朴园心里被压制的情感渐渐抬头,这些都是因为见到侍萍发生的。表面上他果断干练地处理了麻烦,其实他当时的言行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侍萍震撼了他的心。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以侍萍为导火线才能攻破他的礼教防线,与侍萍的见面成为他复活的转折点。周朴园与侍萍见面的情节表层上是他作为一个家长应付自如与虚伪的体现,潜层上是内心儒家自我与真情交织挣扎的过程,这就为最后的彻底忏悔作了铺垫。
当鲁大海骂周朴园“你发的是绝子绝孙的昧心财”,周萍与仆人一起打大海时,周朴园厉声说“不要打人”。此时他的内心一定是很不好受,很痛苦的。无论鲁大海说的“你故意淹死了两千二百个小工,每一个小工的性命你扣三百块钱”是否属实,他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儿子心情肯定是异常复杂的。无论就人类的普遍感情还是儒家对父子关系的重视来说,周朴园对这个儿子肯定具有天然的父爱的,可偏偏又不能相认。但矛盾的是,这个儿子又注定是他的最大对手。“不要打人”既是他深沉之爱的表达,又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唯一能做到的帮助这个没有名分的儿子的无奈之举。在鲁大海走了之后,他又训斥了周萍“你太莽撞了”,这也是对大海之爱的一种变形表达。鲁大海这个人物的设计是很巧妙的,儿子是传宗接代最合法与最可靠的唯一代表,可现在周朴园不能认他,他这个体面人物和一家之主连亲生儿子的名分都给不了。而且大海一辈子都不知道他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真相快被揭露时侍萍叫他去外面叫车,他回来时却跟仆人打架,周朴园主动要他进来时,他却跑了。假如他进来,在两个儿子都死的乱局下,周朴园肯定会尽力与他相认的。曹禺应该有意安排让鲁大海终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周朴园,这种对儒家伦理关系的嘲讽更是让周朴园痛心。整部剧中鲁大海对周朴园的心理打击可能是最大的,因为在儒家思想中父子关系是一切伦理关系的起点与核心。
当侍萍发现四凤重回周公馆并爱上了自己的亲哥哥,她发出了“天哪”的惊叹。当得知四凤怀上了周萍的孩子,面对自己的亲生儿女想出走而苦苦哀求时,她有一长段独白。她首先认为孩子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他们是我的干净孩子,他们应当好好地活着,享着福”。然后罪责在己:“我一个人有罪,我先走错了一步”;“冤孽是在我心里头,苦也应当我一个人尝”;“天真有了什么,也就让我一个人担待吧”。这一大段自责有因果报应思想的流露,更主要是出于母爱为自己的子女开脱而宁愿一个人来承担一切。这段独白的关键其实是第一句话:“啊,天知道谁犯了罪,谁造的孽!”这句话首先出口,是侍萍的本能反应,道出了她心里对命运的不解。接下来的话表面看来是在回答是谁犯了罪,其实侍萍自己也不相信这个答案。所以她在表达孩子的无辜和自责时语义上多有重复,是她有意来宽慰和说服自己而内心充满了困惑的体现。曹禺写出了侍萍多层次的微妙心理,这句话既是侍萍对命运不可捉摸的感叹,也为最后周朴园超越自责直面根本罪过的忏悔作了铺垫。
“有些事简直是想不到的,天意很有些古怪,今天一天叫我忽然悟到为人太冒险,太荒唐。”周朴园已开始发现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儒教思想已在他心里摇摇欲坠了。他还沉重地对周萍说:“萍儿,你原谅我。我一生就做错了这一件事”。这句话虽然是在他误以为无法隐瞒真相的情况下所说,但道出了积压在心头的隐痛,的确是肺腑之言。随后他又对侍萍说:“我老了,刚才我叫你走,我后悔。”结合周朴园半夜面对周冲就流露出的脆弱,我们可以知道他已从保持心理平衡式的反省开始走向彻底的忏悔。
五、复活
第四幕结尾时,周朴园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相继死去,发出了“天!”的悲叹。妻子与儿子乱伦,再加上绝种,这是对儒家核心价值的父权与夫权的绝妙讽刺与对儒家纲常秩序彻底的颠覆。这就是周朴园30年来以礼教原则苦心经营的成果。这种悲惨结局是他为一直维护的儒家礼教规范所付出的代价。随着巴赫圣乐的响起,周家只剩孤零零清醒着的周朴园。“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自己——情感的或理性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机遇的或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骄傲着,以为是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做着最愚蠢的事么?”[6]355这是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感叹,更是周朴园救赎之前的写照。这种命运之罪使周朴园的救赎更具有了一种迫切性。
曹禺在《雷雨》序里说序幕与尾声是为了达到艺术上“欣赏的距离”之效果。其实对观众来说是拉开了欣赏的空间距离,而对周朴园来说则是十年彻底反省的时间距离,是灵魂炼狱的过程。由于戏剧体裁的限制,我们无法知道周朴园激烈的心理冲突到底是怎样的,只是留下了让我们自己来想象的余地。“我更恨人群中一些冥顽不灵的自命为人的动物,他们偏若充耳不闻,不肯听旷野里那伟大的凄厉的唤声,他们闭着眼,情愿做地穴里的鼹鼠,避开阳光,鸵鸟似地把头插在愚蠢里。”[7]375所幸的是周朴园以感情上与精神上巨大的苦难为契机开始了忏悔,从恶人变成了罪人,从儒家的表演式忏悔到对自己原罪的彻底拷问,已经不是一只鼹鼠了。
周朴园最后无妻无子,不知道他从何而来,要回哪里,没有一点家的讯息。他是孤独的,摆脱了一切依附性的伦理关系,无法再从世俗的亲情关系或事功中获得安慰。在上帝面前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每个人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个人。这样他才能成为上帝面前的独立个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当然这不是说有家的人就不是自由人了,只是说周朴园原来的传统包袱太重,只有通过彻底清理原罪才能获得自由。那他现在是不是一无所有了呢?他有了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爱,虽然这是付出极大代价换来的。他现在心里先想着看望侍萍,也没有忘记蘩漪,10年间还一直在寻找鲁大海。而且他已超越原来狭隘的情欲之爱,进入博爱的高境界。
同样在这个周公馆,10年前曾发生过鲁贵的市侩行径,母子偷情,家长横行,兄妹乱伦。而现在它已成了教堂医院,等级与名分的儒教世界已烟消云散,代之以基督宗教世界的自由宁静。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儿童无忧无虑的玩乐,过去的乱伦故事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笑话。唯有两个疯女人提醒着大家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人同鲁贵那样窥探与猜测他人的隐私,两位修女以为周朴园每次都来看侍萍是因为鲁贵曾在周家当差,她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与自己有丁点关系的人也需要去关怀。更没有人会为利益或情欲中挣扎了。在这个自由的世界里,周朴园也变得没有机心。序幕尾声里周朴园的形象是很微妙,曹禺用了“迷惘”、“失神”等词来形容他,对话时他也有些迟钝,这当然是年老与过去创伤的影响。不过还有另外一面,他“眼睛沉静而忧郁”,说话用“沉静”的语气,可见心里充满安宁。开幕时,“外面远处有钟声。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幕落时,周朴园“呆呆地望着火”。姑乙“拿了本圣经来读。”在世俗眼里,周朴园是落寞的;但他们不知道,他在静静地倾听超越凡俗的声音,在静穆中迈向救赎之途。
如何从具有原罪的文化传统中真正走出来一直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思考的主题。以鲁迅为代表的通过个人心灵的忏悔与文化传统的忏悔相结合是很多文学作品的主题模式。曹禺创作《雷雨》时是1933年,当时才22岁,作为五四一代的后辈,他继承了他们的精神脉络,也试图通过审视西方文化来寻求拯救之路。但他比五四前辈们激进反传统的观点似乎要更成熟,他深入到了自身传统内部进行剖析,而不是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外在的否定。
他以同情的笔触刻画了周朴园的罪与罚,展示了其不仅是社会与文化悲剧的制造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周朴园身处的文化传统同他本人一样,以现实的礼制压制人的自然情欲,同时又阻止任何超越性的自由精神的出现。周朴园最后得到了救赎,也象征着他所承载的文化传统有了新生的机会。周朴园从一个儒教的信徒重生为一个具有基督教博爱精神的自由人的救赎过程喻示了带有精神原罪的民族如何得到救赎这一议题。曹禺对传统文化原罪的深刻同情与彻底忏悔至今是我们学习的遗产。《雷雨》让人憧憬的不是周冲脆弱的幻想,而是在悲天悯人的情愫下隐含着的希望之路。
[1]王富仁.雷雨的典型意义和人物塑造[J].文学评论丛刊:1985,23辑.
[2]张耀杰,盛红.雷雨的误读与误改[M]//曹禺评说七十年.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
[3]宋剑华.前瞻性理念[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4]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5.
[5]张均.中国现代文学与儒家传统[M].长沙:岳麓书社,2007.
[6]曹禺.论戏剧[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责任编辑:汪小珍)
B 97,I 207.99
A
1001-4225(2015)01-0088-06
2014-01-14
陈旭东(1976-),男,浙江安吉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讲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奥斯维辛之后宽恕困境的哲学反思”(13YJC720005)
——话剧《雷雨》中周冲的价值
——从周冲追求四凤说起
——周朴园对侍萍的情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