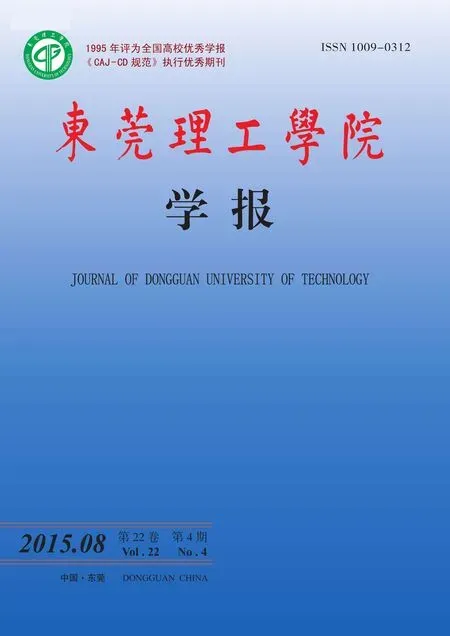智性叙述下的人性欲望
——评严前海的文学新作《绝美时代》
李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智性叙述下的人性欲望
——评严前海的文学新作《绝美时代》
李石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绝美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思辨性的、从容舒缓的智性叙述风格,让人有陌生感、距离感但又魅力无限;其思辨性叙述不同于五四时期《狂人日记》、《沉沦》的直陈式语言,其选取的人物视角也不同于当代文学中以莫言等为代表的农民视角,而是当前我们所处的消费主义时代的孤独个体。小说中,“我”既是当前时代的成功参与者又是时代规则运作下的牺牲品,因此小说所提供的批判和思考显得更加成熟和深刻。小说的外层讲述的是一个吸引人心的情欲故事,其内层则是通过和伟人的沟通来寻求个体和历史的某种气质同构,进而伸拓到对人类历史、社会、时代的叩问上,这才是《绝美时代》最大的精神效能。
智性叙述;人性欲望;《绝美时代》
智性叙述,从内容上看它对人类的天赋形态、智慧形态和精神能力所能达到的高度具有相当高的好奇心和表现欲,从而构建其对人类生存本身的哲学探索和生命追问;从形式上则是对文学语言的思辨性、逻辑性追求,这不同于感觉性、意象性、情绪性的表达方式,而语言形式正构成智性叙述更为重要的特征。智性叙述是理性的、从容的,充满着奇思妙想的,而人性欲望则是本能的、激情的、狂热的。《绝美时代》中的“我”并非常人眼里那种智能超群的天才,但却是如哈姆雷特般对人世充满着困惑和疑问的哲人。《绝美时代》是一部通过思辨性叙述来表达人性欲望的文学新作,它交融着情欲的迷狂和理智的内省,其独特魅力就在于那种奇妙的、自成一体的、成熟从容的叙述语调。
一
不得不承认,《绝美时代》是一部好作品。
为一部优秀的文学新作寻找其在文学传统上的继承关系,是批评者们永远乐此不疲的事情。文学批评需要承担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新的好作品寻找到一种文学史上的对比坐标。评论家陈涛说,阅读严前海的《绝美时代》很容易联想到我国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即鲁迅的《狂人日记》[1]。但是,《绝美时代》的气质绝非《狂人日记》式的风格。如果非要寻找共同点,这两篇小说的共同之处是其主人公都是作为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局外人角色冷冷地审视着整个世俗人生。由此,我们甚至想到了鲁迅的另一篇小说《孤独者》以及郁达夫的《沉沦》。不管是《狂人日记》、《孤独者》还是《沉沦》,我们都能够看到主人公对中国那个特定时代产生的绝望感和孤独感,并迫切渴望着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希望诞生,由此整个社会以及个人也许能够获得拯救。
现在,我们是否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当然,如今的中国早已一扫以往积贫积弱的形象,雄踞世界第二的GDP,不断攀升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前所未有的娱乐消费狂欢,而《绝美时代》的主人公(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商)就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员,他有能力有金钱,能够随心所欲地去体验醉生梦死的生活,可是,我们却依然从他内心的独白中读到生而为人的困惑和愤懑。《狂人日记》和《沉沦》中的人物,他们与整个时代是决裂的,显示了对社会的一种对抗性姿态,但《绝美时代》的“我”却是从容的、成熟的。他参与到了整个时代的规则里,并享受到了谙熟规则带来的各种收益和好处,但最终还是躲不过锒铛入狱,成为了权力规则操作下的牺牲品。《狂人日记》和《沉沦》中的人物多多少少带有受迫害者的形象出现,他们是社会的游离分子;而《绝美
时代》里的“我”既是时代的参与者、同流合污者,因此他是一个强者,但又是一个精神的极度孤独者。如果“我”要和鲁迅、郁达夫笔下的人物进行对话,那么他必定要发问,就算社会改变了又怎样?国家富强了又怎样?他是社会的妥协合作者,但是他又厌恶着整个社会,他早就跳出了某种简单的是非判断。这样的视角给我们提供了更为深刻的批判和讽刺。这种差异,造就了《绝美时代》和《狂人日记》在气质上的截然不同。体现在小说的叙述语调上,《狂人日记》和《沉沦》是直陈式的叙述语言,而《绝美时代》则充满着思辨性的叙述风格。在这种语调掌控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给我们所提供的多维度的哲理思考。鲁迅和郁达夫的小说是时代的产物,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讲,“救救孩子”、“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可以看成是他们对那个时代的愤怒和绝望的表达,但是,在《绝美时代》中,尽管作者有愤怒,他却力图将自身的愤怒稀释掉,而代之以源源不断的内省和思考,由此《绝美时代》显得更为从容、大气和深刻。
即使放到当代文学的坐标上进行考察,《绝美时代》依然显得陌生。比如余华、莫言、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等作家,他们似乎更为钟情于写中国农村的乡土风情,描写农民、工人本身的生命欲望和困境。《活着》、《红高粱》、《丰乳肥臀》、《白鹿原》、《一句顶一万句》、《小鲍庄》等等,无不是写中国近现代以来底层农民的命运变迁和人性变幻。陈思和认为,这些作家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走的多是民间道路,由于他们的民间背景而保留了来自底层的鲜活信息和生命体验。因此,这些作家都是从农民的视角来写农民,他们写出了农民的乐观、宽厚、朴实,也写出了农民的自私、狭隘、龌龊[2]。而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可以看成是世界对中国当代这一重要支脉的文学成就作出的肯定。这不同于中国“五四”以来的以鲁迅和郁达夫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学。由此,我们反观《绝美时代》,作者严前海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写出了这篇小说?当然不是民间立场,尽管小说主人公来自于农村,但是他所呈现出来的生命体验更为贴近于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他的自我叙述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极具审美力以及高智力的带着哲学家气质的人。塑造一个农民的形象跟塑造一个哲学家形象是截然不同的,他们说话的内容、语气、水平也有着天壤之别。但同时,《绝美时代》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学,从文学史上看,精英文学带有更多的启蒙意义上的时代使命,虽然《绝美时代》极力为读者们提供更为丰富的哲理性思考,但是对于“启蒙”的知识分子责任似乎是超脱的。因此,在中国白话文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绝美时代》显得奇特。
二
如果在一个更高的维度,从世界文学的范围内审视这部新作,某种程度上《绝美时代》则更为接近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小说中“我”对于妻子许鸣的迷恋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当许鸣从水中钻出来,带着一身滚落的水珠,双手按住深蓝色的池沿,一使劲,一抬腿,像开完弓后一样站上池边,一股巨大的挫败感痛击我的胸口。”这是被一个完美女性的身体一击即中所产生的自卑感,但是这种自卑感却又在接下来的想念和欲望中逐渐变成一种炽烈的迷恋感和占有欲。“我”不迷恋小说的另外两个女性兰羚和曾霞,是因为她们给他顺从感、亲切感和安全感。但许鸣在“我”的眼中是一个难以充分把握的美丽存在,“她冰清玉洁的身体,是德彪西音乐和莫奈色彩的奇妙混合,我是说,那是视觉与听觉之后进入幻觉的魔沼”。于是,在“我”对许鸣的情欲驱动下,读者们被带入了一个疯狂奇妙的世界,一个道德模糊的世界,一个情欲难填的世界。
对于情欲的迷恋,无论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或是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我们都可以从中找到“我”的类似特征。特别是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笔下人物的情欲煎熬。从本质上看,肉欲的激情就像生机勃勃的罪恶,是对平淡舒适和庸常古板的生命处境的某种惊艳反抗。《绝美时代》的“我”和《洛丽塔》的亨伯特一样,他们对性的渴求就像对生的留恋,情欲的欢腾既是青春的神圣特权,也是生命的强力证明。因此,对于身体的渴求同样显示了他们对于衰老和死亡的恐惧。
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说《绝美时代》是一部情欲小说?如果从“我”对许鸣的无限迷恋上看,答案是肯定的。情欲小说的魔力在于它力图把人在情欲驱逼下流露出来的所有激情、冲动、嫉妒、贪婪、自私、卑鄙、偏执等等表现出来。无论是普鲁斯特笔下的阿尔贝蒂娜还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洛丽塔,她们都不过是男性眼中的情欲幻
影,而许鸣在“我”的眼里同样如此。“我”对许鸣的迷恋不过是一个男人崇慕女性青春的一种短暂的形式。因为在小说中,“我”居然能够完全不为所动地欣赏着许鸣的眼泪和悲伤,尽管这是她在讲述早年被强暴的经历时留下的辛酸的眼泪。也就是说,“我”对许鸣的爱,实际上超越了我们通常所认可的世俗之爱,那种带着相濡以沫的真正的理解式的温情之爱。换而言之,“我”对许鸣的爱情实质上是一种疯狂的欲望(或者许鸣对我也是如此?),因此注定了双方不可能进入意愿相投的阶段,否则它会风干、会衰弱。即便如此,与《追忆似水年华》、《洛丽塔》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相比,《绝美时代》所提供的情欲叙述又有何特别之处?它哪里比得上《洛丽塔》和《威尼斯之死》中那懦弱的好色老头对那些少男少女的畸形爱恋来得惊世骇俗?它哪里比得上《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和阿尔贝蒂娜在嫉妒的愤恨中相互煎熬来得催逼人心?都没有。上述作品中的人物对于爱情和肉欲的极度偏执可以看成是一种纯真的本能,而《绝美时代》中的“我”即使同样对情欲有着本能的渴望,但是作者在叙述中对情欲部分的叙述是保持着距离的。“我”迷恋许鸣,但是我对许鸣没有偏执的掌控欲,“我”对许鸣的渴求、对许鸣的欣赏,都是在不疾不徐从容推进的叙述风度中保留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哲理视角,这种风度更为接近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实际上,《绝美时代》通篇都保持着这种贯穿始终的语调,它并不力图通过语言来建构一些感受性的、冲击性的场面或情节来感染读者,即使是“海上谋杀”的那场叙述,它同样保持着舒缓的节奏。一种思辨性的、哲理性的叙述语调,这是《绝美时代》最重要的特征。《绝美时代》的叙述语言的成熟度,是那种自成一体的成熟,就像一个抽着香烟的沉迷于往事的男人,拒人于千里之外却魅力无限。《绝美时代》读者是分三次读完的,奇妙的是,小说行文的流畅感居然完全没有因此被打断。这篇分十二章节的小说,完全可以从任何一个部分进入,一旦进入,就会被其思辨性叙述拖着走。不过,要抽身出来,也很容易。《绝美时代》的小说语言游离而陌生,它从容的节奏就像《绝美之城》里调度纯熟的电影镜头。
三
《大家》2014年第6期,同时刊登了两位批评家关于这篇小说的评论。无论是陈涛还是黄忠顺的文章,都将《绝美时代》定位成关于谋杀的小说。在笔者看来,“海上谋杀”和“狱中反思”是《绝美时代》前后最主要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谋杀情节,尚构不成作者叙事的核心。黄忠顺教授用“惯例”和“参与”两个词来解读《绝美时代》,认为小说中的商人是一个看透了社会规则的聪明人,他总是能够根据自身需求来与整个社会进行周旋,周旋在妻子和其情人的陷害之间,周旋在官商勾结的交易之间,周旋的过程也是参与的过程——参与和妻子的调情、参与事业上的生意[3]。通过对这一商人的刻画,透露出作者对整个时代社会的无奈感,或者说失望感。但这样一来,似乎就将男主人公理解成了一个老谋深算、懂得趋利避害的人,虽然这一点也符合商人的性格特征。但这种理解并没有抵达小说的真正核心。实际上,这些算计在“我”眼里,都是无所谓的。他对妻子没有道德上的要求,对社会没有过多的期望,也因此没有失望,也不会有无奈。在商人眼里,一切都是可以的,没有反抗,没有激动,不期待这个社会,不评判这个社会,也正因此,他反而能够平静地将内心最丰富的人性体验呈现出来。
对于时代独特的内心体验,是每一个作家都力求要表达和呈现的,这不足为奇,关键在于呈现的方式。前文述及,对于小说创作,作者追求的是思辨性的智性叙事,但是作者不可能在创作中直接把这些呈现在读者面前,那么,在《绝美时代》中,作者如何将思辨性的东西编织到小说的叙事肌理当中?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在小说通篇的哲理性语言中感受到一种思索的快感。但小说不仅要有语言,还要有一些集中的爆发点,也就是小说的高潮。《绝美时代》的两处高潮,一个是“海上搏杀”,另一个则是“狱中写信”。这两处精彩叙述,显示了作者娴熟的叙事技巧。对于“海上搏杀”,作者在前文中早已作出了精心的情节交待,随着情节的演进而逐渐推向高潮。作者将主人公描写成一个经济富裕的精明商人,这种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俯拾皆是,他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有钱但不太注重财富,反而读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有着极高的文化修养和思考能力,因此他对于历史、社会,以及自我有着清醒的认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看透人世,享受着自我孤独和自由,却不太愿意积极行动的人。所以,这个商人,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不完全是情色的纵欲者,而更多的是随顺的对生命的光荣、高贵、
屈辱和苦难的承受者。他渴望真正的温情而不得,但他也享受着脱离温情的孤独和超脱,这样反而更能轻易地得到他想得到的,而不需要担负相应的责任。许鸣在坚决要求他陪同去海上游泳之前,还挑逗他完成了一次酣畅淋漓的性爱,主要目的是消耗他的体力,以便让那场海上谋杀更加顺利。他一定知道妻子的目的,尽管心里有迟疑,也有过恐惧,但还是保持了沉默。而海滩边的人山人海,也让热爱大海,习惯于远离人群的他越游越远,由此而逼近那场海上搏杀。同样的生命承受,我们可以在小说后面描写监狱生活的部分中看到。监狱中的屈辱和肮脏,和之前在大海中的自由感、畅快感截然相反,但正是如此的屈辱,才给他的精神内心提供了一个自然喷发和表现得实实在在的现实感。因权钱交易而锒铛入狱决不是他的选择,但是他却几乎不做任何反抗。一般来讲,如果有得选择,没有人愿意去过屈辱的生活,但就是有一些人在屈辱和苦痛中反而更加渴望寻求精神对话。他在狱中回忆自身的童年,回忆父亲的狂暴和母亲的偏执,对他们的爱和恨。由此可以了解他苦难的过去,也因此我们了解了他对生命承受的情感来源。但这些还不够,他从自己出发,去追问历史和文化,在与古人的精神对话中,不断地询问着世间的丑恶和黑暗,生命和死亡,也追求人世的高贵和美好。
这种承受的结果如何?在前一个叙述高潮里,主人公在无人之境的深海和情敌展开相互角逐,最终他成了胜利者,或者说他无意间成了胜利者,他在不带任何目的的情况下成了胜利者。因此,如果说他是一个谋杀者,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本来就没有谋杀情敌的明确意愿。他只是在承受情敌意图谋杀的过程中无意间成了一个“谋杀者”。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在大海深处展示了自身的生命强健。而在后一个叙述高潮,主人公则展示了对于屈辱的承受以及精神的强健。无论是美丽的大海还是象征着耻辱的监狱,都成了他的栖居之地。由此可知,无论是大海还是监狱,其实,都是作者为主人公故意构造的“绝境”。“绝美时代”这个题目,时代不过是一个依托,作者真正想要写的是绝美,叙述生命和精神的绝境之美,绝处逢生之美。这种美,是以“局外人”的视角,顺其自然地去体验,去感受,去选择(不做选择也是选择),去思考,去爱,去恨。但所有的美都不是针对于外在,而全部在内心中得以完成。
四
如果《绝美时代》仅被看成是一篇情欲小说,或者我们只关注到它的语言风格、叙述形式,那么它的精神效能还只是有限的。《绝美时代》更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超越了一个吸引人心的情欲故事,进而伸拓到对人类历史、社会、时代以及是非、善恶的叩问上。如果没有小说后段的“监狱写信”部分,我们不会知道一个个体对外在世界的体悟和思考将会抵达什么样的深度与厚度。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的叙述外层不过是一个通俗的家庭故事,但是在内层却包含着在权力下人性的善和恶、真实和虚伪的大课题;再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其外层讲述的是一个已婚女子背叛自己的丈夫最终毁灭的婚外情事,但另一层却通过列文的视角来表达他对世界、道德、宗教的哲理思考。
《绝美时代》是否能与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作品高度相提并论,笔者无法比较。但是在结构上,《绝美时代》与《李尔王》及《安娜·卡列尼娜》的相似之处在于其意图承载的绝非仅仅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疯狂情欲,更何况这样的故事也许在千千万万个“我”身上都会发生,而且,人性的欲望和迷狂早已在更多的文学作品中有过充分的精彩表现。如前所述,《绝美时代》的真正价值在于“我”对历史伟人们的叩问,这是对历史曾出现过的崇高的疑问。因为“我”并不崇高,也不相信崇高。“我”对许鸣的追求似乎是对这个荒谬世界的一场崇高的肉欲反抗,可是“我”对许鸣婚姻所运用的挑拨离间的手段却那么不光彩,但如果不这样,“我”怎么获得许鸣的肉体?因为,人类并不那么崇高,也不那么丑陋。既然“我”在生活里见识过那么多的暴力、背叛、卑鄙和龌蹉,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历史提供给我们的高贵的伟岸生命曾经存在?但似乎“我”又无法否认他们的存在。为什么耶稣这样的肉体凡胎能够忍受着身体的剧痛走上十字架?为什么庄子、李白、司马迁、兰陵笑笑生能够留下千古的篇章?为什么苏格拉底能够无惧从容地走向死亡而丝毫没有本能上的恐惧?……“我”被这些人吓住了。原来人世间有一种哲学,不管外在如何卑鄙和残酷,仍然无法阻挡住人性本身的欲望表达和追求。因此,即使“我”早已知道许鸣和前夫要合谋杀“我”,“我”依然保持沉默,就是为了继续享受许鸣的美妙身体,这是一
种无法遏制持续生长着的欲望。就像印度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哲学,你可以对我使用暴力,我不会反击,但你阻止不了我对正义的追求。“我”对这个世界是看穿的,是绝望的,但“我”依然具有欲望,依然需要不断地寻找释放欲望的场所。“我”在无人的海上是前所未有的放松,“我”觉得肮脏的监狱反而是干净之地,“我”的精神孤独得面对社会圈起了坚硬的围墙,但却愿意让一群陌生的青年男女看到“我”悲伤的眼泪,“我”最温情的时刻是面对着成为植物人的父亲和单纯顺从的继母……这是《绝美时代》“我”人性最为复杂的地方。在作者笔下,对情欲的渴望是个体生命欲望的某种承载。可以说,小说所展示的生命体验,包括性的快感、肉体的接触、抚摸、身体的疼痛是“我”跟整个世界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个体欲望太多了,何止情欲?权力、宗教、信仰、金钱、艺术、知识、科学……而“我”在众多历史伟人面前的震惊正在于他们在各自的领域让自身的欲望在历史上留下了华丽的回应,尽管他们曾经承受过巨大的生命创痛和困境。因此,我们才看到,“我”在一种看穿一切的语调中貌似早已厌倦了世间的一切,却丝毫没有任何妥协的情绪,反而流露出一种强烈的困惑和愤懑,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他对善和恶、生和死依然感到全身心的不解。狱中写信那部分过后的“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而是一种新层次上的个体闪耀。“我”和伟人们的通信,构成了一种远古的具有相似气质的生命之间的强力传递,这也让这部内省之作在个体感受的伸拓上更加强悍有力。
由此可以说,“我”对许鸣的迷恋以及由此引发的情欲谋杀是《绝美时代》的鲜活血肉,而这部作品内层的精髓却是对人性欲望的某种深刻的洞察和剖析。吊诡的是,也许大多数人永远关注和记住的是前者,而忽略了后者,而后者才恰恰是《绝美时代》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哲理。但实际上作者想表达的真是这样吗?笔者希望自己是对的,可又希望解读这篇小说的答案是不确定的。就像加缪说,“不确定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归宿”[4],如同他在评论卡夫卡的小说时讲到,“这部作品提出了一切可能性,但一个也没有证实,这就是它的命运,也许还是它的伟大”[5]。那么,《绝美时代》将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
[1] 陈涛.面向内心的掘进与抗争[J].大家,2014(6):36-38.
[2] 陈思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J].扬子江评论,2014(5):18-24.
[3] 黄忠顺.我们时代的“惯例”与“参与”[J].大家,2014(6):39-41.
[4] 加缪.加缪全集·散文卷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191.
[5] 加缪.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诞[M]//叶廷芳.论卡夫卡.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13.
Hum an Desire in the Intellectual Narration:Comments on Yan Qianhai’s The Age o f Great Beauty
Li Shi
(Literature College,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The most impressive feature of The Age of Great Beauty lies in its speculative,calm and soothing intellectual narrative style,showing an unfamiliar sense but an infinite charming.Its speculative nar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straightforward narrative language,such as A Madman’s Diary and Degradation of May Fourth period;the character perspective of this novel is a lonely individual who lives in our currentage of consumerism,which i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folk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such as Mo Yan’s works.In the novel,the character“I”is a successful participant of our society as well as the victim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rules.Therefore,it can provide more mature and profound critical thinking.The novel looks like an attractive erotic story,but it actually shows that the individual tries to seek for identification from the history through writing to the great people of the past,and further extends the inquiry into the whole human history,the society and the era,which is the biggest spiri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novel.
intellectual narration;human desires;The Age of Great Beauty
I207.42
A
1009-0312(2015)04-0038-05
2015-05-07
李石(1990—),男,广东茂名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审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