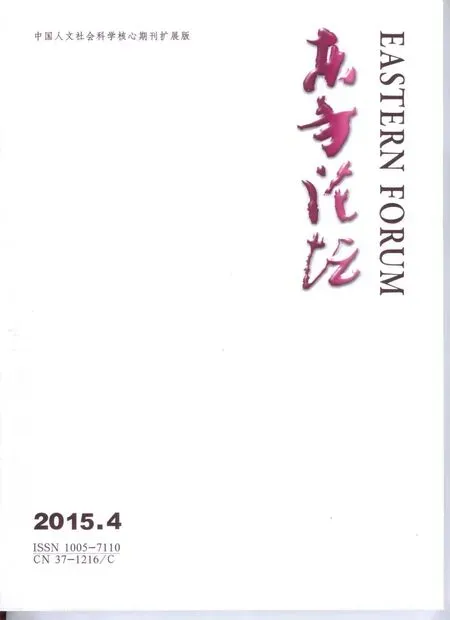文化身份的坚守与性别身份的困境——裘帕·拉希莉小说中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形象分析
张 玮
(安庆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印裔美籍作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又译茱帕·拉希里)以短篇小说集《疾病解说者》(Interpreter of Maladies,1999)获得2000年度普利策小说奖。随后,她出版长篇小说《同名人》(The Namesake,2003),《低地》(The Lowland,2013)和短篇小说集《不适之地》(Unaccustomed Earth,2008年),其中《低地》荣登2013年度“布克奖”短名单。对于这位祖籍印度、出生在伦敦的女作家,国内外学者多从流散文学、女性主义和身份认同等角度来研究其作品。如刘立珍在《流散者:文化漂泊之下的情感疼痛》中分析《同名人》里印度两代流散者的多重心灵体验,梅晓云“以‘姓名’为聚焦点,讨论‘姓名’及其背后的意义,认为在姓名符号规则的混乱背后,深刻地反映了移民在身份和认同上的文化困境”[1]。笔者也曾从《同名人》中第二代印度青年移民的异族婚恋现象分析他们在自我身份认同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然而,在裘帕·拉希莉作品中有一类女性即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们的身份认同困境显得与众不同,值得分析。
尽管社会不断发展,印度传统婚姻方式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包办婚姻仍然是印度青年男女步入婚姻的主要途径,即使一些生活在海外的印度人也不能避免。他们遵从父母的安排,回国相亲、完婚后带着印度妻子回到海外生活。拉希莉的作品中就塑造出很多这样的女性,如《同名人》中阿西玛,《疾病解说者》中森太太,《不适之地》中的亚潘娜等。她们从印度的家国文化空间来到美国异质文化空间中生活,不得不面对文化身份被影响、被改写的局面,她们同时还面临女性性别身份的困境。在空间文化理论的视角下,本文选取裘帕·拉希莉小说中此类女性形象里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剖析她们在异质文化空间里对文化身份的维护和坚持,及其被忽略的性别身份困境。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空间也是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化身。1974年,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列裴伏尔的《空间的生产》被认为是第一部关于社会空间的系统理论性著作,之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发展给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带来新研究方向。1996年,美国后现代人文地理学家爱德华·W·索雅(Edward W Soja)出版《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他在列裴伏尔空间思想的启发下提出“第三空间”概念,成为种族、阶级、边缘、文化身份、性别地理等方面研究的一种新视角。福柯、霍米·巴巴、米歇尔·迪尔和拉什迪等人也用过“第三空间”概念,如霍米·巴巴用它来指代生活在西方社会中的、来自非西方国家的人们的文化处境,分析文化冲突和种族纠纷,他认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持续不断地处于混杂性的过程中。拉什迪的“第三空间”概念包括当代人的身份认同(包括国族、阶级、种族和性别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话语场。拉希莉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家国(印度)文化空间和异质(美国)文化空间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成为浓缩和聚焦印度移民群体文化身份认同问题的符码,本文以空间文化理论视角来考察拉希莉笔下人物的社会文化空间。
一、文化身份的坚守
“散居的族裔身在海外,生活在所居住的社会文化结构中,但是他们对其他时空仍然残留这集体的记忆,在想像中创造出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属”[2](P6-7),列斐伏尔也说过,“为了改变生活,我们必须首先要改造空间”[3]。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利用家庭和交往的印度朋友圈营造出印度文化空间,她们在这种被创造出的空间里采取种种方式保持与印度传统相近的生活方式,在异质文化空间内探寻、维持着自身的文化身份。
具象化的家国文化符号,如语言、日常着装、饮食习惯等成为维系、标识文化身份的工具。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坚持使用印度语言,“到图书馆去,坐在阅览室一把皮革开裂的扶手椅上,给母亲写信,阅读杂志或一本从家里带来的孟加拉文书”[4](P58)。她们会送孩子去上朋友在家开设的孟加拉语课,学习祖先传下来的字母。服装、配饰等印度传统装扮成为文化身份的醒目标签。亚潘娜在纽约街头被询问是不是印度人,就是因为她“戴着孟加拉结婚妇女才会佩戴的红白手环,身穿一件寻常的坦盖尔纱丽,中分的发间洒上厚厚的一层朱红色粉末”[5](P53)。森太太即使待在家里也会穿上适合在晚间聚会才穿的“微微闪烁的、饰有橘黄色佩兹利旋花图案的白色莎丽”[6](P116)。印度口味的食物和传统的进食方式也保留在家庭这个印度文化空间里,“果戈理已经开始学习自己用手指吃饭,不让食物沾染了手掌。”[4](P62)
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空间被以群体聚会的方式拓展为较大一些的印度文化空间,这种聚会进一步界定参与者文化身份的类别和集体属性,进一步强化他们个人文化身份的标签。“他们认识了好多孟加拉人,几乎没有哪个周末是闲着的,以至于果戈理一生都将记得:孩提时代的星期六晚上,总是单一而重复的景象:一幢三间卧室的郊区住房里,三十多个人济济一堂,孩子们在地下室看电视、下棋,大人们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孩子之间不讲的孟加拉语聊天。”[4](P71)此种聚会是侨居海外的印度人熟悉的生活方式,屡屡出现在拉希莉其它短篇作品中。在异质文化大空间内,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人为地营造出可视、可感、可触的小印度文化空间以安慰、缓解思乡之情,使她们可以在熟悉的家国文化空间里维持着自己所熟悉的印度文化身份。即使这样,她们的文化身份也会受到异质文化的迁移和影响,丈夫和孩子成为异质文化进入家庭文化空间的中介。食物、节庆日等原来用以强化家国文化的元素被或多或少地掺入异质文化形式,“感恩节,他们学着烤鸡,尽管抹的是蒜、茴香和辣椒粉”,“他们越来越大张旗鼓地庆祝基督的诞辰了;比起敬拜女神杜伽和萨拉斯瓦蒂来,这个日子孩子们盼望得多了。”[4](P73)久而久之,她们在一些事情上也就入乡随俗了,如给孩子们准备西式食物,会接受自己的孩子“也是个美国小孩的事实”[5](P71),这种逐渐发生的变化也模糊和异化了她们的文化身份。
人为地将家国文化空间扩大,暂时、局部地缓解了印度妻子们对文化空间需求。回国省亲时,她们再次回到熟悉的、渴望的家国文化空间里,短时期内迅速加强她们略显模糊化的文化身份,然而在两种文化空间内的移位后,会剥落刚刚加固的文化身份外壳,稀释并进一步模糊她们的文化身份,“一切便彻底回复了原样,仿佛他们压根没去过印度。”[4](P99)加强和弱化之间一次次的循环,她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也就常态化了。随着时间推移,印度妻子们也会步入异质文化空间,“在无所事事多年后,她五十岁时决定到附近的一所大学攻读图书馆学学位。”[5](P71)即使在丈夫去世后,有些印度妻子不必再待在异国他乡,然而,一年里她们也会选择一半的时间在印度生活,一半的时间回到她们曾经度过大半生的异乡,文化身份的迁移和变化是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
身份认同问题是每一个流散海外的人都会遇到的困境,身份更多的是文化和社会影响的结果,对家国文化身份的坚守和异质文化对身份的迁移,使得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在多重文化空间里形成“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者或他者)”[7](P28)的混杂文化身份,一种富有新意的、居间的、或混杂的身份。
二、性别身份的困境
弗洛伊德认为,性别身份是人类身份的首要构成因素,确立身份的第一步就是对性别的判断和区分。对女性“性别身份”的研究,当代女性主义者在身份的本质和构成方面有不同的观点。在考察性别身份时,除了要关注男女生理上本质的差异外,也应注意到种族、阶级、文化、教育等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论述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与妇女解放的关系时,斯皮瓦克认为印度妇女的解放话语常常被男权社会的解放话语所淹没。与此相类似,海外印度妻子们的性别身份困境在与男性(丈夫)一起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被忽略,甚至被掩盖。拉希莉的作品一方面展现在异质文化与家国文化之间的碰撞时,她们在文化身份方面的迷失、困惑、坚守与重构,另一方面,作家也冷静地描述出在家国文化的影响下,她们性别身份所带来的家庭困境和情感困境等。
受印度传统文化习惯影响,印度妻子很少外出工作,大多待在家庭里照顾家人生活,生活在海外的印度妻子也是如此。因此异质文化空间并没有直接地带给她们性别身份的困境,在家庭空间里与丈夫、子女和朋友的关系是她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拉希莉展现她们在日常生活空间里的生存体验和性别身份困境。
与丈夫的关系是她们首要面对的困境,在海外的印度女性来说同样受到印度传统文化规定性的制约。小说里苏西玛、亚潘娜等女性在相亲时与丈夫匆忙见上一面,婚礼后就立刻来到美国,在父权、夫权等多重权力支配下,她们的身体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文化空间中被迫接受新的文化习俗。她们被局限在由丈夫(男性)“强行安排”而位于异国的家庭空间里,从一开始,她们就毫无选择地要面对印度文化空间的缺失和陌生家庭空间里的性别身份困境。她们对于丈夫一无所知,即使在共同营造的家庭文化空间内(这种文化空间的主要目的是坚守共同的文化身份),与丈夫之间的陌生感和家里冷清的环境也把她们淹没在寂寞里。“我一放学回家就看到妈妈已经穿上外套,皮包搁在大腿上,迫不及待想逃开这个她独自待了一整天的公寓。”[5](P55)“她会一连几个小时在家里打瞌睡,生闷气,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读那五篇孟加拉文的小说。”[4](P40)森太太从加尔各答到美国陪丈夫,丈夫上班后她就一个人孤零零地待在家里。她一次次地带所看护的美国孩子去海边买鱼,在买鱼、做鱼和吃鱼的过程中回忆、感受和重温在加尔各答的印度生活,那个美国孩子成为她寂寞生活的观众。对于妻子在家里的处境,丈夫们不但没有半句安慰的话,反而会说:“如果你这么不快乐,那就回加尔各答算了。”[5](P66)
与其他异性的感情关系是她们的另一种困境。在异域的孤独感和思乡之情促生了她们由于包办婚姻而被缺失的爱情,亚潘娜“由于包办婚姻,远嫁美国,她在命中注定的婚姻和邂逅的爱情之间的挣扎”[4](P333),她“一整天都期待普叔叔的来访,她换上新纱丽,梳好头发等着他来”[5](P55)。她对“普叔叔”的情感混杂着侨居异乡对同乡人的心理依赖、寂寞家庭妇女对熟悉男性的情感依赖,因此在“普叔叔”决定结婚时,亚潘娜甚至想点燃浇满汽油的纱丽自杀。她的绝望,一方面担心失去来自于非丈夫的印度男性(“普叔叔”)所建立起的文化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更是失去自身情感(爱情)的痛苦。
母亲身份的弱化是她们不得不面对的又一种困境。她们与出生、成长在美国的孩子们不仅有代际间的问题,也有文化认同方面的冲突。在家庭里,她们给孩子准备印度式的饮食,但也不得不答应每周要给孩子准备一次汉堡等这样的西方食物。孩子长大后会向她们隐瞒更多事情,会在朋友的帮助下躲过监视去做一些她们不认可的事情。她们更担心女儿会迷上班上的美国男孩,当她们觉察到什么时,也只能粗暴地禁止女儿参加学校的舞会,而没有其它办法。她们无法按照印度传统习惯去规约在异质文化空间里生活、学习的子女们,她们的“母亲身份”是尴尬的。
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们更多是以妻子、母亲的身份在家庭空间里活动,很少介入异质文化空间中,也无法从中寻找缓解性别身份困境的出口。和其它普通女性(即使文化身份不同)一样,“年纪越大,越看出她的生活是多么孤寂。她从来没有上过班,白天靠着看肥皂剧打发时间。日复一日,她唯一的工作是帮我和我爸爸煮饭打扫。”[5](P66)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们生活在家庭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边缘,同样处于家国文化空间和异质文化空间的边缘,她们要同时面对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的双重困境,而作为流散群体中的一员,她们性别身份的困境被忽略了。
三、余论
生活在海外的印度妻子是一个被忽略的群体。有学者认为在美国所有外来移民中,印度裔家庭不仅最为稳定、离婚率最低,而且族裔间通婚也较少发生。印度移民在不断自我发展、积极融入主流社会的同时,尤其在宗教、婚配、服饰和饮食等方面仍能很好地保持传统文化的延续。[8]可以说,印度族裔的这些特点与侨居海外的印度妻子们的努力和牺牲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她们仍然受制于家国文化传统中对女性性别身份的规定性,她们所坚守的文化身份也是造成她们性别身份困境的原因。小说里的阿西玛、森太太和亚潘娜等女性的主要任务是在异质文化空间和家国文化空间中定位、探寻自身文化身份,而由于身体所处家庭空间的特殊性和封闭性,她们又期望在被创造出的家庭/家国文化空间里得到安慰和保护。作为一位女性流散作家,裘帕·拉希莉不仅深刻理解流散者的身份困境,也能体会到女性性别身份衍生出的问题,在文化身份寻求的同时凸显出的性别身份困境是裘帕·拉希莉作品的特别之处。
[1] 梅晓云.名字的背后是什么[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2] 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UK),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Blackwell,1999.
[4] 裘帕·拉希莉.同名人[M].吴冰清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5] 茱帕·拉希里.不适之地[M].施清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 裘帕·拉希莉.疾病解说者[M].卢肖慧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M].New York:Routledge,1994.
[8] 腾海区.论美国印度裔族群形成及特点[J].美国研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