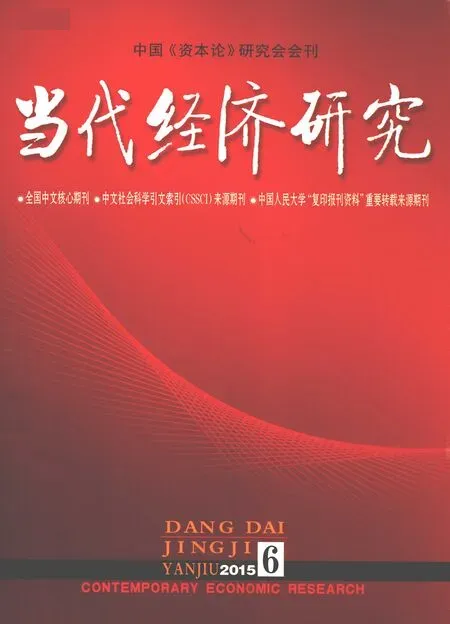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美国敲打日本的历史透视与启示
任东波,李忠远
(吉林大学文学院,长春130012)
20世纪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美国成功逼迫日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日本经济也最终步入了长期低迷的发展轨迹。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一直面临着来自美国保护性经济利益集团、部分国会议员、财政部、甚至美国总统的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压力,美国试图复制敲打日本的成功经验,将人民币汇率置于二十国集团(G20)的“多边”场合来解决所谓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有鉴于此,研究和总结美国敲打日本的经验,对于中国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确保大国地位的稳步提升,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美日汇率博弈
1984年末,日元兑美元汇率已回落至1973年的水平,甚至更低,这为日本的汽车、机械产品、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创造了巨大的竞争优势。由此导致美国国内日益上涨的保护主义压力成为里根政府改变强势美元政策的一个重要背景。时任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通过召集五国集团(G5)在广场饭店开展多边协调,实现了美国汇率政策从不干预到积极促成美元间接贬值、从单边主义到多边合作的战略转变。[1]
美日两国在“广场协议”期间及之后的汇率博弈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日本是所有非美元货币国家中最拥护本币兑美元升值的国家。对日本的谈判代表来说,他们惊恐的是美国日益上升的保护主义压力,因而准备接受一次日元的大幅升值以转移压力。[2]而欧洲人关心的不是美元与其货币的比价,而是日元对其货币的比价。对欧洲人来说,日元升值越多,他们对自己的竞争地位就越感到放心。[3]因此,“G5的行动事实上可被看作美国人联合欧洲人压迫日本人升值日元、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战略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战略、削减其巨大贸易顺差的一次尝试”。[4]二是“广场协议”后日元的升值幅度远超日本预期。按照日方设想,美元兑日元初始贬值10%后,可进一步贬值到1美元兑换210日元乃至200日元的水平。但事实证明,这只是其一厢情愿。在1985年9月22日“广场协议”达成当天,美元兑日元的比价为1:242,随后日元一路飙升,到1986年2月时,日元已对美元累计升值25%。[5]这一失序的状况显然背离了“广场协议”做出的“主要的非美元货币对美元进行有秩序的升值”的承诺。
面对超乎意料的日元大幅升值,日本积极寻求与美国的双边磋商,虽在1986年10月31日达成了初步共识,即“贝克—宫泽喜一协议”,但它“是一个打包的交易,一个用日本的财政激励来换取货币稳定的补偿。一旦美国认定日本的财政努力不足以赢得其汇率支持时,该协议就会走到尽头。事实确实如此”。[6]随后的日元升值态势仍无改观,到1987年1月19日时,日元兑美元汇率已升至149.98:1的战后最高水平。尽管日美双方在两天后再次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也在9天后实施了“广场协议”以来的首次入市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日汇率博弈的终结,而是“通过充分运用日本这张牌来向德国全力施压,并把该策略带到即将在卢浮宫召开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上去”[6]的前奏或预演。
1987年2月的卢浮宫会议被看作是广场饭店会议的延续,但与后者旨在实现美元贬值的目的不同,此次会议旨在实现主要非美元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最终在成员国之间达成了如下共识:各成员国在现行汇率波动至±2.5%的水平时将联手入市干预,波动范围接近±5%时则协商进行强制性政策调整。从“卢浮宫协议”后的发展趋势看,日元兑美元汇率在头5周内相对稳定,但随后大幅升值。到1987年4月6日华盛顿G7会议前夕,日本被迫接受了美方提出的“以1美元兑146日元的中心汇率来确定入市干预和强制性调整的汇率波动边界”的建议。此时,日元兑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已达到±7%,远超“卢浮宫协议”规定的强制调整线。
二、美国为何要在货币层面敲打日本?
美国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在货币层面敲打日本,表面上看是源自日益高涨的国内保护主义压力,但核心目标是终结日本在战后美苏两极对峙局面中长期享受的“搭便车”红利,并借敲打日元的机会达到遏制日本快速崛起的战略目的。
二战后,在美国的大力扶持下,日本经济快速崛起,使美国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乃至威胁,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首先,日本对传统经济强国的成功赶超。日本经济年均增长率在1950~1960年间为8.6%,1960~1970年间为10%。此间,日本迅速超越意大利、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一跃成为西方第二、世界第三的工业强国。1987年,日本超越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这一年,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了美国。[7]其次,日本对美国出口的激增。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低门槛进入美国市场以及日元严格盯住美元汇率的三重助力下,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大举进军美国,不仅引发了美日间的多轮经济冲突,更引发了美国民众对日本(而非苏联)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持续担心。“日本是美国最主要的外国竞争者,反之亦然。没有其他国家对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构成过如此全面和成功的攻击,没有其他国家在如此多的领域追赶和超越过美国在高科技部门中曾无可撼动的领先优势,没有其他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将在超级计算机、半导体、超导、复合材料、电子通讯设备等至关重要的新技术领域对美国的竞争力构成挑战”。[8]最后,日本相对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实力的提高。一是日本银行业的异军突起。据《银行家》杂志的统计,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只有1家日本银行跻身世界前10大银行之列。但到1985年时,已有5家日本银行进入世界前10强,另外有2家日本银行也在逼近前10。相比之下,美国只有花旗集团1家榜上有名,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位居第1,但到1988年已跌至第11,被众多日本银行甩在身后。[9]二是日本作为债权大国的兴起。到1981年时,日本已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资本输出国。1983年日本的净资本输出额仅为177亿美元,一年后就显著上升到497亿美元,第二年更达到645亿美元,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则变成了债务国。到1985年时,美国自1914年以来首次变成净债务国,而且是世界最大的债务国,而在美国借入的外债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后者的投资主要流向了美国的国库券。
三、美国因何能成功敲打日本?
日元的大幅升值并未扭转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激增的局面,但却迫使日本政府为应对汇率冲击进行了低利率调整,从而诱发了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将日本拖入了经济复苏乏力的“失去的二十年”。那么,美国因何能成功敲打日本呢?
首先,日本是一个仰仗美国安全保障的“附庸国”。战后日本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遵循了和平主义的“吉田茂路线”,即搭乘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便车,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在规避了“大国兴衰陷阱”[10]的同时,也把调整国际收支的部分主动权交予了美国。在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面对美国要求调整日元汇率以纠正两国间的贸易收支失衡的压力时,日本不得不以汇率妥协来换取防卫安全。
其次,日本是一个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贸易国家”。作为一个“贸易国家”,日本的贸易模式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一方面,日本大量进口本国无法供给的农副产品及工业原材料、矿物资源和中间产品;另一方面,日本的大部分工业制成品被销往国外,特别是销往需求旺盛的美国。为应对日元大幅升值的冲击,日本企业大大加快了对东亚开展直接投资的步伐,但这些投资据点是作为面向美国的“迂回出口基地”而存在的。日本企业并未在东亚建立起一个商品周转的区域内市场。结果是当美国政府准备压迫其他国家分担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和负担时,日本要比德国更为配合。“贝克-宫泽喜一协议”能够达成,是因为日本意识到,为保卫其出口市场,它需要制止美元兑日元的进一步贬值。相比之下,由于其出口主要面向欧洲共同市场,德国对损失美国市场的威胁感要轻得多,因而拒绝了美国在1986年向其发出的进一步贬值美元的威胁。[11]
最后,日本是一个无法与美国抗衡的“金融弱国”。与本币是世界货币、由本国金融市场调控全球金融资源、有能力引领和有权力制定全球金融规则的美国相比,日本金融崛起的基础是薄弱的,不具备抗击美国货币和金融压力的能力。从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来看,尽管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日元国际化”的问题就被日本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甚至在1984年5月29日达成的《日美日元美元委员会报告书》中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协议内容敲定下来,但长期以来,日元国际化的效果并不明显,日元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国际性货币。[12]
从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看,无论是从金融市场的深度、准入度,还是从金融市场的效率、稳定性,还是从发展的历史、金融工具的创新等角度衡量,东京均无法与纽约相提并论。此外,20世纪8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外汇贷款占日本银行业对外贷款的80%左右。由于美元结算业务是由美国银行承担的,日本银行只承担着美元交易的中介职能,因而,后者只能在国际银行市场上以很高的信用等级、较低的自有资本比率和高杠杆为支撑,以较低的信用实现美元资金的短借长贷。这样,日本以非本币美元的金融交易为中心构筑起来的国际金融竞争优势就具有明显的脆弱性。[13]
四、结论及启示
从“广场协议”到“卢浮宫协议”的两次多边国际货币协调,是美国成功敲打日本的重要事件。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因为日本在安全和贸易上过度依赖美国,以及金融实力上的孱弱。中国可从日本的货币和金融败战中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应由注重贸易大国地位的提升转向重视贸易强国角色的塑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崛起成为世界第一的出口大国。与日本相似,中国也以美国为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并且自2000年起取代日本成为了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来源国。但与日本不同,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商品为主,贸易大国地位的提升并未伴随着向贸易强国角色的转换。这为美国频繁向中国祭起“双反”(反倾销、反补贴)大旗以及国会议员屡次提出人民币汇率议案制造了口实。为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需在三方面塑造自身的贸易强国角色:一是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转型,提升输美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二是寻求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改变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被动局面;三是增加对美国商品,特别是高科技商品的进口,变依赖于美国市场为向美国提供市场。
第二,将建设适合我国的现代化金融体系与参与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重。建设现代化金融体系的关键是稳步推进金融制度的创新,通过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拓展金融市场深度、丰富金融市场品种、降低金融市场风险,来增强本国金融市场对于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这有助于提升中国对美国的讨价还价能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已成为多方共识。通过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倡导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和投票权分布,提升新兴发展中大国在IMF中的金融话语权,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制约美国金融霸权的作用。
第三,将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与参与G20多边金融治理机制并重。日本被美国打压的一个惨痛教训是,日本是单兵作战,背后没有一个成熟和稳固的东亚区域货币体系做支撑。中国如欲避免被美国和美元强力压制的困境,就要将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体系、推进人民币在东亚的国际化程度,作为今后区域合作战略的一个重点。参与G20多边金融治理机制的建设,主要出发点是寻求与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多个成员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避免承担美国转嫁的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本。
[1]姜默竹,李俊久.反思1980年代的美日货币谈判——结构性权力的视角[J].现代日本经济,2013,(3).
[2]泷田洋一.日美货币谈判——内幕20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保罗·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国际货币及对美国领导地位的挑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6:252,253.
[4]Gilpin,R.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164,328 -330.
[5]Henning,C.R.Currencies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Germany,and Japan[M].Washington,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4:145 -147,282.
[6]姜默竹,李俊久.“相容性利益集团”缺乏与日本对美国的金融败战[J].现代日本经济,2015,(2).
[7]江涌,阮建平.“日本奇迹”与中国道路——对中国GDP赶超日本的思考[J].国有资产管理,2010,(12).
[8]Cohen,S.D.United States- Japan Trade Relations[J].Proceedings of the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1990,(37).
[9]郑蔚,王思慧.战后日本金融制度变迁与转型:一个制度金融学的考察[J].现代日本经济,2014,(1).
[10]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11]加文·麦考马克.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12]Silk,L.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J].Foreign Affairs,1986,(65).
[13]崔金哲,杨云峰,李钟林.日本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日本经济,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