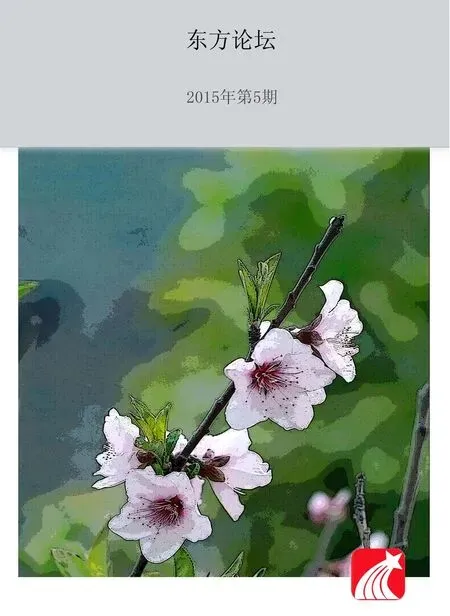也谈《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并与宗福邦教授商榷
李开金 易竹贤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三教授主编的《故训汇纂》[1](以下简称《汇纂》),是继承《经籍籑诂》[2](以下简称《籑诂》)总辑训诂资料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其内容、篇幅以及编排版式等多方面,较《籑诂》都有明显的进步与完善,故出版后受到各方好评。但宗福邦教授的《〈故训汇繤〉 与〈经籍籑诂〉》等几篇论文,对《汇纂》与《籑诂》的评价,往往有失偏颇。笔者不揣浅陋,也想来谈谈这个问题,并与宗君商榷,以期继承和发扬学术评价与论争的优良风气。
一 、关于“复古主义”的帽子
在《〈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3]一文中,宗教授对《汇纂》与《籑诂》两书的比较,是从“编辑思想的差异”开始的,并给《籑诂》戴上“复古主义”的帽子。他说,《籑诂》卷首所列的80 余种书目,“绝大部分是先秦两汉的典籍”;清代的小学是为经学服务的,阮元主编《籑诂》的目的自然也是治经,而他所关注的“经”,“主要是先秦儒家的经典”;经籍的注疏也只收到唐代为止,“唐代以后几成空白”。这样“重汉唐故训而轻唐以后故训”,就是“复古主义”,而且是“清代小学的通病”。
然而据笔者统计,《籑诂》卷首所列书目共85种,《汇纂》与其相同者75 种;其中有关儒家经典的,连后定的《孝经》《孟子》《尔雅》都算上,《籑诂》有21 种;《汇纂》缺4 种,却另有一分为二的两种(多出二种),一分为14 的一种(其中除《老子》《庄子》,多出12 种),实共31 种。这样一算,《汇纂》收录的先秦两汉典籍,与《籑诂》大部相同,仅少10 种;而先秦儒家经典,却较《籑诂》多出10 种。如果要扣“复古主义”帽子的话,《汇纂》戴的可能比《籑诂》的还要大一些,高一些,才相称呢。
但是,我们绝不想给谁扣帽子,而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际出发。自汉武时代,由董仲舒对策而引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因为能适应封建专制大一统帝国的需要,一直占据着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地位;其他的道、法、扬、墨各派便都边缘化,时隐时现,难成大的气候,且都被融合渗透了儒家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事实上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而且,儒家经典的思想,几乎全面渗透进了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以至小学等各个领域。我们今日要学习、研究、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很难离开儒家的经典,或者根本就绕不开儒家的思想文化。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绝不能简单粗暴地扣帽子,而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其次,重汉唐故训而轻唐以后的故训,究竟是不是“复古主义”?对此,王力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汉儒去古未远,经生们说的故训,往往是口口相传的,可信的程度较高”;“我们应该相信汉代人对先秦古籍的语言比我们懂得多些,至少不会把后代产生的意义加在先秦词汇上”。[4]王宁先生也持同样意见,他说,“距离原典产生时代未远的训诂大师们对古代文献所做的解释,时代的接近使他们还保留着对原典语言准确的语感;学养的高超又使他们具有对中国文化综合的深刻的理解力”,有他们为引导,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王宁还进一步肯定说,“正因为如此,阮元的《经籍籑诂》才成为许多专业人员离不开的工具书”。[5]他们的意见,实际上否定了加给《籑诂》的“复古主义”帽子。
二 、有失公允的某些评价
《籑诂》“凡例”说,“此书采辑,杂出众手,传写亦已数过,讹舛之处,或亦不少”。事实上,《汇纂》也有这种情形。例如萧红教授在肯定《汇纂》的同时,也曾指出仅“马”字部便有11 处错失;她指出来为的是“以备编纂者日后修订时采用”。[6]这是一种与人为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可喜态度。《汇纂》的一些编撰者揭举《籑诂》的缺点与错失,也多为吸取其教训、引为鉴戒,这是可以理解,也应予肯定的。但《〈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等文对《籑诂》错舛的指责,却往往有虚夸不实之辞,必须用事实来辨明,并予澄清。
(一)书目数量少吗?
宗文以为,《籑诂》“主要收录的书目80 余种,绝大部分是先秦两汉的典籍,汉以后的著作屈指可数,唐以后的著作几成空白”;而《汇纂》“主要列目书共260 种①按,成书后为228 种。,大体上涵盖了先秦至清末两千多年训诂史上有代表性的著作,资料收录远比《经籍籑诂》广阔”。[3]
事实怎么样呢?笔者通读《籑诂》全书,对其所列书目和用例做有初步统计②本文所用版本,是成都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本。阮书列目书名不怎么规范,多不注撰者姓名和版本。有時一书多名,如《逸周书》,時称《周书》,又称《逸书》。限于学力,我们的统计与书名,也可能有误,恳请指正。,与《汇纂》的228种书目相对照:《籑诂》列目书总共268 种,其中与《汇纂》 同的79 种,书目同版本有异的8 种,《籑诂》独有的181 种。由此可见,《籑诂》书目总数比《汇纂》不仅不少,还多出约40 种,倒可能更“广阔”一些呢。因而《汇纂》主编所一再声称的,该书“涵盖了自先秦至晚清二千多年训诂史的全部成果”,而且是“《经籍籑诂》所不能比拟的”[7],所谓“全部成果”,显然要大打折扣;至少缺了《籑诂》所独有的180 多种书。
我们又以《汇纂》的228 种书目作基础,与《籑诂》相对照,其结果是:两书共有的76 种,书目同而版本有异的32 种,《汇纂》独有的116 种。在《汇纂》独有的116 种中,清代的83 种,版本有异而为清代版的26 种,共109 种;民国時期的1 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時期的3 种,则其下限显然非主编者所说“清末”或“晚清”。这些《汇纂》独有的书及版本,或与阮元同时,大多则可能是阮元之后的。《汇纂》多加使用,乃时间给予的条件,确也形成《汇纂》的某种特色,应该肯定。而《籑诂》之未能使用,也属时间条件问题,不能离开时代实际,对阮元作反历史的苛求。
有人或许会提出问题:既然《汇纂》的列目书比《籑诂》还少,全书总字数怎么会是《籑诂》的几倍呢?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汇纂》所收复音词条资料较《籑诂》多。而另一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一用文言、一用白话的缘故。但是以字数多少来衡论两书优劣的作法,很难说是科学的。
(二)是否排斥宋以后的经籍旧注?
宗教授以为,排斥宋以后经籍旧注,这是《籑诂》的最大失误;又说,《籑诂》的注疏只收到唐代,“唐以后几成空白”,“宋元明阶段训诂资料一片空白”等等。[8]
然而据笔者统计,《籑诂》并不“拒绝宋以后的经籍旧注”,宋元明阶段的训诂资料,也绝非“一片空白”。在该书引用书目中,我们所知为宋代书的,至少在40 种以上。如朱熹《仪礼经传通解》、洪兴祖《楚辞补注》、黄干《仪礼经传通解续》、聂崇义《三礼图集注》,以及《孟子音义》《六经正误》《诗考》《群经音辨》《周易辑闻》等10 来种,都是宋代的“经籍旧注”;还有《广韵》《集韵》《类篇》《礼部韵略》《小尔雅》《韵补》《班马字类》等训诂专书多种;《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类书,以及史书、笔记、书跋、考索、法式、集说等等。至于宋以后的书,辽有陈栎《读诗记》,金有韩道昭《五音篇海》,元明有熊忠《韵会》、程瑞学《春秋本义》、董真卿《周易会通》、吴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杨桓《书学正韵》,以及孙瑴《古微书》等多种,怎么能说是“一片空白”呢?
此外,宗教授具体揭举《籑诂》未收的多种图书,大多并不确实,如:《文选五臣注》见于《籑诂》影本第962 页,《玉篇》首见于《籑诂》影本第32 页,《说文系传》首见于《籑诂》影本第50 页,《孝经疏》首见于《籑诂》影本第3 页,洪兴祖《楚辞补注》首见于《籑诂》影本第22 页,胡三省《通鉴注》首见于《籑诂》影本第4 页。只有邢昺《尔雅疏》《论语疏》、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及宋人的几种笔记,阮书确未收录;但另收有《汇纂》未收录的王应麟《困学纪闻》等多种。
至于宗教授所说《广韵》《集韵》也是《汇纂》“新增的书目”,不知从何说起!《籑诂》“凡例”说,“《佩文韵府》未载之字,据《广韵》补录,《广韵》所无,据《集韵》补录”。三书均无的少数字,则列为“附录”。如《籑诂》 卷一东韵,据《广韵》 登录50字,据《集韵》登录19 字,“附录”3 字。以后各卷各韵,均有这种据《广韵》《集韵》补录的记载。而且,《广韵》和《集韵》作为列目书,也频繁见于集中,《广韵》凡522 见,《集韵》凡737 见。而《籑诂》全书影本总共1072 页,《广韵》和《集韵》两书目总计出现过1259 次,平均每页可能出现一次以上,有时甚至一页出现多次。如《籑诂》 影本第28 页,《广韵》 出现4 次,《集韵》 出现8 次,共12 次;第29 页,《广韵》与《集韵》共出现11 次。只要随便翻翻书,就不难发现这两种列目书。
(三)收录范围窄,资料不丰富吗?
与上述二点相联系,《汇纂》主编者认为,《籑诂》“全然排斥宋、元、明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便在时间上缩短了收录的范围;而为“治经”,阮元引书主要关注“先秦儒家的经典”,又从内容上限制了收录的范围,这样也就会使资料收录不广阔、不丰富了。对此,前文已据事实辩驳得清清楚楚,不再赘说。
至于《汇纂》主编者所说,该书收录有“佛经”“笔记”等书,似乎较阮书广阔。事实上《籑诂》早就收录有此类图书,而且收录得并不少。阮书不仅率先收录有《一切经音义》《华严经音义》,还收录有《弘明集》《广弘明集》以及《翻译名义集》等佛学书;笔记则收录有晋张华的《博物志》,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以及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诸书。
清代小学鼎盛,成果丰硕。阮元的书也并非不利用这方面的成就。例如,据《佩文韵府》归字编辑,便是最明显的用例与成绩。其他如石经、碑版,引述颇多;地理、校勘,亦有发明。而利用辑佚、考证,更为突出。如《竹书纪年》,是晋代发现于汲郡战国魏墓中所藏竹简古文史书,后佚失。清代学者多有考证此书的成果,如朱右曾辑《汲冢纪年存真》、雷学淇有《竹书纪年义证》等。《籑诂》列目《竹书纪年》,显然利用了清代考证辑佚的成果。这方面的例证颇多,如《元和姓纂》《世本》《尸子》《楚汉春秋》《韩诗内传》等均此;而《佩文韵府拾遗补》《周氏孟子四考》《古经传鈎沉》等,更是直接引用清人著作。婉转责备《籑诂》不反映清代小学成就,“缺少了两千多年训诂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其实也不符合实际。
《籑诂》列目书和资料并非不广阔不丰富,还有一特别表现,即纬书资料的使用。“纬书”本是相对“经书”而言的,它产生于西汉,流衍于东汉,称“内学”,至隋炀帝时禁毁。这是一种混合神学附会儒家经义的书,其中混有神学迷信,但也保存了一些天文、历法、地理知识以及古代神话传说等,可资利用。至明代,孙瑴辑编有《古微书》36卷,包括易纬、尚书纬、礼纬、春秋纬、诗纬、乐纬、孝经纬等“七纬”,又有论语谶、河图、洛书等,因合称“谶纬”。清亦有多种辑本。阮元《籑诂》开始使用纬书时,似乎还有点缩手缩脚,多通过《古微书》“引”的方式,如影本第3 页、第7 页引《春秋考异邮》,第9 页引《春秋元命苞》,均如此,但还放不开手脚。到后来,便逐渐大胆使用,常见使用的多至19 种以上。应该说,这可能是阮书突破儒家经学界限的大胆创造,是有利于训诂,而无损于经学的可贵创造。这大约是《汇纂》主编者所不曾想到的吧。
(四)所谓“掠美”之嫌
宗教授还说,《籑诂》卷首的列目书里,有洪适的《隶释》《隶续》,而在正文里“却从不提及洪氏考释的成果”;并举有“四组材料”相对照,以图证明编者阮元有“掠美”之嫌。[8]这“罪名”近乎今日论著的 “抄袭”“剽窃”行径,是相当严重的。但笔者要用事实证明:这是唐突枉责先人!《籑诂》卷34 上声纸韵“旨”字下即明确列出:“《隶释·衡方碑》乐—君子,只作—”。至于“四组材料”,限于篇幅,这里只能就第4 组来说一说。《籑诂》影本第63 页支韵“朞”字下,引有4 碑,然后总括说“一皆作基”,这明显不是《隶释》体式。该书虽多释通假,但通假并非“释”之重点,故多以小字双行置于最末;且每碑分说,未见数碑通假总说的。其重点乃在“释”汉碑,兼及少量魏碑。碑之文字绝大多数为隶书,洪适首先“易隶为楷”,以楷书写定;然后进行考释,如建碑时间和地点、碑之史实、碑文说明、文字考证等,均附碑文后,低一字排,以帮助人们阅读汉碑。例如第“四组材料”中的第一篇《汉灵台碑》,全称《成阳灵台碑》,收录在《隶释》卷一,碑文中有“基年鱼复生”语,洪适估计将有人不懂,需加解释,于是引《淮南子》传说史事,释云:“ 鱼如鲤鱼,有神灵者,乘行九野。读如蚌”;又谓“汉代修祠之后,鱼复生,故有灵台”,且“服之延寿”等。释文近百字。宗教授把阮书所引碑文的“”抄掉了,也辜负了洪氏的解释。而所举第“四组材料”的第四碑《严举碑》,宗教授称《隶释·严举碑》,笔者遍查《隶释》,并无此碑;再查中华书局1985年11月版的《隶书》《隶续》合印本(影本),在《隶续》卷十一,收录有《都乡孝子严举碑》及“碑阴”;《籑诂》所引的正是此碑。事实证明:前碑漏一“”,后碑错一“续”,纯属宗文之误;而阮元则并无“掠美”之嫌。
三 、开创者与模仿者
有清一代学术之开派宗师顾炎武曾论著书之难:“其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其可传也与。”(《日知录》卷十九)既不蹈袭古人,又对后世有用,正是开创者追求的“独创”精神和“务实致用”品格。著书如此,编书何尝不如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阮元主编《经籍籑诂》,所体现的也正是这种开创者的“独创”精神和“务实致用”品格。他曾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尝病古人之诂散而难稽也,于督学浙江时,聚诸生于西湖孤山之麓,成《经籍籑诂》百有六卷。”[9]钱大昕《籑诂》序中也曾指出,亁嘉学者多认为“治经必通训诂,而载籍极博,未有会撮成一编者”;前此,戴震等虽曾创议,却未及实行;阮元完全无所依傍,凭其雄才卓识,于视学浙江时,“手定凡例,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择浙士之秀者若干人分门编录,成书百有六卷。[2](P1)于是实现了王念孙在《籑诂》序中所称誉的境地:“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2](P2)因而在学术史上,开创了一种“总纂体式”——网罗前训,征引群书,汇辑各种训诂资料,不加刊改,保存原貌,纂辑成有关训诂的一种大型工具书。而其所定“凡例”,便构成这“总纂体式”的诸多构件系统:从采辑训诂的种种源头,传注诂训的组构方式及术语系统的创设,因韵归字办法,同诂详略与诸书叠见者的次第安排,以及本义、引申义和名物象数之先后,群经次第,引书称名,注疏称谓,诂训版式等等,皆详为设定,从各方面具体体现“总纂体式”,成为纂辑全书的指南。
前些年,有关《汇纂》的许多评论文章,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汇纂》远远超过了《籑诂》;表扬一下《汇纂》,必贬损一下《籑诂》。但被邀与会的学界朋友,评价也并非一律。例如尉迟治平教授虽也表彰《汇纂》,却不曾着意去贬损《籑诂》;并对阮元这部书作了相当深刻,也相当精彩的评价:
《经籍籑诂》在学术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创立了故训总纂这样一种文献体制……这种展现故训本来面貌,提供语料原始形态的思想,可以说是工具书编纂的“绿色环保”意识,是《经籍籑诂》学术价值精粹所在。[10]
读尉迟文章,喜闻“创体”高论,不禁拍案称赏!毕竟不负开创者阮元前辈的一番苦心。
阮元的《籑诂》,既是“古人之所未及”的开创性著作,也是“后世之所不可无”的致用好书。不少论者曾指出,清郝懿行《尔雅义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日本的《大汉和辞典》、台湾的《中文大辞典》、大陆近年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等,都受益于《经籍籑诂》,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而当《汇纂》出版以后,有的老先生和少先生宣布,要把《经籍籑诂》“拉下马”、弃置不用的时候,却有位吴金华先生出来说话了。他也肯定《汇繤》,原先也准备不看《经籍籑诂》了,“特别是电脑发展以后,觉得《经籍籑诂》用处就不是很大了”,但前两年突然又用了,为什么?
因为有一位博士生研究日本的《万象名义》。这本书里引用了大量的故训,很不好整理,疑点、难点、盲点不可胜数。这些怪故训是哪里来的?这本博士论文后面附了一大堆,全部打问号,空在那里。我看了这些,觉得很眼熟,便试着把《经籍籑诂》拿出来,一个晚上就找到十多处。我当时想,这是不是偶合?第二天晚上又翻出十多处。不是我的水平比那位博士高,是有《经籍籑诂》。尽管它是很陈旧的,但它告诉你这是韦昭的注,这是孔颖达诗经注中的一小段。然后再去对原文,很快你就找出来了,错字,漏文全部纠正了。[11]
他的话说得很具体,也很生动。《籑诂》的价值,对后世,对我们今日,还是有用的。这书的功用,吴金华总结说,是“通过时间来检验的”。他也推断后继者《汇纂》的价值,说的是“将来”,也就是还得“通过时间来检验”。
笔者也曾使用过《汇纂》。某年,读曾国藩的日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初二日末署“初度日识”。“初度日”怎么讲?搬来《汇纂》,查到第223 页“初”字下第②注项,“—始也”。后引《楚辞·离骚》“皇览揆余—度兮”,王逸注,仅顺同一注项释“初度”为“始也”。这显然不能解决疑问。而《汇纂》的列目书《山带阁注楚辞》,注谓“初度,初年之器度”;《汇纂》却未采录。只好再去翻《籑诂》,在影本第89 页上平声六鱼“初”字下的注项,基本为《汇纂》所沿用,但“始生也”一项,却被《汇纂》抄录者漏掉了。王逸注为屈原降生的年月日;钱澄之《屈诂》谓“初度,犹初生也”;吴世尚《楚辞疏》称“初度,始生之日也。在天为度,在历为日”[12](P227);王夫之《楚辞通释》注为“初生之日”,最简明。由此,后世即以“初度”指生日。曾国藩的日记,九月初二后间断月余。他生于辛未(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至辛丑(1841)十月十一日三十岁生日这天,再续写日记,多自责自勉的话,故有“初度日识”云云。次日即是十月十二日的日记了。
再者,有书才有义项或注项;缺了某一种书,就必定会缺少某些义项或注项。《籑诂》列目书共260 多种,其中的180 多种书,是《汇纂》所没有的。例如,《汇纂》“中”字下尽管有多达528 个注项,因为没有《孟子章指》这一种书,也就缺少了“履其正者乃可为中”这一个重要的注项。又如,《籑诂》卷二“冬”字下,共32 注项,《汇纂》沿用8 项,漏收的约20 项,几占三分之二;而因没有《初学记》《洪范五行传》等书,缺的即达4 项。因此,笔者与吴金华先生有同样的感觉:《经籍籑诂》还是有用的一本好书;碰到《汇纂》上找不到的,不妨查查《籑诂》,幸或亦有收获。
在纂辑体式上,作为后继者的《汇纂》显然是对《籑诂》的继承与模仿。这种继承与模仿的过程,自然也能有创造,有超越。但后继者的创造,一般来说难以超出《经籍籑诂》所开创的“总纂体式”。正如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书写体式,后继者班固的《汉书》,在继承与模仿中确有创造,其“志”如《艺文志》等便为后来一些史书所承继;但在整体上并未超出“纪传体”模式。后此官修的20 来种史书亦复如此。在对《籑诂》的继承与模仿中,《汇纂》确也有不少进步与创造:
(一)在编排格式方面。 《籑诂·凡例》 规定,“以本义前列,其引申之义辗转相训者次之,名物象数又次之”;每条注项之间,加圆圈隔开;所释字头,在引文中以“—”代替。这些大都为《汇纂》所沿用,而《汇纂》的“凡例”规定得更细致,格式更为完善;每一注项,分别用阿拉伯数码编号,提行排列,比《籑诂》双行小字联排的版式,更显层次分明,清爽多多。这自然也反映出辞书编写在现代取得的巨大成绩以及现代印刷技术的巨大进步。
(二)在检索便利方面。《籑诂》“归字谨遵《佩文韵府》”,有利于贯彻“因声求义”的原则与方法;对当年熟悉音韵的文士,也许并不难检索。但200多年后,对今日的一般读者来说,检索就有相当难度了。世界书局1936年的影印本,成都古籍书店1982年影印本,都加上按笔画的《目录索引》,稍方便一些。而《汇纂》改用《康熙字典》214 部首顺次归字,则又方便得多。其中虽然有若干部首,例如犬(犭)、肉(月)、艸(艹)、邑(阝)、阜(阝)、辵(辶)等,也令一些人稍感不便,但记住就好了。《汇纂》还附有汉语拼音索引,可供检索;比《籑诂》的笔画索引编排更合理,更方便。
(三)在资料详备方面。《籑诂》“凡例”中说:“此书采辑,杂出众手,传写亦已数过,讹舛之处,或亦不免。凡取用者宜检查原书,以期确实。至于遗漏,谅亦不少。”《籑诂》正编成书仅二年许,续编“补遗”时间或稍长,但还是过于仓促。《汇纂》历时一十八载。常言道,慢工出细活,其讹误遗漏,自然会较《籑诂》少一些,资料收录也较准确详备一些。
在笔者看来,《汇纂》作为继承者与模仿者,能有如许进步和创造,是值得肯定,值得高兴和欢迎的。但是《汇纂》的主编者似乎还不满足,而认为《汇纂》“远远超过”了《 籑诂》,并希求取代《 籑诂》,期望《汇纂》成为“精品”。今后会怎么样呢?还得“通过时间来检验”。
四 、大锅饭与掌勺人
《籑诂》与《汇纂》,都是“采辑杂出众手,传写亦已数过”的书。用较为时髦的话来说,是“集体”主义、“团队”精神的产品;而通俗的说法,就是“大锅饭”。
在中华文化学术史上,大型的资料总集和大型的工具书,多为众手所编撰。其质量优劣,价值高下,虽与众手相关,但更重要的则取决于主要负责的主编、总撰官之类。“大锅饭”味道如何,好吃与否,取决于“掌勺人”之手。
例如,宋的《资治通鉴》,294 卷,又考异和目录各30 卷,由英宗治平三年(1066)命设书局编撰,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成书,历时一十九年。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始,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计1362年史事,为我国大型编年史书。其主撰司马光,身为进士、大臣,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均亲自动笔。因而此书不仅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也为史学工作者提供了相当系统而完备的资料,堪称上继《春秋》编年史的典范之作。
再如《康熙字典》,由清帝玄烨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三月初九日谕南书房侍直大学士陈廷敬等:“至于字学并关切要,允宜酌订一书”,“勒为成书,垂示永久”。于是朝廷召集许多学者官员,集体编纂,至康熙五十五年编成,有闰三月十九日之《御制康熙字典序》冠于卷首。总阅官张玉书、陈廷敬及纂修官员,有“大学士”,或各部“尚书、侍郎”,或“经筵讲官”,或翰林院“侍读”“侍讲”“编修”等等,均为饱学之士。故《康熙字典》能具三大优点:(一)计收47035 字,200 余年间为我国字数最多的字典;(二)尽力列举每一个字的不同音切和不同意义,可供检择;(三)对每字每义(除少数僻字僻义),都力争引用“始见”古书的用例。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二十九日,奕绘、阿尔邦阿、那清安、王引之等“为重刊字典完竣辑录考证一併进呈”的奏章,称赞说:“诚字学之渊薮,艺苑之津梁也”;然而又说:“卷帙浩繁,成书较速,纂辑诸臣迫于期限”,缺点错误也不少。王引之等所撰《字典考证》,共更正2588 条。①详见《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1月版、1980年第3 次印本所附《康熙字典考证》首页的奏章。但时至今日,《康熙字典》仍然是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者案头必备的重要工具书。
至于本文所论的《籑诂》,如前所述,不仅开创“总纂体式”,而其“凡例”,则具体组成“总纂体式”的诸多构件系统,成为掌控全书的“指南”,并给后继者以深远影响。主编者阮元,博学淹通,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时,年仅二十有五。“早被知遇,敕编石渠宝笈,校勘石经,再入翰林,创编国史儒林、文苑传”;又“集四库未收书172 种,撰提要进御,补中秘之缺”;又采集史书和四库所收天文、历算、技艺等专门人才资料,编成280 人传记的《畴人传》。嘉庆四年(1799),偕大学士朱珪典会试,“一时朴学高才,搜罗殆尽”。可见,在主编《籑诂》之前,阮元的学问就已经相当好,成绩显著,人望也不错。《籑诂》刻本,于上下平声及上、去、入声卷首,均署“经筵讲官、南书房翰林、户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前提督浙江学政阮元撰集”。这许多头衔,均是阮氏主编该书之前所得。后来他还升任湖广、两广、云贵等处总督,以及体仁阁大学士等高位官爵,均非主编《籑诂》所能致者。他在任还继续提倡经学与朴学,校刻《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并由经籍训诂,求证于古代吉金,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著有《积古斋钟鼎款识》等。②参阅《清史稿·阮元传》。按,其中《石渠宝笈》一书,于乾隆十年(1745)先已成初编44 卷,录当時宫廷所藏书画;阮元奉敕参编的,应系指该书的续书“重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或“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现代著名学者钱穆曾给阮氏以高度评价:“芸台犹及乾嘉之盛,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材,领袖一世,实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13](P478)由此可见,阮元“博学淹通”,是一位高明的“掌勺人”。因此,他掌勺编纂的《籑诂》这一“大锅饭”,质量才会相当高,至今人们仍觉得味道不错。
作为《籑诂》的后继者,《汇纂》主编者的情况,似乎与前述三书不大相同,或者竟大不相同。前三书的主编者在主编该书之前,均为饱学之士,其头衔多取得于前,并不依赖于他们所主编的书。《汇纂》的主编者也有不少头銜,但多取得于主编该书之后。《汇纂》是集体协作的“团队”产品,它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大伙的成绩;“掌勺人”只占其中一份。如果个人多占,或更赖以晋升,则不符合公平公正原则,将对学术风气与学界后辈造成不良影响和误导,岂可轻忽!
2015年4月5日草就5、6月间陆续修改于珞珈山寓所
[1] 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主编.故训汇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阮元.经籍籑诂[M].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
[3] 宗福邦.《故训汇纂》与《经籍籑诂》[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
[4] 王力.训诂学上的一些问题[J].中国语文,1962,(1).
[5] 王宁.《故训汇纂》的价值与应用[A].《故训汇纂》研究论文集 [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 萧红.以马部字为例看《故训汇纂》的价值[J].长江学术,2004,(6).
[7] 宗福邦.精品意识·团队精神·严谨学风[J].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5).
[8] 宗福邦.《经籍籑诂》的编纂思想及其得失[J].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2012,7.
[9]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A].揅经室二集:卷七[M].清道光三年(1823)文选楼刻本.
[10] 尉迟治平.面向学术,服务学者——论《故训汇纂》的学术性[A].《故训汇纂》研究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1] 罗积勇.《故训汇纂》学术研讨会综述[A].《故训汇纂》研究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2] 何金松.屈诗编年译解[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
[1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