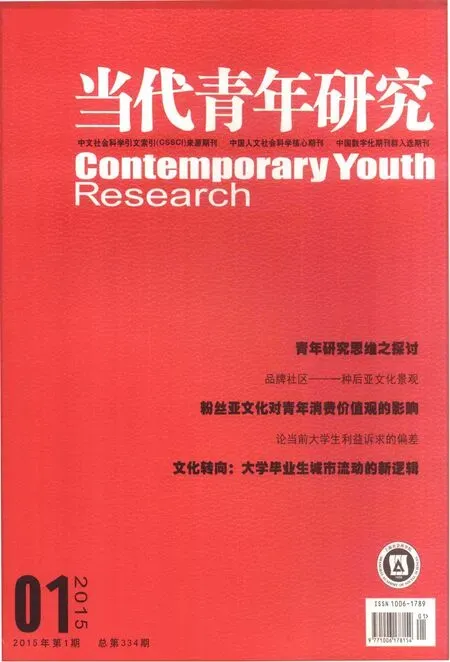青年研究思维之探讨
李 洁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目前,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大多经由“直陈理论式(自发地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为直接目的的具体理论研究)、本体内涵式(以解决理论中的问题为直接目的的对理论的抽象研究)、形式逻辑式(以理论与现实的关系为直接研究对象,直接指向理论的表达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这三个阶段发展到了“实践为中介”(在认识到理论的悖论本性之后,自觉地摆脱抽象的探讨,指向具体问题的实践探讨)的阶段。[1]因此,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也开始了从简单到复杂、线性到非线性、现成到生成、实体到关系、平面到立体、功利到人文的转向。而青年学作为一个直接以多学科、跨学科(涉及哲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医疗卫生等领域)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其学术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自然也随着各学科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变。基于多学科跨视域研究,目前有如下四种青年理论研究思维值得我们关注。
一、群体思维
生态学中有一个种群(population)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占据一定空间的同种生物的所有个体。种群中的个体并不是机械地集合在一起,而是彼此可以交配,并通过繁殖将各自的基因传给后代。种群是进化的基本单位,同一种群的所有生物共用一个基因库。也就是说,每个种群有着与其他种群所相区别的特征,而多个种群共同存于一个生活环境之中则演变为了部落。依据这一概念,人类相对于其他生物而言是一个种群,而青年相对于整个人类部落而言,它又是一个小小的种群。所以,在许多青年研究学者眼里,“青年”是指社会群体中低于“掌握社会权力的长者”的青年群体。[2]这便是群体研究思维的开端。
由于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面临的问题和应对的办法在当代中国日趋多样化和多元化,所以,青年群体分化或群体之间异质性的增强也已成为当代的特征之一。[3]于是,青年演变为了由一个个各具特色的小青年群体所构成的大部落,它可以从年龄、性别、国别、出生地、健康情况、婚育状况、经济水平、文化程度、政治身份、从事职业、法律地位、家庭角色等维度来解构。[4]比如,按年龄有未成年人和青年成人;按性别有男青年、女青年、跨性别青年(包括易装易性者、同性恋、双性人、间性和雌雄同体);按健康情况有身心健康青年、残智障青年和患心理疾病的青年;按婚育状况有已婚族、离异族、丧偶族、丁克族、独身贵族、剩男剩女等;按文化程度有低学历青年和高学历青年;按经济状况有穷二代和富二代;按国别分有中国青年和外国青年;按出生地有农村青年和城市青年;按政治权力有民二代和官二代;按政治身份有党员、民主党派和群众;按法律地位有守法青年和犯罪青年;按家庭同辈成员有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按家庭长辈成员有单亲家庭子女、非单亲家庭子女、隔代抚养的子女;按以职业状况为基础,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有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
在这些青年群体中,有处于相对优势的群体,如成年人、男人、健康青年、高学历青年、富二代、城市青年、官二代、青年白领等;也必有相对弱势的群体,如未成年人、女性、跨性别青年、身心不健康青年、低学历青年、穷二代、农村青年、民二代、犯罪青年、失学无业青年等。同时,因为“边缘效应”(指由于群落交接区生境条件的特殊性、异质性和不稳定性,使得毗邻群落的生物可能集聚在这一生境重迭的交错区域中,不但增大了交接区中物种的多样性和种群密度,而且增大了某些物种的活动强度和生产力),在上述这些青年群体中又会分化出特征更为复杂的特殊小群体,如女汉子、丁克族、独身贵族、剩男剩女、楼宇青年、男幼师或男护工等。因而,青年研究的群体思维不仅是停留在将青年视为社会群体中的一员的层面,而是要进一步关注青年群体内部因社会分化、差异和不平等而产生的多元化、多样化的小群体,尤其是相对弱势和特殊的群体。
二、生活世界思维
“生活世界”是产生于20 世纪20 年代西方现象学和生命哲学的基本范畴。这一概念最早由现象学大师胡塞尔提出。之后,海德格尔、赫勒、哈贝马斯等学者在不同学科领域使用并延伸了这一概念,因而也产生了诸多替代词或义同词,如“生活”、“现实生活世界”、“现实生活”、“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日常共在世界”等。这些哲学家虽然审视生活世界的角度不同,理解各异,但他们仍然有一些共同点——“在他们看来,生活世界不是一个单一的科学世界、物理世界或心理世界,而是一个未经科学专业术语泛化的日常语言和日常意识中的世界;不是观念意识世界或本体世界,而是一个主客统一的生活经验世界;不是由各种符号建构的文化世界,而是历史与现实浑然一体的多样化世界”。[5]可见,在他们眼里,生活世界仍然是一个抽象世界。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家卡尔·马克思认为,生活世界是指人的以物质生活为基础或前提的现实生活过程;是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真正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生活世界本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包括“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生活世界本身是不断生成和更新的——是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生活过程。总括而言,若要把握生活世界的意蕴,其“关键在于意义世界和构造过程,这是造成生活问题或问题生活关键环节”。[6]马克思的这一实践哲学之思弥补了前人形而上之空洞缺陷,让“应有”与“现有”、“理想”与“现实”通过“实践”从“对立”走向了“对话”。可见,生活世界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获得了更科学、更全面、更丰富的内涵意义。
受西方文化哲学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对生活世界进行理论研究始于20 世纪80 年代、90 年代以后研究热情高涨,生活世界这一概念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流话语之一,随即被移植到教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伦理学等各学科研究领域之中。当从事青年问题研究的学者提倡“回归青年的生活世界、绽现青年的生存境遇”之时,说明他们内心深处早已默认“生活世界”为青年学之青年研究的逻辑起点。所谓逻辑起点,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的一个起始范畴,是一门科学或学科理论体系中思维的起点,是学科研究对象系统中的核心要素。生活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物”的概念,是连接青年学学科系统内及本系统与外系统各范畴和概念群的关键点,指转向“人的现实生活,指向人的生命意义”的合乎逻辑思维的开端。
生活世界,站在实践哲学的高度,是指人的全部生活领域,而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它是指人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7]基于此,生活世界的研究思维也可分为实践方式和文化方式两种。首先,实践研究思维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青年的日常生活世界,即青年的衣食住行、休闲健康等日常生活状态;二是青年的社会生活世界,即青年的参政、婚姻、就业、学习、交往等社会生活状态;三是青年的精神生活世界,即青年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心理与能力发展等精神生活状态。[8]其次,文化研究思维方式则将青年的生活世界视为立体的三维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青年为家庭、学校、企业、社区,以及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法律等环境因素由内而外地包围着、浸润着。[9]也就是说,青年的生活世界是青年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结果,即文化世界就是人的生活世界。由于文化的本质结构表现为隐性文化(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心理)与显性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其中隐性文化是文化的最高凝聚或内核,它是一切文化的主体设计和承担者,或者说内隐文化是一切外显文化的制作与表达,所以,生活世界的文化研究思维同样也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青年生活世界的内在深层次结构,即青年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心理;二是青年生活世界的外显文化表征,即青年与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科技、人口等社会文化要素之间互动而形成的相应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文化产物。当研究者运用生活世界思维去考察青年群体通过实践创造的青年文化现象(探究其意义世界与构造过程)之时,如果将实践研究思维与文化研究思维两种方式结合,就能更好地、全面系统地理解青年——这个群体及其生活,或这个观念及其文化。
三、 场域思维
场域(field)这一概念既是多学科观点融合的产物,也是顺应个体和社会关系研究的一个综合平台。最经典的场域理论来自于国外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德裔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一位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勒温的场论与物理学的场论有着一定的联系,是指人的每一个行动均被行动所发生的场域所影响,而场域并非单指物理环境而言,也包括他人的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因素。其中,观察者知觉现实的观念称作心理场(psychological field),被知觉的现实称作物理场(physical field)。因而,勒温的场论通常被作为“心理动力场”,或被定义为“心理生活空间”,即综合可能事件的全体,其包括三个因素:一是准物理事实,即一个人在行为时,对他当时行为能产生影响的自然环境;二是准社会事实,即一个人在行为时,对他当时行为能产生影响的社会环境;三是准概念事实,即一个人在行为时他当时思想上的某事物的概念,这一概念有可能与客观现实中事物的真正概念之间存在差异。[10]
布迪厄的“场域”是指社会高度分化而产生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小世界”,每个小世界都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学术场域、教育场域等,正是这些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子场域”构成了社会这个“大场域”。布迪厄强调,“社会科学的真正对象并非个体。场域才是基本性的,必须作为研究操作的焦点”。具体步骤是:第一,必须分析与权力场域相对的场域的位置。完全自主和孤立的场域是不存在的,其中权力场域相对于其他场域如文学场域、科学场域等更具有“元场域”的特征。第二,必须勾勒出行动者或机构所占据的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结构。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为了控制这一场域特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相互竞争,从而形成了种种关系,制约着不同位置的行动者的策略选择。第三,分析行动者的惯习,即行动者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的千差万别的性情倾向系统。[11]
勒温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虽然都是对个体和社会关系的考察,但是两者的研究路径完全相反:前者以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中心展开,考察其与环境的互动,而后者以环境中的资本(权力与关系)为基点,考察其制约下的行动者及其惯习。尽管如此,他们路径的两极(起点或终点)却都聚焦于人的心理与行为(惯习)。这似乎直接预示着人的心理与行为(惯习)就是场域中最深层次的、最核心的固有本质。换言之,无论是选择勒温还是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青年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的起点或终点都要观照青年的心理与行为(惯习)。如果将青年研究视为一个不断循环发展的自然的连续过程,那么青年的心理与行为(惯习)显然成为了永恒的始发站,而这恰好为笔者所倡导的“青年的精神世界是青年研究场域选择的首要维度也是核心维度”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合理性解释。[12]进而可以推断,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在相互关联的多样化“子场域”还是社会这个“大场域”,凡是“掌握社会权力的长者”在场或出场的地方,青年或青年群体都只能被冠以“次生、非主流、非正式”的标签,因而,“非正式领地”中青年的精神世界则是青年研究“场域”选择的延伸维度之一。然而例外的是,唯有“虚拟社会”这一新兴的子场域为青年网民所掌控,虽然相对于社会这个大场域,这个子场域真的很小,但是,在这里却可以找到其他所有子场域中被长者权力所掩盖的最革命、最新奇和最具有创造力的青年精神世界——它代表了希望和未来,正在加速度地影响和渗透着我们的现实社会这一大场域。所以,“虚拟社会”必然成为青年研究“场域”选择的又一延伸维度。可见,无论是始于还是终于青年的心理与行为(惯习)的场域研究思维,它们都是一种能够很好地顺应并践行青年为本的青年研究思维。
四、圈子思维
1999 年,瑞士心理咨询师 朱瑞·威利提出了“小生境”(niche,即生态位)的概念——个体把自己的环境造成一种个人化的“小生境”。生境是生态学术语,又称栖息地,指一个生物体,或者一个生物群落所栖居的地方,包括周围环境中一切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的综合。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人的生境里包括了许多社会因素。现实生活中,我们只注意到某人的大环境,很少在意他或她的小生境——即直接影响 他或她的具体的人和事。大环境可以载入史册,有据可寻,而具体的有怎样的小生境对他或她施加影响,则只能进入他或她的“私人领地”才能知晓。这个小生境或者说“私人领地”就是本文所说的“圈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生境——圈子,它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心理并左右着他或她的行为选择。所以,圈子思维就是要关注青年的小生境——他或她的“私人领地”。
那么,如何运用圈子思维关注青年的小生境或私人领域呢?我们或许可以先从刑法学有关预防或矫正青少年犯罪行为的研究中获得一些启发。桑普森等人通过调查发现,青少年犯罪是非正式社区秩序混乱和社会支持缺乏的结果,而通过监管和惩罚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效果并不明显。[13]于是,犯罪学家开始尝试运用“恢复性司法理论”(刑法领域兴起的一种新的司法 理论,指在有关机构或组织的主动参与下,促成犯罪人与被害人的直接接触,进而使犯罪人从对方所受的伤害中认识到自己的罪责,再通过协商给被害人以精神上或经济上的补偿,达成双方的和解,并由此最终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与秩序的司法模式[14])开展一种具有行为矫正功能的家庭团体活动,这种家庭团体活动在南美被称为“会议圈”,在北美则被称为“治疗圈”。 在 活动中,罪犯与受害者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在会议中坐成一个圈,讨论犯罪的后果以及怎么纠正自己已做错的事情,目的是让青少年罪犯和受害者的生活一起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圈子里的支持者是多样化的,除了家庭成员或其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外,还可能有本社区的老年人、足球教练、芭蕾舞老师、邻居或有共同爱好的朋友等。在这些支持者中,总会存在青少年罪犯认同或尊敬的人,圈子作用在于发现青少年罪犯认同或尊敬的支持者,通过这些支持者的帮助与感染,激发青少年罪犯想要做痛改前非的另一个自我,重新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显著的变化是会议活动之后,家庭中忽略或虐待青少年的事件在一年中减少了一半,而参加会议的青少年罪犯也比那些去法 庭的青少年罪犯要快乐得多。[15]
与此同时,受到犯罪学家研究成果的启发,教育学中也兴起了一股将恢复性司法理论运用于青少年行为塑造的教育实践之中。与犯罪学家的“会议圈”或“治疗圈”不同,教育学家把他们组织的会议活动称之为“发展圈”或“学习圈”,这里的圈子不是指一个聚集在一起处理犯罪问题的特别小组,而是指青年生活的永恒特征。圈子里有核心成员和临时成员。其中,核心成员有家长或监护人和兄弟姐妹,还有青年人选择的祖父母、姑舅、密友、老师、邻居、运动教练、父母的好友或社区其他成人等,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参与所有的圈子活动直至青少年成功进入大学或者走上工作岗位,甚至当青少年触 犯法律之后作为他们的支持者继续参与“会议圈”或“治疗圈”;而临时成员包括青年人现在的老师、现任女友或男友、新伙伴、由圈子的促成者或家长带来的专家、少年犯罪或恐吓行为中的受害者及其支持者等。一般而言,圈子每6 个月会晤一次。在会晤中,圈子的促进者负责介绍新成员并宣读青少年在上次会晤时拟定的生活目标;青少年则被要求总结他或她这6 个月对生活目标的执行情况,并明确未来6 个月的生活目标;其他成员则被要求报告在这期间来他们是否设法对青少年传递帮助与关爱,或发现青少年生活中的任何危机与挑战——需要关照和支持的地方,并帮助青少年明确未来6 个月的生活目标。圈子成员一起讨论这些主题直到青少年最后说出她或他的新目标以及为他们提供帮助的成员的名字为终止。整个讨论过程始终充满着青少年“实现了什么”、“努力了什么”的寄语,而促进者的关键技能是引导圈子对青少年成功的认可和对他们失败的帮助(而非批判和指责)。研究显示,这种运用社会关系网来管理学校、促进青少年发展的恢复性方法能够将学校暴力减少到一半。[16]
圈子思维之所以在犯罪和教育领域获得成功运用,是因为犯罪学家和教育学家都发现将青少年孤立或隔离起来处理他们的发展问题(如较低的学校表现、仇恨学校、逃学、恐吓、辍学、毒品滥用、犯罪、自杀、孤儿和失业等)的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是失败的),“对孩子而言,内化他们行为和选择的最好方式是帮助他们建立健康的关系并理解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关系,因而,与迫使他们远离群体的做法相反,是让他们说出他们所伤害的人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努力做一些事情去恢复这个关系,比如,可以一起玩游戏表示他们真的很抱歉,想要和大家和好如初”。[17]所以,在家庭、学校和社区关照背景下为所有青少年,不仅是问题青少年或青少年罪犯,还有渴望学习进步的青少年 的发展寻求由圈子所构成的非正式支持(是帮助和关爱而不是指责和放弃),尤其是来自圈子成员的无条件的爱的理解、尊重与信任,才是治疗圈或发展圈的目标与愿景得以成功实现的根本。因而,在青年研究中,圈子思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够发现青少年私人领地或小生境中积极或消极影响到他们成长与发展的具体的人和事的有力武器。对于研究者而言,如果对由这些人和事所构成的非正式支持圈的特征与状况了如指掌,那么无论是想要发现青年现象背后的问题还是要探索促进青年成长与发展的规律,都应该是很容易的。
五、青年研究思维的内涵
思维方式即人们“怎样想”,它直接规范着“想什么”、“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它隐匿于人们的思维深处,制约着人们可能的提问的方式,而这种提问方式,也预设了问题的可能选择、问题的可能求解方式以及可能选择的行动策略。[18]因而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思维问题依然是青年研究中最深层次的问题,它涉及到如何理解并应答青年及与青年相关的问题,而这又将直接影响青年学术发展和青年工作实践。所以,能否有效解决思维的障碍问题是进行青年研究并发展青年学之根本。而上文呈现的 四种理论研究思维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向“实践为中介”转向的产物,它们对于探索青年及与青年相关的问题、顺应以青年为本的青年研究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昭示着青年研究思维方式的本应内涵。
首先是怎样想——置身多元文化视域。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全球化发展,尊重人类文化多样性、差异性已成为人们普遍的共识。不同民族、种族在社会文明进程中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不存在某种文化是完全优秀或低劣的。每一种文化都应当自由、平等,不同文化之间应相互交流与沟通,增加对话与理解。因此,青年研究应加强对不同国家、种族或民族等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青年群体的深入研究,尤其要关涉有特殊需要的弱势群体。
其次是想什么——关注青年个性与发展。有许多研究者将生活世界默认为青年研究的逻辑起点的缘由是他们已将“青年个性与发展”作为青年研究中最基本、最普通的范畴。比如,有学者将青年学的理论体系构成分为青年的认识问题、发展问题与教育问题三部分。青年的认识问题属于个性心理范畴;而青年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青年发展。为了更好地实现促进青年发展,就必须了解青年的心理特征,而群体思维、生活世界思维、场域思维与圈子思维则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其心理特征的有效策略。
再次是做什么——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存在的两种研究范式,“它们相互之间有很多相辅相成之处,其连续性多于两分性”。[19]青年学既然是以多学科跨视域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则必然要求综合运用多元研究方法。只有通过不同范式之间和不同方法之间的平等对话,才能真正使研究者和被研究者获得解放,也才能在视域融合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和新的生长境界。[20]比如,研究者用问卷法可以发现青少年犯罪类型与发展趋势,用访谈法则可探索青少年犯罪生成的心理行为机制,这两种研究范式的成果能为我们全面理解青少年犯罪现象并寻求合理治理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最后是如何做——架构青年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上述四种研究思维在运行过程中始终未曾将青年孤立于社会文化发展之外,反而是淋漓尽致地架构了两者的互动关系。如,青年群体的化分以其社会文化表征为依据,如生理特征、身份地位、文化背景等;生活世界本是青年与社会文化发展不断互动而创造的,其探究方式也离不开实践方式与文化方式;场域思维是考察家庭、学校、企业和社区中青年与“掌握社会权力的长者”之互动关系;圈子思维是关注以青年为中心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见,青年研究只有逃脱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演绎怪圈,走进家庭、走进学校、走入企业、走入社区,通过架构青年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互动,才能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与社会价值。总之,青年本就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下的产物,若脱离了社会文化发展,青年亦不复存在,自然也就没有真正的青年研究。
[1]孙阳春.论教育理论研究思维方式的转换[D].东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2003:8-9.
[2]F.马赫列尔.青年问题和青年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21.
[3]陆玉林.论青年的意义构成[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1):1-6.
[4][8]李洁.2011 年我国青年研究的发展[J].河北学刊,2012(5):194-198.
[5]晏辉.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基本方式[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1-3.
[6]邹兴明,李芳英.走出生活世界“研究之困境”[J].河北学刊,2004(2):51-54.
[7]李洁.海派学习文化研究——来自成人生活世界的考察与分析[M].法律出版社,2011:83-84.
[9]李洁.青年研究路径的教育学探寻[J].学术探索,2012(6):170-173.
[10]勒温的场论[EB/OL]. http://www.pep.com.cn/xgjy/xlyj/xlshuku/xlsk1/xf/xlsk3/201008/t20100827_814994.htm,2014-11-26.
[11]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146-149.
[12]李洁.青年研究“场域”的选择维度[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3):1-5.
[13]桑普森,劳布.汪明亮等译.犯罪之形成:人生道路及其转折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0.
[14]衣家奇,姚华.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理念的重构性转折[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6(2):10.
[15][16]John Braithwaite .Youth Development Circles[J].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2001(2): 239-252.
[17]Heather Metz. Restorative Justice and Educating for Peace[D].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Arts in Education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Social Justice from Prescott College,2008:55.
[18]陈福祥.“复杂范式”视域下的成人教育研究思维方式[J].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7(12):11.
[19][20]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469-483.
- 当代青年研究的其它文章
- 大学生微博中的后现代价值观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