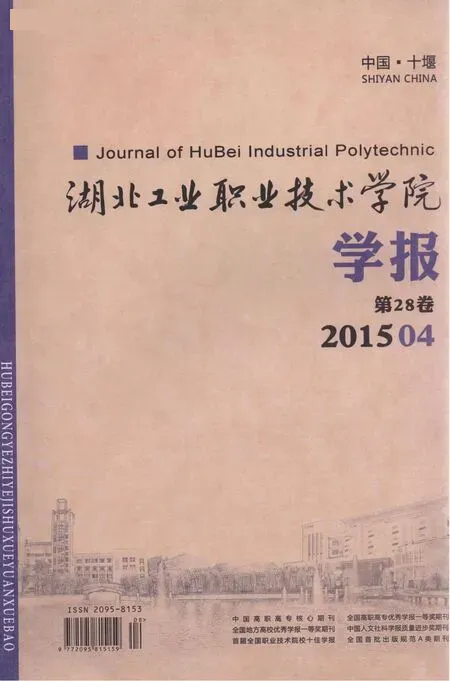重审印刷文明时代创造的“新尺度”
郭英丽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越来越深入地卷入媒介技术形式带来的变革中,对于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如何通过引入“新的尺度”而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的塑造和控制作用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麦克卢汉提醒我们要对媒介在塑造与控制人们的思想过程中以及推进社会变革和文明史的演进过程中所起的隐蔽性的作用保持足够警惕,尤其身处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交接与汇合的时代,也是突破印刷文明的诸多局限以及重新审视人与媒介关系的时候。
在《谷登堡星汉璀璨》中麦克卢汉就向我们宣告:印刷术这种新鲜的媒介形态,是作为将文字书写机械化的技术,不同于口语、书写、电报等技术,“它的主题是关于连续、统一,而且与时空组织相联系的视觉形态的延伸”[1]57,它对人们的感受形式、思维模式以及表达方式的影响以及对于公众、民族主义和新的社会国家环境的构建方式与其他媒介形式都判然有别。之后《理解媒介》继续探讨印刷媒介所塑造的“拼音文字人”、“谷登堡人”或者“机械的人”的说法,麦克卢汉分析了印刷品、印刷词、打字机、书籍等机械时代的媒介,造成了人的肢解和分裂,各种感官的分离,社会的集中制,人类文明非部落化。
根据麦克卢汉“一切媒介作为人的延伸,都能提供转换事物的新视野和新知觉”[2]20的观点,印刷媒介在人的感知觉方面和社会内容方面所创造的“新的尺度”有以下几点:
一、作为转换器的印刷媒介——知识的“内在导向”
作为媒介的“普遍意涵”的意涵(i)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观念:“一种感官(或一种思想)要去体验(或表现)必须有一个中间物。”[3]289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专门讨论了媒介的“中介”作用或曰“转换”作用,也就是“作为转换器的媒介”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知识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知识”[1]109。这是媒介作为一种传播工具或技术最基本的应有之义——媒介作为贮存和转换信息的技术性工具。印刷媒介作为由印刷机与纸张以及文字的联姻而产生的新型的信息贮存方式,最显著的特征即是其整齐划一性和重复使用性,它的这种特征为大规模地复制视觉知识提供了可能,也为人们实现“将非视觉化的思想过程通过图解的方式实现视觉化”提供了可能。
印刷文化相对于抄本文化的贮存信息方式使得其具有了与古典时代和中世界时代所不具有的赋予人们以“内部导向”的功能。麦克卢汉认为“‘内部导向’依赖于‘固定的视角’。一个稳定而一致的社会性格依赖于坚定的人生观,一个几乎催眠般的视角。抄本文化不仅发展速度缓慢,而且发展速度不均匀,从而既无法提供固定的视角,也不习惯于单一思想或信息层面的平稳过渡。”[1]94而印刷文化之所以能够不可避免地赋予人们“内部导向”则是由于它一方面通过“书写的机械化”逐步将抄本文化对视觉元素的强调提高到一个极端的强度,并不断强调视觉官能中固定的透视点的形成;另一方面,印刷过程中通过字模的排列使信息封装图像般的统一空间内,如沃尔特·翁所言,在一幅字模里,排字的过程中“连续语意的构成是按照空间的模式,通过对预构件的组合来完成的[4]3。这使得我们易于以一种恒定的速度来扫描眼前的一行行印刷文字,往往使读者形成某种“立场”或“固定的观点”,印刷术信息贮存的这两方面特征都利于人们在视觉官能的强调中形成冷静的视听解析习惯,从而有力于形成固定的视角,并在统一、可重复地对这种视角的固化并将其规范化的过程中,赋予人们“内在导向”。
可见,麦克卢汉对印刷媒介作为转换器的理解不仅在于他指出印刷术可以起到传统意义上的作为传播过程中作为“转换器”的工具或技术手段的作用,而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他揭示了印刷术不同于口语和抄本文化的方面在于它开始通过机械化的手段实现“书写的机械化”,“印刷术出现以后,直观的视觉辅助手段倍增,符号与象征用编码固定;各种图示和非语音的交流形式迅速被开发出来”[5]151印刷术的这种特点使书籍等作为视觉观能的延伸在视角的可重复性与被固化的过程中,赋予人们“内在导向”,在人们被催眠和痴迷的状态下实现“媒介的内化”。而之后出现的电子媒介更是深入到对人们神经系统的延伸实现了“媒介的内化”。
二、作为一种延伸的印刷媒介——重新定位人媒关系
印刷媒介作为转换器体现了媒介在其信息的贮存和转化过程中,可以赋予人们某种“内在导向”,而媒介之所以能够内化于人,在麦克卢汉看来,这主要是因为媒介本身就是对我们身体和官能的延伸。这种延伸或者“内化”的实现往往是通过它被作为一种物理手段实现人或物在时空维度的全面的延伸,以实现对人们生存领域的拓展。
印刷术首先是以实现视觉的统一性实现了知识在横向与纵向扩张的,印刷时所用的活字字模都“由持续不断的一系列以均质关系组成的静态画面或‘固定视角’所组成”[5]51。印刷术不仅以这种线性的形式展示我们的思想,更试图将知识分门别类地封装在便于携带的印刷书籍中,使知识传播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同时,印刷术可被视为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机械化形态,也是之后一切机械化的原型。其可不断重复的机械化原则使得印刷品实现了批量的产生。所以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基于其视觉上的统一性和生产上可重复的技术偏向以及使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扩张的传播功能,使人类开始真正地凭借技术以实现自身的延伸,这种延伸甚至造成了人类文化由中心向边缘的“外爆”。
印刷术的这种技术特征与传播特点,不仅重塑了人们的感知与思维方式,实现了思想超越时空局限的传播,还重塑了人们的社会组织形态甚至整个文明进程。“当技术延伸了我们的感官之一,文化的新型转化就像新技术的内化一样迅速”[1]220。在麦克卢汉看来,在口传文化阶段,人们生活在“听觉的”世界,人们的交流依赖于口头媒介,此时言语即是人们思想的延伸,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是不分离的,在麦克卢汉看来,这是种部落的、交融的、实践的和单一的文化。而当人们具备了读写能力,尤其这种“书写的机械化”的能力后,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被这个新媒介所改变。写作更强调视觉方面,而非口头和听觉方面,人们开始在线性的文字排列中形成了静态的分析、被动的接受、与生活世界的疏离,使得人们从部落社会的人彻底走向个体的人,又在其视觉统一性对个体的思想逐渐趋于同质化,并慢慢将个体的意识与民族国家的集体意识建立联系,这是印刷媒介对人媒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的生动体现。麦克卢汉在将人类文明进程划分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三个阶段正是以媒介传播形式的口语化传播一印刷文字一电力技术的演变为基础的。
三、作为讯息的印刷媒介——引进感知新尺度
麦克卢汉在开篇即言“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34他随后直接向我们宣告“‘媒介即是讯息’,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1]35,也就是说麦克卢汉所称的一切媒介所传达出来的“讯息”,其实是媒介在人的感知范围和社会领域范围延伸的一种感知新尺度,也是媒介在延伸我们人体的过程中所引起的人们的感知方式、交往方式、行动速度的变化以及人际组合形态的模式的变化等方面的变化,当然媒介所引起的这种变化会因为不同的媒介的技术偏向和传播功能会有所不同,那么印刷媒介所传达的“讯息”则既是不同于口头媒介也是不同于电子媒介的。
“媒介即是讯息”,麦克卢汉首先是在整体的媒介形式的意义上而解释的,不只是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内容”而言的。“由于媒介对于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为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为了讯息”、“使社会受到更加深刻影响时,是人们借以交流的媒介的性质,而不是交流的内容。”[6]237这些论点警示着我们看待印刷媒介或者一切事物时应该不只考虑印刷媒介所做的事情,或者所印刷的“内容”,而且还考虑这种印刷媒介形式本身及印刷媒介赖以运转的“文化母体”。印刷内容对于人和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能传达观念,触及人的思想与情感,而印刷媒介本身则凭其可重复性、可批量生产性等机械化原则既可从更根本意义上塑造人们潜意识层面的思维习惯和感知方式,又可通过在从事与之相应的传播和社会活动中开创人体延伸的新的可能性和为人们带来新的社会变革。这种作用原理正如伊尼斯所言“正是媒介在其形式上的特性——它在多种多样的物质条件下一再重现——而不是任何特定的传播内容构成了媒介的历史行为的功效。”[7]6媒介形式的转型对社会形态与社会心理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有它塑造了人们新的感知方式,包括对人们视觉官能的延伸、强化和放大,感知平衡比率的重塑,线性思维的养成等;它一方面在时空维度上拓展了人们交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其新的信息贮存方式使得不在场交流得以可能,促进了个人主义倾向,限制了人们的交往;它的视觉统一性与可重复性的机械原则,使得它在塑造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分割肢解的、集中制的、肤浅的”[1]27。
如果我们从“媒介即讯息”的第二层含义来理解的话,即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媒介往往会以旧的媒介为其内容,在印刷文化诞生后的机械时代里,“媒介即讯息”的意思是,印刷术作为对口语和拼音字母表进行了再加工,改变了人类的口头传统文化,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工环境,这一新环境的内容是对口语与拼音字母表的彻底加工,这种加工包括对口语文化和拼字文字文化信息的编码方式,和对信息的清晰度和结构方式的强化甚至对信息的解码过程,使得同样是信息,用口语表达和用印刷品承载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单单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媒介技术形式的作用。印刷文化则以文字及文字包含的语言为其内容,对文字与语言进行机械编码,用编码来固定语言符号与其象征意义,这便造成了我们执著于去询问一部小说与一幅画表现的是什么内容,而忽视了去探究小说与画作是如何产生并呈现为如此这样的;我们往往只察觉到了文字,即原有的环境,而忽视了印刷品这一外部环境的存在。
总而言之,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这一命题的提出,如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中所做的表述,其根本目的是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媒介内容引向媒介形式本身。“他关注的是内容夺走我们的注意力,损害我们对媒介的理解,甚至损害我们对媒介的感知,损害我们对媒介周围一切的感知。”[8]134麦克卢汉正是期望通过预见和控制媒介形式的能力,从而避免在对媒介潜在的自恋昏迷状态中使人成为媒介技术的奴役或者成为其伺服系统。
四、作为“热媒介”出现的印刷术——加热社会环境
麦克卢汉称“所谓热媒介是指一种可以把一个感官以‘高限定’的方式来延伸的媒介。高限定是指一种数据饱和的状态。”[1]89例如,印刷品较之口语与手抄本都是高限定的,言语在麦克卢汉看来是一种低清晰度的冷媒介,因为它提供的是少量且低水平的信息,留下了大量的空白让接受者去填补完成。而拼音文字相对于口语是一种“热烈而爆发性的媒介”,开始将“语音转化为统一分布和传递视觉代码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眼睛开始代替听觉去填充并补足它整体的形象。而拼音字母抽象的视觉程度被推向高峰时,就成为印刷术,印刷术作为人类感官的第一次即时性的延伸,就视觉而言它能够接受更多的信息,其信息密集度更高,因此“从视觉上说,印刷很大程度上是比手抄本存在‘更高的概念’。也就是说,印刷是在由“冷的”抄本媒介统治了上千年的世纪中所出现的“热”媒介。”[1]89
印刷术问世之后,其整齐划一的、重复生产的机械生产原则要求其一行行的印刷文字是标准化的、精准简练的、以线性逻辑加以组合和分析的,这极大程度上使得信息结构更加符合逻辑,提高了信息的清晰程度,使得印刷媒介具有了“高清晰度”或者“高限度”;而印刷媒介使文字媒介逐渐升温,将文字这种视觉媒介的抽象程度强化到很高的高度,并以此作为传达人类群体经验和社会现实的语码,这种对视觉的侧重而忽视感官其他因素以及越来越侧重对视觉代码的解读而造成与语义、语境的分裂,使得我们渐渐远离人生世界,并造成了我们与认识对象的疏离,表现了印刷媒介作为“热媒介有排斥性”即拒绝人们过多地卷入或者参与其中;此外,印刷品的传播不再借助一些像石头等笨重不便的、大而无当的冷媒介,也就从而使得是伊尼斯所称的“倚重时间的媒介”以取得纵向时间的粘连,而是借助于纸这种“倚重空间”的热媒介,以求可以将横向的空间联成一片,使得知识或信息由中心向边缘的扩展成为可能,使得印刷媒介作为“热媒介”把社会环境也加热到很高的程度。
印刷媒介的逐渐升温,印书品越来越丰富,其影响自然也越来越深刻而广泛,它是知识“外向爆炸”和许多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对于新的文化模式的产生也产生了影响,但按照麦克卢汉“热媒介只延伸人的一种感觉,并使之有具有‘高清晰度’”的原则,印刷媒介在信息的流通过程中对视觉加热到了支配地位,就会产生催眠的效果,印刷媒介作为机械化的原型被推广到所有的社会组织形态,人们越来越进入了一种分割、专门化的、机械化的文明形态,但是麦克卢汉认为这种媒介加热到了过热的程度就会逆转,信息推向饱和时就会发生沉淀,从而推动着人类的文化模式由这种机械状态再重新进入有机状态,也就是电子媒介的产生带来的人类文化的“重新部落化”状态。
总而言之,印刷媒介作为一种媒介,其意义不限于一种可以实现信息的转换、知识的扩张等技术工具的意义上,也不限于其本身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通道,它还可以内化于我们的思想与情感中,可以组成我们生活的环境,可以参与文明与社会的运转。这种新媒介的生长不仅可以造就个体的感知模式,甚至能影响到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的模式、社会的运转与组织形态,甚至整个新的文明的进程。
五、结论
在麦克卢汉那里,印刷媒介既是近代西方文明的塑造者,它携带着整齐划一性和可重复性等诸多特征似乎催生了近代西方的一切文明,但是印刷媒介又带来了文明在某种程度上的陷落,是“前文字时代”和“电子时代”这两个“有机文明”的断裂。印刷媒介作为一种“断裂界限”将前文字时代面对面交流产生的“活态的文化”贮存压缩到到印刷文字和纸张中,使“直观的视觉辅助手段倍增,符号与象征用编码固定;各种图示和非语音的交流形式迅速被开发出来。”[5]41同时,印刷媒介作为电子媒介出现的前奏,其“静态的、老一套的、无所不包的”等机械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已不再适用于全球化、有机化的电子时代。如果说印刷媒介对人们视觉的高度强调以致造成了感官比率之间的重度分离的话,那么电子媒介则强调将这些感觉的碎片重新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说印刷媒介使人们的思维在一种有界的、线性的、贯序的、结构化的和理性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话,那么电子时代则使我们更加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这种渴望是电子技术的自然而然的附属物。如果说印刷媒介带来了个人主义、民族主义或者人类生活领域的专门化和切割化的话,那么电子媒介又呼唤人重新回到了部落化、集中化的状态以及人们之间相互依存的状态;如果说印刷媒介和其他机械形式是通过机械化、空间方位上由中心到边缘单向扩展方式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能量的外向爆炸(explosion)以及使人们实现了空间上延伸的话,那么当前的电力时代则主要加速度与压缩等方式实现了世界通过“内爆”(implosion)而产生能量,通过“内爆”带来的影响,我们实现了“空间和各种功能的融合”以及感觉感官和神经系统在人类一切社会领域范围内的延伸。
电子媒介先进的文化传播特质使印刷媒介逐渐步入“终结”阶段,印刷媒介将在电子媒介时代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并开始实现“逆转”,即跳出印刷文明创造的诸多“尺度”所带给人的“麻木自恋”的限制,以新的媒介形态下逐渐形成的“新的尺度”来重新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即“西方人的电力技术开始把重视觉的西方人还原为部落模式和口头模式的人。重新再现了视觉的、专门分工的、割裂的文化形式下被遮蔽了口传文化中的某些特征。”[1]235
[1]马歇尔·麦克卢汉.谷登堡星汉璀璨:印刷文明的诞生[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3).
[2]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3]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
[4]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5]伊丽莎白·爱森斯坦.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
[6]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麦克卢汉精粹[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保罗·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