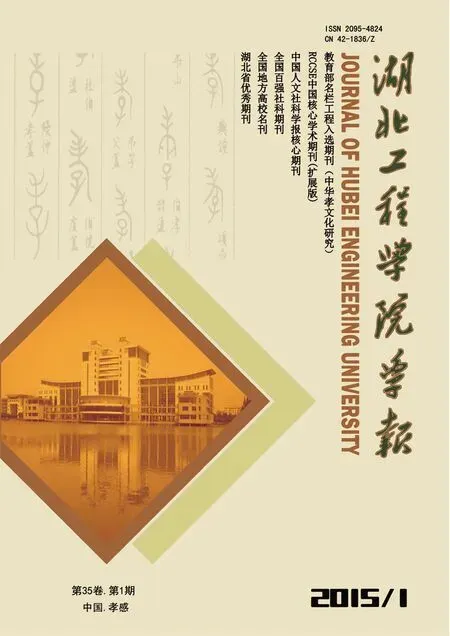个体言说与启蒙叙事
——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1942》
沈思涵,沈嘉达
(1.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个体言说与启蒙叙事
——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1942》
沈思涵1,沈嘉达2
(1.华中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刘震云是一位有思想有行动的作家。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被改编成电影《1942》,不仅仅是载体和主导者的转换,更多的是内蕴的流变和思想的衰减。首先,电影转换了叙事视点,由“我”转换为第三人称。小说充满了主观意味和尖锐痛感,是一种“民间意识”和“个体历史观”,更锐利,更沉重,更荒诞。其次是人物和情节的“重新”设置。电影《1942》让我们回到传统电影的“苦大仇深”时代,回到正统路线上去。历史本身充满复杂性、多维性、不确定性,无论是要丰富历史形态,还是要警惕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对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探索都是必须的。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电影《1942》;个体历史观;启蒙叙事
一
刘震云可以算得上是一位高产作家。1987年后连续发表《塔铺》、《新兵连》、《头人》、《官人》、《官场》、《单位》、《一地鸡毛》等描写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和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作品,就显示出了他独到的思想和敏锐的触角。其后,作者转向“故乡”系列创作——“‘故土’是刘震云进行小说叙事的立足点和基本视点,由‘乡土’、‘乡村’、‘农村’所组成的故土叙事是现代文学乡土中国叙事、乡村中国叙事的延续与发展,其小说文本叙事中的‘故土’文化既是中国经验的叙述,也是现代性焦虑的表达,又是后现代谐谑化的文本呈现。”[1]无论是《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这样的“另类叙事”——其“奇异又深刻地体现出作家对历史、对民众及权力的嘲讽和批判,以及嘲弄与嬉笑之后的蔑视、刺痛与无奈”[2],还是 “尊重文学,也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呈现了另外一种极致,一种用‘闲话’写长篇的极致”,“在故事层面,我们看到的是生命轮回般的戏码一次次重复。而在叙事层面,则可看到作家不断求新求变的勇气与努力”[3],可以说,刘震云始终是一位有思想有意志有行动的作家。
创作于1992年的中篇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继续赋予其独特的思想内蕴并附丽上个人尖锐的话语。当2012年电影版《1942》问世时,作为导演的冯小刚其实是心知肚明的:“我们在北影的一间小平房里开了论证会。与会者一致认为它是部好小说,同时也一致认为它不适合改编电影。因为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4]3
那么,从“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冯式电影成品《1942》,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也就是说,电影《1942》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面目”呢?
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饶曙光研究员在北京举行的电影《1942》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时就肯定地讲:“电影《一九四二》的创作者采取‘尽量客观的,不融入个人的态度来再现那段历史’,与此同时却不失温情和关怀。”“正是这种单纯的客观呈现,使得观众获得了对历史的一种透视和认知”,从而成就了这样 “一部史诗作品”。[5]48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也认为:“冯小刚导演对历史怀有敬畏之心,因此影片的主要目的是呈现历史,而不是作一种简单化的价值判断或是对灾难的历史性审判。”“既有大历史,也有小历史,使得本片成为一部具有独特意义的史诗电影。”[5]48显而易见,他们都强调了电影《1942》的“史诗”品格。
就笔者看来,从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到电影《1942》,不仅仅是少了“温故”二字,也不在于标题是汉字书写还是阿拉伯数字表述,从小说到电影,从小说作者刘震云到电影导演冯小刚,不仅仅是载体和主导者的转换,更多的是内蕴的流变和思想的衰减,正如有论者所尖锐指出的,“影片中,在表面上,民族的奴性,阿Q精神,‘幽默’对待生死的卑贱,暴政下的自相残杀,这些‘深刻’的东西在故事的进展中均有呈现,但直到最后,我们感受最深的却不是这段历史所反映的真谛——‘专制统治猛于天灾’——我们没有听到影片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感受到一种近似‘以和为贵,谁都不容易’的含混呻吟。”因为“我们看完电影的感受是:灾民不容易!委员长不容易!日本人不容易”[6]。
本来对待一部作品见仁见智是非常正常的事,“不正常”的是,何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1942》到底怎么了?
仔细思来,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了电影《1942》的“变异”。
首先,电影《1942》符合冯小刚导演的一贯理念与风格,而偏离了刘震云的艺术个性。正如尹鸿所言:“从《甲方乙方》系列起,冯小刚就一直随着电影政策、市场环境、观众审美情趣、社会风尚、预算成本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市场运作方式,主动调整所拍摄电影的类型、叙事和视听风格,以艺术的变化来适应市场、扩大市场,形成了贺岁系列、以《天下无贼》为代表的商业类型片和以《夜宴》为代表的国际化大制作电影三个不同阶段的商业电影美学。”[7]也就是说,冯小刚更多的是关注市场。
其次,是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使然。冯小刚是一个聪明的人,甚至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这种“聪明”不一定在于某种“建构”而在于某种东西的“消减”。换句话说,在于制造某种“平衡”。我们似乎能够理解冯小刚的“艰辛”——从刘震云的小说到冯小刚的电影,从1992到2012,历时20年。即便从冯小刚1995年动了拍摄成电影的念头到2012年电影问世,也历时17年,中间数易其稿,多次送审,屡屡不能通过,“理由是:调子太灰,灾民丑陋,反映人性恶,消极”[4]4。如何寻找到某种平衡并获得“突破”?在几经努力之后,2011年国家电影局终于批准电影《1942》正式立项,下达拍摄许可证。“前提是:第一,拍摄时要把握住1942年摆在我们国家首位的应该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第二,表现民族灾难,也要刻画人性的温暖,释放出善意;第三,影片的结局应该给人以希望;第四,不要夸大美国记者在救灾上的作用,准确把握好宗教问题在影片中的尺度;第五,减少血性场面的描写和拍摄。”[4]6事实是,2012年出品的电影《1942》顺利通过国家电影局的审查,全国放映。也就是说,国家意识形态管理部门所下达的要求,在电影中全部实现。由此,各方皆大欢喜。
再次,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的电影,其属性也不同于小说。电影一般在90分钟(《1942》长达145分钟),长于叙事,这就决定了电影必须要有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冲突。而中国电影观众也都习惯于欣赏具有较强冲突的叙事类电影。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却“没有故事,没有人物,没有情节”,必须要进行改编。这样,结合国家电影局规定的明确的“主题”要求,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电影《1942》庶几完全有异于充斥个人风格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了。
二
具体到电影,冯小刚是如何实现这种“战略意图转移”的?
就笔者看来,电影的最大变化就在于叙事视点的转换。确定拍摄电影之后,冯小刚便开始选点准备,“重走长征路”。“最大的收获是在逃荒路上,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颠覆性的转换,这些转换有力地推动着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4]4准确地说,就是由小说中“我”的主观性很强的视点转换到第三人称身上,也就是全知全能视角上。本来,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我”既深入到1942年大灾荒之中,引导读者“还原”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又不时跳出事件本身,从大时代、大历史的角度对此进行反讽式评说,充满了主观意味和尖锐痛感,是一种“民间意识”和“个体历史观”,更锐利,更沉重,更荒诞。然而,当个体叙事变成了“宏大叙事”,“文献检索”变成了“史诗”呈现时,就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合二为一,共同承担起了正统述说而遮蔽了个性诉求。
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要澄清,是否“个体诉求”就一定比意识形态叙事更具有先进性?可不可以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笔者的看法是,刘震云这样的具有尖锐思想的“个体作家”在小说中所表达的民间意识,是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的。实际上,从最初的“官人”系列到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正是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而成为时代的“独行侠”。很大意义上说,卓然独立正是刘震云小说生命力之所在。淹没或遮蔽其思想,便是取消了刘震云的小说存在价值。另一个问题,电影“兼容”了小说中的“个性”了吗?就我看来,正是这种“含混”造成了电影风格和主题的紊乱,也导致了电影的受人诟病和读者的无所适从。也就是说,“平衡”的结果造就的是效果的平淡,并没有为电影增光添彩。“温故”没有了,《一九四二》变成了《1942》。
其次,与视点转移相关联的是人物和情节的设置。小说《温故一九四二》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作为主线的叙事线索,有的,是作者对人物命运的沉思和中华民族历史的反省,是对统治者的反讽和对时代的警惕。然而,电影《1942》让我们重新回到传统电影的“苦大仇深”时代,回到正统路线上去。那就是范东家的由富人到灾民的沦落,由花枝、栓柱、瞎鹿等人的命运引发观者对蒋介石统治的同仇敌忾,故事催人泪下,情节层层递进,而电影离小说是渐行渐远了。
比较小说与电影,我们很容易发现,由小说中的只言片语“生长”出了四条线索:一是灾民范东家由富人“逃荒”变成“灾民”逃难,这在小说中是由“撇下花爪舅舅,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一句引起的——其实,小说中所述寥寥;由“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一句,引发出瞎鹿和花枝的故事;至于灾民在范东家家里吃大户,源自小说中范克俭舅舅的一句回忆:“饿死许多人,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拿着几把大闸刀、红缨枪,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杀猪宰羊,说要起兵,一时来俺家吃白饭的有上千人”云云,不一而足。二是蒋介石“救灾”事,在小说中,远远比不上作者用文献方式对受灾状况的“考证”和对蒋委员长与宋美龄住在重庆黄山官邸里晚上是不是分居的执意猜测,因为蒋委员长真正在“日理万机”,他所思索的是中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就是:“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第三条线索是关于教士安西满传教,第四条是日本人军粮救灾笼络民心。当然,电影中主线是范东家的逃荒历程以及瞎鹿、栓柱等人的悲惨遭遇。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突出”灾民的苦难生活,由此激起对国民政府的彻骨仇恨。如此而已。
笔者感兴趣的是,对照小说和电影,从刘震云到冯小刚,又有了哪些“衰减”?而这恰恰是颇有意味而又无人论说的。毕竟,小说本身是最刘震云的。
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处理”:一是小说第四节写到“我”去采访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这位七十岁的老婆婆,五十年前在逃荒路上被爹娘卖掉“过了五年皮肉生涯”,本来这段屈辱的历史一直被尘封,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许多畅销书作者计划要写“我的妓女生涯”这样的自传体畅销书,“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可当儿女们意识到个中的屈辱后,对包括“我”在内的采访者怒目相向,甚至要拿大棒子驱赶“我”。对此,“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便有了“我”与派出所所长的一段对话。小说名曰《温故一九四二》,题意重在“温故”二字,所谓温故而知新也。对话的“温故”之意再明显不过,就是要爱民、惜民,不如此,所谓的国家大事、世界大事都是扯淡。此真耐人寻味!
与此相通的,是小说中日本人对河南灾民实施救济的“淡化”处理。本来,小说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叙写和议论超过了1500字。“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本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结果,“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这是我温故一九四二,所得到的最后结论。”思考触目惊心,发人深省!而在电影中,将其设计为冈村宁次的巨大阴谋,同时一再渲染日本飞机对难民的轰炸,从而彻底淡化了作者的历史思考,回归到了正统轨道上来。
对于教会在河南的救灾表述同样意味深长。政府要甩包袱给日本人,蒋鼎文将军死死咬住三千万担军粮不放而全然不顾河南大灾荒,剩下的就只有教会有限的救灾力量了。小说写道:“教会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孤儿太多,教会根本收留不过来。尽管如此,“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这该是多么大的嘲讽啊!而在电影中,更多的是以安西满传教的失败,引发人们对宗教的怀疑,这种暗渡陈仓式的“位移”完全消解了小说思想的力量,由尖锐而变成了平庸。同样道理,小说中特别写道:“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到。”——因为“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大忙”[4]46。这就是以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为首的新闻记者曝光了灾荒事实并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象征性地救灾。——这可是对国民政府的莫大讽刺啊!这些,在电影中都“牺牲”掉了。
还必须指出的是,从已经“变异”了的电影剧本到电影成品,一些尖锐触角再次“衰减”。譬如电影剧本写到,逃荒路上饿极了的瞎鹿,偷了白修德的驴子准备吃掉,后来驴子逃掉,被同样作为灾民的另一拨人杀掉。瞎鹿要驴,与另一拨灾民“争执起来”,“这帮灾民也急了,疤痢眼灾民一棒子下去,不小心打在瞎鹿头上,瞎鹿一头栽倒了肉锅里”。就是说,是另一拨灾民为求生杀死了瞎鹿。这正深刻地应和了“吃”的主旨。然而,在电影中,这个血淋淋的细节被改编了,成了溃兵杀了逃驴并杀死了瞎鹿。“思想”再次变成了“思量”,因为改变了的细节可以将愤怒转移到国民政府及其溃兵身上,而难民则变成了纯粹的受害者。
三
李建军在谈到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入围中篇小说时指出:“在丰富多样的现实主义叙事中,‘底层叙事’无疑是当下影响最大的一种叙事模式。有人可能会对这种‘苦难叙事’很不耐烦,也很不以为然,但是我却觉得在当代文学的整体构成中,底层写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的一个观点是,真正伟大的文学总是关注和同情弱者,总是把目光投向那些不幸的人……在我看来,同情底层人和不幸者,则是整个人类文学的精神纲领。因为,文学的精神就是一种以爱为核心的伦理精神,就是一种给人以光明和温暖的精神,就是一种把对不幸者的怜悯和拯救当作自己的使命的精神。所以,无论我们的底层叙事存在多少不足和问题,它们都是值得赞许的。”[8]陈思和将“底层”换成了“民间”,认为知识分子采用民间立场写作,强调它“属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和传统”,“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在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他接着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启蒙话语的消解和私人生活的叙事视角等创作现象”,“多种声音的交响共同构成一个时代多元丰富的文化精神整体”。[9]
按照巴尔扎克的说法,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如何表现这种“秘史”,当然见仁见智。有大开大合、纵横捭阖、叙写风云际会的史诗性巨著,也会有充满个人情怀、一只眼睛看世界的个体世界,所谓新历史主义等即是如此。刘震云从来就不是一位“安分守己”的作家,笔者当初就曾对其《故乡天下黄花》做过评说。“简略地说,传统的历史小说有两个质点:一是写历史,写历史上发生过的故事;其二,作家是‘历史地写’,即作家梦想达到‘历史的真实’(信史)这个终极目的。”[10]具体到《温故一九四二》中,对“历史”的叙写与记忆,显然,刘震云与冯小刚是不一样的,就是说,刘震云的历史是“个体”历史,冯小刚的历史是非民间历史。譬如说,电影《1942》我们更多地记忆起的是难民范东家、栓柱、瞎鹿、花枝等的苦难历程,是作为执政当局首脑蒋介石的政治图谋(救不救灾依政治需要而定),其叙事效果便是顺理成章地引向了对万恶旧社会的仇恨和对劳动人民的深刻同情(范东家由土财主最终也变成了难民,庶几可以划入劳动人民行列)。而小说中,触目惊心的是对于天灾人祸的麻木:“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4]6是花爪舅舅的“荒诞话语”:当年花爪舅舅被抓壮丁,一打仗,“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悔”[4]27。不是后悔没有好好杀敌为民族复仇多杀几个日本鬼子,而是后悔“当初不开溜,(要是)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犟驴,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是郭有运儿子今日的“惊人论调”:“命都顾不住了,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逃荒是)不当亡国奴,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你是当亡国奴好呢,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不也没人疼没人管吗?”[4]33如此等等,难以尽述。
有趣的是,并不是人们都能够接受这种个人记忆与个体表述。即便是“完全拍成了一部悲剧或正剧,主创们反复强调这是一部民族史诗,不能被遗忘的民族记忆和灾难,而媒体也把这部电影称为‘中国电影的良心之作’”的电影《1942》[11]15,也有论者愤然发问:如此拍摄,能想像“仅仅六七年以后,就诞生了新中国,这么有朝气的蓬勃向上、气象一新的新国家、新社会,是从哪儿产生的? 从整个电影的叙述逻辑看,你能想像,仅仅六七年以后就出现了新中国吗?和这个情况相联系的是影片中的刻意的回避”。影片“刻意地回避了当时就在河南周边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比如晋冀鲁豫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和豫皖苏根据地,这些地方当时也受灾了,但情况和国统区、沦陷区完全不一样。丁玲在《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这篇文章里提到,当时的太岳区接收了20万河南难民,太行区接收了5万,另外别的资料还提到,当时陕北也接收了1万多灾民。也就是说当时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是参与到救灾当中的,而在影片中没有丝毫体现,只字不提。这不是疏忽或遗漏,是刻意的回避”。“到底是历史错了,还是他们的叙事框架有问题?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11]14
历史是什么?这是一个具有悖论性质的话题。笔者并不主张相对主义历史观、虚无主义历史观,或将历史看作是小媳妇任人揉捏,只是想说历史是多棱镜,是由意识形态书写和民间讲述共同组成的多元结合体。当我们将历史简化处理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有所遮蔽。因为它可能违背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诚然,历史又是以一种已然进化了的状态向前推进,从文明进化的角度讲,又是可以触摸到的,它具有某种基本形态。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多维性、不确定性,又难以让人们对其下简单结论。无论是要丰富历史形态,还是要警惕历史悲剧重演,我们对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探索都是必须的。更何况刘震云小说已经清清楚楚地表明——“温故”,而我们这个民族恰恰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容忍那种弱弱的个体声音呢?
[1]周全星.论刘震云的故土叙事及其脉络[J].小说评论,2013(3):132.
[2]周叶.《故乡相处流传》的另类叙事[J].安徽文学,2011(1):62.
[3]贺彩虹.试论刘震云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闲话体”语言[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6):108.
[4]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一部小说和一部电影的缘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5]李雨谏,李国馨.《一九四二》:历史呈现、影像蕴含与现实参照——《一九四二》学术研讨会综述[J].电影艺术,2013(1).
[6]张晓琦.《一九四二》不是呐喊,只是一声叹息——妥协的《一九四二》[J].电影世界,2012(12):21.
[7]尹鸿,唐建英.冯小刚电影与电影商业美学[J].当代电影,2006(6):51.
[8]李建军.何谓好小说——关于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及其他[J].小说评论,2008(1):39.
[9]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J].当代作家评论,2006(5) :22.
[10]沈嘉达.历史寓言与个人话语——评《故乡天下黄花》兼及其它[J].湖北大学学报,1996(3):103.
[11]李玥阳.《一九四二》:历史及其叙述方式[J].文艺理论与批评,2013(2).
(责任编辑:胡先砚)
2014-09-01
湖北省“十二五”期间省属高校重点学科基金项目(2013XKJS)
沈思涵(1991- ),女,湖北黄冈人,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沈嘉达(1963- ),男,湖北黄冈人,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I207.42
A
2095-4824(2015)01-007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