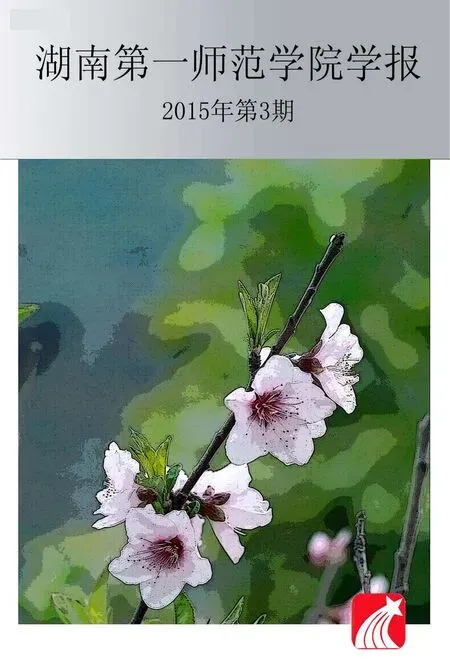论池田大作的天台观
陈红旗
(嘉应学院 文学院,广东 梅州 514015)
天台(538-597)是中国杰出的一位思想巨人,被誉为中国的“释尊”。他开创了中国佛教最早宗派之一的天台宗,这意味着佛教中国化过程的初步完成,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的诞生[1]。池田大作(以下简称“池田”)是一位著名的日本佛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对天台的评价极高,认为:“从佛教史的流脉来说,释尊阐示佛教的根本原理,而天台使佛教作为一个哲学的理论体系得以完成。”[2]与此同时,池田在弘扬佛法尤其是“一念三千论”等天台哲学的过程中,坚信天台思想可以给面临崩溃危机的西欧近代文明体系带来一种新的觉醒。为此,他提出了关涉“人性革命”的系列思想,强调“人性革命”能够使人们增加生命活力、勇气和智慧,能够使世界变得更加和平、美好,进而将这些思想广泛运用于推动创价教育发展等社会实践活动之中。显然,池田的上述做法是继承天台“入世精神”[3]的一种表现。可以说,池田把天台佛法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做法,既推动了佛法的现代化进程,也彰显了其独特的天台观。
一、心怀大志、坚决求道的哲学少年
在池田看来,天台是一个知性精英、洞察人性真理者,天生就具有一种深刻思索、追求真理、宏大有力的精神,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冷漠彻悟的人,因为从《摩诃止观》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深刻洞察力来看,他确实是一个极为细腻和敏锐的人,但当他用锐敏的眼光去透视人类的软弱与坚强、丑恶与华丽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人类的深刻同情和热爱[4]60-61。在这里,池田的说法是有的放矢的,因为天台年少时的所作所为已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之心和真性情。
五胡十六国时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也展开了对江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开发。天台的祖先是在公元4世纪汉民族的大迁移过程中,由北方的颍川移居至长江中游要地荆州的。天台出生于南朝梁代的荆州华容县,卒于隋代,历经梁、陈、隋三个王朝的兴衰过程。这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或曰汉民族实力不断衰弱的一段时期。这意味着天台在他六十年的生命旅程中,将不得不直面这种分裂的时代和动荡的社会。因此,我们在审视天台其人其思时,是不能无视这些历史因素的。值得注意的是,天台生活的时代固然充斥着王朝更迭和盛衰浮沉的现象,但也是中国政治、社会及文化艺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时期,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奠基期。公元538年,即天台出生的这一年,朝鲜百济王给日本大和朝廷赠送了佛像和经论,这标志着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正式传到了日本,进而“逐渐形成了日本的精神和文化的骨架”[5]。及至天台去世十年后,日本与中国进行了正式交流,并开辟了大力汲取中国文化和建设新国家的历史新时代,而在传至日本的中国佛教文化中,天台宗无疑是“汉传佛教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6]。
池田相信,在人的一生中,幼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及其所培育的素养会对个体未来的人生方向、人格乃至人性本质的形成起到本质性影响[4]47。这是有道理的,就天台而言,其幼年时生活的荆州地区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连绵的山脉、宽广的洞庭湖和浩淼的长江都不知不觉地浸润着他的灵魂,这确实有助于他生成宏大的气魄、宽广的胸怀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再者,天台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宗师,与其丰富的家学是分不开的。天台的父亲陈起祖通晓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还擅长武略,是南朝时代一个难得的文武全才,担任过梁代的“使持节”、“散骑常侍”,曾被封为益阳县开国侯,其文化修养和政治地位都非常高。天台的母亲则是一个稳重、温厚、讲礼节、笃信佛教的人。可以想见,天台小时候肯定在文武方面都受过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因为只有在幼时养成健壮的体魄和敏锐的思维,才能使他后来经受住出家时严格修行的考验。天台七岁时曾被母亲带进寺庙,结果他被《法华经》所深深吸引。此外,天台幼时所受的教育也有益于他认同佛教。是时,兼备“玄儒文史”的教养是南朝贵族的理想,富家子弟要成为有教养者,除了要学习儒学外,还要学习玄学、文学、史学乃至“杂学”(琴棋书画、六艺等)。而天台头脑明晰、记忆力超群,加之勤奋好学,所以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和玄学修为,可以说,正是以此为根基,他才能够体得法华妙理、随意驱使经文和著述天台三大部——《法华文句》《法华玄义》《摩诃止观》,进而建构了“中国佛教得以成立的完整佛学体系”[7]。
天台是在十八岁时出家的。要知道,十八岁前后是个体身体和精神的成长期,也是个体产生明晰的自我意识和追求自我实现的重要时期。按理说,就当时的家庭环境和社会取向而言,天台完全可以选择做文官或武官这种仕途捷径,但他拒绝了这种世俗道路,选择了通向佛法之路,那么,其出家的动机和原因何在呢?
以常人视角来看,天台出家是由于梁朝灭亡、陈家家族沦落以及父母双亡事件的刺激,这有一定道理。侯景之乱使得梁朝五十年繁华时代一下子就败落了,使得天台一家丧失了一切地位和财产,也使得天台看到了荣华、权势所支撑的世界的脆弱。进而言之,世界剧变、社会崩溃、富贵易逝,让天台看透了世间的无常,他开始用释迦所掌握的观察、认识问题的视点来凝视社会与人生,并觉悟到要观察和认识“什么是人”、“什么是从根本上支撑人的不变常住之法”这样的问题[4]66-68。梁朝灭亡后不久,天台的父母去世,他在悲哀之余也进一步坚定了出家的决心,他发愿要钻研和体会贯穿于人、社会和自然的宇宙之法,以便拯救和引导沉浸于苦恼的人们与社会。所以天台在出家时就立下了菩萨的“四弘誓愿”①,并以此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因此,乱世确实推进了天台成为伟大思想家的进程。
不过,如果把天台出家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乱世等的刺激,未免将问题简单化了。在池田看来,天台出家少不了上述原因的推动,但究其根底还是源于佛法的巨大魅力和天台自我的精神选择。显然,这种辨析是具有学理性的,也完全契合天台主观意愿下的行为逻辑。天台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和精神追求的人,小时候就有强烈的出家愿望,但囿于厚重的亲情和自己的孝心,起初并未如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钻研佛法、追究人间苦恼之源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终致出家求道,这是必然的。从中国佛教发展史来看,南北朝时期,佛教昌盛,寺庙和僧侣极多,杜牧《江南春》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明证。这意味着佛教已深深渗进当时平民的日常生活、思维方式乃至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之中。再者,佛学作为是时的显学有其先进性,尤其是当人们祈求幸福和安全时,佛教作为某种心灵依靠的作用非常明显。最重要的是,除了深邃、广阔、悠久的佛教,儒教和道教等都不具有使混乱的人心统一或平和的力量,都无法给民众带来心灵的宁静和枷锁的解脱。总之,由于佛教教导人们把信仰的实践当作比理性更为深刻的生命深层的变革和开发强大智慧的途径[8],所以佛法对那些寻求人心变革和智慧者天然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如此,天台笃信佛教也就无足为怪了。
天台在湘州果园寺出家,很快就将住持法绪的知识全部吸收,于是怀着求道的志向去师从著名的学问僧、精通小乘律行和大乘学的慧旷。是时,天台和慧旷都是年青人,二人名为师徒,却情同手足,他们相得益彰的师徒关系,展现了当时中国佛教界在开拓和建设期的朝气。这确如池田所言:“从中国佛教史的长河来看,如果把它比之为人,天台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已经过了佛教传来、学习了解其教义的幼少年时期,逐渐进入了在这一基础上、用自己的手来构筑新的哲理的青年时期。”[4]82天台在慧
二、坚持不懈、苦学佛理的青年求道者
旷门下受了具足戒,时年二十岁,起法号为“智顗”,成为正式僧人,必须终生遵守僧团规范的戒律(管理自治集体程序的纪律)。对于僧人来说,遵守戒律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谈及钻研佛法、为社会行善等问题。实际上,天台本人极其重视戒律法制,他认为严肃戒律法制是修行得道的前提,任何人都不可逾越,为此他后来建立了严格的教团制度[9]。他还提倡“摄律义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即要止恶、发大菩提心、行善事,作一切有利于众生的事情。这意味着天台要不断行善、济渡众生、从事诸多利他的社会实践。如此,他的境界不断得以提升,并向着释迦的境界精进。
天台在受戒后很自然地成为一个彻底的求道者。他怀着伟大的使命感、责任感去精研庞杂的佛经和深奥的佛理,在严于律己、不屈不挠的求法精神推动下,不到五年时间就彻底掌握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并意图建立新的救世之法。可以说,天台之所以能成为佛法的集大成者,完全是源于他青年时期超乎寻常的认真钻研和艰苦修行。就其艰苦修行而言,竟然达到了出家三十多年只穿一套衣服、受人布施从未私用的程度。所以池田慨叹道:“天台严格要求自己、毕生一心求道的形象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可以看出他行住坐卧一刻也不疏忽大意,终生作为佛道的追求者不断前进。”[4]93更令人钦佩的是,天台在研究佛理时,直接就注目于法华经——佛教的真髓,并愿意把佛法理解为现实的人性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源泉。此后,天台在衡州大贤山读诵、精通了法华经,并出现了“胜相”,实现了“心神融净、爽利常日”的境界,这也使他确信只要以法华经为根本,就可以开示佛法的一切。天台在第一次开悟(大贤山的胜相)后发出了“禅悦怏怏,江东无足可问”的豪言。这意味着他一方面坚信自己能够钻研到佛法的顶点,另一方面将继续寻求自己的精神导师。
天台的思想是以《法华经》为根本、以南岳大师慧思(515-577)的思想为源流的。当时,天台为了求法,无畏战乱的危险,北上光州大苏山,成功拜学于一代佛学大家慧思的门下。慧思是一个精进苦行的高僧,为了拯救十方无量众生、斩断十方一切众生的诸烦恼,他高举其坚信的正法,进行了破邪显正的斗争,为沉浸在苦恼、迷失中的人们指点迷津,为真正的佛法的流布而奋斗终生。他以自己在高僧慧文门下体悟的法华三昧境界为基础,建立了把法华经付诸实践的伟大目标,对当时大乘、小乘禅师和论师的观点进行了彻底的研讨和批判,并辩明其教义的正邪。慧思的著述非常精深,其论点都是从自身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社会实践中渗透出来的,内里充满了护持正法和救渡众生而勇敢求道、不惜生命开辟真理道路的先驱者的气概和骄傲,贯穿着拯救恶世末法和一切众生的伟大精神。慧思的禅观——如何证得诸法实相的实践论,后来由天台加以体系化,成为“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的“一心三观”。池田认为,慧思是法华经所说的菩萨行的真正体现者,其“惟有法华经是成佛的捷径”的主张非常伟大,打破了仅重理论的注释学的法华经观,其重实践的教说使法华经恢复了生命力,可以说是一篇划时代的伟大宣言;慧思一生勤奋修禅,但不把佛法当做一种观念,而是企图在自己的生活中当作一种事实来加以体悟和证得,这是非常高明的。反观天台佛法,极其重视佛法与人生的关系、重视教理的实践性和证得性,这无疑源于慧思的智慧。如此看来,正因为有了慧思这样伟大的先驱者,才产生了天台那样伟大的继承人,才使得天台佛法“兼有北方佛教的实践性和江南佛教的学术性,并使之达到更深的层次”[4]108-118。
应该说,天台能够在自己人生中知、情、意最充实的青年时期获得良师的教诲是非常幸运的,这引领他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和轨道上。在慧思的指导下,天台七年如一日地钻研、修行、磨练身心,彻底实践了法华经三昧,达到了“昏晓苦到,如教研心”的程度,终于体得了佛法的真髓,实现了人与经文合一的境界,达到了法华经终极悟达的前阶段,这也是天台开悟的第二个阶段——“大苏妙悟”。但天台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未因此陷入“我已得道”的增上慢,而是依然坚持毕生求道和修炼的精神,如此,才能够在后来建立博大深远的佛法理论的教理体系。天台师事慧思七年,全部体得了慧思的一切,所以慧思在天台三十岁时把“法”托付给他,并嘱咐他要体得佛法、持传法灯、教化众人、令法久住,然后慧思远赴南岳衡山去完成自己另外的使命,而天台带领一干僧众直赴建康,开启了自己传持正统佛法的生命历程。
三、建立最高法华哲学和实践哲理的佛法理论大师
天台带着自身证得之法,怀着弘扬佛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到了南朝的首都建康。天台选择建康作为自己传教的首发地,这种做法与释迦和日莲大圣人的谋略相同,充分体现了其远见卓识。池田解释说,天台致力于真正的佛教哲理和实践,其宗旨必然是变革现实社会,这等于抓住了佛法的根本精神,而选择以首都为中心来开始弘教之旅,是因为首都是一个国家和国民的缩影,解救首都住民的烦恼,是与救渡这个时代的一切众生紧密相连的[4]183。的确,首都历来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影响巨大,如能在这里获得统治者的认可、支持乃至皈依的话,弘法的效果肯定会事半功倍的。
按照布施浩岳先生的中国佛教史五分法②,天台大师处于中国佛教学派时代末期至折衷时代。是时,佛教界内部宗派很多,好在当时寻求佛法者的机根还很纯洁,佛教界有一种寻求更杰出、更高级的法和思想的清新风气。因此,天台始终是在哲理领域里与反对者进行对话和论争的,并在此过程中把混沌的佛教理论加以体系化。其实,对于任何佛教徒而言,要想让佛教这种外来宗教在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社会扎根,均非易事,加之一段时间内寺庙和僧尼数量庞大,导致有的统治者出于多种原因而镇压佛教,“三武一宗废佛”③就是例证。问题还在于,由于佛经晦涩难懂,中国佛教界长期以来一直难以理解其真义,也缺少一种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去理解佛教智慧,所以各门派盛行根据自己的观点对佛法进行解释。这自然加深了天台弘法的难度。幸运的是,当天台在建康弘法时,佛教思想传入中国社会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佛教思想已深深渗入诸多信众的意识中,加上南朝末期动乱频繁,人们希望以出家的方式来保护自身安全,或者希望在佛法世界里寻求人生真谛。所以,天台对其在建康的弘法前景并不悲观。
据史料记载,天台在建康讲说《法华经》很快受到了朝廷、贵族以及进步佛教界的赞赏。这源于天台佛理的正确、高深及其宏大理论体系的强大引领力。“天台智者大师诠释《法华经》的目的,旨在将佛陀整个说教看成一个前后连贯的体系,其判释各种教相即是对一代佛教作体系化的梳理。”[10]在弘法谋略上,天台也非常高明,他先尝试与建康的“名僧”——法济等进行佛学对话,在胜出之后他自然名声大振,于是很多人开始慕名前来请教。接着,天台在蒋山与建康的佛教界进行了充分切磋,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挑战,向人们倾吐他的体得,传布他的思想。天台的发言获得了大忍法师的称赞,认为这不是从书本上照搬来的公式化的知识,而是从深刻的自我生命中迸发出来的生动发言。结果,天台以其深厚的境界和高尚的德行折服了当时的佛教界,以至于老法师法喜和名人徐陵等人都因悟得更高之法而皈依天台。由此池田得出结论:佛法不是某个领域的学问,而是深刻挖掘构成一切基调的“人性”的哲理,人的真正进步归根结底还必须在人自身内在的深化中去寻求;佛教实践者的目的,并不是如何巧妙地组织论理,也不只是满足于钻研真理,而是在于如何救渡包括自己在内的现实中的人们,如何使他们前进一步,乃至如何把时代、社会引向理想的方向[4]207-210。的确,天台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让信众深化自身进而去救渡自己或他人的佛法大师。
天台在建康弘法的收效很显著,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这并不难理解。佛法在中国社会中流布的支柱是佛教徒的守戒和弘法,但真正的佛法哲理往往要通过与政治集团、社会权势的严酷斗争才能取得。我们知道,天台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以“一念三千”为核心的止观学说。“天台宗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止观并重、理论与实践并进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既使它在理论思维方面达到当时哲学思想界的最高水平,也使它在佛教实践方面保持平实稳妥的状态。”[11]因此,天台在瓦官寺讲说法华经时,难免与当时和社会权势相勾结的、注重形而上思考而不重视社会实践的佛教势力产生矛盾,结果双方展开了“公开对决”,即慧荣、法岁、慧暅等人向天台投出巨难”,天台则一一进行反驳。此外,天台还“累旬”受到当时佛教巨擘——兴皇寺法朗及其弟子的刁难,但对方均无功而返;反过来,白马寺的警诏、定林寺的法岁、禅众寺的智令、奉诚寺的法安等佛教领袖纷纷皈依天台。这就从正反两个方面彰显了天台思想的伟大,是故有学者形象地说:“在圆融的大构架内,智顗将世间恶物秽事尽收囊中,不光以柔衣遮之,更辅之以化导之力,彰显与其本具而冥伏不发之善性,终成断屠成佛之功。”[12]
天台在瓦官寺多次讲说法华经,但池田推测说,天台讲说法华经不可能一句一段地进行解释,一定是围绕着妙法莲花经的总论而展开的,是按照法华经的体、宗要及其功德作用和教相的设想,论述了名、体、宗、用、教的“五重玄义”,即妙法莲花经的名目,且这次讲说肯定已具有一个明确的体系,虽然在形式上没有后来《法华玄义》那样完备,但在相当程度上应该完成了其基本骨架[4]225-226。笔者认为,这种推测是成立的。因为天台为了对当时流行的法华经学进行批判,他在摄取过去一切论议和证明各种经典的法理都可以归入法华经的同时,势必要和这些观点针锋相对,如果其理论不成体系,那么其说法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此外,天台在瓦官寺还讲说了《大智度论》《次第禅门》等经论。总之,天台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说,可以让信众体得和觉知自己内在的生命,觉知佛的生命,进而获得佛的智慧。
正当天台大师的名声和地位如日中天时,他却停止了在建康的教化活动,做出了隐居浙江天台山的决定。天台山位于建康东南四百公里处,由于曾是支道林、昙光、高察、僧顺等高僧居留过的灵山而闻名于世,被称为“东南第一名山”。关于天台入山的动机,池田认为是出于其内心的强烈诉求,而非外部原因:其一,天台的名声日益增高,门徒也逐年增多,但真正能体得其所教示之法和境界者反而逐年减少;其二,为了严守师命,令法久住,天台必须要确立正确之法和培育人才;其三,北周的废佛运动给天台带来了震动,也使他洞察了时代演变的奥秘和南朝必然衰落的运命,为此他要重新确立能够经受住这种压力的强大之法;其四,天台在弘教和革新社会时所遭遇的巨大困难,让他痛感必须把自身之法变成一个牢固的哲理体系,变成完美无缺的实践和化导之法;其五,天台佛法在当时广宣流传,但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广大平民中,还有很多令天台不满意之处[4]235-243。也就是说,天台奔赴天台山,乃是为了利用自己的后半生去完成令法久住的重任,更是为了建立后世永放光辉的法华哲学和实践哲理。
天台大师在天台山时期做了很多社会活动来感化民众,如设置放生池让人们自觉体会生命的尊贵,展现佛法“自体关照”的效用及佛法作为一种“富有多样性光辉的世界观”[13]的存在意义。是时,天台尽管看出了陈朝衰败的不可避免性,知道陈朝是不可能令法久住的,但他还是接受了陈后主、永阳王的邀请,下山讲经说法,可见他并不是“为了宗教的人”,而是追求一种“为了人的宗教”,这正是宗教的最高境界[14]。就天台自身而言,他在天台山修行的十年间,最关键的当属完成了其自身开悟的第三个阶段——华顶峰的头陀证悟。这次证悟使他体悟了法华圆顿的中道实相的法理,使其内心所感知到的宇宙生命的佛界得到了确证,也使他构建了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15]。在池田看来,如果说第一阶段开悟打开了天台寻求南岳这位以法华经为根本的实践之师的道路,第二阶段开悟使天台内感佛的生命存在并获得了其理论依据,那么第三次证悟就是完成了天台重新确立自己哲理的基础,进而延伸了释迦佛法的佛理[4]255。就这样,天台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使佛教在中国作为一种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完成,并在近三千年的佛法史上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理论水平。
结语
天台思想曾对佛教界、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日本文化界产生过深刻影响。为此,池田高度评价说:天台站在中国思想的源流和佛教思想的源流的交接点上,使中国佛教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生气的体系;天台是集过去一切佛教哲学之大成的哲人,佛法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在天台的身上已达到顶峰;天台站在佛法的观点上,把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同展开永恒的本质论的印度思想很好地融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进而把过于强调永恒性真理而丧失现实性的印度佛法拉回到个人生活实践之中,成为一种在现实中生活的生命哲理;天台的业绩不止限于佛教界,其哲学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大高峰[4]5-27。显然,池田的观点是非常精辟的,也是发人深思的。就此而言,进一步明确天台在佛教思想史上的位置,探究天台哲学对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以及天台思想和哲学给现代人的启示,是有多重意义的。
注释:
①菩萨的“四弘誓愿”为:众生无边誓愿度——把一切众生都渡达得悟彼岸的誓愿、普渡众生的誓愿;烦恼无边誓愿断——使自己不受一切世俗烦恼的誓愿;法门无尽誓愿知——要学习和懂得无量佛法哲理的誓愿;佛道无上誓愿成——要达到佛法最高彻悟的誓愿。参见池田大作:《我的天台观》,卞立强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2-73页。
②第一期称作格义时代,时间是从佛教传入中国到罗什三藏时代,相当于汉、三国和晋的时代;第二期是学派时代,时间是从鸠摩罗什到北周武帝废佛的时代;第三期是折衷时代,时间是隋代;第四期是宗派时代,时间大体相当于唐代;第五期是祖述时代,时间是从唐末到近世。参见池田大作著,卞立强译:《我的天台观》,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8-189页。
③“三武一宗废佛”的教难,是指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等四位帝王对佛教的大镇压。
[1]洪修平,韦志林.略论天台佛教文化及其影响[J].东南文化1994(2):9.
[2]池田大作.我的天台观:中文版序言[M].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3]张风雷.天台佛学的入世精神[J].中国哲学史,2004(4):13.
[4]池田大作.我的天台观[M].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5]池田大作.续?我的佛教观:中文版序言[M].卞立强,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6]王志远.关于天台哲理的一段联想[J].法音,1998(1):21.
[7]沈海燕.天台智顗对法华妙理的开展[J].上海大学学报,2006(4):96.
[8]池田大作,奥锐里欧·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M].卞立强,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175.
[9]心皓.略述天台智者大师所建立的教团制度[J].法音,2004(1):29.
[10]沈海燕.论天台智顗判教的三条标准[J].法音,2008(8):19.
[11]潘桂明.天台佛学评议[J].世界宗教研究,2003(1):15.
[12]赵平,罗时进,项敏.天台智顗丑学流程解构[J].宗教学研究,2007(2):98.
[13]池田大作,杜维明.对话的文明——池田大作与杜维明对谈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1.
[14]池田大作,戈尔巴乔夫.20世纪的精神教训[M].孙立川,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302.
[15]刘孟骧.天台智顗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J].暨南学报,2001(2):27.